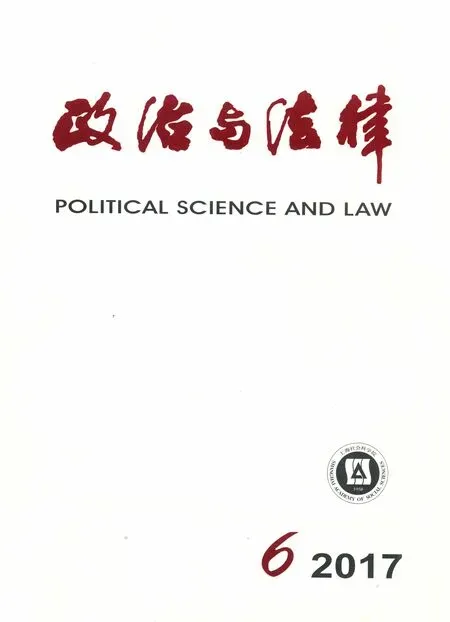“行政决策”概念的证立及行为的刻画*
茅铭晨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行政决策”概念的证立及行为的刻画*
茅铭晨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尽管“行政决策”已被大部分学者作为法学概念使用,而且学者们也从各自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学术表达,但仍未形成共识。在实行以行政行为为对象的行政程序制度和以行政行为为“通道”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我国,是否能够确保“行政决策”概念的成立和“行政决策”作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关系到能否实现对行政决策的法律规制。层层剥离对“行政决策”概念的各种“证伪”理由之外壳,便可看到“行政决策”这一特有行政现象的真实存在,经过抽象后,其可以以法学概念的形式加以表达并进而通过入法成为法律概念。在概念证立的基础上,梳理行政决策的类型,刻画行政决策行为的特征、法律属性及其与相关行政行为界分的边界,行政决策行为在行政行为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清晰可见,由此为构建行政决策法学理论大厦及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铺垫了基石。
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类型;行政决策法治化
“任何一个言谈者都必须应他人的请求就其所主张的内容进行证立,除非他能举出理由证明自己有权拒绝进行证立。”①[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这个被德国当代著名公法与法哲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所称的“普遍理性实践论辩规则”,同样应该适用于“行政决策”概念的证立。
一、“行政决策”概念的独立性与引入行政行为体系的价值
之所以要专门撰文证立“行政决策”可以作为一类独立行政行为的法学和法律概念,是因为“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易懂明了的方式把这些思考转达给他人”。②[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同前注⑥,熊樟林文。在实行以行政行为为对象的行政程序制度和以行政行为为“通道”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我国,是否能够确保“行政决策”概念的成立和“行政决策”作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关系到能否实现对行政决策的法律规制,从而关系到能否实现行政决策的法治化。
尽管迄今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决策”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大多数行政法学者都将行政决策权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行政职权,③如马怀德教授认为:“决策权是国家公权力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权力。”马怀德:《完善权力监督制约关键在于决策法治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3期。同前注⑥,叶必丰文。将“行政决策”作为法学概念使用。其中不少行政法学者还从各自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学术表达,并主张应当把“行政决策”作为一种行政法学新近认识的行政行为类型纳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以加快推进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地方立法及国务院已于2013年将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列为立法研究项目,④据笔者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立法的检索,我国迄今已有20余个省对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了立法,设区的市对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也已经非常普遍。正在推动“行政决策”从法学概念发展成法律概念。
然而,也有一些行政法学研究者对“行政决策”能否作为法学概念或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表示怀疑,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决策”是行政学概念,“非法学概念”。⑤叶必丰:《行政决策的法律表达》,《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行政法学界毫无节制地运用交叉学科的方法,将其他学科的概念盲目塞入到行政法学中,是存有问题的。”⑥熊樟林:《重大行政决策概念证伪及其补正》,《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二,“行政决策”之“决策”可以用“决定”等词汇替换表述,故而其“没有存在空间”。⑦同前注⑤,叶必丰文。第三,我国“主要行政法学教材从来没有讨论和介绍行政决策”,⑧同前注⑤,叶必丰文。说明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不认可“行政决策”能够成为一个法学概念或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第四,“行政决策”只是一种中间性行政行为,因而“绝对不可以像我国现阶段的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一样,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概念”。⑨同前注⑥,熊樟林文。有的学者虽然不认为“行政决策”只是一种中间性行政行为,但却认为其完全可以被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概念所替代,其“在现行或发展中的行政行为类型体系中都无法找到独立的空间”,“没有独立意义可言”。因此,无法将其“作为行政行为的类型嵌入”,试图将其作为法学概念“取代已获广泛认可的行政决定和抽象行政行为这两个概念”,“对学说的沟通功能并无益处”。⑩同前注⑤,叶必丰文。第五,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没有将“行政决策”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类型,而“低位阶的地方政府规章无权予以突破”,因此,试图将“行政决策”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法律概念或法学概念,没有法律依据。①同前注⑤,叶必丰文。第六,在法治发达国家的经典行政法著作、教材和立法文本中,都没有或找不到“行政决策”的表述。具体而言,“无论是在毛雷尔的《行政法学总论》中,还是在盐野宏的《行政法总论》中,我们都找不到行政决策的行为类型或与其类似的行政行为”,“国外立法文本中也找不到类似的表述”,②“王名扬教授的《英国行政法》和《法国行政法》,都没有使用行政决策”。③他们以此说明,“行政决策”也不能在我国成为法学概念和法律概念。
上述理由看似详实周全、有理有据,但笔者认为,“行政决策”发展成法学概念并进而发展成法律概念,既非“对学说的沟通功能并无益处”,也非“没有独立意义可言”而要被“证伪”,④参见前注⑥,熊樟林文。它对推进我国行政决策的法学研究和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具有基础性意义。
第一,在社会现象如此复杂、学科交叉如此密切的今天,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导致跨学科概念的存在甚至大量存在,是一种常见现象。例如,“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授权”等概念,甚至类型化的行政行为概念如“行政立法”、“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均是被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等学科同时广泛使用的概念,无非它们所表达和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现今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行政行为”最初就是由美国著名行政学家H.A.西蒙(Herbert A.Simon)首创并作权威解释,而后流行于二战后的行政学界的。⑤参见林纪东:《行政行为》,载王云五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行政学》,商务印书馆(台北)1973年版,第45页。因此,简单地以“行政决策”概念缘起于行政学,就否定其可以作为法学概念和法律概念,是缺乏说服力的。
第二,词汇的可替换性,并非否定概念独立性的充要条件。事实上,“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这两类行为,甚至在这两类基本行政行为类型之下再进一步细分而来的次一层次的行政行为,也都可以用“决定”表达,但出于对它们分类研究和分类规制的需要,行政法学还是将它们从“决定”中分离了出来。“法律概念可以被视为是用来以一种简略表述方式识别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操作工具”,⑥同前注②,E.博登海默书,第462页。其“重要的不是在手册和专著之导论部分可以找到的定义,而是法学实际运用的法的概念”。⑦[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一个法学概念能否成立,不取决于其是否可以用其他词汇所替换,而是取决于其能否独立地、实质性地表达某种或某类独特的法律现象,取决于其在法的实践中是否具有独特的价值。
第三,迄今为止我国行政法学教科书较少涉及行政决策,只是说明受过去认识水平的制约,行政法学家对行政决策的研究关注不够,尚未形成系统、成熟或较为通行的理论。一部学术史,就是对前人尚未发现、认知的事物和规律不断发现和揭示的历史。“行政决策”过去在行政法学教材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并不能说明它在今后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学者认识到,我国行政法学教材没有讲到对行政决策的法律调整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⑧参见关保英:《行政决策的法律调整》,《决策探索》1993年第6期。事实上,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对行政决策的法学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其提出了有价值的法学认识和见解,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正在推动行政决策法学概念的形成。
第四,尽管,从宏观看,行政决策整体上确实只是行政过程的一个环节,但从微观看,行政决策无疑是特定决策机关正式而完整的意思形成和表示,是一个“最终的”行政行为。因此,将行政决策定位为行政行为而非“中间性”行为是恰当的。行政决策虽有“涉及特定对象”(范围封闭或明确的特定对象、特定事项)和“涉及不特定对象”两种,⑨法学界已逐渐认识到,行政决策可以分为“涉及特定对象”的决策(即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决策)和“涉及不特定对象”的决策(即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决策)。例如,有学者把行政决策分为“形成政府的方针、政策、规定、规划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针对特定对象、特定事件、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两种类型。参见杨海坤、李兵:《建立健全科学民主行政决策的法律机制》,《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但不能以行政决策具有这种跨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跨类性”为由,否定其在我国现今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两分法”的行政行为体系下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类型。只要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使得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不再限于“行政机关对特定对象的具体事项进行处理作出的决定”这样一种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而是能够包括行政机关就行政事务或公共事务作出的涉及特定对象的行政决策(以下简称“具体行政决策”),并且使得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不再限于“行政机关就不特定对象制定法源性规则或非法源性规则”这样一种传统的抽象行政行为范畴,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就行政事务或公共事务作出的涉及不特定对象的行政决策(以下简称“抽象行政决策”),就可以将“具体行政决策”和“抽象行政决策”分别纳入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使得“行政决策”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下的次一层次的行政行为类型,与“行政立法”、“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并列,成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类型,在现今“两分法”的行政行为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说明,认为行政决策在“两分法”的行政行为体系中找不到位置,是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认识停留在传统阶段所致。只要通过理论上的创新,“两分法”就不再会成为行政决策作为一种独立行政行为类型的障碍。而“行政决策”的“跨类性”,只是说明其与传统的行政行为类型相比有显著的特殊性,却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其在概念和行为类型上的独立性。
第五,法律现象确实是法学研究的基础,但法学研究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很强的能动性。现成的法律并不能阻碍法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相反,正是由于法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才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发展。正如学人所言:“并不是法律秩序创造了有助于实现其目的的概念,而恰是概念创造了法律秩序并产生了法律规则。”⑩转引自前注②,E.博登海默书,第469页。事实上,在我国,“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协议”等,都是从学理概念发展成为法律概念的。国外也经常如此。因此,某一概念尚未成为法律概念,并不是判断这一概念当前不能成为学理概念和今后也不能成为法律概念的理由。
第六,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对行政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事项进行决策,这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一种重要的行政权运作方式。之所以在英、美、法、德、日等诸国的经典行政法著作、教材和立法文本中“找不到”“行政决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我国法学界对国外行政决策制度和学说的了解和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实际上,在这些国家,作为法学概念甚至法律概念的“行政决策”是存在的。比如,美国虽然作为普通法系国家并无精细的行政行为理论,但美国法律学者还是经常使用“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来表达“行政决策”并对其进行研究的。①例如,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与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联合主办的“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决策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美国法律学者无论是在向大会提交的纸质论文中,还是在口头交流时,多使用“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来表达“行政决策”。该概念作为与规章制定、裁决、许可、制裁、救济等行政行为并列的一种“其他相似行为”,属于囊括全部行政机关行为的机关行为(Agency Action)的一种类型。②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Fed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规定:“机关行为包括机关的规章制定、裁决、许可、制裁、救济及其他相似行为,或者上述形式的否定行为和不作为的全部或一部”。参见《美国法典》第五编第551条第13项。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在法国,传统上,行政行为(Acte Administratif)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普遍性规则(Règle Générale;其具体形式一般被称为Règlement,即条例)、行政处理(Traitement Administratif;属于Acte Administratif Unilatéral,即单方行政行为)、行政合同(Contrat Administratif)。③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59页。后来,法国行政法学也经常对Décision Administrative (行政决策)这一被逐步受到重视的特殊行政行为类型进行研究。④See Panchaud,André,La Décision Administrative Etude Comparative,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Année 1962,Volume 14,Numéro 4,pp.677-697.该文题目可译为“行政决策比较研究”。德国则用Verwaltungsentscheidung (行政决策)一词表达与Verwaltungsakt(行政处分)有别的一类行政机关行为,甚至还有专门关于行政决策的立法。⑤See Gesetz über die Zustndigkeit und das Verfahren der Gerichte zur Nachprüfung von Verwaltungsentscheidungen..http://www.verfassungen.de/de/ddr/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90.htm.2016年7月26日访问。该法律的名称可译为:《行政决策复查的司法程序和管辖权法》。其实,在文献检索系统或搜索引擎中输入“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Décision Administrative”、“Verwaltungsentscheidung”,就可以发现相关国家有不少研究行政决策的法学文献甚至法律文件。
二是“行政决策”往往被隐藏于“行政规划”、“行政计划”的背后。这是导致我国法学研究者往往只见“行政规划”和“行政计划”,不见“行政决策”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对行政决策具体表现形式的法学研究和法律规制,重点是行政规划和行政计划。例如,日本对行政计划的法学研究非常丰富,其研究的重点是从学理上说明行政计划与行政处分、行政立法和自治立法不同的特点以及行政计划的可诉性问题。随着法治对行政监督的加强,对某些行政计划提起撤销诉讼的可能性开始得到日本最高法院判例的认可。⑥参见日本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平成4年11月26日,第46卷,第8号,第2658页。不过,这只是从司法的角度承认这些行政计划因具有一定的处分性而可以成为撤销之诉的对象。在学术上和实体法上,行政计划整体上仍区别于行政处分,与行政契约、行政指导并列属于“其他行政作用”的一种独立行为形式。⑦参见[日]南博方:《行政法》(第六版),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9页、第75-78页。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行政程序系指“行政机关作成行政处分、缔结行政契约、订定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确定行政计画、实施行政指导及处理陈情等行为之程序”。⑧参见黄荣坚等编纂:《月旦简明六法》,元照出版社(台北)2010年版,第贰-1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台湾地区明确将行政计画(划)定位为与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行政指导、处理陈情并列的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一些行政计划的行政诉讼可诉性还逐渐得到了正式的认可;⑨参见台湾“司法院”秘书处:《大法官会议解释汇编》(再版),三民书局(台北)1999年版,第86-87页。在学术研究中,“行政决策”在台湾也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法学概念。有台湾学者甚至指出:“行政行为研究最受到重视与为人应用的概念是‘决策’。”⑩前注⑤,林纪东文,第46页。
三是与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法制度有关。这些国家或地区一般都有适用面宽泛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决策”作为一种行政权行使的方式,除了出于特定需要对其某些程序专门制定特别程序法之外,其他一般程序自然适用行政程序法典的规范,即无需在行政程序法典中专门对其作程序规范。①See Jamei P.Horsley,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the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Sino-U.S.Workshop on Opennes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xecu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p.103(June,2012).Carol Ann Siciliano,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Sino-U.S.Workshop on Opennes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xecu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p.187(June,2012).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有受案范围宽泛的司法审查或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决策”无需被法律列举就有受到司法审查或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因而,在有关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或行政诉讼的一般法律文件中,自然就难觅“行政决策”之踪影。同时,这也是行政法教材、著作较少研究行政决策的又一个原因。
退一步说,尽管我国学术研究应该重视借鉴国外理论,但国外理论也只能作为“借鉴”,而不能作为“依据”。因此,即使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也不能以此作为我国不能形成适合自己国情的理论的依据。
笔者认为,与上述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没有行政程序法典,并实行对行政行为分类专门立法予以规制、以“行政行为”为行政诉讼“通道”且以“肯定式列举”的方式规定较为狭窄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制度,同时,鉴于我国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的迫切要求,在我国明确确立行政决策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类型,形成既可以进行国际学术对话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话语体系,从而为研究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法律制度和一定范围行政决策的行政诉讼审查制度提供基础理论支持,这对于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行政决策”的法学表达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行政决策的研究是不够重视的。据笔者查考,我国较早在法学专业杂志上研究行政决策并提出行政决策法治化(当时称“法制化”)主张的论文是张农基于1988年4月在《法学评论》“学生论坛”栏目中发表的《浅谈国家行政机关决策程序的法制化》一文。在学术著作中,较早主张把行政决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是1992年杨海坤教授所著的《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②参见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在行政法学教材中,较早把行政决策纳入行政行为范畴的是江国华教授2012年主编的《中国行政法(总论)》。③参见江国华主编:《中国行政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181页。在2005年之前,我国法学界对行政决策的法学研究总体上是零星而“浅尝辄止”的。我国行政法学界在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实行依法决策”之后,才开始对行政决策的研究予以重视。党的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提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的目标之后,我国法学界掀起了行政决策研究热。杨海坤和李兵、王锡锌、于立深、胡建淼、罗豪才、杨寅、应松年、姬亚平、关保英、黄学贤、王万华、戚建刚、马怀德、韩春晖、叶必丰、姜明安等法学研究者相继发表或出版了相关专著和论文。这些研究涉及对行政决策概念及行为的学理认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公民参与、合法性审查、社会影响评价和风险评估、责任追究等机制,以及程序制度的法治化和司法监督等问题。
对行政决策概念的具体表述,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者有的从“行为”的角度作出定义。如皮纯协教授把行政决策定义为“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就行政管理的一定事项,确定目标,制定各种方案,选择方案,以及在执行过程中调整方案的行政行为”。④皮纯协:《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270页。戴建华博士将行政决策定义为“具有法定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有合法权限的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行政目标,依据既定的政策和法律,对面临要解决的问题,拟定并选择活动方案,作出决策的行为”。⑤戴建华:《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有的从“活动”的角度进行表述。如梁津明教授将行政决策表述为“行政决策主体为了履行政府职能,在其权限范围内,就某一公共事务如何处理做出决定的活动”。⑥梁津明:《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决策程序问题的探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王万华教授将行政决策表述为“形成公共政策的行政活动”。⑦王万华:《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构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有的从“决定”的角度提出认识。如杨寅教授认为,行政决策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能,在其管辖权限范围内作出处理公共行政事务的决定”。⑧杨寅主编:《公共行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20页。杨海坤教授等认为:“行政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宪法、法律,发挥行政管理职能作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⑨杨海坤、李兵:《建立健全科学民主行政决策的法律机制》,《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有的则从“过程”的角度表达见解。如刘莘教授主张,“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组织为了实现行政目标,依据既定政策和法律,对面临要解决的问题,拟定并选择活动方案的行为过程”。⑩刘莘主编:《法治政府与行政决策、行政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上述观点分别可以被概括为“行为说”、“活动说”、“决定说”和“过程说”。笔者认为,任何行政机关的行为都是可以从“行为”、“活动”、“决定”和“过程”等角度进行表述的。上述不同的表述只是反映了学者对“行政决策”概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行政决策”本质上属于一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存在分歧。正如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政行为类型,既可以从“行为”的角度作出表达,也可以从“活动”、“决定”和“过程”的角度作出表达,但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不能否定它们属于行政“行为”一样。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行政法的制度是建立在对行政行为规范和监督的基础上的,因而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通常是从“行为”的角度表述的,两者以“行为”对接。因此,从“行为”的角度表达“行政决策”概念,更符合行政决策法学研究的本质要求。
综合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决策概念的不同表达意见,兼采各种表达意见之长,笔者将“行政决策”定义为: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对国家或地方行政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识别、对未来目标进行定位、对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方案经过分析作出选择、对实施方案的行动进行设计而作出的政策性决定或法律性决定的行政行为。
根据这一定义,行政决策可以分为仅具有政策效力的政策性行政决策与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性行政决策。前者属于政策行为,后者属于法律行为。长期以来,行政决策一般被认为是“制定政策”,而对法律性行政决策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能够产生影响的法律属性,法学界却长期缺乏认识。
作为法律行为的法律性行政决策由于能够对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按照传统行政行为理论,当然属于行政行为。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还应当把作为政策行为的政策性行政决策也纳入行政行为范畴。这是因为,虽然政策性行政决策本身只是政策性的,但与行政机关制定的不属于法律渊源却又被纳入行政行为之结果的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类似,它也可以成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从而通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间接对相对方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这就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即能够对社会主体权利义务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不仅有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而且还有行政决策。政策性行政决策能够间接影响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属性,与传统抽象行政行为能够间接影响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属性类似;政策性行政决策的形成方式,与行政机关制定“非法源性”属性的规范性文件过程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似于传统行政行为理论将不属于法律行为的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纳入行政行为范畴的处理方法,将政策性行政决策也纳入行政行为范畴。所不同的是,前者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后者则视其是否针对特定对象,有的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有的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政策性行政决策的存在,并不影响行政决策在整体上可以成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将行政决策(无论是法律性的还是政策性的)定位为行政行为,是以一般行政程序制度或专门行政程序制度规范行政决策,建立对行政决策的行政诉讼审查(直接起诉或附带审查)制度,从而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学理支撑。
三、行政决策的存在形式和分类考察
行政决策在现实中的客观存在,是证立行政决策概念的事实根据,也是对行政决策行为进行学理分析的实证样本。
根据对已经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性文件的考察,笔者发现,各地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划定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趋同性还是比较显著的。经过对这些地方立法关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规定的梳理、归类,并考虑到在国家层面还有国防、外交等专属于国家的行政决策,笔者将重大行政决策归纳为如下十二项:(1)国防、外交等国家决策;(2)贯彻落实和报告请示类决策(在与上级机关和同级党委、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中); (3)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改革政策、措施类决策;(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类决策;(5)城乡建设规划和计划类决策;(6)财政预算类、财政支出类决策;(7)投资项目、国有资产处置类决策; (8)民生和社会事业类决策;(9)资源、生态环境类决策;(10)安全、稳定类决策;(11)政府定价类决策;(12)其他需要政府依职权决策的事项。
尽管上述类型是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地方立法梳理、归类而成的,但笔者认为,这些类型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国全部行政决策的类型。
首先,笔者相信,各地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立法时,对其具体事项的确定是慎重而周全的。各地确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显著趋同性,也说明了除国防、外交等须由国家决策外,上述决策类型客观上普遍涉及了各地共同存在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而除国防、外交等专属于国家行政决策的权限外,基于行政层级关系,国家层面的行政决策与地方层面的行政决策在范围上基本上是对接的,因此,上述类型可以涵盖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重大行政决策。
其次,重大行政决策是相对于一般行政决策而言的,即重大行政决策属于行政决策中事项重要、影响重大的决策,因而,在同一行政层级意义上,与一般行政决策事项相对应,肯定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尽管对于上一行政层级来讲,它不一定重大);而有些决策,如国防、外交等国家决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决策等,肯定是重大行政决策,不存在一般行政决策。另外,下级行政机关的决策权限不会超过上级行政机关的决策权限,因而,重大行政决策在范围上肯定包括但不限于一般行政决策的范围。换言之,上述十二类行政决策类型,不会遗漏一般行政决策。
最后,上述行政决策类型可以涵盖各行政机关在各个具体领域的行政决策,例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收入分配调节、住房保障等重大民生领域的决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体育、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决策,可以纳入民生和社会事业类决策;公安和生产安全管理方面的决策,可以纳入安全、稳定类决策;食品安全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方面的决策,从不同角度可以分别纳入民生类决策和安全、稳定类决策;城市改造、交通领域的规划性决策可以纳入社会发展或城乡建设规划计划类决策,项目性决策则可以纳入投资项目类决策;生态环境保护、土地利用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的决策,可以纳入资源、生态环境类决策,等等。从保守的角度说,即使有前十一项类型之外的个别情形,也可以由第十二项“其他需要政府依职权决策的事项”兜底。
因此,将全部行政决策归纳为上述十二项,是经得起考证的。
尽管地方规范性文件关于行政决策事项的规定只是经验性的,其仅仅展现了行政决策在实践中存在的形式,没有也不可能为人们直接提供对行政决策行为的学理分类,更不可能为人们直接提供对行政决策行为特征的法学刻画、对行政决策行为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学术界分,以及对行政决策行为法律属性的理性认知,但是,它展现的行政决策在实践中的存在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从内容和领域的角度梳理、归纳出的上述行政决策类型,无疑为对行政决策行为的法学研究和经过法学研究建立起有关行政决策的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基础和可靠的分析样本。
由此出发,可以在学理上将行政决策梳理成如下几种主要类型。
第一,从决策层面角度考察,行政决策可分为国家行政决策和地方行政决策。
国家行政决策是中央行政机关作出的决策,包括具有高度主权性、政治性、全局性、整体性特征的决策和不具有上述特征的决策。具有高度主权性、政治性、全局性、整体性特征的决策应属于传统行政法学所谓的具有“不可诉性”的“国家行为”,可简称为“国家决策”,含国家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的国家决策(如国防、外交等决策)和对内作出的国家决策(如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改革政策、措施类行政决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类行政决策,财政预算类行政决策,以及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安全、稳定类行政决策等四类决策)。不具有高度主权性、政治性、全局性、整体性特征的决策系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除“国家决策”之外的其他行政决策,可简称为“国家机关决策”,原则上应具有可诉性。①“国家机关决策”的可诉性根据“具体”还是“抽象”、“法律性”还是“政策性”等不同性质,可被直接起诉或被附带审查。详后。
地方行政决策是地方行政机关作出的决策,包括在本地区具有高度政治性、全局性、整体性特征的决策和不具有上述特征的决策。在本地区具有高度政治性、全局性、整体性特征的决策可以被视为是国家决策在地方的分解,是国家整体意志在地方的具体展现,其政治性、全局性、整体性虽然不是全国性的,但它是区域性的重要决策,与普通的“机关行为”有明显区别,可以与“国家决策”相对应,称其为“地方决策”(如地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改革政策、措施类行政决策,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类行政决策、地方财政预算类行政决策等三类行政决策),应当赋予其不可诉的法律特征。不在本地区具有高度政治性、全局性、整体性特征的决策系地方行政机关作出的除“地方决策”之外的其他行政决策,可简称为“地方机关决策”,原则上应具有可诉性。②“地方机关决策”的可诉性,根据“具体”还是“抽象”、“法律性”还是“政策性”等不同性质,可被直接起诉或被附带审查。详后。
界分国家行政决策和地方行政决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界分“国家决策”和“国家机关决策”、“地方决策”和“地方机关决策”,不仅对于分清行政决策的权力范围和适用的地域范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划定可诉行政决策与不可诉行政决策的界限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从决策事项和影响是否重要、重大角度考察,行政决策可分为重大行政决策和一般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决策和地方行政决策中事项重要、影响重大的决策。一般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决策和地方行政决策中事项重要程度和影响重大程度相对一般的决策。
“国家决策”和“地方决策”分别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上属于重大行政决策,然而重大行政决策又不限于“国家决策”和“地方决策”。“国家机关决策”和“地方机关决策”中,事项重要、影响重大的决策,也应属于重大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决策(无论是其中的具体行政决策还是抽象行政决策,是其中的法律性行政决策还是政策性行政决策)都可以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除具有紧急性、国家秘密性的之外,各种重大行政决策均应当被纳入专门的决策程序规制范围。
界分重大行政决策和一般行政决策,对于研究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专门立法以及如何通过一般程序规则对一般行政决策进行程序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从决策的效力是政策性的还是法律性的角度考察,行政决策可分为政策性行政决策和法律性行政决策。
如前所述,政策性行政决策不能直接涉及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法律性行政决策能够对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如果某一行政决策假借“政策”之名而实质性地影响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则应当揭去其“政策面纱”,视其为法律性行政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行政决策作出后,其有可能被制定成法律,从而转化为法律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其应该适用关于立法行为的概念和规则,而不再适用有关行政决策的概念和规则;③例如,“计划生育”一开始是以行政决策的形式提出的,后来“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表述已分别被写入了我国《宪法》和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也于2015年写入了修改后的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因而,“计划生育”业已成为法律规范,“二孩政策”也已成为“授权性法律规范”,即它们均不属于行政决策,更不属于“政策”。然而,因为过去人们对行政决策经立法后将在性质上转化为法律规范缺乏认识,所以,社会上乃至官方往往将它们表述为“政策”。还有的重大行政决策已经受到专门法律的规范,则其就不再适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的规范。对此,当下我国各地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地方立法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大都将行政机关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以及已有法律予以规范的决策行为,排除在行政决策
范畴之外。④例如,由于已有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予以规范,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地方立法大多将行政机关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决策排除在重大行政决策的范畴之外。
界分政策性行政决策与法律性行政决策、行政决策与法律规范,适用重大行政决策专门程序规范的重大行政决策和不适用重大行政决策专门程序规范的重大行政决策,对于准确认识不同行政决策的性质、效力和救济途径,行政决策与法律规范的区别,以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专门立法的适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从决策涉及的对象是否特定的角度考察,行政决策可分为具体行政决策和抽象行政决策。
对于这一分类,笔者之前已经论及。笔者在这里需要着重讨论的是这两类行政决策的可诉性和司法审查的具体模式。
“抽象行政行为需要通过对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一‘介质’才能对特定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所以其对特定相对方产生的效力具有间接性;具体行政行为无需借助于‘介质’就能对特定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所以其对特定相对方产生的效力具有直接性。”⑤茅铭晨:《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在传统的抽象行政行为中,“行政规定”常常被学者用来指代行政机关作出的除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规定是个行政规则,而不是法律规范。所以它可以成为行政行为的依据(即行政依据),而原则上不能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即司法依据)。”⑥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正因为行政规定可以成为行政行为的依据,从而间接影响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所以具备了受到司法监督的应然性;也正因为行政规定不是司法裁判的依据,司法不受其约束,所以具备了受司法监督的可能性。这正是在现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下行政规定(除国务院的行政规定外)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被附带审查的学理基础。⑦2014年修正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笔者以为,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已然实现了可附带审查的制度背景下,随着法治的推进,抽象行政决策的抽象性也无法成为其不受司法监督的理由。尽管法律性抽象行政决策不是法律规则,其不是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但可以成为行政行为的行政依据;尽管政策性抽象行政决策本来其影响只是政策性的,但其与行政规定类似,也可以成为行政行为的依据。⑧例如,城市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是土地行政部门和规划行政部门作出土地行政许可和规划行政许可的依据。因此,抽象行政决策对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都可以产生间接影响,且不是司法裁判的依据,司法机关对其应具有审查权。除“国家决策”和“地方决策”外,对抽象行政决策(无论是法律性的还是政策性的),原则上可以参照对行政规定附带审查的行政诉讼制度,实行附带审查。也就是说,原告在对行政行为起诉时,可以一并请求法院对作为该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决策进行审查。
“行政决定”一词常常被法律学者用来作为传统概念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别名。⑨参见前注⑥,胡建淼书,第188-194页。法律性具体行政决策对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影响的直接性,因此,对于除“国家决策”和“地方决策”外的法律性具体行政决策,应借鉴日本承认某些“行政计划”具有可诉性的经验,参照我国对行政决定不服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赋予认为权利义务受其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直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即实现法律性具体行政决策的直接可诉性。政策性具体行政决策仅具有政策上的处分性,不具有法律上的处分性,因此,在当下我国行政诉讼的制度框架下,其不具有被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属性。不过,政策性具体行政决策也可以成为其他行政行为的依据,从而通过其他行政行为影响社会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因而也应当赋予其可以被附带审查的法律属性。
界分具体行政决策和抽象行政决策,对于认识行政决策行为的“跨类性”及研究对行政决策司法监督的不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四、行政决策的特征及其与相关行政行为的界分
“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⑩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3页。行政决策的特征,是行政决策显著区别于其他机关或组织的决策(尤其是其他行政行为)而能够成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的标志。因此,刻画行政决策的特征,应该着力于揭示其与相近或相关行政行为概念相区别的征象,这对证立“行政决策”概念具有关键作用。笔者认为,行政决策有如下特征。
1.主体和职权的行政性
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作出的有关国家行政事务或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有别于其他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作出的决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决策,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和废除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决策,关于特赦的决策、关于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的决策,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决策等,不具有主体和职权的行政性,因而不属于行政决策。
2.内容的跨法律性和政策性
如前所述,政策性行政决策的存在,并不影响行政决策在整体上可以成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行政决策内容的跨法律性和政策性,是行政决策与其他行政行为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
3.外部性
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对国家或地方外部性行政事务和公共事务作出的决策,有别于行政机关对其组织内部有关事项作出的决策。不可否认,行政机关也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其内部事项进行“决策”,但这种“决策”适用行政机关内部组织法及内部程序法的规定,不属于我国当下要求实现决策程序法治化和可司法审查性的外部行政决策范畴。正是基于对行政决策外部性的认识,当下我国各地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地方立法,都将行政机关对其内部人事任免、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决策排除在行政决策范畴之外。
4.直接公共性
在“直接”意义上,行政决策是对具有直接公共性的国家、地方行政事务或社会事务作出“决定”。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舒伯特在其《行政决策中的“公共利益”》一文中所指出的,在行政理性主义者眼里,公共利益存在于行政决策程序的理性建构中,自觉地执行公共意志。①Glendon A.Schubert Jr.,“The Public Interest”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7,51(2),pp.347-348.作为传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决定虽然在终极意义上也具有公共性,但其直接处理的对象一般却是非公共性的特定对象和特定事项。例如,行政机关对一片区域作出城市建设规划,其直接出发点是城市公共建设需要,而不是针对这片区域内的有限居民,因而具有直接公共性。行政机关批准特定的开发商在这片区域内进行开发建设,虽然终极意义上也是为了实现城市建设这一公共目的,但其直接意思表示却只是允许行政许可的相对方即该开发商进行开发建设,不具有直接公共性。②司法实践中,个别法院曾经以城市建设涉及公共利益而我国尚未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由,不受理被拆迁户不服政府规划行政许可的起诉和不服开发商低价补偿的起诉,这正是有意或无意混淆直接公共性与间接公共性的表现。可见,直接公共性是行政决策区别于行政决定的重要标志之一。
5.未来导向性
行政决策是面向未来、兼顾各个方面、权衡各种关系、综合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因素作出的前瞻性决定,与作为传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决定相比,具有显著的“战略性”,其目的是为行政机关的工作确定方向性目标、形成政策和策略、提供基准和要求。作为传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决定是仅考虑与决定事项直接相关的因素、不考虑其它不直接相关的因素、对当下的行政事务作出的“就事论事”式的决定,③行政决定如果考虑其它不直接相关的因素,会被认为是违反合理性原则的非“正当考虑”。参见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第32页以下。具有显著的“战术性”。尽管行政决定也会考虑作出行政决定所想要达成的目标,但这种目标主要是战术性的和效果性的。行政决策的未来导向性与行政决定的即时处理性,是区别两者的又一个标志。
6.规(谋)划性
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对国家或地方行政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识别、对未来的目标进行定位、对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方案经过分析作出选择、对实施方案的行动进行设计而作出的具有规划性、谋划性、对策性的行为,其具有问题和目标的确定性、方案和措施的预设性、计划和方法的针对性。这与普通行政行为也有显著区别。
五、行政决策的法律属性
“属性”是事物“本质方面的特性”。④前注⑩,辞海编辑委员会书,第2815页。分析行政决策的法律属性,就是要刻画行政决策在法律上的性质。从法律属性的角度认清行政决策与其他行政行为以及其他行政活动方式在法律性质上的区别,有助于从学理上进一步确立行政决策作为一类独立行政行为类型的地位。笔者认为,行政决策有如下法律属性。
1.权力渊源的宪法性
不同于行政决定权一般需要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具体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即权力渊源的具体法律性),行政决策权(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内容、权力范围和边界)主要是由宪法和作为宪法性法律的组织法直接规定的。具体来说,行政决策权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职权、第90条关于国务院各部和各委员会职权、第107条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规定,组织法依据是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第61条、第63条等关于地方政府职权的规定。而税收征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除了在源头上需要有宪法和组织法的依据外,通常还需要有我国《税收征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等行政管理方面的具体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来详细规范具体的管理或执法活动。权力渊源的宪法性和权力渊源的具体法律性,是行政决策与行政决定在法律属性上的一个显著区别。
2.决策程序的复杂性和法律刚性
由于行政决策对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和重要性,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对其程序法治化要求会越来越高。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国家将专门进行程序立法,将公众参与、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专家论证、集体讨论决定等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特别重大的行政决策还需要经过同级人大审议批准。因此,总体上,行政决策程序比行政决定的程序要求更高,也更为复杂、刚性。这是行政决策的一个显著法律特征。
3.决策效力的约束性
行政决策作出之后,具有执行上的严肃性和约束性,不仅决策机关自己必须受其约束、不得随意变更,而且其下级机关及决策的相关对象也必须受到约束、严肃执行。这种约束力来自于行政机关之间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来自于政策的统一性要求(对于政策性行政决策而言)和法制的统一性的要求(对于法律性行政决策而言)。这是行政决策相对于相对方是否接受“听凭其自主抉择”的行政指导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法律属性。⑤同前注③,罗豪才、湛中东主编书,第297页。
4.决策效力的后及性
行政决策是对未来目标进行定位,对今后将要处理的事项和将要采取的行动作出安排,具有后及性。行政决定是对已经发生的事项、已经出现的情况或已经具备的条件进行处理、审查,具有前溯性。⑥一些行政法学教科书将行政许可描述成具有后及性的行政行为,这是站在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的,即行政许可可以使相对方获得“从今往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权利。然而,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而言,行政许可是根据申请人已经具备的条件,依法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许可与其他行政决定一样,也是对已经发生的事项、已经出现的情况或已经具备的条件进行处理、审查,故是前溯性的行政行为。行政决策的后及性与行政决定的前溯性,也是两者区别的标志之一。
5.非规范性
行政决策虽然具有约束力,其中的抽象行政决策甚至还具有普遍约束力并具有效力持续、能反复适用的属性,但这种约束力不是行为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而是目标意义上的约束力,明显不同于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后果”三要素组成的行为规范。⑦有时,行政机关会就落实行政决策专门出台文件,对相关主体提出要求。这种文件虽然与行政决策有关,但不是行政决策本身,而是对执行行政决策提出行为规范性要求,故属于行政规则,而不属于行政决策。这是行政决策区别于行政规则(即传统抽象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法律特征。
6.原则上的行政诉讼可诉性
如前所述,在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行政决策的行政诉讼可诉性或可司法审查性已得到较高程度的实现。随着我国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政策性行政决策,还是法律性行政决策,无论是具体行政决策,还是抽象行政决策,除“国家决策”、“地方决策”以及按照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应当排除的国务院作出的决策外,行政决策原则上也应当具有可诉性。需要具体区分的,只是哪些行政决策应具有直接可诉性、哪些行政决策应具有可附带审查性而已。具体来说,法律性具体行政决策应具有直接可诉性,政策性具体行政决策和抽象行政决策(无论是法律性的还是政策性的)应具有可附带审查性。尽管我国行政决策的行政诉讼可诉性目前还没有实现,甚至法学界对此研究才刚刚起步,但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行政决策不应当享有不可审查的特权,司法缺位往往导致行政决策法治化无法实现。因此,行政决策原则上的行政诉讼可诉性,是行政决策又一个重要的法律属性。
7.决策责任的可问责性
行政决策问责制度是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决策法治化的重要目标。在我国,决策失误却往往被敷衍为“问题太复杂”、“不可控因素”、“好心办坏事”等,很少有人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这种状况,不是由于行政决策不可问责,而是严格的问责制度还没有建立所致。鉴于行政决策失误将导致社会的严重损失,随着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推进,迫切要求建立行政决策问责制度。在法治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行政决策问责制度已经被有机地镶嵌于行政程序、议会监督、司法监督、竞选政治、罢免弹劾等制度之中,作出错误决策的主体会被追究相应的政治、行政和法律责任。这说明,决策责任的可问责性应当是行政决策的一个重要法律属性。令人欣慰的是,建立健全包括决策问责在内的问责制度,在我国已经开始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决策责任的可问责性正在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均对建立健全问责制度提出了要求。
六、结语
“概念不应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品,而应该是构筑科学思想大厦的工具。”⑨同前注⑦,埃利希书,第9页。通过对“行政决策”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学概念进而可以成为法律概念的证立,将行政决策作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引入行政行为体系,在此基础上,梳理行政决策的类型,刻画行政决策行为的特征、法律属性及其与相关行政行为界分的边界,可以为构建行政决策法学理论大厦铺垫基石。法学界对行政决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终将构建起科学的行政决策法学理论大厦,而构建起这样一个理论大厦,将有助于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理想。
(责任编辑:姚魏)
DF31
A
1005-9512-(2017)06-0108-14
茅铭晨,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东华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行政决策司法审查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7NDJC174YB)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BFX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