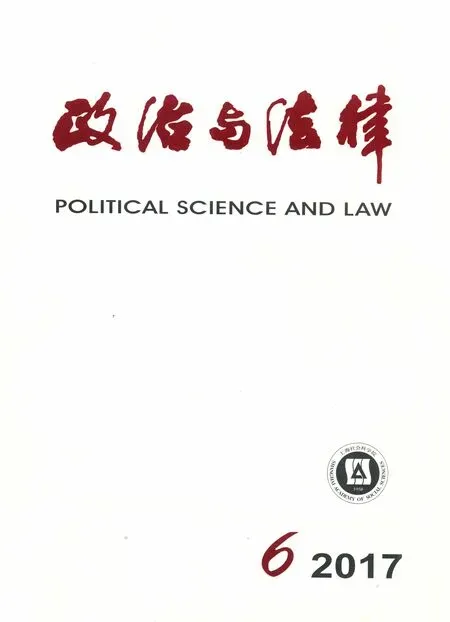作为组织的法院及其决策运作:司法职业保障的系统论考察
刘涛 蔡道通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作为组织的法院及其决策运作:司法职业保障的系统论考察
刘涛 蔡道通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司法职业改革涉及法院组织结构调整问题。作为社会功能分化的产物,组织是一种产生决策并形成决策的自我指涉且吸收沟通中不确定性的系统。决策前提与决策的递归式演进构成了系统的双重封闭及其悖论。“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在法院组织中的构建解除了系统的悖论,从而成为法律系统的中心。对法官职业进行保障,必须将司法活动的规律与组织的决策逻辑结合在一起,也必须将法官审理知识的专业化、法官对组织的忠诚以及案件审理模式理解为作出正确司法决策的组织决策前提;“去行政化”的司法职业保障改革不应在否定法院组织权力结构这一决策前提的基础上展开。同样,作为组织决策问题,司法职业保障不能仅仅通过改革法官从业环境实现,还必须将律师在司法中的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党的领导等关乎司法决策的“前提”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对于具体的司法活动,应当确立的基本认知是,坚守法治并不意味着通过法律“行话”排斥社会情感与普通民众的法律认知。
司法职业保障;法院;系统理论;组织;决策
司法职业改革涉及法院组织结构性调整问题。我国法院案件受理数量以及法官人数决定了司法运作的高度组织化。这与美国基于法官个体释法形成的法院运作机制不同。在一个拥有数百名法官的法院(这在我国并不少见)中,案件审理即使在庭审中体现所谓抗辩式的“司法规律”,也无法避免法院组织结构对裁判生成过程产生的影响。如何维持组织,使得组织中的成员受到正面的激励,努力完成组织设定的目标,实现组织特定的功能,是司法职业保障问题的核心。因此,将组织问题置于法院审判改革的中心,不仅对思考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探索“司法规律”的重要环节,同时,何为组织、何为法院组织、法官履职又如何在组织中得到保障,成为补充现有司法改革研究的重要方面。笔者于本文中将通过系统论的视角透视作为组织的法院之决策过程对司法职业保障的影响,以此审视我国司法改革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法院就是为法律系统决策运作而构建的一种组织结构
(一)组织克服决策悖论的机制
系统论认为,组织通过决策形成。卢曼将组织定义为在决策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系统。组织由决策构成,并且根据其已存的决策不断产生新的决策。①See Seidl,David.“Luhmann’s theory of autopoietic social system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Munich School of Management(2004).p.15.决策是一种特定的系统沟通。②See Luhmann,Niklas.Social system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95.组织是为了实现理性决策(也就是系统内部针对每一个具体情境做出正确选择)的最优化机制。③See Luhmann,Niklas.Social system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97.根据系统理论对个体与社会分离的定位,决策不是由个体产生的,而是通过系统即组织的沟通产生的。④See Seidl,David.“Luhmann’s theory of autopoietic social system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Munich School of Management(2004).p.16.
决策的延续是组织的自创生(autopoiesis),每一个决策是前一个决策的产物并且连接起未来的决策。组织通过“决策前提”(decision premises)稳定系统的期望结构,使得一些决策成为排除其他决策的系统结构条件,⑤决策前提是那些定义当下具体决策情境(decision situation)的组织结构性条件。并不是所有影响决策的因素都是决策前提。从组织运作上的封闭和不断回溯特征上看,决策前提也是一种决策。决策前提与决策的呈现递归状态中的。不仅决策成为后续决策的前提,而且后续决策也会型构决策前提,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他决策的定义。于是,选择的不确定性被吸收了(uncertainty absorption)。⑥See Seidl,David.“Luhmann’s theory of autopoietic social system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Munich School of Management(2004).p.16.任何决策都是在一种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不确定性不会随着决策消除,而只是被后续决策吸收了。由此笔者也发现,决策在吸收不确定性的同时,为了实现延续,还必须创造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与决策的确定性是共生的。See Luhmann,Niklas.Theory of society.Vol.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43.
通过决策前提的构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成了所谓双重的闭合:在运作上(operational)以及在其结构上(structural)的闭合。第一种闭合是指组织不断通过决策延续自身,而且也仅通过决策不断构建自身。组织外部的运作不能进入决策网络,决策也无法溢出组织的沟通。换句话说,在其运作的基础上,组织与其环境不产生交流(contact)。因此,组织内部个体,在运作闭合的角度上来看是处于“无知”和“盲目”的状态。组织的自我指涉在决策基础上建立起来。⑦See Seidl,David.“Luhmann’s theory of autopoietic social system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Munich School of Management(2004).p.19.
组织决策运作上的这种“盲目性”通过组织的结构(也就是决策前提)得到克服。决策前提决定了具体决策的样态。因此,决策前提成为组织运作再生产的动力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决策前提替代了环境,成为组织对外部信息进行吸收和运作的通道。不过,决策前提也是决策,决策前提不是从组织外部诞生的,这也就产生了组织的第二重封闭。因此,运作和结构上的双重封闭造就了组织的悖论。只有那些无法决策的事项才是真正的“决策”。换句话说,在具体的决策情境中,所有的备选项都具有相同的可能性,没有“更好的”选项,如果决策的备选项具有不同的价值、属性等,决策过程也就名不副实了,决策情境成为一种“被决定”的状态。不过,也正因为真正的决策是“难以决策的”,所以在系统论组织学的核心,决策的不可决策性这一悖论被揭示。⑧See Seidl,David.“Luhmann’s theory of autopoietic social system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Munich School of Management(2004).p.20.
在真实的决策状态中,为了防止出现上述悖论,必须构建出一种(或者多种)解除悖论(de-paradoxation)的机制,悖论必须被放置在“别处”。各种组织规则构建使得组织决策能够延续。组织就是这种通过不断构建组织规则、决策前提和决策情境的“解悖论”运作。⑨See Seidl,David.“Luhmann’s theory of autopoietic social system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Munich School of Management(2004).pp.20-21.法院作为一种组织,也必须面对法律系统运作悖论及其解除的问题。
(二)法院解除系统决策悖论的机制:禁止拒绝裁判原则
在法院组织中,解除决策悖论的过程通过构建系统运作上的“禁止拒绝裁判”(prohibition on denial of justice)原则以及结构上支撑这一原则的各种组织决策前提展开。从系统论组织学的视角看,世界不提供任何关于逻辑性的秩序和推导一致性的保障。“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不是从法律规范所具有的逻辑束缚力中推导出来的。因为法官从法律解释中,总能发现规范中的漏洞,从而拒绝裁判。因此,必须有一种制度供给协助法律系统具备一种一般性的能力,从而不断做出决策。⑩See Luhmann,Niklas,Klaus A.Ziegert,and Fatima Kastner.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286.法院就是法律系统沟通中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法官必须不断进行裁判,从而维持规范与事实互动关系的组织结构。
正如学者所言,法院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法律依据不足为由拒绝裁判案件。从这一司法原则出发,可以帮助人们深刻理解法院作为决策组织的属性,同时也有助于认清法院在现代法律生产诸领域中的龙头地位。卢曼认为,现代法律的生产方式有三种,即立法、司法与订立契约。在现代法律生产各领域中,立法机构可以搁置立法提案,合同可以被当事人终止,只有法院在面对案件时不得消极不作为,而必须一鼓作气地对诉讼两造给出裁判结果。正是因为法院往往在时间限制、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决策,这甚至意味着在无法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决策。①参见宾凯:《从决策的观点看司法裁判活动》,《清华法学》2011年第6期。因此,案件进入法律系统运作通过一种组织程序(也就是法院的程序)展开,并且通过职业化的法律意见和活动有效的运行。②See Luhmann,Niklas,Klaus A.Ziegert,and Fatima Kastner.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289.
首先,将法律适用的重心定位在法院组织上意味着作为组织成员的法官不能懈怠,也就是法官必须不断作出决策。通过监督、通过同事间的默契合作(collegiality),法官努力完成组织的期待。波斯纳法官认为作为组织的法院在运行中,同事间良好(或者说至少平等与和平)的关系对于案件审理的效率以及判决的可预期、一致性与延续性都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司法“工匠精神”(judicial workmanship)形成的关键要素,更是“有原则的”(principled)法律解释诞生的组织结构基础。③See Domnarski,William.Richard Posn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127-128.因此,法官职业素质的培养不仅需要现代社会法律教育系统的支撑,更需要法院组织内部决策前提的展开与整合。
其次,将法院看成是一种组织,也意味着组织决策中的“错误”,或者说法律程序中的问题,必须被解读为一种“司法”(judicial)意义上的错误。参与诉讼的人员可以通过上诉程序对司法决策进行质疑和辩论,不过上诉的理由必须被限定在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而且也对提起诉讼的人员资格和能力上设定了决策前提:不仅需要当事人提起,而且律师(也就是组织中的职业人)成为必不可少的结构性条件。没有律师协助当事人提出具有“法律意义”的上诉和申诉理由,法院组织的沟通和决策循环无法展开。法律职业化及其保障可以从法院组织的自创生及其决策前提设置上体现出来。
最后,组织中有不同的职位(positions)、薪酬,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职业生涯(career)区分。每一种职业生涯都依赖特定决策作出的时间和地点,每一次有关组织内部生涯都牵涉不同职业生涯(决策)之间的互动。我国法院中的“竞争上岗(员额)”机制就是这样的例证。这些决策形成了组织内部职业生涯与个体法官行动策略的紧密集合,引起了法官工作与追求升迁的动力机制。
组织对法律运作(也就是案件裁判)后果的重要性在于审判通过组织内部决策前提进行评价,法官的薪水和待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也不应受到系统外部因素(例如媒体报道)的影响。④法官对媒体发表的言论、媒体的案件报道都不是根据法院决策前提做出的,因此不仅应受限制,也应与法院决策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区分开来。See Nobles,Richard,and David Schiff.Observing law through systems theory.Bloomsbury Publishing,2012.p.99.在有关决策后果的评价体系中,法官不能对决策后果承担超越组织决策前提以外的责任,那些系统外部的不确定性通过组织决策前提的结构被“隐藏”,法官的行动不可能对系统外部的未知承担责任。也正是由于对裁判结果外部责任的免除,其他的一些原则(如司法独立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有意义的。⑤参见[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组织的双重封闭决定了法官承担责任的类型和实现机制。⑥See Luhmann,Niklas,Klaus A.Ziegert,and Fatima Kastner.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98-299.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职业改革
由于上述组织特性,法院在法律系统中具备其他法律沟通活动(合同制定、立法、行政执法)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而对稳定和延续法律解决纠纷、构建社会规范期望(normative expectation)起着关键作用。司法职业改革也必须围绕如何重塑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而展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职业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如何构建法院组织的决策自创生,从而将法院组织结构与维持法律的规范性(也就是社会守法精神)勾连起来。
(一)法院组织决策的自创生及其条件:职业分工与庭审实质化
系统理论通过构建作为组织的法院和以法官职业为依托的司法活动,意在说明法律决策是如何确定和限定范围的。卢曼发现,作为组织的法院通过结合决策的独立性原则、对法律文本的依赖、“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以及责任的内部化等结构上的决策前提,来保证决策在运作上的自我指涉。由于地域和时间差异,法院决策前提并非一致。这也使得法官对组织的忠诚度以及法律职业的社会团结(solidarity)形成区隔。⑦See Luhmann,Niklas,Klaus A.Ziegert,and Fatima Kastner.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99-300.除了法官,构成法院决策前提的还有律师、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进一步加强了法院组织“禁止拒绝裁判”目标的实现,法官的职业保障也依赖于法律职业分化的展开。
组织内部的职业分工使得法律共同体形成,律师、法官等人员之间能够保持友好的关系与交往,即使双方代理同一案件时代表了不同的当事人利益,也不影响一种基于组织决策和司法过程产生的共识基础和对话平台的稳定和持续。
法律共同体对于法律纠纷展开一种形式化决策的运作,也就是说,律师与法官都通过法院组织所构成的决策前提形成对具体案件的决策情景,同时,职业与组织的在法律系统中的分出和界定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和利益冲突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⑧See Luhmann,Niklas,Klaus A.Ziegert,and Fatima Kastner.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300-301.法院组织和法律职业对作为自创生的法律系统的构建与延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其不仅对于法院系统内部的沟通具有缓解法官决策压力(特别是承担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社会压力)这一功能,而且法律职业的分工以及法院司法程序(特别是庭审中心主义的程序)的构建使得法律决策的风险即决策的“不可决策性”得到隐藏,司法裁判的可接受度通过系统自我指涉形成的系统决策前提得到评判。
法院庭审实质化还具有连接社会面对面互动,建立一种非在场互动语境的效果。⑨参见前注⑤,卢曼书,第376-377页。法院组织将庭审的互动与抽象的规范连接起来,使庭审不仅对当下案件的裁判有意义,还成为法规范“客观目的”的一部分,从而递归式地连接了系统的过去与未来。⑩由于连接了组织和面对面互动交往,庭审的记录(record)因此也变得重要起来。不过,也正是由于组织决策吸收和隐藏了社会沟通固有的不确定性,庭审记录的公开受到严格限制。See Luhmann,Niklas.Theory of society.Vol.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47-148.法规范通过组织决策的自创生产生了更丰富的内在意涵,具备了适用不同案件的复杂性,使规范的“漏洞”越来越少,“禁止拒绝裁判”愈发可
能。
要达成上述组织决策的自创生(即使遇到所谓的疑难案件),从系统论来看,需要法院组织,或者说法律职业的分化(differentiation)。我国法院在绝对数量上已经具备不小的规模,在内部的组织管理上也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垂直监督乃至管理体系。然而,在水平维度上的司法分工、职业分化以及庭审实质化仍远远不够。无论从律师的绝对数量,还是在人口中的占比,都无法为司法裁判的运作封闭和风险控制提供有效支撑。对法官决策责任的重新界定,以及对干预司法现象的遏制,都不仅涉及一种法院内部职权与人事关系的调整,还与法律职业分工以及庭审实质化有关。①达马斯卡在多年前的著作中对中国司法制度多有批判,其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司法是一种极端的政策推进型(policy-making justice)治理模式,因此不仅当事人的参与度不高,甚至个案的司法结果也不是完全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所决定的。律师参与在审判中就更加无从谈起。See Damaska,Mirjan R.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legal proces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当代中国司法现状已经不同于达马斯卡当年的判断。至少在普通的民事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的角色越来越突出,作为当事人利益代表的律师承担了越来越多原先属于“国家司法工作人员”的责任。庭审过程也不再仅仅是“走过场”,商事审判中激烈的庭审对抗不再罕见。这种变化是国家整体治理方式和国家经济生活市场化所造成的,可以说是一种随着国家体制变化而带来的副产品,当然,也不能否认理念的更新与理论化研究在这种司法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庭审的实质化问题研究必须关注一国政治治理结构和原则的变迁。
(二)法规范回应性与司法职业保障的关系
庭审的实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应当用尽全部诉讼程序,而是可以促进法院沟通渠道在对水平维度上的职业分工。职业的分工与实质庭审的改革还可以区分与细化各种审判程序与审判模式,这些决策前提都是司法职业保障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司法职业保障,特别是在法院组织决策上形成的自创生效果依赖律师数量和律师水平的提高,使之成为法官决策的“帮手”,或者说真正成为司法过程共同的构建者。律师虽然不能代为承接法官所承担的“禁止拒绝裁判”的责任,但其可以使法官较为沉重的办案压力得到一定缓解。“衡量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看改革的法官工作强度是不是有所降低。”②许前飞:《在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在律师对决策过程的充分参与中,更多的“疑难案件”可以进入庭审。疑难案件的审理能够丰富法教义学,使得当下的裁判对未来案件具有指导或者参考价值,而且使得抽象的规范产生回应社会的能力。③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1页。因为法规范需要根据社会结构与案件事实的更新而不断推进,立法又不可能随时展开,在组织决策前提、职业与法律程序分工的影响下,司法过程对规范内涵的调整能够缓解外部的质疑,构建司法过程的正当性。④See Luhmann,Niklas,Klaus A.Ziegert,and Fatima Kastner.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58.
从系统理论上分析,司法职业保障的根基在于法院组织的自我调适以及法规范对社会变迁回应能力的加强。司法只能在回应社会的过程中求得稳定。法律系统需要不断地创新以回应自身的功能,“通过创新完成创新”成为现代社会的口号,“以决策促决策”成为法院组织自我整合的目标。
通过系统论,能够将法律适用的教义学问题与组织决策如何不断产生的问题勾连起来,从而将法律解释问题嵌入组织决策的结构。法院“人事”、“上下级关系”等组织问题与解释学紧密相连,真正实现“突出司法保障为办案服务、为司法决策服务的重点”。⑤周强:《对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会议的重要批示》(2014年11月25日),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编:《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管理研究与参考》(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系统理论的洞见提供了理解司法职业保障的全新视角,也为解决日常司法实践中“法教义学”与“实践司法”脱钩问题提供了有益智识。
(三)法院是法律系统的中心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发现,法律职业群体的分工、组织角色的安排、诉讼参与过程的实质化等作为组织的决策前提,为司法裁判在最终的成果中实现逻辑自洽提供了制度条件。通过法院组织在人员与程序上的分配,系统外部的干扰减弱了。当然,这并非排除(而事实上激发了)那些对法律规范的不满溢出司法过程,通过政治系统的立法程序寻求救济。法院决策的自创生并不意味着穷尽了基于合法/非法二元符码(binary code)的法律沟通,而是给系统内部的再次分化提供了条件,⑥See Luhmann,Niklas,Klaus A.Ziegert,and Fatima Kastner.Law as a social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58.从而为法律与政治系统互动与耦合(coupling)提供了结构上的稳定。
系统间的耦合现象涉及系统理论中对法律系统的中心与边缘(center/periphery)的划分。在卢曼看来,只有法院才能对法律行动者产生纳入与排除(inclusion/exclusion)的效果,⑦参见刘涛:《纳入与排除:卢曼系统理论的第三演进阶段?》,《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1期。此即对法律职业主体资格与能力的认可、否定以及划分,从而也就明晰了法官“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并且,法官的这一司法责任变得特定起来,别的诉讼参与者以及其他法律系统沟通的参与者不再拥有这一权力并承担这一责任。围绕法官这一角色产生了一系列的规范解释方法论。法院成为法律系统的中心。
通过决策前提的构建与完善,法律系统中发生的大量沟通使得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案件会进入法院。法院一方面在立案上对当事人和律师而言具有高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在司法过程中对可裁判(judiciable)案件基于决策前提进行筛选。因为法院必须“自我保护”,使得决策的悖论得到隐藏。司法职业保障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司法化”。司法职业保障的目标在于对那些进入司法的案件提供“通过实质审判”得到合理司法裁判结果与论证的途径。通过组织决策前提的建立,法院筛选了能够进入庭审的案件以及能够承担庭审实质化的组织结构与角色。系统论以组织决策的视角为人们深入理解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职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三、从组织决策视角看当下我国司法职业保障的改革
笔者此前已对作为组织的法院如何设计决策前提,进而保障司法决策的正当和有效进行了分析。除了职业分工、庭审实质化与律师参与,还有一些决策前提的构建和调整对于司法职业保障以及法院运作,特别是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而言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一)组织的权力与司法职业保障
理论和实践中一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法院的运作(至少庭审的运作)不需要权力结构。对法官的管理应当以审判团队独立裁判为基础,司法职业保障也应当促成法院组织内部的“扁平化”。法院的“去行政化”与“去权力结构”(特别是与“去垂直领导”)是否形成对应呢?
从系统论的视角看,组织权力的诞生和运行是一种系统内部的沟通。权力结构是组织决策的沟通渠道。权力的作用对象是组织人事,也就是说,权力能够指向对组织中成员权和职位的认定和调整。院长、庭长对法官和案件的管理,是激励和限制组织成员勤勉工作的制度结构,也是司法决策在结构上形成封闭的条件。在人数众多的我国法院,作为决策前提存在的人员管理和权力结构是支撑法官决策及其责任承担的系统设置。组织是对风险与责任进行细微分配的巨大网络,并且可以通过权力策略控制。⑧参见[德]Niklas Luhmann:《社会之经济》,汤志杰、鲁贵显译注,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台北),第375页。
“扁平化”的审判组织多出现在人员较少的基层法院或派出法庭中,而一旦组织成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就需要对组织进行人事管理。组织中新的结构由此诞生,新的分工细化了。分工的细化带来了进一步权力结构出现的条件,成员职位、岗位以及其他司法保障,都无可避免地通过权力结构展开。这意味着考察法院的薪酬、升迁、员额时,必须将组织权力结构纳入思考的范围。司法改革并非取消法院系统的科层结构。“去行政化”的司法职业保障改革不意味着、也不可能在否定法院组织权力结构这一决策前提的基础上展开。
(二)司法职业保障改革仅是法院内部的决策调控吗
司法职业保障与法院责任追究机制是“硬币的两面”。职业保障,包括薪酬、晋升以及案件外部干预排除机制等是正面激励:职业必须有吸引力,薪酬必须反映职业荣誉;⑨See Luhmann,Niklas.Theory of society.Vol.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43.通过内部“程序正当”的责任追究,其功能在于从反面抑制组织成员“不愿决策”的风险。通过这种内部追责机制,建立司法职业的“地位”与“声望”,使得法官与组织的命运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反,如果“错案追究”主要通过外部责任追究完成,则会使得司法职业的稳定性下降,基于社会流动性,有可能产生对法官追责压力的负面激励,也有可能产生法官“用脚投票”的离职现象。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以及司法职业保障从一体化的公务员编制中的分出和单列,法官职业声望的提高与责任追究的内部化将会产生更为直接的关联;法官职业进出和职位升降将与作为决策组织的法院功能结合更为紧密交织,而不再仅仅是国家公务员管理的一环。
职业声望的构建与追责体系的调整都是为了保证法官坚守“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增强司法的“规则构建”功能。组织化决策的这种不断自我指涉,从系统内部看,能够提升法官职业工作的荣誉感;从系统外部看,则是对社会交往中不确定性的吸收和社会规范期望的建立。从系统论的视角观察,能够将法官责任追究对法律职业内部的作用与社会外部的功能勾连起来,从而使司法职业保障改革的社会整合效果更为明晰。
司法职业保障中的法官薪酬、升迁与内部化的责任追究主要针对法官“禁止拒绝裁判”的职业特点。如果将司法职业保障的“优待”推广至司法职业以外,则不符合上述改革的出发点。组织虽然面对决策进行封闭运作,但是并不意味着组织不存在其他的社会沟通(法院的后勤、财务等部门)。法官员额的调整必然呈现法院内部不同类别人员待遇和地位的差异。司法职业保障改革需要得到法院内部人员的认知和认同。然而,这并非易事,从我国现有的法官人员结构上来看,其仍嵌于国家一体化的科层公务员体制中,这也是《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作出而非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原因。改革是从有权调整公务员体制的国家治理领导层展开的。
因此,党的领导依然是司法职业保障最强有力的“保障”。系统论对现代政治系统做出了“政治”(politics)与“行政”(administration)的区分,⑩See King,Michael,and Christopher J.Thornhill.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law.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3.政治决策能够弥补行政运作的僵化和官僚主义。法院组织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分出也是基于政治决策而非科层行政。司法职业保障改革是一种政治动议,而政治决策的推广和实施一方面依赖政治宣传对法院内部人员自我认知的促动,另一方面也与政治决策与科层制行政治理结构之间冲突的化解与调整有关。也就是说,在我国现有的严密科层行政治理机制中,如何在机构设置上衍生出适合法院组织改革目标的路径,成为司法职业保障能否成功的关键。进一步说,如果从改革的预期来看司法职业保障与责任追究是为了加强法院内部决策机制的稳定,那么当下司法职业保障改革的制度配套依然内嵌于政治治理体系的调整。“法官的忠诚”、法院内部差异的合理化、对未被纳入员额人员的安排以及安抚等看似法院组织和职业内部制度培育问题,实则需要强大的政治(特别是党内决策)的不断供给和支持。在地方的实践中,各级党委的支持与配合成为必要条件。党组织对中央决策的贯彻力度以及党对科层行政的控制能力,将决定司法职业保障的“命运”。
(三)一个例证:司法考核机制
以上论证也适用于分析更为具体的司法职业保障制度设计。激励机制与追责机制一般不会经常使用,对个体的刺激、限制以及个体对组织的“依附”和“忠诚”弥散在法院的日常考核中。尽管存在弊病,考核机制在法院和司法运作中无法取消。组织作为连接社会系统与个体的社会构成,能够不断对个体产生促动和刺激,形成结构上的耦合。系统/环境区分的再生产也依靠组织不断对个体的行动产生指引和调整。①See Nobles,Richard,and David Schiff.Observing law through systems theory.Bloomsbury Publishing,2012.pp.219-220.法院的内部考核机制便是促成这种互动与耦合的制度设计。
从系统论的角度上来看,小型组织不需要建立完整的考核机制。如果“是个小组织,比如一百来人甚至更小的法院,或许这件事可以通过大家的主观评价来实现,因为熟识,比较了解,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②李则立:《法官考核,既非毒药,也非灵药》,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IxODIyMg==&mid=2649797095&idx= 1&sn=cdffb3761579c5e9e6b35a30d14193ca&chksm=87167026b061f930d12f01ce0fab441892d1e311c653e25d1cf871d611a6c9e09674d 2009f9b&mpshare=1&scene=5&srcid=1211ekS8lXftMyZrAWdJxa9L#rd,2016年12月11日访问。我国法院组织人数庞大,案件众多,不进行考核,无法激励法官“禁止拒绝裁判”,特别是无法提高结案率。
当然,考核并非目的。“为了考核而考核”是司法改革需去除的思维误区。案件权重计算、案件分配的随机化都是基于“司法规律”的体制改革。在考核制度中正视“司法规律”,也就意味着要正视如何使得法官不“拒绝裁判”,“认真对待每一个当事人”。
另外,如果法官的“组织化”程度即系统与个体的结构耦合已经十分稳定,考核问题将会成为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问题,无需过多直接控制与监督。在我国法院组织体系中,这又和案件审判模式有关。增加案件审判模式的多样性,推广各种简易程序,将法官的精力和对案件权重的评判集中到那些“复杂”案件中,是完善考核制度的前提。不过,在当下我国法院的案件审判中,一味简化案件审理过程是否可行又是一个问题。
司法考核与“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方向之间存在冲突。在社会转型期,法院必然对数量庞大的案件展开“实质审理”。也就是说,法官在审理中不仅需要“释法”,还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这必然花费法官大量的时间和智慧,使得考核不可能仅仅通过形式化的数据分析进行。从法院的组织化及其考核机制复杂性方面,可以窥见司法职业保障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紧密联系。从个体、组织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上审视司法考核,我国的司法职业保障问题不仅涉及法院内部“决策前提”的调整,而且与整体的改革目标和动力勾连。
因此,在司法改革中法院不仅面临“案多人少”的难题,而且还将更多地承担转型时期化解各种具体社会矛盾的责任。这意味着法官在处理个案中不免会遇到对法律规定与司法过程不熟悉甚至不理解的当事人,法院组织也会面临如何增强社会成员对司法的信任的问题。组织内部的决策和决策前提的构建必须将这些外部环境因素统筹纳入,平衡司法决策的专业性与司法运行社会效果之间的张力。进一步说,这种均衡的实现不仅需要法院创新管理机制,将司法公开、司法为民等能够促进司法社会认同的机制内化于组织系统中的立案、庭前调查、庭审、执行等各个运行阶段,而且需要外部制度,特别是党组织制度的支撑。社会主义法治的发生与发展必然依靠党与政府提供的改革合法性基础。司法对社会生活规则的调整,也依赖于党的权威与支配地位对法院组织的支持。对我国当下社会正走向功能分化的分析,包括对我国法院体系自创生的分析,不仅需要阐释“分化”的正面意义,而且必须关注功能系统自创生的动力机制。法院组织决策前提的构建,在我国始终需要与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建立关联。司法职业保障不仅需要关注法院组织、司法职业共同体、公务员管理体系,而且必须重视党组织在社会系统结构耦合中所起到的推动乃至决定作用。
四、系统组织学视角下司法改革的进路
通过系统论下组织社会学的考察,笔者对司法职业保障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将法院与司法审判均置于组织及其决策的自我指涉上来观察。在上述的论证中也可以发现,对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以及法院组织的建设和改革,都深嵌于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在这里通过系统论对“改革”的意义及其功能的理解做出阐释。
现代社会对政治改革以及司法改革,都需要通过组织机制展开。这也是现代社会沟通方式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与系统化的后果。从系统论视角来看,司法改革是对法院组织内部决策前提的调整。改革成效的评价也应当通过系统内部吸收外部环境复杂性的程度决定。也就是说,司法改革的目标不仅在于提升个别的司法决策(个案审理)质量,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于认真对待法院决策前提的构建问题。对案件审理的“司法性质”与“司法过程”,人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经验积累,但是在法院组织的决策前提(也就是案件管理、评价、考核乃至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上人们依然处在探索阶段。一方面,需要加快去“行政化”的司法制度改革,另一方面,还需要借鉴包括系统论在内的各种组织理论研究和实践,以现代组织管理的视角改革法院职业保障机制。
如前所述,组织决策运作上的封闭是建立在组织结构上的封闭即组织决策前提的构建及其在成员中的广泛认同(组织和人员的结构耦合)基础上的。司法改革力图让“法律的归法律”、“政策的归政策”。法院和法官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案件审理在运作上的自创生牵涉组织在结构上的自我封闭程度。然而在结构的设计和司法决策前提的实践中,并不存在普适的司法审判与管理模式。如果仅仅将司法职业保障看作对法官待遇无条件的保障,看作是法官拒绝与其他社会理性和情感进行沟通的借口,甚至看作法官徇私舞弊的“令箭”,则是错误理解了“司法规律”的内涵。
司法过程在运作上的封闭以及法官在案件决策中的主体地位的体现,建立在社会的司法认同基础上。目前,在继续加强对司法领域贪污腐败查处的同时,还应当适时地调整司法的公众参与方式,努力将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表达和对法律正义的认知纳入法院组织决策的过程,从而体现司法过程的民主性,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便是例证。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也使得对司法的外部监督成本逐渐降低,以组织决策在结构上的丰富性和决策认知层面的开放程度来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
可以说,任何司法规律内生于特定的组织结构。坚守法治的底线并不意味着通过法律“行话”排斥社会情感。法院决策公正、独立和负责的基础是组织决策前提与我国社会的转型、人民的利益诉求的变迁相吻合。司法保障体制的具体改革方向,不仅与不同案件类型相关,也是对国家治理和司法改革整体设计的回应。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法官遇害案件,使司法机关主要关注如何通过外部制度支撑和外部资源获取来保障法官职业安全。③参见《人民法院落实〈保障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法发[2017]4号),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5572.html,2017年2月8日访问。笔者于本文中通过对作为组织的法院及其决策内部运作逻辑的分析,从如何构建和丰富司法体系决策结构的视角阐述了司法职业保障机制建设的意义、功能和路径。笔者认为,法官应当受到社会尊重,司法职业保障也需要政府与社会的支持,然而,司法权威与法治顺利运行的基础性制度条件根植于司法机关对其自身决策能力的认知、反思与调控,只有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增强在变动社会结构中的“适应性”,司法才有可能坚守阵地,并为社会大众提供可靠的规范预期,并最终达到司法职业保障的目标,实现司法的权威性。
(责任编辑:江锴)
DF82
A
1005-9512-(2017)06-0078-09
刘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蔡道通,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