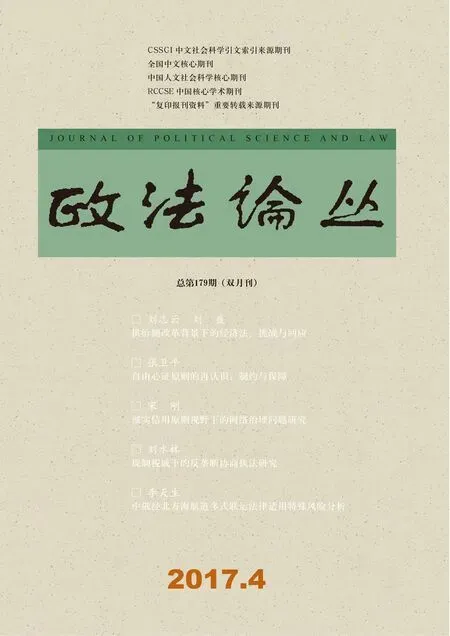共享经济中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以《上海网约车新规》为分析对象
黄 锫
(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092)
共享经济中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以《上海网约车新规》为分析对象
黄 锫
(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092)
行政许可设定是对共享经济实施法律规制的重要方式,应当确保行政许可设定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审查思路分两步骤:第一步是判断受审查的行政许可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第二步是从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条件、程序与期限四个方面继续判断其合法性。依据这一合法性审查思路,《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律属性存在含糊之处,且无论如何定性都与上位法存在矛盾之处。并且目前与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相关的国务院决定、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存在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存在相互冲突与矛盾之处,需要通过立法调整来进行弥补。
共享经济 网约车 行政许可设定
共享经济也即“分享经济”,它是指社会公众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的交易平台,将自身闲置资源与他人分享,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并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共享经济是目前社会经济领域中最活跃、也是最具有发展前景的经济模式,它在我国的规模化发展起始于2010年左右智能手机的普及。随着人们手机上网便利度的提高、互联网可得距离的缩短、利用网络搭建共享平台可能性的增强,许多共享经济企业在2011年开始创建,如蚂蚁短租等短租平台的成立、陆金所等P2P金融平台的成立、51Talk等远程外教平台的成立等。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2年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这两个网约车平台的出现。随着这两个网约车平台的创建与发展,共享经济真正进入我国社会普通大众的视野。之后围绕网约车平台合法性的激烈争论以及政府法律规制框架的逐步成型,共享经济才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各阶层都耳熟能详的经济现象。
共享经济是一种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的全新经济业态,其产生与繁荣的过程伴随着政府法律规制的实施。行政许可的设定是最重要的法律规制途径之一,它通过建立市场准入机制的方式实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对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1]P18-27由此这一法律规制手段在共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运用,成为不可或缺的规制与治理工具。[2]如上海市政府在2016年12月21日公布生效的《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简称《上海网约车新规》)中,就设定了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网约车车辆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约车驾驶员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三个行政许可,对网约车这一共享经济业态实施法律规制。然而规则之治是现代法治的主要含义,[3]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则的框架内实施,这意味着法律规制行为本身也应当合法,通过设定行政许可对共享经济实施规制的行政活动同样不能例外,必须满足基本的合法性要求。否则,即使实现了对新经济业态的规制,那么也会同时对法治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其产生的示范性效应甚至可能会危及法治秩序建设的根本,由此对共享经济中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进行研究也就成为必要。
以下本文将首先探讨对行政许可设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基本思路,其次结合网约车相关法律文件分析《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存在的合法性疑点,最后探讨弥补行政许可设定合法性的途径,以期为今后通过合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方式规制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行政许可设定合法性的审查思路
探讨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应起始于区分行政许可设定中“行政许可的创设”与“行政许可的细化”两种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差异。行政许可的“创设”是指不同的法律文件在上位法没有设定行政许可时,从无到有设定行政许可的行为。例如在无上位法设定行政许可时,通过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设定从事特定共享经济活动的许可就属于创设许可。行政许可的“细化”是指上位法已经设定了行政许可,依据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基本立法原则,下位法就只能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范围内进行细化,而不得违反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的相关内容。例如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已经对特定共享经济活动创设行政许可的前提下,下位法在立法规范该行政许可时就不能突破上位法的规定进行创设,而只能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对该行政许可的相关内容进行细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使用“创设”与“细化”这两个词汇进行区分,而是使用了“设定”与“规定”的词汇区分,也就是说,在《行政许可法》的法律条文中用了“设定”行政许可一词对应“创设”行政许可,使用“规定”行政许可一词对应“细化”行政许可。这种立法方式是容易使人混淆的,因为,《行政许可法》第二章的标题是“行政许可的设定”,从立法逻辑上而言,这意味着行政许可的设定应当包括之后具体条文中的所有内容,属于概括性的法律概念。但是从第二章中的具体条文表述方式看,行政许可的设定实际上指的却仅仅只是对行政许可的“创设”。因此,在本文的论证中为了避免混淆,将“行政许可的设定”定义为包含了“行政许可的创设”和“行政许可的细化”两种部分内容的上位概念,进而讨论共享经济代表性业态——网约车——三个行政许可的合法性问题,这就与《行政许可法》中对于“行政许可设定”的概念界定略有区别。
区分行政许可的创设与细化两种不同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之后,对于其合法性审查将采取不同的标准。就行政许可的创设而言,在《行政许可法》中规定了不同类型法律文件的设定权限,其中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有权创设常设性行政许可,国务院的决定与省级地方政府规章在法定条件下有权创设临时性许可,且地方性法规与省级地方政府规章不得创设涉及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许可。由此,如果法律文件中的行政许可属于创设许可的范畴,主要应通过观察法律文件本身是否具有《行政许可法》所授予的创设权限来审查其合法性。就行政许可的细化而言,依据《立法法》所确立的下位法不得突破上位法的基本规则,下位法对行政许可的细化必须在上位法所创设的行政许可的范围内实施,不得突破上位法的规定。由此,如果法律文件中的行政许可属于细化许可的范畴,主要应通过观察其中设定的行政许可是否与上位法创设的行政许可相冲突来审查其合法性。
无论是对于创设的行政许可抑或细化的行政许可,在审查其合法性时都会涉及行政许可的五方面内容,即许可的事项、实施主体、条件、程序与期限。在这五方面内容中,行政许可的事项是首要内容,因为其关系到行政许可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究竟归于创设还是细化。就法理而言,行政许可的事项本质上是人们的某种特定行为,设定行政许可就是对某种特定行为实施普遍禁止,而授予行政许可则是对许可申请人解除这种普遍性的禁止,允许其实施这种特定行为。因此,某种特定行为是否已经被上位法设定为普遍性禁止且需通过获得行政许可予以解除禁止,就成为区分创设许可与细化许可的关键,进而也成为审查行政许可设定合法性的前提。
就此而言,共享经济中的各类新业态实质上就是各种新类型的特定经济行为。通过设定行政许可的方式对其予以法律规制,也就是先对这些新类型的特定经济行为实施普遍性禁止,继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主体解除这种普遍性禁止。不过,由于共享经济的新业态往往既呈现出与传统业态的高度相关性,又呈现出显著区别于传统业态的自身特色,因而是否属于新类型的特定经济行为就可能会存在争议,而这种争议会直接影响到行政许可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确定。典型如网约车的新经济业态,它即呈现出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高度相似性,又因为私家车的介入而呈现区别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自身特色,业界对于其是否可以归入传统出租车的范畴就存在争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网约车行政许可就成为对现有法律文件中已创设的出租车相关行政许可的细化,应当依据法定的细化权限审查其合法性。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应当依据法定的创设权限审查其合法性。在本文以下的分析中采取了前者的立场,主张网约车属于出租车的范畴,因为两者本质上都是由机动车驾驶员应乘车人的要求为其提供点对点的精确位移服务,这种服务的性质不会因乘车人召唤的方式(路边扬召抑或网络预约)不同而不同,也不会因机动车本身的法律性质(商用抑或家用)不同而不同。
通过事项(特定行为)确定行政许可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之后,就可以从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条件、程序与期限四个方面继续审查其合法性。应注意的是,如果是对创设行政许可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那么其主要判断依据是《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因为在《行政许可法》中明确了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条件、程序与期限的一般规则。而如果是对细化行政许可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那么其主要判断依据除了《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之外,还应包括创设行政许可的上位法中的相关许可规定,也即细化行政许可需要受到已创设行政许可的约束。
在审查已设定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条件、程序与期限四个方面的合法性时,立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是行政许可的授权设定问题。即在法律文件对行政许可的设定过程中,将行政许可中的部分内容授予其他机关制定下位法予以创设。典型如国务院2004年颁布了《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该国务院决定以附件形式创设了500项行政许可,其中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对实施本决定所列各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并予以公布。”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将500项行政许可的“许可条件”授权给国务院下属部门进行创设。这种对行政许可中部分内容的授权设定行为应属违反《行政许可法》第18条的规定,因为该法条中明确要求法律文件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应当明确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其中并未规定创设行政许可的机关可以将行政许可中的部分内容授权与其他主体创设。事实上这种行政许可授权设定的现象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并非孤例,特别是国务院各部委因其在自身工作领域内的专业性而经常获得创设许可条件的授权,进而通过制定部门规章的方式创设具体的许可条件,这实质上是突破了现行《行政许可法》禁止部门规章创设行政许可的立法精神。
其二是行政许可创设中的设定遗漏问题。即在法律文件创设行政许可的过程中,遗漏了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条件、程序或者期限中某一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的内容。由于《行政许可法》中对于行政许可的程序与期限已经有了一般性规定,因此,如果其他法律文件在创设行政许可时遗漏这两方面的内容,只需准用《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即可。但是如果遗漏了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与条件,那么就属于行政许可设定不明,需要重新进行设定。例如,假设在法律文件中仅规定“网约车经营应当获得行政许可”,但是没有明确向何主体申请行政许可,也没有规定获取行政许可的具体条件,那么就属于设定不明,应当依据《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权限进行重新设定。
综上,对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审查思路可以区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应判断受审查的行政许可属于创设的行政许可抑或细化的行政许可,其判断依据是许可事项是否已经在上位法中被创设;第二步应在第一步判断的基础上,依据行政许可的创设与细化的不同合法性审查标准,从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条件、程序或者期限四个方面进行判断。以下将依据这一合法性审查思路,对《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合法性进行分析。
二、《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疑点
分析《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应明确其所涉及的关联法律文件。梳理之后可以发现,目前在上海市范围内与《上海网约车新规》(省级地方政府规章)中设定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相关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四部: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的决定——《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简称《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在2016年制定实施的部门规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简称《网约车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在2016年修订生效的部门规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以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2015年修订生效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与以上四部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相互纠缠,使其合法性存在诸多疑点,以下将逐一分析:
(一)《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
对《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合法性的探讨,起始于判断这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是创设许可还是细化许可。如前文所述,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同法律文件拥有对行政许可不同的创设权与细化权,其权限范围大相径庭。并且《行政许可法》中对于行政许可创设权与细化权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分清《上海网约车新规》中究竟是创设行政许可还是细化行政许可,是审查其行政许可设定合法性的前提。而这一判断的关键点在于上位法中是否已经创设了这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上海网约车新规》就是对上位法中已创设行政许可的细化,反之则是对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创设。
那么,《上海网约车新规》的上位法是否已经创设了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呢?这个问题存在着争议。目前最可能相关的法律文件是交通运输部制定的《网约车暂行办法》,因为正是这份部门规章的条文中首次出现了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立法表述。但是,根据我国《立法法》第91条的规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从《立法法》确定的法律位阶角度观察,《网约车暂行办法》并非《上海网约车新规》的上位法。更何况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4、15条的规定,部门规章并不拥有创设行政许可的权力,因此学者们通常将网约车界定为出租车的一种新类型,并进而认为《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上位法来源是《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在《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国务院以附件表格目录的形式保留了500项行政许可,这实质就是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创设了500项行政许可。①在该决定的附件表格目录的第112项,保留了与出租车相关的出租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三个行政许可,这三个出租车相关的行政许可就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上位规定。
然而,将《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作为《上海网约车新规》的上位法依据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我国《立法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务院的决定与省级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法律效力等级关系。并且依据《立法法》第82条的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的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并不包括国务院的决定。从这一点可以推导出国务院的决定并没有被《立法法》承认为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依据,因此也就并非属于地方政府规章的上位法(不过这一点是可以论辩的,详见本文下一部分的讨论),由此,《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虽然创设了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但是并不能作为《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行政许可的上位法依据。
于是,只有《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可能成为《上海网约车新规》设定行政许可的上位法依据,因为依据《立法法》第89条第1款的规定,它作为地方性法规在法律效力上高于作为省级地方政府规章的《上海网约车新规》。并且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款的规定,地方性法规也有权在上位法未设定行政许可时创设许可。同时通过细读法条,我们可以将网络预约出租车的方式纳入《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19条:“客运服务实行扬手招车、电话预订和站点租乘等方式”的“等”字中加以理解。不过,如果将《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作为《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网约车行政许可的上位法依据,那么《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网约车行政许可就会因为与《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定的不一致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其中典型的例子如《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11条第1款第3项要求出租车驾驶员必须具备上海市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而在《上海网约车新规》中却取消了这一规定,不要求网约车驾驶员具备上海市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又如《上海网约车新规》中明确规定从事网约车的车辆轴距应达到2600毫米以上,这在《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中并没有相关的要求。这种矛盾冲突意味着《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许多规定会因为违反作为上位法的《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而无效。
为了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我们可以不将《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视为《上海网约车新规》的上位法依据,而是将其视为专门规制巡游出租车的法律文件,与专门规制网约出租车的《上海网约车新规》并行不悖,分别规制两种不同类型的出租车。由于《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在制定时主要针对的也就是传统的巡游出租车,而非网约车,因此从实际操作层面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这样考虑,那么《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行政许可就并非是对上位法的细化,而是对行政许可的创设。这意味着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款的规定,《上海网约车新规》中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属于省级地方政府规章创设的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有效期只有1年,到期后必须提请有权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律属性很尴尬:如果它是对上位法创设的网约车行政许可的细化,那么它的许多条款就会因为违反作为上位法《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而无效。而如果将它视为对网约车行政许可的创设,那么它所创设的行政许可只能是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有效期只有1年。
(二)《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设定行政许可的合法性
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径路是仍然将《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创设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作为《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上位法依据,然后再依此分析后者的合法性。②然而依照这一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这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本身的合法性就存在疑问。
详言之,《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从法律性质上而言属于国务院发布的“决定”。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的规定,国务院决定的确有权创设行政许可。但是根据同一条款的限制,国务院决定创设行政许可应在“必要”时实施,并且国务院决定创设的行政许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法律解释开始于文义解释,同时也终结于文义解释,[4]因此,对国务院决定创设行政许可权限的解释必须严格依据《行政许可法》条文的文义进行理解。也就是说,依据《行政许可法》的条文文义的严格解释,国务院决定创设的行政许可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性行政许可,并不属于常态化的行政许可,应当同时满足“必要性”和“临时性”两种限制。③就“必要性”的限制条件而言,一般指特殊情况下一时难以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5]P129在《行政许可法》生效之时,原先由部门规章《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所创设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随之失效,④而出租车行业的既有行政管理活动又不能被打乱,制度的改革需要有延续性。因此,当时通过《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保留这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满足了“必要性”的要求。但是就“临时性”的限制条件而言,2004年《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出台后直到目前,已经十余年过去,然而这一国务院决定仍然创设着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这并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中“临时性”的要求。虽然该款中对于国务院何时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并无规定,也就是说,对于何为“及时”目前并无权威解释,但是在十余年时间内都没有提请有权机关制定法律或自行制定行政法规,这很难被认同为符合该条款所要求的“临时性”,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批评。[6]
此外,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8条的规定,法律文件在创设行政许可时,应当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创设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时,以附件目录的形式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的实施机关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从行政许可设定的法理观察,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创设了行政许可的两方面内容:一是需要经过行政许可的事项,二是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也就是说,《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规定了出租车相关的三类事项需要经过许可才能实施,同时规定这三个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是县级以上政府出租车行政主管部门。另外在《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还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对实施本决定所列各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并予以公布。有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和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执行。”依据这一规定的内容,可以认为,《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将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和期限界定为参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执行,而将拟定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条件的权力授权给“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发布,具体而言就是将拟定三种行政许可条件的权力授权给国务院下属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由于《行政许可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法律效力等级上高于国务院制定的决定,因此,《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规定参照《行政许可法》中的实施程序与期限执行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将拟定三个行政许可条件的权力授权给国务院部门来具体规定,就值得商榷。行政许可从其法理特质上而言是对普遍禁止行为的一种解除,对某种事项创设行政许可意味着禁止所有主体实施特定种类的行为,而行政许可的条件决定了特定主体能否被允许从事该普遍禁止的行为,是行政许可创设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甚至有学者指出在行政许可各部分内容设定过程中,只有行政许可的条件设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设许可,其他内容都只是对《行政许可法》中相关规定的细化。[7]P52-55《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的这种授权事实上意味着使国务院部门有权通过制定部门规章的方式创设行政许可的条件,这就使得部门规章变相拥有了创设行政许可的权力,这与《行政许可法》中禁止部门规章创设行政许可的立法思路是相悖的。从网约车行政许可的立法实践来看,目前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基础许可条件都是由交通运输部制定的部门规章——《网约车暂行办法》所创设,这实质上是通过部门规章创设了网约车行政许可中最重要的内容,虽然有国务院决定的授权,但这种授权本身的合法性就存在瑕疵。
更进一步而言,交通运输部在得到《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的授权后,在《网约车暂行办法》创设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的条件时,又再次授权地方政府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其他行政许可条件。如交通运输部在《网约车暂行办法》第13条第2款中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对网约车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上海网约车新规》第8条中规定,在上海市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辆必须具备额外的7项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网约车必须在上海市注册登记(也即必须是沪牌车辆)、车辆轴距必须达到2600毫米以上等。同时,在《网约车暂行办法》第14条第1款第4项中规定网约车驾驶员必须具备“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据此,《上海网约车新规》第9条中规定,在上海市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必须具备额外的4项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网约车驾驶员必须具备上海市户籍(也即必须是沪人)。《网约车暂行办法》中的这种再授权从现实的行政管理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法律角度看,正如上文曾论述的,《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对部门规章设定行政许可条件的授权本身合法性就是有瑕疵的,作为部门规章的《网约车暂行办法》基于这种在法律上本不稳固的授权,再次授权给地方政府制定额外的网约车行政许可条件,其合法性显然更加值得质疑。在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另一网约车相关部门规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在该部门规章的第10条设定了申请参加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4个条件,并且在第4个条件中也授权地方政府制定其他的许可条件,这种对行政许可条件的设定与再授权同样存在合法性根基不稳的问题。
(三)其他合法性问题
除了以上两方面的合法性疑点外,《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创设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与作为地方性法规的《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中创设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的关系也值得探讨。《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早在1995年就已经制定生效,在其中第9、10条中创设了从事出租车客运服务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行政许可条件,在第11条中创设了出租车驾驶员的行政许可条件,在第14条中创设了从事出租车客运服务的车辆的行政许可。这三个由地方性法规创设的行政许可并没有因《行政许可法》的生效而失去效力,因为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可以创设行政许可的事项,如果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创设行政许可。《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并非法律,也非行政法规,因此,虽然其中创设了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也不能因此否认《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创设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同时,在我国的《立法法》中,并没有规定国务院决定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法律效力等级关系,因此,当两者都对出租车相关的行政许可进行创设时,难以依据法律规范的冲突适用规则进行推定,只能认为两者同时存在并都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在上海区域范围内,《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与《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分别创设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同时存在,并与《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行为并存,这导致了上海区域范围内出租车行业行政许可法律依据的混乱,网约车的法律规制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法律依据混乱的影响。
最后,也并非不重要的,无论是否有上位法的依据,《上海网约车新规》中对于网约车经营服务所设定的“沪人沪牌”的行政许可条件,虽然从一个特大型城市的日常管理角度看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却与《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所背离。因为在《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中,明确要求省级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沪人沪牌”的许可条件排除了上海以外地区的人员在上海市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可能性,应属于《行政许可法》的这一条款所禁止的行政许可设定行为。
三、《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行政许可设定合法性的补救途径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与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甚至存在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面对网约车这一社会中涌现的共享经济形态,通过设定行政许可的方式进行法律规制时,更应当遵循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在法治的框架内实施。当然,由于共享经济属于新出现的经济业态,原有的法律规制体系必然会存在与其不相适应之处,新制定的法律规制措施(如本文所重点探讨的行政许可设定问题)也可能会存在各种瑕疵,这就需要通过认真的分析与研究,探明通过何种途径进行立法调整,以便既可以对共享经济这种新经济业态进行有效规制,又同时确保规制行为本身的合法性。
具体到《上海网约车新规》及其相关法律文件中设定的行政许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立法调整,从而实现对网约车相关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补救:
第一,国家立法层面。从国家立法层面而言,应当尽快将《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中设定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上升为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从而消除这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依据现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只能算是临时性行政许可的尴尬地位。同时在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时,应当明确这三个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许可条件、许可程序与期限等内容,以满足《行政许可法》第18条的法律要求。这一立法工作是消除网约车相关行政许可违法性的最基本途径,否则网约车相关的行政许可即使在实践中顺利实施,也会随时面临合法性的质疑。
同时笔者认为,就目前网约车规制的现状来看,甚至制定行政法规也难以完全解决其中设定的行政许可的合法性问题,只有通过制定法律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这是因为,我国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网约车的具体规制方式也会存在差别,的确需要由各地政府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设定差异化的行政许可条件来进行规制。《网约车暂行办法》中授权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制定行政许可条件的立法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其作为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过低,其授权的效力在法理上是存在争议的。即使是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来授权各地政府制定适宜自身的行政许可条件,也会存在违反《行政许可法》的可能。因为《行政许可法》第18条是要求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创设机关)设定行政许可的条件,且并没有授权设定机关可以再将这一权力授权给其他主体。所以,作为法律效力低于《行政许可法》的行政法规也无权授权各地政府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行政许可条件。由此推导,只有制定法律才有可能绕开《行政许可法》的这一限制。因为,假如通过制定法律来设定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并在立法时将设定行政许可具体条件的权力授予各地政府,那么这一立法相对于《行政许可法》来说就属于特别法规定,依据《立法法》所确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法律适用规则,当特别法规定与一般法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遵从特别法的规定,由此各地政府获得的授权才不违背《行政许可法》的要求。
第二,地方立法层面。如果国家层面的立法不能在短时期内调整,那么只能通过调整地方立法来确保网约车相关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比较适宜的方式是修订作为地方性法规的《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修订的内容是将网约车的规制(包括相关行政许可的设定)纳入到这部地方性法规中,使其成为同时规制巡游出租车和网络出租车的地方性法规。并且在修订时要仔细设定《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与《上海网约车新规》中的行政许可条件,确保两部上下位法之间的协调,避免违反《行政许可法》中关于行政许可创设权与细化权的规定。从立法体系上看,这样的调整意味着,《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创设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符合《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款对地方性法规的授权。《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行政许可就可以被视为对该部地方性法规中设定的行政许可的细化规定。
还有一种可以考虑的地方立法思路是将《上海网约车新规》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同时将《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修订成为专门规制巡游(出租)车的地方性法规。这种立法思路与目前交通运输部分别用两部部门规章平行规制巡游车和网约车的思路是一致的。这种立法调整意味着由专门的上海市地方性法规来创设网约车的行政许可,也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虽然以上两种地方立法的调整无法解决与《国务院2004年412号决定》设定的三个出租车行政许可并行的尴尬局面,但是至少理清了上海市区域范围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在设定网约车相关行政许可时确保地方性立法之于《行政许可法》的合法性。以上立法的调整思路也可以为规制网约车以外的共享经济形态提供借鉴。
四、余 论
以上本文以《上海网约车新规》中设定的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为例分析了共享经济中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分析将会对我国各类共享经济新业态的法律规制提供借鉴。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加速车道,诸如共享单车、共享住宿乃至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共享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崭新的共享经济形态亟需法律规制,且对法律规制的本身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虽然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共享经济法律规制的新思路,如“合作监管+自律监管”的混合规制[8]、“增量赋权”规制[9],主张充分发挥各类网络平台的自我监管和调解能力等[10],但这些成果更多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相对缺乏微观视角的探讨。本文则是从行政许可设定这一微观规制工具的合法性入手进行分析,着力探讨共享经济法律规制具体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这一研究可以对今后我国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提供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行政许可的设定是共享经济法律规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然而在设定行政许可对共享经济实施法律规制时,规制机关往往过于重视法律规制的有效性,却相对忽视了法律规制的合法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法律规制的合法性与法律规制的有效性应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否则,即使法律规制实现了预定的规制目标,也会因其本身的合法性缺陷而构成对法治秩序的破坏,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从长期来看对于法治秩序的建设与维系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降低法律的权威性。
第二,由于共享经济的新业态往往与传统业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通过行政许可的设定来规制共享经济时,应当仔细鉴别规制对象是否属于全新的经济业态,这一点直接关系到设定的行政许可属许可抑或细化许可,而这种区分又决定了为确保其合法性而必须遵守的标准:如果属于全新的共享经济业态,应当依据《行政许可法》中关于不同位阶法律文件创设许可的权限,来决定通过何种类型的法律文件设定相关行政许可;如果属于传统经济业态范畴内演变出的新业态(如源于传统出租车业务的网约车业务),那么在设定行政许可进行法律规制时,就应当仔细分析现行上位法中已经创设的行政许可,并在其创设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及期限的范围之内进行细化规定,以确保其合法性。
第三,依据目前《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部门规章没有行政许可的创设权限,这意味着部门规章就法理而言不能创设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许可条件、程序与期限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一规定在立法时本是为了防止国务院下属各部门通过滥设行政许可的方式扩充本部门的行政权力,并且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然而在共享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当下,需要设定的行政许可条件纷繁芜杂且往往十分急迫,必须借助国务院下属各部门的专业优势予以确定,并且繁琐冗长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也无法适用共享经济业态快速发展的需要,本文的分析过程也展现了这种矛盾在实践中的后果。因此建议应通过修订《行政许可法》,规定法律或行政法规在保留行政许可事项创设权限的同时,有权将创设行政许可条件的权力授权给部门规章。这一规定既可以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垄断行政许可事项创设的权力来防止部门规章滥设行政许可,也可以同时兼顾共享经济时代对设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专业化要求。
综上所述,行政许可的设定是政府规制共享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之一,随着共享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这种法律规制手段的使用也将会日趋频繁,如何确保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将会是在共享经济发展中不断遇到的法律问题,本文的写作期望能为今后共享经济的相关立法提供一定的理论积淀。
注释:
① 《行政许可法》制定通过后,其中对行政许可设定权限规定的十分严格,而之前我国行政管理领域中又通过部门规章设定了大量的行政许可,一旦《行政许可法》生效,这些行政许可都将同时失效,行政机关仓促间无法建立替代性的规制途径,这就可能会导致我国许多行政管理领域出现混乱。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国务院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的授权,制定了《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并与《行政许可法》同日(2004年7月1日)生效。
② 当然这一思考径路的前提是证成国务院的决定属于地方政府规章的上位法。虽然上文我们依据《立法法》第82条推定国务院的决定不是地方政府规章的上位法,但是由于我国《立法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国务院的决定与省级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这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论辩提供了便利。依据《立法法》第80条的规定,国务院的决定是部门规章的制定依据,而依据同法第91条的规定,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效力相等,于是我们也可以推导出国务院决定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的效力,属于其上位法。
③ 在《行政许可法》的制定过程中,对于是否赋予国务院通过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是具有争议的,最终之所以规定国务院的决定有权设定行政许可,其主要考虑是依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些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立法的时机和条件不成熟,但又需要必要的行政管理,因此立法授权国务院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临时性的行政许可措施是有必要的。
④ 在《行政许可法》正式生效之前,由于我国没有国家法律层面统一的行政许可设定的规范,因此对于出租车行业行政许可的设定十分混乱,各地并不统一。其中具有全国效力的是由当时建设部和公安部联合制定发布、并于1998年2月1日生效的部门规章—《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该部门规章的第二章中明确规定了出租车经营企业、出租车个体工商户、出租车驾驶员所必需具备的许可条件,并规定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委托的客运管理机构有权颁发出租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三种行政许可证书。
[1] 张卿. 行政许可--法和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爱尔兰]Colin Scott.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J].法学研究,2014,2.
[3] 张志铭,于浩. 现代法治释义[J]. 政法论丛,2015,1.
[4] 徐明.文义解释的语用分析与构建[J]. 政法论丛,2016,3.
[5] 曾哲.行政许可执法制度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6] 沈福俊.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行政许可设定权分析—以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第112项为分析视角[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6.
[7] 王太高.行政许可条件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8] 唐清利. “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J]. 中国法学,2015,4.
[9] 张东. 法治如何促进大众创新创业-基于专车服务微观样本的分析[J]. 法学,2016,3.
[10] 熊丙万. 专车拼车管制新探[J]. 清华法学,2016,2.
ResearchontheLegalityoftheEstablishmentoftheAdministrativeLicenseforSharingEconomy:ChoosingShanghaiRegulationofCar-hailingOnlineasanAnalysisSample
HuangPei
(Law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dministrative license is the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gul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so its legality is also important. The legal review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dministrative license includes two steps: the first step i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icense and the making specific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icense. The second step is to review the legality of the implementing organ, conditions, procedures and time limit of an administrative license. Three kind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s for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Shanghai government’s regulation have some legal defects. The deci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regulation of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the local regulation relation to the three kind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have also some legal defects.
sharing economy;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dministrative license
1002—6274(2017)04—060—09
DF312
A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选择性行政执法的法律规制研究”(17BFX175)的阶段性成果。
黄 锫(1979-),男,浙江东阳人,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责任编辑:唐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