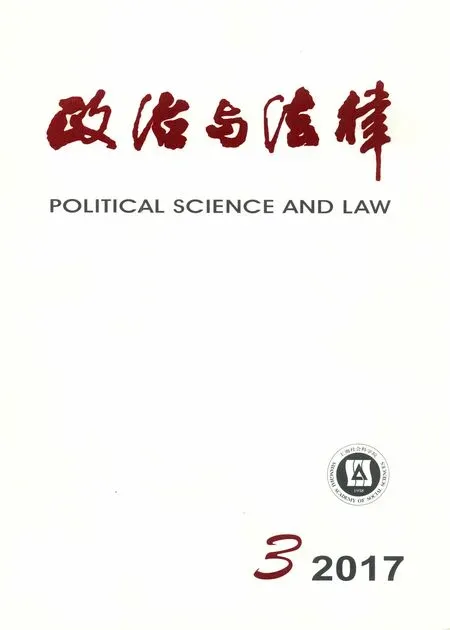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的评价困境与刑法调适*
——以100个随机案例为切入
陈家林 汪雪城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的评价困境与刑法调适*
——以100个随机案例为切入
陈家林 汪雪城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传统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评价标准为“数额+(升格刑)情节”,其中以数额为中心标准,情节依附于数额。对于网络诈骗而言,诈骗次数、被害人人次等等,甚至利用网络发送诈骗信息的手段行为,均属于网络诈骗刑事责任的评价要素。这些变化,现行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均未予以重视,使得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体系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为改变当前以“数额”为中心的评价体系,须以“人次标准+物次标准”的形式对责任刑要素进行必要的扩容,并将其中部分要素置于和数额同等的评价地位,同时,重视一般预防刑,增加其在立法中的考量比重,以弥补刑事惩罚的不确定性,遏制网络诈骗的犯罪态势。
网络诈骗;责任刑;一般预防刑;要素扩容;立法模式
一、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体系的局限性和滞后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由“信息媒介”向“生活平台”转换,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第二空间。*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法学》2010年第10期。网络空间自成体系,具有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0页。其群体遍布全球,具备明显不同于物态社会的特征,故人们一般称其为网络社会或者虚拟社会。对于这种线上线下并存的社会结构,有学者称之为“双层社会”。*于志刚:《网络、网络犯罪的演变与司法解释的关注方向》,《法律适用》2013年第11期。其本质,则是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的无限交融,从而使得现代社会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特征。随着行为失范的增多,网络空间成为全新的犯罪场域。在这一犯罪场域中,不但新的犯罪得以滋生,传统犯罪亦产生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表现形式,使得传统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司法规则处于难以适用的尴尬境地,有学者称之为“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参见于志刚:《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网络社会集聚了数量庞大的社会财富,网络犯罪也更多地转向网络经济领域,诈骗犯罪即为其中的典型。网络诈骗是传统诈骗的网络异化,行为人以网络作为犯罪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产。*在我国学术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与此相关的概念主要有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以及电信网络诈骗,在使用过程中比较混乱,其各自的内涵、外延不甚明确,彼此之间有交叉。不过,一般而言,电信诈骗多指利用短信、电话进行的诈骗,网络诈骗指利用互联网实施的诈骗;电信网络诈骗范围最广,包括利用短信、电话、互联网等进行的诈骗。不过随着电信业务的网络化,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的区分正逐步缩小乃至趋于同化,前者最终会为后者所吸收,从而成为真正的“网络”诈骗。为更为准确地涵盖现行的这类诈骗行为,宜用“电信网络诈骗”,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网络诈骗”为未来趋向,故本文采用网络诈骗一词,取其广义,具体指利用短信、电话和互联网实施的全部或主要行为发生于网络空间的犯罪现象。其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的匿名性和隐蔽性、危害结果的叠加性和扩散性,此为其区分于传统诈骗的最主要特点。在行为流程方面,它亦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设法使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产,这和传统诈骗并无二致。正如学者所断言,源于网络的平台效应,即使某个网络犯罪行为与传统犯罪别无二致,其社会危害性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Maria Laura Sudulich. Digital Citizenship: The Internet, Society, and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 vol.11, no.7, 2008, p.1035.这主要归因于网络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变异作用,具体体现为社会危害性的复制性、聚焦性、扩散性。*参见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社会危害性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对传统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提出挑战,网络诈骗尤其如此。
传统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评价标准为“数额+(升格刑)情节”,其中以数额为中心标准,不达一定数额者不构成犯罪既遂。对于网络诈骗而言,除数额以外,诈骗次数、诈骗时长、被害人人次等等,甚至利用网络发送虚假消息的手段行为,均属于网络诈骗刑事责任的评价要素,其中部分要素的评价位阶甚至不低于数额要素。针对这些变化,现行刑事法律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使得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为此,本文重点探讨以下问题:其一,与传统诈骗犯罪相比,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如何影响其行为方式和危害后果?其二,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遇到哪些问题?对此,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已作出何种调整,尚存在哪些不足?其三,面对网络诈骗的日益猖獗,我国刑事法律当如何回应以及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又应怎样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
二、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其刑事责任评价的司法现状
为了对网络诈骗犯罪有更直观的认识,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随机抽取100个司法案例,*笔者于2016年10月10日,以“网络诈骗”为关键字,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全文检索,时间限定为1997年10月1日到2016年10月1日(共20年),检索到刑事裁判405件,其中一审裁判330件,二审裁判75件,按照分层抽样法,随机抽取81件一审案例,19件二审案例。并利用统计学方法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同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探求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其刑事责任评价的司法现状。
(一)网络诈骗的犯罪特点
网络诈骗以网络作为犯罪工具,自然具备网络的主要技术特点,此即为其行为评价、危害后果明显异于传统诈骗的主要原因。根据网络的技术特点,并结合统计数据,笔者认为网络诈骗具有四个显著的犯罪特点。
1.辐射性和即时性
辐射性是指,网络诈骗以行为人为中心,向全国乃至全球扩散。因此,其多表现为“一对多”的侵害方式,侵害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侵害后果具有很强的叠加性。*参见前注⑦,于志刚文。根据100个案件的统计分析可知,我国网络诈骗的辐射源主要集中于华南地区,占比63%,远高于其他各区域数量之和。其中,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的案件数量分别为25件、16件、12件、10件。
即时性是指利用网络发布的诈骗信息,可瞬时传遍全网,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网络用户均有获取该信息的可能性。这一特性和信息技术瞬时的、非纸面化的交流密切相关,*参见[澳]汤姆·福雷斯特、佩里·莫里森:《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学中的警示与伦理困境》,陆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从而使得网络诈骗行为打破时间障碍,极大地降低了时间成本。即时性的特点说明了网络诈骗犯罪事前控制的必要性。
2.跨地域性
网络诈骗的跨地域性,同上述辐射性相承接,此特点进一步表明诈骗行为的辐射范围不再限于某一区域,而是突破空间限制,以“缺场”的形式对其他远距离区域产生影响。网络诈骗的跨地域性,主要基于网络的两大特点:第一,网络的超时空性,*参见前注⑦,于志刚文。此特性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使地域性解体、时间性消除,产生学者所谓的“流动空间”、“无时间之时间”,*参见前注②,曼纽尔·卡斯特书,第465页。网络犯罪已突破时空限制;第二,网络的无限延展性,此特性可使信息无限复制和快速传输,有助于信息共享,*Thomas J. Holt and Adam M. Bossler. Examin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Lifestyle-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 for Cybercrime Victimization. Deviant Behavior, vol. 30, no.1, 2009, p.22.但同时使得网络行为经无限延展,对其他地区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从上述100个案件的统计分类可知,网络诈骗的行为发生地虽主要集中于华南地区,但影响却覆盖全国,此为其跨地域性的表现之一。同时,通过对100个随机案例是否具有涉域外因素进行统计,发现有6起属于涉外案件,表现出一定的跨地域性。考虑到此类案件的侦查难度和犯罪黑数,6%的比例已然不低,网络诈骗的广度显露无疑。
3.低成本、低风险和高收益
网络诈骗犯罪的低成本,主要表现为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双重低廉。网络诈骗的行为人无需特定的“办公”场所,只需借助计算机、手机等基础设备,就可以最低限度的成本将诈骗性的信息大批量地发往全世界。*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页。同时,由于网络的即时性、信息的可复制性,行为人在编辑少量的原始诈骗消息后,就可经批量复制而迅速地传遍全国乃至全球。
网络社会中,人们多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匿名性给人们提供了逾越社会规范的机会和空间。*参见张彦:《计算机犯罪的多因素分析与犯罪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正是基于这种匿名性,网络诈骗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较低,为诈骗者逃脱舆论监督和刑罚制裁提供了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行为人的个体身份与现实社会中真实身份发生错位与割裂,导致维系传统道德的舆论指向出现错位,*参见于志刚:《虚拟空间中的刑法理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行为人在现实社会中恰可以逃避舆论压力,道德风险直线降低。网络诈骗手段隐蔽,难以侦查,犯罪黑数巨大,导致其法律风险大大减少。据芬·穆勒研究,目前发现的计算机犯罪数和未发现的犯罪数比率是1比10;简·贝克则称,计算机犯罪的发现率仅为1%,*参见蒋平:《计算机犯罪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5-106页。网络诈骗的犯罪黑数当与此差别不大。
网络诈骗多为小额诈骗*参见秦新承:《电子支付方式下诈骗罪的非纯正数额犯趋势》,《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2期。,但其受害人具有群体性(参见图1),使得整体涉案数额往往十分巨大(参见图2),犯罪收益非常可观。*需说明的是,在100个随机案件中,明确提及被害人数量的有77件,载明实得数额的有99件(1件属于诈骗未遂)。此外,在图1中,被害人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有1件,50人至100人的有3件,10人至50人的有16件,共计20件,占比26%;10人以下的虽有57件,其中仅1名被害人的有28件,意味着有29件属于2人至10人。由此观之,网络诈骗被害人确实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在图2中,实得数额50万以上的有12件,占比13%,属于诈骗罪中的“数额特别巨大”;3万元至50万元的有60件,占案件总量的64%,一般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3千元至3万元的有21件,比例为23%,属于“数额较大”。由此可知,网络诈骗的犯罪收益甚高,加之其低成本、低风险,此为网络诈骗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4.群体化和组织化
在网络诈骗中,行为人人数较多,分工明确,日益呈现出群体化和组织化的特点。根据笔者统计的数据(参见图3),诈骗行为人在3人以上的案例有61件,占比61%,为绝大多数;单独作案的仅有19件。由此观之,网络诈骗的群体化特征非常明显。此外,在实施网络诈骗活动中,发送虚假信息、诱骗被害人财产、得逞后银行取钱等等一系列行为流程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其组织化已颇为成熟。网络诈骗的这种群体化和组织化,必然使其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刑法对此当有所作为。
(二)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的司法现状
1.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要素的实证考察
在司法裁判文书中,对网络诈骗刑事责任的评价要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案件事实查明中载明的评价要素,另一类是裁判论理中注重的评价要素。经过对100个随机案件的统计,笔者将其分布情况归纳分类于表1、表2之中。*对这些普遍适用于传统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评价要素,如自首、立功、累犯、未满十八周岁、退还被骗财物等,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本文仅以网络诈骗中较为新型的、一般为传统诈骗所不具备的评价要素为研究对象(“数额”要素除外),表1、表2就是对这些评价要素的统计分类结果。
由表1可知,在100个案件中,载明数额的有99件,未载明数额的有1件(属于诈骗未遂),这表明我国网络诈骗犯罪以数额要素为中心标准的司法现状。载明被害人人数的有77件,占比77%,说明被害人数量属于司法评价中的重要因素。载明诈骗次数的有3件,仅占3%,比例非常低,属于案件查明中有所关注但未予重视的评价要素。表1反映了法院在案件事实查明中的评价倾向,但其最终对网络诈骗的刑事责任如何具体评价,尚需根据表2,对其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表2,法院在对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的个案裁判中,以“数额”作为评价要素的案件有99件,和表1观察结果相一致,说明网络诈骗和传统诈骗相比,其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并无本质变化。但是除数额要素以外,表2中第2种至第8种评价要素,则往往为传统诈骗所不具备,此为司法实践对网络诈骗刑事责任评价体系的部分调整。其中,“以互联网、电话为工具,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虚假信息”作为评价要素的案例有32件,占比32%,远超“数额”之外的其他要素,说明法院已认识到网络对传统诈骗的异化作用,故而将利用网络(电话)的手段行为,作为独立要素对刑事责任评价发挥作用。以“诈骗次数”作为评价要素的有9件,占比9%,为少部分法院纳入责任评价体系,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被害人人数”、“发送虚假信息数量”、“诈骗时长”、“诈骗老年人”、“诈骗财物为网络财产”等五种评价因素,只在1件或2件案例中有所体现,仅得到个别法院的认可。在刑事责任评价作用方面,法院以数额作为评价基础,以第2种至第7种要素酌定从重,以第8种要素酌定从轻。
2.司法实践中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的具体问题
根据表1、表2所展示的实证考察结果,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评价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刑事责任评价要素范围不明,不同法院之间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网络诈骗作为传统诈骗的网络异化,各法院对其认识程度不同,在评价其刑事责任时所注重的要素亦存在明显差别。在表2中,利用网络的手段行为,仅为32个案件所采纳,在具体量刑时予以考量,这意味着其他68个案件并未将其纳入责任评价体系之内。第3种至第8种要素,更是仅为少量法院所认可。由此可见,不同法院对网络诈骗刑事责任的裁判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其评价要素的范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现状显然不利于量刑规范化,有损司法权威。
第二,各要素之间位阶不明,评价比重认识不一。在司法实践中,除数额要素作为责任评价的中心要素之外,其他要素之间的位阶不十分明确。何种要素位阶更高,处于优先地位,何种要素位阶较低,发挥辅助作用,这些在审判实务中并未形成统一标准。表2载明的各个评价要素,在个案量刑中法院多以“酌定从重”予以表述,至于从重的程度、考量的比重则缺乏阐述。此外,部分法院依据表2中某一种要素对行为人酌定从重处罚,其他法院则依据其中两种乃至多种要素才酌定从重。因此,对各个评价要素的不同认识、不同考量,必然导致“同案不同判”,有违同等对待的基本原则。
第三,未区分责任刑要素和预防刑要素,刑事责任评价不甚科学。表2涉及的8种要素,哪些属于罪责评价的责任刑要素,哪些属于社会防卫评价的预防刑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尚未被关注。不同类型的评价要素,在量刑过程中的作用差别甚大,我国颇具影响的一种量刑理论就认为: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先确定责任刑(点),在点之下根据预防必要性的大小确定宣告刑。*参见张明楷:《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以点的理论为中心》,《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对评价要素类型的不同认识,自然影响到责任刑(点)的确定,从而影响刑罚的上限,最终产生结果不同的宣告刑。当然,对责任刑与预防刑要素未能加以区分,存在于整个量刑规范化的过程中,*参见冉巨火:《经验而非逻辑:责任主义量刑原则如何实现》,《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6期。并非仅针对网络诈骗犯罪。然而,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对责任刑要素和预防刑要素的区分尤为重要,在此须特别指出。
三、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的法律应对困境
(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尴尬”转变
1.刑事立法的具体调整
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罪在我国属于纯正数额犯,须以“数额较大”为定罪门槛,“情节”仅作为法定刑的升格要素。因此,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为“数额+(升格刑)情节”,其中数额为中心标准,情节依附于数额。金融诈骗类犯罪刑事责任评价模式与此相同。*信用证诈骗罪除外,其基本刑并未明确要求数额较大。在笔者统计的100个案件中,98件为诈骗罪,2件为信用卡诈骗罪,因未有涉及信用证诈骗罪的情形,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单独探讨。同时,我国《刑法》第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该条反映了立法者的基本立场:网络犯罪只是传统犯罪在网络时代的新犯罪形式,按照现有刑法规定就可以处罚;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形式不增减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有加重或减轻的影响。*参见皮勇:《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网络犯罪立法》,《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犯罪逐渐增多,为了维护互联网安全和信息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12月28日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其中第4条第3项规定,“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定性规定并未超出刑法典原有范畴,亦未对条文适用作出实质性的改动,仅是一种提示性的立法解释。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决定》并未涉及网络诈骗的定量问题,对其刑事责任评价关注不足。
2015年,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将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信息的预备行为实行化,以加大刑法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实现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该罪名的增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立法对网络诈骗关注的不足,其重点对以下两种网络诈骗行为发挥出规制作用:*当然,根据法律规定,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地步。此处情节严重的判断,当以网络安全秩序为中心法益,具体判断时应根据行为人发布信息的具体内容、数量、发布范围、获取的非法利益、受害人的多少、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解读全编——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全新阐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需说明的是,上述“非法利益”、“受害人”,是指基于设立网站、通讯群组、发布违法犯罪信息或者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行为而产生的,其实质上指这些犯罪预备行为所导致的危害后果,至于因后续实行行为所产生的犯罪利益、被害人等,则不在此罪规制范围之内。①为实施诈骗犯罪而设立网站、通讯群组的行为,这类行为仅属于网络诈骗的预备行为,后续的诈骗实行行为则不在该罪名适用范围之内;②为实施诈骗犯罪而发布信息的行为,包括利用合法网站或非法网站发布诈骗信息,这类行为属于“普遍撒网”的预备行为,尚未具体到特定人,否则,就属于诈骗实行行为而不再受该罪名的评价。因此,结合我国诈骗罪的现行规定,可以发现对于网络诈骗行为仍存在大范围的评价空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①利用网络实施诈骗,在仅成立诈骗罪或者同时成立两罪但以诈骗罪处断时,对上述利用网络的预备行为缺乏评价,尤其是欠缺一般预防刑的考量;②当行为人向不特定多数人打电话、发邮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发送诈骗信息时,则不属于上述两类预备行为,无论是否成立诈骗罪,均无法在现行法中得到相应评价;③对于网络诈骗中的犯罪常态,如多次诈骗、被害人数量庞大等情节,在现行刑事责任评价体系中难以获得其应有的评价地位。
2.刑事司法的应对举措
针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应对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发布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第2条、第5条中的部分规定涉及网络诈骗刑事责任评价的调整。
《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了5种酌情从严惩处的情形,其中第1种情形为“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该条第2款规定:“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1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此条将“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行为,作为酌情从严惩处的情形,亦即,将利用网络发送虚假信息的手段行为,独立作为刑事责任评价的从重要素。此举加大了对网络诈骗的惩处力度,客观上可部分弥补上述刑事立法的评价空白,具有一定的司法实践价值。只是这一司法解释已突破立法规定,具备了“二级立法”或者“准立法”属性,*参见梁根林:《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解释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有僭越立法权之嫌,其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均值得商榷。
《解释》第5条规定,*《解释》第5条规定:“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1)发送诈骗信息5千条以上的;(2)拨打诈骗电话5百人次以上的;(3)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1)、(2)项规定标准10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在“诈骗未遂”或者“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如行为人是“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并且发送诈骗信息、拨打诈骗电话达到一定数量或者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以未遂犯定罪处罚。其进步性在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网络诈骗的技术特征,将未达到数额标准但符合特定条件的网络诈骗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之内,亦即,这些“特定条件”作为刑事责任评价要素进入司法者视野,弥补了以数额为中心的评价体系的不足。不过,这种弥补作用十分有限,因为其一,“特定条件”过窄,仅包括“发送诈骗信息、拨打诈骗电话”的数量,而“手段恶劣、危害严重”过于模糊,操作性不强;其二,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诈骗立案难、侦查难,未遂案件往往无法进入侦查程序,根据笔者的统计分析,100件案例中仅有1件为诈骗未遂,这意味着上述第5条规定适用空间十分狭窄,难以发挥弥补立法不足的效果。
为对上述《解释》的规定作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在2016年12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电信网络诈骗作出针对性规定,对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在实体法方面,其重点涉及以下内容:①将电信网络诈骗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起点分别列为三千元、三万元和五十万元,取《解释》中的最低值,以降低入罪门槛;②增设十种酌定从重处罚的情形,*这十种情形分别为:(1)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2)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3)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4)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5)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6)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7)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款物的;(8)以赈灾、募捐等社会公益、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9)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门工作的;(10)利用“钓鱼网站”链接、“木马”程序链接、网络渗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并在具有上述情形的条件下,再次降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起点;③在《解释》中短信数量、电话人次的基础之上,增加网页浏览量这一评价要素,扩充“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④在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时,一般就高选择,并且严格控制适用缓刑的范围、条件,同时更加注重适用财产刑,加大经济上的惩罚力度;⑤对诈骗行为的“周边行为”、“边缘行为”进行概括和提炼,*参见周光权:《精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人民法院报》2016年12月23日,第002版。全面惩处关联犯罪,并就认定共同犯罪作进一步规定。但是,对于完善网络诈骗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而言,《意见》的作用十分有限,除“特定条件”依然过窄、“准立法”属性欠缺正当依据之外,还存在以下问题:①忽视网络诈骗的信息特点和技术特征,将不具有网络关联性的行为作为从重情节,如上述十种情形中的第1点、第2点、第3点、第6点、第7点、第8点,并不具备针对性从重处罚的正当根据;②拨打电话、发送信息的数量认定标准过于僵化,*《意见》规定:拨打诈骗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拨电话。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未考虑到其背后的评价依据乃是人次标准,对同一被害人的电话次数、短信数量重复计算,并不具备合理性,有过度处罚之嫌。
(二)刑事法律应对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缺乏深入的认识,在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调整过程中,应对明显不足,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其次,对“非数额情节”重视不足,以数额为中心的评价体系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长期对经济性、侵财性犯罪在定罪量刑上存在唯数额论的片面认识和做法,导致那些非法占有财物未达数额较大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或者恶劣情节的行为,无法作为犯罪处理。随着刑法典的修正,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和抢夺罪逐步摆脱仅以数额论罪的现状,将更多的“非数额情节”纳入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当中,使得刑事法网愈加严密。然而,对于诈骗罪而言,我国立法者对其缺乏应有的关注,尤其是面对网络诈骗日益严峻的犯罪态势,其评价标准依然局限于数额,导致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犯罪行为评价不能。网络诈骗犯罪具有跨地域、受害者众多、取证难等问题,*参见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在侦办过程中难以将诈骗数额一一查明,尤其是将数额固定于特定被害人更是难上加难,导致大量网络诈骗案件以行政手段处理,无法受到刑事追究。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的增设,虽可以将惩治犯罪的环节前移、及时切断犯罪链条,防止更为严重的后果发生,*参见上注,臧铁伟书,第204页。但正如笔者所分析的,其仅作用于部分预备行为,从而留下大面积的评价空白。对此,应立足于网络诈骗的犯罪样态,扭转以数额为中心的评价体系,提高其他“非数额情节”的评价地位,从而破除网络诈骗犯罪的应对困境。
最后,对一般预防刑缺乏足够的重视。刑罚的目的是预防,*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即便是报应主义的拥护者,亦不会否定刑罚的预防目的。在立法上,应充分重视刑罚的预防作用,通过有目的的立法,减少刑罚的恶害效应,促进社会秩序的良善运行。在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中,将为实施诈骗而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信息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之内,其原因在于设立网站和发布信息通常比其他的预备行为具有更突出的作用,*参见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法学》2015年第10期。更有一般预防的必要性。但是其适用范围过窄,难以涵盖形式各异的网络诈骗行为,而对于这类行为,恰恰处于一般预防刑的评价空白。至于《解释》中将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的手段行为,作为酌定从严处断的情形,客观上弥补了刑事立法对一般预防刑重视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言,我国诈骗罪的入罪门槛为“数额较大”,并无情节方面的规定,其不具备扩充解释的空间。因此,上述司法解释并非“解释”,实质上属于“准立法”,故其连基本的形式合法性都存有疑义。综上,我国刑事法律对网络诈骗的一般预防刑重视不足,对此当有所反思。
四、网络诈骗犯罪刑事责任评价体系的调适:基于宏观思路和具体路径的双重考量
(一)宏观思路:责任刑要素的扩容和一般预防刑的重视
1.刑法调适的基本理念
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技术与现代社会的深度交融,原有的时空观念已不复存在,地域性被打破,时间性被消除,从指尖传出的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瞬时传遍全球,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细微的举动,经过网络蝴蝶效应般的传播,最终产生何种结果,往往难以预测。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刑法作为自由保护、人权保障之法,不能再以完全消极的姿态,无涉于社会管理。对此,刑法应以忠诚于法的市民为对象,*参见陈兴良:《一般预防的观念转变》,《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肯定法规范所认定之价值,*参见柯耀程:《变动中的刑法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借此凸显规范的意义,引导公众按照行为规范行事,以促进刑法的公众认同,从而达到从规范上预防将来犯罪的效果。*参见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与积极一般预防》,《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在刑事立法方面,应提高预防犯罪的有效性,*参见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使刑罚制度根据社会条件以及民众价值不断调适,逐步走向回应型立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应坚持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防止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避免过于激进的、情绪化的刑事立法。
2.责任刑要素的扩容
无论传统诈骗还是网络诈骗,其保护法益均应界定为公私财产,此为衡量其刑事责任的中心标准。只是在传统诈骗中,多表现为“一对一”的犯罪模式,诈骗次数、被害人人数等数量较低,故以数额作为入罪的唯一标准有其合理性。但在网络诈骗中,借助互联网平台,行为人多表现为“一对多”的侵害模式,犯罪样态发生根本转变,对此必须摆脱实得数额的窠臼,引入新的评价要素,对责任刑要素进行适当的扩容。当然,在选择扩容的评价要素时,须以网络诈骗的技术特征和网络特征为基础,避免出现上述《意见》中的不当扩张。
(1)人次标准的扩容
对于诈骗犯罪而言,实得数额和被害人人数应是衡量其责任刑的基本标准,前者是其罪责程度的指标,后者是其罪责辐射广度的指标。传统诈骗中,直接被害人人数一般较少,潜在被害人亦不具备出现的现实基础。但在网络诈骗时代,被害人具有群体性,其单个个人可能仅属于小额受骗,但因人数众多,对人们的安全情感产生巨大破坏,最终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经由网络平台效应的发酵,网络诈骗行为会导致难计其数的潜在被害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造成巨大的危险。人次标准,就是衡量被害人和潜在被害人的标准,是对网络诈骗危害性辐射范围的评价,其中有些标准亦属于对网络公共安全秩序危害程度的判断指标。人次标准的扩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①浏览次数;②点击次数;③注册会员数;④电话拨打人次;⑤短信发送人次;⑥实时通讯工具如QQ、微信等发送人次;⑦通讯群组的成员数量;⑧被害人人数。
(2)物次标准的扩容
(3)责任刑要素之间的位阶调整
在网络诈骗中,各责任刑要素之间并非完全平行,而是存在主次、上下的排列地位。这种地位的判断,以罪责为基本的判断标准。罪责的判断并非事实的、客观的判断,其恰恰属于规范的、价值的判断,受特定时空条件下国民整体观念的制约,对此应根据社会环境的变迁,对罪责的评判标准进行调适。据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应注重责任刑要素之间的位阶调整,以扭转现行的以数额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在以上扩容的诸多要素之中,笔者认为,至少应提高诈骗次数和被害人人数两个评价要素的位阶,将其置于同数额要素平行的判断地位。
诈骗次数,指行为人实行诈骗的次数,此时诈骗已超越预备阶段,对他人财产产生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或实害。笔者之所以主张将诈骗次数置于和数额同等的评价地位,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首先,在一次行为就造成一个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结果的犯罪中,多次行为就意味着造成了多个法益侵害结果,自然就意味着需进行多次刑罚评价。诈骗次数的多少,决定了罪责程度的轻重,当其达到一定标准时,就具有刑法单独评价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此为其法理基础。其次,对网络诈骗形态而言,多次诈骗乃是犯罪常态,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不违反“法律不理会琐细之事”的法谚,*更准确地说,是立法者不尊重稀罕之事,不得以稀罕之事为据制定法律。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第173页。不会浪费立法资源。此为其现实基础。最后,在我国现行立法中,行为次数已经渗透到财产性犯罪中,作为独立的入罪标准,比如《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多次敲诈勒索”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多次抢夺”行为,盗窃罪、抢劫罪则自1997年刑法即将“多次盗窃”、“多次抢劫”纳入规制范围。此为其立法基础。当然,这里的“多次”并非指“三次以上”,而是指在实践调研基础之上设定的较为科学的数量标准。
被害人人数,指实际上当受骗、财产受损的被害人数量,此为诈骗犯罪的终极指向,亦为诈骗既遂的标志之一。无论行为人如何准备,其最终目标均是具体个人的财产,潜在被害人也只有在此时方成为现实被害人,从而成为刑法上具有评判意义的对象。将被害人人数作为独立的入罪标准,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被害人人数和诈骗次数具有关联性,前者是后者的实现形态。诈骗次数的累计,包括未遂和既遂两种形式,其既遂的结果即为被害人的产生。因此,在数量相同的情况下,被害人人数比诈骗次数代表更大的罪量。此为其独立评价的罪责基础。第二,正如笔者在上文所分析的,网络诈骗的被害人具有群体性特征(详见图2),此为其区别于传统诈骗的犯罪样态,因此被害人人数作为评价要素亦具备现实基础。第三,现行法中暂无相关立法例,正是基于立法基础的不同,盗窃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在刑法制定或修改时,均以物态社会为立法基础,其行为次数容易查明,无需以被害人人数为视角进行刑事评价,*对盗窃罪而言,借助网络进行盗窃的行为愈加频繁,其盗窃次数的标准、查明的难度均不同于物态社会中的盗窃。因此,是否将被害人人数引入盗窃罪中,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对于网络诈骗而言,诈骗次数有时难以查明,被害人人数反而可以作为新的切入点,由刑法进行“迂回评价”。同时,诈骗次数和被害人人数并不具有必然的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比如,多次诈骗可能只有一次既遂,产生一个被害人;一次诈骗既遂,也可能产生多个被害人。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评价标准,故在立法时应予以区分。
3.一般预防刑的重视
(二)具体路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应对举措
1.立法层面:扭转诈骗犯罪以“数额”为中心的立法模式
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之所以出现评价困境,其根源在于立法和现实的龃龉不合。传统诈骗以数额为中心的立法模式,导致评价要素容量过窄,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新特点。对此,须从立法层面扭转诈骗犯罪的评价标准,在扩容责任刑要素和重视一般预防刑的基础之上,构建科学的、与时俱进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对此,我国学者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笔者经过梳理,对其利弊作简要分析,以确定当前最为合适的立法方向。
根据是否将网络诈骗单独设罪,可分为区分性立法模式和统一性立法模式,前者又可分为单章节立法模式和单罪名立法模式,后者则可以分为单设加重条款、增设入罪标准和“数额+情节”的立法模式,其内涵、利弊分述如下。
单章节立法模式主张,在刑法中规定专门的网络诈骗罪罪名,作为新的一章,将以网络为工具实施的利用金融信用卡诈骗犯罪、利用计算机系统犯罪及合同诈骗罪等客体有所差异的犯罪形式均纳入其中。*参见杨燮蛟、魏彬、赵雪:《网络诈骗现状与预防体系的建构》,《行政与法》2011年第8期。这有点类似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单罪名立法模式要求,增设电信诈骗罪,并将其划归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参见刘爱娇:《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6期。主张单罪名立法模式的还有: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陈增明、陈锦然、刘欣然:《信息化背景下财产诈骗犯罪的实证分析——基于法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东南学术》2015年第1期;蔡卫宁:《通讯网络诈骗犯罪侦防对策研究》,《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以区别于传统的诈骗罪。上述两种区分性的立法模式,其进步性在于,认识到网络诈骗的信息特点,对其构建不同于传统诈骗的刑事责任评价标准,立法更具针对性。然而,这种立法模式具有根本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其一,过于强调网络诈骗(或电信诈骗)对信息法益的危害程度,*参见上注,葛磊文。将财产法益的中心地位虚化,导致立法目的的偏移;其二,我国已增设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对于网络安全秩序可由该罪进行保护,通过单设网络诈骗罪名来凸显网络安全法益,有重复立法之嫌,浪费立法资源。
单设加重条款是指,在诈骗罪中单设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对利用网络实施诈骗的行为从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即属于此种模式。其“刑法”第339条为(普通)诈欺罪,该条第1款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其“刑法”第339条之4为(加重)诈欺罪,第1款规定:“犯第339条诈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1)冒用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名义犯之;(2)三人以上共同犯之;(3)以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媒体等传播工具,对公众散布而犯之。”由此可知,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对网络诈骗行为仍定性为“诈欺罪”,但在“量刑”时单设加重条款,以加大处罚力度。该立法模式重视网络诈骗的一般预防刑,通过对此类行为从严从重处罚以遏制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其缺陷亦较为明显:其一,未扭转以数额为中心的评价体系,无法解决实践中大量网络诈骗案件难以侦办的困境;其二,对于诈骗次数多、被害人数量庞大的网络诈骗而言,有时须升格法定刑,作加重评价,从重处罚的规定并不能使罪责刑相适应;其三,从重处罚的概括性规定,难以根据各评价要素的地位、数量等具体情况,作出相对应的幅度调整,从而无法实现责任刑要素的扩容。
增设入罪标准是指,仿照盗窃罪的立法模式,增加独立入罪的门槛,从而改变诈骗罪纯正数额犯的现状。对此,须解决的前提问题是哪些标准可作为独立的入罪标准。笔者认为,至少要包括上述论证的诈骗次数、被害人人数较多的行为。至于利用网络诈骗的手段行为,能否不受其他标准的限制,作为独立的入罪门槛,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其一,网络诈骗所侵犯的中心法益是公私财产,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的手段行为,距离法益侵害危险或者实害结果过远,不宜单独入罪;其二,利用网络实施诈骗,其可谴责性和非利用网络的诈骗行为并无太大差异,仅以手段行为而入罪,导致刑罚圈过度扩张;其三,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的增设,一定程度上可评价利用网络的诈骗行为,其并无单独入罪的必要性。对此需说明的是,网络诈骗在对财产法益产生实际影响时,必须作为评价要素影响量刑乃至定罪,此处只是强调手段行为单独入罪不甚妥当。采取增设入罪标准的立法模式,可以转变以数额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同时亦可较好地应对因数额难以查证而评价不能的司法现状。然而,其缺点在于:①基于网络的平台效应,对于数量庞大的潜在被害人而言,其财产权益面临巨大危险,上述立法模式对这种辐射性危险缺乏评价;②根据犯罪样态的不同,增设入罪标准的重点规制对象虽是网络诈骗,但是并未在定罪量刑方面区分于传统诈骗,一般预防刑重视不足;③缺少前瞻性,不具备解释空间,易产生司法僭越立法的问题。
为更为直观地比较上述五种立法模式的优缺点,笔者将其汇总于表3。
经过上述比较,笔者更倾向于“数额+情节”的立法模式,其优势自不待言,现对其劣势的修补作一回应。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因法律用语并非外延明确的概念而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3页。对此须立法者作进一步解释。但在我国当下,立法内容简单、立法技术粗劣普遍存在,*参见原永红、孙炳瑞:《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趋势探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待解释问题过多,导致立法者消极不作为或者难以作为,最终只得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统一解释,司法解释权的扩张有其现实基础。此外,司法解释中“准立法”属性的条款普遍存在,司法解释权过度扩张已为既定事实,并非某种立法模式导致的个例。基于以上现实,与其抨击司法解释过度扩张不具有实质合法性,不如赋予其相应的解释权,在立法上留有解释空间,从而使得司法解释至少在形式层面具有合法性,避免司法解释在形式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依然大行其道的尴尬。至于如何限制司法解释权的过度扩张,则需在我国立法者积极作为时再作探讨,否则只是属于缺乏现实基础的空谈。
2.司法层面:构建“人次标准+物次标准”的责任评价体系
在立法者以“数额+情节”的模式对传统的以数额为中心的责任评价体系作出修正之后,司法者当根据社会实践中的犯罪样态作出更为精细的解释,以将立法规定落实到可供操作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数额”而言,《解释》中已有规定,无需赘言,但是这里的“情节”,显然需要司法机关作具体解释,可以此为契机,构建“人次标准+物次标准”的责任评价体系,从而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首先,“情节”分为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人次标准和物次标准亦存在相对应的评价标准,其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层级差别,至于具体数值的确定,则由司法机关在实证调研基础之上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这里仅对网络诈骗定罪量刑评价体系的建构进行阐述,并对如何具体扩容责任刑要素和实现一般预防刑作重点说明。
所谓“人次标准+物次标准”的责任评价体系,就是指将“情节”的评判标准,分为人次标准和物次标准,并以此对网络诈骗行为的罪与非罪、刑量大小进行判断。人次标准和物次标准,二者相互平行,属于择一的关系,只需满足其一即可。在人次标准和物次标准均达到“较重情节”时,则以其中一种为定罪标准,另外一种调整量刑幅度。当然,如二者之和已突破“较重情节”,达到“严重情节”的标准时,则升格法定刑。此外,数额作为情节的一种特殊要素,当其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时,可配合人次标准或物次标准中的部分要素,构成“较重情节”,对此以诈骗既遂定罪处罚;否则,一般不予定罪处罚。
人次标准和物次标准分别具有独立的评价体系,其内容详见表4。
其次,基本评价要素是独立的“定罪”情节,决定入罪门槛,只要达到法定的数量要求,即可认定为“较重情节”;辅助性评价要素是“量刑”情节,调整刑罚幅度,在罪名成立的前提下,影响诈骗行为的刑量大小。当基本评价要素接近定罪标准,并具备一定的辅助性评价要素时,可认定为“较重情节”,以诈骗犯罪既遂处断。
需强调的是,无论是传统诈骗还是网络诈骗,其数额、诈骗次数和被害人人数的入罪标准应是一致的,因为这些评价要素所蕴含的可谴责性并不因手段行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只是对于传统诈骗而言,一般难以达到诈骗次数和被害人人数的入罪起点,所以其实然层面上仍是以惩治网络诈骗为主。另外,上述辅助性评价要素,恰是根据网络诈骗的信息特征所确定,以此调整其刑事责任的大小,进而将网络诈骗和传统诈骗在量刑方面区别开来,以达到针对网络诈骗进行刑法调适的立法目标。
(责任编辑:杜小丽)
陈家林,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雪城,武汉大学法学院2015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97刑法以来刑事立法理由的实证分析与反思”(项目编号:15CFX02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由陈家林确定主题框架、论证思路、写作结构并修改定稿,由汪雪城统计数据并撰写初稿。
DF625
A
1005-9512-(2017)03-00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