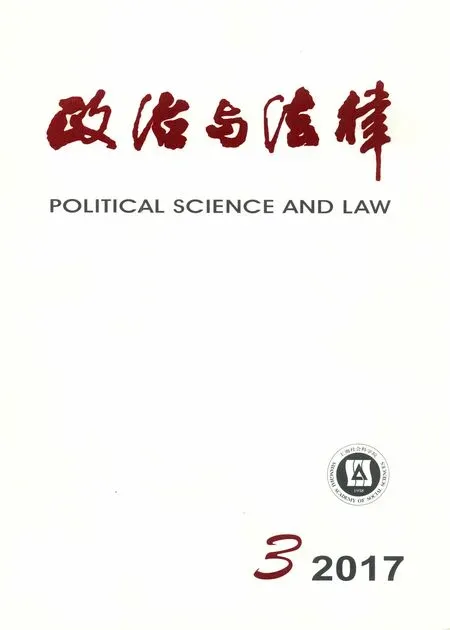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
——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
刘艳红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
——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
刘艳红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受全球化风险社会影响,我国二十年来刑事立法为了应对日益突发的各类风险,也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象征性立法。为了回应国民的“体感治安”,民众的安心感成为晚近以来恐怖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等新型风险犯罪的立法理由。象征性立法因过多地服务于安全目的而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因谦抑不足而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执行不足而损害了刑法的实用主义功能。在风险抗制与刑事治理的紧张关系之中,宜尽量恪守自由刑法的法治特质;刑法相对于其他法的关系应处于“被动式”地位,在站位问题上,属于最后序列。
风险犯罪;安全;象征性立法;刑法功能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至当下被称为“风险社会”的社会,社会结构的变革带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巨大影响和变化。法律作为人类控制社会矛盾的手段,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刑法作为所有法律手段的最后手段,其立法定位与性质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契约与自由为基础的传统刑法学地位尴尬,以风险与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刑法学全面攻城掠地。随着风险概念对刑法的不断冲击,刑法领域中的危险/风险的概念不断扩张,造成刑事立法日益凸显象征性的特征。回望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从1997 年现行刑法的施行到九个刑法修正案的颁布,可以说,中国刑法在尚未完成自由刑法所赋予的法治国自由与人权保障任务的情况下,即已匆匆转换角色步入安全刑法与预防刑法的新境地。如何面对社会结构与法律变革对刑事立法所带来的影响,并评价我国刑事立法的得与失,总结二十年来刑事立法的经验,是当下我国刑事法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一、象征性立法:现代风险社会刑法的应对趋势
象征性立法是现代社会各国刑事立法的共同趋势。自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的命题以来,风险社会便成为当代社会学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贝克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传统农业社会带给人们的安全感被工业化高科技发展席卷而去,网络的发展使世界日益全球化;风险社会也因此成为全球“风险网络体”,世界各国对风险与风险社会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几乎波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制》,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总序第1页。在自然科学之外的领域,催生了诸如风险政治学、风险社会学、风险心理学、风险法学等各交叉学科。风险法学企图通过设立各种法律规范抗制风险,阻止或预防风险的发生,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全目标。各国治理风险最重要的法律手段是公法,刑法作为公法体系中最严厉和最具惩罚性的法律,便率先披上了抗制风险的战袍,被各国立法者频繁使用,风险刑法概念由此产生。风险刑法的最重要方法是,将风险概念刑法化并纳入刑事立法轨道,通过象征性立法来抗制风险。
“象征性立法(symbolishche Gesetzgebung)”概念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及瑞士学者关于立法理论的分析。立法的正当性何在?一部法律除了具备程序合法等形式正当性,还要求具备实质正当性。瑞士学者皮特·诺儿(Peter Noll)指出,立法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出一套解决纠纷的理性方法,*Peter Noll, Gestzgebungslehre, Hamburg: Rowohlt,1973,S.72.而不仅仅是立法过程的正当性。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金德曼(Harald Kindermann)指出,一部法律被赋予的意义在于,立法本身必须要以“目的为导向(zweckgerichtet)”,立法者总是试图让法规范发挥所预设的规制效果以及体现其背后的政策重点,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的,“符合此等条件的立法结果应具有积极影响特定社会活动事实的能力,而让社会导向正面的发展”。*Vgl.Kindermann, Symbolische Gesetzgebung, in: Grimm/Maihofer(Hrsg.), Gesetzgebungstheorie und Rechtspolitik(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13),1988,S.222.德国学者克雷姆斯(Krems)指出,如果立法只是为了作一份“规范申明(Deklaration der Normen),其规范的目的只是国家期待在社会大众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法与不法意识,实质上并不想影响任何个人的行为取向”,那么这样的立法就是“象征立法(symbolishche Gesetzgebung)”。*Krems, Grundfragen der Gesetzgebungslehre, Berlin:Dunker& Humblot GmbH,1979,S.34.可见,象征立法传递的是立法者在特定时空与社会背景下对于社会问题的情绪或者价值偏好,而并不发挥“实质的规制效果”;*Vgl.Kindermann, Symbolische Gesetzgebung, in: Grimm/Maihofer(Hrsg.), Gesetzgebungstheorie und Rechtspolitik(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13),1988,S.225.在此,法只是形式意义的存在,而立法者只是“为了单纯满足社会期待,通过不断修改刑法宣示国家已经着手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来抗制风险,并逐步将公众所认为的风险纳入象征性立法的法规范体系之中”。*Peter-Alexis Albrecht, Das nach-pr?ventive Strafrecht, in: Institut für Kriminalwissenschaften und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 a.M.(Hrsg.), Jenseit des rechtsstaatlichen Strafrechts,,2007, S.5.由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这决定了象征性立法都是建立在“此种立法或许可以消除或者抗制可能发生的风险”这一逻辑基础之上的,因此,象征性立法重视的是对犯罪的积极预防,通过刑事立法拦截风险以防范未然;是事先预防,而不是针对法益侵害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进行惩罚。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Claus Roxin)一针见血地指出,象征性刑事立法“不是服务于法益保护。对于保障和平的共同生活不是必要的,但为了谋求刑法之外的目的,就像安抚选民或者表达国家自我姿态的法律规定”。*[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可见,象征性立法最大的特点是,立法是一种对犯罪施以威胁的姿态或情绪。象征性立法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此种立法不追求刑罚规范的实际效果,而更多的只是为了表达立法者的某种姿态与情绪、态度与立场。
如德国扩大修改《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煽动罪,规定对纳粹整体的国际刑法上的罪行公开地或者在集会上予以赞同、否认或者粉饰的,构成煽动罪,这被认为是象征性立法的典型例子。因为,纳粹行为已属历史,完全或者部分否认历史事实,不承认犯罪,并不损害当代活着的人们的共同生活。该条设立的意义在于,表达德国对于纳粹时代不隐瞒不回避的态度。*同上注,罗克辛文。对于立法者而言,某项立法的颁布重要的不是实际有效地控制某种犯罪,而只是出于政治或政策层面的考虑,对国民所关切的某个领域的安全问题作出必要的应急反应;它们体现的是立法者对国民渴望安全心态的安抚,以及通过快速反应体现出国家与民众同在的姿态,这种姿态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取得国民认同的心理效果,并为国民营造出安全感。另外,修改强奸罪的立法举措则是德国象征性立法新近的典型例证。2015年12月31日,以大教堂闻名的德国西部重镇科隆爆发了一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性侵案。上千名醉醺醺的男子在科隆火车站对女性进行调戏、性侵和抢劫,事件发生后,多名妇女在科隆大教堂前集会示威,抗议新年夜妇女遭受的巨大伤害,愤怒的声音瞬间在全国蔓延,民众对政府难民安置、社会安保及法律现状等各方面谴责严厉。《德国刑法典》第177条原规定为:“以下列方式,强迫他人忍受行为人或第三人的性行为,或让其与行为人或第三人为性行为,处1年以上自由刑:1.暴力,2.以对他人的身体或生命立即予以加害或威胁,3.利用被害人由行为人任意摆布的无助处境。”据此,“任意摆布”这一实质要件成为德国刑法中强奸行为入罪的关键。德国联邦法院(BGH)2012年的一起强奸案判决显示,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没有被德国最高院认定为“表现出强烈的‘不’的意识”,比如没有哭喊、逃避、反击等,是无法被认定为达到“任意摆布”程度的。*参见华忆昕:《德国用修法来回应科隆性侵事件》,《检察风云》2016年第17期。在刑事诉讼阶段,被害人必须就控告构成强奸的罪行做出自我辩护,仅仅说“不行”是不能给被控强奸者定罪的。可见,德国刑事司法对强奸罪认定标准非常之高。在科隆性侵案后,民众的愤怒也转向对强奸罪严格规定的不满,德国政府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决定修改相关规定。2016年7月7日,德国议院通过了刑法修改案,扩大了强奸罪定义,在刑法第177条中增加“不就是不”条款(NeinHeisstNein),亦即,根据受害方行为和语言,“说‘不’意味着没有自愿,也就可以判为强奸”。*《德国将修改强奸法律定义:“不”就是“不”》,新闻,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7-07/7931480.shtml,2017年1月20日访问。这意味着,今后德国认定强奸罪,无须要求被害人行动上的自卫性反击,哪怕只是言语上的不愿意,也可以给被控强奸者定罪;这包括那些类似于科隆性侵事件中突袭式的“团体性侵犯”,因为这类性侵中被害人无法预料来不及判断也因恐惧未能说“不”,此时也应理解为被害人有“不”的意识。然而,由于此次修改,对于强奸罪之前即已存在的老问题,例如如何认定究竟是“不”还是“自愿”,并无多大帮助,同时对于修改之后引发的新问题诸如什么是“团体性侵犯”等又未能解决。因此,虽然德国法律已经做出了对于科隆性侵案的回应,“然而法律专家估计新法通过后,情形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为受害者不愿重温性侵事件,更不愿将事情公开化,再加上很少能找到目击证人,因此取证难度大,导致法庭上经常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难以定夺。这也显示了法律功能的有限与无奈”。*同前注⑩,华忆昕文。德国此次修法充分体现了象征性立法的特点:安抚国民、回应社会以表明政府确保国民安全的姿态,但无论是否修改和如何修改,往往都无实效。
日本刑法也是如此。一直以来,日本刑法只处罚法益侵害行为是其基本原则,“但是,近年来刑事立法的一个特征是,将国民存在不安的行为,广泛地作为刑罚处罚的对象,存在给予国民安心感的倾向”,*参见[日]松原芳博:《国民の意識が生み出す犯罪と刑罰》,《世界》2007年2月号,第53页。从而也开始向象征性立法的方向发展。2013年12月13日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即为适例。2013年1月阿尔及利亚人质事件中有10名日本公民死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涉及人质被困及解救的“情报错综复杂,而且没有可靠的情报”。事件结束后日本自民党认为,“由于日本没有足够充分的法律保护重大机密信息,存在别国政府拒绝提供情报给日本政府的情况”,所以才导致未能成功解救人质。日本政府认为“其他国家觉得我们嘴不紧,所以不愿意把情报告诉我们”,*《日本为什么要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这会带来什么影响?》,知乎网,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203948/answer/31902442, 2017年1月20日访问。既然这样,不如通过国内法管紧自己的嘴巴;同时,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机密信息都给予了特别的法律保护,这也是对国家安全与本国国民负责的体现。为此,日本政府颁布了《特定秘密保护法》。该法规定,国家公务员泄密将被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合谋者和教唆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内阁允许后,特定秘密的保密期限可长达60年。该法的颁布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打击非法泄露本国信息以确保国家与国民安全的姿态,并对泄密行为体现出强烈的不满与谴责情绪,以及对国民受伤心理的精神安慰。事实上,此类事件发生概率极低,阿尔及利亚事件也已过去,该法的颁布对此已于事无补,它的实际目的只是绥靖有权者的感情、粉饰国家的形象等。因此,这一立法被日本学者认为是象征性立法。
日本最近出现的象征性立法则是针对熊本大地震中的盗抢行为而修改盗窃罪的例子。2016年4月,日本熊本发生7.3级大地震,共有47人遇难,1000多人受伤。在大地震中,熊本县灾区已经发生了多起盗窃事件,一些受灾者的家庭和公司遭到盗抢。2016年5月10日,“针对日本熊本大地震中,出现了针对商店、超市的抢夺、盗窃和抢劫犯罪,立法者认为,针对没有任何防备的受灾者实施盗窃行为,要比一般的盗窃更加恶劣,犯罪性更高,可以说是非难性更强的行为。因此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这种行为和一般的盗窃行为进行对比,进而类型化为‘灾害时盗窃罪’,设定更加严厉的刑罚”。*[日]園田寿:《災害時窃盗罪の新設は必要なのか》,http://bylines.news.yahoo.co.jp/sonodahisashi/20160515-00057689/, 2017年1月19日访问。这一立法,就是为了安抚在自然灾害中受盗抢行为二次伤害的日本国民的无助与痛苦的心理,同时也是日本政府急于表明国家对此类行为的立场与姿态。此外,日本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2000年的《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与《骚扰规制法》等法的规定也都存在着象征性立法的问题。
象征性立法对国民精神创伤的安抚性功效,在功利主义社会之中日益被立法与民众双方喜好,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象征性立法的活跃。对此种现象,德国学者温弗里德·哈塞默尔(Winfried Hassemer)指出,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在每一种令人愤慨的状态中,都把刑法作为解决生活问题的神奇武器,并且完全无限地信赖这种神奇武器的功效”。*[德]哈塞默尔:《面对各种新型犯罪的刑法》,冯军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刑事法学的当代展开》,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每当社会中产生风险,立法者即快速动用立法资源,跟进风险推动立法制造新罪名,立法者的惩恶扬善情绪得以表达,捍卫国民安全之态度得以传递;通过这样的立法,国民获得的印象是“采取一些今天能满足公民控制需要的措施就是进行了控制,而不是只有控制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状况导致“把刑法和警察法进行的犯罪控制作为纯粹的安慰剂来接受,完全不取决于控制的有效性”。*同上注,哈赛默尔文。通过立法,国家和民众似乎在此寻找到了实现安全感的共同途径。
象征性立法之所以被频繁使用,原因在于风险社会下公众对于风险的心理态度。类似于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美国“9·11”、英国的疯牛病等巨大社会风险,给全世界人们心理造成了极大恐慌。互联网使世界全球化、事件可视化、传播及时化,“很容易将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传播至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许多人因此认识到风险的存在并因无法预测和控制风险而倾向于向风险制造者“采取严厉的措施,藉以回避风险,因而亦可称为风险嫌恶社会”。*[日]守山正、安部哲夫:《ビギナーズ刑事政策》,成文堂2008年版,第48页。同时,由于风险的不确定和难以预测,尤其是诸如恐怖犯罪这样杀伤力大、计划隐秘、行动迅速的风险,更会令人们生活在一种不安全与不确定感之中,从而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慌心理。民众舒缓这种恐慌心理常常会通过相互议论、媒体上暴露或者发泄自己的情绪、相互猜测或者敌意他人等等方式表达出来,这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这种恐慌被美国学者戴维·丹尼(David Denny)称之为“道德恐慌”,这种恐慌“经由媒体不断传播,造成一些明显不相当或夸大的社会反应,因而形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不安全感下的道德恐慌,它包含疑虑、敌意、舆论、不对称与反复无常”。*[美]David Denny:《面对风险社会》,吕奕欣、郑佩岚译,台湾“国立”编译馆2009年版,第130页。社会层面的道德恐慌直接动摇了国民对国家的信赖,国家无法视而不见。为此,较之于打击恐怖犯罪等投入与成效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的措施而言,动用国家机器行使风险控制的系列立法,无疑容易得多,此举因此成为各国应对风险的最快捷手段。民众的“安心感”或者说“国民生活的平稳”成为立法理由,这种“为了回应国民‘体感治安’的降低,试图保护其‘安心感’,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色彩要更浓一些”。*[日]松原方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作为回应民众不安全的恐慌和不安,象征性立法所起到了公众情绪安抚作用,国家风险控制的表态作用,由此象征性立法似乎寻找到了立法的正当性。
二、象征性立法: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之趋势
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自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大规模的城镇化和飞速的工业化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也步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也许,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还不能说是也可能的确不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风险社会,但中国所面临的诸如太湖污染等环境问题、三鹿奶粉等食品问题、大规模疾病如SARS等疫情问题、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等恐怖犯罪问题逐渐增多,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些威胁社会安全的风险,我国也选择了与同德日等国极为相似的做法,即试图通过立法实现对风险的管控以摆脱风险;其中,刑事立法走在各项立法之前列,并进行了一些象征性刑事立法。纵览1997年至2017年间我国刑事立法的历程,一共颁布了九个刑法修正案,新增了59个罪名,*参见刘艳红主编:《刑法学(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其中有些新罪名或其他修改的罪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象征性立法的特点。
象征性立法之一:恐怖犯罪。近二十年来,我国最为典型的象征性刑事立法当属恐怖犯罪无疑。 “从严治恐”始于2001年 12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三)》),至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时达到顶峰。《刑法修正案(三)》提高了《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九)》又增加了该罪的财产刑;《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第120条之一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为其新罪状,使该罪罪名变更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三)》新增了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 修改《刑法》第66条规定,扩大恐怖犯罪构成特殊累犯的宽松条件;《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5个恐怖犯罪罪名。至此,恐怖犯罪罪名由1997年的1个增加到目前的9个。这些恐怖犯罪立法的特点是,入罪门槛降低,处罚范围扩大,刑罚惩处严厉。
恐怖犯罪刑事立法虽然活跃,但是实质效果欠佳。恐怖犯罪的9个罪名,在实践中司法适用率极低。北大法宝案例库显示,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为止,《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5个恐怖犯罪均为0个案例;其他4个恐怖犯罪罪名的案例数量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为3个,帮助恐怖活动罪为0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3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为23个。这表明,恐怖犯罪的罪名虽然较之1997年现行刑法典刚颁布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是,其司法适用率非常之低,实际效果似乎有限。恐怖犯罪具有准战争的性质,它们多采用武装袭击或者自杀式爆炸袭击,事先布置周密,事后恐怖分子或死亡或逃亡而极难抓获,对之绳之以法的概率很低。这决定了各国打击恐怖犯罪刑事立法的效果也非常有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联合国即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开始制定有关惩治恐怖犯罪的国际公约,至今为止可谓不计其数;但是,伴随着几十年国际社会反恐立法的是频发甚至是愈演愈烈的恐怖犯罪袭击,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刑事法治手段反恐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实质效果。
象征性立法之二:网络犯罪。随着网络空间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二空间”,网络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网络犯罪立法的修改和完善,成为我国二十年来最为活跃的领域。二十年来,经过刑法修正案的反复修改完善,网络犯罪由原来的3个增加为10个。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后,增加了第285条第2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第285条第3款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刑法修正案(九)》对网络犯罪修改最大:一是在《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外,新增《刑法》第286条之1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二是增加单位为《刑法》第285条3个罪名与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主体;三是在《刑法》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有关犯罪的规定之外,新增第287条之1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2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四是修改《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将原“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定罪条件改为“情节严重的”;五是新增《刑法》第291条之1第2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此外,《刑法修正案(三)》新增的第291条之1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既属于恐怖犯罪范围之内,也属于网络犯罪之列。经过反复修改,我国刑法中的网络犯罪入罪门槛更低,处罚范围更广泛。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习惯于将上述犯罪称为计算机犯罪,但是,这一概念不如网络犯罪更有涵摄性和时代性。网络犯罪本身属于高科技犯罪,它意味着既要使用作为硬件的计算机,又要使用作为软件的网络信号,因此,使用科技网络犯罪无疑较之计算机犯罪的概念更为合适。由于计算机与网络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或科技网络犯罪三个概念之间其实不再有特别清晰的界限。
二十年来,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如同恐怖犯罪立法一样,是传达立法者姿态与情绪的象征性立法。恐怖犯罪与网络犯罪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恐怖主义是一种跨国界的全球性现象,而网络则是没有物理边界的虚拟空间,“计算机网络开发出的新型技术可以使用户匿名使用网络、进行秘密交流、利用成熟的加密技术传送或储存数据。这样,全球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实施网络恐怖主义和追求其他国际恐怖主义目标的环境”。*[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页。“网络恐怖主义”或者说“恐怖犯罪网络化”,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参见上注,乌尔里希·齐白书,第298-302页。我国国内的恐怖犯罪与网络使用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目前的恐怖势力主要是境内新疆分裂势力与境外“东突”组织,而后者也是通过怂恿和支持疆独藏独来实施恐怖活动,因此,中国近年来重大暴恐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新疆。与此同时,新疆恐怖主义在境外组织的影响和支持之下,也经历了一个从录像时代到摄影时代,再到网络时代的发展进程。*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东突”恐怖势力个体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网民数量超过千万规模的为26个;在分省网民规模上,新疆的互联网普及率排名第十,基本达到了类似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的水平。*《CNNIC:2016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分省网民规模(三)》,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7年1月22日发布。很显然,新疆恐怖组织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恐怖主义发展在同步进行。因此,一方面,网络犯罪实际上是恐怖犯罪的外围罪名,即除了刑法典含有“恐怖”二字罪名之外的恐怖犯罪相关罪名;另一方面,我国网络犯罪立法如同前述恐怖犯罪立法一样,是刑法“适应犯罪形势变化及其应对的需要,加强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惩治”的结果。为了配合打击恐怖犯罪,作为恐怖犯罪网络化之下的网络犯罪刑事治理,选择了如同恐怖犯罪一样的立法路径,降低入罪门槛,扩大处罚范围,加强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治理。因此,我国的网络犯罪立法和恐怖犯罪立法一样,是“立法回应社会关切”之体现。*记者殷泓、王逸吟:《刑法为什么这样改》,《光明日报》2015年8月31日,第10版。
同样地,网络犯罪立法欠缺实质效果。不同于网络犯罪立法的异常活跃,我国司法实务中网络犯罪罪名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北大法宝案例库显示,截至2016年12月31日,1997年刑法中原有三个网络犯罪罪名,其案例数分别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47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105个;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案例为23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案例为63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的案例为0个;至于《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4个罪名即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其案例数均为0个。虽然北大法宝是“全面精选收录我国大陆法院的各类案例”而不是对我国法院案例的全样本收录,但上述案例数仍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6个网络犯罪的适用情况。这说明,从1997年至今,我国网络犯罪罪名适用率极低。在立法层面上,象征性立法重视的是对犯罪的积极预防,从此角度,网络犯罪立法向社会民众起到了宣示作用,通过明确的法规范的讯息传达,以期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在司法层面,“司法机关依法判决,向国民传达刑法法规的有效性,以儆效尤。传达犯罪会被惩罚与有人犯罪真的受到惩罚的讯息,使有意犯罪但害怕被惩罚的潜在犯罪人,产生心理强制的作用而不为犯罪行为”。*黄国瑞:《刑法在风险社会的课题》,《警大法学论集》2016年3月第30期(台北)。二十年间,在中国法律信息服务的领导品牌、具有最大市场占有率的北大法宝案例库中,10个网络犯罪罪名案例总数仅为240个,而且其中5个罪名的案例数为0个,如此低的适用率显然无法向国民传达“刑法法规的有效性”并发挥犯罪预防的作用,换言之,我国网络犯罪的刑罚法规缺乏法律本该具有的实质效果。
象征性立法之三:环境犯罪。从1997年至今,共有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进行了修改,新增1个环境犯罪罪名,扩大6个原有环境犯罪罪名处罚范围。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二)》)专门针对环境犯罪而颁布,它将《刑法》第342条的犯罪对象在“耕地”之外增加了“林地等农用地”,从而将罪名修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四)》)新增了第152条第2款走私废物罪;将《刑法》第344条打击对象从珍贵树木扩大到“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将该条罪名修改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将《刑法》第345条第3款新增“运输”行为,并删除了“以牟利为目的”的规定,将该条罪名修改为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338条“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删除了《刑法》第343条“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规定,降低了非法采矿罪入罪门槛。以上三部刑法修正案对环境犯罪立法的象征性极为明显。
首先,环境犯罪刑事立法都是立法者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下,以立法手段抗制生态风险的姿态之体现,但对于环境犯罪的治理却难以发挥实效。当今中国环境污染极其严重,水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森林资源遭到滥砍滥伐,雾霾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生态危机时时刻刻提醒着中国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生态风险面前,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还停留在“应急性”层面,立法者急于通过刑法手段抗制生态风险的情绪表露无疑,治理生态风险的姿态明确。《刑法修正案(二)》是“为了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保护生态环境,对刑法有关条文作相应修改和明确法律的含义”而颁布的。*顾昂然:《刑法有关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报告 严惩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 保护生态环境》,2001年8月27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刑法修正案(四)》修改环境犯罪的理由基本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提出近年来某种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比较严重”,以及“有关部门提出,除珍贵树木以外,根据国家关于野生植物保护的规定,还有许多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野生植物同样具有重要经济和文化科学研究价值。近年来毁坏珍贵野生植物的情况较为严重,有人建议刑法对这种新情况作出相应规定”;“有关部门提出,近年来各地加大了植树的力度,林区与非林区的界限已不明显”,“有关部门反映,这类犯罪案件大量在运输环节查获”等。*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草案)〉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刑法修正案(八)》则是为了“加强刑法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保护”。*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2010年8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显然,在“污染控制”这一“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规制领域之一”,中国“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要引入适当的规制措施让国民放心”,*[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学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于是不断修改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以表明姿态,而这正是象征性立法的主要特点。然而,象征性立法对于生态风险的治理效果欠缺。由于生态环境是一种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从被害者角度分析极易遭受侵害,而且,此类侵害行为在发生之前又不易为外界所察觉,等到结果发生之后污染环境事实又已造成,且危害难以短时间消除。这也是为什么刑事立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越来越严,而现实生活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却未有减少的原因之一。当下国人所处的环境似乎也证明了环境犯罪立法的实效乏力。
其次,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使得法益概念更加稀薄,这正是象征性立法的特质。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表明,在“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理论、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生态环境理念等浪潮推动下,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观念正聚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传统刑法的谦抑主义”。*参见刘艳红:《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使得该罪认定不再置重于结果或者实害,只要有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废物或有毒物质的行为就基本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与此同时,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对“严重污染环境”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尤其是,其中“(十)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也是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之一,而其具体内容则并未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修改,意味着我国刑法治理环境污染最重要的罪名——污染环境罪,从结果犯变成了彻底的抽象危险犯。“在环境法上,预防之概念与危险及风险可谓两相左右如影随形”,*蔡志方、蔡达智:《论科技法律之概念与衍生之问题》,《汽车科技安全法制》,正典文化出版社(台北)2010年版,第49页。通过预防环境污染危险进而预防生态风险的发生,而且,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观也由人类中心主义递进为生态中心主义;后者的法益观,是以人类社会对生态安全的保护为宗旨,它是一种集体性而非个人性法益,按照哈塞默尔教授的观点,“如果刑法被用来保护集体性或者弥散性的法益的话,比如说刑法用来保护环境的话,这是很有问题的”,“如果单纯造成自然本身的损害的话,还不能动用刑法,只有侵害了个人核心利益才可以动用刑法进行处罚”,*[德]基墨:《安全、风险与刑法》,江溯译,载梁根林主编:《当代刑法思潮论坛(第三卷): 刑事政策与刑法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否则,将会动摇刑法的根基。
事实上,工业社会的破坏力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石油资源的破坏性开发、海洋资源受到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如果人类不停止破坏性开采,并反思工业社会对利益的无限制索求,未来世界的各种巨大环境风险更是难以预期;仅仅在“刑法典里面将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犯罪化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想要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刑法方案,可能是相当困难的”。*同上注,基黑文。“对于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风险和灾难的行为,我们即使采取最激烈的态度和最严格的措施来反对和阻止它,并且还肯定能够得到官方的全力支持,但是这种反对和阻止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各种努力终究还是有一个限度。”*[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即使在美国,在打击环境犯罪时,“那些主要依靠威慑和机械化施加处罚的执法策略不再受到重用”,“执法重点放在对公司进行法律培训上,帮助公司努力守法”。*[美]尼尔·沙佛、阿隆·S罗特:《美国应对环境犯罪的行政范式与刑事对策》,颜九红译,《刑事法学》2009年第10期。抗制生态风险,最为有效的手段应该是朝着理性行政的方向发展,制定有效的行业、企业、产业生产标准体系,从源头而非从末端抓起,在这一点上,充分运用行政机制的“英国模式”可能值得我国借鉴。*[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 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恐怖犯罪、网络犯罪与环境犯罪,是二十年来我国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根据象征性立法的特征分析,九个刑法修正案中还存在着其他象征性立法。例如,人身类犯罪中的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这三个罪名的案例在北大法宝案例库中均显示为0个,它们对于保护未成年人事实上未能发挥任何实效。又如,财产类犯罪中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也是象征性刑事立法。《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一个“稻草人”罪名,该罪立法也只具有打击欠薪行为和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的象征性意义而并无实际效果。*参见刘艳红:《当下中国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以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为例之批判性分析》,《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再如,《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事故安全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侵犯市场经济犯罪中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虚假破产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虚假破产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贿赂犯罪中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等等。
当然,二十年来我国刑事立法也有许多实效性立法的成功典范,比如,《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刑法》第350条,增加非法生产、运输制毒物品行为为犯罪;《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等。
三、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
以抗制风险为己任的所谓现代刑法日益增多的象征性刑事立法,固然与风险全球化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国际条约下的折中妥协及实现国内政策目标等政治性的考量,主导着各国刑事立法的整体走向”。*[日]高山佳奈子:《“政治”主导下近年日本刑事立法》,谢煜伟译,《月旦法学》(台北)2009年9月第172期。如果各国法治国的理念和目标不变,对这种走向必须予以反思。当今象征性刑事立法已经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和实用功能,如同哈塞默尔指出的那样,它使得“刑法最大的功能在于象征性的功能,而这种象征性的功能成为现代刑法(相对于刑法固有的古典性预测)的共通(且独立重要的)内涵,亦可称为现代刑法的主要功能”,这也成为现代刑法的特征与危机。*Hassemer, Symbolische,2001,S.1001-1019.转引自林宗翰:《风险与功能——论风险刑法的理论基础》,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年7月),第85页。
其一,象征性刑事立法服务于安全目的而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只能保护具体的法益,而不允许保护政治或者道德信仰,宗教教义和信条,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或者纯粹的感情”。*同前注⑧,罗克辛文。象征性立法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安全目标,而不是具体的法益,从而使得法益概念丧失了其本该具有的“告诉立法者合法刑罚处罚的界限”,*同前注⑧,罗克辛文。即合理限定刑法处罚范围的作用。
其三,象征性刑事立法因执行不足而损害了刑法的实用主义功能。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用性与实效性。“法律中所存在着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是以实用性、以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立法的实用性与法的适用紧密相连,立法的实效性与法的效益或者效果紧密相关。
象征性刑事立法实效性的欠缺其实也并非立法本身的问题。风险犯罪的全球性也决定了对它们打击的难度非常之大,以恐怖犯罪为例,出于预防这些犯罪的目的而建立的全球性监管机构常常面临难题。“全球性的监管以多种形式出现,并出现了一系列负载的机构。它主要依赖于犯罪发生地国所进行的刑事追诉。然而,这些国家不愿意赋予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其领土上确定和实现全球监管的权力。”*Shover Neal and Andrew Hochstetler, “Choosing white-collar crime”,New York: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8 、转引自[美]亨利·N蓬特尔、威廉K·布莱克、吉尔伯特·盖斯:《忽视极端的犯罪率:理论、实践及全球经济崩溃》,蔡雅奇译,《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期。没有各国的通力合作,打击恐怖犯罪等以抗制人类社会巨大且难以预料的风险显然难以奏效。当今社会中的风险,或是大国政治或者异教徒政治所致,例如恐怖主义、核危机等,或是工业社会经济过度发展所致,比如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等。对这些风险,不妨将它们还原为或政治或军事或经济问题。企图通过刑法这一法治手段化解或抗制风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对于政治、军事与经济领域的问题,动用法律手段尤其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屏障——刑法手段解决,无异于望梅止渴和小材大用,它将政治军事问题降低为法律问题,将经济问题混谈为法律问题,最终导致象征性立法难以产生实效。
四、结 语
(责任编辑:杜小丽)
刘艳红,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DF61
A
1005-9512-(2017)03-00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