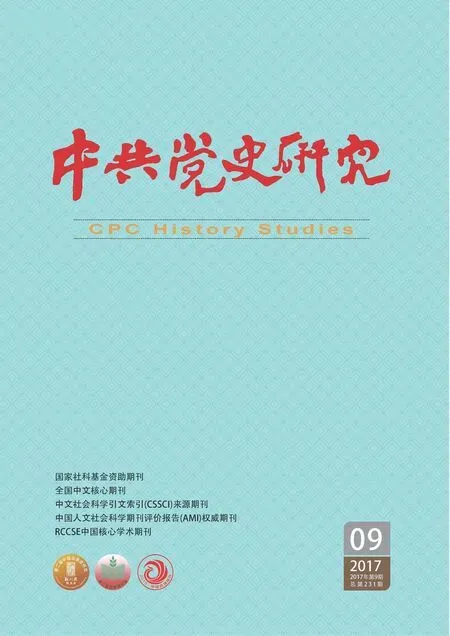抗日根据地的田赋整理*
张 孝 芳
(本文作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北京 100029)
抗日根据地的田赋整理*
张 孝 芳
抗战期间,面对日军的军事压力, 抗日根据地政权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为抗战服务。作为“国家正供”,田赋在各个根据地相继恢复。由于横亘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盘剥者截流了本应该由国家政权统一支配的税赋,根据地政权遂对田赋征收体系进行了整理。这些整理措施包括废除社书、清理粮册和清查田亩等。在民国以来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情况下,根据地政权进一步通过改造村政权来消除这些中间盘剥者,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
抗日根据地;田赋整理;国家政权建设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在日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中共需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出钱出粮,以使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存、发展和壮大。但是,由于历代沿袭下来的积弊陋规,横亘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盘剥者截流了税赋,使得根据地政权难以有效地汲取原本就紧张的社会资源。因此,减少乃至消除这些中间盘剥者在税收体系中的作用,对于根据地政权收入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相对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田赋征收的丰富研究成果,学术界关于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散见于有关各个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论著中。除了关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的一篇论文外*参见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考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目前还几乎没有对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问题的专门探讨和分析。由此,本文旨在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分析抗日根据地的田赋整理,从而展现田赋整理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根本意义,并希望通过新视角的引入来丰富和深化对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与整理问题的研究。
一、税收体系中的中间盘剥者:延续的旧议程
财政是国家政权得以生存的基础。没有财政收入,国家的任何活动都无法展开。而田赋则是中国历代政府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来源。与各种苛捐杂税相比,作为“国家正供”的田赋在征收上更为规范,但仍存在着各种积弊陋规。至少自明代以来,这些积弊陋规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
为了有效征税,明代曾经绘制了“鱼鳞册”来登记土地田亩*“鱼鳞册”亦称“地亩册”。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国子监学生到各地,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召集里甲、耆民等亲赴田亩丈量,将各田亩之方圆绘成图表,写上田主之名以及田之四至,类编为册。由于绘成之图似鱼鳞,所以称为“鱼鳞册”。参见钱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262页。。这种册籍一直沿用到清代和民国时期。即使到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在征收田赋时也要用到“鱼鳞册”,尽管许多地区的这种册籍已经遗失。“鱼鳞册”上田亩各有业主,田亩易主时需要在册上添注。*钱穆:《中国经济史》,第263页。在明代早期确立的里甲制度下,这一税收登记系统可以为政府的税收提供比较简明的基准。但进入16世纪以后,这一税收登记系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官僚、地主在兼并土地时,往往不过户,而将应纳的赋税转移到农民身上。对于新开发的土地,朝廷也没有统一和规范的办法将其添加到税收登记系统中,从而产生了大量逃避赋税的黑地。此外,农民除了缴纳田赋正额外,还要缴纳附属的附加税以及部分摊入田赋之中的兵饷、役银等,税收种类繁多。对于税收管理中的这些问题,明代的政治体系是难以有效解决的。
在明代的官员选任制度下,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只有三年任期。根据回避原则,这些官员往往被委派到距离家乡很远的地方。由于“风土不谙,语音不晓”,地方官员只有依靠中介者或者代理人来完成征收任务。这些官员首先依靠的是县衙中的胥吏。“钱粮文册通常是留给书算手一类文书人员去准备,但对其又缺乏监督。这些下层吏书常年操持部门的日常事务,渔蠹其中,作弊钱粮,这是明代行政管理上的一个突出特点。”*〔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0页。但是,一个县负责税收的吏书人员一般不会超过6人,面对上万的纳税户仍不堪其用。这样,地方官员不得不将征税的实际运作交给各种民间代理人,即“总催”“收兑”“听解”“柜头”等里甲之外的各类民间辅助人员*“总催”负责了解该区内其监管下的所有纳税户的情况并催办他们按时交税;“收兑”负责将里甲所征收的钱粮统一交由运军解运;“听解”从事远距离的解运和税银征收;“柜头”则负责在县衙管理银柜。参见〔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194—195页。。这些税收催办者经常私侵纳税户的钱粮,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作为一条鞭法的主要推动者,明末的改革家张居正希望将所有纳税者置于文官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取代这些中间盘剥者。但是,这些中间盘剥者或代理人在实际生活中仍然被保留下来,或者以新的形式出现。
清代的税收制度是从明代继承而来的。在清代的税收体系中,有两类政府代理人:政府之内的胥吏、政府之外的乡村精英。依赖这两类代理人的协助,地方官员才能够完成征税任务。胥吏被认为是依附于政府和纳税人身上的寄生阶层。“税收已经成为由地方政府内部操纵的一桩油水丰厚的借贷生意。即便人们拖欠税款,县衙的胥吏们也必须按时完成税收指标。于是,他们索性通过发放高利贷来为农民垫付税款,从而将这个难题转变为有利可图的生意。”*〔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73—74页。尽管如此,作为官方体制内的一部分,胥吏在捞取油水之外,也会按照规矩基本完成国家的任务,即在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也会协助地方官员实现国家税收的最大化。
与胥吏有所不同的是,政府之外的乡村精英除了谋求自身的利益,也会同时维护与地方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从而使其在国家税收上的使命大打折扣*参见〔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第159页。。1726年实行“摊丁入亩”后,朝廷废除了里甲制,里长管理税册的职能逐渐由社书(也称“里书”)承担*社是由若干村庄组成的非正式区划,社书是各社负责税收的识文断字之人,担任该职的人包括低级功名持有者、普通土地所有者、衙役甚至无地之人。参见〔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第152页。。由于垄断着赋税记录,社书在钱粮征收和税册编造上经常采取种种舞弊行为,比如 “飞洒”,即减少或消除某些纳税者的税额,将它们“飞洒”到其他纳税者身上。再比如“诡寄”,即以假名登记土地,以便让真正的地主逃脱税赋,或者以一个功名持有者的头衔来登记土地,以便以较低的税率纳税。还有一种是“换兑”,即改变在册土地的等级以提高或者降低税率。*〔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第154页。通过这些行为,社书中饱私囊,为非作歹,鱼肉人民,使田赋征收及农民田赋负担脱离于政府的控制。
在20世纪以前国家财政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各类中间盘剥者、纳税者之间,还能勉强维持微妙的平衡和必要的合作,尽管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促成抗税暴乱的偶发。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家对税收需求的急剧增长,这些以往尚能勉力维持的平衡便被彻底打破了。
自1900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以来,中国的统治者都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作为名义或实际上的发展目标。为了创办新式军队、警察、学校等现代化事业,国家需要筹措更多的资金。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以及30年代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带来急剧的军费增长,使国家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但是,这些对税收的强烈需求并没有真正地带来国家政权的成长和汲取能力的增强。为此,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专门用“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政权建设面临的新困境。
根据杜赞奇的定义,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乡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页。换言之,在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汲取资源的数量增长并不会推动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建立直接统治。
无论是1900年以后的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试图采取各种手段来加强对财政资源的汲取,以提高财政收入。面对来自政府如此庞大而紧迫的税收需求,乡村精英作为国家税收代理人和地方社区成员的双重身份之间的冲突也更加激烈、更难以回避。到了二三十年代,过去那些保护乡村社区的精英只好从公共事务中纷纷“引退”,使得村政权更多地落入那些希望从公职中捞取个人物质利益的土豪和无赖之手。这些人将征税看作是榨取钱财的大好时机。乡村公职不再是可以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职位而被人所追求。相反,充任这些公职的人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赢利型经纪人一样,充任职务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之所在。*〔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乡村》,第115页。结果,横亘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盘剥者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变得更加不受约束了。农民的负担急剧增加,但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资源却更多地为土豪劣绅所占有。
从明代到民国的财政史,正是一部国家政权和各类中间盘剥者争夺财政资源的政治史。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将税收体系重新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是旧体制关于国家建设的议程中根基最牢靠的一部分。”*〔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92页。而随着1937年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中共在政权建设中依然面临这一延续性的议程。
二、战争压力下田赋在各根据地的恢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逐步开辟了多个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政权已经瓦解而抗日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尚未巩固的初创时期,为了筹集战争所急需的财政资源,保障党政军民供给需要,许多根据地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非常规化的方式动员人民出钱出粮。这种动员习惯上称为筹粮筹款,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没收罚款和捐募。
没收罚款是指没收日本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或对汉奸课以罚款,充当抗日经费。抗战初期,在陕甘宁边区、山东根据地、淮南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都采用过这种筹款方式。捐募(又叫捐献、捐助、捐赠、献金等)是用号召、感染、鼓励等方式筹集粮款的一种形式,是在正规税收制度未建立时采用的一种过渡形式和临时应急措施。晋绥边区开展的“四献”(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兵)运动,山东根据地的募救国捐、募救国公债,冀中区募集的抗日救国捐,苏中根据地募的抗日自卫捐等,都是这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95—196页。捐募动员的对象主要是富有者,不过农民主动捐献的也不少。
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过渡办法,捐募与没收罚款虽然能缓解一时之需,但由于各自为政,筹粮筹款缺乏明确的标准,任何机关都可以筹款,都可以乱打汉奸,因而引起社会很大的不安。就没收罚款来说,有的地方在没收汉奸财产的过程中出现同时没收地主和资本家财产的现象,对那些并未沦为汉奸的地主、资本家也采取了捉人罚款的办法,严重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捐募本应该遵循自愿原则,但在一些根据地变成强制性的摊派。比如在冀中区,各地驻军异常复杂,指挥不统一,饷粮一概就地筹拨,流弊横出。“新崛起的各色各样的抗日武装,对于军需供给的解决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正常的办法,一般的情形是粮款草料就地征发,住那里,吃那里,开条子要东西,找对象‘动员’一下是常有的事,数目没有限制范围,也没有标准”*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79页。。晋绥边区在“四献”运动开始后,也曾普遍出现强迫命令、甚至吊打处罚的偏向。地主有的逃跑、有的恐惧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边区因“四献”运动不当而逃到敌占区和阎锡山统治区的富户有900多户,岚县、临县自杀的共有21人。*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同时,所有的开支都靠临时的派款解决,并且随筹随支,因而出现严重的浪费和个别贪污的现象。
总体来看,作为根据地抗日政权初创阶段财政款项的主要来源,捐募和没收罚款不仅造成一系列负面问题,而且筹得的粮款有限,也不稳定,因此无法持续地保障战时供给。随着中共中央对乱打乱罚现象的关注和纠偏,各根据地从没收罚款中所得的收入逐年减少。在陕甘宁边区,没收罚款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1937年为4.41%,在1938年为3.95%,到1939年为1.07%,到1940年为1.62%。*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58页。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曾指出:“漫无限制的、零碎的、频繁的、随征随用的办法,是最糟糕的办法,是使人民不胜其苦,而公家却收入无几的办法。”*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随着抗日政权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和完善,田赋在各根据地相继恢复征收,没收罚款与捐募就下降为财政收入的辅助性来源。
对于各根据地的新生政权而言,找到相对稳定的大宗财政收入来源无疑是生存的第一要务。作为古已有之的旧例,田赋首先成为各个根据地考虑的财政收入来源。田赋至少具有三个优点:其一,在根据地新的税收制度来不及创立的情况下,征收田赋可以沿用现成的惯例和规则。其二,基于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人民将交纳田赋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容易接受。其三,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根据地,田赋是政府可靠而稳定的大宗财政来源。根据地的领导人也注意到这些优点对政权建设的意义,指出:“田赋在最初一个时期是免除的,后来又照征。因为几十年来田赋形成了人民与地方政府的定型联系,而同时取消田赋无补于佃农,反而有利于地主,并减少了政府的收入。”*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78页。因此,许多根据地在建立之初停征田赋这一旧税种后,又相继恢复征收,直到后来一些地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后,才将其并入后者,而山东、华中等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征收到抗战胜利之时。
作为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在边区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宣布恢复征收田赋。1938年3月6日,边区行政委员会向各县发布开征田赋的指示:“今年局势初定,社会稍安,欲为长久之计,对于目前紊乱之财政自不能不速加以有效之整理。兹经本会第二次委员会议议决……各县粮银一律实行征收。”*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第145页。晋察冀边区征收了三年田赋,到1941年将田赋并入统一累进税内。在实行统一累进税之前,田赋是晋察冀边区正式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参见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第45页。
晋冀鲁豫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最大的一个根据地。晋东南、冀南、冀鲁豫各抗日政权机构建立后,陆续取消了苛捐杂税,但仍保留了田赋。各区每年按上忙、下忙两期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田赋在各区财政收入中占据了较大比重。1940年,太行区财政总收入为622926元,其中田赋为466486元,所占比重达到74.9%。*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253页。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将田赋并入统一累进税。
晋绥根据地在1939年和1940年按照旧田赋基础征收银两,每年征收约39万元。1941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曾豁免了全部田赋。但由于财政困难,到1942年又决定继续征收田赋,全年共征收田赋406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9.7%。*《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413—414页。
在山东根据地,田赋是财政收入中的主要项目。各区在开始建立政权时就征收田赋,并着手对旧田赋进行整理和改造。各区征收田赋的做法各有不同,有的按旧银两征收,有的在清查田亩的基础上按亩征收。总体来看,田赋征收逐年增加,成为山东根据地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来源。1940年,田赋收入占财政收入的32.48%;1941年,田赋收入占财政收入的54.51%;1942年,田赋收入占财政收入的51.71%。*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2辑,1985年,第108—109页。
华中各根据地征税征粮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田赋。苏中区自1942年起将田赋与公粮合并,统一征收粮食,在麦收、秋收后分两次缴纳,税率按土地等级来分别确定。1945年,田赋占财粮收入的1/3。*参见《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507页。鄂豫边区行署在1942年重新对户口田亩进行了登记,按田亩分等级征收,田赋改征实物。淮北区则于1941年开征田赋,一次征收三个年度(1939年至1941年)的赋额。征收方法有两种:按土地平均年收获量征收实物、按田亩等级征收法币。1943年秋,又将田赋和公粮合并,改为全部征收实物。在淮南区,自政权建立后,公粮、田赋也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占财粮收入总数的2/3。*参见《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552页。
除了以上根据地,华南敌后的东江根据地在1944年、1945年也相继征收田赋,其与公粮一起成为根据地财粮供给的主要来源。*参见《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566页。
三、田赋积弊的整理
田赋是一个旧税种,随着其恢复,征收中的各种积弊陋规成为根据地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肃清征收中的积弊陋规,使征收趋向合理,也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保障战争供给,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对田赋进行了整理和改进。具体来说,这些整理措施包括废除社书、清理粮册和清查田亩等。
第一,废除社书。田赋征收通常分为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两种。间接征收主要指田赋征收时,需要通过掌握和把持粮名和里甲粮簿信息的社书等中间人来进行缴纳。而直接征收又被称为“自封投柜”,即政府设立粮柜,人民在开征期间自行投柜缴纳,完纳后粮柜即给予粮串作为完粮凭证。在这种征收方式中,征收人员舞弊的机会较小。*李铁强:《土地、国家与农民:基于湖北田赋问题的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为此,各根据地政权在田赋征收时抛开旧的征收人员,由依赖社书乡约等间接征收转向由政府直接征收。
在晋察冀根据地,田赋征收恢复后,就逐步取消了社书的掮客地位,改由政府直接征收。1938年4月,冀中区各县政府,动员社书交出粮食底册后,直接向纳税者开征田赋。这样,“因为采用直接由人民向政府径征处缴纳的办法,所谓‘诡飞寄酒’、‘吃色空’、‘扫部加征’以及‘打网’、‘摆会’、‘卖酒’种种积弊完全剔除”。*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683页。
在山东根据地,1938年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后拟订的土地登记办法规定:废除乡约、地保等操纵征收与附征津贴费、粮串费的做法,代之以村长直接征收。1939年,北海专署公布的征收田赋暂行办法规定:各行署设立田赋征收股,在田赋征收股成立前传令各乡约、保长由各村村长指挥共同负责限期提交,如有置之不理或执行不力者便密派便衣拘留或严办。*参见李炜光、赵云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7页。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即太行区)于1940年发布指示,要求各地以村为单位征收田赋,取消里甲都社代完代收制度,建立县、区、村三级整理田赋委员会,其成员由县、区、村长,财粮负责人及群众团体负责人组成*参见赵秀山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1941年,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发布整理田赋办法,指示所辖各地改正以前有粮无地、有地无粮的积弊,剔除书吏中饱,改革征收方法*参见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253页。。
第二,清理粮册。如前所述,登记土地田亩的册籍是明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册籍本身与粮地的现实情况相差甚远,名不副实。粮簿按“里甲”或“都”编制,粮名多数不以户为单位。有的一家分立数户,有的几户一个粮名,有的沿用祖先名字,到征收时,须向里甲都社的吏人询问,否则无法交纳。根据地政权从社书等中间人手中夺回对这些册籍的控制权之后,仍需要对这些册籍进行清理。在财政工作逐步稳定和走上正轨后,为了使田赋征收有据可依,根据地政权对粮册也进行了整理工作,以达到粮地相符的目的。
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成立后就指出:“过去各县田赋征收办法陈陈相因,积弊甚多,管理田赋的人,故意弄得神奇奥妙,以便专利……各县粮册有的遗失,便无从查考。”1940年12月,推行委员会颁发《整理及征收田赋暂行办法》,并于1941年9月又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条例规定:“粮册未遗失的地方,仍按旧粮册征收,但因粮册之编定多沿用旧法,如几社几甲等,同时花户姓名也不符,有的沿用他祖宗的名字或堂号,有的张三用李四的名字。应按现在区乡村系统,以村为单位另行誊编,同时将花名一律换成现名”;而“旧粮册遗失的地方,应用尽一切方法,向旧日管过田赋的人或存有粮册的地方访查,或收买过来。如物色不到时,可责成各村村长、农救会的主任等,会同各花户将全村地亩钱粮数另行整理,定立粮册”。针对旧制度中粮册存在的大量有粮无地、有地无粮的不公平现象,条例还提出了具体的整理办法:其一,发动有粮无地的花户自行报告,根据钱粮追查地亩所在,追问出无粮之地亩时,即将钱粮过拨有地无粮之花户;其二,发动民众互相举发,政府根据民众报告情形,审慎调查确实后,有地者纳粮,无地者豁免。*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6页。
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取消里甲都社制度的同时,也对粮册进行了清理。晋东南第三专署1940年发布《整理田赋及征收暂行办法》,指示各地对粮册进行整理,要求建立以户为单位的红簿,将原来一家数个粮名合并为一个粮名,原来数户一个粮名据实分开,做到统一粮户。按照统一制发的红簿格式,由有粮花户先自行填报,然后进行复核,统一编制红簿。已逃亡粮户,或有粮无地空粮,经审查呈请县政府核准取消。总之,征收依据是由县、区、村三级整理田赋委员会据实而编写出红簿清册。*参见赵秀山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第296页。
1942年,晋绥边区行署在整理田赋的规定中也提出了清理粮册办法:“有粮册的地区,有粮无地者免征,有地无粮者增派;在遗失粮册的地区,调查登记地亩,按旧标准重新派粮;对旧粮制中的各种中间剥削,一概取消。”*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262页。其他根据地在田赋整理办法中也强调了类似的内容。通过对旧粮册的修正和新粮册的订立,各根据地的钱粮征收工作有了更可靠、更合理的依据,为提高政府赋税征收的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清查田亩。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粮册究竟是否和真实情况相符,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政府对土地数量、质量等基本数据的度量和掌握。税收制度的发展史表明:“如果对土地或者收入征税,统治者也许受益更多,但是他们无法度量土地的价值或者收入多少。因此,在特定社会中,统治者能够课以税收的财富种类决定了他们依靠何人寻求经济资源。度量难度也能提高岁入的提取费用”。*〔美〕玛格丽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页。按照这样的逻辑,清查田亩也成为各根据地政权整理田赋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专署于1938年成立后就拟定土地登记法,准备登记土地,但未来得及实行。1939年,掖县曾自行进行过土地整理。该县原有地亩80万亩,在两个区尚未整理的情况下就整理出75.2万地亩。*《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443页。1941年10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继公布《整理及征收田赋暂行办法》之后,又颁行《清查土地登记人口暂行办法》,要求各级政府确切了解所辖区域内的土地人口数据,以便为推行民主政治,实行公平负担,整理田赋等工作提供切实的依据。*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1985年,第53页。《暂行办法》还详细规定:各地在清查土地时,以官亩确定土地面积,以土地产量确定土地等级,其结果除由土地清查委员会详细审定外,还须经过各村民众的民主决定。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晋东南第三专署在1940年要求各地核实土地田亩数。各户土地数量、土质优劣、每亩产量及各种地每亩纳田赋等,均由各户按统一格式自行填报,并与各村的社账进行核对,还设立密告柜,互相监督。最后,经整理田赋委员核实查明后张榜公布。少报土地或黑地隐匿不报,则处以相应罚金。*参见赵秀山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第296页;《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360页。晋绥边区行署在1940年的清查田亩工作中,将辖区内的所有土地分为水地、平地、旱地三种,并以每种土地的地价将其细分为上、中、下三级,共三等九级*参见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262页。。
相对于华北各根据地,华中根据地建立和巩固的时间较晚,清查田亩的时间也较晚。淮海区在1942年发布《清查田亩实施纲要》,要求以乡为单位组织清查田亩委员会,在业主陈报并核对后对契纸所载数字与陈报数字不符者以及其他可疑者或被检举者予以田亩丈量。土地陈报和丈量的结果都登记造册,以此作为政府征收田赋的依据。“每乡田亩清册及佃户清册造具完毕后,即连田亩登记册、地图等一并送交该区清查田亩督导委员核收。督导委员汇集该区各乡田亩清册及佃户清册送交县财粮科核收。”*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合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2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22页。淮北区行政公署在1944年发布《关于土地复查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土地复查中“确定其收获量,编造串册”,规定“自此以后,个人每年公粮田赋,即根据此确定之收获量,按照税率缴纳粮赋,每年如此,丰年不加,荒年不减”*朱超南、杨辉远、陆文培:《淮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淮南区1941年开始进行土地查登。查登以乡为单位,先“依户求田”,然后按田的好坏分四等。经复查修正后由政府颁发田主管业执照。盐阜区行署则于1942年公布《盐阜区清查田亩暂行办法》,以乡镇为单位,采用土地陈报办法,由业主实地丈量,填写陈报书,据实向乡镇清查田亩委员会陈报。委员会根据各业主陈报,编制乡田亩清册,在本村公布,并随时派遣清查组在各乡镇抽查。经过这次土地清查,全区增加了200多万亩。阜宁县一区增加土地43.9%,二区增加土地32.6%。*《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511页。1944年,盐阜区又开展了土地复查,将租进之田和典进之田都加以清查,将土地收获量分类分等,并在乡、区、县编造土地户口统计表作为粮税征收依据,从而使田赋征收进一步合理化。
作为整理田赋的措施,废除社书、清理粮册和清查田亩是相互联系的,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因地制宜,各有先后与侧重。如前所述,山东根据地在废除社书后逐步清理粮册并清查田亩。在晋察冀根据地,冀中区田赋整理工作相对早一些。1938年就通过按亩课征、调查土地和动员社书交出底册等办法来实现由政府直接向人民征收田赋。*参见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683页。1941年,晋察冀边区实施统一累进税。为了配合这一工作,边区对土地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调查。*参见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第322页。华中的一些根据地则是在清查田亩的基础上废除社书制度,并建立起新的田赋征收体系。比如,苏北区“在清查田亩的基础上,废除了旧的册书、粮吏,废除了中间剥削,实行按田亩种类分等征收并以乡为征收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83页。。又如,盐阜区于1941年“在清查田亩的基础上,废除了旧的册书、粮吏,废除中间剥削,实行按地亩种类分等征收,并以乡为征收单位,这样大大方便了人民,同时也增加政府财政上的收入”*《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2卷,第286页。。
四、田赋整理与村政权的重建
对任何税制改革来说,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事件,也不是单一的财政问题,它必须以权力的竞争、权利的制度化配置为背景*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抗日根据地政权针对土地税收积弊的田赋整理,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因此,整理田赋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清查土地,登记人口,是政权工作之基本工作。为建立巩固的民主政权,确实执行政策的急务,亦为中国民主政治之创举与艰巨任务”*《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第25页。。在这个意义上,田赋整理是抗日根据地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
在整理田赋的过程中,作为基本单位的村政权是根据地各项政策法令最重要的执行和实施者。无论是清理粮册,还是清查田亩,都需要村政权的直接参与和实际操作,如统计和掌握一些基本信息,包括“村里边的人口数目,人的好坏,耕地面积,土地分配情形,产量数量种类,村中副业,消费与运销,参加部队的人数,抗属人数,负担数目,文盲数目,学生数目”等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4—155页。。对于这些人口、生产等方面信息的掌握,都倚赖于村政权组织发挥切实而有力的作用。因此,村政权是否坚强有力,是否严格遵守政府指令,对于整理田赋的效果至关重要。
然而,在各根据地,村政权在政权组织层级中却是最薄弱的一环。如前所述,从民国初年到南京政府时期,许多村政权都落到土豪劣绅手中。抗日根据地所接手的村政权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当时村政权组织悉依旧制——编乡编村,村长副闾邻长制。村政权仍为少数人把持。且以抗战以后,村里的事忙起来了,也难做,因而有许多公正人士不愿意干,逃避当村长的现象到处普遍发生,当选村长村副中有许多流氓地痞,以应付公事。”*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488页。在华中根据地,苏中区“下层机构(区以下)不健全,大部的乡保政权还未经过改造。因此,苏中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头,半封建势力的脚,上面发下去的新民主主义的法令,在下面实行时还是旧的、封建的一套。因乡保长在执行这法令时,还是采用他的老办法”。*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在山东根据地,很大一部分村庄仍由传统势力所统治,即“群众尚未发动,有专门应付上级的一套工农青妇等形式的名义组织,有几个专门应付差使的‘群众头子’;村长有明的有暗的,有雇的也有选的,实际都是封建势力直接或间接操纵的”*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5—107页。。这样的村政权不仅难以有效地动员群众支援抗战,而且横亘在中共政权与纳税者之间,极大地阻隔了根据地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使各项政策法令和行政工作无法有效地推行和展开,严重影响了中共政权对财政资源的汲取和自身组织体系的建立。
鉴于村政权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06页。,改造村政权就成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在对村政权的改造中,各根据地不仅对村政权的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还在村级政权层面进行了民主选举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重构。具体来说,各根据地在对保甲闾邻等旧的制度修正或废除的基础上,建立了村代表会议和村政委员会(即村公所)制度。村代表会议是民意机关与执行机关的统一体。由村代表会议选出村长和村政委员以构成村政委员会,或直接由民选村长与村政委员来担负村政事务。村政委员会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如民政、财政、文教、经建、调解、锄奸、抗敌自卫等。
作为中共在敌后开辟的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各根据地的前列。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开始第一次村选举,选举新村长,撤换旧村长。但此时村政权的机构仍采用编乡、编村形式,村长村副下仍以族姓设闾邻长。1939年1月2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关于村选举的指示信,开始实施对村政权的改造。其一,村公所之上设村民代表会,由村公民每15人中选举代表1人组织之;村民代表会于每月月初开会1次,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会议主席由代表互推之;村民代表会于村民大会闭会期为村最高议事机关;村民代表会遵照村民大会决议,计划全村之行政。其二,村公所之下设调解、经济、生产、教育4个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1人,总理该会事务;其中经济委员会负责编制预决算,指导合作社,合理负担,优待抗属,征收公粮、公款。*参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07页。在村选举基础上产生的村政权不仅健全了组织机构,还明确了各自的职能任务,使繁杂的村政各项事务有了专门的执行机构,极大地方便了根据地各项政策法令和抗战动员的上传下达工作。
在改造村政权的基础上,根据地的财政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提高了汲取社会资源的有效性。1939年11月,平山县颁布村合理负担办法:村民先据实自填民产土地登记表1份,交村公所经评议会核定。村合理负担评议会由村长、村副以及各委员会主任、代表秘书、各团体代表以及村民互推的代表等组成。评议会完成核定后,将评议分数公布于众,召开村民大会通过后施行,并由评议员签字以防止舞弊。*参见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第160—161页。通过村合理负担评议会的组织,村政权能够较准确地核定土地价值和土地收入,其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村政权改造措施实行后,虽然村政权发生了质的变化,但由于“闾邻制的未加破坏”,“村代表会与村公所分设,行政力量仍不够强”*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489页。。在村政权改造仍不彻底的情况下,当日军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时,刚刚整理就绪的村财政又发生了紊乱自流的情况:“在村政权经过改造基本群众掌握了政权的村庄,由于这些新起来的农民,对管理财政没经验,不注意花钱,花钱随便,不习惯遵守制度,因而发生了混乱浪费现象。在村政权改造不彻底的村庄,政权仍为落后势力或投机分子操纵把持,他们对抗战没有信心,只抱着抓取势力,乘机发财,准备将来过好日子的念头,于是任意花,随便派,财政不公开,负担不合理,贪污浪费种种黑暗现象,还严重的存在着。”*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687页。这样,村政权仍需要继续进行改造。
1940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为进一步强化村政权,不仅废除了闾邻制,还明确规定村代表会为村政最高权力机关,其主席、副主席即兼任村长、村副。在闾范围之内,由公民代表互选1人为闾主任代表,辅佐村公所执行村政。1941年,边区实行编组行政村,确定以户划分。1个行政村,不超过5个自然村。*参见谢忠厚、居之芬、李铁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第151—152页。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将村公所的各委员会的设置重新加以确定。鉴于筹集钱粮的责任很重,这次调整将经济委员会分为财政委员会与粮秣委员会。村公所改设为民政、财政、教育、粮秣和生产5个委员会。在改造和强化的基础上,村政权的结构和来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晋冀鲁豫根据地也根据抗战需要对村政权进行了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了对村财政的稽查与监督。1942年,冀南区由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两头缩小,游击区增大,绝大多数村庄采取了两面应付的办法。因此,掌握村政权的两面派,争取革命的两面派,成为村政权工作的主要部分。*参见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2辑,山西大学,1981年,第184页。1943年4 月,边区政府颁布《关于村财政委员会暂行组织办法与工作规则的通令》,规定由村财政委员会负责推行村财政,其任务包括:清丈土地、评议负担、整理与保管各种统计表册;经征、保管、解交边区粮款、地方粮款及报告会计事项;整理登记保管与征收村公产公地等*参见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461页。。1943年,冀鲁豫区又公布《村级经费制度草案》,规定村公所不准随意向民户摊征钱财、粮秣、物品,凡属田赋、公粮、公款、公柴等之征收,应完全遵照县政府命令之规定办理,不得私自增加或减少数目*参见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四),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501页。。对于对钱财粮秣负有直接责任的村财粮委员会或财粮委员,冀鲁豫区特别规定:“在任期内如有非法行为,或违反上级政府法令,或损害人民利益,或违反财粮制度,经人民告发或被查觉,得由当地政民领导监督全村另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四),第502页。在改造村政权的基础上,这些措施有效地规范了村政权的财政征收行为。
山东根据地也对村政权进行了改造工作,其做法与晋察冀根据地类似。根据1941年10月颁布的《关于村政组织与工作的新决定》,山东根据地取消了中心村制,代之以行政村制:“凡自然村户口在百户以上,人口在四百人以上者,即化为一个行政村,为村公所下之一个行政单位。凡百户以下之小村,应与附近之其他小村合编为一个行政村”。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为村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由村中每15人成立1个公民小组,选举代表1人组织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闭幕后村政权属于村公所,村公所下设村政委员会和村长村副各1人。同时,修正以户为单位的邻闾保甲制度,取消邻级,改为15家为一闾,直接受村公所领导。*《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第394—399页。随着战争情势的变化,山东根据地的村政权也出现了分化。为此,根据地在实践上分门别类地加以改造:对传统势力统治的村庄,在村中寻找积极分子,撤换原有村长,指派比较进步分子或临时由群众推选1人充当村长,开展群众工作;对中间性质的村庄,即“减租减息不彻底,村政多贪污,封建势力或明或暗的操纵村政”,则是反贪污,查减增资,反恶霸;对已经过民主改选的村庄,则发动群众对村干部实行民主检查,解决群众要求,通过批评教育来改造具有新官僚主义和办事不公的村干部。*参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4辑,第105—107页。通过对村政权的改造,山东根据地在基层财政管理上开始走上正规化的轨道。
在晋绥边区,1940年1月行政公署第一次行政会议确定了村长民选原则。1941年3月至5月间,在边区各地进行了普遍的村选运动。根据对兴县等11个县55个行政村的调查,这次村选运动后产生的村长中32%是中农,54%是贫农,14%是地主、富农。*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3页。村选后,大批英雄模范和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取代了原来村里大量不负责任的或者违抗懈怠的落后分子。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在条件成熟时对村政权进行了改造。在苏中区,行政公署先是撤换旧乡保长,委任或民选新的乡保长或加派副乡长,随后把建立在个人负责上的乡、保、甲改造为乡政府制。这种新乡制度包括三种类型:正规民主新乡制,半正规的民主新乡制,临时的乡镇政府。*《苏中抗日根据地》,第223页。
根据地对村政权的改造极大地强化了中共和边区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拉近了中共与农民的距离,使村政权成为中共开展乡村工作的强有力助手。不仅群众对村政权的监督和参与大大增加,而且村政权执行政策法令的能力也显著增强。“有了村政委员会和简单的分工之后,较之以前村长个人突出的情形好多了。例如在征收田赋、公粮工作上,往往只要几个钟头就可以完成一个行政村的征收工作”*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3页。。村政权的加强使政府能够切实掌握田赋征收所需要的可靠信息,从而在没有大幅提高田赋税率的情况下就能有效增加田赋的征收数量。“田赋的增加,与土地等级提高总平均产量加大有直接关系。所以主署决定增加1%之田赋,在表面看来是很少的一点,但实际上今年的田赋比去年增加52.12%,即一半以上。这明显的看出,田赋的增加还是由于地级提高的原因。”*《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第172页。这样,随着对村政权的改造,农业社会中最基层的政权被有效地纳入根据地政权的行政网络中,使得根据地政权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五、结 语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各种政权组织形式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对物质资源的汲取。本文的研究表明:在频繁而残酷的军事斗争压力下,抗日根据地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援抗战,因此形成对财政资源汲取的极大需求。在政权初创时期,临时性的筹集粮款方式——捐募和没收罚款,由于其随意性和强制性不仅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而且无法持续。为了筹措更多的物质资源,中共开始探索财政收入的正规化和制度化模式,在各个根据地相继恢复田赋征收。但是,田赋征收中历代相承的积弊陋习使根据地政权无法最大限度地汲取社会资源,而横亘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社书等中间盘剥者实际上截流和分享了本应由国家政权统一支配的社会资源。为此,根据地政权通过废除社书、清理粮册和清查田亩等手段进行了田赋整理,以减少这些中间盘剥者在税收体系中的作用。鉴于村政权在田赋整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根据地政权又进一步通过改造村政权,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健全和充实村政权的结构和职能,建立起和农民的直接联系,从而更有效地渗透入乡村社会,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共在根据地财政征收和资源汲取中采取的一系列肃清流弊的举措,不仅有效地减少甚至部分消除了各种中间盘剥者在政权和纳税者之间的阻断,而且使政权在乡村社会得以扩展和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突破国家政权内卷化开辟了道路。
抗战时期是中共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转折期。在抗战中所开辟的根据地政权开创并积累了中共走向全国性政权的基础和经验。1949年以后,中共在税收体系中消解中间盘剥者的努力仍在延续着,其范围从根据地扩展到全国。如同孔飞力所揭示的,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通过其“作为”而使一大部分税赋收入到不了国家手里的“国家代理人”阶级,而统购统销的实行则更沉重地打击了那些中介者,从而保证了国家对农民剩余产品的占有份额。*参见〔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93—98页。在这个意义上,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对税收积弊的斗争延续了至少自明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个旧议程,开启了将税收体系重新置于国家政权控制之下的新努力。
TheRestructuringoftheAgriculturalTaxSystemintheAnti-JapaneseBaseAreas
Zhang Xiaofang
Facing military pressure from the Japanese army, the local state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had to mobilize as many social resources as possib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a normal state tax, the agricultural tax system was reestablished in these areas. Since the middleme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easants withheld state revenue, the local state in these base areas restructured the agricultural tax system. The local state took measures, such as direct expropriations, the cleaning up of the grain books, and carrying out land inventories, in order to restructure the agricultural tax system. In the case of the in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regim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ocal state in these base areas eliminated the middlemen by restructuring the village governments, thus more effectively realizing direct rule by the state in rural society.
(本文作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北京 100029)
D231;K26
A
1003-3815(2017)-09-0030-1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嬗变”(11CDJ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王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