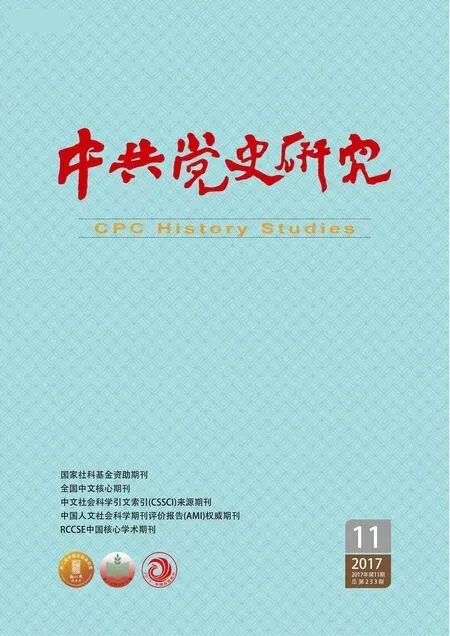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新文化史与中国红色文化研究
魏 本 权
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一脉,红色文化理应纳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新文化史将全面拓展红色文化研究的领域,诸如革命年代留存的日记、图像、绘画、木刻、肖像、标语以及歌谣、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革命节日、民俗、习惯、信仰、休闲娱乐、社会心理、群体与个人心态、思想观念、价值观等行为文化与心态文化,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及生活方式,以翻身、解放、民主、自由、革命为中心的新式话语系统,围绕服装、发饰、放足、婚姻等为中心的身体建构,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文化等等均可纳入研究视野,研究者可以解读革命文化生产、传播、接受的基本元素、表征与符号,有关图像、文本、话语如何体现生产者的革命心态、价值观念、信念信仰,并为大众默化、认同和接受;解释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关系;大众文化在革命动员和日常生活变迁中的作用,大众文化进入日常生活的途径与机制;提炼中共在抗战时期掌控文化领导权与话语权的基本策略,如何将以革命理念为中心的大众文化逐步建构为主流文化。可见,新文化史可以为红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包括心态史、记忆史、时间史、空间史、身体史、医疗史、环境史、日常生活史等新的研究形态,将有效地再现革命潮流中鲜活而立体的大众日常生活,呈现传统文化史与革命史研究所忽略的大众文化场域。同时,新文化史还将为红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如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方法,前者可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梳理红色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后者将突出红色文化的先进性与时代性的研究;文化发生学、文化生态学则注重考察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近百年来红色文化演变发展的文化生态,揭示红色文化现象的成因;微观史研究方法则可以在宏大历史命题之下进入革命年代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世界,以个案方式解读大众文化;口述史和田野调查则可以倾听革命年代健在者对当时生活的理解、感受和体验,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还原大众文化;其他如社会记忆理论、符号学、叙事学、大众文化研究等都可成为相关的方法论资源。总之,新文化史视野下的红色文化研究,应秉持开放的学术心态,坚持和倡导跨学科导向,尊重历史,注重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研究的深入。(吴志军摘自《红色文化学刊》2017年第1期暨创刊号,全文约12000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反转”现象研究
姜 喜 咏
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早期传播进程中,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反转”现象:十月革命前,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和地域,都热烈拥抱马克思主义,争相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了无功利和偏见的较纯粹的学术批评,展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尊敬和热忱,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鲜明地突现出来,历史主体的阶级意识和身份也愈加清晰,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队伍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开始转而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反转”原因的梳理很清楚,但多将“反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看待,而较少注意到它也具有历史事件的性质。实际上,只要看到“反转”现象具有鲜明而公开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其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某种断裂,无论从传播学、历史学还是政治学角度看,它都不仅仅是一种密集短促的历史现象,而是形成和具备了“历史事件”的基本特征,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传播事件或政治事件。在这样的观念和视域下,“反转”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局面和传播主体的反转,而且是传播性质的反转,它标志着一个旧的传播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传播阶段的酝酿与开启,这显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具体阶段及其性质。“反转”现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属性,即文化性居于主导地位,政治性一度尚未被涉及或没有被自觉地注意到。“反转”现象的最终发生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构中存在着的政治性与文化性发展的不平衡常态,即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属性,文化性是建立在政治性基础上的,是次要的或派生的属性。因此,“反转”现象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存在着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裂与悖论:一方面,政治认同高于文化认同,简单地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以及随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是很片面的;另一方面,政治上出于现实阶级利益的考量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而文化上却还是认同的,文化认同在非无产阶级的进步派那里有可能处于深隐状态。(吴志军摘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全文约11000字)
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
黄 道 炫
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敌后根据地面对日军武力“清剿”,生存困难。中共开展政治、社会、经济的全方位抵抗,与日军周旋。由于在军事上居于劣势,要想“拿大兵力把敌人打垮打开局面,是不可能的”,维持相持的平衡局面,是中共这一阶段的目标;而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日军要想彻底消灭自身控制区域里的中共武装,改变这种平衡关系,也无法实现。这种状况形成了一种看起来摇摇欲坠却又坚持不倒的平衡,是为“弱平衡”。看起来是强弱分明的不对等均衡,现实中却又意外地坚韧。这种弱平衡状态的形成和延续,除了中共的努力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包括战争的国际性质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达成弱平衡的关键。要在敌后生存,必须坚持战斗,不可游而不击;由于自身居于弱势,这种战斗又必须以有利为原则,不能以损害自身生存为代价。中共在敌后顽强坚持的结果,就是他们顺利通过大考,渡过难关,积累了全方位战争的宝贵经验和人才资源。事非经过不知难,当年中共在日军眼皮底下的生存,远非想象中那样简单。日后宣传不断重塑的抗战形象,随着凯歌行进一面的不断突出,历史现场中的艰难困苦却有意无意中被慢慢淡化,以致中共敌后战场的抵抗决心、艰难程度及生存价值等都受到怀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学术化的历史研究还是普及性的政治宣传,一旦无视历史具体情境中的曲折复杂,都会成为准确认知的大敌。(吴志军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全文约32000字)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研究评析
代 红 凯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研究既包括对《年谱》编纂特征和学术价值的研究,也包括基于《年谱》而开展的对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历史实践的研究。目前学界关于《年谱》的研究呈现多学科切入、多维度展开和多层面进行的特点,并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但关于《年谱》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限制。如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整体上呈现横向宏观审视居多、纵向深化梳理缺乏的特征,很多研究成果缺少鲜活感和动态感,忽略了毛泽东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的精彩细微之处,无法触摸并展现思想、历史和逻辑的深处结构。而《年谱》则在一定程度上细致呈现了毛泽东相关思想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故而利用《年谱》的丰富史料,拓宽毛泽东研究方式,重视纵向深化和细微梳理毛泽东相关思想的发展演变史,分析其相关思想的来龙去脉,在重要历史关节点处的历史嬗变等,无疑能够增加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刻度和鲜活感。又如,目前学界对《年谱》的研究还存在文献材料使用单一的弊端,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某些党史和国史问题时,往往只参考选用《年谱》这一种文献进行论证,这就大大降低了《年谱》研究的丰富性和说服力。鉴于此,研究者应该在反复研读《年谱》的基础上,重视与其他中共重要领导人年谱之间的比较分析,重视各种文献材料之间的印证互补,这无疑是进一步深化《年谱》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吴志军摘自《毛泽东研究》2017年第4期,全文约1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