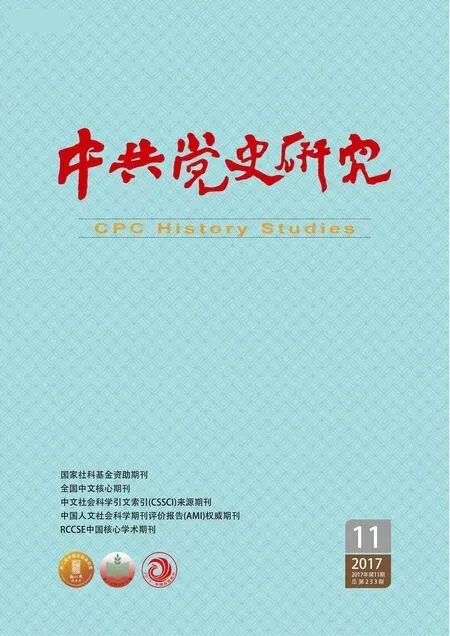中共党史领域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思考*
陈 红 娟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1)
中共党史领域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思考*
陈 红 娟
20世纪以来,英美哲学历经“语言学转向”,不少学科都尝试运用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反思与自我建构,历史学亦不例外。当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概念史研究范式运用到中共党史领域。然而,党史领域哪些概念值得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则尚待厘清。“词汇必须经过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被使用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和认可,才能成为‘概念’”*李宏图、周保巍:《概念史:观照现实的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3日。,但并不是任何一个概念都能够成为概念史研究的对象。概念史探讨的是那些在中共历史上发挥着“基本”作用且具有社会进程指示器、推动器功能的“概念”。当然,这些概念应具有回溯性和前瞻性,否则恐难以从“史”的角度加以开掘。笔者目力所及,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概念值得研究。
(一)时代转换过程中消解与重生的概念
概念是对“经验事实”的社会性描述,不同概念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附,共同支撑着特定时代的社会共识。然而,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启都意味着在以往形成的社会共识解构的同时,新的社会共识得以生成。在时代转换中,贯穿两个时代的概念将面临着新的转变:一方面被质疑、批判,以解构旧时代共识,另一方面则连接新的经验、价值、预期,以建构新时代的共识。这样,概念在见证时代转换的过程中,本身亦沉淀着“历史印记”,经历了弱化、消解、赋义与重生的变迁。概念的变迁是概念史研究的重点,那些经历了时代转换并在日后成为中共话语体系核心的概念都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中共党史发展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主题,而“只有在语言阐释的基础上,社会才得以认知、理解和重塑自己”*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概念见证并参与了党史时代主题的转换,经历着消解与重生的“磨难”,改革开放领域的概念史研究便十分典型。过去党史学界主要从政策、体制变革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而思想解放方面研究较弱。事实上,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毕竟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需要在思想上肃清“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歪理邪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首先表现为重新启用、扶正那些一度在以“革命”为主题的话语体系中被打入另册的概念,并在新的语境中赋予它们以新的政治意义。
研究改革开放领域的概念史,可以发现以下典型现象。一是表达同一概念的态度发生强烈反差,既可由“褒”至“贬”,亦可由“贬”至“褒”。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流行的“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等于资产阶级法权论”,“生产力”“按劳分配”是与复兴资本主义相关联的“负面”“贬义”的概念。但改革开放后,“生产力”“按劳分配”等概念则在定性上脱离与“资本主义”的正向关联,实现了语言色彩由“贬”至“褒”的逆转,成为中共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二是在建构新共识的过程中,概念发生退场与入场的新变化。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诸如“对立”“斗争”“矛盾”等一批曾在革命话语体系中使用频繁的概念逐渐退场,而诸如“物质生产”“市场”“商品”“资本”“私有制”等一些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概念则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一度被遮蔽的语义再次被激活、复述、修正、赋义,并最终融入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时代转换中,中共如何实现概念从过去的否定、批判到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审视、予以肯定的转变?中共赋予这些概念以哪些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中共在使用、锻造这些概念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对旧有价值观念的改造?研究时代转换中概念的消解与重生,将展现“概念”使用标准、语义指涉范围、表达态度等方面的变化,从微观层面重现概念如何经历延续、变化与革新并最终成为党史“标识”的过程。
(二)跨文化过程中移植与嬗变的概念
任何概念只有置于特定语境才有意义,脱离语境的概念并不存在。概念本身具有语义承载能力,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将融入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而概念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移植与嬗变,在不同语境下产生“一体性”与“差异性”,“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其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原始意义与衍生意义并存一体,但隐蔽了差异性。分析概念的这种‘一体性’与‘差异性’及其关系,就成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中共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基本上建立在对日本、苏联或者西欧等渠道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加以融合、延续、承转与批判的基础上。由日本、苏联、西欧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不仅构成了中共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前理解”,而且成为中共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基础。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融入中共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从西方语境、日本语境、苏联语境跨入中国语境的时空挤压。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跨文化过程中的移植与嬗变,研究者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被重新诠释,面临着消亡、延续与革新等不同的命运。一是经历传播、使用但最终被实践抛弃而消亡的概念,例如源自苏联语境的“苏维埃”。二是概念助力中国革命,被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所吸纳、融汇,获得历史性延续,例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等。三是中共要让马克思主义概念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概念,必然要剥离概念在其他语境中沉淀的文化、惯习、政治诉求等,赋予其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意义。这些概念经过中共审视、批判、改造,最终被沉淀着中国革命经验的新概念所替代,比如“中心城市暴动”被“农村包围城市”所革新。因此,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源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相比,必然产生差异。而只有厘清跨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探讨中共塑造新概念、赋予概念新意涵和政治功能才成为可能。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跨文化中的原初指涉及其在时空挤压下发生的嬗变是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如“阶级”“阶级斗争”“资产者”“资产阶级”“无产者”“无产阶级”等在源语境中如何表述、有着怎样的语义,进入中国语境后的对等词都有哪些、语词本身发生怎样的语义变迁,为什么会发生变迁,在这过程中它们被赋予了怎样的中国社会、政治的经验与意义,发挥着怎样的文化功能等等内容均值得深入探讨。以“阶级斗争”为例,“class struggle”的“对等词”经历“阶级竞争”“阶级战争”“阶级争斗”“阶级斗争”的变迁,其理解从自然界物种竞争的实然状态转变为只能用阶级斗争加以解决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围绕“阶级斗争”展开的概念源流考证,既能展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跨文化过程中的变迁,又能够揭示中共理解、塑造马克思主义概念时所发生的思想变革。
(三)在话语争夺进程中共产党创制的“概念”
“‘概念’表征思想,并为思想所用,这些思想已经浓缩在‘概念’中”*〔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2页。,一个政党若要表达自己的思想,首先就要创制或者改造出有说服力的概念。然而,概念在意义上具有多元性,可以连接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经验或预期。这样,它“吸引并动员那些追求不同价值,甚至完全处于对立状态的政治和社会群体,使他们以‘概念’为工具‘去说服、去协商,去战斗’”*周保巍:《概念史研究对象的辨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由于不同主体根据不同的目的使用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将呈现不同的语义指涉,彰显不同的政治功能。因此,政党间的舆论、话语的争夺首先呈现为“概念”的交锋。
自1921年到1949年间,国共两党根据自身意图与期望构建各自的话语体系。与国民党宣扬之“国民革命”相对,中共形成一套“阶级革命”话语体系,话语竞争是两党所处的常态。在竞争性语义场中,中共要澄明或批判被国民党固化和标准化的概念,通过拓展或重塑旧概念的意义空间以打破国民党对概念的“专制”,弱化甚至消解国民革命话语的说服力,比较典型的有国共两党的“真假三民主义”之争以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概念。同时,概念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以言成事”、指涉行动,中共通过铸造新的概念,开展革命动员,促使革命行动的发生。这些概念体现着中共革命的意图并成为革命实践的一部分。同样是动员革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概念语义指涉、表达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共产党在农村革命动员中常常使用的“搞革命”“干革命”等概念,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中并不存在。然而,正是这样的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口号、标语与土地纠纷、社会地位等利益性概念与“农民”“地主”等身份性概念相互关联,互相支撑,建构起新的意义世界,充分彰显了农村革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助力中共革命力量向农村渗透。
事实上,任何一个被历史选择并流传下来的概念都是竞争与博弈的结果,因此那些具有竞争性、体现党派意图的概念都是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在革命史中,围绕同一概念,国共两党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批驳、斗争,在历史上留下大量可供研究的史料。研究者应该利用这些史料来研究政党间交锋中的“概念”,揭示它们的政治性与实践性。这样的概念史研究不仅能够透析概念在价值理念塑造或“经验事实”建构中发挥的作用,而且可以管窥政党铸造概念的意图和策略。
正如历史学家斯金纳所言:“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以及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芬兰〕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等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序言”第5页。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概念如同一个支点从微观层面折射着中共改变旧观念、传播新价值、建构信仰体系的过程。笔者谈及的三个方面选题,虽切入角度不同,但其最终落脚点都离不开对中共建构信仰体系的观照。
中共党史领域引入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将打破以往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历史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旧范式,以“单元概念”为支点,实现新的整合与贯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概念具有工具性特征,概念史研究亦属新兴事物,对将其引入中共党史领域可能存在的问题应予以思考。
第一,应观照思想发展主线。借鉴概念史理论与方法主要是为深化党史研究而服务,即通过对概念的微观实证研究来确证、深描、充实中共历史的发展主线。然而,概念史研究出自后现代理论,其中蕴含着离散性的偏执,隐含着“解构主流”的风险。与以往强调连贯性与整体性的思想史研究不同,概念史所展现的不仅是思想的一致性,它还将呈现思想的差异性、异质性甚至断裂性。因此,研究者应对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例如消解中共整体观念、偏离主流思想发展的确定性和权威性等问题有所警惕,在具体研究中应充分观照中共思想发展的主线索或总体发展趋势。总之,概念史研究既要彰显微观深描历史的优势,又要嵌入宏观历史叙事的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互证与自洽。
第二,要规避时代误置。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历史研究呈现可视化、数据处理的趋势。词频、字频检索、统计与概念史研究相结合,促进其朝着实证化方向发展,但也存在抽样和挑选的风险,在分析中更可能陷入“时代误置”的泥潭,“我们可能‘发现’某位著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页。。概念史研究需要理清哪些是“碰巧”使用的概念、哪些是有意塑造而使用的概念,避免将那些零星的、即兴使用的概念拔升至意图高度,更不能将历史语境中的习俗、惯用剥离出来并在当下视野中追溯为“神话预言”。总之,概念史研究既要注重实证性,增强说服力,又要对数据进行科学处理,规避时代误置的陷阱。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 ”(14CKS00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