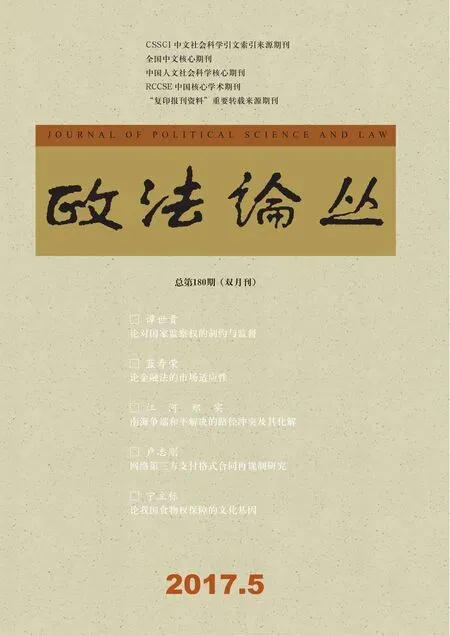香港政制改革的宪法学透视*
刘志刚 张 晗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3)
香港政制改革的宪法学透视*
刘志刚 张 晗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3)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主动解释香港基本法,不需要基于香港终审法院的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2004年释法决定不存在法理上的问题。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释法决定确立的香港政改“五部曲”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精神。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是正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以“决定”的形式规定香港特首产生的具体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中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原则符合香港基本法和现行宪法的规定。
香港政制改革 2004年释法决定 2014年“8·31”决定 合法性
香港政制改革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改革,其制度层面的动因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第45条①和第68条②中所预设的改革空间。自2004年起,香港特别行政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政制改革实践③,但是,人们对政制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改革方案存在诸多理解上的歧义,甚至由此衍生出实践层面诸如“占中公投”之类的过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影响到了香港政制改革的有序进行。总观香港政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各方人士围绕香港政制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的问题: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的合法性、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合法性。在本文中,笔者意欲不揣浅陋,对前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从形式和内容分别作一框架性的宪法学理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并期望能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的政制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的梳理。
一、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释法决定之程序上的合法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作出释法决定④之后,实践中有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基本法的做法提出质疑⑤,认为该种做法违反《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对此,笔者秉持否定的立场。具体理由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具有明显的衍生性,其解释权限范围受到限制。
“一国两制”是处理中央和香港相互关系的宪法原则。其中,“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制”是在坚持“一国”原则前提下的展开。依据“一国”原则,中央对香港拥有主权性权威,香港自治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尊重“一国”原则的前提之下。香港的自治权不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它的。现行宪法第31条⑥和《香港基本法》第2条⑦中对此均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在制定《香港基本法》的时候,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有可能影响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因素⑧,最终构筑了“二元型”解释体制,在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解释权的同时,也赋予香港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但是,后者所拥有的基本法解释权是前者赋予它的,具有明显的衍生性。由于“一国”以及人大制度方面的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时居于主导地位。依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受到诸多限制,它原则上只能对《香港基本法》中关涉香港自治的条款进行解释。如果对自治范围之外的条款进行解释,不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相关解释相冲突,否则无效。从法理上来说,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因此,它固然也可以行使基本法解释权,但是不能影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更不能本末倒置,反过来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立基于此,那种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主动解释基本法的立场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是不成立的。⑨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依据《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香港基本法》中的相关(程序性)规定解释基本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固然有权解释基本法,但是,由于基本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其解释基本法的程序,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究竟可以依据哪些程序解释基本法在制度上存在较大程度的模糊性,由此衍生出了基本法解释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引发人们理解上的歧义。笔者认为,《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应当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诚然,从直观上来看,前述法律并不属于可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但是,由于《立法法》中规定了法律解释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中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程序,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时候依据前述法律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需要《香港基本法》中对此作出重复性规定。《香港基本法》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⑩。既然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作为法律的《香港基本法》的时候当然要依据《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相关程序性规定。作为会议型的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行使的方式就是开会,而会议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包括基本法解释权在内的国家权力的时候,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程序性规定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依据《立法法》(2000)第43条的规定,国务院等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均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立法法》(2000)第44条、第45条及第46条的规定加以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2条第2款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条第3款均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可以向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2009)第1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此外,依据《香港基本法》第43条的规定,香港特首应当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统合前述,笔者认为,尽管《香港基本法》中并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但是,依据《香港基本法》第43条以及《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国务院”、“香港特首”等主体的提案或者提请,主动解释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提请并不必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前置性程序。
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释法决定之内容上的合法性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释法决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作了解释,确定了香港政制改革的“五部曲”。在其确定的“五部曲”中,只有“后三部”是《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规定的,“前两部”在《香港基本法》中并未作出规定。2004年对基本法作出解释之后,香港社会一些人对该解释的内容提出质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决定中增加的“前两部”在基本法中没有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进行解释,而是对它们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这种做法是违反现行宪法第31条的规定的。[1]P165对此,笔者秉持否定立场。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方式不甚相同。
依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均拥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但是,二者解释基本法的方式不甚相同,由此导致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知,进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释法决定在香港民众中的可接受性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但是,在解释香港基本法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上没有解释法律的具体实践。所以,其解释法律时究竟会采取何种方式实际上并不清楚。[2]P151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对香港基本法所作的四次解释中,反复表明其解释基本法的方式——原意解释。例如,在其1999年针对“居港权案”所作的第一次释法决定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出,香港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件中并没有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而它自己作出的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很显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目的在于挖掘内蕴于基本法条文之中的立法原意,最大限度地尊重立法者。有学者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采取原意解释的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立法解释体制的影响”;其二,“维护自身解释高于特区解释正当性的需要;”其三,“强调自己是释法而非修法的需要”;其四,“化解特区内部对基本法理解分歧的需要”。[3]与内地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方式更多地受到了来自普通法的影响。按照传统的普通法理论,法院解释法律的时候应当遵循“文义解释”、“黄金规则”以及“除弊规则”[4]等三大规则。其中,“文义解释”是法院解释法律时最为经常使用的方式。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实践中,曾经一度采取目的解释的方式,但2001年“庄丰源案”以来,香港法院开始逐步转向文义解释的方式。有学者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释基本法时之所以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普通法传统的影响”;其二,“基本法立法目的的不确定性使法官舍弃了原意解释”;其三,“对所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释法为名行修法之实’的担忧”;其四,“政治因素的考量”[3]。笔者认为,香港社会之所以有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2004年释法决定提出质疑,认为它是在“实质性修改”香港基本法,归根结底是由于对其秉持之迥然相异于香港法院之法律解释方式理解上的差异所造成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要义是“根据法律的解释”,既是为了落实法律,也是为了使法律更加适合社会。[5]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主要受大陆法的影响,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释基本法时却主要受普通法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以填补法律条文空白为主旨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普通法系国家的视野中根本不是对法律的解释,而是对法律的修改。从目的解释方法的视角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的释法决定中确定“政改五部曲”的做法,实质上是通过法律解释来填补法律条文的空白,而不是实质性修改基本法,更不是创设香港政改制度。香港部分社会民众之所以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解释是在“实质性修改”基本法,实际上是受到了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依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法院有权解释基本法。尽管基本法中并没有明确言及,但香港法院遵循普通法的传统,对基本法进行文义解释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央并未给予限制。反之,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大陆法的传统,对基本法进行目的性解释,也应该受到香港法院的尊重,香港民众对此应该予以理解和支持。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通过立法程序来解释法律的,它有权明确法律条文的界限或者对其作内容上的补充。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均拥有基本法解释权,但是,二者解释基本法的性质不同。由于香港法院是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基本法进行解释的,因此,其解释权本质上属于一种司法行为。与之相比,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时却并不依托具体的案件,而是通过立法程序对基本法进行解释的,其解释的权限范围也迥然相异于香港法院。因此,该种解释本质上属于一种立法行为,而不是司法行为。对此,学界也有不同的立场。笔者认为,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行为本质上应当属于立法行为,而不是什么“半立法”“半司法”行为,具体理由是: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程序是立法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程序包括:1.提案程序。《立法法》(2000)第43条对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的主体作了列举性规定,《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2条第2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2009)第11条第1款分别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委员长会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其职权范围内议案的权力作了规定。2.拟定、修改法律草案的程序。《立法法》(2000)第44条、第45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修改法律解释草案的权力作了具体规定。3.对法律解释草案的表决程序。《立法法》(2000)第46条对法律解释草案的表决程序作了规定。将上述法律解释程序与立法程序相比,二者尽管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立法程序的总体框架结构在法律解释中得到了适用,该种程序可以说是一种准立法程序。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所作解释的效力与立法相同,其法律解释权限具有立法性。依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事项进行解释。《立法法》(2000)第42条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依据前述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解释的权限范围迥然相异于最高人民法院,后者只能对审判工作中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具有明显的立法性。舍此而外,《立法法》(2000)第47条还进而对法律解释的效力作了规定。统合前述,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行为是一种立法性质的行为,迥然相异于法院的司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常规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相比,其对基本法的解释与对一般法律的解释不甚相同。但是,由于《香港基本法》中并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程序,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避免地要依据前述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来解释基本法。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和解释的效力均迥然相异于香港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不能从香港法院的视角来识别和判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所作解释的正当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所作之2004年的释法决定中尽管增加了两个香港基本法附件中没有规定的政制改革程序,但是它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对基本法的实质性修改,是对现行《宪法》第31条的违反,而应当将其理解为是进一步明确基本法中模糊条款的涵义或者对基本法作出补充规定,这完全符合《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权限范围的规定。香港社会之所以有人对2004年释法决定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理解不清所造成的。
三、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之形式上的合法性
根据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确立的“政改五部曲”,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针对此前的政改咨询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确定。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所作“8·31”决定中原则上同意了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改革,并对香港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作了进一步的规定。“8·31”决定作出之后,香港社会有人对该决定的性质、内容及其对香港政制改革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规定香港政制改革问题,违反了现行《宪法》第31条和《立法法》(2000)第8条中的有关规定,提出要重新审视该决定,甚至鼓动香港民众进行所谓的“抗争”[6]。对此,笔者秉持否定立场。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决定的性质是什么?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每年都会通过若干“决定”或者“决议”,这些“决定”或者“决议”的性质究竟是属于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的决定,现行《宪法》和《立法法》中均未作出明确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15条第2款首次提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但是,其性质究竟是否属于法律,该法中似乎也未作出明确厘定。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决定的性质问题较为复杂,它既有可能是法律,也有可能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甚至还有可能是一般的决定。容易引发人们理解上歧义的主要是法律和有关法律的决定。对此,相关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学界对界分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法律”与“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之间的区别标准所秉持的立场也不甚相同。有学者认为,界分“法律”与“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标准是“制定机关+公布机关”的判断标准。从制定机关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制定主体既包括全国人大,也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制定主体却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公布机关的角度来看,根据现行《宪法》第80条的规定只有国家主席才有权公布法律[7]。但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却不是由国家主席公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也有学者认为,界分“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标准包括三个,分别是“名称标准”“制定程序标准”以及“实质内容标准”[8]。笔者认为,界分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决定究竟是“法律”还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应当从“制定程序”、“公布机关”这两个方面来加以界定。依据该标准,“8·31”决定的性质不是法律,而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其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是否违反了其2004年作出的释法决定?
香港社会有观点认为,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释法决定,在香港政制改革“五部曲”的第二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交的报告,就“是否需要修改”进行确定。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进而对“如何修改”问题加以具体规定。由于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已经涉及“如何修改”问题,所以该决定越权违法。[6]对此,笔者秉持否定的立场。诚如前文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在性质上不属于法律,而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同时,由于该决定也不是按照《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程序作出的,因此,其性质也迥然相异于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就其法律地位而言,“8·31”决定在位阶上应当低于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对此,理论上不存在什么悬疑之处。同时,由于《立法法》(2015)第50条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放在与法律相同的效力位阶上,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在法律位阶上也应当低于其对基本法所作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8·31”决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2004年释法决定相抵触,就应当象香港部分人所说的那样,是“越权违法”的。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8·31”决定和2004年释法决定并不存在相抵触之处。诚然,从直观上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2004年释法决定确定的“五部曲”中仅仅规定“行政长官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是否需要修改”,并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具体规定“如何修改”,“8·31”决定中对香港特首普选问题所作的具体安排似乎已经超出了明确“是否需要修改”的范围,涉及“如何修改”的问题,因而两者之间相抵触。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释法决定中阐述香港政改“五部曲”时,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政改第二步对普选办法之具体问题作出规定的意思。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释法决定中所作的相关表述是“是否需要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但在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大04年释法”所作的说明中已经表明“是否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决定权在中央”[9],这足以说明2004年释法决定的原初意图。之所以如此设计,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五部曲”的最后一步,即中央对香港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只能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不能再作修改。[10]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在“8·31”决定中对香港特首普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的话,中央对香港政制改革的决策权将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因此,“8·31”决定中对香港特首普选所作的具体规定并不是对2004年释法决定的违反,恰恰相反,是对2004年释法决定内容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这是符合2004年释法决定的目的和精神的。
其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是否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中的相关规定?
香港社会有观点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实质上是以“决定”的方式规定了香港特首的普选问题,违反了《立法法》第8条第3项的规定,属于违法决定。[6]由于现行宪法第31条中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大以法律加以规定。因此,香港社会有人提出“8·31”决定同时也是违反宪法的决定。对此,笔者秉持否定的立场。笔者认为,该种观点实质上将“区分行使专属立法权时所采纳的法律形式与行使《香港基本法》授权时所采纳的法律形式混为一谈”了。国内有学者曾经撰文指出,“特别行政区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真正意思是:有关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整体框架应当由全国人大立法予以规定,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在《香港基本法》这一宪制性法律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在行使《香港基本法》的授权对特别行政区的具体问题予以规范的时候,应当可以通过其他立法形式,只要不违反基本法内容、不超越授权即可。[11]该种观点值得参考。按照该立场,《立法法》中固然将关涉“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事项归入到法律保留的范围之列,但是,该类事项并不属于绝对保留的范围,全国人大可以通过授权的形式交由其他国家机关行使。《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香港政制改革方案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全国人大通过其制定的《香港基本法》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香港政制改革方案的权力。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该种授权之后,究竟是通过制定法律还是通过发布决定的方式来规定香港政制改革方案,那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情了,《立法法》中并未对此作出限制性的要求。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以“决定”的形式对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的时候,不能违反全国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不能超越《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对它的“授权”范围。立基于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对香港特首产生方式作出具体规定的做法并不违反《立法法》和《宪法》。
四、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之内容上的合法性
“8·31”决定作出之后,香港社会部分民众对其规定的“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提出质疑。“泛民主派”认为,行政长官的爱国爱港义务在基本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它属于政治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以“爱国爱港”作为香港特首的当选条件存在政治筛查嫌疑,它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对行政长官政治品质的实质性设定与一种关于行政长官普选的纯粹民主原理之间产生的规范性的矛盾与冲突”[12]P97。对此,笔者秉持否定立场。笔者认为,以“爱国爱港”作为香港特首的当选条件合乎宪法的精神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宪问题。具体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以存在的宪法基础
现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是香港共同的宪制基础。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现行宪法在香港是否适用?国内有学者秉持否定立场,认为宪法不适用于香港。笔者认为,该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具体理由是:(1)宪法序言不具有高于宪法规范的效力。宪法序言的效力和宪法规范的效力应当类同。只是“由于宪法序言在外观形式上迥然相异于宪法规范的特点,其效力不同于宪法规范,有些内容表现为直接的宪法效力,有些内容表现为间接的宪法效力,具体要视其表述的内容而定。但是,认为宪法序言具有高于宪法正文效力的观点缺乏实证法层面的依据。”[13]以《宪法》第31条违反宪法序言为由否认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是难以成立的。(2)《香港基本法》是宪法在香港适用的主要形式。对于宪法在香港的适用问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宪法在香港的适用是指宪法中所有条款在香港均具有适用性。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宪法在香港的适用是指,对于宪法中所有条款所规定的制度和内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受到反对和破坏,这种适用是以“认可、尊重”的形态存在的”[14]P81。依据前种观点,宪法在香港部分适用;依据后种观点,宪法在香港全部适用。由此观之,对宪法在香港究竟是否适用这一问题所秉持的立场实际上是以对“宪法适用”之内涵的厘定为前提的。笔者认为,宪法适用的内涵应当是:“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规定,在具体活动中贯彻、执行宪法的行为”[15]。立法、行政、司法均是宪法适用的路径,于我国而言,立法在宪法适用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应当将“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理解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贯彻和执行,而贯彻执行的主要途径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香港基本法。2.《香港基本法》不足以结构性取代宪法在香港的适用。学界对《香港基本法》性质的理解不甚相同:有学者认为基本法是“小宪法”[16]P15,有学者认为基本法是“代议机关的制定法、宪法的下位法”[17]P16,也有学者肯定了其基本法律的性质,并延伸指出基本法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法”[18]P85、“宪法性法律”[1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香港基本法》应是宪法的特别法,由于其特别法这一性质,基本法不因与宪法的抵触而无效;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效力是通过其特别法,即香港基本法得以实现的[20]。笔者认为,《香港基本法》本质上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既不是什么宪法的特别法,也不是什么小宪法,后者仅仅是一种通俗意义上的称谓,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理上的范畴。从法律地位上来说,《香港基本法》与宪法相比,属于下位法,是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贯彻实施。但是,《香港基本法》与宪法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结构性取代宪法在香港地区的适用。宪法在香港的实施主要是通过《香港基本法》来获得实现的,但是,宪法中承载国家主权、表征国家统一的条款在香港依然具有适用性,宪法和基本法是香港共同的宪制基础。
(二)将“爱国爱港”作为香港特首产生的条件是否违反《香港基本法》和《宪法》
诚如前文所述,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是香港共同的宪制基础。将“爱国爱港”作为香港特首的产生条件是否妥当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合乎香港基本法和宪法的精神。对此应当看以下两个方面:1.宪法中的哪些条款适用于香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对于宪法中究竟哪些条文可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均未见明确规定。国内有学者曾经提出,在基本法中将可以适用于香港的宪法条文逐条罗列出来,但是该种立场不仅在立法技术上行不通,而且在法理上也无法解释清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中究竟哪些条文可以适用于香港,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立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基本法解释加以解决的问题,它在本质上属于一个宪法解释层面的问题。当然,由于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在事实上处于虚置状态,全国人大常委会难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对此加以厘定。目前,较为可行的方式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基本法的解释,将宪法文本中相关条文的精神贯彻其中,以此发挥宪法在香港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该种解释,将宪法精神过当地输入对基本法的解释之中,从而危及香港迥然相异于大陆的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两制”的总体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的时候,应当秉持“一国两制”的原则,既要保证宪法中承载“一国”精神的主权条款在宪法得到贯彻落实,也要避免过当压制乃至破坏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此,笔者在他文中曾经作过相关的阐述[13]。2.“爱国爱港”义务在《香港基本法》和宪法中的具体体现。诚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均未直接规定“爱国爱港”的内容,但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爱国爱港”义务在其中均有体现。《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效忠。因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必须践行其承诺,真正担当起“爱港”的法律义务。此外,《香港基本法》第44条关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任职条件的规定也体现了“爱国爱港”的精神。作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显然他必须“爱港”;作为“中国公民”,显然他必须“爱国”。否则,就违反香港基本法的前述规定。诚如前文所述,确定现行宪法中何种内容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宪法中承载“一国”精神的条款在香港应当得到全体“香港居民”的尊重和保障。此外,现行宪法中还专门规定了“中国公民”的“爱国”义务。依据香港基本法的前述规定,既然香港特首必须是“中国公民”,且宪法中承载“一国”精神的条款在香港具有适用性,因此香港特首必须“爱国”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宪法的固有精神。统合前述,将“爱国爱港”作为香港特首的任职条件不仅不违反香港基本法和宪法的规定,恰恰相反,该条件是内蕴于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文本之中的。
统合前述四个方面所作的总体阐述,笔者意图阐明的立场是:目前实践中围绕香港政制改革所产生的争议本质上是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而展开的,既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实体方面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政制改革所作的2004年释法决定和2014年所作“8.31”决定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均不存在法理问题,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精神和现行宪法的规定。
注释:
① 《香港基本法》第4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行政长官产生的具体办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规定。”
② 《香港基本法》第68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产生的具体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由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规定。”
③ 自2004年起,香港特别行政区针对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的选举、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的选举进行了三次政制改革实践。
④ 2004年4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
⑤ 秉持反对立场的人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基本法的时候,方才能够解释基本法。
⑥ 现行《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⑦ 《香港基本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⑧ 例如,现行宪法中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普通法传统及其高度自治权的行使等。
⑨ “香港特区法院认为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被动的,必须由特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才能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并且是否符合提请释法的标准由特区法院自主认定,这实际上架空了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享有的解释权。”参见季金华:《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问题探析》,《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如果只有香港终审法院才能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解释的程序,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就完全受制于香港终审法院,这既不符合基本法规定,也违反授权原理。”参见邹平学:《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⑩ 围绕香港基本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其一,认为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其地位低于宪法但高于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参见许崇德:《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殷啸虎:《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法学》2010年第1期;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刘茂林:《香港基本法是宪制性法律》,《法学家》2007年第3期。其二,认为香港基本法,既不是普通法律,也不是宪法,而是宪法的特别法。参见李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香港基本法是小宪法。其三,认为香港基本法是基本法律,其地位与普通法律类同,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就其内容来看,应该属于宪法性法律。多数学者秉持该种立场。
[1] 陈弘毅. 一国两制的法治实践[A]. 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文集[C].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2] Lin Feng and P. Y. Lo. One Term,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Justific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A]. Huang Fu, Lison Harris, and Simon NM Yong, interpreting Hong Kong’s Basic Law[C].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 姚国建,王勇. 论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冲突与调适[J]. 法学评论,2013,5.
[4]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v. Fisher[1980] AC319,329E.
[5] 陈金钊.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上)[J]. 政法论丛,2013,3.
[6] 施路. 揭开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面纱[N]. 香港:苹果日报, 2014-09-08,(A19).
[7] 王竹. 我国到底有多少部现行有效法律——兼论“准法律决定”的合宪性完善[J]. 社会科学,2011,10.
[8] 江辉.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与法律的区别[J]. 人大研究,2012,1.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释法答记者问[EB /OL]. http://www.fmprc.gov.cn/ce/cohk/chn/zt/zzfz/t82589.htm,2016-9-4.
[10] 李飞.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政治和法律内涵——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级官员简介会上的讲话[EB /OL]. 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902/2707720.html,2016-12-19.
[11] 张春生. 对全国人大专属立法权的理论思考[J]. 行政法学研究,2000,3.
[12] 田飞龙. “爱国爱港”的法学思考[A]. 邹平学主编.港澳基本法实施评论(2014年卷·总第1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3] 刘志刚.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J]. 北方法学,2014,6.
[14] 韩大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的基础[A].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文集[C].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15] 殷啸虎. 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J]. 法学,2010,1.
[16] 杨静辉,李祥琴. 港澳基本法比较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郑贤君. 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评全国人大常委会’99《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释法例[J]. 中国法学,2000,4.
[17] 许崇德. 港澳基本法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8] 孙笑侠. 法律对行政的控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郑贤君. 联邦制和单一制下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之理论比较[J]. 法学家,1999,4.
[19] 刘茂林. 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J]. 法学家,2007,3.
[20] 李琦.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J]. 厦门大学学报,2002,5.
TheConstitutionalAnalysisofPoliticalReforminHongKong
LiuZhi-gangZhangHan
(Law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ma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xplain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no need to take the proposal of the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as a prerequisite.There is no legal controversy in the 2004 legal interpretation made by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The five steps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reform conform to the legislative spirit of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The 8.31 legal interpretation made by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has validity:the Standing Committee has the right to stipulate the concrete procedure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The principl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must be patriotic and love Hong Kong”conforms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and the constitution.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the 2004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8.31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2014; validity
1002—6274(2017)05—038—09
DF29
A
(责任编辑:孙培福)
本文系教育部2015年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人权观及人权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5JZ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志刚(1971-),男,河南汤阴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张晗(1982-),女,湖北黄冈人,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