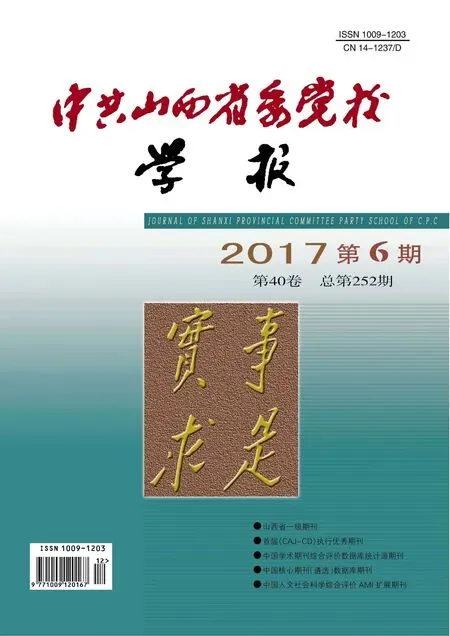革命与建设中的文化批判
——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卢文忠
(广东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230)
革命与建设中的文化批判
——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卢文忠
(广东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230)
十月革命前后的文化批判,是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掌握和运用的精神武器,是内在于政治和经济革命任务中的文化革命,也是政治和经济革命所蕴含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的实践体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对十月革命批判性的继续,革命后的建设也是对其后发展模式批判性的继续,正确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批判立场来积极思考对西方外来文化的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等三个重大问题,推进文化建设。
十月革命;列宁;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指出,“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1〕。在当今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100年前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依然在继续前进,尽管这一新时代曾经经历了革命发源地的巨大挫折,但是这一新时代的后续引领者能够在世界风云变幻之中,坚持用革命所锻造的先进武器来积极应对在新时代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把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种先进的武器之一就是在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文化斗争和促进思想文化建设的文化批判。
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所讲:“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2〕563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完成政治意义上的革命任务,也要完成文化意义上的革命任务。建立新的国家必须批判和清除旧社会的文化遗毒和文化障碍,使人民群众从腐朽落后的文化奴役和制约中解放出来。在列宁的领导下,这种清除工作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比法国大革命还要广泛和深刻。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对新社会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及其在新社会的残余进行批判和革命。革命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文化精神的实践。十月革命及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国家在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对于其他国家革命与建设、文化斗争与文化建设关系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给予了重要启示,是值得当代人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俄国十月革命进程中的文化批判斗争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革命全面意义的理解和论述,其实质在于阐明经济层面上的革命与文化层面上的革命相统一的必要性。只有对传统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观念进行批判性的变革,才能彻底改变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是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变中的封建专制的农业国,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下。俄国沙皇政权无法维系动荡的国内局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俄国元气大伤,社会矛盾激化,俄国的现代化道路陷入严重困境,这些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和矛盾造就着空前的革命形势。“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4〕69。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俄国革命群众掀起了狂欢。“狂欢中的人们破坏旧时代的标志,创造新的革命象征,是二月革命否定旧文化、形成自己的革命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革命本身的重要表现”〔4〕118,狂欢中的人们广泛破坏和清除着旧政权的精神文化符号。从革命的基本立场来看,对象征专制政权的各种精神文化符号的否定和摒弃,反映了人们对旧社会文化专制和文化矛盾的反抗和不满,实质上就是内在于并推动着政治革命进程的文化批判,以期在精神上彻底摧毁旧政权。同时,专制政权的倒塌,两大政权的对峙,传统社会的瓦解,在尚未接受科学理论指导和缺乏国家治理节制的环境下,群众批判性的狂欢呈现出自发性的狂乱,社会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引发了文化污染的乱象,这无疑成为革命的丑陋反面,并使革命性的文化批判走向了反面,为贫瘠的精神文化雪上加霜。再加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作出了继续参战的错误选择,加剧了社会危机。可以说,摆在革命者面前的任务是,既要推进政治革命,同时也要进行文化批判,制止政治和文化上的无序与混乱。这一时期俄国突出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是原有封建专制下广大民众的文化愚昧以及战争祸乱中严重的文化破坏。
列宁根据俄国的革命形势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5〕对于俄国所遭受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而言,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就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文化免遭战争破坏,才能在新制度的条件下消除社会的文化愚昧。在列宁看来,俄国政治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俄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同样,在文化层面上的革命和批判,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列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批判性地观察和审视俄国的文化态势,揭露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对社会进步的实质危害,深知消除文化愚昧和文化破坏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反对和否定文化专制和文化愚昧,反对和批判普列汉诺夫的沙文主义、考茨基的机会主义、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民粹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对于起义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说,文化层面上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活动激发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意识,使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形成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主体。可见,在十月革命爆发前,政治层面的革命行动推动着新时代的来临,文化层面的批判活动也同样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革命性的文化批判成为战争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体现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
二、苏俄革命政权建立后的文化批判转变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然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6〕。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并未因此立即改变旧政权所面对的经济凋敝和文化落后的困局。相反,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最基本的问题——“兑现承诺”即人民群众渴求的和平、面包、土地和自由问题尤为严重。面对种种复杂严峻的形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积极的同时也是迫不得已的诸多措施稳定了局面,并且在“铁与血”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
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建设新的国家开辟道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革命战争胜利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指出:“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2〕136对于列宁来说,他在这些成就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指导俄国革命的先进文化武器。此外,列宁还主张寻求来自欧美的创立了大生产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技术,强调提高俄国民众的文化觉悟,以期用来改变俄国文化落后的局面,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由于政治革命形势所迫,列宁更侧重于凸显为政治革命服务的文化批判的斗争性一面。文化批判的斗争性比其建设性更符合现实需要,疾风骤雨的环境还不允许把工作重心放在借鉴欧美的最新文化成就上。
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文化建设成为重要任务,文化批判就应该顺应实际转变为以建设性为主的价值取向,成为和平建设时期除旧布新的文化武器。列宁对这种转变作了明确论述:“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2〕773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和平环境下,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过去的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当然,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文化革命的革命之意,不在于破而在于立,不在于消灭敌对的势力,而在于消除陈腐的状况。“列宁文化革命概念的内涵就是在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即清除旧思想,树立新思想;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7〕。在这种文化批判的立场上,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革命,在其现实意义上而言是否定和改变文化落后的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主义”工作的建设性武器,这意味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必需的知识、文化、技术,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俄国不断从野蛮愚昧和严重破坏的文化困境中解放出来。同时,斗争性的文化批判也是必要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面对‘无产阶级文化派’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揭露了他们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和政治上的反动性,从而逐渐消除了他们的影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8〕。后来,斯大林也提出了克服旧社会遗留下的传统和习气的文化批判任务,并要求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因此,和平建设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斗争同样不可松懈。
列宁指出:“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9〕在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的转变中,列宁的论述和苏俄革命的经验,展现了进行文化批判所坚持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革命的理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批判的根本武器,批判和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和研究方法,从俄国文化斗争和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把文化批判与文化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第三,坚持把经济和政治层面的革命与文化层面的批判相结合,对旧社会进行整体性的彻底改造。第四,坚持对具体历史时期作具体分析。随着战争时期转为和平时期,应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建设,发挥文化批判的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第五,坚持辩证法的否定精神,既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同时也要坚决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蚀。
总的来说,十月革命前后的文化批判,是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掌握和运用的精神武器,是内在于政治和经济革命任务中的文化革命,也是政治和经济革命所蕴含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的实践体现,促进了俄国走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相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乃至遭到苏联解体的巨大挫折,恰恰是一些苏共领导人未能实事求是地运用批判的武器来纠正党内错误、未能以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来改革僵化的体制、未能正确处理文化批判的建设性和斗争性的统一关系、未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文化领域的错误思潮进行文化批判甚至最后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根本的理论武器的严重恶果,也是一些苏共领导人不加批判地全盘照搬西方模式、走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背叛十月革命在俄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惨痛教训。
三、中国走自己的道路上的文化批判实践
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为其他民族国家的革命指出了新道路,中国革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这一新时代走上了新道路。“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苏俄革命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批判“城市中心论”的“左”的革命道路,坚决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批判和斗争。可以说,中国革命对十月革命的这种继续,实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继续,也就是对苏俄革命的经验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选择而最终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对十月革命的批判,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
中国革命的成功,为建设新中国扫除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障碍。无论是疾风骤雨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都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有着十分相似的国情:经济文化的落后,帝国主义的入侵。这决定了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现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抄苏联模式来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像对十月革命批判性的继续一样,坚持对苏联模式批判性的继续,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在建设道路上批判性的继续,又是对国情的正确把握,并努力从革命的思维和实践转向建设的思维和实践。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1〕在毛泽东看来,执掌全国政权,从农村到城市的重心转变,中国共产党将要在和平建设中与旧势力进行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斗争,党自身就必须抵制和克服各种反动腐朽文化的侵害,而且要积极学习和借鉴一切先进文化来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批判依然是重要的精神武器,要继续发挥文化批判吐故纳新、去芜存菁的作用,既要体现文化批判斗争性的一面来否定和破除各种文化障碍,更要凸显文化批判建设性的一面,把文化批判主要特点的转变与我国国情的转变统一起来。也就是说,相对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批判而言,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体现为一种建设性的文化批判,使之服务于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建设。相反,如果过度夸大了斗争性,用阶级斗争的政治批判方式来处理文化批判的问题,就会演变成极“左”的严重祸害。
正是对“左”的错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把中心工作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始进行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改革的目的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12〕。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既是中国革命的继续,实质上也是一种批判性的继续。这种批判性的继续,一方面是相对于否定社会进步的各种障碍而言的,要求必须彻底破除陈腐的体制和观念,体现了对革命的批判性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否定革命方式的具体手段而言的,要求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发展问题,体现了对革命的批判性的转变。就此而言,改革是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实践体现,是革命精神和革命立场在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党清醒地认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即在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3〕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文化批判,才能正确应对文化矛盾,坚持斗争性与建设性在文化建设实践中的统一,否定和克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以及其他一切陈腐的思想观念,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四、当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文化批判进路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对“第二次革命”的继续。在这场继续坚持的“革命”中,在各领域改革的同时,党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对自身的改革就是题中之义,而且是全部改革的核心要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4〕。这种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是一种彻底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精神的活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党勇于直面现实问题、革除缺点错误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指向。党只有正确地进行自我革命,才能使党内政治文化积极健康发展、党内政治生态得以全面净化、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才能革除自身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存在的障碍和弊端,克服现代化进程中自身出现的文化矛盾。“在和平建设年代,同时也是物化程度越来越深的时代,物欲化与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之间形成了某种矛盾,因为权力失控、利益及欲望等因素,执政党内滋生出严重的贪腐现象,改革本身也形成了阻碍深化改革的利益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显然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15〕。如果不能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就没有改革的全面深化。
同时,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密切相关,自我革命往往与文化领域的革命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必须对社会的精神文化结构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提升,使之与党的自我革命及其精神塑造形成一致性的文化重构趋势,形成对文化矛盾的反思与批判和抵制消极腐朽文化因素的共同着力点,用先进文化的发展来取代此类文化的存在。这种文化领域的革命,必须坚持和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成功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即充分运用在过去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武器,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驱动,成为与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文化武器,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自我革命、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文化机制。
具体来说,在文化领域,与全面深化改革和自我革命精神相适应的文化批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批判立场来积极思考和应对三个重大文化批判问题。第一,基于借鉴维度对西方外来文化的批判。从源头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源自西方并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传入中国的理论武器和文化资源,并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化武器。没有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指南。同时,掌握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文化武器,就意味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来批判“洋教条”,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先进文化资源。第二,基于传承维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后进入中国并逐步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武器,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为其中国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依托,是两者相结合的成果。“中国传统文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实现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16〕。当然,这种结合是批判性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批判“古教条”,扬弃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华的继承,奠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第三,基于创新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批判理论,不仅以革命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也以改革的立场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还以创新的立场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批判,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备的批判性精神来批判“马教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解决文化发展矛盾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革命本质上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具体实践。革命需要批判的武器,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也需要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类解放的历史道路,为揭示文化批判的现实内涵和文化批判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最根本的科学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把文化批判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使文化批判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17〕。十月革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武器,推动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中国革命也运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武器,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正是在掌握这种文化批判武器的意义上来说,中国革命是对十月革命批判性的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必须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武器,对已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和革新。这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文化批判,是党和人民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精神武器,也是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精神武器。
〔1〕毛泽东文集:第 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2.
〔2〕列宁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3.
〔4〕姚 海.俄国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列宁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7〕李国宏.列宁文化革命概念辨析〔J〕.东北亚论坛,2007(6):123-126.
〔8〕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80.
〔9〕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3.
〔10〕于 沛.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纪念十月革命 90 周年〔J〕.中国社会科学,2007(5):4-17.
〔11〕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9.
〔12〕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49.
〔13〕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
〔15〕邹诗鹏.追求制度文明——基于“四个全面”的思考〔J〕.探索与争鸣,2015(6):62-67.
〔16〕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7.
〔17〕卢文忠.论文化批判的内在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维度〔J〕.学习论坛,2015(8):59-62.
责任编辑 周 荣
D616
A
1009-1203(2017)06-0044-05
2017-10-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29)。
卢文忠(1985-),男,广东广州人,广东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