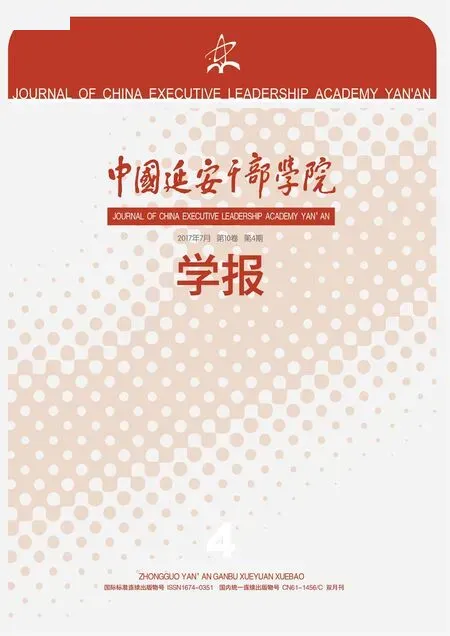从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
张志芳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山西 太原 030006)
从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
张志芳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山西 太原 030006)
认识与把握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不能仅仅局限于直接性、狭义性意义上的“十月革命”,要在注重事实依据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科学认识方法的意义上,从“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内在统一,“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与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内在统一关系中来把握,由此澄清由直接性、狭义性理解对十月革命历史定位问题上造成的种种迷雾。
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改革创新
发生于百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定位,本来是并不复杂的问题。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十月革命历史档案的解封,围绕这一长期以来定位于“20世纪最重大、最伟大的革命”[1]的争执逐渐多起来,而盛行于一定范围内的诸如十月革命是“少数人的意志”,是“偶然发生的”,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小部分人发动的“政变”等观点,更引起了诸多对十月革命历史定位的含混认知。
厘清这样的“含混”,需要有对十月革命史料文献更全面、更深入的掌握与分析。同时,任何意义上的文献事实都是与历史本身的逻辑演绎进程相关联的,前者应当是后者的自然结果或体现,面对同样的史实文献,不同的思想认识方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因此,在注重史实分析的基础上,在分析方法上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内蕴着的内在逻辑予以更深入的考量,是认识、把握十月革命历史定位问题应当具有的方法选择。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试图从十月革命发生发展的三重内在逻辑统一性的分析中,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加以思考。
一、从“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内在统一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
一般说的十月革命,其实包含两重内涵,即“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
换言之,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还是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关于十月革命历史定位中的“十月革命”,其完整的内涵,是应当基于事件本身特定指代“十月革命”当天呢,还是应当既包括“十月革命”当天,也包括“十月革命”之前以及随后连带而形成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呢?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攻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驻地圣彼得堡冬宫,推翻临时政府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一事件被称为“十月革命”,人们也会在一般(不存在歧义)的意义上,把这次武装起义称为“十月革命”,并籍此论及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如,“1917年10月25日(俄历),在当时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十月革命”[2] 199, “10月25日成了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3]258。
在过往的很长时间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生活中,关于十月革命及其历史定位并没有出现较大争议。可在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十月革命及其历史定位却出现了诸多不同声音。有人以十月武装起义“一共死了6个人”[1]等为借口,提出十月革命是“偶然发生”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一小部分职业革命家,利用当时俄国的混乱局势发动的“政变”等观点。这些观点给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造成极大认知混乱。
有鉴于此,恰当区分“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两个概念,并从二者内在统一的关联性上认识和把握十月革命历史定位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十月革命”首先是基于1917年10月25日(俄历)武装起义事件本身而形成的概念,是一个直接、狭义的概念。如果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和理解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在此基础上对诸如十月革命“偶然发生”的观点进行相应的辨析,尽管有其必要性。但与十月革命历史定位这样的重大主题相比,不仅在解释、说明上有难度,而且也确有难于深入之嫌。
而就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不能局限于1917年10月25日(俄历)当天而言,相关的认识,也绝对不是在最直接、狭义的理解上形成的。比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1471的著名论断,以及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重大、最伟大的革命”等认识,实际上是同“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5]314的认识统一于一体的。这里的“一声炮响”和“20世纪最重大、最伟大的革命”,内蕴着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经由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制度、道路和方向等。后者如果仅仅局限于1917年10月25日(俄历)当天,肯定是说不通的。
因而,有必要正确区分和厘清“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两个密不可分但又确实不同的概念。简言之,十月革命是指1917年10月25日(俄历)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的特定事件。“十月革命时期”则至少具有两方面内涵:从时间上看,包括以十月革命前,特别是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路线的《四月提纲》和发生临时政府血腥镇压示威工人的“七月流血事变”,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进行武装起义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为起始,后由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历经1918—1920年的苏俄国内战争,直到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的一段时间;从实践上看,包括布尔什维克为结束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立局面进行的斗争、对推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进行的较长时间的准备,以及10月25日(俄历)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和其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
对“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之后即不难看出,“十月革命”的特定内涵,是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的特定事件;“十月革命时期”的特定内涵,则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准备和领导武装起义成功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整个过程。因此,当人们把观察、分析问题的全部视角仅仅集中于“十月革命”这个特定事件之上时,实际上就在无形中割裂了“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内在统一性,并在似乎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把十月革命与1917年10月25日(俄历)当天临时政府军队大量集中于对德战争前线,圣彼得堡内部空虚,以及武装起义“一共死了6个人”等带有“偶然性”的因素联系于一起,并籍此诠释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尽管这种诠释本身也背离了事物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性(有关阐述目前已有大量学者专门论及[1]),但其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确实为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平添了诸多困难。后者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对“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两个概念不加以区分的消极后果。
而通过对“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两个概念的分析就更容易发现,区分“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两个概念的深刻意义,在于有利于揭示二者间存在着的绝对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十月革命”开启了“十月革命时期”的历史进程;“十月革命时期”延续了“十月革命”的实践进程,并将这个进程推进到了获取理论结晶、道路选择和制度成果的阶段,并由此形成完整的,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所以,没有“十月革命”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时期”,脱离了“十月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就成为某种孤立性事件,难于获得深刻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意蕴。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十月革命之后历史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关于十月革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等历史定位的认识,事实上是以统一于一体的“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为依托点的,人们在谈到十月革命及其历史定位时,就是从这样的统一性上来认识、来理解的。例如,“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4]1357“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6]667等著名的论述中,如果只是指10月25日(俄历)当天发生的起义,而不是指“十月革命时期”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话,从理论上就是根本说不过去的。可以说,当时尽管没有从学理上区分“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两个概念,但几乎所有关于十月革命及其历史定位的解读,都不仅仅是从“十月革命”这一特定事件的意义上来把握的,人们在使用“十月革命”这个概念的同时,其实就包含了“十月革命时期”所内蕴着的理论与思想指导、道路与制度选择。因此,只要对这样两个概念的内在统一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关于十月革命历史定位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十月革命在“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作用下发生、发展的客观性。包括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当天诸如“一共死了6个人”等“偶然性”在内的资料,当其与“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多次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资产阶级政府对这些抗议、示威活动镇压激发出的“革命形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赢得信任与崇高的威信,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赢得国内战争胜利、苏维埃政府的巩固,以及其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分析,也就是把“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当天的事件放在“十月革命时期”中加以分析认识时,就完全可以从一系列看似具有某些“偶然性”的十月武装起义中,把握隐身于其中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进而能够从这样的必然性中确定十月革命历史定位的立足点。
第二,“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十月革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历史定位的科学性。作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其“伟大”之处,至少包含了由“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相统一而产生的三大实践成就:其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与实践,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向制度形态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其二,从十月武装起义、苏俄国内战争,直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其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的建立,拉开了二十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序幕,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促进了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这三大实践成就,不仅在20世纪没有其他事件可以相比拟,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第三,“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十月革命提供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先进性。只要结合十月革命事件本身的前后发展、苏俄内战、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对“十月革命道路”加以分析,人们的视野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事件本身有多少人参与、伤亡几许等具体因素上,也不会因此判断其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而会从“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统一中,感悟和理解“十月革命道路”为什么能够激励处于极端困境当中的布尔什维克战胜内外敌对势力的围剿、干涉,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不到40年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就形成了包括十多个国家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了在社会主义影响下风起云涌的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抑或说,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最好说明。新近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了解到,在遭遇20多年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经历后,俄罗斯普通群众中肯定十月革命“开创了俄国历史新纪元”“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7]的正面评价,远远高于“一场灾难”之类的负面评价。
二、从“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
列宁对十月革命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8]132。毛泽东则提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5]314
“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和“全人类发展共同的光明大道”启示我们,仅仅于俄国一隅认识与把握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具有太大的局限性。十月革命不仅是“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内在统一,同时也是“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
这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诞生了包括欧亚拉美地区十多个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面对两种社会制度的选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终倾向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我们从“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无疑是很好的说明。
更为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80—90年代,世界性社会主义发展尽管进入低潮,但社会主义并没有像它的对立面预料的那样江河日下、奄奄一息,反而是在实践的挫折中大有凤凰涅槃、东山再起之势。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东欧发生历史性剧变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上的一些人、一些组织、一些国家,在跟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附和性或被蒙蔽地嘲笑、诋毁十月革命及其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时,也不得不惊讶地发现,伴随苏联东欧这个“庞然大物”的退出,西方社会 “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新干涉主义、新殖民主义行径顿时失却了有效的遏制和制衡,发展中国家在面临“休克疗法”“先发制人”“颜色革命”战略攻势,以及严重干涉其国家主权、颠覆国家政权的强盗做法时,既遭遇了内部经济发展的困境和政局的动荡,也产生了某种缺少依托和无所皈依的困惑。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国家和组织在相继抛弃新自由主义、抵御西方制度选择和价值观念,期冀寻求非西方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再次对“社会主义”投以更多的关注。“环顾全球,当代世界有一种奇特的新现象引人注目,促人深思: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出现挫折和问题,另一方面是自称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党派越来越多。”[9]1
历史的事实告诫人们,“十月革命在俄国”一旦发生,其影响便超越了俄国的疆域,成为“十月革命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因而,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也必须从“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中来认识,即“十月革命在俄国”为“十月革命在世界”提供了价值、制度与道路选择;“十月革命在世界”则使“十月革命在俄国”的影响与发展扩展到了国际的疆域,社会主义的价值、制度与道路成为当代世界文明最新、最富于生命力的文明形态。按照这样的思路,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就应当有如下的思考。
第一,“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决定了社会主义为国际政治发展提供了取代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发展模式的制度形态。十月革命在否定俄国社会剥削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掌权执政的同时,促进了人类社会先进的制度形态进入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十月革命前,国际政治格局中不同国家的制度形态,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摆脱不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属性,后者甚至被诠释为制度选择的天然合理性。而十月革命催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经走向世界,就以其不同于以往任何类型制度形态的本质特性,撕下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长时期被赋予的天然合理性的面具,否定了一个社会中以极少数人对最大多数人统治的传统治理模式,昭示了人类社会走出以一种剥削制度替代另一种剥削制度恶性循环的必然性与可行性。由此所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国际政治的全部实践,出现了进行新的制度选择的可能性。这正如毛泽东所深刻揭示的那样:“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10]289;“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6]667显然,十月革命特别是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与仰慕,表现的正是对人剥削人、以富欺贫、恃强凌弱制度形态的厌恶与摒弃心态。
第二,“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决定了社会主义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维护公正、崇尚正义的价值目标。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的是逐步由蒙昧向开明、由低级向高级形态的运行轨迹。然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特别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却不断为非民主、非平等、非公正所主导,甚至出现排斥的行进取向。资本主义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剥削、干涉甚至侵略,满足其产品推销、市场扩张的需求,通过不断的战争达到对其它国家、民族控制的目的,“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11]645,人类在这样的进程中并没有把物质文明、科技发展不断获取的成果转化为价值性成就。十月革命在从俄国走向世界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一方面,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平等和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导向,使人类文明的价值选择,趋于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方向,它把千百年来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同工同酬、普遍教育、普通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享受社会保障等具体形式体现了出来,人类社会趋善趋真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形成了社会性的价值行为,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此,就连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勒特·约翰逊在1939年考察苏联后也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保证都有工作,不存在失业,消灭了经济危机。”[12]117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平等和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导向,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持续性推进不得已的内部改良,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性地推行了所谓的“新政”,把过去他们指责、辱骂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府调节、政策干预、劳资协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纳入自己的法律条文和政策主张当中,由此缓解内部矛盾、延缓自身寿命。戴勒姆—克莱斯勒国际康采恩主席施伦普在1997年德国举办的“21世纪与资本主义”大会上,就这样感叹:“全球化不仅是市场的竞争,而且也是价值的竞争……,我们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和我们的经济道德都处于竞争之中”[13]37。可以说,人类文明在价值领域的这种进步与发展,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价值感召力量,其实是不可能,或至少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十月革命在俄国”与“十月革命在世界”的内在统一,决定了社会主义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提供了抗衡殖民统治和国际强权政治的制约力量。十月革命从俄国走向世界之后,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形成了足以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对抗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打破了国际范围内千百年来经济、政治秩序形成、运行中通行的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国际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特权主义和霸权行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民族所关注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问题,开始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许多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言行拘谨、动辄看大国强国脸色行事的穷国、弱国和小国,开始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找回了曾经失去了的自信与尊严;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组织及其活动,标志着发展中国家逐步启动了由被动向主动发展转变的进程,他们在开始行使对国际经济政治生活参与、变革主动权的过程中,发现并实际上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而且也迫使在本意上并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处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变革调整中,违心地放弃许多原有的殖民地与殖民政策,在国际交往中对发展中国家作出某种让步和妥协。毫无疑问,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扩大着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旧的世界历史进程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予以理性的怀疑与变革。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对于国际强权行径的有效遏制和制衡,上述变化是不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发生历史性剧变之后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状况,则从反面验证了这一点。当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牵制与制约作用的力量突然消失或削弱后,便出现诸如肢解南斯拉夫,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并造成这些国家内部动荡的乱象等。历史事实逐渐使世界上更多的有识之士看到,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开始出现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使西方国家在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中,又一次肆无忌惮地试图以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思维方式设计并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国家开始“宣称总得有人来治理世界,为什么不是美国呢?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惜把大英帝国甚至罗马帝国的旧皇历重新搬出来,从中获得整治世界的经验教训”。[14]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局面,从一个极为特殊的侧面,对“十月革命在世界”之伟大历史作用给予了得力的注脚。
三、从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与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内在统一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
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向制度形态的转变,这无疑是构成其“20世纪最重大、最伟大的革命”历史定位的重要原因。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必然有一个与其发生过程密切相连的逐步巩固、发展和完善的演进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凡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巩固、发展和完善要求不相吻合的观念性、体制性和操作性要素,都应在改革之列,凡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巩固、发展和完善实践相吻合的观念性、体制性和操作性要求,都需要创新性发展。这就是说,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需要放诸十月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由此决定的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改革创新的内在统一关系中来认识,即十月革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就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时代大幕,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改革创新和自我完善的实践,又使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意义不断得到丰富与充实。换言之,没有十月革命,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巩固完善;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巩固完善,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就会显得十分微小。所以,必须从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与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内在统一中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
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与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内在统一,体现于十月革命本身的发生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建立的过程当中。这就是说,十月革命的发生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前述“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期”统一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选择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创新的一次突破性实践。事实上,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首先遇到的,是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卡夫丁峡谷”、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正是在反驳了第二国际苏汉诺夫等人否认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可能性的“理论教条”的基础上,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得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5]687,而是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进而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过程中,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定位,必然与其深刻内蕴着的两大创新特质联系于一体。第一个特质,是十月革命从理论与实践上,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自由资本主义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共同胜利”的成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这一新的时代本质特征,科学揭示帝国主义战线有可能在它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的客观规律,不仅在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俄国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且还基于“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8]777的创造性认识,运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逐步走向社会主义,最终找到了一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第二个特质,是十月革命后,无论是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建立人民委员会各部、人民法院、工农检查院、工人警察,并组建新的工农红军和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还是击退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赢得国内战争,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以及建立苏联,都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和不可能预见和设想的,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创新性实践。这样两个鲜明的特质告诉我们,十月革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结果,其在启动这样的改革创新的同时,就为其后社会主义在后来发展中的改革创新提供了范本,孕育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与社会主义改革创新内在统一的深远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与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内在统一,体现于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改革创新的发展当中。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一经发生,其影响就绝不仅仅存在于这个事件本身了。十月革命作为“20世纪最重大、最伟大的革命”更是如此。它本身在社会主义改革创新方面的生动实践,对其后发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改革创新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从观念形态上说,十月革命的发生,证明的是这样一条真理:“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6]399,因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1]777可以说,十月革命本身在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上的不囿成说、先行先试,成为后来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解放思想、勇于“走自己的路”大胆探索的经典依据。正是有了十月革命的这种勇敢探索,才促使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能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而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得出关于“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8]773的深邃感悟。世界范围内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认识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7]3,“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根据各国的特点来进行,这一历史的教训我们已经很好地吸取”[18];古巴共产党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巴西实际相结合,建设“巴西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19];越南共产党认为“不能再空谈理论与政治了”,应当推进社会主义革新,“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9]234-235
从实践发展上说,十月革命,特别是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改革的先河。后来一段时间内,尽管受教条式、僵化式思想观念的影响, “苏联模式”一度成为束缚社会主义发展的“桎梏”,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革并没有停止。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出现的由改革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科别尔曼争论”引发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中国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始考虑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形成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思路;5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南斯拉夫建立“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等。这些可贵的探索虽然在以后的实践中大都未能有效地坚持,但其无疑都反映着十月革命对社会主义发展创新实践的深刻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以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集中代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30多年改革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只要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当初,是如何回顾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论述,如何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经验中接受启示,则不难看出十月革命本身进行的社会主义发展创新实践,对其后各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所具有的影响。
从目标取向上说,十月革命本身对社会主义发展进行的创新性探索,无论从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皈依于一个明确的坐标定位,即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完善。这一点,促使全世界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自身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即便面对极其复杂的局面和艰辛的任务,都始终不忘“老祖宗不能丢”[17]369的道理,始终坚持着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与之相反,诸如苏联东欧国家由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导致社会主义成果被葬送的教训,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十月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对保证社会主义改革创新顺利推进所具有的意义。
综上所述,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绝不能从“十月革命”当天这个直接的、狭义意义上的概念与事件上来认识与把握,而必须从十月革命整个发展进程所体现出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中去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列宁关于十月革命“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8]563的论断,才能有更为亲切与深刻的感悟。
[1] 高放.俄国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J].科学社会主义,2017(1).
[2]宋士昌.科学社会主义通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李永全.俄国政党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列宁和十月革命[J].红旗文稿,2016(9).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9]高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1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1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2]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13]季正聚,彭萍萍,王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学术对话[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4]罗文东,刘晓辉.美国学者大卫·科兹谈“新帝国主义”[J].高校理论战线,2007(3).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6]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徐世澄.劳尔·卡斯特罗有关古巴经济变革的论述与古巴经济变革的最新动向[J].当代世界,2011(3).
[19]王建礼.苏东剧变以来巴西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2010(4).
【责任编辑曹祖明】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 Positi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from the Unity of its Internal Logic
ZHANG Zhifang
(College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hanxi Committee, Taiyuan, Shanxi 030006)
To get into perspectiv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t is important to view it from the inherent unity betwee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era of the Revolution, betwee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socialist reform and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facts and with scientific methodology, instead of being confined to its direct and narrow sense, so as to unravel the puzzles caused by the narrowness.
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t system; socialist values; socialist reform and innovation
D15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码号
号】1674—0351(2017)04—0095—07
2017-06-25
张志芳,中共山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