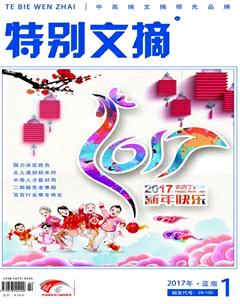粥和面包
扫舍 王寅
11岁的儿子终于喝粥了,对于中国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所有的法国孩子见到中国的粥,几乎都会做出呕吐状。他们觉得被煮烂的米粒黏答答地混在面目不清的汤水里,很像呕吐物。
有段时间,我在上海虹桥的一所法国小学里临时代课,每天下午的时候,中国阿姨总是会给孩子们送来课间的小餐:菜粥和水果。法国孩子们总是将水果吃得干干净净,菜粥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
被孩子拒绝的粥,对于我来说却有重大的意义,往小了说是暖胃的那一口,往大了说就是乡愁了。
在成都的家乡话里,粥是被叫作稀饭的。始终记得夏天的时候,母亲会花两分钱在街上买乡下人带来的荷叶,中午就煮好一锅荷叶稀饭,放凉到晚饭时吃。小饭桌上的配菜总是简单的,凉拌的大头菜丝,炒得香香的黑豆豉,遇到过节,也不过增加一盘红心咸鸭蛋。饭食是再朴实不过的了。不过,正是这样的饭食会让所有的中国胃觉得安逸和妥帖。
粥对中国人来说,是食物、药物,也是爱意。日常的饮食,生病时的调养,母爱的表达,一碗粥里都有了。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许多习惯都变了,对粥的喜好仍然不改。
法国是个连米都是舶来品的国家,哪里认得粥。他们从小是喝着牛奶吃着面包长大的。有个法国人也对我回忆过他童年时母亲做的早餐,母亲在面包进烤炉前会重重地一拍,在面胚上留下个深深的手印,他最念念不忘的,是这个散发着麦香的手印。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法国妈妈的手印也不太能见着了。法国孩子最常见的早餐是工业化生产的各种麦片,热量、蛋白质、营养都经过均衡配搭,简易,快速,健康,一切都好,就是没有任何情感回忆在里面。
住在巴黎中国城的法国人,有时候也会大惊小怪地问我:“你们中国人的碗里是什么啊?糊涂一团的东西。”说这话时,多少有些西方人的优越感,和他们说中国人吃狗肉是一个口吻。我泰然自若,你有你的面包,我有我的粥,没觉得喝粥就让我有羞愧感。只是现在我喝粥的机会也不多了,孩子们不喜欢,我是孤掌难鸣,家里也就难得做粥。所以旅行时如果遇到酒店的早餐有粥,我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白色的小米粒,温润的汤水,这是我的生命无法改变的一种状态。就如同我最适应、最不能离开的文化,注定了还是中国人的文化,汉语的语境。年龄越大,越是能感觉到时尚的、舶来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淡去,相反,一些最基本的中国生活元素,越来越让人觉得放松和舒服。
我的11岁的儿子,在这天早晨主动地要求要尝尝中国的粥。我说喝白粥一定要就着小菜,要不没味道的。儿子像冒险一样地鼓着勇气喝下去半勺粥,咂咂嘴,说还不赖,然后决定去盛上一碗来吃。
一个愿意喝粥的儿子让我感到如此亲切,如同我可以和他分享一些生命中独特的密码了,在他出生11年之后,他母亲的中国DNA终于发芽了。他未必需要喜欢粥,他当然会更喜欢法式面包,但是有一天他会理解,一个爱粥的母亲,即使生了法国籍的孩子,也仍然是个中国母亲。
(摘自《灰屋顶的巴黎》 金城出版社 图/黄煜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