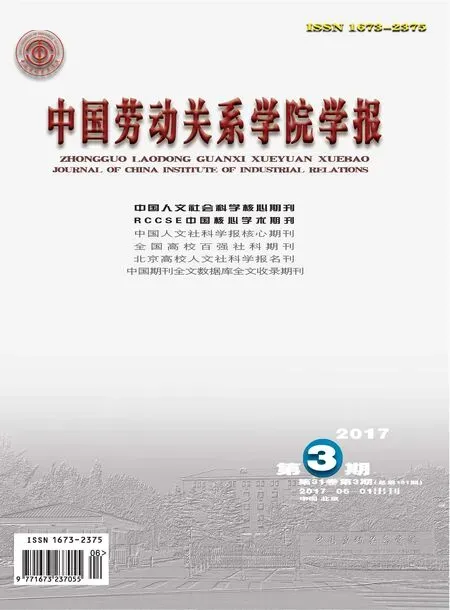推进工会体制创新是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根本路径*
—— 与常凯教授和游正林教授商榷
孙永生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推进工会体制创新是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根本路径*
—— 与常凯教授和游正林教授商榷
孙永生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是劳动关系结构和调整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尚未形成。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不能依赖于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劳动关系深层结构调整需要政府的合理干预。与市场经济国家先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立法、然后规范自发的工会组建与集体行动过程、逐步完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路径不同,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顶层设计”,首先要完成体制内企业工会职能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构建集体劳动关系法律体系,从而推动形成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劳动关系;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六期刊载了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的《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一文(以下简称“常文”)[1]。常文着力论述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起因、动力及途径,同时讨论了政府劳工政策调整与完善的对策。此后不久,游正林教授对常文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是一种历史进程”及“中国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型”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并阐述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现状,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三期上以《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另一种解读——与常凯教授商榷》为题发表(以下简称“游文”)[2]。两位教授就中国劳动关系转型这一重大问题表述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常文和游文各自提出的几个核心观点仍值得商榷。
一、“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命题的内涵界定以及多角度审视
常文提出“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这一命题,虽然文中没有对其内涵作出明确界定,但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是指劳动关系调整方式“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转变为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过程。劳动关系是指劳方(雇员、雇员组织)和资方(雇主、雇主组织)之间,因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共同创造与分享合作收益的过程中结成的所有正式及非正式的关系,其本质是体现劳方和资方双方权利与义务安排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依据劳动关系主体及劳资双方权利、义务规范与调整方式的不同,劳动关系存在个别劳动关系与集体劳动关系两种形态。个别劳动关系的主体是个别劳动者与雇主,个别劳动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一般由个别劳动者和雇主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劳动合同来确定和规范。集体劳动关系主体是劳动者组织(如工会)与雇主或雇主组织,集体劳动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则由劳动者组织和雇主或雇主组织通过集体谈判等协商交涉的方式来确定和规范。笔者理解,常文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就是集体劳动关系培育和形成的过程。
游文对常文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概念提出了质疑,并依据浙江省诸暨市党政部门软性调控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若干举措,对我国劳动关系转型作出了另一种解读。按照游文的列举,我国劳动关系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党组织融入私营企业;(2)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延伸到私营企业;(3)对非公经济人事进行政治安排与综合评价;(4)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活动;(5)组织开展有关评比活动,以引导、激励资方改善员工工作生活条件等。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游文提出的我国劳动关系的另一种转型,“虽然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转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是常文所谓的‘集体化转型’”。游文从多个方面归纳了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现状,提出“中国劳动关系的另一种转型”,按照游文的论述,笔者将这种“转型”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党政机构融入了私营企业组织;其二是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引导、激励私营企业雇主改善劳动关系,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正当权益。这两个方面的改变实则可归结为一条,即政府对企业劳动关系调整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加多元化。在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仍不和谐、群体性劳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加强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对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争议特别是群体性劳动关系事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我国劳动关系调整的这种改变,也面临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党组织融入私营企业后,党组织与企业、党组织与劳资双方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延伸到私营企业劳动关系领域,如何保障员工合法的维权行为?如何发挥政府在劳资双方权益调整中的应有职责?实践中,私营企业存在“工会老板化”的现象,那么有什么机制可以防止私营企业党组织不被“老板化”呢?游文并没有涉足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劳动关系的另一种转型”将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其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难以产生建设性的作用。
常文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与游文的“中国劳动关系的另一种转型”,表面看虽然都在谈论“劳动关系转型”,但不论在劳动关系深层结构的变化上,还是在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与义务调整的功能上,均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实质是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就外在形式,衡量的重要指标是工会组建率和集体合同签订率。从结构上看,由个别劳动关系转变为集体劳动关系所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劳动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改变了劳动关系中个别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使得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功能上,集体劳动关系矫正了个别劳动关系在维护员工权益方面的不足,员工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与雇主协商谈判,以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核心是建立起以集体团结和组织力量为基础的员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力救济”机制。
因此,不难看出,常文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是劳动关系深层结构的改变,特别是员工自己组织的形成及集体化维权机制的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劳动关系体系中个别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使得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基本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均衡,从而奠定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博弈基础,体现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本质内涵。游文的“中国劳动关系的另一种转型”,所改变的主要是政府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干预方式及干预强度,但处理劳动关系的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更迭,劳动关系的深层结构也未发生显著变化,仍然保持着个别劳动关系的格局,属于劳动关系的“非根本性改变”[3]。
二、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究竟应不应该算作是“一种历史进程”
常文基于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演进实践及劳动关系理论发展,分析了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型的重要意义和必然趋势,认为“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结构和调整的一种历史进程”。游文通过剖析美国劳动关系发展历史,明确指出,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并非一种历史进程”。按照游文列举的事实,1935年美国的《瓦格纳法》颁布,“实际上开启了美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在此后的20年里,美国的工会活动明显增强。”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国家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美国的集体化转型”。之所以“集体化转型并非一种历史进程”,游文的理由是,进入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美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人集体谈判协议的覆盖率在下降,非工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受到重视。因此,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至少在美国就没有成为一种历史进程”,相反,还面临着“去集体化”的转型。另外,游文发现,“我国的劳动关系并没有出现集体化转型”,更支持了“集体化转型并非一种历史进程”的观点。
笔者对游文的这一推理不敢苟同。具体理由在于:其一,尽管劳动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再有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工人入会率及集体协议覆盖率降低,个别劳动关系受到重视,但美国的集体劳动关系并没有消失,法律赋予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所产生的强大威慑作用,时刻影响着劳资双方的力量博弈。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和限制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情况下,即便在美国市场,能有多少企业雇主会自觉自愿地真心维护员工的权益。正是完善的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对组建了工会采用集体协商规范双方权益的企业员工,产生了直接而富有成效的保障作用,而对没有组建工会或没有参加工会的员工,同样可分享到集体劳动关系带来的“溢出效应”。美国要在逐渐弱化的集体劳动关系框架内,发展具有更高竞争力和柔性的个体劳动关系和非典型雇佣关系[4],这是在全球化发展背景及集体劳动关系威慑下理性雇主的更优选择。因此,不存在劳动关系“去集体化”的转型。其二,《瓦格纳法》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了工人组建工会和实施集体谈判的权力,意味着集体劳动关系在法律上已经确立。自《瓦格纳法》颁布及美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劳动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在近40年的发展中,不论从制度规范还是从劳动关系实践判断,美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早已成为美国劳动关系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其三,我国劳动关系当下没有出现集体化转型,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发生,显然,因为没有看到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而否定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必然趋势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可取的。
正如常文的相关分析所言,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员工追求自我保护的权利诉求,是对个别劳动关系在维护员工权益方面存在缺陷的克服。从主要依靠个别劳动关系调整,逐步转向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依托,是劳动关系调整发展的一般轨迹,也是各国劳动关系调整的通常做法。从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实践可以看到,员工合法权益的正当维护客观上需要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而逐步提升的劳动者权利意识和集体意识成为集体劳动关系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也是提高政府劳动监管效能、节约社会成本的更优选择。因此,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同样是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一种历史进程”。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三、到现在为止,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尚未完全形成,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常文正确分析和指出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但对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则过于乐观,认为“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从常文通篇论述中可以看出,支撑这一观点的理由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认为劳动关系实践中,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权利诉求相当强烈,个别企业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推动了集体谈判及工会的改革,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方式在这类企业似乎已经形成。其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契机和新起点”,并列举了三点理由:(1)《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制度层面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2)《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普遍提升了全社会的劳动法制理念;(3)《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提升了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集体意识。
就《劳动合同法》实施对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转型产生的影响,游文分析认为“这三点理由均难以成立”,“常文对《劳动合同法》实施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对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意义的判断未免武断”。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对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以及全社会的劳动法制观念一定会产生提升作用,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制度层面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这一论点值得商榷。之所以持此言论,是因为:首先,正如游文所言,《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涉及劳工的集体权利问题,不是集体劳动关系制度的设计。其次,“以劳动合同制度为主要标志的个别劳动关系的规范和稳定,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了需求”这一理解也不正确。如果以劳动合同制度为主要标志的个别劳动关系实现了规范与稳定,有效保障了劳工权益,集体劳动关系没有必要构建。正是由于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中劳资双方不对等的权利诉求与维权行动,无法有效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集体劳动关系构建才有了需求。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需要规范的劳动法律制度,但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当集体劳动关系主体不清晰、不独立的时候,法律规范如何调整?在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中,如果现有工会的多元主体地位及职责不变,仅靠法律上规定“集体协商中工会必须代表员工利益”这样的条文是没有意义的。实践中,大量侵害员工权益的违法事件的发生,不是法律没有规定,也不是工会组织不了解,而是工会组织没能唯一代表员工权益所致。所以,可以认为常文夸大了《劳动合同法》实施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对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作用。
至于在具体的劳动关系实践中,个别企业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对集体谈判及工会改革的推动作用,及其对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转型产生的影响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也值得商榷。就某个当事企业而言,“南海本田”式的工人自发集体停工事件可以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如果政府部门能够采取“理智对待,法制解决”的方式,在当事企业确实有效推动了集体协商谈判及工会的改革。但“南海本田”的工人自发集体停工事件,在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属于极少发生且成功应对的典型案例。而这种工人自发集体停工产生的“威慑”作用,需要机制化、合法化,更需要得到社会大众的接受和认可。因此,正如游文所言,“即使存在常文所说的上述作用,那也只是局部的、短期的作用,并未在整体上对我国的劳动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从目前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实践中来看,工会组建率和集体合同签订率,不难发现,我国的集体劳动关系的外在形式已经具备。但正如常文所言,对于集体劳动关系是否已经形成的判断,“更要看集体合同是否经过了协商谈判,其内容是否规范有效并能够落实”,“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内容,集体劳动关系便不可能形成”。此外,“中国企业工会组建和集体协商是党政主导以行政化手段推行的,存在着严重的指标化、数字化和形式化等问题。”现在,一些企业工会组建主要由雇主控制和主导,形成了许多“挂牌工会”、“空壳工会”和“老板工会”。现有的集体协商谈判,不是企业劳资双方的主动行为,这一制度没有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产业关系的系统框架[5]。在一些地方,集体协商谈判及集体合同制度,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维护劳动者权益和调整劳动关系的原意,而演变为一种政绩工程[6]。可以看出,真正意义上或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的集体劳动关系在我国远没有形成。事实上,常文也是明确指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的劳动关系,其性质基本上仍然处于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状态,即一个雇主面对一群工人的这种个别劳动关系的构成状态。”
四、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不能依赖于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
一方面,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是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又不能自然发生,需要政府和劳动者的共同推动。那么我国劳动关系如何实现集体化转型呢?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与常文商榷,并提出自己的思路。
需要强调的是,常文详细论述了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路径与特点。首先明确指出,与个别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主要是政府推动所不同,“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则是由政府和劳动者共同推动进行的”;其次,提出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过程中,“有两种力量和两种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然后,重点论述了党政主导的自上而下建构集体劳动关系这一途径的诸多缺陷,以及劳动者自发的集体行动对集体劳动关系形成的有效推动作用。常文肯定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实际推动作用,认为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劳动关系集体化的两个基本指标方面”,即“有效推动了集体协商谈判的进行”和“促进了工会改革,加强了工会和工人的联系”。基本结论是,“工人的集体行动以及各方对于事件处理的理智态度,促进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两种路径的结合及相互促进,积极推动了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
常文虽区分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两种路径”,但从文中描述的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个案看,常文的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路径实则是“两种路径的结合”。笔者将常文的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路径理解为这样一种过程:在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直接推动下,通过政府干预,完善工会对工人权益的代表性,然后由工会组织与资方开展集体谈判并达成集体合同。这一路径的核心要件是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政府干预及集体谈判,而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没有工人集体行动的“威慑”,加之一些地方注重表面形象的“政绩工程”的掩护,“老板工会”与资方的集体谈判及达成的集体合同必然流于形式[6]。
常文正确指出,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需要政府和劳动者的共同推动,也就是实现“两种力量和两种路径的结合及相互促进”。但常文以“南海本田事件”为蓝图,将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寄希望于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的思路笔者不敢苟同。“南海本田事件”的发生与成功处理,彰显了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在维护员工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会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典型的个案在当时发生的情况下,由于受到媒体、官方、学界等社会各方面的关注,通常都会“理智对待,法制解决”,员工当时的权利诉求一般也会较好地满足。但这种劳工事件难以形成“南海本田事件”式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长效机制,非当事企业原有的“资强劳弱”的劳动关系格局依然存在,工会组织的多重身份及多元化利益导向没有改变,因此并没有解决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在中国情景下,鼓励企业员工以这种无序抗争的集体罢工方式,向企业、工会及政府施压,来求得员工权益的维护,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也可能导致劳资矛盾演变为员工与企业、政府甚至工会多方的矛盾。政府、工会及企业管理方亦不会让这种事件重复发生,当事企业及类似企业会受到各方的格外关注,致使集体行动能力被进一步弱化。所以常文提出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路径只可能存在于局部地区的个别企业,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是暂时的。
五、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应该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可行路径
目前,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形成的主要制约因素,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的缺失及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特别是劳动者组织主体的不完备性。在现有工会组织的利益代表多元化问题没有改变之前,单纯推行形式上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无助于从根本上维护员工权益,反而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合理合法”的侵权事实。因此,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最关键的障碍,是如何在现有工会组织框架下真正代表和发挥维护员工权益的作用,也就是常文所说的“如何处理工会组织和工人的关系问题”。
常文客观而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两种劳工力量主导的两种劳工运动(即体制内以全总为代表的现行工会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会运动,及体制外劳动者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劳工运动),深刻地阐述了工会组织与工人的关系现状,也清晰地表达了现有工会组织不能有效代表工人合法权益的尴尬境地。但常文提出,通过“两种劳工力量的相互支援和相互补充”,便可有效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进而推动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反观近些年我国劳动关系实践,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迫使工会组织维护员工权益,但体制内的工会组织很少会主动支援工人的集体行动,只要发生了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之后,工会及企业管理方都会尽一切可能防范工人集体行动的再次发生。工会与工人“两种力量”的矛盾与对立是我国劳动关系的“怪象”,凸显了工会组织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与其把真正代表员工权益的工会组织的培育寄希望于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不如通过“顶层设计”,推动体制内工会组织进行主动的市场化变革。
不论体制内工会组织的市场化变革,还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的完善,都需要政府扮演核心角色。因此,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路径,应该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推动体制内企业工会组织的变革和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的完善,培育员工自己的组织主体,均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格局,并规范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权利诉求方式,创造劳资自治的内在条件,逐步形成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关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律的重要性法学界早已认识并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准备,所面临的最主要阻力其实不是法律本身,而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要调整的劳工组织主体的功能缺失或不清晰。现有工会组织不能真正代表员工权益的缺陷仅靠法律条文是无法解决的,如果集体劳动关系立法以现有工会组织体制为基础,其结果可能是要么有法难依流于形式,要么偏离确认和保障“劳工三权”的立法宗旨。因此,与市场经济国家先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立法、然后规范自发的工会组建与集体行动过程、逐步完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路径不同,我国已经存在体系完整、功能强大的工会组织,不可能依靠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在现有工会体系之外自然成长起工人自己的组织。我国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顶层设计”,首先推动体制内企业工会职能变革,培育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并构建集体劳动关系法律体系,最终形成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事实上,有关劳动关系的任何制度变革在缺乏政府积极干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7]。劳动法律的制定、劳动合同的实施、工会职能的发挥、劳动争议处理等均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干预。游文列举的“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种种表现,例如为改善劳资关系,将党组织融入企业、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延伸到企业等做法,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企业劳动关系干预的重视程度。但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核心职责,是制定、监管劳动法律政策的顺利实施,并推动劳动关系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如常文所言,“政府劳动关系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政府协调下的劳资自治”。如果只是单纯出于稳定社会治安,以防止和化解劳资矛盾,尤其是针对群体性劳工事件为目标的政府干预对策安排,可以部分地产生“堵水”的作用,但很难形成“治水”的长效机制。当前,实现劳资自治的最大障碍是劳资双方特别是员工组织主体的不完善。没有清晰独立的调整主体,政府干预或法律规范都无从着手。因此政府干预的当务之急首先是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的培育,其次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律体系的构建。
六、推进企业工会组织职能变革是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首要任务
我国工会体系完整且功能强大,但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工会的独立性、效率和凝聚力都存在一些问题,往往既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更受到雇主力量的制约[8]。使得工会既具有“国家属性”又具有“社团属性”,集体协商中扮演的是“双重代理”角色,既代表员工的利益,同时又要代表政府的利益[9]。企业工会肩负着维权、维稳和维序的多重任务,从实践中的运行情况看,当这些角色发生冲突时,工会更多选择站在企业一方,因为当前我国企业工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企业[10]。这种多重身份、多元化的利益取向以及实践中不规范的运作,导致“地方工会行政化”和“企业工会老板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工会与劳动者脱离的问题一定程度存在[11]。如常文指出的,近些年各地频发的“工人集体停工事件”表明体制内工会并未有效代表劳动者权益,集体合同也没有发挥协调劳动关系的作用。显然,不能保障工人自己组织的有效性,集体劳动关系就无从谈起。
因此,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体制内企业工会组织职能变革,更好地服务于员工维护其权益。可以通过体制内工会组织的深化改革,去除弊端,为维护职工权益和社会发展服务。基本思路是,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工会组织的职能分割,完善工会对于员工权益的代表性;针对基层工会改革,政府成立企业工会指导委员会,指导员工通过直选产生企业工会组织,从源头上赋予企业工会代表员工权益的职能。可在企业层面同时存在企业工会指导委员会和企业工会,企业工会指导委员会具有国家属性,代表国家利益,指导和监督企业工会的运作。企业工会具有社团属性,唯一代表员工利益,成为集体劳动关系中员工的组织主体。企业应赋予这一员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知情权和协商权,以增强员工参与企业决策及维护自身权益的影响力。
在企业工会的职能得以更好地发挥之后,为保证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规范进行,需要明确界定工人和雇主各自组织的权利界限在哪里、工人集体行动发起和组织处理的程序是什么、以及工会和雇主在劳资冲突中应承担哪些权利和义务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完善的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目前由人大通过的所有劳动法律中,除了《工会法》及个别法律中的个别条文之外,都是对个别劳动关系调整的规定,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尚处于零散残缺的状态。集体劳动关系法律主要是围绕工会组织、工人集体行动或罢工、集体合同、集体争议等问题进行立法,其核心是确认和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即“劳工三权”的实现。
体制内企业工会完成职能分割、主体重塑及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完善后,政府对企业工会的领导方式会发生变化,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成效也会提升。(1)政府通过工会指导委员会对企业工会的组建和运行产生直接影响,权责清晰,指向明确。(2)企业工会组织自然承担了个体员工权益维护的职责,政府无需面对数量庞大、权责各异的个体对象,行政监管的难度和成本都会降低。(3)工人集体行动有了组织领导和法律规范,也会变得有序和更加理性。(4)最重要的是营造了“劳资自治”格局,劳资双方的权责安排及相关争议处理,可以通过面对面的协商谈判解决。“劳资自治”是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机制,这一机制得以有效运作的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规范和政府监管的外部作用;其二是劳资合作的企业制度基础。企业是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共同实现价值创造和追求合作收益的经济组织,“共同实现价值创造及对合作收益的追求”是劳方与资方建立“关系”的根本原因,也客观上决定了劳方与资方必然是不可或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因此,法律规范与政府协调下的“劳资自治”是调整劳动关系的理想选择。
[1]常凯. 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J].中国社会科学, 2013(6).
[2]游正林. 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另一种解读——与常凯教授商榷[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3).
[3]Christopher L. Erickson and Sarosh Kuruvilla,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Transformation[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8(1).
[4]张立富. 中国和美国劳动关系转型的比较分析[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0(4).
[5] Clarke S., Chang-Hee Lee and Qi Li.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4(2).
[6]王晶. 集体协商谈判制度须以劳工三权为基础[J]. 战略与管理, 2011(5).
[7]Chris Howe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French Industrial Relations: Labor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ate in a Post-Dirigiste Era[J]. Politics & Society, 2009(2).
[8]夏小林. 私营部门: 劳资关系及协调机制[J]. 管理世界, 2004(6).
[9]吴清军. 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J].社会学研究, 2012(3).
[10]陈维政, 任晗, 朱玖华, 王西枘, 陈玉玲. 中国企业工会角色冲突对工会职能作用发挥的影响和对策研究[J]. 管理学报, 2016(3).
[11]程延园. 世界视阈下的和谐劳动关系调整机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5).
Innovating Trade Union System is the Fundamental Path to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Consulting with Professor Chang Kai and Professor You Zhenglin
SUN Yongsheng
(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Shannxi Province, China )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relations structure and adjustment mode, but the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are not yet formed.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can not depend o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worker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deep structure of labor relations requires reasonabl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countries through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legislation, then regulating spontaneous union formation path and collective action process, and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can only be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top-level design", the fi rst to complete the system change of the enterprise trade union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adjustment mechanism.
labor relations;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
D412.6
A
1673-2375(2017)06-0104-08
[责任编辑:简 洁]
2017-02-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3YJA630080);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5JZ031);西安工程大学学科建设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07091202)。
孙永生(1971—),甘肃庆阳人,博士,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企业员工激励及劳动关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