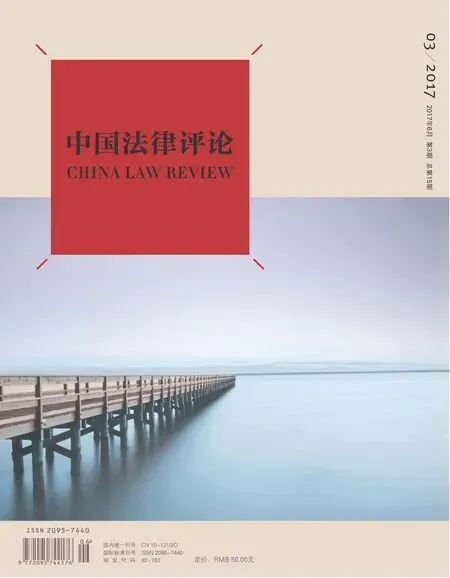法学教育的历史批判
——张伟仁教授《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读后
翟志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教育的历史批判
——张伟仁教授《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读后
翟志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重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并把培养涉外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口,从而探索“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探索“国内—海外合作培养”机制,建设80个左右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20个左右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对于何为卓越法律人才、如何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意见》并没有明确说明,学界对此虽有诸多探讨,1参见岳彩申、盛学军主编:《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国内—海外合作培养”的高门槛和高成本,《意见》基本上落实为“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因而成为所谓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主要培养机制。
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迫切性,学界早有探索,真正理论与实践并行的,莫过于已故的何美欢教授,她只身在清华大学撑起了“一个人的法学院”。2有关何美欢教授在清华法学院的探索和实践,参见王振民等:《君子务本——怀念清华大学法学院何美欢老师》,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版。“一个人的法学院”是赵晓力老师对何美欢教授所从事的事业的概括。但是,即便将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为培养律师的何教授,亦坚决反对法学教育沦落为法律实用技能的培训。她区分了“理解、适用、分析、归纳、评价”这样的智能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和诉讼技巧这样的实务技能,指出前者应由法学院的学术训练提供,而后者应由实务部门的实践经验提供。因此,即便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也应该是且必须是“学术性的”和“博雅的”(liberal)职业教育,中国法学教育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致力于不应该且无能力提供的实务技能培训,而抛弃了它本应该且必须提供的智能技能的训练。因此法学教育的失败不是它不够“应用”,而是它不够“学术”。3参见何美欢:《理想的法律教育》,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九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40页;亦可参见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123页。遗憾的是,中国法学教育并没有认真对待何美欢教授以生命代价探索出的“理想的法学教育”,而是继续坚定地站在既往的错误之上奋力前行。
2012年1月,张伟仁教授出版了《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如果说何美欢教授从一个纯正的西方法律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诊断中国的法学教育,那么张伟仁教授则从传统中国的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角度把脉现时代的法学教育,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进一步思考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审视中国法学教育的“秦镜”。读者或许惊诧,传统中国没有法治,又何来的法学教育?不过惊诧和质疑之前,不妨先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这本文集不只是纯粹书斋里的学术思考,而且是张伟仁教授法律人生的切身体验与感悟。张伟仁教授一生辗转大陆、台湾地区和海外,从早年的私塾教育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西式教育,从一个孜孜以求的国际法学生到一位名贯中西的中国法制史学者,他的学术人生可谓浓缩了古今中西法律教育的诸多因素,其自身可谓近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部活历史。4有关张伟仁教授的学术经历,参见张伟仁:《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第291—305页;亦可参见张伟仁:《学习法史三十年》,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287页。因此,他的观察和思考,他的夫子自道,对于今天关心中国法学教育的人士来说,不可不察。
一、多元规范中的法律
我们对法律的认知,决定了我们对法学教育的理解。虽然《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一书副标题强调这是一部法学教育论文集,但是通读全书就会发现,它首先是一部法理学著作,集中展现了作者关于何为法律、法律的功用与限度、法律与其他规范的关系、谁具有立法权威、权威的正当性何在等最为基本的法理学问题的思考。5作者对这些问题更为全面的探讨和资料整理,参见张伟仁辑:《先秦政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进文:《权威与规范之间——读〈先秦政法理论〉》,载许章润主编:《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311页。这种思考的一个基本框架是,法律只不过是多元规范体系中的一种规范。作者有关法学教育应该如何的讨论,同样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之上的,因此有必要先对这个问题略作说明。
在作者看来,“在我国的传统观念里,社会的安宁秩序要靠许多规范的协同运作才能适当地维持,其中包括自然的天理、神旨、道德、礼俗以及人为的法律、家训、乡约、行规等。”(第228页)这些规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规范体系,相辅相成,共同维持社会的公平和谐。其中天理最高,神旨、道德、礼俗次之,而法律仅仅是人为规范中的一种,并且因其人为性,法律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规范。因此,传统中国形成一种“天理、国法、人情”的整体性规范秩序观念,“在国人心目里,法律绝不是最高、唯一的规范,它不仅要受天理的指导,还要确切地配合人情,否则就没有遵循的价值了。”(第246页)
正因为社会秩序要靠一整套规范来维持,因此法律的运作事实上需要其他规范的制约、支持和补充。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除了讲法律最终需要人的执行之外,还意在强调法律只有置于整个规范体系内才能得到有效运行。如果一个社会过分地重视法律,将法律视为最高的和唯一的规范,那么“一般民众看到国家只重视法律,当然就将礼、义等高阶规范置诸不顾,也不再尊敬社会权威,而只是顽强地抱着一套法条,斤斤计较其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第230—231页)轻视法律不可取,“拜法教”亦不可取。
这样的论述对于汲汲于法治的国人来说,显得有点刺耳。我们仍在致力于法治实现,怎么又让我们不要迷信法律呢?作者显然意识到会有这种质疑,因此给予了充分的解释。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人对待权威与法律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往返,要么就是绝对的屈从,要么就是绝对的拒斥。对于权威,要么就是青天,要么就是昏官;对于法律,要么就是善法,要么就是恶法。但无论是权威还是规范,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事实可能处于这两极之间,但是中庸的事物都不易造成鲜明深刻的印象,难怪人们不容易建立起一套平衡而切实的观念,一想到权威和规范,在许多人的心目里所显现的,往往只是那两种极端形象。”(第225页)然而,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都不是常态。一种理想而惬意的社会秩序,往往展现的是生活本身的“常态、常规与常例”,反映的是人心本身的“常识、常理与常情”。法律不是别的,实乃世道人心的镜像。“作为规则,法律描述和呈现的不外此世道人心,将人间世换形为可得检索的条文。作为规则背后的意义体系,法律要叙说和满足的还是这世道人心,将理性和情感牵连一体。”6参见许章润:《法律的人性》,载氏著:《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世道人心是法律的魂魄》,载氏著:《六事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作者进一步分析,几千年来之所以建立不起来这样一种中庸之道,实在是因为普通民众没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之中,只能在不满现实和向往理想两个极端之间打转。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扩大政治参与,只有当民众成为国家治理和法律制定的参与者时,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建立起公允持平的观念和秩序。7正如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所阐明的,现代法律的正当性要求“法律规范的承受者应当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把自己理解为这些规范的理性创制者”,“现代法律的基础是一种以公民角色为核心,并且最终来自交往行动的团结。”如果公民未能参与法律的创制,那么必然会从工具主义的立场来对待强加给他们的法律。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41、127页。
之前我们缺少法治,所以今天急切地盼望着法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拜法教”的后果是贬低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将法律尊奉为最高的和唯一的规范,其结果往往是真正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法律反倒成为工具主义的社会治理技术。因此,法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法律条文之治,法律必须在整个规范体系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功用,法治的真正实现,必然有赖于规范体系的整体有效性。作者告诫学法之人:“法不是一种独立自足可以自判其是非良窳的规范,它的意义可能不明确,目的可能不妥当,适用范围可能不周密,种种缺失皆须依据其他规范,特别是道德,加以厘定、评判、补正,这种法与其他规范并存互补的关系是学习法律的人必须牢记在心的。”(第311页)就此而言,法学教育就不能仅仅专注于逐字逐句的文义解释和理则分析,而要拓展到法律规则之外,关注整个规范体系。
二、法学教育而非法律教育
作者开篇引《西京杂记》8《西京杂记》,(汉)刘歆撰,(晋)葛洪辑,是一部古代笔记小说集,“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首都长安。该书记载了诸多帝王后妃、公侯将相、方士文人的遗闻轶事。中的故事,以“秦镜”喻清明正直、擅长断狱的官吏,而磨出这样一面镜子自然就是法学教育的具象化了。作者先概述清代的法学教育,进而以汪辉祖和陈天锡为个案,剖析传统法学教育产生的结果。“清代正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都不重视法学,当时直接从事法制工作的官吏、书役等人所需的法律知识,大致都由自修、历练而得。”(第86页)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应用型”人才,接受的是“学徒制”的实践教育。与此同时,“他们大多是科举考试的落第士子,在学习法律之前,已经受过相当完整的传统制式教育,对于中国文化已有了相当深度的认识,因而可以接受法学教育,而不仅仅是法律教育。从他们留下的一些著作来看,他们处理司法事务时不仅能妥善地引用法律,并且能够顾及道德习俗,做到通情达理,可见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序,第6页)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复合型”人才,不是只知道法律条文的法律工匠。说起来有些吊诡,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非正规的学徒制,却培养出今天求之不得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而今天大学里正规的法学教育,却对此无能为力,以至于要靠建“基地”来解决。那么今天的法学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作者依据多年来在大陆多所学校教书的切身体验,结合自己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一针见血地概述了中国法学教育的三大弊病。
首先是偏狭浅薄。“一般学法之人仅仅抱着一些中外法条和学说咬文嚼字,不知法律之外还有其他规范,法学之外还有别的学问,对于中外文化和现实社会大多茫然无知,至于世界情势、时局趋向和人类应该追寻的理想,更无法掌握,目光如豆,只能以极小的观点去看问题,犹如坐井观天之蛙。”(序,第8页)现如今的法学教育在司法考试的无形指引下,急切地希望与实务对接,最终沦落为司法考试的培训机构,司法考试大纲俨然成为法学教育的纲目,能够迅速地解决实务问题,成为法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法律之外的学问无意也无暇顾及。更为严重的是,现如今的法学教育完全教条化了,所学都是抽离现实的抽象概念和条文,看似很“应用”,实则与真实的法律实践差距甚远,学生参加工作后,仍要从头学起。对这种过分追求“应用”,而忽略了法之精义的情形,作者引荀子之言告诫学法者:“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荀子·君道》)(第242、317页)冯象先生也有类似的警告:“法律教育就不应附丽于法治的需求,囿于培训实用人才或法律技工,虽然这是雇主们的愿望和资本的利益所在。”但却不应成为一流法学院追求的目标。9冯象:《法学院往何处去》,载氏著:《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其次是崇洋忘本。刻下中国法学院课程“教的几乎全是外国的东西,一般学法之人没有能力去探究其背景,只好熟诵强记,然后开口闭口不是外国某一法学家怎么说,就是外国某一法条、某一制度、某一实践如何如何,犹如学舌的鹦鹉。”(序,第8页)清末以来新法制的建设固然需要我们了解移植而来的西方法律,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脱离了西方法律得以运作的语境,法律完全变为僵死的概念和规范。“中国法学教材大部分已经‘去知识化’,因为,它们遵循从清末开始的同一套路:追溯法律的西方源头,重述西方法律原理,以同一句法表达法律概念的定义,将相似概念放在一起比较、解释和分析法条——这一切都是脱离经验的形而上学,但法学绝对不是形而上学的自说自话。”因此,法学教育必须回到中国的法律实践,只有将法学概念、法律条文和它们适用于具体情形的推理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能形成新的知识。10方流芳:《法律人为什么容易学坏?》,载http://fangliu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50056,2013年2月6日访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多不合逻辑的扞格与龃龉,对此的阐述和理解,实际上需要我们不断地回溯历史。新的法律制度很容易被制定出来,但却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传统思想塑造成的,要了解现代人的行为,尤其是涉及法制的行为,必须对传统的法律思想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第301页)11历史之于法学的意义,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已有充分的论述,在萨维尼看来,“任何时代都不是独立地和任意地创造出它的世界,而是在与整个过往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做到这一点的。”历史提供当下与过往的有机关联,在这种相互关联中,我们才能拨开外在现象,把握其内在本质。[德]F. K. V. 萨维尼:《论〈历史法学杂志〉的目标》,朱虎译,载许章润主编:《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最后是伦理缺位。“这种教育重在讲述技术性的法条,忽视了学生的德育,以致他们大多成了擅长利用法律、钻研条文的法匠或刀笔吏,不仅在工作时无视于职业道德,甚至在个人生活里也悖理背义,而且自以为是,不知廉耻。”(序,第8页)伦理缺位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但无疑今天是最严峻的时刻。清末以来新法制的建设,从反面来看就是一个驱除伦理和道德的过程,而法律人如果伦理缺失,无疑是法治建设最大的灾难。“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越高,越会损害社会。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越精,越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12杨兆龙:《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载《杨兆龙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方流芳教授有关“法律人为什么容易学坏”的研究,无疑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伦理教育的缺位,导致的结果是“现在大多的司法者似乎都只见到法律条文,对于条文应该遵循并追求的高阶原则和理想没有什么认识,更没有遵循并追求此等原则和理想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和律己敬业的修养” 。(第178页)
令作者痛心疾首的是,中国当下的法学教育,完全沦落为纯粹的法律技术教育,但法学既然办在大学里,就不应该自贬身价,甘当法律实务技能培训班,否则大学就无须办法学教育了,回归传统的学徒制岂不是更好?再回到作者开篇所述的“秦镜”,作者以磨镜来比喻法律人才的培养,这是一个缓慢和精细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磨出一面真正的秦镜,仅仅学习法律是不够的,还要学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以现代的知识分科而言,包括历史、哲学、文学、各种社会科学和一些基本的自然科学。这样的教育可以称为法学教育,而不是法律教育。”(序,第2—3页)真正的法学院应该提供超越法律条文的法学教育,这种教育对于学生的意义,正如冯象先生所言:“法学院即真正一流的法学院的教育,对于你们最大的好处不是职业训练,而是职业批判:通过批判丰富你们的知识,训练独立的思维,树立人生的理想。”13冯象:《法学院往何处去》,载氏著:《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对于法学教育至关重要,法律人不是简单的法律适用机器,而必须致力于对现行法制的不断改善,这必然需要法律人的批判精神和能力,这种精神和能力是无法从法律条文的学习中获得的,需要扩展到法律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14马汉宝:《法律教育之前瞻与基础法学》,载氏著:《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9页。正如张伟仁教授引英国上议院前法律大臣拉德克利夫所言:“我们无法通过学习法律来认识法”(We cannot learn Law by learning Law)(第317页)。
三、通识教育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无论是应用型还是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仍然是在法律教育而非法学教学的框框里打转,并自以为是与国际特别是与美国法学教育接轨。但何美欢教授早就提出告诫,我们对于作为职业教育的美国法学教育存在重大误解。美国法学院所谓的职业教育,并非实务型的而是非常学术化的,近些年来更是跨学科的,虽然有案例教学、法律诊所,但所训练的是学生的智能技能而非实务技能,且这些并非法学教育的核心。美国法学院这些年新进的教师大多都有一个非法学的博士学位,因此这里的“联合”是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而非法学院与实务部门的联合。此外,由于美国法学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学生在本科阶段已经接受了非法学的学士教育,其中重要的部分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这使得法学院毕业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15参见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2页。就此而言,《意见》提出的“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不但未能扭转错误的方向,反而是越走越远,背离了大学教育真义,彻底走向了职业培训。
张伟仁教授根据传统中国法学教育的经验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倡言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对于法学教育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西方法学教育的普遍做法,而且“中国历代认真学习法律的人也都是先受过传统教育的训练,对于经典、文学具有相当的认识。因为这些人对于所处的社会所知深刻,所以能对当时的立法、司法及法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不是仅仅注目于法律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第312页)在何美欢教授设计的七年制的法学教育基本课程中,前四年基本上就是一个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课程方案,法学类课程仅有一门中国法制史;而且她的方案比美国的法学教育更进一步,因为这一方案的前四年非法律类课程与后三年的法律类课程息息相关,都是相关的人文社科类课程,而美国法学教育对本科所学课程并没有严格要求。16参见何美欢:《理想的法律教育》,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九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8页。何美欢教授是律师出身,并坚定地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律师,但她所设计的理想的法学教育课程中一多半却是人文社科类课程,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古典时期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现代延续,“其目的是培养出一个对于自身、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17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通识教育鼓励一种超越具体学科的整体的知识观,珍视“非功利”的学习的价值,认为“通过坚持基础知识、反思、艺术创造与分析的重要性,通过坚持科学概念与经验的精确性,一种宽广的和基础的教育将改变和解放学生。”18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urricular Renewal in Harvard College, 2006, pp.74-75, http://isites.harvard.edu/fs/ docs/icb.topic830823.files/Curricular%20Renewal%20in%20Harvard%20College, 2013年2月6日访问。因此它与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能力的专业教育截然有别,它旨在“解放”学生,而非“规训”学生。通识教育在20世纪初兴起,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应对19世纪末急剧分化的专业教育所带来的知识碎片化,从而保证学生将来成为各种各样的专家的同时,仍不失健全的人格和自由的品性。
不仅如此,在一个日益多元复杂和全球化的时代,通识教育承担凝聚社会共识、培养合格公民的时代使命。特别是在崇尚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通识教育不但要塑造个体的自由人格,还要为社会提供基本的价值共识,以免在多元分化的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抉择瓦解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进而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石。从美国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次通识教育的重大讨论或改革,其背后都能看到某种社会与文明危机的影子。因此,通识教育在培养完整的“人”之时,还要培养适合于现代社会的自由且具有美德的公民。由此就不难理解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方案设定的目标了:通识教育为学生的公民参与预做准备;通识教育教导学生将自己视为诸人文、观念和价值传统的产物,并参与到这些传统中;通识教育为学生批判性地和建设性地应对变革预作准备;通识教育培育学生对其所言所行的伦理维度的理解。19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 Harvard College, 2007, pp.5-6, http://isites.harvard.edu/fs/docs/icb. topic830823.files/Report%20of%20the%20Taskforce%20on%20General%20Education.pdf, 2013年2月6日访问。
回到法学教育,何谓卓越法律人才?如何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再来看看民国先贤是怎么理解的。燕树堂先生曾论断,“法律教育之目的在训练社会服务的人才,不是在造就个人谋生的能力。”因此要造就学法之人的“法律头脑”,包括:社会的常识,即对社会人情之了解;剖辨的能力,即前述何美欢教授所谓的智能技能;远大的理想,即辨理俗事的任务而有超俗的思想;历史的眼光,不明社会的过去,无以明了社会的现在,更无以推测社会的将来。这样一种法律头脑的养成,自然需要法律之外其他学科的教育。20燕树堂:《法律教育之目的》,载氏著:《公道、自由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7页。吴经熊先生对燕树堂先生的论断大为赞赏,并进一步申述了“远大的理想”和“历史的眼光”。杨兆龙先生则批评法学教育中非法学的补助课程不完备。蔡枢衡先生倡言:“假定要求法学者对于法学以外的学问保有各该部门最高的水准以上的知识,固然不合理;硬把某些部门排压在法学者应有的知识之范围外,也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抑且不必逐一列举和法学有关的学问之部门,但却不妨认为,任何知识都和法学直接、间接保有或深或浅的关系。这是现代知识的教训,也是近代式的中国法学的历史之启示。”21分别参见吴经熊:《法律教育与法律头脑》,载氏著:《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17页;杨兆龙:《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载《杨兆龙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5页;蔡枢衡:《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载氏著:《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2页。只可惜,这个“历史之启示”,张伟仁教授今天依然要继续讲下去。
张伟仁教授认为:“学习法律而求实用并没有错,但是不可以只求小匠之用,仅仅盘弄盘弄条文;而应该探求大师之用——首先认清法律与社会的根本关系,然后去参与立法、司法的工作,使法律发挥出最妥当的社会功能。”(第288页)因此所谓卓越法律人才,一定不是搬弄法条的技术工匠,而应该是正义秩序的缔造者、法律的批判和创造者、广义上的立法者;他们所需要具备的,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和社会科学知识,从而能够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创造出一种中国文明的法律秩序。这是每一个学法之人应该秉具的远大理想,更何况所谓的卓越法律人才。因此,在不打破现有法学教育的制度框架的情况下,减少一些专业课程的学分,增设一些通识教育课程,在培养专业法律人才的同时,使其具备健全的人格和自由的品性,是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基础性工作。这是中国法学教育急于接轨的美国法学教育的惯常做法,更是中国传统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历史启示。
策 略
Strategies
*张伟仁:《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为了简洁起见,以后凡引用该书文字,仅在引文后的括号内标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