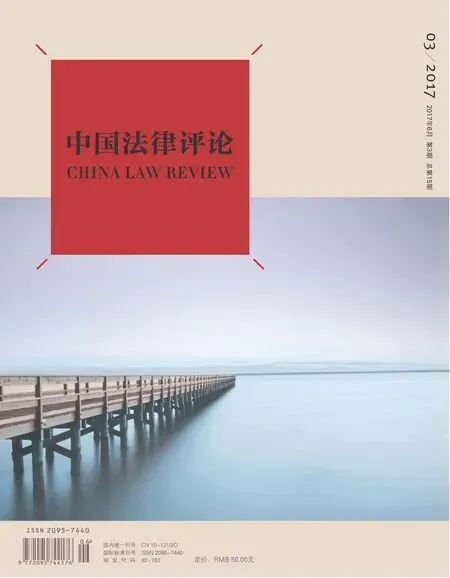体系为纲,总分相宜
——从民法典理论看大陆新制定的《民法总则》
苏永钦
体系为纲,总分相宜
——从民法典理论看大陆新制定的《民法总则》
苏永钦*
《民法总则》的通过,意味立法者做了两个不可逆的重大决定,一是制订民法典,二是必须是一部体系严谨、告别部门化民法的法典。以三年的时间完成各分编,虽然是相当艰巨的工程,但以大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这样一部同时可为自治和管制制度装备的大民法,几乎也是唯一的选择。就其内容而言,相当清楚地刻画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增加德国民法典所无的基本原则规定,也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不过大醇小疵毕竟难免,比如某些《民法通则》规定的移入,显示对延续通则仍有不必要的罣碍,法人部分的类型化显示体系思维的不周延,而某些章节的处理又可看出提取公因式的法典技术还有改善空间。结构上最大的缺漏恐怕是法律行为的体系刻意规避负担和处分的二分,有让以总则冠顶的美意打折扣之虞。但无论如何,法典编纂的工作已不容等待,这一步跨出去,海阔天空。
民法典 部门民法 自治与管制 提取公因式 法律行为
目 次
前言
一、民法典繁华褪尽而体系长存
二、混合体制更需要大民法模式
三、在部门法化和法典化间摆荡
四、总则在法制和经济上的意义
五、各分编的配套整合遗大投艰
六、私法自治贯穿民事基础关系
七、法人分类显示体系思维不足
八、提取公因式以形成有机组合
九、法律行为重启物权变动争议
十、特写宪法的规范性反而着相
结语
前言
2014年10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1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2013年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延续,对于1999年即写进宪法的依法治国原则有何特别意义,尤其是与我们一般理解的法治理念有何同异,可参见笔者的比较分析,苏永钦:《法治、法治国和依法治国》,载《中国法研究》第3期,2016年6月,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出版。,“编纂民法典”被明确纳入工作项目,作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一环,算起来已是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从1949年废止《中华民国民法》之后第五次启动民法典的大工程2第一次是1954—1956年,第二次是1962—1964年,第三次是1979—1982年,第四次是2002年,可参见张玉敏主编:《新中国民法典起草50年回顾与展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相对于这个比较形式的分期记录,江平教授在2016年4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讲座:“改革开放和民事立法”,则是从社会转型和民法学发展阶段来观察,把大陆自改革开放以后的民事立法分成四期:1978—1986年的“重提民事立法”时期,1986—1998年的“以民法通则为核心”时期,1998—2014年的“恢复起草民法典”时期和2014年开始的“公开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时期,指出一个9人组成的“民事立法研究小组”从1998年开始主导推动法典化的角色,载http://dxw.ifeng.com/shilu/jiangpig/1.shtml。,而且剑及履及的分配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其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法学会则是共同参加单位,2016年7月即已向社会公布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并说明整部民法典的立法计划,2017年3月如期完成总则的立法,接下来计划再用最长三年的时间审议其余各分编。从这样“一年点睛,三年画龙”的时程规划,一方面可看出此番完成民法典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显示主事者对于形成编纂共识仍非易事的充分了然。放眼国际,这无疑会是继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西欧荷兰民法典3参见王卫国主编:《荷兰经验与民法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从社会主义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俄罗斯民法典4参见魏磊杰、张建文主编:《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过去、现在及其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之后,最受瞩目的一件大事,当然有高度的研究价值。
对于具有“定石”作用的总则,该给予何种评价,还是应该要回到法典化的“必要性”,也就是从民法典兴衰起伏的整体经验出发,看看法典化究竟还是不是一种普适的路径。如果肯定,又要问民法典在诸多功能都已不复重要后,久经社会变迁锤炼而仍为新世纪所需的,是否即在其高度体系效益(以下第一、二节)?同属大前提而必须考虑的是大陆环境的特殊性,现阶段推动民法典有何特别的意义,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陆,其社会发展是否也到了必须从比较长程的观点建立一套足以反映基础民事关系法制的时候(第三节)?笔者基本上对以上问题都抱持肯定看法,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对大陆制订总则的立法政策敬表赞同(第四节),并相信未来几年分编的重订整合会是此番法典化面临的真正“硬战”(第五节),对总则的内容,也提出几点简单的看法(第六至十节),受限于阅读的文献和时间不足,谬误或者不到之处难免,就当是抛砖引玉吧。
一、民法典繁华褪尽而体系长存
两个世纪前的拿破仑民法典,不论其内容和形式,都为现代意义的法典奠定了基础5用Csaba Varga引用C. J. Friedrich的三分法,古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只是汇编式(digestive)法典,在法国民法典前后的普鲁士邦法典、奥地利民法典等,则可归类于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内容力求广泛的自然法(natural law)法典,只有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才堪称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民法典,可参见Csaba Varga, Codification as a socialhistorical phenomenon, 1991, 321, Budaspest, Akadémial Kiadó。。一个世纪前又因德国民法典的问世,带动了制订民法典的风潮,在风格上不尽相同的瑞士、巴西民法典等一一出台,明显受到德国民法典影响的则有苏联、土耳其和遥远的日本、泰国、中国。但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法典摇篮的西欧即开始出现质疑法典价值的声浪。包括重要的法史学者弗朗茨·维亚克尔(Franz Wieacker)提出古典民法典背后的社会模式已经过时的观点6可参见其相关文集:Franz Wieack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und Privatrechtsordnung, 1974。,公司法大家弗里德里希·库伯勒(Friedrich Kübler)则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主张法典这种高度体系化的立法模式不符合民主政治的需要7Friedrich Kübler, Kodifikation und Demokratie, JZ 1969, 645 ff.;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那达林若·伊尔蒂(Natalino Irti)更从现象观察到方法建构提出“解法典化”的理论,认定民法典的原则法地位已经因为特别法的枝繁叶茂而动摇,并且在很多地方已经从实质走向边缘化,各部门独立发展的结果,也使得民法典在专业教育上原有的基础知识定位趋于模糊。司法者越来越不受法典体系的束缚,立法者也开始尝试其他的体系化方式,比如各种微型的法典8参见陆青:《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古典民法典的诸多功能,如统一国法、揭示价值、集中信息、社会宪章等几乎都已弱化,乃至完全走入历史9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章“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但就在否定民法典的理论达到高峰之际,我们又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看到一些反向的发展,几个重要的新民法典在荷兰、俄罗斯等国完成制定,进入21世纪以后,更陆续在各地涌现新的民法典,比如远东的菲律宾、越南,中东的以色列10以色列的法制兼有英美法和欧陆法的背景,因此在世纪初期突然推动制订民法典受到特别多的注意,可参见Pablo Lerner, Alfredo Mordechai Rabello, The (re)codification of Israeli private law: Support for, and criticism of, the Israeli Draft Civil Law Code, 59 Am. J. Comp. L. 763-803; Nir Kedar, Law, culture and civil codification in a mixed legal system, 22 No.2 Can. J.L. & Soc'y 177-195。,北美的魁北克,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欧洲的立陶宛、乌克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11比较全面的整理可参见魏磊杰:《比较法视野下的民法典重构研究:聚焦法典编纂的最新趋势》,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章。,德国、日本、法国也都进行了债法的全面翻修。对于民法典这样几度浮沉,从“解”法典又转向“再”法典化的转变,已有多场国际研讨会从不同观点加以分析、解释和评价12Wen-Yeu Wang (Edi.), Codif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2nd IACL Thematic Conference, 2014 (Springer) ;Symposium: The challenge of recodification worldwide, 83 Tulane L.R.2009;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Symposium: Codifi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31 UCDLR 1998。,大体的共识是:民法典的形式与功能确已大幅改变,但至少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既是国家治理达到一定境界的象征,也是有利于继续自我改善的开始。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的律动其实正反映民法典对社会变迁的响应,其原因十分多样,包括自治与管制的新辩证关系、美国法唯实主义的启发、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幅转型及法移植国家开始认真进行本土化等13讨论的文章甚多,比如Maria Luisa Murillo, The evolution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ivil law legal systems: Towards decodification and recodification, 11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 Policy 163-182 (2001); Olivier Moréteau, Augustin Parise, Recodification in Louisiana and Latin America, 83 Tulane Law Review 1103-1162 (2009);学者在使用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的时候,往往只是隐约采取某种实质的理解,而不仅指比如特别法的数量达到多少,或者民法典修正达到什么程度。Michael McAuley比较清楚地以是否涉及法律背后的“法秩序”(legal order)理念的变动来区隔单纯修正和再法典化,所以解法典化固然不必是民法典在形式上走向解体,再法典化也不一定要新订法典,或在条文修正数量达到二分之一,或条次变更,可参所撰“Proposal for a Theory and a Method of Recodification”, 49 Loyola Law Review 261-285 (2003),这和Franz Wieacker特别强调近代民法典都被当成一种治理计划而不仅是条文堆砌而已,可以相呼应。实质理解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虽有助于观察法典在社会变迁下的律动,但有时也会引发一些特别有趣、看起来不合逻辑的说法,比如尽管主要内容已经到位、仅形式上迄未法典化的大陆民法,甚至已可观察到某种解法典化的现象,从而也使得未来形式上的法典化,不啻一种再法典化。可参见陆青文,前注8。;但无论如何都显示,法典只要不是一成不变,应尚无碍于国家治理的自我改善。而且今天看起来好像已经更清楚,越能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民法典,生命力也越强韧。反过来看,越是肩负意识形态重任的民法典,越难逃过反复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的命运。民法典的“放空”,不但无碍于各种社会经济立法对分配正义的落实,反而因为本身的功能单纯而更可凸显其体系营造的效益,如果正确理解德国民法典其实自始即未承担任何社经模式,就知道它的高度稳定,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地走到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就是普通法模式成功的最好证明。大陆在过去十几年有关民法典大大小小的研讨会及重要法典与文章的翻译已如汗牛充栋,应可推知这些反思也已经在理论与实务界发酵,才会在思考法治经济时,决定编纂一部高度体系化、以总则来提纲挈领的民法典。
20世纪中期德国民法学者古斯塔夫·博莫尔(Gustav Boehmer)是第一个用“提出括号前”(vor die Klammer ziehen)来总结德国民法典体系方法的学者14Gustav Boehmer, Grundlagen der Bürgerlichen Rechtsordnung II/1, 72f. 1951.,不论赞成与否,没有人怀疑这个潜在方法的真实性。从小括号到中括号,中括号再到大括号,把公因式不断往外提。人类的很多生活领域其实都在进行类似的思考,先归纳再演绎,只是这里用在“应然”的领域而已。因此内容固然各有千秋,谈起民法典的体系化,到今天仍然不出这个基本套路。作为一种实用的社会规范,法律的体系化追求不可能只是基于一种单纯的美感,体系化最原始的功能还是在帮助找法,法律适用所形成的教义学,又会不断强化体系。面对不断涌现且显然更能适应当代民主政治的单行法,民法典的存在如果有助于提升总体效益,即仍可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体系不仅储存大量规范,而且通过统一的概念和规范间逻辑的排列组合,可内化规则间的矛盾,便于推论出规则适用的优先次序,大量减少找法过程中的搜寻、比较、权衡、记录成本,其效益即十分宏大。德国民法典依据法教义学的推演归纳所创设的上位概念“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虽一直受到过于抽象的批评15这样的批评从未间断,比如Folke Schmidt, The German abstract approach to law, Comments on the system of the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in: Scandinavian studies of law, 1965;脍炙人口的比较法教科书Konrad Zweigert, Hein Ktz,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auf dem Gebiet des Privatrechts, 3A., 145-147, 1996年更直指德国民法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其实多仅适合用在债权契约。,但整体实践显示确实大大地提高了民法响应社会生活需要的能力,结果不仅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在法学上完全跟进,连法国也借鉴形成了类似的、比契约要宽广的法律行为(actes juridiques)概念,原来继受法国民法的荷兰民法,更是在新法典第3编财产法通则以第2章专章正面引进法律行为的制度(Rechtshandelingen),就是最好的说明。
“提出括号前”的方法随着德国民法典也被许多民法典使用,有些情形甚至已经比德国民法典操作得还要到位。不像法学阶梯体系把人法放在物法之前,潘德克吞体系是按普通(lex generalis)特别(lex specialis)的关系来决定先后次序,完全没有“人文”“物文”的考虑,以德国民法典的五编而言,亲属继承编既以特定亲属间的财产与非财产关系为规范对象,自然放在处理关系不以特定亲属关系为限的债、物二编之后。至于债先于物,一方面,符合一般事物的序列规则;另一方面,物权关系采法定原则,宁属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先债后物也较符合普通特别关系。普通法化的民法典在找法上,相对于大而全的法典或部门化的法律,是分中有序而非合中失序。一般而言,找法者可从普通法的民法典对系争法律关系作初步定位,再进一步探究是否涉及特别法,乃至特别法的特别法,常常还会在其他要件特别法未规定时,又层层回到普通法去找,比起民法典内也置入不少特别管制规定,以至于无法用“普通—特别”关系去作何者优先的判断,还要加上“后法—前法”等其他规则来作判断,争议可以少很多。不同于大而全的民法典(如意大利民法典)或部门民法,坚守普通法定位的民法典不需要引致任何特别法,反倒是特别法基于立法经济考虑常常概括引致民法典(“本法未规定者依民法规定”)。
体系的效益又不以储法、找法、用法为限,必然还惠及立法和专业教育。立法者在既有体系的基础上,更精准地掌握“下一个”立法如何更好地“嵌入”既有的体系,哪些必须着墨较深,哪些可以大幅省略。甚至在法理相通的情形下,借鉴不同领域的概念或规则——比如行政程序法对民法典的借鉴。再就是法律专业的教育,如果基础的教育终究只能传承“钓鱼”的技巧,而非直接授予“几大桶鱼”,则其重心必然就是体系的基本思维。所以法典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对于立法和法律专业的教育越能产生正面的影响。一部好的法典,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因此,如果肯定民法典仍然保有的优势,其实就在于较高的体系效益。评鉴法典的优劣,大致也就在于以下几点:1.储存规范的容量;2.寻找规范的便捷;3.调整规范的准确;4.教育专业的成本。另外,笔者曾经整理12项体系规则可提供进一步检视的小指标,包括形式方面的积木规则、蜂窝规则、星系规则、串联规则、序列规则、标兵规则和实体方面的中立规则、人性规则、效率规则、文化规则、木马规则、鬼牌规则16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章“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其详不再赘述。
二、混合体制更需要大民法模式
引发或驱动再法典化的多种动力中,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应该就是管制与自治的新辩证关系。众所周知,现代多数的民事交易早就不是在一个无政策介入的环境下完成,而政府也很少有什么政策只靠由上而下的指令就可以达标。但当管制与自治还处于替代性的高度管制(压缩自治)与解除管制(高度自治)的循环时,对于德国模式的民法典而言,都还应付裕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波对民法典“社经模式落伍”的批判,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对混合经济体制(mixed economy)和法治的关联性,在大西洋两岸都有不少深入的研究,比如著名的国际法和法理学者沃尔夫冈·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n)便指出,现代政府几无例外地都要同时扮演民生给付者、行为管制者、市场参与者与争议裁判者的多元角色,而传统法治已经很难应付这样复杂的情况,大陆法系出身而又深谙英美法思维的他提出的建议是放弃自戴雪(Albert Venn Dicey)以来对行政法的偏见,而以更多元的法院组织来响应17Wolfgang Friedmann, The Stat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 Mixed Economy, 1971.。但在这样管制与自治各行其是的混合体制下,规范基础民事关系的民法典仍有其明确的功能定位,还不需要作太大的调整。反倒是在“撒切尔—里根”掀起解除管制的体制改革后,欧美国家重新发展出新一代的混合体制,某种让管制与自治相互工具化、你侬我侬的再管制(管制与自治同时扩张)时18可参见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探讨:Claude Ménard, Michel Ghertman (ed.), Regulation, Deregulation, Reregulatio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2009。,仅仅善于承受管制的这种民法典,包括系统化程度最高的德国模式往往都显得底气不足,因此促成民法典变动的原因固有多端,回应此一新辩证关系而有所调整,使民法典不只是消极地容让公法,而是更积极地让它也能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使国家在直接管制之外更能善用市场机制来替代直接干预,才是最具挑战性而影响最大的变革,称之为一种2.0版的潘德克吞模式,也无可厚非。对于大陆这样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内化转型的国家而言,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国家每天面对的问题要远比其他工业国家复杂得多,而人民对于国家的期待也趋于更高,如何善用民法典的工具来提高治理能力,更使得这种可与再管制理念配套的(再)法典化工程,取得了更高的正当性。
换句话说,当混合的社会经济体制发展到今天这样,国家和人民常常处于某种伙伴关系因而公私因素高度交错的情形19参见詹镇荣:《公私协力与行政合作法》,新学林出版社2014年版。,需要的反而是一个真正的“大民法”,也就是可以为市场交易保留最大空间,同时又为公共政策保留最大空间的民法,好让政府和人民都有最多的选择,去适当响应多元多变的需要,如都市更新、环境保育、老年照护、频谱配置等,无不如此。这原本就是潘德克吞学派以普通—特别关系建构的层级民法典真正的强项,民法作为国家处理公共事务的手段,完全可以视其主体、对象、事务、地区或阶段而精准地运用,使国家的介入机动而又恰如其分20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章“从以房养老看物权的自由化”。。所谓2.0版的潘德克吞模式强调的就是扩大系统容量和提供更鲜明的选项或参照(benchmark)。民法典的设计,也开始要多从政策设计工具箱的角度思考——不是针对特定民事议题提供完整答案,而是让管制者有更多引导发展的空间。怎样在古罗马法开始建构的概念和规则体系中不断发现盲点,或如英国18世纪的重要法理学者边沁(Jeremy Bentham)在提出他的法典理论时特别强调要剔除的“历史偶然”21参见Joachim Münch, Strukturprobleme der Kodifikation, in: Okko Behrendes, Wolfgang Sellert (hrsg.), De Kodifikationsgedanke und das Model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BGB), 2000, 148; 边沁痛恨未经体系化思考的法规范,他甚至谑称法官造法为“狗法”(dog-law):“你知道法官怎么造法的吗?就像人为他养的狗造法一样,当你想要改变狗的某种行为时,你只能等牠做这件事,一做了就打,你就是这样对狗造法,法官对你造法不也是这样?”参见Dean Alfange Jr.,“ Jeremy Bentham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Law”, 55 Cornell Law Review 65, 1969。,把小脚放大,让既有的概念更纯净,或排除规则中非属逻辑必然要求的教义罣碍,就变得非常重要。笔者过去即以荷兰民法创设的“可登记财益”(registergoederen)为例,认为可登记财益和不可登记财益的二分将来必可替代动产、不动产、权利等作为贯穿交易规范的轴线22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章“可登记财产利益的交易自由”。,也就是当新科技的运用已可巨幅降低登记的信息成本后,财产法的设计已完全不在乎交易目标是动产、不动产、空间;应有部分、债权、物权、知识产权、营业秘密、股份、配额、次序、机会还是其他的财产利益,只问这里涉及的是可登记还是不可登记的财产利益。而对于可登记财益的交易,也应该从开放最多选择的角度,逐个审酌维持“种类与内容法定”(numerus clausus)的必要性,原则上让交易者就相对效力或绝对效力保有选择自由。作为法典化后发者的大陆,鉴于其未来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及法典化一次投入成本应有的长程考虑,这样的突破不仅可能,也是最好的机会。如果真要掌握这个机会朝上述方向规划,包括分编问题及总则草案有关交易客体、民事权利等,因为变动较大,可能需要所有参与者都能以更宽宏的视野来共同讨论形成共识23比如物权如不再维持法定原则,合同法就可以朝涵盖所有限制物权的大合同法方向设计,剩下所有权、占有的物权仍然独立成编即难以合理化,此一改变当然还会有很大的连动影响,无待赘述。,这里就只点到为止。
三、在部门法化和法典化间摆荡
普通法取向的民法典对于社会经济体制剧烈转变的国家,确实会有较大的适应困难,花许多时间研订一部高度抽象且几乎都不能完整处理任何重要问题的民法典,有时显得过于奢侈。转型政府可能更倾向针对不同领域的问题,依其急迫性“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每个法都尽可能完整处理相关的问题,由不同机关负责执行。特别是对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公私问题夹杂,最好一次讲清楚,而不必在普通—特别之间来回逡巡,机关和民众都很难跟得上这样的法典模式。这种对比的模式也许可以称之为“部门民法”,若把这种不分普通、特别且公私夹杂的部门民法汇编成一部法典,就是大而全的民法典。因为在范围上作了界定,从交易的公平到作为交易前提的市场参与者(主体)、交易目标的资源初始分配乃至基于公共政策考虑对某些交易行为的管制,全都放进去作系统化的编排,尽可能用一个法律解决所有相关问题,或至少可以明确联结其他法律,以方便机关的执法、司法和民众的用法、守法。这种垂直切割的民事立法,特别是对于一个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社会,正因为公私法的纠结还难以理清,会有特别明显的好处。但个别法律间在技术的接轨和政策的协调上,又难免有层出不穷的问题,有时候A法律的适用问题得到解决,潜在地却制造了B、C、D法律更多的问题,原因就在只顾到作单行法内的体系解释,少了跨越各法的体系化规范。对于以成文法律为主要法源、讲究体系一致性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此一外部调适的边际成本会随着市场复杂性的不断升高而变得难以承受。立法上不断彼此复制,专业教育上也不易集中传授共同基本的知识。因此部门民法模式虽在短期内有利于加速转型,长期而言反而不利于新社会经济体制的成熟稳定。
回顾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同于“休克疗法”之处正在于其极为务实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先为初期的市场经济提供残补式的规范指引,等到政策方向确定将全面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时,20世纪末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在法制定位上已和古典民法典契约法的普通法定位一致,取代了经济合同法等部门性的契约法。《合同法》似乎只是民法典先期到位的一个分编,类似国民政府时代的分期立法,果然到了2002年全国人大就作了10年完成民法典的宣示。但时移势易,接下来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即明显不再坚持普通法的风格,比如舍弃了单纯物权的类型,如所有权、地上权,而从土地所有权的初始分配出发区分不同的所有权,地上权也分成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法为了满足和谐社会的需求还承担了一部分土地管理法的功能,连征收补偿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显然已经不只是处理基础的自治关系,因此里面也不断引致其他法律的规定。民法典的原则取向风格,到了侵权责任法再被问题取向(casuistic)风格取代,医疗责任、环境责任这些必须结合相关行政法来形成完整要件的侵权责任,其背后的公共政策思维,多大程度上可以抽象化为普通法内过错责任的例外,同样不够清楚24台湾地区“民法”有关侵权责任的规定在1999年的修正也作了几个新的公因式提取,包括增订违法侵权的责任类型,及作为过失责任原则的例外的三种危险责任;虽不够精致,但已尽力凸显基础关系中的原则例外法理,大部分的特别侵权规定还是留在特别法中,以维护民法的普通法定位。。因此侵权责任法既不被期待是完整的民事侵权责任法,也失去了为私法自治定锚、为不断变动的社会储存规范、减轻特别法不断相互复制规则以及提供法律专业类似基本文法规则的教材的功能,而更倾向于一部较为实用(如果能不断修改)的部门民法25孙宪忠教授在谈民法典的体系化时也特以侵权责任法内容过于枝节化而造成“叠床架屋”为例来说明,参见刘宪忠:《从立法体系化科学化的角度看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载《澳门法学》2016年第1期(总第30期)。。法典化的努力自此迅速冷却,当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代表常委会做工作报告,宣告中国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已经如期完成时,等于宣告了法典化政策的终结。这三十多年,可以说是从部门民法到小法典,再走向大法典,最后又还是回到了部门民法。因此面对以总则带路的新一波民法典尝试,不能不仔细观察的是,这样的来回摆荡,是不是到了终局确定的时候?所谓的编纂民法典,到底是何种意义的法典?
四、总则在法制和经济上的意义
如前所述,大陆民事法的基本到位,本来是2011年官方就已经确认的事,在这些单行法的基础上再编纂一部民法典,如果不能创造超出原来诸法已经储备的规范能量,其意义何在?以立法者明确宣示的三项目标而言,仅仅把既有的法律从形式上汇编成一部法典,既不可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不会对人民权益的保障有何改善,当然也看不出来和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有何关系26这三点正是总则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所作说明开宗明义宣示的“编纂民法典的总体考虑”。。民法典的编纂会出现在深化法治的改革鸿图中自有其深意,说明大陆面对社会快速多元的发展,已经意识到必须在立法上作出更符合长程需要的新规划27参见王利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事实上从民法总则草案有关立法方式的说明,即已显示立法者要的不只是既有各法的汇编,而是建构一部体系井然的法典;所谓“内容协调一致,结构严谨科学”点出将实质整合之前因应当时环境制定的、在结构风格上不尽一致的各法的意图。又按所谓潘德克吞模式的“提取公因式”方法制订民法总则,以统率其他各编,如果其他各编在整体法制上并不具有相对的原则性地位,以及在规范抽象度上相对更高,逻辑上如何作为总则用以“提取公因式”的基础?足见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虽未明言法典在整体民商法制中的“普通法”定位,而把必须个别考虑公共政策、在民事关系的某个环节去作特别规定者,保留给特别法去调整的意图,此一定位的抉择已经呼之欲出。比较民法的研究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设总则固不代表该法典一定不具普通法的定位,比如德国民法典之后出台的瑞士民法典和大修的债法,以及大修的奥地利民法典,实际上都已深受德国民法的法律行为理论影响,只是仍以其过度抽象而不愿立即条文化,少了此一核心制度,总则又显得过于单薄,因此都未跟进加设总则28参见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2A., 1967, 486-488; Filippo Ranieri, Die deutsche Pandektistik: Europischer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ein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Modells, in: Joachim Lege (hrsg.), Greifswald-Spiegel der deutschen Rechtswissenschaft 1815 bis 1945, 419-421, 2009。;但这几部民法典在抽象建构基础民事关系的风格上其实都与德国民法典无太大差异,而和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意大利民法典那样“大而全”的规范风格截然不同。但反过来,一旦民法典决定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设置总则,就更明确宣示了民法典除了抽象建构基础民事关系外,一次完善其体系的决心,否则毫无意义29担任学会领导人的王利明教授在编纂民法典的政策出台后,即为文表示必须尽快制订总则,“因缺乏具有统率性和广泛适用性的总则,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地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
在各法之外补上一个总则,除了体系上的提纲挈领外,对当前大陆迅猛发展的经济另外还有一个深层的意义。简言之,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摸索前进,基本上都能及时得到相关财产法的支撑,从合同法、物权法及各种知识产权法作为基础结构的建制,到领域性面对问题推动的制度改革,如农地的三权分置、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新型物权担保的逐步认可、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行等30正因为这些措施影响面甚广,争议当然都不小,有的也连带引发财产权基本结构的讨论,比如针对三权分置的改革,参见高圣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但另一方面,也诚如龙卫球教授最近在一场研讨会中所指出的,新科技带动的新经济关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和发展,在财产法制未及响应以前,常常只能按“丛林法则”来办事31龙卫球:《中国大陆财产权制度的新发展——基于市场化进步和新型财产关系的双重进路》,发表于2016年10月20日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两岸民事法之创新发展研讨会”。。就此而言,可能也只有普通法的民法典才足以为新经济关系起到框范的作用,也就是无论如何还可以回到最抽象的基本原则规定,不但市场参与者得据以自治,政府得据以作政策引导,发生争议也可由司法者去作权衡,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四中全会决议是把编纂民法典置于“法治经济”的项目下32参见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部分第(四)点,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而编纂民法典则是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
五、各分编的配套整合遗大投艰
表面上看起来现有的五分编都已先后完成且施行有年,应该可以参考当初国民政府制订民法典所采分段通过立法、一次合编成典的先例,在屋顶加盖总则后,即把编章节条重排理顺而完成新典。但不仅原来各法的内容实施多年已有再全盘检视而作因应调整的必要,其偏向部门法的风格,有时处理议题过于繁琐而不尽符合法典规范基础关系的定位,有时也会因当初部门立法背后隐藏的小而全的思维而在本可相互串联之处有意无意地彼此复制(如在《物权法》的物权保护章中规定侵害物权的侵权责任),都有必要在进行法典化时重新梳理汰删。更重要的是,总则释出的严整体系讯息,对于总则以下各编是否达到足够抽象化而可层层相因的程度,各分编间是否也能按某种普通特别关系排序,都还有待仔细考究,但从当初总则草案说明中对于整部法典的规划说明,连最后要有几编都还保留弹性,只含蓄地说“目前考虑”前述五编,遑论其排序关系,显然法典的基本构成方式还需要建立更高的共识,所以才预留了长达三年的时间来决定,学者对于体系建构各有坚持已非一日,到激烈处甚至难免意气,因此用“暗潮汹涌”来形容总则后的立法旅程应不为过33如按王利明教授的构想在完成制订总则后,就应该起草人格权编,接着还要起草债法总则编,可参见前揭文(注29),但就这两点都还有不少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
比如依目前考虑中的规划,这92条的侵权责任法似乎就要独立成编,走出自瑞士债务法以来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共同放在法定之债的伞下,而和约定之债的契约从“特定人之间的请求关系”观点共同提取“债的关系”的传统——不论把法定之债放在债法总则,如瑞士;或债法分则,如德国,这将是第一次把其中一种的法定之债单独成编,如果原因只在于条文的数量,小括号自动就变成中括号,当然不利于体系的运作,但和其他法定之债一块儿处理,又会回到争议已久、要不要制订债编的老问题34可参见柳经纬主编:《共和国60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专题“关于债的概念及立法问题的讨论”,第262—271页。。将就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自成体系的现实,而把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往二法里面塞,立刻会发现,无因管理放在合同法总则问题还不大(本来就是“准合同”),其功能主要在填补合同法与侵权法不足的不当得利法又当归何处?如果再考虑,约定之债和法定之债共同的债务不履行、多数债权人或债务人、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乃至债权关系消灭的问题,应该会同意瑞士、德国民法典以债编总其成,运作起来还是最为顺畅,也较能储存未来社会发生更多变化所需的规范,荷兰民法典以债法通则独立成编来总其成,意思也一样。只是合同法特别肥大,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规范量相对要小很多,侵权责任法则居中,环肥燕瘦的结构有欠均匀,从这个角度来看,荷兰民法典的整合方式倒也不失允执厥中。
分编的问题当然不止于此,大陆学者对于同属私法的民商法间的暧昧关系,说合实分,说分又经常回到民法找规范,多主张制订民法典时已不能再予回避,有学者比较整理过去二十五年24部新民法典的法典化策略,按商行为和商组织由民法典或商法(特别法或商法典)规定共分成四类:“大合一”“小合一”“小分立”“大分立”,发现明显的主流趋势是整合度第二高的小合一(指仅商合同规定于民法典,商组织仍留特别法规定,共18部民法典可归类于此)35参见纪海龙:《现代商法的特征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未刊稿),拟载《中德私法研究》2017年第15卷。。但即使确定走这条路,商行为要“入典”到何种程度,又可有多种不同的安排36可参见王建文:《中国商法立法体系:批判与建构》,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95页。,订不订债编会更具关键性。各知识产权则在20世纪逐渐从法定的独占地位提升为私法上的权利,自GATT 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在序言中正式宣告其“私权”地位后,也同样产生了如何与民法典连结的问题。只是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考虑仍然相当浓厚,行政管制乃至对违法者刑事责任的科处一时都还无法全部去除,因此也有类似商法的大合到大分的诸多法典化选择。早期知识产权法的学者还对入典有相当憧憬,整理出近百条的通则规定37,近年则多倾向于继续以特别法的方式存在,但要不要另订微型的法典,则仍有争议。无论如何,即使都只在法典中得到确认,以何种形式落脚,仍需要不少讨论38近期的相关整理,可参见吴汉东:《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最不好处理的,恐怕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人格权讨论39前注34,第4专题“关于人格权立法问题的论争”,第71—91页。,人格权的私权化早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确定,只是对于个别人格权以外要不要肯认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德国、瑞士民法各有所好。大陆则从这个世纪初掀起了在民法典中特别突出人格权的主张,不仅独立成编,而且突破20世纪民法典的格局使其居于各分编之首,引发极大的争议。相对于商法和知识产权法的过于庞大,人格权单独成编则有规范量过于单薄的问题,看起来这仍将是未来决策上最大的难题。
六、私法自治贯穿民事基础关系
尽管未来如何分编,现在还很有想象的空间,而分编未确定前,如何“提取公因式”组成总则,逻辑上好像真的有本末倒置的问题,国民政府时期分段制订民法典,虽也是先订总则,但坦白说当时基本上就是整套继受,既已决定以德国民法典为师,龙身的粗模已定,眼睛先点后点便不是那么要紧,二者尚不能并论40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章有清晰的整理。。不过进一步思考,总则内含的体系思维,对于分编的走向无论如何仍有其定锚作用——各分编应尽可能在规范抽象度上达到仅次于总则的程度,且相互间应呈现某种有机的组合,而且总则所要总的规则尽管提取自下层各分编的规范,从而难免因为分编内容或组合方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民法典的核心任务既已定位于基础民事关系的宣示,从“目前考虑”的各分编也已可大致掌握其各自主要的指导原则,则作为基础中的基础的总则,该有什么内容,即不能再说无从下手。简言之,潘德克吞模式的民法典期待的总则,就是要把私法自治这个不变的总原则建立起基本的框架。依笔者一向的看法,所谓私法自治,可以从垂直的国家—人民关系来看,也可以从水平的人民之间相互关系来看。前者彰显的是公权力对私领域的尊重——包括私决定的自主形成与实现,私资源的使用交换只要跨过基本门坎均予肯认,私人间的竞争合作尽可能开放,私争议的私下解决原则上不干预等;后者彰显的则是私人间相互的尊重——包括各自管理本身事物,自享利益自承风险,个别义务与责任的明确厘清,相互间基于人性或信赖可期待的照应等。在这两个维度以外,也许还可以加上时间的维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垂直和水平的尊重都预设了时间的限制。换言之,基于整体社会秩序的考虑,人民只能在可合理期待的时间内得到尊重——包括当事人作合理计算的期限、合理注意的期限、合理行使权利的期限、合理独占的期限等41继续性的债权关系或所有权以外的限制物权是否已可提取一般性的最高期限,而于期限届至时课予再协商义务(Neuverhandlungspflicht),这在1980年德国联邦法务部做研修债编准备时即为受到相当重视的议题,可参见Norbert Horn, Vertragsdauer, in: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hrsg.), Gutachten und Vorschlge zur 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d.1, 1981, 551-645。台湾地区“民法”近年修正已废除无终期的永佃权,背后也就是自治的时间维度考虑。。总则如果能盱衡各分编处理的事物及宣示的指导原则,就这三个维度有序地提到更抽象的层次,应该可以创造很高的体系效益。整体而言,一百多年前德国民法总则呈现的就是私法自治这三维,甫通过的总则结构上其实相去不远,权利义务和法律行为的主体是一个重点(第2、3、4章),民事法律行为(第6章)加上相关的代理(第7章),条文数虽少于前者,仍应该算是主轴,还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第9章)及技术性的期间计算(第10章)、附则(第11章)。不同之处是继受了《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第1章),舍弃了客体之一的物,留到物权去规定,以及有关担保提供的专章。另有关于民事权利(第5章)与民事责任(第8章)的专章,不同于德国民法总则的权利行使与正当防卫。
从揭橥私法自治理念的观点来看,基本原则中最具定石效果的还是继受《民法通则》的第2条,宣示民事法律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就私法自治的第一维而言,特别是面对国家对社会方方面面普遍进行管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和其他公权力主体如果以不行使高权,也就是以平等主体的方式与人民互动,同样可有民法的适用(仍属公法关系的行政契约或行政委托则不属此),可为国家推动现代的治理打开很大的空间,已如前述42面对社会主义体制国家无所不在的情况,所谓国家不行使高权的真实性有多高,大陆学者已有深入的讨论,质疑此一命题者有尹田:《民法调整对象之争:从“民法通则”到“物权法”——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民事立法主要障碍之形成、再形成及其克服》,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最近还有徐国栋:《民法对象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99—406页。有关调整对象一般性的整理可参见前注34,第1专题“民法调整对象之争”。。这里说的平等,也常被解读为第二维的平等,果如此,第4条即成了赘文。所以第4条才应该解读为第二维的平等,有人提到这里应不排除自愿的(如劳雇间的从属关系),或非自愿的(如父母与未成年子女)进入不平等关系,求全的话确实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把非自愿的例外情形,即行为能力有欠缺者明文除外。另外一个规定则是第9条有关保护环境的原则,原草案还另在有关权利行使的章中有一条遥相呼应,终未纳入,此一原则相信是呼应徐国栋教授“绿色民法典”的思维,从中立原则出发,会认为包括环境政策在内的各种反映时代思潮的良善政策仍应留给特别法去规定,以贯彻民法典仅就平等主体间的基础关系加以规定的结构性原则。但环境确实已经是世人无可回避、也不能走回头路的议题,正如前面在比较无争议的人性规则外,也肯认了具有指导性质的效率规则,环境思维背后的资源可持续性好像也可从古老的罗马法得到相当的印证,并反映于近代的民法典上。因此如果从继受罗马法的古典民法本来就有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微出发,把环境作为私法自治第四维,虽未见于其他民法典,好像确有新意,只是这里所谓原则和其他偏向指导交易的规范原则不同,比较适合作为民法典中某些权义发生“法定”变动规定的解释原则,即使目前尚无法从各分编中提到总则——如曾世雄教授所建议的在法律行为外也对事实行为等作统摄性规定43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第2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49页;近年比较完整的理论研究可参见常鹏翱:《事实行为的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似仍可从各分编这类规定中推导出来。不过仔细阅读“绿色民法典”的相关主张会发现,这里涉及的价值权衡——如发展与环保——既仍须交由政治部门审时度势去作阶段性决策,“绿色民法典”中某些明显可归类于公共政策主张者,如控制生育、环境权人格权化等,显然更适宜借助公法工具,以维持民法典的政策中立(中立原则)。另提到民法原有规定的强化,如时效取得、专利强制授权、放宽死亡标准、监护浪费人、共有物及遗产分割等,牵涉面甚广,于环境的关系也未必很大;意思表示的错误,乃至转租、分时度假等交易关系,好像也不太适合以保护环境之名介入。这些“绿色民法典”提出的进步规定,目前总则未见收纳,未来各分编会不会照单全收,也不得而知。推估只有性质属法定不动产役权的相邻关系、动产权利的法定变动等,有可能再从环境的观点加以强化。但整体而言,若仅以部分针对特定事实赋予法定效果的规定为其辐射范围,在总则宣示此一解释原则的形式意义显然大于实质,教义学上能不能挤出一个私法自治的第四维——环境,目前看来好像过于牵强。这个私法原则的内涵,显然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仔细的琢磨。
基本原则层次不能不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民法典所建构的体系的开放性——这个从瑞士民法典开始,所有民法典都无法回避的、要不要开放司法造法的问题44《德国民法典》虽未直接规定,但《施行法》第2条即明确规定“民法典及本法所称的法(Gesetz)为所有法规范(Rechtsnorm)”,一般认为法官造的习惯法就包括在里面。另在方法论上,代表主流的Karl Larenz从“立法计划”(Regelungsplan)的假想确认漏洞,也还是朝维护体系的方向去找填补漏洞的规范,方法上包括类推、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因此和正常的解释法律一样,每个法官都像个织布者,要把国家的法律照原图案的构想织成无缝之布,也和《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款的精神完全一致:“法律若无相当规定可适用,法院应依习惯法,若无习惯法时,应提出立法者应当会提出的规则做成决定。”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则简化的继受了《瑞士民法典》第1条,有关其功能的讨论可参见苏永钦:《“民法”第1条的规范意义》,载《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就此第10条显然被赋予了法源宣示的功能:“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里都提到习惯了,却不提没有习惯时可否造法,好像有意排除由法官来补充漏洞,其背后如果不是类似拿破仑法典先贤不信任法官的想法,就是刻意从法典为一无漏洞的封闭体系出发。但规范民事关系、追求对等正义的民法不像刑法,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不能预设民法典的体系已无漏洞,司法者依宪法既有给付审判的义务,如果确认民法有漏洞,又没有习惯可供引用,则再不被信任,也只能找出填补漏洞的方法作成裁判。道理如此明显,所以笔者认为立法者未必真的有封闭体系的想法,或许只是想让法官造法的问题由实务和学说去发展。不过台湾地区“法”在习惯之后也只多了三个字:“依法理”,不像瑞士法明确要求法官参酌学说和实务,但什么是法理,除了学说可否涵盖法院稳定的实务见解,一如在法国法上常用的“jurisprudence constante”,当然还有解释的空间。45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也没有完全像《瑞士民法》第1条第3款那样明确细分稳妥学说(bewhrte Lehre)和实务见解(berlieferung)作为补充法源,但多数学者认为判例可为法理所涵摄。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判例,大陆也已经有类似的指导性案例的建制,显然都已经看到了司法造法的必要。因此既已规定法源,又刻意省略法官填补漏洞的授权,确实有点可惜。此处或许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明文授权”的担忧,不过民事法官终究还得作出裁判,因此要追求真正的稳定,还须靠法学教育和法教义学的深耕、法院审级的金字塔化。这一规定,将来有机会还是以调整为宜。
七、法人分类显示体系思维不足
总则用了最多条文处理主体的问题,比较特别而且引起较多讨论的是法人,不同于多数民法典有关主体(含法律行为、权义、责任)的规定,从其为意思表示及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方式的本质差异切入,浑为一体的自然人是实存的人格,这些都不难理解及确认;法律上创造的虚拟人格,要具备哪些条件才便于理解及确认且符合自治的精神,则是需要经验基础的,因此从组织条件上区分的社团法人和捐助(财团)法人二分法,一为人合而保留充分意思形成空间的社团法人,二为以捐助财产为基础执行捐助人意思的财团法人,不仅彰显自治精神,而且已累积充分经验印证其高度的普适性,提取到最抽象层次的自治主体,谁曰不宜?现在总则改以营利、非营利这样下一层的功能区分为最上位的二分主体,而把人格组织上截然不同的非营利社团法人、捐助法人和事业单位等凑在一块,明显有别于德国民法以来的法典体例,确有其新意。不过若仅以国家管制的思维来评价,把功能相近者放在一起,不论管制政策或工具的配套都会比较有条理,但如果从民法典作为私法自治基础关系的角度来看,法人格的组织差异显然更具基础性,这样的分类便显得本末倒置而有失焦之虞46《民法总则》采取这样的特殊设计,除了沿用《民法通则》区分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的经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要规避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无所依归的窘境,可参见梁慧星教授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法治与改革国际高端论坛(2016)——“私法与法治经济建设”上的发言:中国民法总则的制定——介绍民法总则草案(第二次审议稿)。但这类官方与半官方法人组织在欧洲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常见,有关其组织与民事行为的要件、效力都还是可以按情形比附总则有关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规定处理,或如机关从事不行使公权力的民事行为,从总则明确划分法人基本类型的高度来看,这样的规避处理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张谷教授就此所提抓住原则、清通简要的立法方向,更值赞同,可参见张谷:《管制还是自治,的确是个问题!——对〈民法总则(草案)〉“法人”章的评论》,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德国对于社团(Verein)、台湾地区对于人民团体,都从兼顾结社自由和社会秩序的角度另订专法加以管理,这时是否具有法人格就无关紧要,是单纯的管制法,足见管制与自治确实是可区分也有必要区分的思维。又法人因为创设私法人格,难免要用到比较多的技术性规定而使总则在重要性的比例上显得失衡,日本近年修改民法,总则部分即有意地为法人章减重,改在法典外另订三部特别的法人法47参见周江洪:《日本非营利法人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6期。,台湾地区“行政院”也才在2017年4月6日通过“财团法人法草案”,针对当局捐助和民间捐助在管理上作了不同的规定,应该也有减压的功能。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营利和非营利法人之外,还有特别法人的专节;在自然人和法人之外,又有非法人组织的专章,这个新体例是否代表什么教义学的体系突破?第96条把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等统括为特别法人。从第97条规定“承担行政职能”、第99条和第100条提到行政法规、第101条有关自治组织法人的规定,可推知这里讲的就是不同形式的公法人,只因为要明确化这些公法人可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可以从事私法活动,而特订专节。因此正确地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私法人,公法人并不需要取得私法人的身份才能从事私法交易,如前所述,当第2条宣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时,应该已为具有公法人身份者,在不行使公权力的情形下因与自然人或私法人为“平等主体”而保留了适用民法的空间。特别把这样的公法人规定于民法总则的法人章,好像要在公法人的人格外创造另一个私法人的人格,恐怕是治丝益棼。这其实只说明了公法人的概念还不十分明确,台湾地区有关公法人的法制整备以及教义学的定位也不成熟,比如工商团体到底是公法人还是私法人,学者就有不同见解,多数情形是由实务逐渐厘清,法律上公法人定位比较明确的只有农田水利会,以及2011年制定的“行政法人法”。但让民法总则去承担厘清公法人身份的功能好像也不是好办法。这就和物权法上把性质为公法财产关系的事项也规定进来一样,对于体系只会带来更多混乱。同样地,自然人和法人之外,另有非法人组织,但真正有权利能力的仍只限于前两者,《德国民法典》第54条仅仅是“阐明”没有权利能力的社团,适用合伙的规定,如今体例上刻意把一些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变成与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并列的主体,反而会造成观念的混淆。
这些体例的安排一方面有部门民法的思维——相关的事物尽可能兜在一起,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安置”通则规定的想法。但从民法典要力求“结构严谨科学”的目标来看,外部体例的不逻辑就是很大的缺陷,而且从法典施行第一天开始就要面对内在体系严格的批判,能避免还是以避免为宜。虽然立法者面对现实社会的诸多需求,有时难免将就还是可以理解的,德国民法总则在21世纪初也在自然人章增列消费者和企业,即完全是应欧盟消费者指令而仓促增订,体系上是否妥当,笔者就有相当质疑,《民法总则》在此并未效颦,应该是对的48债法改革的结果虽为多数接受,但如非决策者一反过去处理民法修正的恭谨态度,出其不意地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作出决定,很可能和过去一样不了了之,可参见Mathias Reimann,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Reform of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 83 Tulane Law Review (2009)。把企业和消费者提取到总则和自然人并列,仅从其出现的范围不出债编少数条文,即知相当牵强。日本近年修改民法也曾讨论企业和消费者应否列入主体的问题,最后因没有共识而打消。。
八、提取公因式以形成有机组合
至于总则该放进哪些规定,争议相对较小,整体而言,它和开风气之先的德国民法总则在结构上相去不远,权利义务和法律行为的主体是一个重点(第2、3、4章),民事法律行为(第6章)加上相关的代理(第7章),条文数虽少于前者,仍应该算是真正的主轴,另有关于时效的规定(第9章)及技术性的期间计算(第10章)、附则(第11章)等,足可凸显私法自治作为民事基本关系的大原则。以自然人和法人统摄财产和身份关系的主体,法律行为统摄其行为,虽于身份关系较为勉强,在一百年前的德国民法即因此备受批评,但总则的实践仍显示其面对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各种新型法律关系所储存规范的重大功能,应可认为已经通过考验。总则不同之处是继受了《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第1章),舍弃了客体之一的物,留到物权去规定,以及有关担保提供的专章。另有关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的专章(第5、8章),不同于德国民法总则的权利行使与正当防卫。这些规定是否真属“提取公因式”,从而与其他各编能否更有机的组合,当然不是全无再斟酌的余地。
所谓“提取公因式”,要不就是把大多数共同者留给上位阶规范去处理,而使下位阶规范仅需处理“例外”的情形,这时的提取是“普通—特别”的方式,比如总则规定法律行为附条件、期限的类型、要件、效力,各编对于法律行为只需就不得附条件、期限,或有何特别效力的情形加以规定即可;要不就是从下位阶规范的制度提取更抽象的规范内涵规定于上一位阶的规定,不仅足以概括下位阶的相关规定,还可储存供下位阶规范所不及者适用,这时的提取是“公同—个别”的方式,比如从契约、单独行为等提取法律行为,此种类型的提取主要功能即在扩大备载容量以响应下位规范的不足,因此必须这些提出于上位阶规范者在规范内涵上超越下位阶规范的总和,才有提取的意义。如果提取的结果并没有储存多余的规范容量,只是在上一层的总则中再作一次综合整理,像写教科书一样,则这样的提取应属多余,一旦增订下位阶规范,还得配合修正上位阶规范,徒滋争议而已。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和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各章的规定,往往即给人这样的感觉,比如自愿原则本可以从法律行为核心的意思表示反面推论出来,遵守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等,从法律行为章排除其效力,也可反面推论,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的规定更多属此,总则不作任何规定,也不会有何不同,其提取即属多余49最后新增加的第185条则又是反其道而行,问题不在无必要的“提取”,而是不适当的“新增”下位阶的具体规范(侵害英雄烈士的人格权)到应该是最抽象的总则,颇有天外飞来的感觉。。法律的每个规范都应有其独特内涵,这是立法学的基本要求,工整完备固然是法典的美德,但不必如教科书一样的反复阐明。法教义学还无法找到适当的“公因式”时,即宁可从缺,德国民法总则提取了法律行为,却提不出事实行为,就是一个例子。
大陆的立法者不会不明白这一层道理,其中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考虑,基本原则的规定主要还是承继《民法通则》,事实上总则继受通则的情形十分普遍,除了基本原则外,在自然人章中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单列一节,也是一例。然而三十年前制定一共才156条的通则时并未预设后面还有一个个具体化的分编,其功能更类似1975年出台的《东德民法典》(共480条),是小法典而非总则,因此像基本原则的规定,以当时整体民事规范的简陋与市场经济所处边缘地位而言,不能说没有宣示引导的意义,后来“民法通则”的很多规定都被合同法、物权法等更细致的规定所取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规范也见于其他法规,现在要不要放进总则即应视这些规定是否真属“提取公因式”,从而与其他各编能否更有机地组合,并非当然都要保留,总则的立法者其实大可不必有“遗漏”通则规定的罣碍,因为就功能而言,通则本来就不那么总则。另外还有一些可能的考虑,比如民事权利一章,确认知识产权的类型(第123条),就可能有让知识产权在民法典生根的目的,解决前面提到的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的分合争议,但这样象征性的小合一,并未储存任何新的规范内涵,到底有多大意义,而且同样会有修特别法即须配合修民法典的问题,毕竟不能无疑。从《民法通则》移植过来的无因管理(第121条)、不当得利(第122条),可能更适合在将来的某个分编里规定,这里暂时省略,过渡期间还是可以用《民法通则》。总之,民事责任和民事权利不是不能于法教义学发展到更成熟时提取更高的“公因式”,如有关主客观责任条件、赔偿与补偿、金钱或其他利益的返还等,或有关权利种类、内容的意定或法定,相对或绝对等,提出一般性的原则,如果既不是“普通—特别”,也不是“共同—个别”,只是对分编或特别法上已经规定的重新在总则上作总点名,可说毫无意义,有时还会无中生有地制造无谓争议。
九、法律行为重启物权变动争议
德国民法发展出来的法律行为概念,统摄所有源于自由意志的私法行为,可说是逻辑归纳的精致产物,对于身份行为也许不太能提供许多重要的补充规范,但对于财产行为却开创了很大的交易空间。其他西欧国家的民法学实际上也很难抗拒这样的概念建构,但为免影响债权契约可生物权变动的既有制度(意思主义),意大利就把法律行为放在债编契约总论之始算是简单交代,法国在2016年大幅重构了债编的体系,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未采五十年前一度要走的方向——把法律行为放在实质上财产法总则的地位(第4卷第1编),先于契约法而可适用于契约——而是回到契约法为中心的传统,只在后面准用其规定于其他法律行为50参见李世刚:《中国债编体系构建中若干基础关系的协调——从法国重构债法体系的经验观察》,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另参见Xavier Blanc-Jouvan, “Towards the Reform of the Obligations in France: The Reasons for the Reform”, 83 Tulane Law Review 853-876, 2009。。其主要考虑就是,避免提到上位阶规范对不区分负担和处分行为的契约法造成过大的冲击,宁可牺牲总则的建构51瑞士民法典在制订时即肯定契约上位概念的法律行为,甚至也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没有在民法典中设置总则的主要理由还是其刻意标榜的区隔法学与立法的理念,公认的法典之父Eugen Huber在立法总说明中即明确表示:“法学要教我们法律是什么,立法者只管用法律下命令”(Die Wissenschaft will belehrenüber das, was ist. Der Gesetzgeber befiehlt.)。参见Pio Caroni, Einleitungstitel des Zivilgesetzbuches, 1996, 5。。反过来看,一旦民法典高调地设了总则,而把法律行为这样的概念“提取”到总则,凡依自由意志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除有违反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者,国家原则上都肯认其效力,而发生何种效力,即端视其“法效意思”为何而定。则后面又有债和物的分编,不论政策上采无因或有因,但至少以负担为法效意思的负担行为不能发生处分的效力,当年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像在浴缸发现浮力原理的阿基米德(Archimeds)一样“发现”的独立物权行为即已无所遁形,否则在法典整体的释义上就会捉襟见肘、吃尽苦头,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先法后德”的荷兰,现在的处理方式是把法律行为放在债编前面的财产法通则,和物权一起,没有那么符合逻辑,但已明确不以法律行为依附于债权契约,反而成了它的上位概念52参见Wolfgang Mincke, Einführung in das niederlndische Recht, 2002, 103-112。。大陆现在的情况则是《民法通则》虽把民事法律行为规定在前,合同反而放在后面民事权利的债权内,但后发的《合同法》早已羽翼丰满,可完全无需操烦《民法通则》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去自主运作,一旦又增设以法律行为为其灵魂的总则(连同代理共44条),总则和《合同法》的矛盾就完全无法回避了。
《民法总则》虽和台湾地区的“民法”一样,未如德国民法总则在法律行为下规定契约,但台湾地区规定于物权编的物权“合意”(第761条第1项后段),一般还是认为相当于债权的“契约”,因此可以类推适用债法的契约规定,显然肯定独立物权行为的存在。大陆则不但在《物权法》上看不到这样的物权行为,《合同法》第51条还把处分权有无和债权合同的效力混为一谈:“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到底有没有独立的物权行为?如果只凭负担的意思,如何发生处分的效力?这个问题在大陆的学界和实务一直高度分歧53前注34,第8专题“关于物权行为理论问题的讨论”,第159—182页。,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一物二卖契约效力的见解一变再变54参见王轶:《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立法建议》,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看来已经步入日本此部分教义学混乱的后尘,现在应该是很好的机会釜底抽薪作一解决。可惜最后在法律行为部分仍然未见处理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规定,让人担心主其事者是不是真的还没意识到此一混沌状态的严重后果。客观地说,日本人是在一百年前因匆忙完成混合继受才犯此错误,情有可原,事到如今财产法教义学已经有点积重难返。法国和意大利则为贯彻意思主义而舍弃物权行为并把法律行为一并作小,连带地也舍弃了总则的冠顶。大陆这样隆重地制订总则而又以法律行为贯穿轴心55这里还是要提一下,总则实际上仍然保留了《民法通则》的“民事法律行为”用语,并没有采纳绝大多数民法学者改为“法律行为”的意见,但因为民事法律行为主要造成的问题在于同时并存的“民事行为”,此一二分法在法教义学上几无市场,现在总则总算从善如流地舍弃了,因此梁慧星教授认为法律行为前面多了“民事”两字仍只能说是退了半步(比起更早期草案),问题已经不大,可参见所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笔者猜测,如果未来民法采用民事法律行为,实际的结果可能是大家在法教义学的沟通上仍予漠视,让“民事”两个字只存在于法典,或最多见于裁判,长此以往对于民法典仍会是不小的伤害,值得反思。,如果连物权行为是否存在都仍不明确,又是为何?
十、特写宪法的规范性反而着相
最后也许还可以谈谈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立法争论:宪法的角色。正因为2005年物权法的立法即以受到违宪质疑而停顿,最后硬是推迟了一年才完成,总则起草时也引发了不小的宪法争议,会不会再度造成推迟,一度让人捏把冷汗。先是一位民法学者对于草案第1条,承继过去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先例,宣示其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应属多余,有伤追求私法自治的民法典的自主性。此一质疑在2005年即曾引发民法宪法同位说、私法优位说及宪法优位说的争议,此次果然又引发多位公法学者的反弹,认为规范民事关系的民法和其他法律一样不能自外于宪法,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更明白地写道:“所有立法要符合宪法精神”,因此从内容到程序,民法典也都要能体现宪法宣示的各项核心价值,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表明宪法依据,也才足以建立法典的正当性与合法性56详见“主题研讨——宪法与民法的对话”系列文章,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还好这段看起来只是立法前夕的插曲,并没有普遍展开,后来也在无争议中通过第1条,其内容还合并了原来放在民事权利章的一个条文:“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笔者认为这样的对话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与其话赶话地连回旋空间都不留,不如仔细聆听发言者的深刻用心,双方未必都有什么恶意。几位宪法学者从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出发,一方面强调私法自治理念已历经变迁,另一方面指出宪法也不再仅以规范统治者为务,20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法制发展,也大都肯认宪法内含价值对社会的拘束性,始有宪法“私法化”的纵横并进。这些见解主要针对的是部分民法学者过度强调民法源于历史的独立性,认为其规范内涵的自发、宽泛与多元,不应受限于后发的宪法。类此“民法是民法,宪法是宪法”的观点多年前也曾经在德国引发争议,我猜想不少国家也会出现。德国出来作“鲁仲连”的反倒是民商法大师卡纳里斯(Canaris),他明确指出不直接受宪法规范的只限于民事关系,但民事立法本身就是公法行为,当然“直接”受到宪法约制。法国民法和法社会学教授让·卡尔波尼埃(Jean Carbonnier)的确曾把拿破仑法典描述为现代国家的“社会宪法”,从19世纪的欧洲宪法多把重点放在国家组织的背景来理解,法国民法典有关所有权绝对(§544)、契约的法效(§1134)等宣示确有时代纶音的分量,足以互补。宪法和民法典散发的都是自由主义的理念,一则规范国家,二则规范社会,反映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后来虽然时代已大不同,许多同样追求现代化的主权国家,仍然会在制定宪法的同时制定一部民法典。或者如加拿大的魁北克,1976年独立意识高涨时,通过了一部自己的大宪章,并积极推动民法的再法典化。但如前所述,宪法在各工业国家的实际发展早已走过这样的国家社会二元论分工模式,现在只有少数制度主义者还主张宪法应该专注于政府组织的规定,人权和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普遍都受到宪法关切,违宪审查制度也多把民法纳入审查目标。因此在宪法之下的民法,常常只是具体化宪法命定的社会经济模式,如果自外于此,宪法本身便成为解法典化的主要动力。到这里,我认为宪法学者的评论都非常中肯。但如果进一步了解民法在立法技术上的特性,以及立法者必须保有的合理立法裁量,包括同样可达宪法目的在立法模式上的选择自由,恐怕就不会立刻下结论,说非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连结民法背后的宪法意旨不可,甚至不惜陷入放眼各国民法典,几乎只此一家的窘境——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民法不能自外于宪法?笔者过去已经多次提到德国民法典草案公布时的一场论争,以有机体理论享誉的奥托·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直指德国民法典代表“曼彻斯特式的个人主义和一面倒的资本主义倾向”,且具有“与共同体为敌、推向让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根本就是反社会的方向”,身为主要起草者之一的戈特利布·普朗克(Gottlieb Planck)法官,面对已经高度工业化、城市化,也已经开始推动社会政策的德国,没有以自由主义的政经理念去回复这样的批评,坚持民法在整体法制的独立性,反而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观点去强调为什么民法典要维持意识形态的中立:“特殊利益的社会化处理只能留给中央或地方的特别法去作”57参见Planck, Zur Kritik des Entwurfs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AcP 1889, 327, 405 ff。一个世纪过去,德国学者重新审视这样的法典化策略,更为肯定它能历经无数次的左右摆荡,正是拜其所赐。20世纪末联邦政府于迎向立法百年而准备全盘改革债法时所以诚惶诚恐,一开始连改革(reform)的用语都刻意规避,而用“检视”(berarbeitung),就是因看到它经历巨大社会变迁仍备受学界尊崇之故,详见自始参与1980—2002年债法修改的Gerhard Hohloch于2016年12月在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做的报告:Schuldrechtsreform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ngen bis Heute (1980-2002-2016)。,换言之,如果正确理解宪法的操作,应该会知道民法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诫命,在选择了“普通—特别”立法模式时,只能从整体民事法制来看,比如有没有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土地管理法规去落实农民利益的保护、劳工法规去落实劳工利益的保护,而不必强求规范“民事基础关系”,也就是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才适用的民法典,也要承担这些功能,以致在民法的找法、用法、立法等方面都变得更为复杂。民法学者所强调的“独立性”,如果指的不过就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抽离,并非有意在意识形态上自外于宪法,而宪法学者所强调的“宪法自觉”,也不过强调民法不能自外于宪法,未必要民法典去承担宪法课与国家各种公任务的达成58持此观点的宪法学者甚至也认为民法典不宜规定土地征收,应保持公共政策的中立,参见苗连营、郑磊:《民法典编纂中的宪法三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这场争论大概也可以就此化解。在我看来,现在总则第1条只有提示、阐明的功能,即使不写也是如此,反倒是特别写了,碰到其他法律不写,会不会滋生“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解释争议?定位于普通法的民法典,其规范对象(addressee, Addressat)本即预设为裁判者而非交易者,不同于有意引导人民行为而势必以民众为其规范对象的特别法,适不适合像部门民法一样放进这些教示的规定,恐怕较具全观视野的宪法学者,如果正确理解了民法典的体系功能,也会同意立法者最后的收手,否则才正应了古人所谓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在《民法总则》里以这种方式宣扬宪法的诫命,应该绝对不是宪法的本意吧?
结语
大陆于1999年出台《合同法》,启动了法典化的讨论后,民法学界旋即卷起千堆雪,有主张应采松散、汇编式的法典者——类似美国的重述(Restatement),其实就是弃欧从美、改走案例法的路线。在较多的制订法典主张中,也有认为应回到罗马法先人后物的思路,彻底抹掉从中华民国民法到苏联民法里的潘德克吞体系。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追求逻辑性、体系性的民法传统。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上时任法工委主任顾昂然突然提出多达九编的民法典草案,其内容明显只是急就章,但十年内完成民法典的宣示意义非凡,松散法典的路线基本上已经出局,法典化没有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要怎样的民法典。结果几年间由学者合作提出各种草案建议稿,对各项争议问题都能充分表达立场,且展示了强烈的抱负和动员能力。比如2003年由梁慧星主持提出的七编建议稿:总则、物权、债总、合同、侵权、亲属、继承,共1924条;2004年由徐国栋主编的“绿色民法典”——依编、分编、题、章、节、目的体例,各分编自起条次,共得序编、人身关系法(自然人、法人、婚姻家庭、继承)、财产关系法(物权、知识产权、债总、债分)、附编及尾题,共5333条,有高度创新性;2005年由王利明领衔提出的八编建议稿:总则、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总、合同、侵权,共2057条。各版基本上都作了大部分的整合(既有法)和消化(外国法典)的工作,只是梁版传统,徐版浪漫,王版中庸,可谓各有千秋,漪欤盛哉。2014年重新吹起编纂民法典的号角,这些学者努力的成果,加上最近十年个别领域产出的教科书和论文,提供了法教义学的丰富资源,已可比拟19世纪末期德国编纂民法典的盛况,最终会产生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大家都拭目以待。
大陆此时此刻制订民法典,有其后发和主体的优势,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走到必须深化的阶段,也因其内在的一些矛盾而有其劣势。笔者仍然相信,如果主事者能掌握各国民法典在其不断累积和选择的整体发展下59一个简单的整理也许即可看出世界上的民法典无不是在选择下传承:法国民法(1804年)→奥地利民法(1811年)→荷兰民法(1838年)→意大利民法(1865年)→葡萄牙民法(1867年)→瑞士债务法(1881年)→西班牙民法(1889年)→德国民法(1896年)→日本民法(1898年)→瑞士民法(1911年)→巴西民法(1916年)→苏联民法(1922年)→土耳其民法(1926年)→中国民法(1930年)→意大利民法(1942年)→埃及民法(1949年)→苏联民法(1964年)→荷兰民法(1992年) →俄罗斯民法(1994年)→巴西民法(2003年)。在整理荷兰经验时,荷兰学者J. Hijma即特别提到荷兰新民法典在有关法律行为的内容上有 4.5%是借鉴了中国民法(指的是台湾地区现在用的中华民国民法),包括一些她认为并不妥当的地方,参见前注3、23。,看到体系化的追求实为真正不变的趋势,化繁为简地在这个主轴上寻求各方共识,应该比较容易去善用优势而趋避劣势,建立一个稳妥的架构而舍弃立法完美主义,抓紧时间应该可以在三年内产出一部朴实好用的民法典,以大陆近年培植的青年民商法菁英人数之伙,中国民法的鼎盛可期于未来。
*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