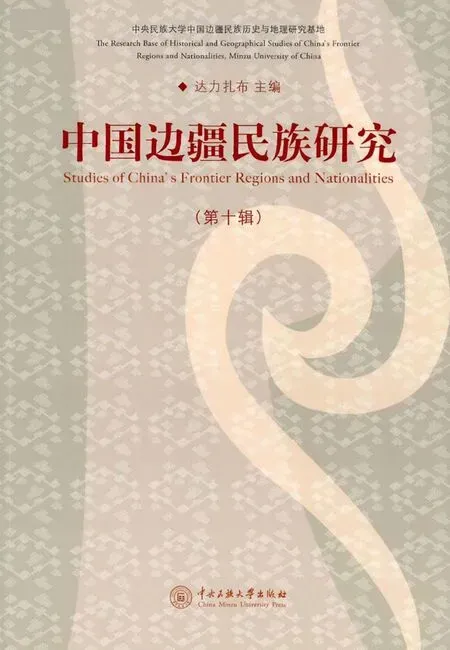契丹古城和日木·登吉与和硕-柴达木碑铭上的托固城
——八世纪早期土拉河城市的起源与种族文化属性问题
[俄]谢·亚·瓦休金著 陈 恳译
内容提要:在对土拉河古城和日木·登吉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俄蒙考察队发现了可能与突厥-回鹘时期有关联的地层。基于对书面材料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和硕-柴达木碑铭中提到的土拉河城市属于回鹘的假说。文章还论证了契丹城市和日木·登吉是与和硕-柴达木碑铭上回鹘早期的托固城建造在同一地址上,在回鹘汗国时代是一个大型城市中心,相应地保留了许多回鹘城市发展的特征。
在2010年,由历史学博士克拉金(Н.Н.Крадин)教授率领的俄蒙考察队对土拉河上的契丹古城和日木·登吉(Хэрмэн Дэнж)(在中央省扎马尔苏木)下部地层的更早期材料进行了发掘[10, с.433–434]。在最后的土层中是陶器和碗碟,呈现出回鹘汗国定居点与埋葬物的特征。特别地,器皿及土层中碗碟的风格很像回鹘贵族墓葬中的工艺品(德日维勒仁〔Дэрвэлжин〕四方形遗址)[17]。由此,古城和日木·登吉至少属于两个文化年代传统:1)早期的,可与突厥-回鹘时期相联系;2)晚期的,与契丹时期相联系。这就提出了关于该城年代及最初种族文化属性的问题。本文尝试处理关于土拉河早期城市书面材料中相当偶然与极富争议的一些信息,并提出关于其可能起源的看法。
在已公布的突厥卢尼文材料中,我们注意到在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纪念碑铭里提到了突厥和九姓乌古斯的几次战斗①作者诚挚地致谢于谢尔盖·格里高利耶维奇·克利亚什托尔内(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Кляшторный),他对关于毗伽可汗与阙特勤碑铭中提到的回鹘城市托固的问题提供了详实的参考意见。。在阙特勤大碑的铭文里讲到:“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由于天地失序而成为敌人。一年之中我们(和他们)交战五次。最初我们交战于托固(Тогу)城(Toγu balyq)”[11, с.42]。在毗伽可汗碑铭中有重要的阐述:“最初我与他们交战于托固城。泅渡过土拉河(Toγla ügüz)后,我攻击了他们的部队……”[12, с.21]。由此可知,在和硕-柴达木纪念碑铭所确定的八世纪30年代,托固城(Toγu balyq)在托格拉(Тогла)河(Toγla ügüz)。
此外,在阙特勤和毗伽可汗碑铭中对付九姓乌古斯的同一处地方提到了阿姆格(Амгы)堡(Амга, Магы Курган)。特别地,在阙特勤碑铭中记载:“在玛格(Магы)(或阿姆格)过冬休养之后,春天我们出军讨伐乌古斯”[11, с.42]。
所述事件发生在兔年,即介于715年2月9日与716年1月27日之间[19, с.80–81]。由于突厥人必须过冬,托固城的战斗可能发生在715年夏季末到秋季之间(在这一时段可以涉水越过土拉河)。阿姆格堡在其他突厥文本中都没有提到,而只出现在突厥人与九姓乌古斯冲突的事件中,且突厥人在该地过冬(即从本部出动,通过军事征讨平定叛乱),那么它很可能是一个九姓乌古斯的城堡。由此可知,和硕-柴达木文本中提到的土拉河畔托固城与阿姆格堡不晚于715年。并且城市和城堡都确定无疑地关联于回鹘所领导的九姓乌古斯部落联盟的聚居地。
更加精准地确定城市的位置有助于我们将其与托格拉河联系在一起。《古突厥语词典》(«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м словаре»)已经考定卢尼文碑铭上的托格拉河就是现在鄂尔浑河的支流图勒(Туул)(土拉)河[4, с.571]。还需注意的是,唐代编年史书中出现的独乐(Дулэ)(Долу; Дуло)都可以勘同于土拉河[例见:1, с.273]。基于此,位于土拉河畔的托固城便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点。
阿姆格堡也极为有趣,但那是另一个独立的题目,需要专门的研究。城堡据信应位于九姓乌古斯的领地,这就意味着城市和设防的定居点在九姓乌古斯内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可以讨论较早(前帝国)时代的回鹘(九姓乌古斯)城市规划了。
在突厥碑铭和其他材料中并未确定地说托固就是回鹘城市。但是土拉河及其流域在七世纪到八世纪初的事件记述中经常与回鹘及其他九姓乌古斯部落联系在一起。暾欲谷纪念碑铭中描述了一则轶事,当时暾欲谷正奉颉跌利施(Ильтериш)可汗之命率领突厥军队沿着翁金河(Онгин-гол)(文本中作 Кёк Онг)河谷行进前往于都斤(Отюкен)。在土拉河他们遇到了乌古斯人,后者从土拉河“前来”,“带着牛车”[11, с.66]。克利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说,乌古斯人放牧自己的牛群。同样,可波干(Капаган)可汗死前不久也是在土拉河击败了拔野古(баегу / байегу)的军队,然后殒命的[1, с.273;13, с.124]。
然而与土拉河联系最紧密的资料是关于仆固(пугу / bugu, bokut; буку, боку, бокут)部落的。中国学者丁谦(Дин Цянь)基于书面材料提出,仆固的领地在土拉河之北。另一位研究者岑仲勉(Чэнь Чжунмянь)同意丁谦的看法,但同时指出其缺乏直接的证据[14, с.139; 注释50, 51]。
现在,由于绍隆多布(Шороон Дов)土堆的发掘及其中发现的汉文文本,使我们有了仆固领地中心在土拉河的直接证据。绍隆多布土堆位于和日木·登吉城东北约两公里半的地方,我认为这绝非巧合。
如达尼罗夫(С.В.Данилов)领导的俄蒙联合队文中所述,“绍隆多布土堆中石板上刻铭的初步释读表明,这是纪念乙宎玥(И Яо Юэ)①据罗新(2011)和杨富学(2012)的考订,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苏木土拉河畔绍隆多布土堆仆固墓志主人的名讳为“乙突”,原墓志有“君讳乙突朔野金山人”的记载,其中“突”、“朔”的字形同“宎”、“玥”较为接近,作者或因此将墓主名讳读作“И / Yi(乙) Яо / Yao(宎?) Юэ / Yue(玥?)”。——译者注。的墓志铭——墓主是金徽州(Цзинь Хуй Чжоу)②据原墓志图版,此处应为“金微州”,但作者读出文字的标音却是“Цзинь / Jin(金) Хуй / Hui(徽) Чжоу / Zhou(州)”,盖因字形相近,作者将“微”字读作了“徽”。——译者注。都督、林中(Линь Чжун)县首领、仆固领地的统治者,卒于677年,时年44岁。其祖父Гэ Цзянь(Во Янь)①据原墓志图版,此处应为“歌滥拔延”,但作者读出文字的标音却是“Гэ / Ge(歌) Цзянь / Jian(槛?) Во / Wo(沃?) Янь / Yan(延)”。——译者注。是皇朝左武卫大将军、金徽州都督。父亲也是金徽州都督[3, с.256]。
Гэ Цзянь(墓主之祖父)可以考定为《新唐书》中提到的仆固首领俟利发歌滥拔延(Сылифа Гэлань Баянь)。在647年,薛延陀覆灭之后,12位部落首领带着礼物和印信来到唐朝宫廷(据另一个版本,是皇帝在灵州接见了他们)。中国政府统治了戈壁以外的领土,将铁勒部落的土地划分为六个都督府和七个州。仆固的土地设立金微州(Цзиньвэйчжоу),老歌滥拔延被任命为右武卫大将军及自己领地的都督[13, с.114,118]。
根据《新唐书》43Б,金微都督是为统治仆固部落所据领地而设②史料中提到还有一个仆固州(仆固州都督府),但该州位于边境地区,且只是临时侨寄在朔方(Шофан)县城管内。显然,在这一边境地区安置的只是仆固部落中的流亡部众,故而该处的人口普查显示一共只有122户(673人)[14, с.25],而从《新唐书》的《回鹘传》中我们得知,仆固部落有帐户三万,胜兵一万[1, с.344]。,即确为仆固原居地。并且金微都督府连着一个大州仙萼(色楞格河名称转写的一种变体),还包括游牧部落回纥(回鹘)的领土瀚海都督府、拔野古部落的土地幽陵都督府等[14, с.25, 137,注释49]。这无疑是九姓乌古斯在中部和北部蒙古的直接聚居地。
马里亚夫金(А.Г.Малявкин)和许多其他学者曾经高度质疑为回鹘、仆固、拔野古、同罗、结骨及其他部落所设置的府州的存在。特别地,马里亚夫金写道:“这些行政管理机构都是虚构的,是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办事公署。唐朝帝国的威权极为经常和宽泛地使用这种‘设立’府州的方法……”[14, с.25]。
然而绍隆多布土堆的文本证明,在蒙古的府州管理并非虚构。墓志文本清晰地指出了仆固领地(州)总督 / 统治者(都督)的存在,而且是第三代(!)。所有这些表明,马里亚夫金的评估并不完全准确。来自中国政府的管理控制无疑是有限的,因为都督及州长都由当地部落首领担任(戈壁里是没有唐朝官员的;他们只驻扎在边境城镇,控制进贡、协调游牧贵族觐见天朝等)。据《新唐书》记载,当太宗皇帝(626-649)“抚慰突厥时”,各蛮族首领“渐渐开始变得服从(中央王国)”,唐朝在这些部落的领土上“设立州县”,“而(对)大部落则设立都督(都督府)。这些部落首领被任命为都督及州长(刺史)”,可以“世袭”。根据唐朝编年史料,这些部落“缴纳贡赋”,但其州县不“被列入登记的土地”,而其人口则列入“在户丁册”[14, с.12–13]。
可以设想,在某些情况或某些时期,中国政府有能力使用直接的方式来控制游牧民族。于是,在647年薛延陀汗国覆灭之后,一些九姓乌古斯部落(仆固、同罗及其他铁勒部落)积极参与反抗薛延陀的斗争,回鹘(吐迷度)、仆固(歌滥拔延)、拔野古(屈利失)、同罗(时健)的俟利发,多滥葛俟斤末,及浑、斛薛、思结、阿跌、契苾与白霫的部落首领都带着礼物来到宫廷,请求“建立对草原的统治”[13, с.114, 118]。另一个例子——在660-663年九姓乌古斯部落(回鹘、思结、拔野古、仆固、同罗、多滥葛及其他)反叛中国。作为回应,中央王国的军队进入蒙古草原,数次惩罚并击败了游牧民,于663年“平息了”他们。在这之后进行了行政改革:所有草原上的都督府和州都接受位于回鹘土地上的瀚海长官的管理。为首的总督是一位中国官员刘审礼[13, с.119–120]。绍隆多布土堆的墓志文本表明,像仆固及其他九姓乌古斯部落那样出身部落首领的总督们对于中国并不总是只有名义上的效忠与附属,他们也需要向中国皇帝进献游牧民的礼品和贡奉,并参与大唐帝国对外敌的军事征讨行动。
但在一般情况下,天朝对于戈壁以外(即漠北)领土进行直接控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中国任命九姓乌古斯首领为都督及州长之后,回鹘统治者吐迷度于647年自称可汗绝非偶然[1, с.305; 13, с.118; 14, с.22]。这使得马里亚夫金 [14, с.22]提出,在中部及北部蒙古产生了一个新的游牧政权——即所谓回鹘第一汗国(先前的研究者认为回鹘宣称汗国是在上述660-663年的事件中提到的[14, с.119–120, 125])。这一观点也被卡马洛夫(А.К.Камалов )[5, с.7, 62–63]所支持。
尚需强调的是,各种头衔的游牧首领的俸禄不算稀少,但并不意味着其接受中国统治者这样或那样的直接监控,也不能保证其对天朝的效忠。中国人多次授予可波干可汗各种头衔:为镇压契丹叛乱他被封为左卫大将军的军事爵位和归国公的贵族爵位,为摧毁松漠之地他更被封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1, с.268]。而这些都完全无视突厥军队年年掠夺中国财物的事实(!)。如此即使是唐帝国最公开的敌人也可以被授予各种头衔。
因此,从中国编年史的资料、绍隆多布土堆的墓志与该墓志的位置来判断,仆固活动于土拉河流域,其土地的政治中心位于离和日木·登吉城不远的地方。
然而土拉河地区也是回鹘极为关注之所在。还在628年时回鹘首领菩萨(Пуса)在马鬃山(Ма-цзун-шань)打败了一支突厥主力部队。《新唐书》中记载说“他声振北方”。菩萨于是投附薛延陀,他们“相唇齿”。采用“活颉利发”(Хо-Гейлифа)的称号之后,菩萨“树牙独乐水上”[1, с.302]。在647年俟利发吐迷度自称可汗之后,回鹘的政治中心很可能仍然在土拉河下游。迄今尚未发现有材料提到回鹘牙帐从土拉河迁移到其他地方。在北方——色楞格河流域与鄂尔浑河下游——如所周知是回鹘的主要游牧地区[12,с.22; 1, с.302; 9, с.60]。此外随着薛延陀汗国的覆灭及其主体部落迁往西域[1, с.343; 13,с.114],回鹘与其他九姓乌古斯联盟中的部落很可能占领了其遗弃的领土。于是我们发现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九姓乌古斯在土拉河就并非偶然了。如上所述,暾欲谷在土拉河击败了放牧畜群的乌古斯(大概他们正在当地草场放牧)。而在715年阙特勤与毗伽可汗则率领军队渡过土拉河去袭击托固城的回鹘人。
还应注意到,回鹘和仆固在七世纪到八世纪初的许多事件中都是一同行动的。七世纪初回鹘与仆固、同罗和拔野古从东突厥叛逃出来[1, с.301; 13, с.117]。628-630年仆固、拔野古和同罗支持薛延陀和回鹘[Малявкин, 1980, с.107]。649年中国军队与回鹘及仆固击败车鼻(Чеби)汗[1, с.264]。七世纪中期回鹘与九姓乌古斯部落参加了对西突厥与高丽的战争[1, с.290, 305]。662年或663年初回鹘、仆固与同罗侵扰大唐帝国边境地区[13, с.120]。之后,回鹘败于突厥,部分回鹘与仆固迁移到外南山(Принаньшань)地区,后又于727年一同返回草原。然后为建立回鹘的霸权一同抗击突厥[14, с.24]。所有这些意在强调回鹘和仆固的紧密联系,它们在军事政治方面相互关联,它们在土拉河流域的牧地则可能相邻。
回到土拉河的托固城,可以设想其起源过程如下:
1)药罗葛王朝回鹘统治者菩萨的牙帐(628年);
2)仆固部落首领及金微都督府总督的牙帐(绍隆多布土堆靠近该聚居地当非偶然);
3)七世纪下半叶回鹘可汗的牙帐。
在蒙古草原的突厥帝国(突厥第二汗国)复兴之后,九姓乌古斯部落保留了其在土拉河流域的牧地,而托固城也许仍然是回鹘或仆固的行政中心。毗伽可汗纪念碑铭所载715年五次战斗中的第一次[12, с.21],以及阙特勤纪念碑铭所载第四次[11, с.42],这些突厥与乌古斯之间的战斗都发生在托固城附近,就不是偶然的了。
若我们概括史料,则可追踪其中的语义关联:回鹘—牙帐—土拉河—仆固—托固城—土拉河—回鹘。可以设想,在628-630年击败突厥后,回鹘占领了土拉河流域地区并在此建立了牙帐——这正是回鹘在军事政治上宣告独立的明证。不排除菩萨设于土拉河的牙帐在吐迷度及其后继者中仍保有其价值。另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知道,于677年,在可能是托固城的契丹修建的和日木·登吉古城不远处,建有仆固统治者乙宎玥的墓地。中国工匠制作了两块墓碑,指出仆固首领同时是金微地区(金微州,金徽州)的将军—总督(都督)。有可能,这一时期在托固城这一地点已经有了设防聚居点或牙帐。然而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史料中与土拉河相联系的通常是回鹘(乌古斯),看起来他们又重新占领了土拉河下游。基于此,托固城可以被确定为回鹘(乌古斯)的早期城市中心。我们提出的这一说法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土拉河回鹘城市的完全出现,极可能是在八世纪下半叶回鹘汗国积极进行城市规划时形成的。起初,回鹘帝国的行政中心是牙帐—堡垒。在铁兹(Тэсин)碑和铁尔痕(Терхин)碑的文本中以及毛盖西耐—乌苏(Могойн Шине-Усу)的碑铭中,讲到了翳德蜜施毗伽(Элетмиш Бильге)可汗几处类似牙帐的建立。碑铭的作者在开始的地方将其称为于都斤 / 于都斤后部(杭爱)的中心,也就是回鹘击败突厥之后重新聚居之处。翳德蜜施的牙帐依次建立在周边,或位于于都斤后部的中心,或位于需要控制当地民众的偏远地区:由此,带防御城墙的牙帐被设置在于都斤后部“雅巴什(Ябаш)(艾巴什〔Айбаш〕)河与图库什(Тукуш)河汇合处”[12, с.40; 9, с.63],“于都斤西面铁兹(Тез)河上游”[12, с.40; 8, с.89; 9, с.63],在龙年(752)“于都斤中部、圣峰孙古斯·巴什汗(Сюнгюз Башкан)之西”[7, с.92]。克利亚什托尔内提出,此处所谈及的便是斡耳朵八里(Орду-Балык)(喀喇巴拉哈逊〔Карабалгасун〕,哈拉巴勒嘎斯〔Хара-балгасун〕,八里里〔Балаклык〕)——未来的汗国首都[7, с.94]。在毛盖西耐—乌苏的碑铭中有一处直接指出将汗国主要的牙帐建设在“鄂尔浑与八里里(Балыклык)的连接处”(该处即后来的斡耳朵八里)。这里便建置为“政府的牙帐”与“君主的宝座”[12, с.42; 9, с.65]。
只在有一处,铁兹碑铭中提到,翳德蜜施毗伽可汗“在东边的艾勒萨尔(Эльсер)驻跸”,并“下令”打制“自己的印记与诏谕”[Кляшторный, 1983, с.89],但对于牙帐的建立则未提及。可以假定,于都斤后部东边的牙帐已经在艾勒萨尔建立起来了。遗憾的是,克利亚什托尔内对于“Эльсер”一词未作任何注解。有可能,这一概念与“故国”、回鹘国家的故土相关联[4, с.493, 496],但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唯有依靠突厥语文学领域的专家。另一有趣之处,在于这一地方的位置。如果铁兹碑铭的作者在空间上的方向描述是基于如下事实,即在回鹘汗国存在期间回鹘领地政治与神圣的中心是于都斤后部,那么“东边”可能即是指杭爱的东方边区,即土拉河流域。如果此假说成立,那么显然这就是翳德蜜施毗伽可汗未在此处修建牙帐的原因。这样的牙帐早已存在了——这就是托固城。故而仅仅竖立了一块带有铭文的石碑。
在回鹘汗国极盛时期,托固城是最大的城市中心之一。2010年的发掘表明,突厥—回鹘时期的地层在和日木·登吉城的北区和南区都有出现[10, с.432, 433, 434]。这说明回鹘城市的规模与后期契丹城市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其西边的墙体长度为534米,东边为538米,北边为328米,毁坏的南边大约有450米[10, с.431]。此外,紧挨着城市中心的是固定的贸易区和整片的复合聚居区[15, с.141–149; 10, с.432],在那里的部分提取物中发现了突厥—回鹘时期的陶器碎片。
据《辽史》,994年辽国军队曾进军蒙古讨伐阻卜(цзубу)。编年史记载,在回鹘可敦(Кэдун)城的所在地修建了契丹的镇州(Чжэньчжоу)城[10, с.438]。由此,可以建立一个纪念碑起源与发展的时间链条:回鹘首领菩萨的牙帐(628年)——回鹘汗国中心的牙帐——七世纪下半叶——托固城(715年)——回鹘汗国的城市中心(745-840年)——契丹编年史中的“故可敦城”——契丹的镇州城(九世纪末—十二世纪初)。
就这样,土拉河畔的城市存在了很长时间,跨越了中世纪早期的大部分年代。这也解释了为何和日木·登吉城跟蒙古其他的契丹城市不太相像的原因。契丹的和日木·登吉在外形上很好辨认,与那些回鹘古城很相似。当然,某些契丹城市规划的特征也很明显:依照光线分布的清晰的空间朝向,北边墙上不设城门,城市划分为南北两部分。但同时也没有带瓮城的城门,没有明显伸出墙体外(15-20米)的正面与拐角的塔楼等等。在许多结构特征上(围猎式墙体与塔楼的建筑技术、高大的城墙、正面与拐角塔楼的形状),和日木·登吉非常类似于斡耳朵八里、博尔巴仁(Пор-Бажын)、富贵城(Бей-Балык)及其他回鹘城市[6, с.64–65; 2, с.56–66, 118–119及其他]。所有这一切表明,在修筑契丹镇州城时,保留了回鹘可敦城的墙体、塔楼及其他防御设施。契丹人将其翻新,加固墙体,建造了一座汉—辽体系风格的城市。
不应忽略的是,按照托尔斯托夫(С.П.Толстов)的意见[16, с.71–75],“балык”的词源可能与土坯、墙坯有关。15-20厘米的粘土薄层是用围墙技术(木制框架)来填充的。游牧民自身难以建造这样的防御工事。很可能,托固—可敦城的修建是由粟特人或来自中国的汉人所从事的。在七—八世纪初,回鹘与粟特人及天朝居民的联系极为广泛(例如,回鹘参与了击败七河地区西突厥汗国的出征;在七世纪末被突厥击败后,回鹘贵族与人民迁移到中国边境地区[14, с.22, 24])。与粟特人的联系可能是通过七世纪中期到末期独立的回鹘可汗来维持的。在这一时期游牧民的使节经常前往中国。如果中国工匠参与了绍隆多布土堆的修筑及仆固首领墓碑的建造,那么就不能排除他们也参与了托固城墙的建筑。
汇总研究结果可知,土拉河上的托固城很可能是蒙古最早的中世纪城市。它起源于土拉河流域,其地在628年被回鹘占据,与仆固部落的土地紧密相连。回鹘统治者的牙帐渐渐演变为一个小型城市。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八世纪下半叶到九世纪时回鹘汗国的大城市(可敦城),及十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的契丹城市镇州。在前帝国时代的早期回鹘城市里,都市人口极可能呈现多种族的特征。这使得我们可以探讨回鹘原初社会形成的特点,部分地解释回鹘对城市和堡垒的需求,并确定其在回鹘汗国结构中的内在因素。城市占据了战略要地,覆盖了土拉河的渡口,在后来突厥统治于都斤后部时更成为回鹘同其他九姓乌古斯部落相互渗透的前哨,于是终成为回鹘汗国的东方牙帐。因此契丹人修复了这一重要的城市中心。在十一世纪时作为城市—堡垒的镇州守卫着契丹在中央蒙古的其他大城市,使其免遭北方游牧民的攻击。
俄文原书名:Киданьское городище Хэрмэн Дэнж и Тогу-Балык кошо-цайдамских надписей: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города начала VIII в.на р.Толе。本文的撰写受资助于 РГНФ-Монголия (2011-2013) №11-21-03001 а/Mon《契丹辽国史》(«История кидань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Ляо»)。①原文发表于:Вестник Бурят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2011.№ 4.– С.63–71.,网址:http://www.bscnet.ru/upload/iblock/a01/vestnik_4.pdf——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