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彦 好的策展人与好的展览能构成美术史书写
李旭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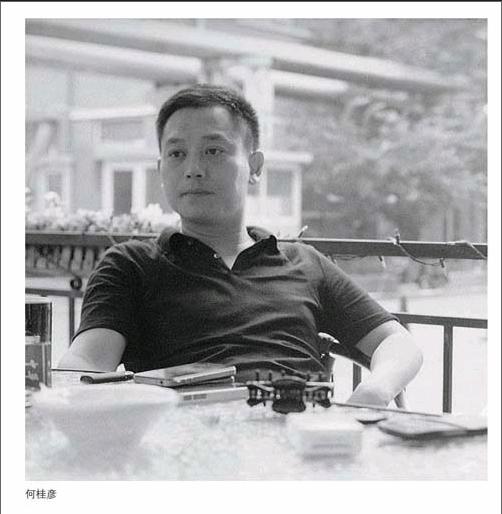


在策展人何桂彦的工作中,无论是在“1976——2006乡土现代性到都市乌托邦,四川画派学术回顾展”,“走向后抽象”,“清晰的地平线——1978以来的中国当代雕塑”等展览中总是能看出其在美术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代艺术有着较其他人更为系统而严谨的描述。而且在当代艺术本土化的进程中,其策展工作所描绘的线索也对其他艺术学者的工作大有裨益。
艺术汇:从2007年“1976-2006乡土现代性到都市乌托邦”群展开始的,策展就与你的美术史教师身份不可分割。那么在你的理论研究和策展之间是否也有着某种阶段性的统一或分离?
何桂彦:“四川画派”三十年回顾展侧重理论上的梳理。这个展览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美术史的上下文,一个考虑文化现代性的变化。艺术史的角度主要讨論现实主义内部的变迁,即从“伤痕”的批判现实主义到“乡土”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文化现代性的内涵包含了文化的地域性,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即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到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转变。在2007年以后的展览策划中,我个人希望展览与美术史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尽量为展览构筑一个美术史的历史情境。
艺术汇:你从事大量架上和非架上艺术作品的展览策划,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所跨越的边界是什么,在策划展览中对空间安排上有具体的细节对比吗?
何桂彦:架上和非架上只是形态上存在差异,当代艺术早已摆脱媒介意义的划分。实际上,重要的不是架上,或者形态的区别,而是作品的内涵。就展览而言,核心还是作品与展览主题是否契合。一般来说,装置与雕塑类的作品对空间会有更高的要求。
艺术汇:你是怎样看待艺术家的地域的,例如说西南艺术家大多数以架上艺术为主。而沿海地区却能出现不少用影像和装置艺术家?
何桂彦:1980年代初,地域性是很重要的。但因为“新潮美术”的兴起,地域性很快就消退了。1980年代后期,只有在“西藏题材”中还保留了一些地域的、风情的、异国情调的东西。不过,它们是边缘的。1990年代中后期曾再一次讨论过地域性,但与1980年代比较,这个时候的参照系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一种“中国身份”背后的地域性。至于艺术家们使用不同的媒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氛围与创作惯性使然。
艺术汇:策展人在19世纪时期随着印象派对抗法国沙龙文化的出现,在野兽派乔治·德瓦里尔(Georges Desvalli eres)和超现实主义安德鲁·布勒东(Andre Breton)的策展中获得一种定型效应。那么欧洲这种由艺术学者组织的带有介入性的展览在中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之间也有类似策展人出现,那么你是如何理解策展人在文化中的生成,以及今天策展人所具有的意义?
何桂彦:从艺术与文化的自觉,尤其是展览的自觉来说,欧美策展人的崛起还是“二战”之后,尤其是1960年代。我个人觉得,现代主义时期,罗杰·弗莱、阿尔弗雷德·巴尔代表第一代策展人的出现。1969年,塞曼策划了“当态度变成形式”,这个展览是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重要分水岭,而塞曼也是战后最有代表性的策展人。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美术馆制度和展览制度的完善,策展人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展览已经成为当代艺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中国批评家介入展览策划,第一个高峰是1985到1989年。但策展人这个概念是1990年代初才传到国内的。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才有了真正的独立策展人。我们都知道,当代艺术有自己的历史。其实,展览也有自己的历史,即展览史。而展览史则是构成当代艺术史书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好的策展人与好的展览,是能构成美术史书写的。
艺术汇:在中国,策展人不仅要调动学术资源,而且也要与一级市场。甚至是二级市场做好沟通,这方面是特殊的中国国情。或者还是在艺术平台搭建的初级状态下,策展人必须面临的问题,欧洲是否有其完善的策展人制度。有供借鉴的优点吗?
何桂彦:这是一种初级状态。今天,策展人有点像一个项目经理,或一个包工头。我们希望中国的展览制度能尽快的完善,能形成一些好的范式,能真正做到国际接轨。比较而言,西方的展览制度要健全很多,他们更重视策展人的学术性与问题意识。经费与具体的项目都有其他渠道或机制解决,这样一来,策展人的工作就会纯粹一些。
艺术汇:在上世纪末像奥利瓦这样的国际策展人的带动下,中国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类型的艺术大行其道,并目一度成为市场的宠儿,那么回过头来再观望这种有选择性的策展行为带来的文化成果,一方面是正面的,它远离了早期政治控制下的集体审美。但在资本的引诱下又出现新的怪相,早期你曾经撰文谈论过此事。那么今天再来看这种艺术行业的渲染模式,在社会中影响仍然很大。策展人扮演了一种同样的角色,那么是资本时代策展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模式吗?
何桂彦:“东方之路”那届威尼斯双年展在选择艺术家上是存在偶然性的。因为奥里瓦当时并不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也不熟悉中国的艺术家。但是,他有自己的学术判断。那就是在“后冷战”与东欧的巨变的大背景下来选择中国的艺术作品。加之,1980年代,他就提出了“文化游牧”的概念。“政治波普”与“玩世”的走红在当时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语境,所以,那批艺术家是很幸运的。商业是后来才介入的。不过,1993-1996也是中国当代批评出现“后殖民”话语的重要时期。许多批评家都提出了批评的看法。我个人觉得,策展人是否拥抱资本,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尤其是学术立场。
艺术汇:你的博士论文是谈论形式主义的终结,但你很多策展项目却和乡土艺术有关,那么这似乎也是构成你研究方式的两面性。一种是从纯粹美学上去讨论,但另一种却要涉及到大量经验文本,那么作为一个策展人。你是怎样看待这两种不同知识在现代中国的链接和重合?
何桂彦:当时的论文是对西方现代批评的一个梳理。20世纪上半叶,形式批评很重要,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围绕“形式”建构了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它的发展谱系也很清晰,早期形式主义批评(如罗杰·弗莱)——盛期形式主义(如格林伯格)、后期形式主义(如罗莎琳·克劳斯)。但我在策划展览时,考虑的还是展览的主题。主题的背后就必然有问题意识。问题来自不同方面,可以侧重艺术本体方面的内容,如形式、语言、修辞、观念,也可以围绕某些话题与现象展开,如“社会风景”、“神话与叙事”、“近观与冥想”、日常话语与微观政治、“后传统与新语境”等等。展览不在于规模的大小,作品的多少,是否有明星效应,而是是否能提出问题,能否改变既有的认知,是否能提供一个介入艺术史的新的切入点。
艺术汇:随着信息的方便,艺术家和策展人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往已经超越了以往。但正是这种地球村式地交往方式。反而淡化以往策展人与艺术家那种紧密的传统书信联系,在这个时代批量化处理信息不仅是策展人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那么你是否有怀念过去策展人与志同道和文化人工作的情境,对于批量化的信息介入你是怎样考虑的?
何桂彦:这个在“新潮时期”体现得最为充分。“新潮”是中国批评界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批评家与艺术家是亲密的朋友,也是战友,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有共同的假想敌。书信是彼此沟通,交流,表达情感的最重要的方式。今天的情况早已天壤之别,大多数时候,人们愿意选择更为便捷的沟通方式。当然,策展人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就与艺术家的友谊而言,仍然是因人而异。
艺术汇:作为一个文化建构的时代。有些策展人将传统文化的建构树立在后现代思潮的平台之上,那么作为一个策展人,你是怎么看待今天中国文化现场和传统文化的沟通和构建?
何桂彦: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今天,“传统”之所以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主要还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伴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个民族国家应具有的民族文化身份,及其文化主体性问题。这种语境自然会唤起中国当代艺术在文化主体意识上的自觉。当然,这种自觉一方面体现为,需要对过去30多年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各个时期的文化与艺术诉求进行反思与检审;另一方面,我们要逐渐从过去那种由西方标准和“后殖民”趣味所支配的当代艺术的范式中走出来,重新建构当代艺术的评价尺度与价值标准。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传统”是可以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文化资源的。但是,其间也需要对传统进行有效的转化,单纯的回归传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相反,我们讨论传统的落脚点,应放在如何才能在当代的文化视野下,对传统资源进行有效地转换,使其动态的再生。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回归传统也只是当代艺术的一条发展路径,而不是全部,因为,今天当代艺术赖以依存的文化语境是多元而丰富的。而且,我们也要警惕的是,在以后的几年内,当代艺术会不会借助“回归传统”而打“传统牌”,将“传统”变为一种文化策略,尤其是在艺术资本可以操纵当代艺术的创作与生产的今天,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一点是,所谓的回归传统,恰好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正确”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