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域下读者与创作者的关系
——以诗人冯至新中国成立后对其旧作《我只能》的改动为例
⊙林存斐[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接受美学视域下读者与创作者的关系——以诗人冯至新中国成立后对其旧作《我只能》的改动为例
⊙林存斐[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本文主要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下来看待读者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借引“潜在的读者”这一概念,举现代诗人冯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其1926年的旧作《我只能》的改动为例,来看待时代精神的影响之下,“潜在的读者”如何支配着作家的创作。
“潜在的读者” 接受美学 冯至
接受美学的学科历史虽然不长,但其着眼于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关注审美接受,引起了美学各个流派的重视。“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然而,接受美学强调对文学艺术活动中的读者的关注,分析阐释读者观众在审美活动中对艺术文学作品的实现和建构作用,却往往忽视了在读者与文本接触的这一审美活动中作者所受到的影响。所以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思想史》一书中介绍接受美学时,在结尾引介学者瑙曼将接受美学从读者向作者的扩展,做了这样的一个评价:“瑙曼讲接受主体的范围从读者扩展至作者,克服了接受美学片面强调读者的倾向,是文学批评涵盖了文学的整体活动。”然而,瑙曼的观点还未尽彻底,虽说瑙曼将作者引入接受主体的范畴在某些方面纠正了接受美学的局限,然而,他只是将作者纳入接受主体,究其实质讲其实还是在读者的范围里谈论,只是这个读者的范围被拓展延伸了。我想进一步将“作者”的问题引入接受美学探索的话,还应在接受主体的基础上引向作者的问题,特别是作者的创作问题。
其实每个作家艺术家的心里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有着某种预设的读者,这些预设假想的读者影响着支配着他们的创作。作家张爱玲就曾经很明确地讲过,“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也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从作家的自我陈述中可以看到作家对读者角色的设想,虽然这样读者的角色可能是现实的,抑或是看不见的。
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在他的著作《暗隐的读者》(又译为《隐含的读者》)曾这样解释他所提出的“暗隐的读者”这一术语的内涵:“这一术语运用了本文潜在意义的先结构和读者通过阅读过程使这种潜力现实化”。这句话实际上在说的是“暗隐的读者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读者,一种植根于本文结构中、与本文结构暗示方向吻合的读者”。伊瑟尔虽然没有谈及读者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所指出的“暗隐的读者”显然是一个能够不受制于文本的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甚至能将自己的意志现实化为艺术品的“读者”。而进一步,朱立元先生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潜在的读者”这一概念。他这样解释这一概念:“‘潜在的读者’并不实际存在,但有可能存在;‘他’是过去某些或某一类读者的一个典范或代表,但‘他’又可能在对未来作品的阅读中出现;‘他’不是西方接受美学批评家心目中理想的或者有知识的读者,而是活在作家心中时时缠绕并干预、参与作者创作的读者。说得更明白些,潜在的读者是作家想象出来的他未来作品的可能的读者。”不可小觑这种“潜在的读者”的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潜在的读者”能够支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理论》中分析让-保罗·萨特的《什么是文学》这本著作时说过这样的观点:“并非只是作者‘需要读者’:作者所运用的语言已经包含着可能存在的一种读者范畴而不是另一种范畴,在这一点上他未必有多少抉择权。一个作家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某种特定的读者,他可能对谁读他的作品毫不介意,但仅写作行为本身就已经把某种读者作为文本的内在结构包括进去了。”
所以,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中,“潜在的读者”是基于创作论而言的,是探索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悖立与整合的关系的。读者不仅是主动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支配着创作。那么,我想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冯至对他的诗作《我只能》的创作及其改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个例去探索“潜在的读者”如何支配诗人的创作。
冯至的《我只能》一诗写于1926年。而新中国成立之初冯至重新编选他的诗文出版《冯至诗文选集》中,《我只能》一诗出现了一些改动。本文透过这样的改动来分析“潜在的读者”是如何“支配”了作家的创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首诗。左边的《我只能》是1926年时候的诗歌原貌,原载1928年11月28日《新中华报·副刊》第5号。而本篇论文因为材料的局限,《我只能》一诗选自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中国新文学史料丛书中《中国新文学大系》(朱自清编选)第一个十年的诗集。右边的《我只能》选自195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冯至诗文选集》。

歌唱这音乐的黄昏
它是空际的游丝,
它是水上的浮萍,
它是风中的黄叶,
它是残絮的飘零:
轻飘飘,没有爱情,
轻飘飘,没有生命!
我只能歌唱,
歌唱这音乐的黄昏
它是空际的游丝,
它是水上的浮萍,
它是风中的黄叶,
它是残絮的飘零:
轻飘飘,没有爱情,
轻飘飘,没有生命!


拉琴的是这窗外的寒风,
独唱的是心头的微跳,
没有一个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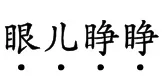
死沉沉,没有爱情,
死沉沉,没有生命!
我也能演出,
演出这夜半的音乐
拉琴的是窗外的寒风,
独唱的是心头的微跳,
没有一个听众,
除了我自己的灵魂:
死沉沉,没有爱情,

死沉沉,没有生命!

有红花,有绿叶,有太阳,
有希望,又失望,有幻想,
有坟墓,有婚筵,
有生产,有死亡:
欢腾腾,都是爱情,
欢腾腾,都是生命!
我怎样才能谱出
正午的一套大曲——
有红花,有绿叶,有太阳,
有希望,又失望,有幻想,
有坟墓,有婚筵,
有生产,有死亡:
欢腾腾,都是爱情,
欢腾腾,都是生命!
我将这两首诗的差异用加粗和着重号的方式呈现出来,很明显,1926年《我只能》一诗的版本比起1955年的版本,最为关键的是分别“为你”“向你”和“为你”三个词的消失。这个不能不让我们细思,诗歌中“我”与“你”的这样一种对话关系的消失在表达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先把“我”与“你”这样关系的问题先搁置一旁。来看一下,作者歌唱的是什么,不敢歌唱和害怕歌唱的是什么东西。
从诗作中看出,实际上作者歌唱的是一个破败的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爱情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衰颓的画面。而最怕想起或最怕奏出的是“正午的大曲”,什么是“正午的大曲”呢?“正午的大曲”里面有“红花”“绿叶”“太阳”“希望”“失望”“幻想”“坟墓”“婚筵”“生产”“死亡”“爱情”“生命”,而这些又是什么呢?这些是生命的百态,是我们最切实的生活,最真实生命中的一切,或者讲说这些意象表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最最基础的东西。然而,诗人最怕想起或最怕奏出,潜台词就是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消失,或者说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秩序已经被打散了。
那么,我们着眼来分析“我”与“你”的对话关系在诗中的存在或者删去给诗的表情达意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分析1926年作者未经改动的版本。前两节中,表现主题应该是“我”只能为“你”带来的是“没有爱情,没有生命”。这里面便产生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可能是一个衰颓的、失去生命、失去爱情的个体,所以演唱表现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生命,没有爱情”;另一种情况是“你”可能是一个衰颓的、失去生命、失去爱情的个体,那么,“我”也只能对“你”唱的对“你”表达的是“没有爱情,没有生命”。然而,当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能解释的“我”和“你”所代表的特殊的衰颓的身份在这首诗中是不能成立的。第三节诗中表现的“红花”“绿叶”“太阳”“希望”“失望”“幻想”“坟墓”“婚筵”“生产”“死亡”“爱情”“生命”是最最日常的生命,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象征事物。所以,诗中提到的“我”和“你”的所指便不可能是上面我所举的两种情况,而是最最普遍的,最具一般性的人的个体。那么,我们便可淡化对“我”“你”关系的猜测,而是探讨“我”只能为“你”或者最怕为“你”的原因,很明显从“我”只能为“你”所做的事情与“我”最怕为“你”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是对环境的一种控诉,是某种时空之下导致了“我”与“你”的这般关系。在“我”与“你”的关系的背后,实际上是表达的作者某种莫名恐惧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作者没有明指,我们简括言之应该是一种时代社会的背景。还可以作为辅证的是,1926年的原作第二节中“眼儿睁睁”一词,能够让人们较为明确地知道作者在此有个“眼儿睁睁”的对象所指,像在仇视着什么对抗者着什么,而1955年出版的修改作中,这一词被删去。所以,《我只能》这诗未改动之前的1926年的版本,通过“我”与“你”之间关系的描述,表达的是对环境的不满或者说是对环境的控诉。而1955年修改后的“我”与“你”关系的消失,那便只剩下“我”的个人情绪的抒发,是个人悲观的一些思索,像是一份独白,已经没有了对环境的控诉或者诉求。
从这里,我们比较了1926年写作时的《我只能》一诗的原貌与1955年作者修改之后的诗歌状貌,可以看出,原先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对环境的对抗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5年作者修改之后的版本中的消失。当然,对于这样的改变,我们可以透过分析时代精神气质的转变来探索,我们可以说1926年时期深处环境恶劣的旧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诗歌表达对旧中国环境的控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潮中,集体主义思潮的空前上扬取代了对环境的控诉。这样的解释固然可以,但是我们如果再深究下去呢?这种时代精神是如何作用在作者身上呢?我想单纯的时代精神分析法似乎还不能很有效地解决我们的疑问。诚如朱立元先生所讲的“人们常说,作家感受到时代精神的脉搏,时代精神支配着作家的创作。但时代精神作为代表一个时代前进方向的思想、精神、观点,如何具体地对作家发生支配作用呢?人们没有回答。我认为,主要是同通过接受和体现时代先进思想的读者和批评家对作品的审美反应、评论,时代精神逐步转化为审美的潜在的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作家的心灵,暗中制约着他的创作活动。换言之,时代精神不是直接支配作家创作的,而是通过某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决定创作过程的,潜在的读者当是最重要的中介之一”。
我们引入“潜在的读者”这个概念来解答“时代精神”影响“作家”创作之间关系的空白。我们可以具体到上述所举的冯至的诗歌来做个实证。
1926年,处于新文化运动初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展现出来的是启蒙民众的心态,希望能够唤醒民众对所处时代的憎恶来引发疗救的作用。就像鲁迅先生在其《〈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就是要通过文学来唤起当时的读者对当时时代的认知,让读者能够冲围带有强烈破坏感的时代。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讲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所以,作家心中的“潜在的读者”就是那些在生活中不自觉的民众,作家默认自己的潜在的意图就是唤醒民众。而冯至《我只能》1926年的版本正是这一时代主题的呼应,对“潜在的读者”的呼应与尽应尽之责。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性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角度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他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发展方向。“一些文学史著作称之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而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是意味着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已经无法延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下去了。作家与“潜在的读者”的关系,不再是去唤醒他们,去开启他们的蒙昧。“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表面上看似乎“人民”成为四五十年代作家创作的“潜在的读者”,然而“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意味着知识分子“启蒙”的不再,意味着“潜在的读者”中包含着政治方面锐利的锋芒。其实,冯至在“建国”之后,便主动向新文艺发展方向靠拢,他开始注意自己所服务的读者的转换。他在1949年7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写在文代会开会前》,他说:“这是我理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这样明显的严肃性:在人民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我听到一个从来没有这样响亮的呼唤:‘人民的需要。’”冯至,很清楚地表现了他的文学创作将是“人民的需要”,在写作过程中,自然有意无意地将“潜在的读者”设置为的政治概念中的“人民”,通过写作去融入“人民”,融入集体主义。那么对环境的抗争的消解也就成了必然。
我们经常讲时代精神能够影响作家的写作,然而这种影响如何发生呢?我想,引入接受美学的“潜在的读者”作为一个考察的视域,或许能够让我们透析这种影响的内在肌理,引向创作论方面问题的思考。
注释
①[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②朱立元:《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3页。
③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收录于《张爱玲集·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④《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68页中引了这段话,详情请见[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⑥⑧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⑦[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⑨鲁迅:《〈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版。
⑩李泽厚:引自《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⑫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版,第5页。
[1][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75.
[2]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73.
[3]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69.
[4][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81.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1987.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7]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
[8]张爱玲.张爱玲集·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9]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作 者:
林存斐,集美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编 辑:
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