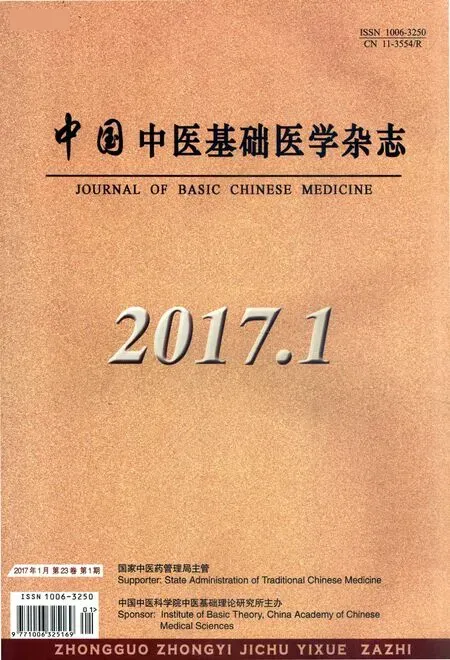《伤寒论》“不存在症”的临床意义探析*
张朝宁,李金田
(1.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兰州 730000;2.敦煌医学与转化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伤寒论》“不存在症”的临床意义探析*
张朝宁1,李金田2△
(1.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兰州 730000;2.敦煌医学与转化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伤寒论》中很多“不存在症”如不恶寒、不发热、不渴等是张仲景辨别病证和治疗用药的重要依据,是张仲景“平脉辨证”和“谨守病机”思想的主要体现,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辨证内容和极高的思辨水平。“不存在症”为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提供了独特的思路,理解“不存在症”的意义可以更准确地掌握张仲景方证,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和临床疗效,故从辨病辨证、鉴别诊断、遣方用药3个方面阐述了“不存在症”的临床意义。
《伤寒论》;不存在症;临床意义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伤寒论》是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专著,为中医临床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中一些“不存在症”[1],即不存在的或者没有表现出的症状,如“不渴、不呕、不恶寒、不发热、不痛”等,对临床辨证论治意义重大。本文就《伤寒论》中“不存在症”的临床意义试分析如下,以期广大同道斧正。
1 提供辨病辨证关键条件
《易传·系辞》云:“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说文解字》解释“辨,判也”,理论体系萌发于古代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中医学当然也以“辨”为首要任务。《周易》以“变易”思想阐释事物。《易传·系辞》曰:“通变之谓神”,“通变”即指变化,对变化的事物则强调“惟变所是”,此“变易”观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就是用动态观念认识不断变化的疾病,知其常晓其变,识其有辨其无,从而确立相应的治则以变应变,即辨证论治。最早明确记载“辨证”的是《伤寒论·序》中的“平脉辨证”。细研《伤寒论》发现,论中一些“不存在症”也体现了张仲景“平脉辨证”的思想,张仲景不仅从已出现的症状和脉象来判断病证,而且也于不存在的或未出现的症状中辨别证候,以探求机理。
《伤寒论》温病卫分证与太阳病特点类似,如何鉴别太阳病与温病,“不存在症”提供了关键条件。如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句为温病的提纲证。温病是感受温热邪气引起的外感病,温热之邪犯表、营卫不和易伤阴液,故发热而渴。尤在泾认为,“伤寒阳为寒郁,故身发热而恶寒;温病阳为邪引,故发热而不恶寒也”[2];柯琴认为“温病内外皆热,所以别于中风、伤寒之恶寒发热也。[3]”由此可见,张仲景用“不恶寒”作为温病和太阳中风、伤寒证辨别的关键点之一。
在阳明病辨证中,“不恶寒”同样作为辨别病证的重要条件而被多次论述。第48条:“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此条中“不恶寒”是辨证的关键点之一,阐述了二阳并病的原因及转属阳明的病机和表现。太阳病初起应以汗解,若汗不得法可致汗出不彻,不能驱邪外出,阳气闭郁化热,表证未罢,阳明里热证已现,此为二阳并病。若由无汗变为汗出不断,恶寒变为不恶寒,则提示病已转属阳明,“不恶寒”为转属阳明病的辨证要点之一。再如第182条:“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第198条:“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第212条:“……日哺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第221条:“阳明病……不恶寒……身重。”第244条:“……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以上这些条文中,“不恶寒”均为确诊病入阳明的重要辨证依据之一。尤在泾认为,“经邪未变故恶寒,入府则变热而不寒,恶寒为伤寒在表之的证,恶热为阳明入府之的证”[2],故而只有恶寒不存在或消失时方能说明表证已罢,邪入阳明。
在太阴病的辨证中,同样体现了这种以“不存在症”为重要辨证依据的临床思维方法。如第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此条指出了太阴病的主证、病机和治则。因中焦脾胃阳虚,运化失职,寒湿内停,故下利,但下利不重且无热邪伤津,故口不渴。与太阴提纲证“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273条)相参,加以“不渴”这个不存在的症状,使太阴病脾胃阳虚、寒湿内盛的临床辨证更加完善,故张仲景十分肯定的说“属太阴”。
第141条:“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仅不渴者,服文蛤散。”这是邪在表,当汗不汗,而以冷水灌之,热被寒劫,热伏水内不得散,故虽欲饮水,但口反不渴,以文蛤散去水热互结之气。“不渴”这一不存在的症状恰恰是辨别表间有水的关键点。
2 提供鉴别诊断主要指征
对比分析是张仲景辨析疾病的特点之一,而以“不存在症”作为鉴别主要指征的这种思维方法在《伤寒论》中处处体现。如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此条中发热表示机体正气充盛,与邪抗争多为阳经病的表现,无热则为正气不足,无力抗邪多为阴经病的特点,“无热”这一不存在的症状作为阴经、阳经受邪之异的主要鉴别点。
第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此条因太阳病先下后汗,继而出现烦躁、发热、不呕提示非少阳病,不渴提示非阳明病,无表证则非太阳病,故而排除三阳病阳热实证烦躁的可能,以“不呕、不渴、无表证”这一组不存在的症状为鉴别关键点,辨证为阳虚阴盛证,因汗下后损伤阳气,阴寒内盛所致。再如第73条:“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此条张仲景惜字如金,只以“渴与不渴”对比鉴别水蓄下焦与水停中焦的不同。太阳病汗不如法,损伤太阳经气,膀胱气化不利,水蓄下焦,津液不布,故必见口渴,治以五苓散。若不渴,是因汗后胃阳被伤,腐熟无权,水停中焦,治以茯苓甘草汤。“不渴”既作为茯苓甘草汤的主要临床特点,又是五苓散证与茯苓甘草汤证的鉴别关键点之一。
第149条论述少阳病误下后的3种转归,且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提出了痞证与小柴胡汤证、结胸证的鉴别:“若心下满而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文中以“不痛”作为结胸证与痞证的鉴别关键点,误下后邪热内陷,与痰饮互结于胸膈则为心下满而痛的结胸证,误下后脾胃之气损伤,邪气乘机内陷,脾胃升降失常,气机痞塞则为满而不痛的痞证。
第166条:“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气上冲喉咽,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此条以“头不痛、项不强”强调桂枝证与胸中痰食阻滞的鉴别。痰食阻滞上焦,营卫之气不利,腠理开合失司,故也有发热、汗出、恶风等症,但因“头不痛、项不强”这组不存在的症状,则非桂枝汤证,结合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等症,辨为痰食阻滞胸膈之证。
3 提供治疗用药重要依据
《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有此症应当探求其机理,无彼症也应探究其原因,务求与病机相合。由此可见,“不存在症”是张仲景病机辨证的体现。在治疗用药过程中,全面准确地审查并掌握疾病病机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伤寒论》中针对同一症状治疗的方剂甚多,在根据其他兼症无法判断其病机时,张仲景通过“不存在症”排除相应可能的病机,从而确定正确的治疗原则,并选择适宜的方药。
如第15条:“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误下之后,正气重伤,无力抗邪,表邪内陷,变证已成,故“不上冲”这个不存在症为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不能再用桂枝汤。再如第61条干姜附子汤证,以“不呕不渴,无表证”排除三阳证,辨证为阳虚阴盛,故选用干姜附子汤。第96条:“或胸中烦而不呕……或不渴,身有微热……小柴胡汤主之”,方后加减中“胸中烦,但不呕”,说明邪未犯胃,故去降逆止呕的半夏,加栝楼实清热涤痰;“不渴”排除阳明热盛,“身有微热”判断病势在表,故去益气生津的人参,加桂枝和表。第174条:“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此条以“不呕、不渴”说明里无热,乃风寒湿邪为患,故加附子以温阳散寒。
在用药过程中,张仲景根据“不存在症”调整用药。如第141条:“不利,进热粥一杯”,指巴豆类药物是通过下利而驱除寒积达到病除,若不见下利,则进热粥以助巴豆下利驱邪,因巴豆“得热则行”。第166条:“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瓜蒂散因势利导,通过催吐作用使胸中寒痰、食积从上外越,若服药后未出现吐则为病重药轻,应逐渐加大剂量,以吐为治疗目的。第209条:“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鞕,后必溏,不可攻之。”服用小承气汤后本该出现转矢气,提示燥屎已成,可用大承气汤攻下,若不转矢气说明燥屎未成,不可误攻。
《伤寒论》中“不存在症”是辨病辨证和鉴别诊断的关键条件,是治疗用药的重要依据,探讨“不存在症”对拓宽医者临床辨证论治思维大有裨益,值得伤寒学者重视与学习。
[1]吴修符.《伤寒论》“不存在症”辨证意义的探讨[J].中医药信息,1993,5(1):2-4.
[2]尤怡.伤寒贯珠集[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3]柯琴.伤寒来苏集[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0.
R222.2
A
1006-3250(2017)01-0035-02
2016-05-24
敦煌医学诊疗技术与临床应用(DHYX1415-004)
张朝宁(1980-),女,甘肃会宁人,主治医师,在读博士,从事中医药防治西北地区常见病的研究。
△通讯作者:李金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药防治西北地区常见病的研究,Tel:13609356623,E-mail: 17546488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