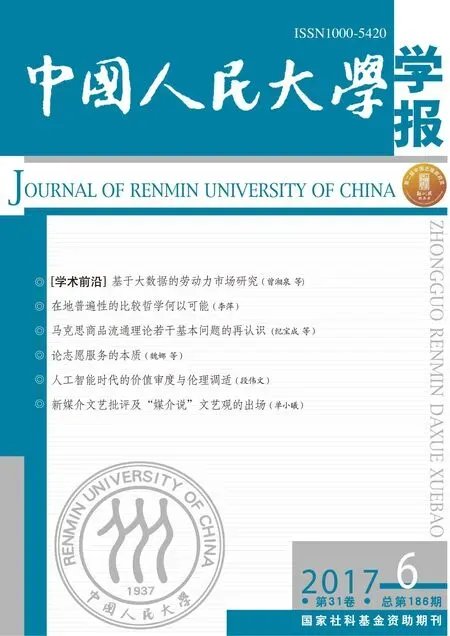论戏曲表演与身体美学
肖 英
论戏曲表演与身体美学
肖 英
长期以来,在西方美学思想中,身体的价值和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自20世纪以来,身体才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研究。人们开始意识到生命与世界的感知联系,是因为身体的存在而产生的,并借身体达到表意作用。在中国的戏曲表演中,身体所蕴含的美学思想极其丰富,所体现的美学特征极具意味。演员通过“以身化物”、“以虚拟实”的方式来代替舞美布景和时空的具体表现,不但讲究造型的优美,而且在表现角色的喜怒哀乐以及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一整套程式化、虚拟化和写意化的身体语汇。
戏曲表演;身体美学;道家思想
近现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所谓“身体的转向”,学者们或借身体立场控诉精神压制,或以身体符号来批判社会权力。可以说,有关身体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长期以来,在西方美学思想中,身体的价值和意义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知。苏格拉底就把身体当作人类获得知识的一道阻隔;柏拉图更是贬低身体的地位,并视之为“真理的敌人”;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身体仍然是一种被视为消极的不需过多研究的事物;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中,身体虽然被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但仍只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只是随着“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身体本体论的出现,这一历千年而不衰的非自足的身体观才得以彻底地改观”[1]。人们认识到,感觉绝不是纯粹的生理或心理问题,它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随便产生,也不是哪一个行为人的首创,其发生和肢体表达是一种习惯的反映。“它们是行动中的思考,受到意义和价值体系的支撑。它们根植于某种身体文化中。而这种身体原则上可以被和它同源社会文化的人所认知,体现出特有的社会构筑和文化风格。”[2](P3)
身体不是被动地呈现文化,而是积极地创造文化。人通过身体来认知、理解世界和他人,并给自身带来内心反应。没有身体就没有表演,身体是表演的载体,表演需要身体来呈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演员运用身体语言“以虚拟实”、“以身化物”,使整个舞台呈现出一种情、景、诗、画交融的象外之象。可以说,戏曲表演中所蕴含的丰富的身体美学思想是中国戏曲艺术延绵传承的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在梳理身体美学与戏曲审美、道家文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运用身体美学和道家文化的相关理论,对戏曲表演中的身体审美特征进行深入的阐释与研究。
一、身体美学视域下的戏曲审美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拥有表意功能。身体是意义产生的前提,生命与世界的感知联系是因为身体的存在而产生的,并借身体达到表意作用。换言之,身体动作是一种表达,有其自身的意义。例如,疯狂、愤怒、喜悦等内在感受,都可以通过相关的身体动作得到充分表现。这种实践的身体意识把我们带进了生命领域,即身体是一个暗含原初意义的身体,我们借由身体展开对世界的具体知觉,而意义借由身体而体现。可见,身体是一种表意图景,“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3](P194)。戏剧作为人类用来表达对世界理解的一种艺术形式,与身体美学有着先天的关系,因为物质化的身体正是戏剧表演的依据和基础。从原始狩猎模仿、巫术模仿到图腾模仿,戏剧里的角色原型越来越清晰,观演关系也得到不断加强。原始戏剧就是反映了先民狩猎的假定性场景。
尽管中国传统思想里没有“身体意向性”这个哲学概念,但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古人对“生意之意”[4](P468)的普遍关注。这种对“身体意向性”的强调可见于“身,伸也”[5](P26)的词源学解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身体无一例外地都不是被看做是实体论的,而是被看做动态的、开放的、充满活性和张力的。
形体态度、声调、面部表情等都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而人类的表演必然包含这些影响因素。正如陈伯海所说:“审美活动实起于由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矛盾统一所引发的精神自我超越的需求,而这种自我超越的需求亦构成了身体(即人的生命活动)自身的一个维度。”[6]一种戏剧艺术需要找到自己的身体姿态。在戏曲表演中,“一个圆场八百里,万仞高山三五步”。它不是通过舞美布景等具体的“物”来表现,而是通过“人”,即通过演员的身体语言,以“以身化物”的虚拟方式来代替舞美布景和时空的具体表现。例如,舞台上原本没有“花”的道具,但通过一个“卧鱼”的嗅花身体动作,美丽的“花朵”就形象地“绽放”在观众的想象之中。
诚如戏谚所云:“万物皆备我身”。在戏曲舞台上,观众所看到的一切景物皆是演员的身体语言。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正与道家所崇尚的“物我合一”的思想相契合。例如,在《拾玉镯》的舞台上,仅有一桌二椅,演员通过开门的虚拟动作,让观众看到孙玉娇走出房间来到了院子。演员先是走到舞台的左前方,斜侧半蹲,以手势的虚拟(无实物)动作开鸡圈门;圈门打开,观众仿佛看到了一群鸡争先恐后地向外涌出,而扬起的灰尘进入了演员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虚拟的擦眼睛动作;给鸡喂食时,演员通过想象准确地感知鸡的位置、方向,将食物一份一份地撒向不同的位置,看着群鸡争先恐后地进餐,对于没抢到食物的鸡,还会再次多给它喂点儿;当数鸡时(虚拟动作),突然发现少了一只,惊讶(动作停顿)、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赶紧再数一遍(这时,无论是心理节奏还是动作的外部节奏都已加快),当证实确实少了一只时,慌忙四处寻找;当找到那只丢失的鸡后,如释重负般地深吐一口气,兰花指绕指同时配上一个轻轻的、俏皮的跺脚动作指向这只鸡,表示对这只鸡充满爱怜的、淡淡的埋怨之情。由此可见,戏曲舞台上的“景物”是这样诞生的:首先,演员通过虚拟想象,心里有物;然后,演员通过“以身化物”的身体语言,以写意的方式表现出来;最后,观众和演员一样,也“心里有物”,在审美意境上实现“物我一体”。
同类的例子在戏曲表演中可以说不胜枚举,《打渔杀家》中的“行舟”,《杨七娘》中的夜晚“骑马征程”,《游西湖》中的“游湖”,都是演员在用身体语言来描述、表现环境。《蝴蝶杯》在“游龟山”一折戏中可以不用任何具体的布景,只需要通过演员的唱腔、身体语言,即可表现出长江、龟山、黄鹤楼等环境。这种景致使观众看后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个幻化的戏剧情境,使舞台的空间变化无穷,灵活自由。
舒斯特曼说:“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7](P3)无疑,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积淀了华夏民族对美的独到感悟,其身体语言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戏曲这种“以身化物”的表演方式,带给观众一种“物我一体”的审美体验。而观众在欣赏戏曲表演时为演员“身心合一”的表演所带动,最终完成了一次耐人寻味的巅峰的审美体验。
二、戏曲身体与道家文化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任何身体都不仅仅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与其所处的整个文化环境相生共存。刘峻骧在《东方人体文化》中指出:“‘子午阴阳,求圆占中’既是东方人体文化的宇宙观的体现,又是美学情趣的发生依据。”[8](P144)
身体与文化唇齿相依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体绝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形躯之身,而是“天生人成”的后天养成之身。古代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视身体为人类罪恶的温床,而是强调它的连续性和协调性。如果说儒家采用了“践行”的修身方式,那么道家则是强调“涤除玄览”的心境,通过“坐忘”使身体与天地产生化合。可见,这是一种“栖居式的审美”,可以体验到“心游万仞”的精神境界。
无疑,道家的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智慧。叶维廉认为:“道家美学,指的是从《老子》、《庄子》激发出来的观物感物的独特方式和表达策略。”[9](P1)陈望衡也说:“从实质来看,散文诗般的《老子》既是哲学著作,也是美学著作。《老子》的美学智慧就寄寓在它的哲学之中,只要换一副眼光去看,那‘五千精妙’的《老子》俨然就是美学。”[10](P31)例如,“传神写照”、“意象”等重要概念都来源于道家思想。徐复观更是明确指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上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上系由此思想系统所导出。”[11](P28)道家的这种“艺中有道”的审美理想,直接地影响了戏曲表演的身体美学。
我们知道,中国戏曲艺术是在农耕社会舞台技术落后的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虚拟化和写意化的表演风格,是戏曲反映生活的最基本的特征,它和西方话剧写实逼真的表演风格截然不同,其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老子认为“道”是有与无的统一,舞台上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道”产生的。正如沈达人所言:“正由于戏曲的舞台时间和舞台空间是心理上的时间和心理上的空间,所以在虚拟表演的作用下,才能够可放可收,或隐或显,浓缩蔓衍,变化自如。”[12](P193)众所周知,“写意”和“写实”一样,同样要以“真”和“现实”作为基础,关键在于前者对于客观形象采取的不是一种“模仿”的方式,而是在创造中化被动为主动。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戏曲运用高度的概括、想象和创造力,着重对形象的“神”进行升华和突显,使它成为“以形传神”的虚拟表演。
另外,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道家并没有致力于研究世界的运动规律,也不着眼于人和自然的冲突矛盾,而是把人看做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和大自然成为一个不可割裂的生命整体。对于大自然,我们不是单纯地从物质利用上去征服它,破坏它的和谐,而是要把世界始终看成是和人的精神与情感交融一体的存在。因此,人应该摆脱“物欲”,用纯朴的心灵去拥抱大自然,用最广阔的胸怀消弭那“客体”与“主体”、“物”与“我”的界限,把自己的身心融化在大自然中,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既然从精神上摆脱了物欲的支配,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也就不至于一切都受制于“物”的支配。戏曲艺术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以藏胜露”的艺术力量,尽可能地摆脱“物扰”、“物累”,把自然环境几乎全部虚化,使舞台上一片空灵,只突显“人”与“情”,从而在空灵之中获得写意抒情上极大的时空自由。与此同时,为了突显人物,摆脱物累,戏曲的虚拟表现还可以把一切笨重、烦琐、流动性大的生活实物虚化,化为“以无胜有”的抒情表演,来突显人物的情态、神韵。例如,在“以简胜繁”的表达中,把千军万马简化为人群的意象(几对龙套);在“以虚带实”的表达中,把大帐化为三军司令或床的意象……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演员虚实相生的表演,使整个大自然如山、河、路、桥、风、花、雪、月等都呈现在舞台上。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形式都带有鲜明的飘逸写意的美学风格。宗白华说:“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13](P31)因此,戏曲表演艺术跟中国诗画一样都深受道家美学影响,在审美追求上极具相似性。陈幼韩提出“‘诗画交融’是戏曲表演艺术的总体美学特征”[14](P51)。在戏曲表演中,身体语言所呈现出的舞台场面,既如一幅诗意盎然的风景画,又似一首空灵飘逸的写意诗。诗画融于一“身”的美的呈现,在戏曲表演艺术中不胜枚举。
当然,戏曲演员在“以身化物”时,还要注重融入角色的感情。戏谚有所谓“戏从心上起,满堂都动情”之说。昆曲名家华传浩指出:“不能仅搬身段,必须联系生活感情,否则就没有内容,没有灵魂,也不会达到血肉交融的美的境界……小和尚念的四句词,是他乍出山门,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丽景物,顿然心旷神怡起来,所以‘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尽量抒发他开朗愉快的胸怀。”[15](P129)在《孽海记·双下山》一折戏中,华传浩在表现小和尚本无偷溜出山门时,运用了一系列精彩的身体语言,使台下的观众也身临其境。于是,原本空无一物的舞台,在观众眼前呈现出紫燕衔泥,黄鹂娇啼,穿花蝴蝶的景象。
戏曲表演中所蕴藏着丰富的道家美学思想。道家对繁复的人为之美抱以消极的批判态度,强调“恬淡为上,胜而不美”[16](P79),“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7](P111)。中国戏曲艺术充分汲取了道家美学的精髓,以最朴素的外在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的身体功能,它不仅能够摆脱物累,不为物役,而且能够在人和物的互动交融中,通过对生活的提升,于虚拟和写意之中创造出情景交融的神韵意境来。戏曲表演中演员身体语言所还原的“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是剧中人物情感的投影,是一种“心化之景”,也就是道家所谓的“以艺求道”。
三、戏曲表演中的身体审美特征
戏剧表演是“通过舞台行动过程展示角色形象,当场征服观众的艺术”[18](P5)。“在舞台上要动作,动作、活动是戏剧艺术、演员艺术的基础。”[19](P78)演员要向观众进行信息、角色情感、思想、心理及剧情的传达。也就是说,演员是运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创造出鲜明的角色形象。正因为如此,在舞台上,身体语言对演员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戏曲载歌载舞的表演形态和表演手段都是身体范畴的总和。无论是唱念做打,还是手眼身步,都是通过身体来完成的,都是身体语言的组成部分。傅谨指出:“在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演员‘身上’的玩意儿才是关键,戏曲表演是诸身体的艺术,‘身上’的功夫——演员的身体语言才是戏曲表演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
在中国戏曲中,身体动作不但讲究协调的韵味和造型的优美,而且要求动作内(心里)外(身体)结合,充分表达意思,展现角色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无论是在表现角色的悲、喜、哀、乐,还是仪态、风度等方面,戏曲都有一整套虚拟、写意的程式动作语汇。例如步法,不同的行当会以不同的台步来表现角色的特定性格。戏曲舞台上用扇,不全是表示季节,大多是用来刻画人物个性、表现人物情绪情感、美化人物形象的。风流小生垂扇画圈,表示高兴;缓缓煽扇,表示儒雅;合扇化掌,表示思考。双撑袖表现人物观望或胆战心惊,遮面袖表现人物害羞和不愿观看,甩袖表示不满情绪,小云花袖表示心花怒放,等等。每一个水袖动作都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情感,它无声无息地使人物内心的所思所想的种种变化得以表现。
首先,在戏曲身体语言中,广泛地运用了圆形的规则,体现了中国历代艺术家独特的美学追求。陈永祥在《戏曲舞蹈艺术》中写道:“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与圆相关,圆形首尾相衔,没有破绽,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21](P22)“圆”是中国古人对整个宇宙认识的凝练和升华,蕴含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之理,因此,“以圆为美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审美心理定势,在戏曲表演的‘唱、念、做、打’的外显形式及其内在的构成关系上, 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由辩证对立或多样性的统一所构成的圆美观,讲的都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之理”[22]。
戏曲表演中的身体动作造型、构图丰富多彩,样式千姿百态。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的造型,都是用不同规格、多维的“圆形”组成的。常用的手位如“按掌”、“提襟”、“撑掌”、“山膀”、“顺风旗”、“扬臂”等,都要臂圆腋空,呈弧圆形。另外,动态的运行轨迹也都是圆的,如常用的“云手”、“大刀花”、“划掌”、“缓手”、“掏掌”、“分掌”、“小五花”等动作,在运转过程中,手臂都保持弧形,支撑手臂运转的力度要消除棱角,慢动作婉转轻柔,快动作迅速有力。再如“剑穗花”、“枪花”、“刀花”、“扇子花”、“棍花”、“手巾花”等,在表演时更是用连续不断的圆圈流畅地连接而成。
戏曲表演中的调度线路也多是弧线,并以此为基础演变成圆线、波浪线、曲线、绕八字、倾斜线、二龙出水等程式。人物上场多半走一个小弧线,下场一般也是走曲线下场,在迂回进退之中表现出“翩若惊鸿”的形式美。
各个行当的身体站姿也是多循曲线呈现,基本侧身面向观众。如旦角在舞台上的站立,只有脚、腰、头呈三个不同方位,如左脚尖向右前方,下身呈右侧面站,而上身向左拧,形成曲线形(如S形),反之,右脚尖向左前方,下身呈左侧面站,而上身向右拧(面向观众),这样站在舞台上才有女人的妩媚与妖娆。如梅兰芳扮演《醉酒》中的杨贵妃时,充分利用扇子与水袖进行不同的曲线弧形造型和构图,不但展示了人物雍容华贵的气质,同时又透出了人物的妩媚和俏丽。
其次,动静相衬是戏曲身体表演中的审美特点之一。正如朱熹所言:“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便阳往交易阴,阴来交易阳,两边各各相对。”[23](P143)在梨园界,一向讲究“要有子午相”,“要有阴阳面”。这“子午阴阳”既是戏曲表演的外在形式,也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戏曲表演中的内在体现,是刚柔、动静、高低、快慢、进退等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从而构成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圆融空灵之美。戏曲表演中的运动也具有一定的形式规范,一般来说,由四个环节组成一个动作,即起、行、顿、止。
“起”在业界称“起法儿”,是指动作的开端和起始,其在一个动作中所占的时间很短,却为动作提供适当的幅度、力量和趋向。我们时常看到演员做“云手”时,有个“单山膀”的起势动作。也就是说,做“云手”前是从“单山膀”的动作起始的。“行”是动作的运行过程,是“起”的延续,一般是动作的主体。如连续“翻身”、“跟斗”、“转帕”、“水袖花”等动态造型,一方面是为剧情服务,另一方面也起到强化情感和渲染气氛的作用。“行”有时也是静止姿态的装饰铺垫,如“翻腕”、“穿掌”、“划掌”等。“顿”是动作瞬间的顿歇,也是“止”前的准备和铺垫,如“亮相”,甩头前必先回头。没有动,就显不出静;没有静,也就无所谓动。如果说回头是甩头前的最后一静,那么甩头是静前的最后一动,从而增强了动与静的对比。“止”是动作的结果,直接影响着静的优劣。 “起”与“行”是动的部分,“顿”与“止”是静的部分。“止”是动作的结束点,既是动后相对静,又是静前聚集力量的动。
具备以上四个环节,在表演中才算一个完整的动作。可见,身体语言就是由无数这样的表演单位组成的。正是运用了身体语言的动静对比,以各种优美动人的姿态,才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的精神美和形态美。由于戏曲的动静相衬,使得戏曲表演中的身体语言具有较强的功能,以表现各种打斗场面以及人物的细微反应。如穆桂英是经常奔赴战场的女中豪杰,所以她的动静相衬就要鲜明而大气,而《拾玉镯》中小家碧玉的孙玉娇的动静相衬就要小而灵活。
再次,在戏曲表演中,动作的“迂回”是其又一审美特征。老子所谓“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24](P161),讲的就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道理。戏曲表演中的身体语言用迂回曲线的方法,使动作突出对比,相互衬托,把有限空间充分利用,以达到无限伸展和延续。它是用有限空间表现无限生活的一种巧妙处理方法,从而使戏曲身体语言更加有张力,更加鲜明生动,同时使动作造型具有一定的韵律感,给人以余味无穷的艺术享受。
戏曲身体动作的迂回法则是欲左先右、欲前先后、欲上先下、欲强先弱、欲快先慢等。它是动作的突出强调,起到了渲染和强化的作用。欲进先退,斜线曲折,既渲染情绪和气氛,又是传情的一种手段。在戏曲舞台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听到某种异议时,演员往往愤然后退,然后再往前以表示说理。如果亲友重逢用后退的方式,还不足以表达见面时激动的心情,就会运用其他抒情的手段进行烘托或者渲染。这既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太极式”的周流运转、和谐贯通的圆融境界,使得迂回的身体状态在舞台上获得了审美的意义。
最后,戏曲表演追求“手、眼、身、步”和谐统一的规范美。戏曲是典型的以“技”求“艺”的程式化艺术,它的身体语言非常讲究动作的严谨规范。任何动作的圆形曲线、幅度大小、速度快慢、力度强弱、姿态方位、音乐节奏、表达分寸等,都有一定的规范要求。戏曲表演一旦做到了规范的精准,就自然呈现出协调的规范美。
戏曲界讲究“三节六合”。所谓“三节”,指以整个人的身体来说,头是梢节,腰是中节,脚跟是根节;以腿来说,脚是梢节,膝是中节,胯是根节;以手臂来说,手是梢节,肘是中节,肩是根节。所谓“六合”,通常指手与脸合、脸与眼合、眼与身合、身与气合、气与意合、意与情合。“六合”也分为“内三合”与“外三合”。“内三合”是手与眼合、意与形(形体)合、情与技合;“外三合”是手与脚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只有做到手动、步动、面部表情、眼睛神态、呼吸状态等的有机配合,才能使动作造型或构图达意准确、神韵生辉。
在戏曲表演中,表情和眼神的传达是身体语言规范中的重要环节。戏剧界古训:“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情动于衷而形于外,以眼传神”。当演员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出场时,眼睛就成了关键点:或左右转动表现活泼可爱、敏锐机灵,或圆睁双目而状其威武,或顾盼多姿而状其洒脱飘逸,或嫣然凝视而状其妩媚,或引目四瞩而状其英姿挺拔,让观众一眼就感觉出角色的身份、品第和性格来。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时,当穆桂英接过帅印,两只眼睛睁大炯炯有神地扫场一周,高高举起帅印时,回头(松收眼光),随即亮相,眼神光芒四射(一刹那间观众都被他的眼神抓住了),通过一双光彩逼人的眼睛刻画出当年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的形象,体现了穆桂英的雄心和热情。
总之,戏曲艺术中的身体动作讲究协调的韵味,广泛融入了圆的美学精神,巧妙地运用了动静相衬、“迂回”等构图原则,追求“手、眼、身、步”和谐统一的规范美,并且要求动作内(心里)外(身体)充分结合,最终体现出一种“以身化物”、“神形兼备”的审美特征。
四、结语
当下学术界对身体的关注得益于现代艺术的兴起与发展。现代艺术主张通过身体来感知世界与生命,并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身体不仅有自然物质属性,体现个体生命状态和思想情感,同时也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在现代艺术家眼里,我们的身体既是存在着、被经验着的客体对象,也是经验着、意识着的生命主体。他们反对身体被社会的枷锁禁锢——被禁锢的身体具有社会的习惯标识,产生自动化的反应机制,因而隐藏自我。特佐普罗斯曾言:“我们试图调动整个身体的活力,了解身体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常常笨拙地舞蹈,表现新生、生命,死亡的旋舞由此从混乱中诞生。我们要用新眼光看世界,张大身体之限……超越身体极限,通过身体传递能量,或使身体成为交流第一手材料的场所。”[25](P42)
在多元化戏剧理念的冲击下,当今的舞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那么,戏曲在思想表达和演出形式上,如何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前提下突破创新?笔者认为,即使我们积极地拥抱新事物,戏曲舞台也应该是结合了中国戏曲的身体审美特性,有选择地利用时尚元素在跨界中实现多元、兼容。戏曲演员需要适应现代表演,但更要强调戏曲内存的身体表达和传统美学,不能违背戏曲的表演规律,更不能简单地用话剧改造它。我们期待国内的学者能够运用民族化的审美传统,拥有国际化的思想视野,用一种有别于西方理解的新维度全面阐释中国戏曲表演的身体审美及其文化。当然,强调中国身体文化的特殊性是有条件的,不能简单笼统地、捕风捉影地把中国的身体观概括成一个“家族概念”,将传统文化中所有有关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观念全都“装进身体”里,甚至轻率地将身心关系看成诸如生命场域、修养境界等虚无缥缈的个人修行。
[1] 张再林:《“我有一个身体”与“我是身体”——中西身体观之比较》,载《哲学研究》,2015(6)。
[2] 大卫·勒布雷东:《日常激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3]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5] 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陈伯海:《“肉身”也能“证道”———论审美活动中的身心关系》,载《文史哲》,2010(5)。
[7]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 刘峻骧:《东方人体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9] 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 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 沈达人:《戏曲意象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
[13] 宗白华:《艺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4] 陈幼韩:《戏曲表演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15] 华传浩:《我演昆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16][17] 饶尚宽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
[18] 叶涛、张马力:《话剧表演艺术概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19]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精华》,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0] 傅谨:《身体对文学的反抗》,载《读书》,2006(4)。
[21] 陈永祥:《戏曲舞蹈艺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
[22] 危磊:《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圆美观》,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5)。
[23] 朱熹、吕祖谦:《朱子近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4] 老子:《道德经》(四部精要第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5] 特佐普罗斯:《特佐普罗斯和阿提斯剧院:历史、方法和评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
AStudyofDramaPerformanceandBodyAesthetics
XIAO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Shaanxi 710049)
In western aesthetic ideology,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body have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until the 20th century when human body became a topic of great concer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perceptive connection between life and the world originates from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ody which is used to express. In drama performance, human body contains rich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highly meaningful aesthetic features. Actors use their bodies instead of stage scenery or concrete space-time manifestation to express things and feelings. It emphasizes not only on beautifully designed looking, but also on a full set of stylized, virtualized and impressionistic physical vocabulary to express the characters’ emotion and personalities. Taking practical plays likePickuptheJadeBracelet,GoDowntheMountainsTogetheras example,this paper adopted theories about body aesthetics and Chinese Taoism culture in an attempt to probe into body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in drama performance.
drama performance; body aesthetics; Taoism philosophy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成果(SH1510GFXK)
肖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陕西 西安 710049)
(责任编辑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