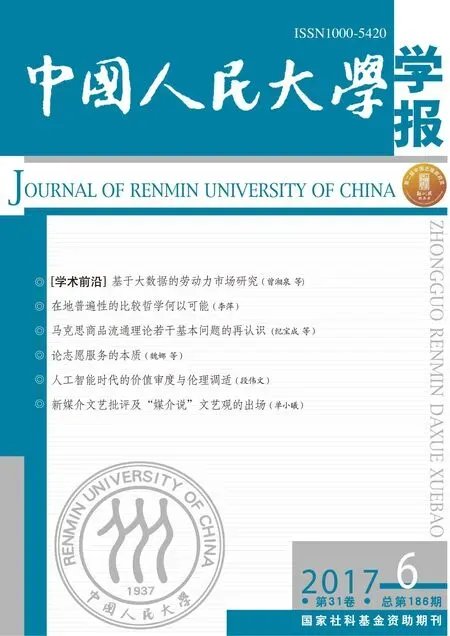秦县中的史类吏员研究
朱 腾
秦县中的史类吏员研究
朱 腾
在秦县中存在着大量以“某史”为官称的吏员,他们是活跃于秦县行政第一线的书记小吏。秦以官文书为行政运转的必要渠道,这些史类吏员则以官文书之书写、制作与保管为其基本职能。不仅如此,由于县中的长吏们往往因政务繁多而无暇事必躬亲,面对官文书所涉事项,他们往往会令“某史”们调查事态。这使史类吏员广泛参与了秦县的治理,从而获得了衍生性职能。至于“某史”们何以能适应官文书的不断流转,其职业素养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此种素养是在其以史学童的身份学习行政文字时逐渐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秦的文书行政就是官文书、史类吏员及行政文字的合成物。
史类吏员;官文书;行政文字;官僚制
在古代中国,将先民们的事迹及情感记录下来,使其传之后世者主要是史官。然而,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代的文献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另一种被称为“某史”的职官,他们活跃于行政第一线且对传统中国官僚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官谓版图文书之处’——在中国古代,‘官’很早就与版图文书密切相关。早期史官的主书主法之责,为战国秦汉的官僚制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深厚土壤。行政日趋合理化,中央集权日趋强化,都不能不和‘史’的贡献联系起来。”[1](P79-80)事实上,学界对介入政务运行的“某史”确实多有关注。但是,在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前,由于秦史料的严重不足,前辈学者对秦汉时代的此类吏员的考察明显表现出重汉轻秦、以汉论秦的倾向,即便以搜罗史料达极致而闻名的严耕望先生,亦不能完全摆脱此种习惯性做法的束缚。*有关严耕望先生对秦史官的论述,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73-146页、216-24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这当然只可归因于条件所限,不能苛责前人。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后,有关秦的史料陡增,在考察“某史”时以汉论秦的倾向也有所改变。近年来,随着新简牍尤其是官文书简的陆续出土和公布,秦行政运行的实态尤其是秦县的政务流转生动地出现在学者们面前,“某史”在基层行政中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简牍文献为基础并参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对秦县中诸史的概貌及如何通过官文书影响政务处理等问题展开考察。
一、秦县中的史类吏员之设置
根据学者们的既有研究成果,秦县衙是由县廷和诸官构成的[2],而在这些机构中就设有大量以“史”为官称的吏员。
在县廷的层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令史和尉史的存在。如,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有一段记载涉及墓主人的仕宦经历,其中就提到了“令史”二字:
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3](P11)
里耶秦简8-761则述及尉史的活动:
卅三年十月甲辰朔壬戌,发弩绎、尉史过出貣罚戍士五(伍)醴阳同□錄。[4](P218)
更值得注意的是,里耶秦简所收《迁陵吏志》云:
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官啬夫十人……校长六人……官佐五十三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5]

卅年□月丙申,迁陵丞昌,狱史堪【讯】。[7](P216)
此外,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描述了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咸阳县女子婢所遭遇的一件白昼抢劫案;为了侦破此案,县廷先后派遣了顺、去疢、忠文、□固及举闾五位狱史调查案情。[8](P377-378)这些简文既指明了咸阳县廷与迁陵县廷一样设有狱史一职的事实,也直接揭示了秦县廷内担任狱史者的人数之多。概言之,以秦县廷内“某史”的种类及人数论,若说他们是秦县廷之行政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或许是不过分的。
在诸官的层面,诸官乃秦县负责各种具体事务的职能机构,其长官被统称为官啬夫[9],分而言之,又包括仓啬夫、厩啬夫、乡啬夫等等*有关官啬夫的具体设置情况,参见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65-10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单印飞:《略论秦代迁陵县吏员设置》,载《简帛》,第十一辑,92-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在这些啬夫中,辖下存有史类佐官者并不少。如,睡虎地秦简《效律》云:
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籍之曰:“其廥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禀人某。”[10](P158)
《效律》所规定的是谷物入仓时的储积标准及保管方法,而从“籍之曰”的内容来看,史类吏员显然是作为仓啬夫的属官参与了谷物入仓的管理过程。又如,里耶秦简8-269收入了资中县令史釦的阀阅簿,其文句曰:
十一年九月隃为史。为乡史九岁一日。为田部史四岁三月十一日。[11](P125)
釦是以乡史的身份初入宦途的,乡的长官为乡啬夫,所以釦这位乡史应当是乡啬夫的手下。至于简文所说的“田部”,陈伟先生认为,田部与乡、司空相当,乃隶属于县的官署之一,其长官田啬夫主管全县农事。[12]如此看来,釦在任乡史九岁零一日之后转任田部史,从而成为田啬夫的下僚。再如,里耶秦简9-981载:
卅年九月丙辰朔己巳,田官守敬……史逐,将作者泛、中,具志已前。[13](P94)
有关“田官”的机构性质,虽然学者们的观点各有差异[14],但以同简的其他简文对田官之职官组织的记录论,似应认同陈伟先生的主张,即田官与仓、司空无异,亦为迁陵县下辖的官署,负责官府经营的公田,其长官为田官啬夫,上引简文中的“田官守敬”则为田官啬夫的代理。[15]以陈伟先生之说为前提,似可认为,“史逐”之“史”乃田官史的略称,实指田官啬夫的史类属官。综合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诸官内,史类吏员也是颇为繁杂的,可谓诸官之官长在履行职责时需要倚赖的助手。
既然对以县廷和诸官为外在形象的秦县衙的官僚队伍而言,史类吏员乃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介入秦县的行政运行的呢?
二、官文书与史类吏员的职能
有关上一节末尾抛出的问题,如果要先予以回答,似可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收《内史杂律》的规定中寻觅关键性信息:
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16](P146)
可见,秦对行政运行方式有强行要求,即官吏应通过官文书说明自己对公务的处理情况,而不可亲自或托人以口头为之。如此一来,大量官文书的做成乃理所当然之事,史类吏员则承担着官文书的抄写、制作或保管之责,这是他们在秦的行政体制下斩获的基本职能,以下将尝试做出说明。
首先来看里耶秦简的如下记载:
A、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佐州里烦故为公田吏,徙属。事荅不备,分负各十五石少半斗,直钱三百一十四。烦冗佐署迁陵。今上责校券二,谒告问可(何)计付,署计年为报。敢言之。
B、三月辛亥,旬阳丞滂赶告迁陵丞主:写移,移券,可为报。敢告主。/兼手。


里耶秦简简文的另一段记述提到:
A、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债)发。敢言之。
B、四月己酉,阳陵守丞厨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之。/儋手。
C、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阳陵守庆敢言之:未报,谒追,敢言之。/堪手。
D、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觿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其以律令从事,报之。当腾,【腾】。/嘉手。以洞庭司马印行事。敬手。[18](P57-58)
这段简文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与上一段所引简文一样亦为追债,只不过官文书的发送目的地从县变成了郡,其原因无非就是阳陵县不在洞庭郡辖区内*有关此处出现的阳陵县的地望不在洞庭郡辖区内的重要理由,晏昌贵、钟炜先生已经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参见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牍所见阳陵考》,载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7,2005-11-03;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4)。,欠债人毋死在洞庭郡的何处戍守并不明确,需要洞庭郡查实。简文由四部分组成:A、阳陵县司空腾对县廷发出的要求县廷向洞庭郡寄送追债文书的申请;B、阳陵县守丞厨对洞庭郡发出的追债请求;C、阳陵县守丞庆因守丞厨的请求未得洞庭郡回复而再次发送的追债文书;D、洞庭假尉觿在收到文书后对毋死所戍守的迁陵县下达的“以律令从事”的命令。以此四部分观之,官文书的流转线路是极为清晰的,即他郡下属的阳陵县→洞庭郡→洞庭郡下属的迁陵县,而确保每一个环节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应当就是“某手”所示的“某”们,其中自然不乏史类吏员。
上引实例表明,秦县的政务都是以官文书不断流转的方式被处理的,而史类吏员就是官文书的抄写、制作者,当然也应是其保管者。*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内史杂律》规定:“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官。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参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一·上),15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其大意是说,不准把火带入藏有器物或文书的府库,吏将器物或文书收藏完毕后,官啬夫等应轮番看守,消除火灾隐患并关闭府库门;令史则须经常巡视府库情况。令史之所以承担巡视之责,很可能是因为两点:其一,令史为官文书的保管者;其二,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为官文书所记录,令史则以保管官文书之故而对这些信息颇为熟悉。由官文书推动的行政运行自然有其优势,它既可以促进行政的高效化,也可以在行政的某一环节失灵时迅速地明确并追究责任。比如,在阳陵县的事例中,阳陵县方面的官文书提到毋死“戍洞庭郡不知何县、署”,这显然是因为洞庭郡方面对戍卒的登记疏忽所致;阳陵县守丞庆又不无抱怨地指出“未报,谒追”,据此就可追问洞庭郡为何一年多时间内怠于回复阳陵县的追债请求。正因为以官文书为媒介的行政方式存在诸多优势,所以,正如里耶出土的一万七千多枚有字简大多为迁陵县所保管的官文书和簿籍一样*有关里耶简简文内容的介绍,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前言”第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另外,有关县廷在文书行政中的重要地位,还可参见土口史记:“戦国·秦代の県—県廷と「官」の関係をめぐる一考察—”,载《史林》,2012,(1)。,秦的各县廷每年所收发的文书必然像雪片一样纷纷飞来,史类吏员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进一步的问题是,对“案牍之劳形”感受颇深的史类吏员之于秦县行政的重要性究竟如何。众所周知,秦崇奉“明主治吏不治民”[19](P806)的法家哲学,对官吏的管理则实行“循名责实”的原则,“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20](P126)。如此一来,面对各类行政事项,长官们恐怕不会在未做调查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决定。同时,既然官文书的制作者是“某史”们,那么长官们就会自然地令他们走向政务处理的第一线以确保官文书的抄写等言之有据并进而避免被追责。于是,研究者们就可以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频繁地看到这样的记载:
□□□爰书:某里公士甲自告曰:“以五月晦与同里士五(伍)丙盗某里士五(伍)丁千钱,毋(无)它坐,来自告,告丙。”即令【令】史某往执丙。[21](P292)
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署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智(知)可(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令史某爰书……[22](P306)
也就是说,在刑案发生时,令史总是被派往案发地了解情况并制作爰书。其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秦的诉讼文书包含着“定名事里”(即当事人的名字、案情、住所)这一要素*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有鞫”就记载:“敢告某县主: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五(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何),可(何)辠(罪)赦,或(又)覆问毋(无)有,遣职者以律封守,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参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一·上),28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而此类信息大多是记录在“某史”们所保管的名籍簿中的。前文曾多次提到令史行庙,这表明史官还介入了祭祀活动。一应事例其实已相当清晰地指明,由于官文书所涉行政事项驳杂,因此与官文书密切相连的史类吏员也广泛地参与了秦帝国的基层治理。考虑到前文所列“循名责实”的原则,此种参与也不可能只是形式性地做样子,如“执”、“诊”、行庙等行动无一不具有实质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史类吏员是各类行政事务的真正操办者,长官们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制作的文书做出决断,而在决断的过程中很可能又听取了他们的建议。*日本学者宫宅洁在考察秦汉的审判制度时曾提出“狱吏主导型”审判模式这一概念,其具体内容为“下僚起案,上官裁决”。参见宫宅洁:《秦汉时期的审判制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载杨一凡总主编,寺田浩明编主编,籾山明卷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一卷),316-3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宫宅氏的研究所揭示的只不过是长吏与小吏在政务活动中承担不同职能的一个事例,却颇具参考价值。可以想见,在史官广泛介入政务的情况下,包括史官等在内的小吏承担大量的工作、长官则在其工作结论的基础上做出裁决这种权力运行机制不可能只存在于诉讼的场合,相反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被概括为史类吏员之职能的大幅度衍生。
毋庸置疑,长官们理应了解作为小吏的“某史”们的职能扩张,但为何似乎又对此种扩张持顺其自然的态度呢?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长官们事务繁忙,无力顾及官文书的书写、制作等问题;另一方面恐怕也在于史官们自身所具备的职业素质,但这种职业素质又是如何养成的呢?
三、文字与史类吏员之职业素质的养成
睡虎地秦简的简文收入了一条律文:“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辠(罪)。”[23](P148)这条律文揭示了史类吏员之职业素质的重要来源,但他们究竟学了什么?目前已有的秦史料并没有透露相关信息,但《二年律令·史律》中却有如下条文: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太)史,大(太)史诵课,取冣(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一并课,取冣(最)一人以为尙书卒史。[24](P297)
《二年律令》乃汉初的法律,由此反推秦的情况,或可解决上面的疑问:史学童所学的应当是文字。问题在于,此类文字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于史学童能通过学习而具备担任史类吏员的职业素质。
循此思路,考察秦时的习字教材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汉书·艺文志》载: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

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迹行上究为贵人,丞相御史郎中君……远取财物主平均,皋陶造狱法律存。诛罚诈伪劾罪人,廷尉正监承古先。总领烦乱决疑文,变斗杀伤捕伍邻。亭长游徼共杂诊,盗贼系囚榜笞臀……籍受证验记问年,闾里乡县趣辟论。鬼薪白粲钳釱髡,不肯谨慎自令然……疻痏保辜謕呼号,乏兴猥逮诇讂求。辄觉没入檄报留,受赇枉法忿怒仇。[28](P22-26)
在上引文句中,起始的“宦学”二字即表明其下文字皆与宦途有关。具体说来,除了最初两句强调儒家经典的重要性而体现出汉代重儒学的官方论调之外,其他语句涉及官职、罪名、户籍、刑罚等各类事项,无一不是贯穿于秦汉时代的制度名词的汇编。这进一步证明,从《苍颉篇》至《急就篇》的习字教科书具有内在的行政化风格,此可谓史学童所学文字的内容特征。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内容特征还是从形式特征上说,史学童所学习的文字具有较强的与政务及官文书相对接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被命名为“行政文字”。由此,史类吏员在其求学阶段其实已对官文书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在其成为“某史”之后通过实际操作和日常文字练习而得到强化,以至于其独特的职业能力也不断被提升,部分史类吏员更会因其职场表现逐渐晋升为高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秦帝国的文书行政及政府架构是建立在行政文字—官文书—“某史”这一官吏养成模式之上的。
四、结论
在古代中国,从商周尤其是西周时代开始,文书档案的制作、作为书记官的史类官员的设置及其专业训练等就已逐渐发展起来。经春秋战国,到秦时,至少在县的层面,“某史”可谓官僚队伍的重要成员。他们在作为史学童而学习行政文字时就已初步具备了应对官文书的能力。当正式成为史类吏员之后,由于秦以官文书为行政沟通的主要渠道,他们必然会经常面对各类官文书。这令他们获得了展现其初始能力的舞台,并以官文书书写等的反复操作之故而使其职业素养精进,从而成了县的长吏们的合格佐官。秦县治理亦随之凝聚在“某史”们的刀笔之上。
与文书小吏对秦帝国行政的重要意义相关,我们不禁产生如下疑问:“某史”们会不会营私舞弊,朝廷又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限制其谋利之举?对此类问题的考察将揭示出秦官僚制更为复杂的面相。不过,本文篇幅有限,只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尝试回答了。
[1]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 青木俊介:《里耶秦簡に見える縣の部局組織》,载《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九号,2005;土口史记:《戦国·秦代の県—県廷と「官」の関係をめぐる一考察—》,载《史林》,2012,95(1);叶山:《解读里耶秦简——秦代地方行政制度》,载《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郭洪伯:《稗官与诸曹》,载《简帛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孙闻博:《秦县的列曹与诸官》,载《简帛》,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10][16][21][22][23]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一·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4][6][7][11][17]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5] 里耶秦简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一),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8, 2014-09-01。
[8][24]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 郑实:《啬夫考——读云梦秦简札记》,载《文物》,1978(2);高敏:《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1);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2][15] 陈伟:《里耶秦简所见的“田”与“田官”》,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4)。
[13][18]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1);卜宪群:《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探讨》,载《南都学坛》,2006(1);王彦辉:《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叶山:《解读里耶秦简——秦代地方行政制度》,载《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9][20] 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5][26][27]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8] 史游:《急就篇》,长沙,岳麓书社,1989。
[29][30]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ResearchontheOfficialsofShiintheCountyofQin
ZHU Teng
(School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re were lots of officials owning the title of Shi in the county of Qin.They had low status, with writing archives as their function, but were activated 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y.Qin regarded the archives as indispensable channel for the opera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e officials of Shi’s basic function was just the writing, making and protecting the archives.Furthermore, when the officials of high status in the county encountered the government affairs written in the archives, as they could not dispose all of the affairs of 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 heavy weight of these affairs, they would let the officials of Shi investigate the affairs.It may make they take part in the rule to the county extensively, and thus acquired derivative functions.To the reason why the officials of Shi could adjust to the continuously operation of the archives, their vocational quality may be important, and this quality was progressively formed when they studied the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s as a student of Shi.To some extent, the archive administration of Qin was the compound of archives, officials of Shi and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s.
officials of Shi; archives;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s; bureaucrac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简牍所见秦县治理研究”( 17CFX006)
朱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