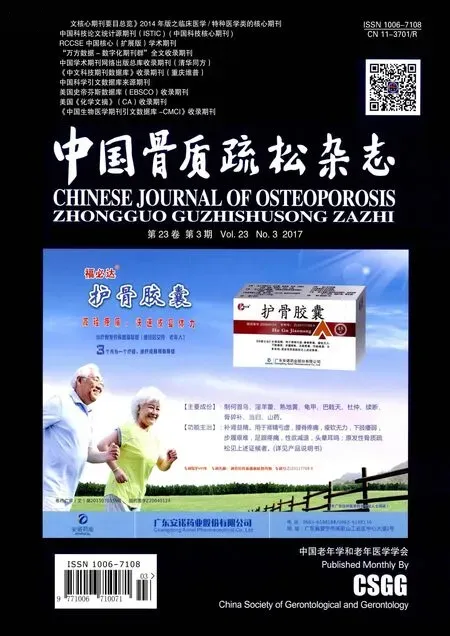肠道菌群:绝经后骨质疏松防治新靶点
贾小玥 郑黎薇 袁泉 周学东 徐欣*
1.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41 2.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四川 成都 610041 3.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四川 成都 610041 4.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牙种植科,四川 成都 610041
绝经后骨质疏松(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是一类由雌激素缺乏引起的,以骨骼强度减弱为特点,从而诱发骨折风险增加的骨骼疾病[1]。PMO常隐匿发病于绝经后的女性群体中,脆性骨折是其最常见的临床并发症。骨折在非外伤或轻度外伤的情况下即可发生,常累及髋骨、股骨和脊柱等部位并导致疼痛、畸形、功能障碍甚至死亡。调查显示PMO最严重的并发症髋部骨折在发生后第一年内的致死率为17%[2],在随后两年的死亡率达12%~20%[3]。因此,对PMO进行早期干预性治疗十分重要。目前,PMO的治疗药物主要包括双膦酸盐、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激素替代剂和降钙素等,已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但部分药物的潜在并发症及副作用也随之突显。双膦酸盐可导致部分患者出现严重的骨、关节或肌肉不适[4],少数患者在患牙科疾病或接受侵入性牙科治疗时发生颌骨骨坏死的风险升高[5]。阿仑膦酸的长期使用还与股骨粗隆下和股骨骨干骨折的发生有关[6]。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雷洛昔芬可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症和中风的风险[7]。在激素替代治疗中,雌激素可增加子宫完整患者子宫内膜增生和患癌的风险,且胆结石病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率也增加2~3倍[1]。由此可见,亟需寻求PMO防治新靶点,开辟一条安全有效的治疗途径。
近期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与机体骨代谢调控密切相关。肠道菌群是定植在人体肠道内的微生物总集,包含了大约10万亿个细菌,其菌群的总基因数是人体细胞总基因数的150倍[8]。肠道菌群主要由专性厌氧菌构成的优势菌群和需氧菌或兼性厌氧菌构成的次要菌群组成,包含了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3类菌群。作为人体内最大的微生物储存库,肠道微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变化与机体健康息息相关。研究表明,机体内外环境的改变可破坏肠道菌群内部以及肠道菌群与机体间的平衡状态,引发肠炎、风湿性关节炎、脊柱关节病、骨质疏松、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炎症性或代谢性疾病[9-12]。肠道菌群和骨骼健康或疾病状态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诸多关注,提示肠道菌群可作为PMO防治的潜在靶点。
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结构可通过饮食、抗生素或益生菌的使用来改变或修饰[13-17]。益生菌是一类由人体有益肠道菌组成的膳食或药物补剂,可通过抑制肠道内有害菌生长、促进有益菌增殖来改善或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促进宿主机体健康[18-20]。目前已知的近20种益生菌大致可分为以下5类:乳杆菌(如干酪乳杆菌、嗜酸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拉曼乳杆菌、发酵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等)、双歧杆菌(如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和婴儿双歧杆菌等)、酵母菌、链球菌(如嗜热链球菌等)以及其他细菌(如丙酸杆菌、粪链球菌、大肠杆菌等)[21]。目前关于益生菌对人体健康及疾病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益生菌可有效改善小儿腹泻、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女性泌尿生殖器感染、呼吸道感染、过敏反应、II型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炎症性和代谢性疾病[14,21-23],其中益生菌与骨质疏松的相关研究为PMO的致病机制与新治疗方法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本文旨在对肠道菌群在PMO致病机制中的作用、益生菌在PMO治疗中的应用以及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进行综述。
1 肠道菌群与PMO的相关性研究
1.1 PMO动物模型
PMO动物模型可通过手术法或化学法建立。卵巢切除术(ovariectomy,OVX)是最常见的PMO动物模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关于PMO治疗用药的临床前与临床评估指南表明,OVX大鼠模型中胫骨近端、股骨远端和腰椎的情况可以模拟绝经后妇女相应的骨质疏松疾病状态,且适用于骨质疏松治疗用药疗效的评估[24]。化学法通过使用外源性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s,GnRHa)抑制内源性GnRH分泌,进而抑制各种相关激素分泌,建立雌激素缺乏动物模型[25-26]。Kurabayashi等[25]研究发现,GnRHa处理时间为6个月的SD大鼠(sprague-dawley rat)在实验第360天的骨量明显低于用GnRHa处理3个月的SD大鼠,并且在GnRHa处理中断后,骨密度和骨转换率可有一定程度地恢复。因此,使用化学法建立动物模型是否能可靠地模拟PMO仍需要进一步实验研究验证。目前已报道的PMO动物模型建立时间差异较大,包括8w[27]、10w[28-29]、12w[30-31]、14w[32]和16w[33-36]龄小鼠和10w[29]、13w[25]和20w[37]龄大鼠进行OVX或GnRHa处理。动物模型建立时的鼠年龄大小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实验结果。如果选用青春期前的鼠建立PMO模型,可因其快速的骨生长和骨改建而更易显示出骨的变化[30],且不能排除生长激素的干扰。而小鼠在5~6个月龄时开始出现不可逆的衰老症状[38],可能出现老年性骨吸收或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而对实验形成干扰。因此,选择成年鼠建立PMO动物模型最为适宜。
1.2 肠道菌群对PMO的影响
Li等[28]将10周龄的雌性C57BL/6L小鼠分为无菌组、无特定病原体(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组和无菌鼠定植常规肠道菌群组,并对以上3组小鼠均进行为期10 w的GnRHa亮丙瑞林药物诱导雌激素缺乏和对照处理。实验结果发现与对照处理的无菌小鼠相比,亮丙瑞林处理的无菌小鼠肠道与骨髓中促破骨细胞形成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核因子κ 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for nuclear factor-κ B ligand,RANKL)和白细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的量无显著增加,同时两者骨小梁体积分数(bone volume/trabecular volume,BV/TV)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而SPF和肠道菌定植小鼠中,亮丙瑞林处理组的促破骨细胞形成因子明显高于对照组,且BV/TV值明显低于对照组。该研究提示在无菌小鼠中,雌激素缺乏不会诱发骨小梁吸收,肠道细菌在雌激素缺乏所诱导的松质骨吸收中必不可少。此外,PMO骨吸收与基因背景密切相关。宿主的基因背景一方面可通过基础骨量的差异影响骨吸收率[31],另一方面依赖于各种肠道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的特异性分布[39]。肠道菌群则可能通过生成不同的致病产物作用于肠道APC,进而影响骨吸收。
1.3 益生菌在PMO治疗中的作用
益生菌可显著抑制雌激素缺乏所诱导的骨吸收。Britton等[30]将12周龄Balb/c小鼠分为OVX处理组和对照处理组,并在手术1w后均给予为期4w的罗伊氏乳杆菌ATCC PTA 6475治疗,实验结果表明该益生菌可完全阻止OVX小鼠股骨和椎骨骨松质的吸收,其BV/TV值和非OVX组小鼠相近,其他相应的参数(如骨小梁厚度、骨小梁数量和骨小梁间隙)亦有改善。Li等[28]分别用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GG(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LGG)、鼠李糖乳杆菌菌毛突变株(LGG pili mutant LGG,LGGM)、大肠杆菌和市售VSL#3益生菌混合制剂(包含短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乳杆菌嗜酸、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等8种益生菌)对OVX术后的C57BL/6L小鼠灌胃4w,结果显示在OVX术后2w和4w,仅LGG组和VSL#3组的小鼠脊柱的BV/TV值均与基线一致,提示益生菌LGG和VSL#3可完全抑制OVX诱导的脊柱骨小梁的吸收,而大肠杆菌处理组与对照组小鼠BV/TV值显著降低,LGGM处理组小鼠BV/TV值亦有一定减少。Ohlsson等[27]研究表明副干酪乳酸杆菌DSM 13434和3种益生菌混合物(副干酪乳酸杆菌DSM 13434、植物乳杆菌DSM 15312和DSM 15313)均能完全抑制OVX小鼠的骨皮质吸收。
益生菌对骨组织的作用受机体全身状况影响。McCabe等[32]用罗伊氏乳杆菌ATCC PTA 6475对15周龄C57BL/6L小鼠灌胃4w,发现该益生菌可改善健康雄鼠股骨远端干骺区和腰椎的骨小梁参数,而对健康雌鼠无明显影响,提示罗伊氏乳杆菌对骨的影响与宿主雌激素水平相关。该益生菌可能通过激活雄性小鼠体内的雌激素途径影响骨代谢,而成年雌性小鼠体内的雌激素充足,因此成年雌鼠对罗伊氏乳杆菌的作用不敏感。Collins等[40]对行背部切口和未做背部切口的雌激素充足的12周龄雌性Balb/c小鼠予以罗伊氏乳杆菌 ATCC PTA 6475治疗8w,结果显示该菌株只能显著增加背部切口处理组雌鼠股骨远端的BV/TV值和骨小梁数量并降低其骨小梁间隙,而骨皮质的结构和强度无明显改变。同样,Li等[28]对雌性C57BL/6L小鼠进行OVX和假手术对照处理,随后予以4w的益生菌LGG或混合益生菌制剂VSL#3治疗,结果显示益生菌治疗的假手术组雌鼠的脊柱BV/TV值相对于基线时有明显增加。由此可见,宿主的炎症免疫状态可能是驱动益生菌对骨组织的作用的一条途径。
2 肠道菌群、雌激素和益生菌在PMO致病与治疗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机制
由肠道菌群介导、雌激素缺乏所诱发的骨吸收本质是由抗原导致的免疫反应过程。肠道菌群、肠道上皮屏障和宿主免疫系统的动态平衡与交互作用维持并促进宿主机体健康。当各种内外因素破坏肠道微生态系统与宿主的平衡状态时,肠道菌群作为抗原侵入宿主体内,引发一系列免疫反应,导致骨量与骨结构的改变。益生菌可通过作用于肠道菌群、宿主上皮屏障和免疫系统,恢复肠道微生态系统与宿主之间的稳态,抑制免疫反应,阻止骨的吸收和破坏。
2.1 肠道菌群生物多样性
宿主绝经期前,雌激素充足且机体处于健康状态,肠道菌群呈现生物多样性。有益菌为优势菌群,可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和有害物质的产生,维持肠道菌群的稳定性。绝经后机体雌激素缺乏,当肠道菌群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作用时,其组成和结构可发生变化,导致其生物多样性降低。Flores等[41]通过对25名男性、7名绝经后女性和19名未绝经女性的临床研究发现,在男性和绝经后女性中,尿总雌激素和雌激素代谢物的水平不但与粪便中微生物丰富程度和α多样性密切相关,且与粪便中梭菌类的丰度显著相关。Fuhrman等[42]对60名随机挑选的健康绝经后女性进行检查,结果显示粪便中微生物的多样性、梭菌属和杆菌属的相对丰度与尿雌激素代谢产物正相关,且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随着尿中羟基化雌激素代谢产物比例的增高而增加。雌激素水平降低致使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减少,包括梭菌属在内的厚壁菌门细菌丰度降低[12, 41-42]。厚壁菌门细菌具有免疫系统调节作用,其中梭菌属可以上调免疫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cells,Tregs)的形成和功能,后者在维持宿主免疫系统稳态方面有重要作用[43-44]。因此,雌激素缺乏可导致肠道菌群生物多样性破坏,具有免疫调节的有益菌群数量减少,条件致病菌数量增加,从而启动一系列炎症免疫反应,导致疾病。
在PMO治疗中,益生菌可通过改变宿主肠道菌群组成、恢复其多样性和稳态来抑制骨吸收。Preidis等[45]分别用单一益生菌罗伊氏乳杆菌DSM 17938和罗伊氏乳杆菌ATCC PTA 6457对远交系CD1新生小鼠进行灌胃,24h后发现两组小鼠粪便微生物组群的多样性和均匀度均有增加。罗伊氏乳杆菌可产生具有抗菌作用的罗伊氏菌素,后者通过对蛋白质和小分子进行巯基化修饰来诱导细胞中的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抑制拟杆菌属等有害菌,增加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梭菌数量[30, 46]。乳酸乳球菌G50可抑制产H2S的有害菌,增强小鼠肠道菌群的稳定性[38]。Kimoto-Nira等[47]通过用SAMP6小鼠建立老年性骨质疏松模型,研究发现益生菌乳酸乳球菌H61可抑制肠道内葡萄球菌属的数量,并改善部分老年性骨质疏松的临床症状(如皮肤溃疡和脱发),但该益生菌是否在PMO治疗中起到相同的作用尚未见相关报道。因此,益生菌可通过合成胞外物质等途径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和有害代谢物的产生,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增加肠道菌群生物多样性并抑制骨吸收。
2.2 肠道上皮屏障
肠道上皮是宿主抵抗肠道致病菌的物理屏障和第一道防线,不仅可选择性吸收水和营养物质,还能限制外源性有害抗原物质入侵宿主体内。肠道上皮屏障功能主要依赖跨细胞途径和细胞旁途径。其中细胞旁途径的基本结构为紧密连接(tight junction,TJ),其渗透性可由跨上皮电阻(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TEER)来反映,TER增加,细胞旁途径的渗透性降低[48-49]。TJ是一个由Claudins蛋白、Occludin蛋白和Zo蛋白组成的蛋白复合体结构。生理或病理因素均可影响TJ蛋白的合成与分布,改变TJ的渗透性和完整性。各种刺激因素主要通过蛋白激酶A(protein kinase A,PKA)、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蛋白激酶G(protein kinase G,PKG)、丝氨酸/苏氨酸(serine/threonine,Ser/Thr)、Rho、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磷脂酰肌醇3激酶/Akt(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Akt,PI3k/Akt)以及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MLCK)等途径对TJ蛋白磷酸化来调控[50-51]。因此,TJ的完整性和对离子、小分子的选择性渗透特性对肠道上皮的屏障功能具有重要影响。
机体雌激素水平较高时,雌激素与肠道上皮的雌激素受体作用,激活三磷酸鸟苷结合蛋白Ras和一系列胞质激酶(Raf、MEK1/2和Erk1/2),诱导胞质蛋白以及胞核内转录因子的磷酸化,上调TJ跨膜蛋白Occludin的表达,进而增强肠道上皮屏障的功能,抵抗肠道细菌及相关代谢产物侵入[50, 52-54]。绝经后,雌激素缺失导致以上效应减弱,肠道上皮细胞旁途径的渗透性增加,肠道菌的有害代谢产物作为抗原进入上皮下组织引发免疫反应。同时,免疫反应中生成的大量TNF-α和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可激活MAPK通路中的Ras-Raf-MEK1/2-Erk1/2与MLKs- MKK3/6-p38途径,下调TJ蛋白Occludin和Zo-1并增加TJ阳离子通道组成蛋白Claudin-2的合成,导致细胞旁途径的渗透性增加[55]。此外,促炎因子IL-17可以通过激活MAPK通路中的Ras-Raf-MEK1/2-Erk1/2途径来上调TJ蛋白Claudin-1的表达,增强肠道上皮功能[56]。然而IL-17对肠道上皮屏障功能的正向作用不能完全抵消TNF-α和IFN-γ对上皮屏障功能的减损,可能与TNF-α和IFN-γ是肠道菌诱发的机体免疫反应中最主要的促炎因子有关。
在PMO治疗中,益生菌可增强肠道上皮屏障的功能,减少肠道致病菌及其有害代谢产物侵入宿主。益生菌可通过改变与TJ相关的蛋白表达,调节TJ蛋白的合成与分布,降低肠道上皮屏障的渗透性。Anderson等[57]通过测量单层人克隆结肠腺癌细胞(the human colon carcinoma cell line,Caco-2)层的TEER值来评估植物乳杆菌MB452对TJ完整性的影响,发现该益生菌可增加单层结肠癌细胞间的TEER且该效应和益生菌的使用剂量有关;植物乳杆菌MB452可诱导与TJ相关的19个基因的表达改变,其中包括跨膜蛋白Occludin和附着斑蛋白Zo的基因表达上调,同时还通过影响微管蛋白和蛋白酶的基因表达来增强肠道上皮屏障功能。Qin等[58]亦通过建立Caco-2模型,证实植物乳杆菌可以通过增加Claudin-1、Occludin和Zo-1等TJ蛋白的表达并重排TJ蛋白,改善由肠侵袭性大肠杆菌诱导的Caco-2单层细胞完整性破坏和渗透性增高。Ewaschuk等[59]分别在存在或缺失TNF-α和IFN-γ因子的情况下,应用婴儿双歧杆菌培养基培养T84人上皮细胞,并且对IL-10缺乏的小鼠分别予以婴儿双歧杆菌Ussing灌流室短时处理或为期4w的婴儿双歧杆菌治疗,以观察该益生菌对结肠上皮渗透性的急速效应或长期影响。实验结果发现婴儿双歧杆菌可通过分泌多肽生物活性因子来提高磷酸化ERK水平并降低磷酸化p38水平,上调TJ蛋白Zo-1和Occludin表达,并减少Claudin-2生成,增加上皮细胞的TER,最终增强上皮屏障功能。此外,婴儿双歧杆菌可抑制由炎症因子TNF-α和IFN-γ诱导的上皮细胞TER降低,同时重排TJ蛋白。Mennigen等[60]对由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诱发急性结肠炎的小鼠给予益生菌混合物VSL#3处理,发现VSL#3可显著增加Occludin、Zo-1和Claudin-1等蛋白表达和重新分布,最终降低肠道上皮的渗透性。
益生菌还可通过影响肠道上皮细胞的生长和运动来调节上皮屏障功能。Panigrahi等[61]研究表明益生菌可改变与肠道上皮转录调控、蛋白质合成、代谢、细胞粘附、泛素化和细胞凋亡等过程相关的基因表达,影响宿主各种生理和病理过程。益生菌对肠道上皮细胞凋亡的抑制作用在Mennigen[60]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Preidis等[45]通过向远交系CD1新生小鼠分别灌食罗伊氏乳杆菌菌株DSM17938和罗伊氏乳杆菌菌株ATCC PTA 6475,结果显示罗伊氏乳杆菌DSM 17938可大幅增加小鼠肠上皮细胞的迁移、增殖和肠道上皮隐窝深度,而菌株ATCC PTA 6475只增加细胞迁移而不影响隐窝细胞增殖活性,进而改善肠道上皮的屏障功能和吸收功能。Ardita等[62]进一步揭示了益生菌影响肠道上皮增殖的作用机制。LGG通过SPAC菌毛蛋白亚基促进LGG对肠道上皮的直接黏附、诱导肠道上皮表达生理水平的ROS,后者可作为第二信使激活细胞外信号并调节细胞内ERK/MAPK信号通路,最终诱导肠道上皮细胞的增殖。Jones等[63]研究发现鼠或果蝇肠内植物乳杆菌的定植可诱导NADPH氧化酶1(NADPH oxidase 1,NOX1)依赖性的ROS生成和肠道上皮细胞增殖,对维持肠稳态过程起着关键作用。此外,益生菌可阻止肠道致病菌及相关产物对肠道上皮的毒性作用。Han等[64]发现双歧杆菌能减少肠道上皮细胞内自噬相关蛋白的水平和分布,进而有效抑制革兰氏阴性菌内毒素(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肠道上皮细胞的自噬,改善和维持肠道上皮的屏障功能。
2.3 宿主免疫反应
免疫系统是宿主抵抗肠道致病菌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PMO病理过程和治疗干预的最后环节。肠道上皮下固有层的APC可分为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和巨噬细胞[39]。所有巨噬细胞和DC均能够诱导Foxp3+Tregs的分化,且巨噬细胞的诱导更高效[39]。相比之下,只有部分DC能有效诱导Th17细胞的分化[39]。Treg细胞是一组能抑制Th1、Th2和Th17分化和功能的CD4+T细胞[65],可分泌抗炎因子IL-4、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抑制单核细胞分化为破骨细胞[66-69]。因此,Treg细胞在维持免疫系统稳态和避免骨吸收中起着重要作用。Th17细胞具有显著的促破骨细胞分化能力,可分泌高水平的IL-17、RANKL和TNF-α[70],参与PMO骨吸收。
肠道菌群多样性与较高的雌激素水平均有助于维持机体免疫系统的稳态。Atarashi等[43]在小鼠肠道菌群中进行梭菌菌株的定植,发现梭菌属能促进Treg细胞的聚集、增加Treg细胞的数量并增强其功能,形成一个富含TGF-β的环境,进而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雌激素则主要通过下调机体炎症免疫应答,影响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两条途径来抑制骨吸收[71]。雌激素可直接作用于破骨细胞表面的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并激活促凋亡的Fas/FasL系统,诱导成熟破骨细胞凋亡[72-75];雌激素还可激活Treg细胞并增加TGF-β1的生成,或通过ER抑制Th17细胞的分化并减少TNF-α和RANKL的生成,间接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66-67,69,76-78]。此外,雌激素可通过激活胞外信号调节激酶转导途径,阻止成骨细胞和骨细胞凋亡[75,79]。
绝经后雌激素缺失和肠道有益菌减少可导致以上骨保护效应减弱。有害抗原经肠道上皮进入宿主体内并引发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首先,雌激素缺乏可增强DC和巨噬细胞的抗原呈递功能。雌激素缺失诱导骨髓细胞内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堆积[80-81],后者增强DC的功能并激活CD4+T细胞,随即增加的IFN-γ通过上调MHCII的生成增强骨髓巨噬细胞(bone marrow macrophage,BMM)功能[82-86]。雌激素缺乏还可通过上调CD80的表达增加骨髓中DC数量并增强其功能[83]。骨髓DC和BMM功能的增强可直接上调包括Th17在内的CD4+T细胞的数量和活性[65,87]。除抗原呈递的直接激活作用外,雌激素缺乏诱导的IFN-γ、IL-7增加和TGF-β降低也可间接导致部分骨髓T细胞的活化与增殖[65, 87-88],产生大量TNF-α,诱导PMO骨吸收[78,89-92]。TNF-α在诱导PMO骨吸收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可通过CD40L和DLK1/FA-1诱导RANKL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M-CSF)的生成,并下调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OPG)[65, 83, 93]。TNF-α还可直接作用于破骨细胞前体细胞并促进其分化成熟[94],并可通过受体p55来增强BMM对M-CSF和RANKL诱导的反应,间接促进BMM分化形成破骨细胞[78]。雌激素缺失还可上调成骨细胞表面Act1适配蛋白的表达并激活IL-17信号通路,最终诱导破骨细胞的形成[95- 96]。因此,包括Th17细胞在内的CD4+T细胞和TNF-α等促破骨细胞生成因子是肠道菌介导的PMO骨吸收的关键因素。
在PMO治疗中,益生菌可通过调节机体对肠道菌群的免疫反应,抑制骨吸收。益生菌可通过分泌小分子物质调节宿主免疫反应过程。益生菌可通过发酵底物合成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GPR41和GPR43是SCFAs的受体,其中GPR43主要分布在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等免疫细胞中[97]。SCFAs特别是丁酸可通过与GPR43受体结合,特异性抑制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生成,抑制由LPS诱导的TNF-α、INF-γ和IL-12等细胞因子合成,同时上调抗炎因子TGF-β1、IL-4和IL-10的表达,最终激活CD4+Treg,下调炎症免疫反应[27, 97-101]。此外,罗伊氏乳杆菌6475可转化膳食中L-组氨酸生成组胺,通过H2受体阻止MEK1/2和下游ERK1/2通路的激活,进一步抑制单核细胞生成TNF-α[102]。乳杆菌属还可通过表达具有相关DNA基序抑制作用的分子配体,阻止炎症过程中DC的功能,并促进Treg细胞的转化[103]。
3 展望
PMO骨吸收是雌激素、肠道菌群和机体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雌激素缺失诱导肠道菌群失调、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减弱和免疫系统反应性增强,导致肠道致病菌有害代谢物可以通过肠道上皮屏障进入机体,进一步引发CD4+T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生成大量以TNF-α为主的促破骨细胞生成因子,最终促进破骨细胞的激活和骨吸收。其中,肠道菌群是PMO致病过程中的始发因素。而益生菌可从调节肠道菌群、恢复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和稳定机体免疫系统等途径来抑制骨吸收和避免骨组织结构的破坏。
尽管目前已有部分研究深入探讨了PMO致病过程中的免疫应答机制,有关肠道菌群介导的免疫反应上游调控过程和相关的基因仍不清楚,雌激素缺失诱导肠道菌生物多样性改变的分子机制亟待深入研究。IFN-γ和IL-7在促进骨髓DC和BMM抗原呈递功能增强方面的作用正逐渐受到关注,其直接影响了随后的T细胞的激活与破骨细胞的分化。此外,尽管现有研究显示益生菌具有众多调节功能,不同益生菌对宿主的影响是否具有个体差异性或种属特异性仍待进一步研究。同时,益生菌在PMO治疗中的生物安全性、安全剂量、最适剂量和剂型的确定也亟需相应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中研究验证。将肠道菌群作为PMO致病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有望全面揭示PMO骨吸收的分子机制,为PMO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靶点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