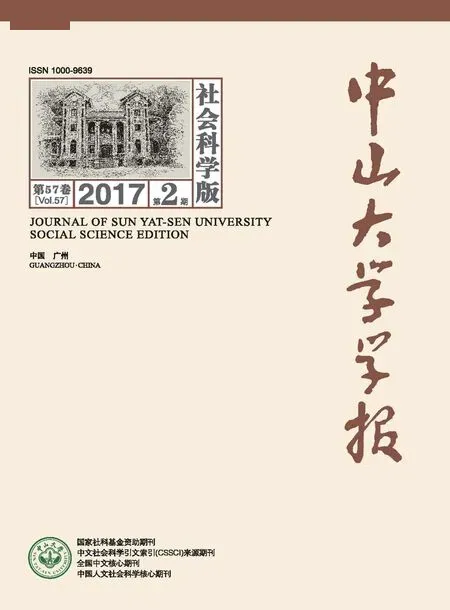井上圆了与蔡元培的妖怪学*
——近代中日的启蒙与反启蒙
廖 钦 彬
井上圆了与蔡元培的妖怪学*
——近代中日的启蒙与反启蒙
廖 钦 彬
近代中日两国教育家、思想家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在接收与消化西方知识体系与世界观后,分别以妖怪学和美学提倡本国的启蒙教育。在此过程中,两人不仅呈现出各自的理性主义面向,甚至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面向,因此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色彩。井上奠基于“相即的逻辑”或“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理论之妖怪学,成了两者沟通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判准。妖怪学有助于分判井上以宗教的方式(自、他力)、蔡元培以美学的方式(直觉、直观)来沟通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鸿沟。井上与蔡元培在疏通这两个世界的过程中,虽然分别呈现出各自在理念上的连续性与在实践方法上的断裂性,但这恰好显示出近代中日面对西方时所呈现的启蒙与反启蒙互具的辩证面貌。
妖怪学; 美学; 启蒙; 反启蒙; 相即的逻辑; 宗教
一、前言
日本明治政府1868年颁布“祭政一致”“神祇官复兴”及“神佛分离令”后,神道的国教化及神道主义的国民教化如火如荼地展开。传统佛教随之受到打压,甚至遭遇到民间“废佛毁释”运动的命运。净土真宗进入明治期后,亦面临存亡问题。
井上圆了(Inoue Enryō,1858—1919)在净土真宗的近代化方针下,接受东京大学的近代化教育,并以哲学为出发点,重新看待传统佛教及其教义。井上与教团分道扬镳后,前半期设立哲学馆,致力于教育的近代化、哲学的弘扬、妖怪学科的建立、传统宗教教义的理性化(去魅)以及宗教改革等;后半期则将心力放在海内外的演讲。妖怪学是他将哲学(理性主义)推广到民间各地的产物。
妖怪学首先详述流传于民间的妖怪传说以及民间所谓的妖怪现象,尔后再用哲学中的逻辑学(归纳与演绎法)或自然、社会科学的方式(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来说明坊间所谓妖怪不过是有违逻辑、不符自然或社会科学法则的现象。针对这些违背某种规定、法则或脱轨的现象,井上给予各种称呼,例如迷信、幻像、妄念、假相,甚至是伪怪、假怪。他试图透过此种讲述的方式,来破除一般民众的迷信与妄想*井上认为除了正规(正则)教育外,还要有变规(变则)教育,并指出:“今日之教育,其区域甚狭,仅以学校教育为目的,若广对社会,就种种妖怪之事实,而为之说明,非别设一科专门之学不能,是变式学之所以对正式而起也。”([日]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录(总论)》,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40页)相对于正规教育的常态学,妖怪学则是一种变态学,属于变则教育。。
曾将井上的妖怪学著作《妖怪学讲义》(1894)译介给中国知识界的蔡元培(1868—1940)在教化及启蒙中国人民的思想工作上,和井上比较起来,显然有多遑不让的硕然成果。他处在中国新旧交替(清末民初)的时代,更能体会出未开化与开化、蒙昧与启蒙交杂的文明景象。
套用井上妖怪学的说法,对蔡元培而言,民国初期以宗教(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孔教)救国的思想或运动若是一种迷信或假怪的话,那么所谓的正信或真怪*“真怪”在井上的语境里有以下诸概念:“真怪本境”“真际”“本体”“绝对无限之体”“妙意识之关门”“平等无差别之境”“无限之神光”“成佛”“悟道”“涅槃”“真如”“理想”等。井上认为任何相对性的概念,都无法形容那样的世界。那些称谓,在每个学问领域或人生、价值观当中,自然会有所不同。他认为:“要之,其名虽异,其体皆同。”([日]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第210页)。则是一种无法具名的本体或实体*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说道:提到实体虽不可名,然既是一种观念,就必须给个名称。因此他举出道、太极、神、黑暗之意识、无识之意志,并强调:“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33页)。针对清末民初种种迷信或假怪的出现,蔡元培和井上一样,皆以西方的哲学与科学来进行具体的批判,甚至对现象世界给予消极的评价。
蔡元培的人生观、教育观、世界观可说是日本与西方启蒙的缩影。所谓的实体世界(理想世界),对他而言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事实上,这关系到他自身的教育理念,亦即和德、智、体、美四育中的美育有关。
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井上提出妖怪学并主张从庶民、底层无知人民来进行近代教育的做法,蔡元培则从高等教育机构出发,主张近代教育不可缺乏美学的熏陶与涵养。前者透过低俗、不可思议、迷信之说,由下而上,寻求真怪(理想境地);后者则透过向知识分子讲述美学、美育、美感、艺术等,由具美感的文化层面,来追寻美的普遍境界。前者看似低俗,后者则显得高雅难攀*张晓唯的《蔡元培评传》不时有如此的评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蔡元培大力提倡美学及美育,实有格格不入之感。这透露出提出和现实世界相距甚远的理想或理念,通常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正是蔡元培的反启蒙特质。。但就两者藉由追求理想世界,试图重探现实、现象世界(假境)与本体、真实世界(真境)之间关系的态度,可知两者走的道路并无二致*王青的《蔡元培与井上圆了的宗教思想之比较研究》(原载《国际井上圆了研究》2013年第1号)一文比较蔡元培与井上圆了对宗教所采取的态度,一方面强调前者最后以美学替代宗教来实施教育,符合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秉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排除宗教的迷信以救国);另一方面主张后者为了护国而改良宗教,并藉此来说明两者对宗教的消极与积极之态度。此论强调两者在思想上的断裂性,笔者则从哲学方法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两者思想的断裂性与连续性,藉以突出井上与蔡元培的启蒙与反启蒙面貌。。如后所述,无论是井上寻求真怪(理想境地)还是蔡元培追寻美的普遍境界,都意味着一种东方式的反启蒙立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者虽背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名号,却同时高举着反启蒙、反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旗帜。
二、井上的宗教哲学
(一)“相即的逻辑”
井上哲学形成得非常早,在《哲学一夕话》(1887)中可窥见其形迹。该书序言透过对物、心、神与真理的理解,明确地提出自身哲学的立场*⑥ [日]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1卷,东京:东洋大学,1987年,第34,48页。。在第三篇《论真理的性质》中,井上表示哲学不外乎是判定物、心、神三者关系的学问,若要厘清此关系必须设立真理的标准,而界定此标准又以外部物界的经验、内部心界的思想、此两界的统合以及物心以外的神为主。但井上认为此四种基准,皆有偏颇,应取物心、内外的中道⑥。他主张无论是物、心还是神,都可成为真理的标准。物、心、神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此意味着差别、诸多、相对门与平等、同一、绝对门的同体、相即不离关系*菊地章太在《妖怪学之祖井上圆了》(第38—43页)中指出,此“相即的逻辑”来自其师原坦山(Hara Tanzan,1819—1892)思考佛教经典的理论(真如与现象互具)。。这正是井上的哲学立场*[日]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1卷,第81—84页。。
此种“一体两面、相即不离”的理论在《佛教活论序论》(1887)中,透过井上的宗教改革论不断被凸显出来。井上在此道明自己爱真理、护国、兴教及排耶稣教的使命。护国之本在于复兴佛教,复教之本在于排耶稣教。在排耶稣教的过程中,井上提出一种情与智、想像与理性、非真理与真理并重(一体两面)的宗教新形态。他认为耶稣教属于情、想像、非真理的宗教,佛教则兼具前后者,有成为普遍宗教的资格。
井上以大小二乘、顿渐二类、一乘三乘、显教密教、圣道净土等概念将佛教做出大致的梳理与区分。由于人有圣贤、凡愚之分,其成佛之道也随之而异,圣道门与净土门因应而生,两者分别代表自力难行教(华严、天台、俱舍、唯识)与他力易行教(净土宗、净土真宗),因此佛教包含哲学与宗教两个层面*④⑤⑥ [日]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3卷,第357—358,360,362—372,389页。。井上称圣道门是哲学、智力的宗教,净土门是想像、情感的宗教④。
井上对上述宗派的判教,在理论上以天台的“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或“圆融相即”的法门及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与绝对不离说)为归依⑤,在情感上则以净土宗、真宗的他力信仰为归依,并说道:“圣道与净土也同样带有表里两面的关系。”“释迦的本意在于保持圣道与净土的权衡,、期望智力与情感的两全。”⑥
综上可知,井上的“相即的逻辑”不仅是处理哲学问题的思想根源,还是他在判教时的理论基础。井上主张情与智、想像与理性、非真理与真理相即的宗教新形态,藉以爱民、护国、贡献世界。我们可以察知他的“相即的逻辑”是东方宗教(天台的空、假、中理论)与西方哲学(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偶然相遇下的呈现。
(二)《真宗哲学序论》中的自力与他力
井上出版《佛教活论本论》第一编《破邪活论》(1887)与第二编《显正活论》(1890)批判耶稣教、显现佛教真理,接着又陆续出版了《真宗哲学序论》(1892)、《禅宗哲学序论》(1893)、《日宗哲学序论》(1895)、《日本佛教》(1912)等。《真宗哲学序论》是补充《显正活论》中真宗论述不足的著作。他在序言中认为真宗是最完备的宗教,它作为天台宗(圣道门)的反动,虽是想像、情感、超越理智的宗教,从哲学来看,却是“佛教彻头彻尾的哲理运用”*⑧⑨⑩ [日]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6卷,第181,192—199,201,204—205页。。此种既想像又哲学、既情感又智力、既超越理智又理智的论调,是“相即的逻辑”的进一步发挥。
井上在《真宗哲学序论》的第一段,回应了“真宗是没有理论、下等愚民的宗教”的评论。他认为真宗虽带情感的性质,但只不过是覆盖在智力骨髓上的皮肉而已,基于爱理、护国的心理,有必要将理智与情感兼具的真宗的真实面貌显现出来。其论证的顺序为:其一,哲学原理论;其二,佛教原理论;其三,真宗原理论⑧。
在《哲学原理论》中,井上认为古今东西哲学的难题在于如何统一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思想与感觉、有形与无形、本体与现象、绝对与相对、可知与不可知、有限与无限、单一与杂多、平等与差别等的对立。面对这种难题,井上主张真理无二致、一体的真理具有两样道理,并提出“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真理之说法⑨。
“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真理,不仅能处理哲学上的难题,还能统合古今的宗教论争。自古以来宗教分成依道理、可考究的自然宗教与道理以外、不可考究的启示宗教。前者属智力、道理的宗教,后者属情感、想像的宗教。此两种的统合才是完整的宗教⑩。此主张正显示出他自身的判教轨迹。
在《佛教原理论》中,井上将佛教分成道理或理论宗(如俱舍、法相、天台等)与实际宗(如净土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并认为惟有“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真理才能揉合佛教各派间的对立。真宗如何是理论与实际、哲学与想像兼具的最完美宗教?在《真宗原理论》中,井上叙述属净土他力的真宗与属圣道自力的天台之间的关系:“净土门犹如长江大河,远以天台中道的高岭为源头,经有、空二门的幽谷,流动注入旷野、平原,所有村落没有不受其恩泽的。特别是到了真宗,无论是愚夫愚妇没有不沐浴在其慈水之中的。”*[日]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6卷,第213页。此处透露井上想揉合着重在自力修行的难行道与着重在他力信仰的易行道,因为两者的一脉相通之处便在于“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真理。
若回顾以上内容可知,井上期望的宗教新形态透过“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真理,被置放在他对真宗原理的诠释上。自力与他力在井上的真宗判教上,显然是理性诠释下的宗教哲学概念、近代化与合理化的标志。自力与他力是佛教(真宗)近代化、合理化、普遍化的标杆。
这种自、他力的看法以及上述“相即的逻辑”与“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真理等,在井上妖怪学论著当中,亦可见其踪影。
三、妖怪学的真相
井上在《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的《绪言》中明确表示,妖怪学的目的在于“研究妖怪之为何,并为之说明”以及“扫假怪、开真怪”。此种目的和佛教的“转迷开悟”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妖怪学是要破除种种迷信、妄想、假相、幻像等,达到“真怪本境”“真际”“本体”“绝对无限之体”“妙意识之关门”“平等无差别之境”“无限之神光”“成佛”“悟道”“涅槃”“真如”“理想”等的学问。以下为井上的妖怪分类全图*③ [日]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第250,251—252页。。
┃伪怪(人为的妖怪)┃个人的、社会的妖怪
┃虚怪┃误怪(偶然的妖怪)┃客观的、主观的妖怪
妖怪
=======================================
┃实怪┃假怪(自然的妖怪)┃物怪(物理的妖怪) ┃有机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
┃无机的┃植物、动物、人类
┃心怪(心理的妖怪) ┃变觉、变情、变智、变意
┃真怪(超理的妖怪) ┃秘怪 ┃灵怪、神怪
┃理怪
┃妙怪
据上可知,井上将妖怪分成虚怪与实怪两大类,又将虚怪分成伪怪与误怪,实怪分成伪怪与真怪。所谓伪怪,便是由人的意志打造出来的妖怪。在个人方面,例如因为奇情、利己、假话、说谎等而产生。在社会方面,例如因政治的权谋术数、战争时的谋略等而产生。误怪则是将偶然发生的事相误认为妖怪。至于假怪,则是非人为、非偶然,是自然发生的妖怪。井上又将此假怪分成物理的妖怪和心理的妖怪。关于前者破除的方式,例如用物理或化学等科学方式,可证明被称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其实是一种物理或化学现象。关于后者破除的方式,比如精神疾病患者说出天马行空的话,透过心理学或精神病理学的方式,可证明那只是一种内部意识产生异化的现象。所谓真怪,是指绝对无限之体。那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存在,无法具名③。
井上在说明妖怪的种类后,接着将伪怪、假怪、真怪对应到人的世界、有限相对世界、无限绝对世界,并说:“就其关系于真怪而开示其理于人又能讲体达之道者,即宗教也。次研究假怪之道理而明之者,一般之学科也。而关于伪怪而成立者,人情、风俗、政事等也。故研究伪怪者,得知社会人情之奇智妙用;研究假怪者,得晓万有自然之奇变妙化;研究真怪者,得悟神佛之奇相妙体。”*②③ [日]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第253,210,246—247页。三种妖怪及其世界的阐明皆不可缺,而且去伪怪、拂假怪、开真怪是妖怪学的最大目的。
井上针对相对世界的虚与实之妖怪,亦即相对有限的妖怪,设置了绝对世界的真怪,亦即绝对无限的妖怪。笔者认为井上建构妖怪学所运用的,正是“相即的逻辑”与“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理论。进一步来说,真怪不离假怪、假怪不离真怪,真、假怪处于一种“二而一、一而二”的辩证关系当中。关于此点,在井上以下的说明当中,可得到论证:“虽然,吾人之心象,虽现境幻境,而其内部具心体之世界,势不得不联络心体而说心象。真怪非离假怪而别存,存于假怪之里面、心象之内部者,现境一变而无识界,无识一变而幻境,幻境一变而于兹开真际(真妖:笔者注)。”②
如前所述,井上的“相即的逻辑”或“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理论,在他对自、他力的诠释中,被表露无遗。事实上,井上的自、他力论述,亦可在妖怪学中见其踪影。何以自、他力概念会和妖怪学扯上关系?这是因为妖怪学的目的在于“扫假怪、开真怪”“转迷开悟”,而自力与他力的诠释正是如何达到该目的的方法。换言之,井上的自、他力论述牵涉如何“扫假怪、开真怪”“转迷开悟”的问题。
关于自、他力与妖怪学的关系,井上说道:
佛教有自力、他力之二道,吾人之力,得开示真怪,是谓自力;若吾人之力不能达之,而由真怪本境启示于吾人之上,所谓他力也。此二论者,其实同一。盖以吾人之心,解为相对性之心象,而非绝对性之心体。则于吾心之上,发真怪之光者,不可为吾人之力。若反之,而以吾人之心,纵为相对性心象,然此心象者,本绝对性之一部分,自于吾人之心中,含有绝对之真怪,所以体达之者,亦不外吾人之力。故在于佛教唱自力之宗旨者,说我心本体即佛,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吾人之感应悟道,在开现本来我心象中所包有之心体,是自力及他力之所由分,又同一宗教所以存此二说也。虽然,更溯二说之本源而推穷之,其理一而无二致,可知。③
井上这种心象与心体的不即与不离之说法,显露出以他力或自力来“扫假怪、开真怪”“转迷开悟”的面向。事实上,就他看来,自力与他力处于“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因此无论是“扫假怪”或“开真怪”、“转迷”或“开悟”都不能没有自、他力的介入。若是如此,则假怪必不能脱离真怪,反之亦然。
我们若对蔡元培在《哲学大纲》中的《宗教思想》(1915)、《一九〇〇年以来的教育之进步》(1915)、《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1916)、《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以美育代宗教》(1930)、《战后之中国教育问题》(1919)等文章的宗教观进行检视,便会发现他并非无宗教主义者。他所批判的宗教,大多数是西方宗教没落与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抬头这种情况下的宗教。
也就是说,标志着教授西方近代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中国新教育,必须避免倒回西方中世的宗教垄断一切的时代,必须保持每个学科的独立运作。这也是直接促使蔡元培对清末明初“揭示孔教以救国”的宗教运动表示否认态度的主要原因。对蔡元培来说,世界必会遵循进化论这个轨道,无止尽地发展下去,不再走回头路。但笔者认为,这不会让蔡元培变成绝对理性主义者以及无宗教主义者。
蔡元培积极否认西方基督宗教与中国孔教(亦即排除假怪)的理由,在于一方面要在中国推展西方启蒙或理性主义下的新教育,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地肯定西方美学(甚至是东西美学)的普遍境地(亦即开显真怪)。
四、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中国的教育及知识界,从清朝到民国,历经巨大的转变。在此背景下,蔡元培始终坚持教育的独立性。他认为理想的教育应兼顾现实与理想,而不是只顾其中一方。以下就其教育理念及美育观进行探讨。
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立即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他主张中国的教育不应将过去专制时代隶属于政治的“军国民教育”以及“实利主义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共和时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公民道德的教育。所谓道德教育,是以法国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博爱)为核心的教育。蔡元培随即举出孔孟思想中的义、恕、仁来对应,并认为此种公民教育还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其最终目标,应该是“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亦即“现世的幸福”。他更进一步说明,只专注眼前或现世的幸福还不能算是最大的幸福,因为:“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况鹄的不止于此者乎?”*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2—133,133,134页。据此可知,蔡元培的新教育理念不能缺乏超越现世或形而上的观念。
关于现世与理想,蔡元培说:“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然则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区别何在耶?曰: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之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故实体世界者,不可名言者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2—133,133,134页。
这里道出教育不可脱离相对的现象世界与绝对的实体世界。接着,他又说道:“现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这让我们联想到井上的宗教哲学与妖怪学中的“相即的逻辑”或“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理论。
事实上,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景象,分别是井上妖怪学中的假怪与真怪,只是论述的方式不同而已。用井上的话来说,蔡元培所采取的是正规教育、常态学的态度。此处所言的宗教,显然不是假怪,而是真怪。这和蔡元培在往后的教育主张或美学论述中所欲排除的西方基督教及孔教(假怪),是截然不同的。
如何打破偏颇于政治、现世幸福、现象世界的教育,让出世间的幸福、实体世界的教育显现出来?如何才能达到这两个世界的统合呢?蔡元培认为:“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而且必须“合现象世界各别之意识为浑同,而得与实体吻合焉”*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2—133,133,134页。。对于这种统合现象与实体的教育,他称为“世界观教育”。他甚至援引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美学,主张“美感之教育”能沟通相对的现象世界与绝对的实体世界,并强调以军国民、实利、德育为主的政治教育与以世界观、美育为核心的超越教育皆不可偏废。笔者认为这恰好显示出蔡元培教育理念中的启蒙与反启蒙立场。
此处所言五种教育皆不可偏,和井上的“相即的逻辑”或“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理论有关,而“美感之教育”可对照在井上的自、他力论述上。因为自、他力的宗教实践,在蔡元培的语境里则是直观的美学实践。蔡元培站在正规教育、常态学的立场上,以美学统合了相对的现象世界与绝对的实体世界。这是井上与蔡元培的非连续性关系。这和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听到或接触的课程内容有关,而两者的连续性则在于“相即的逻辑”或“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理论之运用。
关于沟通现象与实体的美感,蔡元培的《美学的进化》(1921)有详细说明。他说:“他(康德:笔者注)著《纯粹理性批评》,评定人类和知识的性质,又著《实践理性批评》,评定人类意志的性质。前的说现象界的必然性,后的说本体界的自由性。这两种性质怎么能调和呢?依康德见解,人类的感情是有普遍的自由性,有结合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作用。由快不快的感情起美不美的判断,所以他又著《判断力批评》一书……美论上说明美的快感是超脱的,与呵末同。他说官能上适与不适,实用上良与不良,道德上善与不善,都是用一个目标作标准。美感是没有目的,不过主观上认为有合目的性,所以超脱。因为超脱,与个人的利害没有关系,所以普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1—22页。
美感是沟通现象界的必然性与本体界的自由性之桥梁,因它没有目的与利害关系,所以具有超脱性与普遍性。显然的,蔡元培并不是用井上的宗教方式,而是用康德的美学方式,来沟通现世的教育与出世间的教育。我们现今看到的所有教育,只能停留在相对有限的现象世界。针对这种专门教育,蔡元培认为应该以“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4,379页。的态度来对待。
蔡元培的新教育理念,虽然重视西方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但亦不忘中国传统,甚至利用西方的方法论来重新发挥、创造中国的传统。他的《中国伦理学史》(1910)便是发挥西方治学精神的产物。此外,他还期望透过具有超越、普遍性的美学,来弥补现世教育可能会出现的弊害,进而打造出一种兼具现世与超世面向的教育。用妖怪学的话语来说,此便是假怪与真怪并存的教育,同时是笔者认为的启蒙与反启蒙之教育。那么,井上所追求的理想宗教(真妖),是否就从蔡元培的新教育思想中消失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五、非宗教思维与妖怪学
蔡元培在《中国的文艺中兴》(1923)中说明了文艺复兴始于中国18世纪的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因为这些学问已具有欧洲的科学精神;而真正的复兴则始于清末民初的海外留学生所带来的新知识与新世界观。这种以近代欧美及日本为模式,来重新看待中国传统的做法,在其论著中随处可见。近代欧美的知识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假怪)中解放出来后,得以自由伸展。对蔡元培而言,这样的世界观才是中国必须学习的。因此将孔子思想宗教化后,再藉由孔教(宗教、假怪)来统筹中国的新教育,可说是违背了进化论的原则*《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1917)谈到信仰自由时,亦说道:西方的学术、政治、人的品行、风俗会优于中国,并不是因为基督宗教的关系,而是因为其教育普及、科学发达、法律完备的缘故。其中还批判高举孔教以救国的想法(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页)。事实上,将孔子思想宗教化,已有康有为的失败先例,对蔡元培而言,已不足为取。但这并不代表蔡元培摒弃了孔子思想。。
蔡元培在《哲学大纲》的《宗教思想》里讽刺:“宗教规定一切道德,其所谓的创造天地及万物说或有关自然定律的说法,随人类智慧(科学)的进步,无不一一被揭穿。”这里说明了知识主导的权力,已在产生位移。宗教所说的不合理性、不可思议性,在现今人类面前,显然已无法被掩盖(此即妖怪学中的假怪)。他还批评:“然则最后之宗教,其所含者,仅有玄学中最高之主旨,所谓超生死而绝经验者,其研究一方面,谓之玄学;其信仰一方面,则谓之宗教云尔。”*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4,379页。这里更是道出只谈非现实、出世间的一切,事实上只是另外一种假怪,因为真正的妖怪无法脱离假怪。也就是说,真正或终极的宗教,应该是一种形而上与形而下互具、现世与出世不离、生死与超生死无间、经验与绝经验相待、假怪即真怪的状态。
蔡元培在《一九〇〇年以来的教育之进步》中提到法国的教育已经切割宗教,普通教育已经开始脱离宗教,而教会学校显然已经和国立学校无法相抗衡。他接着将话题衔接到中国,认为孔子之道(儒家思想)和天主教虽然不同,但在往昔的科举制度下,俨然已带有宗教性质,尔后随着科举的废除,才逐渐淡出教育界。这里并非蔡元培的排孔儒主张,相反地我们应该理解为被宗教化、妖怪化、蒙昧化的孔道、儒家思想(妖怪),应该透过现代的科学精神来重新被打造。
关于孔教(儒教)*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称儒家思想为儒教,主要原因在于儒家思想在其发展史、政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上被宗教化、妖怪化(高书平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73、93、101页)。的问题,蔡元培的《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有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认为孔子和宗教不相干,孔子不废几近宗教的礼制,是因为顺从风俗的缘故。世间叫嚷要将孔教作为国教,亦是他要批评的。既无孔教,如何成为国教?更何况国家和宗教,亦是相互抵触的二物。此演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宗教在民智浅陋、半开化人的时代,是人类的主宰及价值观的所有来源。然民智开化后,宗教的所有言论或教义,就逐渐地被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所攻破。人的信仰心,也因此渐渐转移到哲学家的主张上。然这里所说的宗教,显然是妖怪学中的假怪。
最被视为蔡元培反宗教或非宗教的文章,则是《非宗教运动》(1922)与《以美育代宗教》。仔细一读,仍可判别出蔡元培批判的是妖怪学中的假怪。比如,蔡元培说道:“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79页。对他而言,终极的宗教是转迷开悟、排假怪开真怪的宗教。同样,蔡元培排斥当时腐败的基督教,目的在于民众开悟。至于信教自由的问题,他认为可信、也可不信,因为这是每个人的自由。这里并无全面或彻底否定宗教的意思,只是蔡元培用美学来替代而已。说到底,美学若没有警觉自己有一天也会和陈腐的宗教一样,变成堕落或暴力的美学的话,那么美学也只是假怪而已。蔡元培所追求的美学因带有反启蒙的性格(亦即真怪性格),因此才能不断地否定任何属于假怪的现实存在物。
至于《以美育代宗教》的铺陈,亦和上述内容雷同,大多是讲述民智开化,宗教的知识权被解放在各个学科后,宗教的存在必要性就会消失。蔡元培的三个主张亦即:“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501页。其中的宗教只是假怪,因为真正的宗教和美学(美感)不会是对立的。须留意的是,美育也有可能堕落到强制的、保守的、有界的境地。美育必须具有反启蒙(真怪)的性格,才能算是真正的美育。
六、结论
本文目的不是要传达蔡元培亦有妖怪学或者也讲述妖怪学,而是想透过井上的妖怪学方法及其理念,来检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以及其美学观与宗教观的关系。从两者的时代背景之差异,可观察出两者沟通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的方法之不同。相对于井上以宗教的方式(自、他力),蔡元培则以美学的方式(直觉、直观)来处理。然如本文所示,两者的路径虽然不同,但两者所追求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亦即追求现实与理念不即不离(或者是启蒙与反启蒙不即不离)的中庸之道。
关于蔡元培的非宗教立场,若对照到井上的妖怪学,可知蔡元培并非全面否认宗教。他否认的是脱离中庸之道的宗教,用妖怪学的语境来说便是假怪。若厘清这点,便可了解蔡元培批判被宗教化的孔子思想(假怪),同时又用西方近代的治学理念来重新评价孔子思想这种两极的态度。甚至可以看到,井上与蔡元培两者思想的关连性,亦即坚守“相即的逻辑”或“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理论的关连性以及两者思想的断裂性,也就是分别透过宗教实践与美学实践来沟通现实与理念的断裂性。毋庸置疑,这里同时透露出近代中国与日本面对西方所呈现的两种不同的启蒙与反启蒙互具的辩证面貌。
本文透过比较井上圆了与蔡元培的思想,目的正在于探讨此处所说的关连性与断裂性。此二者分别代表了理论的普遍性与恒常性以及历史现实的特殊性与流动性。就前者与后者互具、不即不离的原则来说,显然谈论历史现实的种种主观现象,不能缺乏理论的种种客观思考,反之亦然。这种结果正好显示出探讨东亚人文学互动时可以参考的一种指标。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赵洪艳】
2016—03—16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三大建设”项目
廖钦彬,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广州510275)。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