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下)
张荣生
钱瑗和钱钟书的先后离去,对杨绛来说,不止是人天两隔的永别,而是失去了自己生命的大部分,三人世界如今只剩下了杨绛自己,何况还是个八十七岁的老人,杨绛留在人世间,决心打扫现场,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
她的责任太多了,钱钟书留下那么多的手稿、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等她整理和处理,事情够繁重也够琐碎,她得付出很大的脑力和体力才能胜任。此刻她已身心交瘁,第一得为她那颗伤痛的心找到一个可以逃避的庇护所,心有所属,她才喘歇得一口气来。
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
“钱钟书藏书不多,我在家藏的几柜子书里寻寻觅觅,找可以安慰的书,可以指导我的书,尤其要找一本可以逃避悲伤的书,一头扎进书里,把自己忘掉。忘掉自己,就是逃避。
她读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中文的书,读了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沉思录》Epictetus(爱比克泰德)的《金玉良言》《柏拉图对话录》,最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好多遍,决意翻译此书。
《斐多篇》不到100页,描绘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在雅典监狱与门徒的对话,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所谓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所谓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立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肉体留在世上我们叫尸体,灵魂虽然看不见,它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生存,天鹅临死的时候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因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苏格拉底在《斐多篇》里清晰的区分了在喝过毒芹酒变成一具尸体的自我与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是不同的,苏格拉底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宁可饮毒酒而死。
杨绛译注的《斐多》2000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相继出版了繁体字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又出版了汉英对照本。辽宁版《斐多》首印一万册,很快脱销。北京二外一位年轻的英语教授跑了很多书店才买到一本。
处理钟书的大量笔记
自从钱钟书去世,很多朋友都担心杨绛的健康,怕她过度哀伤而影响身体。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莫芝宜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与钱、杨结识以来,一直保持亲密的友谊,她所译的《围城》,是唯一能让读者笑出声来的外语译本,莫芝宜佳也是最早研究钱钟书《管锥篇》的外国学者。1999年暑假,她专程来北京探望杨绛,当时杨绛还在大连,她追到大连与杨绛同住了几日,又一起飞回北京。莫芝宜佳精通希腊文,熟悉柏拉图,见杨绛正在翻译《斐多篇》,欣然为中文译本作序。莫芝宜佳理解杨绛是凭借全神贯注的工作压抑自己的悲痛,工作不会停顿下来,便问杨绛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杨绛回答:“打扫现场,最重要的是处理钱钟书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留下的大量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杨绛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处理有困难。莫芝宜佳看了钱钟书笔记目录和部分内容,这位懂汉、英、德、意、希腊、拉丁多种文字的教授又惊又喜,“馋”得不得了,自告奋勇编排全部外文笔记,为此第二年暑假又来北京,把钱钟书手稿外文笔记全部整理一遍,写出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详细目录。
除了外文笔记,还有大量中文及中英文相杂的笔记等待杨绛一页一页辨认、收拾,这成为杨绛晚年最大的动力和压力,她每天把手稿摊一桌子,一点一点地粘贴。
杨绛多次诉说:“我来日无多,总怕来不及做完这件事,常常失眠,睡不着觉。”有一天,《钱钟书手稿集》的责任编辑郭红到杨绛家取资料,看见临窗的桌子上摊满了钱钟书残破的手稿,旁边摆着剪刀和胶水,杨绛的眼睛异样的红肿,她说正在拼对钱钟书的手稿呢。每天,她就是这样仔细的辨认那些因年久而模糊的蝇头小楷,并把它们准确的粘贴起来,这只能是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爱书的人,一个了解并尊重钱钟书真正价值的人,也是一位深情妻子的唯一选择。
钱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进进出出。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那里的图书概不外借,去读书只准带笔记本和铅笔,因而只能边读边记。做笔记很费时间,做一遍读书笔记的时间大概是读这本书的时间一倍还多,一本书第二遍再读就会发现第一遍读时的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好几遍才能发现。钱钟书深深懂得“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所以,无数的书读后只剩下笔记,钱钟书没有大量的藏书。
钱钟书留有23本3000多页的读书札记,83本15000多页的中文笔记,211本35000多页的外文笔记。2000年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在全面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后,拜访了杨绛。商务印书馆准备投入300万,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发行,保留原貌,公之于众。杨绛非常感激商务印书馆的支持,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方法。
为此,商务印书馆购进了最先进的扫描设备,聘请技术熟练的扫描员对手稿进行扫描,经过两年的编辑整理,于2003年出版了2570多页的《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巨册,2011年出版了15000多页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2015年出版了35000多页的《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四十九册。
2016年春节前夕,当杨绛拿到外文笔记最后几册新书时,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当她看到柜子上皇皇七十二卷巨制和旁边摆着的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的照片时,杨绛说:“他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我是他的老伴儿,能体会到他的心愿。”
杨绛对清华大学怀有特殊的情感,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前夕,杨绛通过吴学昭找到校领导,在钱钟书病重时,他们一家三口商量,把今后的稿费在清华设立一个奖学金,资助家庭经济有困难但又好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奖学金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而叫“好读书奖学金”,好读书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共同爱好,钱钟书和杨绛都在清华做学生,当教授,杨绛还“三进清华”,正是清华,她与钱钟书系上了月下老人的红线,对于钱瑗,清华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9月7日,杨绛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委员会理事长签订了《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基金信托协议书》,当时决定把她和钱钟书当年的稿费72万和以后所有作品的稿酬,全作为“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到2016年已累计基金2434万元,获奖收益学生达614人。
钱钟书说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作为最贤的妻,从伦敦到巴黎,从沦陷的上海到解放后的北京,她一直为钱钟书遮风挡雨。
“文化大革命”中,文学所革命群众贴出一张大字报,把钱钟书已经查清楚的黑材料捅了出来,杨绛摸黑在这张大字报旁边糊上一张小字报,逐条以事实反驳。革命群众认为“牛鬼蛇神”的杨绛竟然为反动透顶的钱钟书申辩,真是反了天了,杨绛立即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判斗争。
问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回答:是我。
又问:打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回答: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调查澄清。
台下一片厉声呵斥:谁是你的同志!
有人事后回忆说,杨绛如母狮一般,跺着脚说:“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革命群众被惹恼了,给她一根棒槌,一面铜锣,杨绛于是使劲的敲着。
革命群众给她戴上了高帽,挂着一块脏兮兮的木,让她到人多广众的地方游街。杨绛走几步就敲两下锣,喊:“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众才开始知道杨绛不是一个娇弱的女性。为了钱钟书,她可以不顾一切,以后提起此事,杨绛不无得意的说:“‘文革中,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我一个!”
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他大嫂:“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媛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
《记钱钟书与〈围城〉》里,杨绛记叙了钱钟书大量的“痴气”。比如在牛津,杨绛午睡,他用浓墨给她画花脸;在上海,女儿还是娃娃,他在小肚子画个大脸;作为书痴,他只要有书可读,就别无所求。杨绛认为《管锥篇》《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一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杨绛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而这正是钱钟书最可贵处。
作为最才的女
杨绛是优秀的剧作家,她上世纪30年代写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被称为喜剧双璧,如同她喜爱的英国女作家奥斯汀那样,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世态人情,表现出世态人情下诸多人物的内心世界。《称心如意》是通过寄人篱下被踢皮球般出入于亲戚家的孤女遭遇写出了孳生于中西文化病态层面的虚伪和自私。《弄假成真》则深入展示都市的里弄文化。剧中的周母是杨绛为现代话剧史作出贡献的非常有特色的小市民典型。杨绛一方面坚持美好合理的人性标准对小市民进行揶揄批判;另一方面对下层人物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生存又不乏肯定和爱怜,她的剧作摆脱了简单的价值判断从而体现出一种智慧的观照。
作为小说家的杨绛,《洗澡》是她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每写一章,钱钟书就读一章,读完第二部《如匪浣衣》第八章游香山后对杨绛说:“你能写小说,你能无中生有”。小说不是消极的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无中生有的想象与虚构高于现实。《洗澡》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运用对话来塑造人物性格,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经历了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杨绛调动了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积累的丰富素材,写出了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杨绛写完《洗澡》,女儿看了旧版的前言就说:“妈妈这本书走入禁区了,党从未认为思想改造是错。”杨绛说:“我也从未认为知识分子不需要改造思想。人是an alloy of base metals ,人人需要洗练,但这是个人觉悟,政治运动无补于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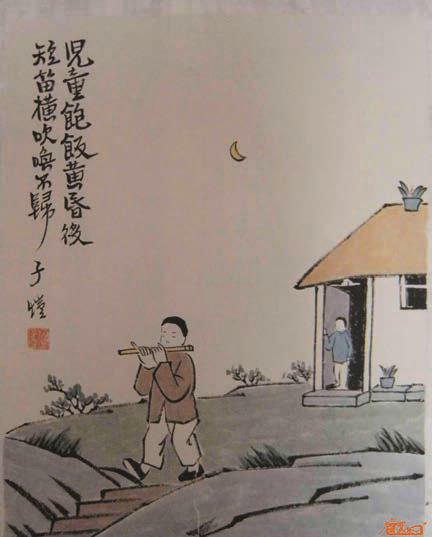
《洗澡》,胡乔木和杨绛谈论过三次,很欣赏,对杨绛说:“你写的几对儿夫妻身份都很合适,你是简·奥斯汀派,不是哈代派。”他也提出一个问题:“这是写得好的一部小说,怎么没一个好的党员?”实际上杨绛没有明写党员,马任之和王正借姚骞掩护,他们都是地下党,王正照顾姚正就是一个例证。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认为,《洗澡》是一部中国杰出的作品,它怀着希望和恐惧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第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杨绛运用她善反讽和妙语的风格,描述遭受挫折的男男女女试图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寻找着落的那个年代,即使觉察到政治狂热和人性残酷,也从不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
笔者认为,王德威指出了这部小说的审美特色。
杨绛是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她写的散文,有的是应约而作,有的是有感而发,《回忆我的父亲》便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要求介绍的简历和传记资料,杨绛经过自己认真的追忆和思索,从国内外搜集和查对有关资料,郑重的写出了这份可供参阅的资料,写完后交给近代所的题目就叫《一份材料》。胡乔木读后给杨绛打电话说:“这样情文并茂的文章,怎么称作材料啊!”胡乔木自作主张把题目改为《回忆我的父亲》,以后在刊物上得以发表。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清末从日本留学回国,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由于被清廷通缉,不得不由日本赴美国留学。进入民国后,担任过一个省的高等审判长,为了判处一个杀人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以至和省长、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在北京担任高等检查长期间把贪污巨款的总长许世英拘留,不准保释,受到的却是停职处分,于是愤而辞职,改任律师,直至退休。《回忆》也写了娴熟能干的的母亲领着全家随父亲南上北下,操持一切。杨绛以优美动人的文笔写尽了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尤其写她母亲在逃难中去世,无法安葬,读来令人泪下。
《回忆我的姑母》写的是杨荫榆,受鲁迅关于女师大学潮文章的影响。人们对杨荫榆的看法是偏颇的,杨绛笔下的三姑母特独立特行,个性鲜明,最后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她畸零不幸的一生令人同情。
《围城》重新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特别是电视剧播出之后,有人一个劲儿的把纯属虚构的方鸿渐往作者钱钟书身上套。为了给钱钟书解围,杨绛写下了这篇《记钱钟书与〈围城〉》。1982年6月,钱钟书读完后在稿子最后一页写下这样几句话:
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的向我询问,而且勤奋的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
钱钟书识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文章写出后,钱钟书开始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意”,不同意发表,后来胡乔木将稿子要过去看,很是赞赏,问为什么不能发表?这时钱钟书想通了(此文写的都是事实),才发表出来。
《记钱钟书与〈围城〉》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2003年初,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要出版《围城》的英译本,定要将杨绛的这一作品译成英文,附于书后,起初杨绛并不同意,但外研社的同志太喜欢这篇作品,杨绛实在拗不过他们的再三要求,同意附在《围城》的英译本之后。
《甲午丁未年记事·乌云与金边》作于1986年,作者说自己写的只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文化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但它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它没有像通常这类题材写残暴、愤怒和仇恨,而是通过一串串记事,一个个细节,耐人寻味的揭示“文革”颠倒是非,人性扭曲以及它的疯狂和荒谬。杨绛写出了人们感受到而又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与温情。读了这篇散文,人们才知道在浓厚的乌云后还有着“金边”,杨绛用自己博大而宽厚的心抒写了那个荒谬的时代的人性,具有独特的意味。
《干校六记》是杨绛散文作品的典范,仿照《浮生六记》,杨绛从两个方面抒写了:一、下放记别;二、凿井记劳;三、学圃记闲;四、小趋记情;五、冒险记幸;六、误传纪妄。通过诸多干校生活的侧面,写出了干校平静后面的不平静。杨绛是费了好番心思写的,自信这部《六记》超出了她以前的作品,动笔前曾告诉钱钟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钱钟书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没有用。”写好后,他为杨绛写了一篇“小引”,这回他是真的觉得好而不是敷衍。
胡乔木下了十六字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女作家丁玲不喜欢反思文字,她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的;《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干校六记》先在香港出版,胡乔木看到后加以肯定,才在三联书店出版,《干校六记》的出版引起国内外的关注,1983年英国《泰晤士报》有一篇书评说《干校六记》是“二十世纪英译中国文字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钱瑗是杨绛作品的热心读者,她对爸爸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yk威士忌)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钱钟书是眼界甚高的人,他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杨绛做为女中的才女,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她翻译的《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堂吉诃德》,几乎囊括了西欧文学中流浪汉小说的全部名著,成绩斐然,可谓译出了一个系列,一个体系,这是其他任何翻译家包括傅雷也没有做到的。
为了翻译《堂吉诃德》,从1958年,杨绛自学西班牙语,每天学习,坚持不懈,1961年着手翻译,当时搞运动,会议多,她只能一点一滴凑工夫翻;文革初,已接近译完,被红卫兵没收;1972年从干校回来接着翻,她觉得一口气断了,接不上,只好从头再翻译。从1958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七十二万字的译著,前后经历了整整二十年。
译本一问世,首印十万套很快售完,过年第二次印刷,又是十万套。
在翻译过程中,杨绛也遇到了疑难。堂吉诃德提到一个人名叫“托斯达多”,他究竟是谁呢,她发现意大利耶稣会神甫艾儒略用文言写的《职方外纪》提到一个叫多斯达笃的人,即西班牙阿维拉主教的译音。“托斯达多”是绰号而不是人名,意思是“焦黄的脸儿”,可是“焦黄的脸儿”这个绰号从何而来呢?在西班牙旅馆的早餐桌上有着各式各样的面包,照例有两片焦黄松脆的面包封在玻璃纸里,纸上印有“Pan tosotade”二字,她想“托斯达多”的脸色,大概就是这种焦黄色。参观一个教堂,历任主教像中没有“托斯达多”的像,请教导游才知道托斯达多的像在阿维拉,这位主教混有吉普赛人的血统,面色焦黄,而一般西班牙的肤色是白色的,所以绰号“焦黄脸儿”,考察到“焦黄脸儿”的缘由,杨绛“出乎意料的高兴”。
杨绛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
2016年5月25日,杨绛走完了她105年的人生历程。著名作家夏衍曾经说过:“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她具有老派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追求和人格魅力,历经风雨寒霜,作为智者,她的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是智之大者,正如老子说的:“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作为勇之大者,她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我是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如果有天堂的话,杨绛当会与钱钟书和钱瑗共聚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