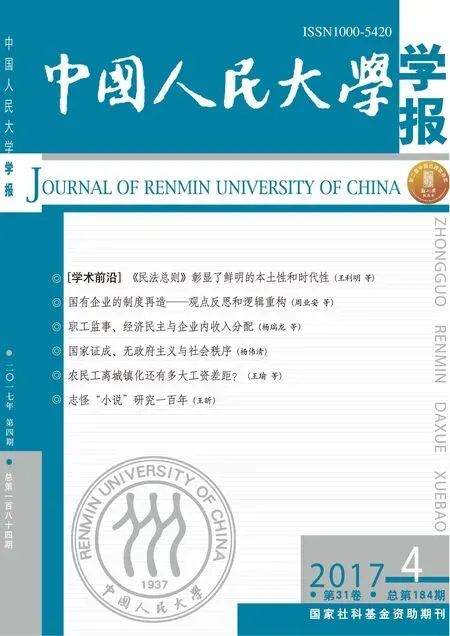家庭中的阶层并置与社会融合
——对兄弟姐妹关系的个案分析
郑丹丹
家庭中的阶层并置与社会融合
——对兄弟姐妹关系的个案分析
郑丹丹
1950年至1980年出生的人可以称其为改革一代。改革一代兄弟姐妹之间出现阶层分化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他们的互动中可能存在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但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助更为普遍。这种互助对施者有意义功能,对受者有资源功能,对社会有补充保障功能。更重要的是,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导致网络家庭中出现了阶层并置。促进阶层之间的交往,提高社会开放度,减少阶层矛盾与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融合。在各个阶层的流动中,保护社会最底层的上升通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在资源保障方面的杠杆放大效应,使其可能成为特别有效率的社会建设策略。
兄弟姐妹关系;阶层分化;社会融合;社会开放度
一、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被忽视的重要议题
家庭,是每个人最熟悉的生活单位,但其界定含混不清。从最容易辨认的一对夫妇与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到多个成年且已经分开生活的兄弟姐妹(及父母)组成的大家庭,甚至是广义的家族,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为家庭。[1]
受帕森斯、古德等人的家庭理论影响,以往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大多以核心家庭为分析单位。伴随着子代核心家庭的普遍化,学术界开始关注由亲代家庭和不共同居住的子代家庭组成的亲属家庭体系。美国学者称之为亲属家庭网络[2],台湾学者提出了“联邦式家庭”[3]与“分合间家庭”[4]等概念,国内学者则分别用“家庭网”[5]、“网络家庭”[6]、“直系组家庭”[7]等称谓指代这一家庭现象。为行文方便,本文将这一家庭现象统称为网络家庭。
人们通常认为,在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核心家庭的亲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薄。[8]然而,很多研究表明,宗族、亲缘等传统先赋关系未必会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松弛、衰落,即便是在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亲戚关系网也可能非常活跃,有些亲戚的帮助甚至胜过称职的官僚机构。[9]
对中国人而言,家庭不仅是经济和利益集团,还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强有力的宗族群体和亲缘网络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历史现象与文化传统,家庭内的连带和相互扶助是永久性的。[10]近年来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研究也表明,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更注重亲属网络的作用。尽管目前核心家庭已占主导地位,但纵向的亲子关系和横向的兄弟姐妹间的互动依然比较频繁。[11]相对而言,对网络家庭的关注以亲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间的代际关系为主,主要探讨代际传承与老年赡养问题,对成年后各自组成核心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探讨较少,即使有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他们在赡养父母过程中的共责与分责关系上。[12]*美国学者对成年子女共同养老的探讨非常具体细致,限于篇幅,仅列出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出生率较之前有较大提高。[13]因此,从1950年到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出生的人,大多有较多的兄弟姐妹。这些人陆续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即市场转型时期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生育政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规模人口流动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共同影响,导致这一群体与他们的父辈和子辈在人生境遇及家庭关系等方面出现巨大差异,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形塑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14]为了便于进行总体描述,根据曼海姆有关“代”的思想[15](P94),我们将其称为“改革一代”。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持续强劲发展,加之几乎同期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之后较长时段的低生育率,改革一代享受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红利的双重利益,从总体上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富裕。分层流动的有关研究表明,由于社会结构及个体特征存在差异,改革一代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财富差距尤其明显。[16]
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改革一代具有社会分化程度高、兄弟姐妹数量多等特征,这些特征是由社会经济政策、人口政策等外部结构性因素塑造的,而这些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的人口与家庭变迁必将对家庭中的个人及家庭关系、家庭功能产生复杂的影响,并反作用于外部社会结构,影响宏观的社会变迁进程,值得深入探究。
具体说来,既然改革一代的社会分化比较严重,且分化原因不仅仅是社会结构性的,还有个体差异因素,那么,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内部的阶层分化。已有的社会流动研究主要关注个体自身的代内流动、父子之间的代际流动,这种家庭内部兄弟姐妹间阶层分化对个人、家庭尤其是宏观社会结构的功能与后果,是以往研究忽视而本文特别关注的问题。
本文资料来源于2014—2016年笔者进行的家庭结构变迁与养老问题的访谈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网络家庭之间存在阶层分化,互动内容丰富,并不局限于协作养老。
二、兄弟姐妹阶层分化的结构性背景
在我们所访谈的多子女家庭中,成年的兄弟姐妹在职业、教育水平、收入等方面完全一致的情况非常少。根据学术标准,有些差异已经构成阶层分化。*现有的调查数据几乎都是基于个体和代际层次,很难精确研究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笔者利用CFPS2010数据中“被调查对象所有孩子的职业”这一问题进行考察,60岁以上被调查者的家庭中,只要多个子女职业有不在一个类别的情况,我们就认为子女之间有职业阶层分化。结果显示,本文所探讨的改革一代,其兄弟姐妹之间出现阶层分化的比率达到39.1%。总体而言,一个家庭中可能有个别或少数孩子由于特殊的机缘脱颖而出,或是出现阶层下滑,拉开了和家庭中其他人的差距。为了便于表述,本文主要考察向上流动的情况,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案例也以原生家庭处于底层的为主。
导致家庭中兄弟姐妹间产生阶层分化的原因很多,大体可分为个体资质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两大类,本文只揭示一些与他们日后互动有关的结构性背景。
首先,制度变迁对个体的人生际遇会产生影响。有时候,天赋资质没有本质差异的兄弟姐妹,由于年龄差异导致所处的时空维度不同,处于实质上不同的社会结构,所能获得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影响改革一代的因素主要包括高考制度、顶替制度、招工招干制度等。
我们访谈的家庭中,很多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哥哥姐姐早早就参军、就业(包括务农),在1977—1979年间非常微小的高考机会中无法胜出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参与,但20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出生的弟弟妹妹则可以从容地学习(他们有可能复读,参加多次高考),因而获得教育机会,实现向上流动。这就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尤其是制度变迁对个体教育机会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了同一家庭中不同个体的人生际遇以及阶层地位,造成本文所探讨的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我们发现,由于个体自身原因(比如不擅长学习)或者这里提到的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家庭内部阶层分化,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往往能比较理性地看待,最多会哀叹自己的命运不济,但不会对处于高阶层的兄弟姐妹产生不满。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家庭中阶层分化的影响。由于改革一代主要成长于物质匮乏年代,很多家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资源竞争,比如稀缺的招工名额、唯一的顶替指标、珍贵的读书机会等。这一竞争过程及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后期网络家庭间的关系和互动。做出牺牲的个体通常自觉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而地位上升者也大多会兑现这种补偿。这是本文要探讨网络家庭能实现部分社会保障功能的重要原因。
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对这一竞争过程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家庭通常会根据长幼排序(优先年长的孩子)或者以能力取胜(挑选可能会有出息的孩子以尽最大努力提高全家的竞争力),但是女性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家庭中,女孩尤其是姐姐可能被牺牲以保障家庭中男孩享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中国在近几十年间出现教育、就业等制度的重大变迁,导致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面临的制度背景出现结构性差异,由于社会资源总体匮乏导致众多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出现竞争,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事实。用西方基于相对平稳发展的社会事实而发展起来的学术传统来解释中国问题,常常有不能完全适用的感觉,或者会忽略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比如本文所探讨的兄弟姐妹间阶层分化问题。因此,恰当地借鉴和运用西方学术研究成果,并立足中国事实建构能解释中国问题的理论,是特别值得关注和努力的。
三、家庭内部阶层分化的社会保障功能
所谓阶层分化,指的是人们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兄弟姐妹之间资源拥有量出现了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但由于亲属关系,他们又难以避免地常常发生互动。由于出现了阶层并置,他们的互动往往潜含着矛盾和冲突,有时候表现得很明显,甚至会激化。但是总体来说,就算是矛盾冲突比较多的家庭,他们之间也并非只有伤害,而是情感和伤害相互交织,各种形式的互助总是存在。显然,家庭中的阶层分化和互动,对个体与家庭而言有其独特的功能,需要深入分析。
(一)兄弟姐妹间的互助
根据对访谈资料的归纳与分析,我们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常常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救急救难。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家庭,都有程度不一的救急救难情况发生。也许只发生在家庭中多个兄弟姐妹间的某一对关系中,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是完全没有互相帮助的情况的。当兄弟姐妹因为生病、离异、下岗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或者因为孩子读书、结婚等经济周转不灵时,大多数人都会程度不一地伸出援手。其他研究也发现这种情况,比如在离婚及困难家庭中,来自兄弟姐妹的帮助非常重要。[17]这种帮助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出力也是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是协助发展。比如买房子、办大事(包括开店、承包鱼塘等各种形式),一时间钱不够,很多家庭的兄弟姐妹都会尽力协助,或资助或提供没有特别明确归还期限的借款。
第三种形式不是特别多见,主要出现在部分家庭成员比较有“能力”的时候,那就是协助就业。这种协助不一定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还包括协助侄儿侄女就业。这种帮助通常被认为含金量最高,甚至直接连带地导致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向上流动,整体地改变全家的社会分层格局。
最后一种是最为常见的形式,也是学术界分析比较多的,那就是在父母养老过程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合作互助,此处不赘述。
1964年出生的丽萍*本文中所提到的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下同。是高校教师,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的丈夫是高校中层干部,丈夫家在农村,有4个兄弟姐妹。丽萍讲了自己家与丈夫家的各种互动,经济上丽萍家对几乎所有兄弟姐妹都有程度不一的扶助,大到20世纪90年代三姐家做生意向他们借了5 000元钱(那时候是大数目)一直没还,小到每次回老家带去的相机都会被某个侄儿侄女喜爱且留下。丽萍特别提到丈夫家人对自己的帮助:她曾经到香港求学,孩子小,大姑姐(老公的姐姐)帮忙带了两年。虽然在经济上丽萍没有亏待大姑姐,但她说起此事还是对大姑姐充满感激,认为这种帮助是她最需要的。
可见,实际生活中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往往是多种形式共存,很难清晰划分。比如丽萍与大姑姐之间很难说是丽萍资助了大姑姐一些金钱,还是大姑姐帮助丽萍带了孩子。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加深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丽萍对家庭互助做了很好的归纳:“我觉得大家庭就像合作社,互相帮忙,也算不清楚吧,总之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先生是农村的,家里就只有他读出来了。不帮衬怎么办?嫁给这样的老公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觉得没什么,很多人做公益慈善,我在家里做,不是一样的吗?我把他家救济了,有余力再救济他村里人,就很好。其实人家也不白要,你看我困难的时候,人家真出手,大姑姐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孩子扔在家里就到北京来帮我带孩子,两年啊,人家没提任何条件,我是没亏待她,但是人家自己真没提什么条件。这就是家庭啊!”
这种合作社式的互助形式在养老等家庭公共事务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小红家共有4个兄妹,只有二哥目前生活状况不是特别好,他更多地承担了具体照料老人的任务。小红说:“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想想,真多亏二哥过得不是特别好,我们出钱,他可以出力照料老人,否则都跟我们一样忙,有心也无力啊。”
那么,对家庭成员而言,兄弟姐妹间的互助有什么功能?其内在动因是什么呢?
(二)家庭的保障功能及其实现
归纳而言,家庭成员间的互相援助,对施者有意义功能,对受者有资源功能,对社会有补充保障功能。
雯雯的父母是表兄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大哥是盲人,二哥是智障。雯雯嫁人后生活过得还不错,出钱给家人在郊区买了一套房,父母亲靠不多的退休金与大哥二哥一起生活。雯雯基本上每周都去看望父母和哥哥,买些蔬菜和生活用品过去。这样的例子当然有些极端,但确实存在。很多的家庭都在极其坚韧地互助生存,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了补充性的社会保障功能。
仔细想来,这样的家庭互助能够实现,常常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兄弟姐妹之间有人要过得比较好,有能力帮助其他人。本文所探讨的阶层分化就是这个重要前提。唐钧等人在1999年前后对上海市贫困人口做的访谈发现,亲戚的帮助很常见,对很多家庭来说很重要,但也并非必然能够实现。如果兄弟姐妹生活水平差不多,都不富裕,那就很难帮衬得上。*参见唐钧、朱耀垠、任振兴:《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9(5)。这里说的亲戚指的是成年并各自组成家庭的兄弟姐妹。因此,可以作出简单归纳,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是需要互助以及能够实现强有力互助的必要条件。这种互助或者说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内在动因。
第一个动因是优胜者的反哺。就教育机会而言,如前所述,在改革一代成长的资源匮乏年代,家庭中读书资质稍差者可能被放弃,转而协助父母为胜出者提供资源。涉及性别关系,甚至是读书资质更好的姐姐、妹妹也会被牺牲来成全哥哥、弟弟享有读书机会。这种状况会造成子女间的阶层分化,并几乎必然地使胜出者产生反哺家庭尤其是对为自己作出牺牲的兄弟姐妹有所回报的情感和道义压力。
1966年出生的俊菲也是大学老师,她自己的父母都是老国企的基层员工,丈夫是大学老师,来自农村,家里只有一个妹妹。俊菲认为自己婚后就背上了包袱,丈夫的父亲和妹妹一直需要她的小家予以各种帮助,给公公养老俊菲觉得是义务,但还得时不时帮助“挑剔”的小姑子找工作甚至贴钱,俊菲觉得很心累,但也很无奈,她说得很明白:“他们家在大山沟里,小时候饭都吃不饱,他妹妹早早地停学了下地干活,累死累活地全家才努力供出他来,你不管他们行吗?我管不了太多,不能保证他老爸(妈妈已经去世)和妹妹能过得多好,我没那个能力,但真没饭吃了我还是得管。他妹妹说,嫂子,要不是为了我哥,我也能读出来。他妹妹聪明着呢,也真是可惜了。”
第二个动因是家庭凝聚力,这主要表现为父母的聚合作用。当兄弟姐妹间需要互助与互动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有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嘛!”访谈中,几乎所有人都能自如地使用“家庭”概念而不会出现混淆,它可以很清楚地根据不同情境各自指代自己的小家庭,以及兄弟姐妹间组成的网络家庭。不少网络家庭都建立了微信群,其中很多都冠以“一家子”、“一家人”、“*家议事厅”之类的名称,充分体现了网络家庭的凝聚力。如果老父老母还有人健在,这种网络家庭之间的互动与联络就明显更强。小红的大哥和三哥各自给二哥的一个孩子解决了就业问题,问及原因,小红说,“一开始大哥三哥没动静,老爸可是不答应,把这几个过得好的孩子组织起来开会,说五指连心,一母同胞,你们不能看着二哥受苦。二哥隐约表示自己能过下去,就是担心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哥三哥还是有压力吧,就拼命努力把事情办了。”
有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助并不涉及具体的原因,并没有感恩回报或者父母的压力,这就涉及第三个动因:中国家庭对个人的意义价值。有学者指出,传统亲缘群体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本体性”需求,是对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的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满足。[18]也许有些人对兄弟姐妹的帮助同时也会受其他因素影响,但除此之外,帮助家人给个人带来的纯粹心理满足感和意义价值也总是可以从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和家庭凝聚力有联系,但也有微妙区别,其动因更具内在性。
第四个动因可以称为制度的人际弹性。如小红家这样由家中上层成员在安排工作、提供生意机会等方面照顾低阶层成员,这样的做法能实现,部分原因也在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制度安排都有人际弹性,留有运作空间。
宗全是农村人,二哥早年当兵后来转业在外地就业,生活过得不错,最小的宗全1978年高考失利,全家经过商议,支持他复读一年,于1979年考取了财校,之后分配到县财政局,1996年前后担任局长职务。之后宗全在3年间陆续将在家务农的2个哥哥和1个姐姐调离了村子,用各种方式安顿在县城。当地人说起宗全家都会羡慕,说他们家“祖坟上长了好大的蒿子,冒了青烟(说明发达)”。三哥没法安排工作,就资助承包了鱼塘,宗全所有的业务关系全部带去三哥的鱼塘钓鱼。细究起来,正是因为中国很多制度都有这样的人际弹性,宗全这样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人才能以一己之力把全家都带向了新生活。
上述家庭都因为个别或者少数子女实现了向上流动。家庭中境遇比较好的子女努力帮助兄弟姐妹改善生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了中国家庭的坚韧性,是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能够行使补充性的社会保障功能。
四、阶层分化中的社会融合机制
(一)兄弟姐妹阶层分化与社会开放度
社会开放度(societal openness)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开放的社会是指,社会结构中各主要群体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可渗透的、易穿越的。否则,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诸多特定资源或机会分配方面的相对差异长期保持不变,一些特定人群具有相对垄断权利,另一些人则被阻隔在外,这种情况学术界称之为阶层固化。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社会开放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一个社会若要健康运转,必须防止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结构。[19]
对于社会开放度,代际的社会流动性、婚姻配对的内婚性程度及阶层间社会交往程度是三个主要测量指标。[20]一方面,有学者指出,“5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几度重大的变革背景下发生的。而工业化国家学者研究的社会流动,一般都是研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的代际流动,所以两者在社会流动的机会、规则、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所以,仅仅应用现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模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许多现象,都不好解释”[21](P9)。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的社会变迁速度比较快,两代之间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巨大差异导致很多因素难以控制,所以很难准确地把握代际流动的规律。笔者认为,用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来分析一个社会的开放度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衡量指标,由于他们所处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更为接近,可能比代际流动更容易准确地揭示个体特征的影响。当然,如前所述,由于数据资料的缺乏,这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另一方面,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其实质是在网络家庭中出现了阶层并置的情况,而且势必会有很多跨阶层的互动与交往,显然,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可以提高社会中不同阶层间的交往程度,因而提高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融合。那么,这种作用具体是怎样产生的呢?其融合机制如何呢?
(二)兄弟姐妹阶层分化中的社会融合机制分析
我们认为,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融合,其具体作用机制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一是柔化机制。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他们常常具备与资源占用量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开放度不高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可能由于陌生感而导致客观的差异转化为主观的对立与冲突。但原本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后天出现了阶层分化,则与原发性的阶层分化有很大不同。首先是惯习方面的家族相似性导致他们大多没有根本的差异和冲突。其次,即便是逐渐产生了惯习方面的差异,但是家庭的情感基础也会使得这样的差异大多数时候被隐藏起来,至少不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很显然,在这样情境中的阶层互动有很强的柔化作用,特别有利于减少底层人民对上层社会的仇视,因为在他们眼里,上等阶层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很容易被具体化为他的兄弟姐妹,因而他很难对之带有抽象的抵触或者仇视,而是容易产生一定的亲近感,仿若他们与之有一些莫名的联系,甚至产生“自己人”的感觉。可以说,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具有一定的稳压器或者安全阀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是连接机制。社会关系具有发散性,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和互动通常并不会仅限于他们之间,由于这种阶层分化,社会阶层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互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会模糊阶层边界,促进阶层交往。我们访谈的很多家庭中,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个体都缔结了跨阶层家庭背景的婚姻,那么这些个体就作为社会的枢纽存在,或者说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节点,他们连接了原本可能区隔开的不同阶层。不论这种互动是顺利(比如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丽萍与夫家的互动)还是不顺利(比如生于职员家庭的俊菲与夫家的互动),都必然会增进阶层间的互动和相互了解,哪怕这种了解的结果不一定美妙,但这种熟悉也是一种社会融合的机制。我们在访谈中常常发现,访谈对象特别愿意跟我们说起家里人的骄傲,就是地位最高的人,仿佛他们自己的地位也提高了。可见,通过兄弟姐妹中伸得最远的这根触角,低阶层的个体可能建立起与高阶层群体的某种间接联系,形成真实的或者想象的阶层互动,促进社会融合。
三是连带机制,也可称为沾光机制。这个机制最为重要。前面已经说过,不论强度如何,中国家庭中兄弟姐妹间的互动都是不可避免的,相互间的帮助非常普遍。同时,在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个体的能力与帮扶意愿都很强的时候,他们可能给兄弟姐妹带去更多福祉,比如资助生产、协助就业等。有些时候,这些个体甚至带动了家庭中很多人的向上流动,比如宗全通过高考以及随后的职场生涯积累实现了阶层大跨越之后,家里除了二哥是原本通过参军实现了向上流动,其他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靠宗全提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可以说宗全就是全家的“贵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宗全的做法是符合传统家族观念的,历史上的宗全形象,其实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的内在机理之一。很多贫困家庭会举全家之力供某个孩子读书,希望日后可以实现宗全式的全家获益,至少是希望能实现俊菲丈夫家的社会保障型帮扶。*也正是部分地由于感受到教育所能带来的向上流动力量的衰减,很多农村家庭不再愿意倾全家之力投资教育。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带有传统思想的中国家庭,“靠”着自己的富贵亲戚,并不是什么稀奇或者丢脸的事情,反而带有顺理成章的意味。访谈中很多人谈到不愿意帮助贫困家人的兄弟姐妹时,都会说“这个哥哥(弟弟)是没有用的”。访谈对象玉芝的丈夫打工发财之后,她最苦恼的是,婆婆和大嫂都觉得大嫂家里的两个儿子以后就应该由玉芝家负责了,觉得他们都“应该跟着叔叔家过上上等人的生活”。可见,由于兄弟姐妹向上流动后带给其他家庭成员的现实流动以及流动预期,部分社会底层成员的主观阶层认同有可能会提高,因而现实地降低了社会压力和矛盾,消弭阶层固化带来的绝望感,促进社会融合与稳定。
五、结论与讨论
(一)简要结论
本文认为,1950年到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间出生的人,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具有社会分化程度高、兄弟姐妹数量多等特征,为了方便整体把握,可以粗略地将这一人群称之为改革一代。对改革一代而言,不少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阶层分化,除了个体资质因素之外,这种分化往往受到制度变迁和社会文化尤其是性别文化的影响,并形塑了日后网络家庭的关系与互动。
兄弟姐妹之间出现阶层分化,他们的互动可能潜含着矛盾和冲突。但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助更为普遍,包括救急救难、协助发展、协助就业以及养老互助等多种形式。家庭成员间的互相援助,对施者有意义功能,对受者有资源功能,对社会有补充保障功能。这种家庭互助或者说保障功能得以实现依赖于几个机制,包括优胜者的反哺、家庭凝聚力、家庭对个人的意义价值以及制度的人际弹性等。
更重要的是,兄弟姐妹间的阶层分化导致网络家庭中出现了阶层并置,这增进了跨阶层的互动与交往,提高了社会的开放程度。由于原本可能很生硬的阶层分化与互动发生在家庭内部,加上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观念的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分化就可能通过柔化机制、连接机制以及连带机制,实现跨阶层交往,减少阶层矛盾与冲突,消减社会分层给底层人民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融合。
(二)进一步讨论
学术界曾经探讨为何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如此之高但依然稳定[22],可能的原因很多,但中国家庭的坚韧性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答案。改革一代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阶层分化固然可能带来家庭成员之间交往的一些困难乃至矛盾和冲突,但更可能因为全家资源增加使得互助得以实现。一部分向上流动者可能带动全家人向上流动,至少是部分地为脆弱家庭人口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不考虑中国家庭的这样一些特殊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很多西方理论便难以有效解释中国事实。
有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阶层固化的趋势[23],这是需要警惕的。本文认为,家庭内部出现阶层分化,往往是行使有效社会保障功能的前提。在各个阶层的流动中,保护社会最底层的上升通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家庭成员可能会一个人带动一家人,都实现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显然,这对于改善中国分层结构是非常有效率的。即便不能实现全家人向上流动,底层家庭中的竞争胜出者也往往难以逃避对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职责,这就能在操作层面减少政府的扶贫压力,极大地稳定了社会底层基础,这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在社会总体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将资源尽力倾斜至社会最底层,尤其是提高教育对其向上流动的作用,精准扶贫中要考虑最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投资。这样的做法不仅符合社会正义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而且是特别有效率的社会建设策略。
由于1980年后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本文所探讨的兄弟姐妹阶层分化问题似乎不再成为重要的社会事实,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令人怀疑。然而我们认为,改革一代是社会的中坚代,当前的社会事实部分地是由他们的行为形塑的,因此理解他们既必要且重要。而且,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在农村仍有大量的多子女家庭,本文探讨的议题对他们也特别吻合。特别是,2015年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开始改变,多子女家庭在未来有可能再次成为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类别。因此,笔者认为,本研究的结论可能并不仅仅限于改革一代,对未来也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7] 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4)。
[2] Sussman,Marvin B. and L.Burchinel. “Kin Family Network: Unheralded Structure in Current Conceptualizat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Living,1962 (3).
[3] 庄英章:《台湾农村家族对现代化的适应——一个田野调查实例的分析》,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72(34)。
[4] 胡台丽:《合与分之间:台湾农村家庭与工业化》,载乔健主编:《中国家庭及其变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香港亚太研究所,1991。
[5] 潘允康:《家庭网和现代家庭生活方式》,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1)。
[6] 郭虹:《亲子网络家庭——中国农村现代化变迁中的一种家庭类型》,载《浙江学刊》,1994(6);王跃生:《网络家庭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以北方农村为分析基础》,载《社会科学》,2009(8);王跃生:《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分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0(4)。
[8] 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9] 古德:《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0] 黄金山:《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和义务》,载《历史研究》,1988(2);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11] 阎云翔:《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载《社会学研究》,1998(6);徐安琪、叶文振:《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来自上海的调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6);张结海、徐安琪:《家庭结构与未成年子女的福利——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6)。
[12]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王树新:《论城市中青年人与老年人分而不离的供养关系》,载《中国人口科学》,1995(3);伍海霞:《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Grigoryeva, Angelina. “Own Gender, Sibling’s Gender, Parent’s Gender: The Division of Elderly Parent Care among Adult Childre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2017 (1).
[13] 马妍:《吉年生吉子?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基于1949—2008年出生人口数》,载《人口研究》,2010(5)。
[14]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12)。
[15] 曼海姆:《曼海姆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 李路路、朱斌、王煜:《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工作组织流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9);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囯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1)。
[17]唐钧、朱耀垠、任振兴:《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9(5)。
[18] 钱杭:《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学术月刊》,1993(4)。
[19] 宋林霖:《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阶层固化:政治学的解释与应对》,载《行政论坛》,2016(4)。
[20] 李煜:《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载《社会学研究》,2011(4)。
[2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2]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载《社会学研究》,2009(1);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载《社会》,2010(3)。
[23]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4)。
(责任编辑 武京闽)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side Network-family ——An Analysi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of China’s “Reform Generation”
ZHENG Dan-dan
(School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This thesis coins a term “Reform Generation” to refer to those born between 1950s and 1980s, explores the class differentiation that might exist among siblings of the “Reform Generation”, and analyzes the function and outcome of such differentiation for individual, family and the macro social structure as a whole.The author argues that class differentiation among siblings does exist universally in the “Reform Generation” and enables widespread mutual assistance inside the network family, which could fulfill the supplementary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in China.Furthermore, the class differentiation among siblings results in hierarchical juxtaposition inside network family which could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enhance societal openness, reduce tension and conflict, and improve societal stability and integration.
sibling relationship; class differenti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etal openness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新媒体影响下的家庭变迁及政策应对”(2017WKZDJC002)
郑丹丹: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