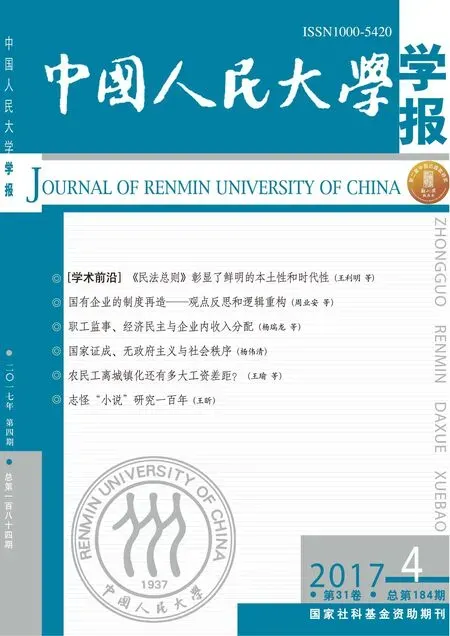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趋势分析
孟 鑫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趋势分析
孟 鑫
新社会运动作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塑造西方社会的重要力量,走向制度化是其发展趋势之一。社会运动制度化实质上是国家的体制构建目标和社会运动的诉求目标互动博弈的产物。这一过程既改造了社会运动,也对国家体制和社会危机管理机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来看,制度化趋势并没有改变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抗议属性和变革目标,它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变革力量。
新社会运动;国家体制;制度化;趋势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公众的政治革命意识逐渐消退,以社会改造为目标的新社会运动渐次兴起。这种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宗教运动、反核和平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同性恋维权运动、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等”[1](P3)。从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到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均属于此范畴。其共同特征是社会群体自下而上、通过非制度化方式表达不满和抗议,力图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变迁。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社会运动以及伴随其后发生的社会变革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新社会运动贯穿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新社会运动史。
新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有相同的一面,它也是一种通过集体行动来促进社会变迁的行为方式;但与政治革命不同的是,新社会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是社会改造,其在激烈性和对抗性上远低于政治革命。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政治革命逐渐消弭的背景下,新社会运动成为替代政治革命促进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变迁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者。作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抗议形式,它已经成为一种塑造西方社会的重要力量。新社会运动在当前也遭遇了发展困境,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做出新的判断和抉择。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新社会运动可能会走向制度化、组织化、非暴力化和全球化等。
一、新社会运动制度化
新社会运动制度化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运动主体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己力量,但其对现有制度仍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二是国家制度虽然对各种社会运动意在抵制,但在法律层面仍有一定程度的容纳。究其本质,这一制度化趋势是各种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博弈的结果。
(一)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学术界对“制度”的认识有一定差异。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2](P51)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3](P3)“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4](P12)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制度化”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是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的模式转化的过程,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它表示个人、组织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程度以及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由非正式系统发展到正式系统、社会制度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5](P387)也就是说,“制度化”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组织或机制从不稳定到相对稳定、从非正式到正式的演变过程;二是行为、组织或机制的运行方式、存在方式被已有社会体制逐渐接纳并认可的过程。就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来说,一方面,对于社会运动参与者,这种接纳和认可,将会使不确定的运动方式转化为可预期的运动模式,进而降低了参与者为寻求新的参与渠道和表达方式而付出更多代价的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参与者运用制度外途径进行社会运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对于现有政治体制,这种制度化可以减缓社会运动冲击,了解社会矛盾状况,扩展社会阶层基础。总的看来,如果能够实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无论是对公民还是对政府而言都可以降低实现目标的代价和成本。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梅耶的分析,社会运动制度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常规化。无论是运动参与者还是制度保护者都有各自熟悉的“剧本”(script)可为遵循,并且都能够采用已经熟练的行动模式,对自身选择的潜在危险及其他可能有预期判断。第二,包容及边缘化。那些愿意遵守常规运动模式的抗议者将会获得在制度体制内进行交流的机会和路径,反之则不然。第三,吸纳。抗议者选择通过维持常规政治系统的方式来实现其诉求。
社会运动的目标是否具有长期性,直接影响到它是否愿意走向制度化这一结果。那些不以制度更迭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往往是希望在短期内对现有制度或体制产生预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就不仅仅是国家制度和体制结构对社会运动的规制与吸纳,它也实现了运动参与主体对制度或体制产生预期影响的运动目标。而那些以制度深层改革甚至制度更迭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往往会遭遇现有政治体制的强力抵制,它们最初也会抵制制度化趋势,但是,如果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无法实现长远目标,为保存实力,延续影响,它们往往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因为这是有利于长远目标实现的战略选择。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中都出现了这种为了长远目标的实现而与国家体制合作的情况。
另外,社会运动能否出现制度化的结果还与某个国家的下列情况相关:一是国家政体的性质。一个国家采用民主体制或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将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应对社会运动的能力和方式。二是国家的阶层结构以及种族、民族关系。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运动制度化实践路径的具体走向和方式。三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包括政治体制与公民互动的历史、运动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程度等。以上因素在不同侧面和不同阶段会对社会运动能否被制度化产生较强影响。
社会运动走向制度化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第一,19世纪中后期的工人运动根本不存在制度化的可能。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尖锐,这一时期的欧洲工人反抗运动猛烈而频繁,运动目标明确而坚定,旨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一阶段的抗议行动大多数采取暴力手段,其自身也坚决抵制被制度化。第二,20世纪初期出现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可能和迹象。随着英、法、美等国改革政治体制,公民政治权利不断扩大。政治环境的改变促使社会抗议运动的行动方式逐渐转型,社会运动的手段和形式有了较大的调整,更多地选择非暴力形式作为抗议手段,这一变化为社会运动制度化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社会运动制度化。第三,20世纪中后期进入新社会运动阶段以后才逐渐出现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趋势。西方主要国家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良,阶级矛盾缓和,阶层结构改变,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运动的宗旨和目标发生了较大变化,政治革命性目标逐渐消弭,生活价值性目标凸显,鉴于此,代表国家制度的法律条文和行政规定对社会抗议运动的容纳力有所提高,政府对游行示威、公开集会等表达或抗议行动的接受度也有所提高,运动参与者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社会运动制度化成为一种可能降低国家和公众成本的双赢选择。查尔斯·蒂利在《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通过对一些西方国家社会运动发展史的深入研究,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运动形式的变化历程,进而揭示出新社会运动在发展中自身运动形式逐渐被体制和制度影响的过程。
(二)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是在几种复杂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它自身不断努力在现有体制内促进社会变迁,制度化是其现实选择之一;另一方面,现有体制如果认为这种制度化有利于缓和社会危机和矛盾,也会努力促进其走向制度化。新社会运动本身并没有抵制这种制度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制度化的运行模式。这种制度化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第一,对现有体制的一定认同。新社会运动对现政权的冲击程度显然小于之前任何形式的革命,包括传统工人运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反倒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改良变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生运动、70年代的民权运动、80年代的生态运动、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21世纪初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社会抗议运动如果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政治革命,而在西方国家的现有制度体系下,这些运动虽仍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冲击力和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但大多数运动最终都以和平收场,而执政者却通过社会运动的爆发和运行过程,更多地发现执政漏洞,完善执政方式。这一切都使新社会运动演变成为改造现有体制和制度的原动力之一。
第二,促使现有制度增强对运动的容纳度。实际上,社会运动制度化就是各种社会运动被吸纳进国家制度框架中,在此过程中各种运动在组织结构、行动方式等方面与现有体制产生一定融合,这一过程也是促使现有制度本身不断调整、增强对社会运动的容纳力的过程。在英、美、法、德等国,随着暴力运动逐步减少,国家在法律和制度层面逐步接纳非暴力的运动形式,一些运动形式也被社会大众所采纳和接受,社会运动最终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
第三,运动形式逐渐走向预期化。社会大众对运动形式、运动主题、运动影响甚至政府的反应都形成一定的预期,运动形式的常规性展示过程和政府的常规性应对模式,已经被社会公众所采纳和接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G·朱格尼和佛罗伦萨·帕西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界定:第一,社会运动与国家政党进行沟通博弈,使其允许社会运动进行信息传播、见解发布以及政策建议等活动;第二,整合后的社会运动被赋予一些执行政策的权责;第三,通过代表和授权,社会运动进行决策和实施活动。[6](P81-107)也就是说,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一般会通过博弈、整合以及实施三个阶段得以实现。
二、新社会运动制度化趋势的现实展现
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趋势主要体现在运动的表现形式、组织过程,以及运动与体制的互动走向常规化和模式化等方面。
(一)运动形式趋于规范化
从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各种运动主题不同、参与群体各异、运动方式独具匠心,但是,诸多类别的社会运动经过多年发展后,逐步具有了“常备剧目库”。此剧目库中包括很多可选“剧本”,诸如“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集会、示威、请愿等政治行为方式的随机组合”[7](P4)。即使是骤然发生的抗议运动,大多数都是采用了剧目库中的备用模式,社会运动从以往的不可预期状态转化为可预期模式。因此,新社会运动出现“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是集体行动方式发生了变化”[8](P172),其典型表现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运动方式正在趋向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运动实践,运动参与者在运动开始之前往往会对抗议活动的发展轨迹和运动模式做出一定的研判,在诉求目标、运动过程和活动结果方面会有一定的预期,而且倾向于采用多年形成的相对稳定和相对规范的运动模式。
(二)运动组织倾向专业化和职业化
一方面,一些社会运动所涉及领域的专业性较强,如生态运动和反核抗议运动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员和资深人员时常会扮演运动理念的提出者或实践问题的发现者的角色。这些人员的参与使抗议活动的发起和组织不像传统工人运动那样高度团体化和组织化,但专业化色彩更为突出。因为他们的学识理念、职业素养对活动主题和活动过程有较大影响,而且,他们身份职业的体制化和专业化,也使得一些社会运动体制化、专业化倾向明显。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对社会运动进行规范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种规定越来越细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使各种类别社会运动的组织更为高效,运行更为有效,这些要求已经促使社会运动的组织行为有了职业化的趋势,在美、法、德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全职的社会运动经理人和组织者,他们为实现抗议活动的目标提供剧本化的策划和组织,各类运动主体往往会在他们的运动策划下参与行动。这些因素都使新社会运动具有更强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征。
(三)运动与体制互动走向模式化
各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一般会要求各种社会运动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报备。这些规定改变了运动与体制的关系,使运动成为体制存在状态的一部分。报备后的社会运动与体制之间形成了新的互动模式。政府和运动参与者之间正在逐渐相互容纳并逐渐相互适应。由于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常常会选择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方式,抗议活动的凝聚力较差,破坏力相对较小,因此,警方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较为宽容,所以,抗议者与警方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二者之间爆发暴力对抗的概率相比传统工人运动较低。另外,运动所造成影响的可预测性,也使得警方的预判能力提高,危机管理能力随之加强。近些年,在反全球化、抗议气候变化及抗议金融危机运动中,也偶尔会发生抗议者与警方的冲突,但是大规模极端暴力的冲突数量正在减少。
总的看来,新社会运动之所以会形成制度化趋势,是因为“社会运动自有其制度化的基础条件。实际上,社会运动是和政党、利益集团类似的政治参与形式。只不过,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组织性更强,其所代表的人群更加明确。而社会运动所代表的人群也许更加多元。回想历史上政党和利益集团也曾被视为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终都被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而成为常态参政机制”[9]。
虽然走向制度化是新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各种社会运动制度化现象频频出现,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运动最终都会完全制度化,某些社会运动可能只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新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程度,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可能获得某种路径进入主流政治和文化体系,但是运动自身的诉求程度可能会被削弱;第二类是运动自身放弃进入主流政治体制发挥影响的目标,转而从事更基础的工作,致力于在参与者中形成清晰的运动观念和目标认同,形成更深层的影响;第三类则会放弃运动主题或者不再重视运动目标,转向重视其他问题,运动个体开始关注个人生活。”[10](P130)
三、新社会运动制度化趋势的深远影响
新社会运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并不仅仅指那些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也包括思想主张表达、行为方式倡导等行动,同时,在不同社会运动中还存在差异化的诉求目标、多样的行动方式以及不同的参与主体。鉴于从具体角度分析新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影响可能缺乏代表性,因此,我们从社会运动自身、国家体制及社会危机应对机制三个较为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新社会运动并没有因出现制度化趋势而走向衰落
新社会运动制度化意味着社会运动与国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这一过程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制度化是否意味着社会运动所秉持的原则被改变,运动走向衰落?制度化是否对社会运动的抗议性质和变革目标产生消极影响?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过程中,它的确存在被整合甚至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制度化往往被视为社会运动走向衰落的起点。制度化对社会运动来说是消极的,它可能会使运动失去其基本特征和有效形式,使运动的组织形式从集群的和分散的转化为科层的和系统的;使运动目标从激进的转化为理性的,使行动方式从有冲击力的转化为温和的。其更大的影响是会使社会运动的抗议理念日渐消失,从而逐渐褪去激进的色彩,进而减弱和消除对现有秩序的改变和冲击能力。
威廉姆·A·甘姆森认为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制度化运动是否走向衰落:一是制度和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挑战群体的诉求目标。挑战群体是否成为合法利益的有效代表者,这实际上涉及这一群体的地位和影响。二是挑战群体及其支持者是否通过参与或支持行动获得了新的优势。[11](P57-77)从第一个标准关注的目标看,无论是女权运动与反核和平运动还是生态运动和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它们的诉求目标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制度和体制在各种运动的冲击下都有一定的改变。从第二个标准关注的目标看,对于大多数社会运动参与者来说,只要将自己的意愿和诉求充分表达出来,进而对体制和社会以及社会成员产生相应影响,就能视为达到运动目标,因为大多数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出发点都是希望通过运动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体制或制度的改变。
因此,制度化并不意味着社会运动反叛属性的消失。制度化趋势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人们应该摆脱制度化等同于社会运动被现有体制整合的理念。原因在于,首先,制度化有利于拓宽运动目标的实现途径。虽然经过报备的社会运动的地位是合法的,但是毕竟属于体制外渠道,制度化的运动在体制内拓展了自己的影响。其次,制度化使社会运动可能获得有利的合法地位。制度化使社会运动有机会在与政府合作和维护运动原则之间保持平衡,这样的运动有机会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进行行动方式的切换和选择,甚至能够充分利用不同方式的优势去实现目标。“社会运动进入常规政治舞台,可以利用体制内政治提供的机会结构施加自己的影响。制度化为社会运动以一种更常规、更稳定的形式在决策、执行等环节中发挥影响提供了渠道。总之,不应该简单地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等同于被现有体制收编或运动失败。”[12]因此,即使出现了制度化,并不标志着社会运动抗议和反叛属性的消弭。
(二)制度化趋势表明新社会运动在短期内仍无法撼动资本主义制度
虽然各种新社会运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变革的目标及其抗议属性,并未因其出现制度化趋势而发生改变,可是,形成制度化趋势这一现实却表明,新社会运动在短期内仍无法撼动资本主义制度。原因如下: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在不断进行改良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利用制度化减缓社会运动带来的冲击。社会运动制度化暂时减缓了它们的压力,它们也在努力促进这种制度化的形成。只要能够将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保持在非暴力状态之中,将运动参与者的诉求纳入制度化轨道,成为体制内的政治表达,使其在国家政治发展中发挥可控的作用和影响,至少暂时可减缓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因此,许多西方国家在促使社会运动制度化方面一直秉承着较为积极的理念,这也是新社会运动出现制度化趋势的深层原因之一。而且,一个国家面对挑战现存制度的社会运动,能否将其制度化,或者能否在不伤及制度体制、价值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和开放自己的政治体系,将其纳入体系之中,使之在可控的范围和趋势内发展,这检验着国家和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这些国家都不想在这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低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基本制度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容纳力。在德国生态环保运动中诞生的绿党,从最初的挑战者角色最终进入国家政治体制,成为国内三个重要政党之一,并且成为联合执政党的事实就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是在付出了较大代价之后才保持了制度的相对稳定,在抗议金融危机运动中,意大利、希腊等国都是在社会运动的冲击下,付出了政府解散、政党轮替的代价才消解了社会运动的冲击,暂时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政党体制和民主制度也在不断调整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努力降低社会运动带来的挑战。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繁爆发对传统政党体制和执政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阶层结构日趋复杂、阶级意识日益淡化的背景下,传统的依靠阶级主体支持的政党体制和执政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尤其是随着新社会运动影响领域的日益拓展,执政党为稳定政局,不得不调整传统理念,转变执政方式,扩展阶层基础,采取“中性政治”改革措施。因此,转变传统的认同方式和执政方式,将抗议和异己力量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成为执政党的最优选择。政党体制的这种改变,对社会运动也产生了影响,使得“同政党建立密切关系是社会运动实现制度化的重要渠道之一”[13]。同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改变了社会运动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从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实践看,各种抗议性运动更可能发生在民主制度下,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甚至有这样的判断——世界上大部分社会运动发生在“强能力的民主政权”[14](P71)之中。实际上,这对执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须具备在现有民主体制下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
(三)制度化趋势推动了危机应对体系的完善却无法根除危机
总体看来,各种社会运动的爆发,本质上仍是社会危机的一种体现。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危机管理及风险应对等方面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论认识和较为系统的实践举措。新社会运动的深度发展和制度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危机管理意识的形成和管理体制的完善,但是,无论怎样的危机应对体系都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危机。
乌尔里希·贝克等学者从社会危机管理以及风险社会产生根源入手,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危机与风险,以及这些危机与风险如何促进了危机管理意识的提高和管理体制的形成。1992年,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走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风险在于全球化的推进和后现代状态的形成,这些因素加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是一个“风险社会”或者已进入“风险时代”。斯科特·拉什指出:“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实际上促成了各种风险的大量产生,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生态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已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此同时,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制度和规范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继续导致各种风险的形成。”[15]他们还认为,由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现代社会还将不断产生新的更大的风险。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管理,我们还可以从哈贝马斯有关政治危机的观点中得到启示。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密切相关,政治危机会导致或加重社会危机。因此,加强对政治危机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对社会危机管理的重视。他强调,政治危机包括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合理性危机是由行政机关等国家机器无法有效和高效地履行经济职能所造成的,属于行政管理能力危机。他说:“公共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缺乏意味着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国家机器不能有效地调节经济系统。”[16](P47)关于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问题》等论著中对这一危机形式做了详尽的论述:“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行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7](P184)合法化危机表现为一种社会认同感危机,是公众对现存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信任度降低,属于忠诚度不足方面的危机。他说:“合法化的缺乏意味着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将规范结构维持或建立在所要求的范围上。”[18](P47)依据对这些风险社会和危机理论的认识,在新社会运动的不断冲击下,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应对措施亦不断完善,社会运动制度化,即是在危机管理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采取的有效应对策略之一。
从表面上看,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危机应对意识的提高和应对举措的加强,新社会运动制度化似乎意味着它被资本主义体制收纳了,实际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己力量,新社会运动这种制度化趋势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通过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存在时间的延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社会力量,新社会运动制度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削弱作用不可低估。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社会运动的街头抗争只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一个凸显阶段,各种运动背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制度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无法被彻底根除。虽然某一次或某一时期的抗议运动不会使资本主义制度伤筋动骨,反而会促使其不断调整并完善危机应对机制,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会因为应对机制的完善而得到彻底消除,反而会因为实施这些短期措施而掩盖深层危机,表面上看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深层危机却在继续发展。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意味着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会长期发挥削弱作用,这一切最终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社会运动的压力不得不进行改良和调整,它为维持制度的存在而不得不采取有利于更多人利益的举措,这些政策和措施往往带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因素不断积累,由量变到质变,进而产生社会制度的更迭和社会形态的进步是可以预期的。
虽然新社会运动存在制度化趋势,但从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会被制度化。一方面,一场社会抗议运动的产生原因、发生背景、抗议主体、宗旨目标、组织结构、动员形式都会对其能否出现制度化产生相应影响;另一方面,某一时期政府的观念立场、执政状况和社会压力都会对其是否选择与社会运动媾和有较大影响。这些复杂因素会导致某些社会运动几乎不存在制度化的可能。英国撒切尔时期出现了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罢工工人立场很坚定,而撒切尔政府也绝不妥协,最终以抗议行动失败而宣告罢工结束,英国矿工工会的政治权力被部分剥夺,其影响力也被极大地削弱。由此可见,社会运动制度化是社会运动各要素和国家制度各要素在某些层面或某一阶段出现目标和利益认同的结果,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体制构建目标和社会运动的诉求目标互动博弈的过程,如果博弈过程破裂,社会运动就不存在制度化的可能。
四、对新社会运动发展趋势的展望
新社会运动虽然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最具有上升潜力、影响最大的一种社会运动,但在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之后,当前它正遭遇发展困境。其主要表现为理论基础庞杂、发展路径不清晰、主导力量不明确、组织形式不规范、抗议手段低效率等。只有直面发展困境,深入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新社会运动才有未来。从发展趋势上看,除了本文分析的制度化趋势之外,新社会运动还可能走向组织化、非暴力化和全球化,同时,它还存在与社会主义运动联动的趋势和可能。
第一,组织化趋势。相对于20世纪中后期的新社会运动,21世纪出现的以反对金融危机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表现出了较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尤其是以反抗政府及其政策为目标的一些抗议运动的组织性越来越强。各国的在野党、左翼党派、工会及一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运动中的组织作用有回归和加强的趋势。近些年多次出现的法国大罢工的主要策划者就是法国联合工会,它确定了罢工计划和抗议目标,并制定了具体罢工方案。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同样展示了运动组织化的威力。
第二,非暴力化趋势。新社会运动主张采取以非暴力和文明表达为特征的抗议方式。多数新社会运动参与者都反对采用暴力手段实现其诉求,摒弃传统工人阶级的武力反抗或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等暴力手段。“非暴力主义”正在成为新社会运动中各团体、各组织不约而同采取的行为原则和斗争策略,在发展走势上,这种非暴力趋势将更为明显。
第三,全球化趋势。全球化因素对新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尤其是新社会运动高度关注的一些问题,如移民问题、生态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已经跨越国界,因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社会运动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的趋势。这一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呈现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国联合的反全球化运动。二是民族国家内的各种社会运动同样也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那些受到全球化影响的个人、组织和团体都在努力寻找自身的定位,包括寻找国家和社会在全球化中的发展方向,同时努力通过社会参与引导全球化进程朝着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四,与社会主义联动趋势。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可能会走向联动。一方面,虽然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弱化了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构成了挑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以自身独具特色的现实表现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同时,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新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和诉求目标中也存在一些缺陷,显然,它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引导。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运动要继续发展,就应吸纳新的思想理念和行动方式,并构建与新社会运动的密切联系。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确定自己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新社会运动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主要承接者。这两方面因素表明,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需要,存在联动发展的趋势。正因为如此,新社会运动的未来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之间,展现出密切关系和多种可能。
[1] Hank,J.and M.Alberlt.NewSocial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5] 《大辞海·政治学、社会学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6] Marco G.Giugni, and P.Florence.“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mplex Societies: New Social Movements betwee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Marco G.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FromContentiontoDemocracy.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1998.
[7]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 Patricia L.H.“Democratic Transition as Protest Cycles: 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in Democratizing Latin America”.In David S.Meyer and Sidney Tarrow.TheSocialMovementSociety:ContentiousPoliticsforaNewCentury.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8.
[9] 唐昊:《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可能》,载《南风窗》,2015(1)。
[10] David S.Meyer.ThePoliticofProtest:SocialMovementsin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William A.Gamson.“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Marco G.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FromContentiontoDemocracy.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12][13] 丁晔:《从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9)。
[14] 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5]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
[16][18] Habermas, J.Legitimation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17]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林 间)
An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of New Social Movement in the West
MENG Xin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lism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91)
New social movement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social movement in the West.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rce to shape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one of its trends of development.The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movement is in essence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goal of stat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target of social movement.The process not only transforms social movement, but also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state system and social crisis governing mechanism.In terms of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nearly half a century,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did not change the protest attribute or the reform objective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It is still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with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ism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new social movement; state system;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孟鑫: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