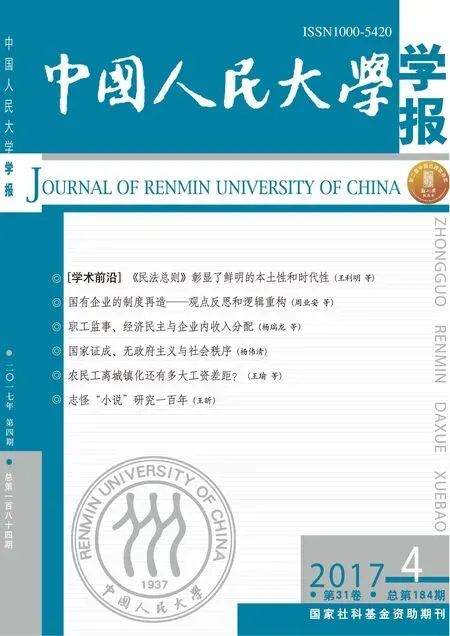试论《民法总则》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王利明
试论《民法总则》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王利明
《民法总则》第109条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做出规定,彰显了21世纪民法的时代精神,强化了人文关怀,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公民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水平。该条关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具有一般人格权的规范属性,体现了人格尊严平等保护的价值理念,具有承接和实施宪法的功能,明确了人格权保护的价值基础。该条也为未来民法典编纂指明了方向。为了进一步强化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应当加强人格权立法,在民法典中构建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
民法总则;人格尊严;人格权;民法典编纂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这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法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该条首次从宏观层面对“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做了规定,在学理上被理解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该规定宣示了人格权制度的立法目的与根本价值,即尊重与保护个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这一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中国现代民事立法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这一规定不仅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公民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水平,而且为我国后续的民法典编纂工程提供了基础性指引。
一、《民法总则》宣示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彰显了21世纪民法的时代精神
人格尊严,是指人作为法律主体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格尊严是人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基本前提,应当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1](P337),各国通常使用“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这一表述取代人格尊严(personal dignity)。从语义上看,人格尊严与人的尊严虽然具有相似性,但人的尊严在内涵上不仅包括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保护,还包括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而人格尊严的内涵则相对狭窄。我国法律历来采用“人格尊严”而非“人的尊严”的表述。从比较法上看,现代民法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主体性的承认和保护。这就是说,法律首先应当确认人的主体性地位,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不能被当成工具,更不能被当做客体来对待。二是对人格尊严的平等保护。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在主体性方面并没有差别,不存在三六九等或者贵贱之分。三是完整性保护。法律应当全面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现代意义上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不仅在消极意义上要求国家不损害个人尊严,还要求为个人尊严的实现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和可能。[2]民法不仅保护物质性人格权,还保护精神性人格权,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贯穿个人的一生,充分体现了民法的人文关怀理念。
《民法总则》宣示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是我国长期立法经验的总结。新中国建立后,“五四宪法”虽然规定了人格自由,但并未规定人格尊严的保护。*参见1954年《宪法》第89条。“文化大革命”期间,“冤狱遍及全国,屠夫弹冠相庆”,诸如“戴高帽”、“架飞机”、“剃阴阳头”、擅自抄家、揪斗等严重侵害个人人格权、践踏人格尊严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侮辱人格、蔑视人权的行径使广大人民群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正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暴行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才规定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该法第 3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了具体落实这一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从该条规定来看,虽然使用了“人格尊严”这一表述,但其主要是对“名誉权”等有限类型人格权的概括,而没有在法律上将其上升到一般人格权的高度。《民法通则》虽然第一次以专节的形式系统全面地规定了人格权,但准确地说,这一时期关于“人格尊严”的讨论主要还处于对各类具体人格权的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尚未认识到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在民法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
《民法总则》总结我国人格权保护的实践,宣示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彰显了21世纪民法的时代精神。我们要制定的民法典是21世纪的民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可以被称为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可以说是20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我们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则应当成为21世纪互联网时代民法典的代表。21世纪也是互联网、高科技时代,但科学技术一旦被滥用,就可能对个人隐私等人格权带来现实威胁。所有这些高科技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就是对个人隐私和人格权的威胁。谈到隐私权时,有美国学者曾经提出“零隐权”(zero privacy)概念,认为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已经无处藏身,隐私暴露不可避免。所有高科技发明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都面临着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从而对个人隐私和隐私权保护构成威胁[3],这就更需要将对人的保护提到更高程度。《民法总则》宣示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彰显了21世纪弘扬人格尊严与价值的时代精神,突出体现了对个人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尊重。
《民法总则》宣示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体现了民法的本质和功能。“私法的基本概念是人(Person)”[4](P20),民法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称为人法。现代民法应当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关爱人、尊重人、爱护人,就像黑格尔所说的,“让人成其为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进入21世纪之后,尊重与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民法关注的重心。民法不仅要尊重个人的主体地位,而且要充分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民法本质上是人法,其目标是服务于人的发展。民法的这种精神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华文化强调人本精神,儒学提倡“仁者爱人”,其实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精神。今天,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更加注重维护其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适应这种需要,《民法总则》第109条确认了保护人格尊严的条款,这也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保障个人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一部充分关爱人、保护人的民法典才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因此,《民法总则》关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彰显了民法的本质特征。
《民法总则》宣示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必然要求建构和完善人格权保护体系。《民法总则》是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对人格权做出的规定,《民法总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正式确认了隐私权。《民法总则》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二是确认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其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包括个人身份、家庭、财产、工作、健康等各方面的信息。三是确认了对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保护。《民法总则》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对于淳化社会风气,弘扬社会正气,促进整个社会尊崇英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四是对人格利益提供全面的兜底保护。《民法总则》第109条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对人格利益进行兜底保护的条款,有利于适应未来人格利益发展的需要。《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都彰显了人格尊严的价值,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平等保护。《民法总则》第109条关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该法将人格尊严放在所有民事权利之首加以规定,也反映了人格尊严是所有民事权利的价值来源和基础。法律保护个人的各种民事权利,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
《民法总则》宣示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彰显了整个民法典的时代性,既为整个民法典的编纂工程奠定了价值底色,也为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价值指引。
二、《民法总则》保护人格尊严条款的基本功能
(一)承接和实施宪法的功能
《民法总则》规定人格尊严条款具有承接宪法基本价值取向的功能。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法和最高法的地位,《宪法》第38条确认的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的原则,应成为各个法律部门都必须予以保护的价值。也就是说,各部门法应当通过制度的建构,具体落实宪法保护人格尊严的精神。《民法总则》开宗明义地宣告,要“根据宪法,制订本法”,并规定人格尊严条款,实际上是对宪法“人格尊严”保护规则的一种具体化,具有承接宪法规则的意义。也就是说,宪法所确认的保护人格尊严的原则必须通过民法具体予以落实:宪法虽然规定了对人格尊严进行保护,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规则往往是粗线条的,具有高度抽象性,许多规定,尤其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还有待于各个部门法的具体落实。[5]宪法中的人格尊严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价值表述和价值指引,无法保证裁判具有相对的确定性,难以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基本正义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予以细化,确定各项人格权的内容和保护范围,将之具体化为能被裁判所适用的有效性规则。《民法总则》对人格尊严保护做出规定,就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尤其应当看到,在我国,宪法不具有可司法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法官在裁判时不能直接援引宪法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4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这就排除了法官在个案中直接通过宪法保护人格尊严的可能。《民法总则》中规定人格尊严保护条款,既具有价值宣示功能,也可作为裁判依据,这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宪法保护人格尊严的立法目的。
(二)提供价值来源和价值指引的功能
《民法总则》采用概括性条款保护人格尊严,具有宣示保护人格尊严和提供价值指引的功能。人格权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各项人格权都体现了人格尊严的保护要求。事实上,许多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如污辱和诽谤他人、毁损他人肖像、传播他人隐私、抽打他人耳光等,均损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从比较法上看,一些国家将人格尊严保护提高到了基本法的层面,如《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第2条就明确规定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该法第1条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第2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或不违反宪政秩序或道德规范者为限。”据此,维护人格尊严在德国被认为是宪法的最高建构原则,也是战后整个德国法秩序的价值基础。[6](P119)《日本民法典》则将人格尊严保护规定为立法目的与宗旨,该法第1条之二规定:“本法须以个人的尊严及男女两性本质性平等为宗旨解释。”其将个人尊严作为解释民法典规则的基础,表明私权本身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尊严,尊严是私权的基础和依归,这实际上是将人格尊严保护作为民法典规则的价值基础。我国《民法总则》将人格尊严保护规定在民事权利之首,其实也宣示了其在民事权利中的价值基础地位。
《民法总则》将人格尊严保护置于各项民事权利之首加以规定,表明人格尊严作为保护民事权利的价值来源和价值基础,也表明其具有最高价值。在法律上,人格尊严是人格权民法保护的核心要素[7](P568),具有绝对性和不可克减性。例如,关于尊严原则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关系,欧洲理事会1997年奥维多公约(《关于人权与生物医学的公约》)第2条即开宗明义地宣称:基于人格尊严原则,“个人的利益和福祉高于单纯的科学利益或社会利益”。科学技术本身是一种工具,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第3 条也规定了同样的内容。可见,人格尊严作为法律秩序的最高价值,具有绝对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牺牲人格尊严为代价去保护其他价值,有学者甚至认为,人格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高于生命权的地位,因为即便在保留死刑的国家,生命权可以被合法剥夺,但人格尊严并不能被剥夺。[9](P397)
(三)人格权益保护的兜底功能
保护人格尊严也可以为人格权提供兜底保护,《民法总则》关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也可以形成权利保护的兜底条款。人格权具有法定性,具体人格权的类型都是由法律规定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型人格利益不断出现,很难通过已有的具体人格权类型予以保护。[10](P30)这就需要借助人格尊严保护规则弥补既有具体人格权规则的不足。例如,在“某超市搜身案”中,某超市的一名保安怀疑某消费者在超市偷拿财物,对其强行搜身,该行为虽然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但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参见“钱缘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搜身侵犯名誉权案”,(1998)虹民初字第2681号,(1998)沪二中民终字第2300号。再如,在另外一起案件中,行为人在受害人举行结婚仪式前,故意将垃圾泼撒在其家门口,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精神损失。*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济民一初字第238号。该案实际上也是侵害人格尊严的纠纷。实践中,许多损害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如就业歧视、有偿代孕等,都难以通过现有的具体人格权予以保护,当出现这些新类型的案件时,首先要用是否侵害人格尊严作为评价标准,如果构成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侵害,则权利人应当受到人格权法的救济,行为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人格尊严的内涵具有开放性,可以为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实现对人格权益的兜底保护。
(四)提升人格权保护水平的功能
对人的关怀不仅需要在静态层面实现对现有人格利益的确认和保护,还要在动态层面充分认识和维护个人人格的自由成长和发展。《民法总则》广泛确认了个人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益,增设了胎儿利益保护规则、成年监护制度、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保护规则等,实现对人“从摇篮到坟墓”各个阶段的保护,每个人都将在民法慈母般爱抚的目光下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在每个阶段都进一步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民法总则》对人格尊严保护做出规定,可以为民法典相关规则的设计和解释提供价值指引,从而提升人格权保护的水平。例如,《民法总则》关于监护制度的构建,改变了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立法禁治产制度仅将被监护人作为管理对象的做法,而真正尊重被监护人的主体地位,维护其人格尊严,这些都有利于尽可能地尊重被监护人的意志和利益。
三、人格尊严具有一般人格权的属性
(一)人格尊严不属于具体人格权
所谓具体人格权,是指由法律确认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具体的人格权利。关于人格尊严是否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值得探讨。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使用了“人格尊严权”的表述,但从《民法总则》第109条的规定来看,其并没有使用“人格尊严权”的表述,而只是使用了“人格尊严”的表述。笔者认为,人格尊严在性质上并不是一项具体人格权,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将人格尊严界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会不当降低其法律地位。如前所述,人格尊严是各项民事权利的价值来源和价值基础,是其他民事权利的母体,将其界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则会弱化其地位和价值。事实上,《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在保护人格尊严时虽然使用了“人格尊严权”这一表述,但该司法解释起草人认为,此处的“人格尊严”应当被理解为“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一般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功能上具有弥补具体人格权类型列举不足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可以以一般人格权对个人的人格利益进行兜底保护。[11][12](P125)例如,名誉权保护个人的社会评价,但并不保护个人的名誉感,这就可以借助人格尊严保护规则对其进行补充保护。[13](P30)
第二,将人格尊严界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不利于发挥人格尊严条款的补充功能。人格尊严条款具有弥补具体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不足的功能[14](P8),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新型的人格利益不断出现,但还难以将其与其他人格利益进行明确区分,与相关权利的关系也不清晰,能否上升为具体人格权也不明确,不应过早赋予其权利的地位,这就需要借助人格尊严对其提供保护。例如,我国法律很长时间一直未确认隐私权的概念,法律经常采用“尊重隐私”等表述,表明立法只是将隐私作为一种利益而非权利,但由于法律没有确认其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实践中主要通过名誉权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直至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2条才正式规定了隐私权。如果将人格尊严规定为一种权利,这类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就不需要类推适用某具体人格权的规则,而可以直接适用人格尊严保护条款,这就可以起到保护新型人格利益的作用。
第三,将人格尊严界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也存在法律技术上的难题。一方面,人格尊严保护的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成为人类共同体成员的基本的价值,这也是法律所保护的最基础的法益,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人格利益,很难将其认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另一方面,将人格尊严界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也会使其与其他具体人格权在内涵上存在一定交叉,难以进行区分。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实际上都体现了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保护。例如,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本质上都保护了个人的人格尊严。因此,将人格尊严界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将面临诸多立法技术和解释上的困难。
(二)人格尊严具有一般人格权的属性
从人格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人格尊严保护与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关系密切。一般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产生于德国。1866年,德国学者诺依内尔(Georg Carl Neuner)提出了人格权的概念,并且将人格权界定为个人主张自我目的并且展开自我目的的权利。有学者认为其属于最早有关一般人格权的理论。[15](P12)1895年,德国学者基尔克(Gierke)在《德国私法》一书中强烈呼吁,应当在法律上规定一般人格权。不过,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并没有接受这一观点,而只是规定了姓名权(第12条)以及生命、健康、身体(第823条第1款)等人格利益的保护。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法逐步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尤其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了对人的尊严的保护,这也促进了人格权理论的发展。在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中,法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将受害人置于一种错误的事实状态中,可能使读者误以为其同情纳粹,这实际上是侵害了原告的人格。法院最终基于宪法的保护功能,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推导出了一般人格权。*Schacht-Brief Decision, 13BGHZ 334 (1954).有关本案的介绍,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805-80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从‘人格尊严’这一最高宪法原则的意义上来说,并不能够直接得出传统意义上对自由的保护,但是从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格保护的需要来说,(一般人格权)存在其出现的必要性。”*BVerfGE 54, 148 [153].可见,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
我国《民法通则》以专节(第五章第四节)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各种具体的人格权,成为《民法通则》的一大亮点,但该法并没有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因而使得对人格权的保护并不周延,不能适应人格权制度不断发展的需要。王泽鉴先生认为,我国《民法通则》通过具体列举的方式规定人格权,对人格权的保护较欠周全,而且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因此很难在自由、贞操、隐私等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予以救济。[16](P293)从我国现实需要来看,也急需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由于具体人格权制度仅对特殊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如对名誉、肖像、姓名等权利的保护,这显然是不够的。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格利益虽然不属于具体人格权,但从维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出发,又需要保护此种利益。
《民法总则》第109条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做出规定,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了一般人格权,确立一般人格权,有利于保持人格权法的开放性,提升对各种新型人格利益的周密保护。一方面,人格利益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尤其是随着现代生活和科技的发展,新型人格将不断出现。目前虽然采取法定主义,但人格权的内容通过具体的列举是难以穷尽的,而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则能够为新型人格利益提供可能的保护。另一方面,肯定一般人格权也有利于规范法官在认定与保护新型人格利益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在保护新型人格利益时创设了一些新型权利,如亲吻权*参见“陶莉萍诉吴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2001)广汉民初字第832号。、悼念权(祭奠权)*参见“崔妍诉崔淑芳侵犯祭奠权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7)丰民初字第08923号,载《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引发了不少争议。如果肯定一般人格权,并借助其与人格尊严的关联性来认定新型人格利益,则可以有效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此外,肯定一般人格权,也有利于克服立法的缺陷,为各种人格利益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例如,《民法总则》第185条规定了英雄、烈士等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但是英烈以外的人格利益如何保护,以及英烈自身的除该条所列举的四种人格利益外,其隐私等人格利益如何保护,则缺乏法律依据。在此可以考虑援引《民法总则》第109条关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则,这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兜底保护的效果。当然,由于一般人格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存在具体人格权时,必须首先适用具体人格权,不能直接适用一般人格权,这就需要排除一般人格权的滥用,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安全性。《民法总则》保护人格尊严条款具有一般条款的功能,能够在保护人格尊严的具体法律适用过程中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四、人格尊严具有平等性
从人格尊严的固有属性来看,尊严本身就具有平等性。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个体,应当受到平等对待,这也是黑格尔所说的使人真正“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17](P46)。尊严受法律平等保护也是康德“人是目的”思想的引申,康德认为人格尊严属于“绝对律令(categorical operatives)”[18],这一思想明确包含了人格尊严受平等尊重的内涵,康德也因此被称为“人的尊严概念的现代之父”(the father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human dignity )[19]。
尊严在国际人权文件与各国宪法中有不同称谓,诸如人的尊严、人格尊严、人性尊严与人类尊严,但都表达了人人平等享有尊严的含义。正如法国学者Molfessis所指出的:“人从来不是其尊严的权利主体……因为尊严所体现的是人之为人的属性,而非每一个具有不同特点的个体的属性。强调存在着一种尊严获得他人尊重的权利,这将导致产生一种新的权利,它与我们所认为的人的尊严可能并无关系。尊严是人的内在条件,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它并不因主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P129)由此可见,确认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实际上就是强调平等保护每个人的尊严,意在强调平等保护的价值。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民法总则》第109条在规定人格尊严保护时并没有使用“平等”这一表述,但仍应当认定其中包含人格尊严平等性的内涵,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我国《民法总则》第109条的人格尊严保护规则源自于宪法规范,宪法在确认个人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时,基于维护社会交往秩序的目的,要求平等保护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也就是说,就人格尊严的保护而言,人生而平等,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和他人的平等对待。另一方面,我国法上人格尊严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应当考虑我国特定的语境。1982年《宪法》第38条规定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其实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进行反思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于人的不同政治身份而导致的歧视和迫害,使个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践踏。因此,1982年《宪法》规定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其实是在反对这种对个人尊严的践踏,意在宣告人格尊严受法律平等保护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任何人,无论其财产多寡,政治地位高低,也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其人格和尊严价值都是平等的,都要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人格尊严的平等保护,既是法治社会的应有内容,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然要求。《民法总则》第109条肯定人格尊严的平等保护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第一,在立法层面,要基于平等维护每个人的尊严的目的构建人格权法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说,我国民法典应当按照人格尊严平等保护的原则构建人格权制度体系。例如,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现在各国法律普遍确认个人信息权,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所蕴含的财产价值,而更在于保护每个人对其信息的平等支配权,每个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都享有平等的不受他人非法利用、处理、非法转让的权利,任何人收集、利用、存储和处理他人信息时都应当依法进行。*参见《欧盟数据保护一般规范(EU-DSGVO)》第6条。即便是对某个流浪汉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也必须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范,获得其同意。应当指出的是,某些人格权尤其是隐私权,具有内容上的可限制性,但法律在做出限制时,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民事主体,而不能仅针对某一类人做出限制。例如,在信息公开时,不能因为性别差异而对女性做出歧视性的对待。基于个人人格尊严的平等性,对个人人格权的限制应当依法进行,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额外的限制条件。例如,在对公众人物人格权进行限制时,应当严格依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该限制不得违反人格平等原则。
第二,在司法层面,要基于平等维护每个人人格尊严的目的切实保护个人的人格权。在人格权受到侵害后,受害人享有平等地获得保护的权利。《民法总则》第179条所规定的“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方式,都可以适用于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形,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就是专门针对人格权的救济方式。正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只有通过平等的保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平等。具体来说,在人格权被侵害时,受害人都应当享有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从而维护人格权的完整状态,恢复受侵害的权利。按照人格尊严平等保护规则,在人格权受到侵害时,个人所能够援引的法律规则应当是相同的,对于类似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权利人也应当获得类似的法律救济。
第三,在解释层面,应当基于人格尊严平等原则解释相关的规则,禁止人格歧视。例如,近年来发生的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否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是否应当使女性和男性享有同样的机会,以及对女性公务员求职是否应该进行性病检查等等纠纷[21],都涉及人格权的平等保护问题。对于此类纠纷,应当基于人格尊严平等解释相关规则、确定其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也采取了此种做法。例如,在“高彬诉北京敦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酒吧工作人员以原告“面容不太好,怕影响店中生意”为由而拒绝其入内。法院认定,被告因原告“外形不好”而拒绝其进入消费属不当的人格歧视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22]这一判决是合理的。当然,某些俱乐部专门以特定类型的社会群体作为服务对象,如女子健身俱乐部等,并没有包含对特定个人的人格歧视,因而并不违反人格平等原则,也不构成人格歧视。
《民法总则》人格尊严保护规则虽然蕴含了平等保护的内涵,而且对立法、司法以及法律解释均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格尊严保护规则可以代替平等原则,因为二者的目的和功能存在一定的差别:平等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禁止歧视和没有任何理由的差别待遇问题,其主要适用于社会法领域;而人格尊严保护规则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我决定,防止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与侵害,其人道价值更为突出,主要适用于生命伦理法领域。在民法领域,平等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适用于整个民法,而人格尊严保护主要适用于对个人尊严的保护领域,在适用范围上要小于平等原则。
五、保护人格尊严应当使人格权独立成编
《民法总则》第109条的人格尊严保护规则也为未来民法典编纂指明了方向,为强化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应当进一步加强人格权立法,在民法典中构建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
《民法总则》虽然用三个条款(第109条、110条、185条)规定了人格权保护,但从总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来看,实际上,相对于世界发展趋势和现实的社会需要,还显得过于原则化,未能彰显全面保护人格权益的立法目的。要全面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显然不能认为总则的三个条文足以保护全部的人格利益。近几十年颁行的民法典,如1991年的《魁北克民法典》、2002年的《巴西民法典》、2009年的《罗马尼亚民法典》,都有十多个条文规定了人格权,这表明最新的立法趋势是进一步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即使和《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对于人格权的保护也是不够的,因为《民法通则》用了九个条文保护人格权。还要看到,《民法总则》第2条在确定民法的调整对象时,明确规定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并且将人身关系置于财产关系之前,可见,与《民法通则》第2条相比较,该条更凸显了对人身关系的重视。这实际上表明我国的民法典进一步强化了对人身权益的保护。财产关系已经在分则中分别独立成编,表现为物权、合同债权,而人身关系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身份关系将表现为婚姻、继承,人格关系则没有对应设编,因此,人格权不能独立成编成为民法典体系的一大缺陷。
人格权独立设编首先是保障每个人人格尊严的需要。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此背景下,我们不仅要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富足,也要使每个人活得有尊严,维护尊严本身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人类社会已进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以及各种高科技的发明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个人人格权的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23]人格权独立设编也有利于回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需要。在实践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人肉搜索泛滥,网上不少博客辱骂诽谤他人。所谓网络谣言,很多涉及对人格权的侵害,这些行为也污染了网络空间。还有人非法跟踪、窃听、性骚扰、非法侵入他人邮箱等等,这些行为都侵犯了他人人格权。还有的贩卖个人信息,严重侵害个人信息权。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人格权保护事业任重道远。因此,需要在民法法典化进程中加强人格权立法,这是21世纪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体现,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人权方面的立法的要求”的具体举措。
人格权独立设编与《民法通则》的立法经验是一脉相承的。《民法通则》以专节的形式单独对人格权做出规定,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先进的立法经验,这也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奠定了基础。为了维持立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继承和总结《民法通则》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在民法典中专设人格权一编,这实际上也是我国立法的一贯做法。例如,2002年的民法典草案也已经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一立法经验应当继续延续。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在拟订的民法典分则中,将要制订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侵权责任法也不能替代人格权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侵权责任法主要是救济法,并不具有确权功能,不能从正面确认各项具体人格权。而人格权法是权利法,具有从正面规定各项人格权内容的功能。只有通过人格权法才能规定各类人格权及其内容、效力等,从而为侵权法的救济提供基础。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颁行了“姓名权立法解释”,该解释对姓名权的内涵、效力等规则做出规定,这些规则属于证明确权性质的规定,而不属于侵权保护的问题,难以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不能具体规定各项人格权的具体内容。每一种具体人格权都具有自身的作用或功能,这些权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例如,隐私权的内容较为复杂,可以类型化为多种权利,包括独处的权利、个人生活秘密的权利、通信自由、私人生活安宁、住宅隐私等等。就私人生活秘密而言,又可以进一步分类为身体隐私、个人信息隐私、家庭隐私、基因隐私、健康隐私等。还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隐私利益在权利内容及侵权构成要件上都可能有所差异。因此,只有制定人格权法,才能全面确认人格权的各项具体内容,从而满足人格权私权行使和保护的需求。此外,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无法规定人格权的利用、行使等规则。尽管人格权原则上不能转让,但权利人可以通过许可使用等方式,对其人格权进行利用。例如,权利人可以许可他人利用其肖像权。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颁行虽然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但这不应影响人格权法的制定和颁行。相反,为了配合侵权责任法共同实现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应当制定独立的人格权法。
《民法总则》第109条对人格尊严的保护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美好的生活不仅要求丰衣足食,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而且要求活得有尊严。“中国梦”也是个人尊严梦,是对人民有尊严生活的期许。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当让每个中国人有尊严地生活,让人格尊严作为基本人权受到法律保障。
[1] 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2][19] 郑贤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辨》,载《中国法学》,2012(2)。
[3][23] A. Michael Froomkin. “Cyberspace and Privacy. A New legal Paradigm? The Death of Privacy?”.StanfordLawReview, 2000,52(5).
[4]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5]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Grundrechtstheorie und Grundrechtsinterpretation”.NeueJuristischeWochenschrift, 1974(35).
[6] Dürig. “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In Peter Badura, Rüdiger Breuer, Horst Ehmke, Jochen Abr,Frowein,Peter Häberle, Peter Lerche, Gerhard Robbers.ArchivdesöffentlichenRechts.Tübingen:Mohr Siebeck,2014.
[7] Gert Brüggemeier, Aurelia Colombi Ciacchi, Patrick O. Callaghan.PersonalityRightsinEuropeanTort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8] 王卫国:《技术理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载《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3)。
[9] Patrick Fraisseix:“la protection de la dignité de la personne et de l’espèce humaines dans le domaine de la biomédecine: l’exemple de la Convention d’Oviedo”.Revueinternationalededroitcomparé, 2000(2).
[10][13] 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11] 陈现杰:《人格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步和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1-03-28。
[12] 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4] 杨立新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 Stefan Gottwald.DasallgemeinePersönlichkeitsrecht:einzeitgeschichtlichesErklärungsmodell. Berlin: Verlag Arno Spitz, 1996.
[16]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0] N. Molfessis.“Le respect de la dignité de la personne humaine en droit civil”. In Thierry Revet (dir.).Lerespectdeladignitédelapersonnehumaine.Paris: Economica, 1999.
[21] 《女公务员录用查性病被指间接歧视》,载《京华时报》,2012-03-20。
[22] 刘心稳、亓培冰:《“人格歧视”离我们有多远?》,载《人民法院报》,2002-05-21。
(责任编辑 李 理)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byGeneralProvisionsoftheCivilLawofChina
WANG Li-ming
(School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of China Article 109 stipulates that natural persons’ personal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legally protected.This articl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 of humanism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helps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a.As the general clause of personality rights, this stipulation reflects the value and notion of equal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It not only follows and enforces the clause of human dignity in Chinese Constitution, but also points out the approach of China’s ongoing project of Civil Code compilation.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rights, China’s future Civil Code should include a separate book stipulating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personality rights.
GeneralProvisionsoftheCivilLawofChina; human dignity; personality rights;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王利明: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