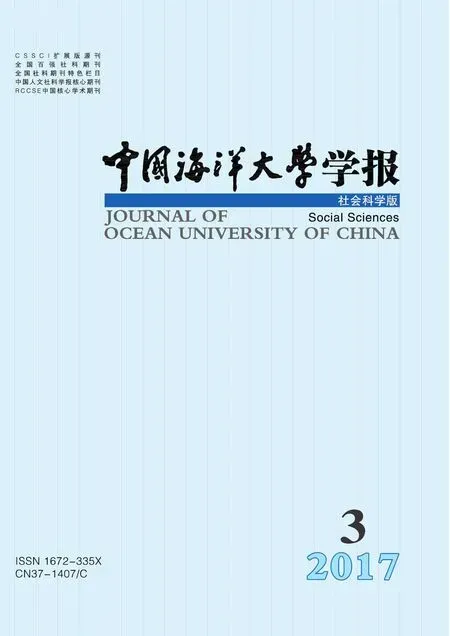鲁迅对“四库”评价的转向: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骆耀军
(1.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麦吉尔大学 东亚研究系,加拿大 蒙特利尔 H3A3R1)
鲁迅对“四库”评价的转向: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骆耀军1,2
(1.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麦吉尔大学 东亚研究系,加拿大 蒙特利尔 H3A3R1)
仔细研读鲁迅著作、书信发现,以1934年为界,鲁迅对《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向,从最初的古籍善本上的学理探讨转向寓“古”讽“今”的批评。批评《四库全书》由最初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注意其是“钦定”,后期受国民政府文网禁令的影响而放大为“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态度,同时鲁迅中国小说研究、古籍序跋等文字和论述又充满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风格。距乾隆四库开馆仅百余年时间,鲁迅等学者对“四库”书籍,顾宪成、袁宏道等明清士人评价的反转,站在现在的角度来反思民国时期以及接下来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批评或认同变化,是值得深挖的。
鲁迅;《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转向
鲁迅与《四库全书》的关系,从任教育部科长时为让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而积极奔走始,到《鲁迅全集》中众多提及《四库全书》的记载,都呈现出二者有着极深的关系。李希泌、崔石岗等学人有文章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论述,*参看李希泌的《鲁迅与图书馆(1912-1919)》(《国家图书馆学刊》,1979年第1期,第92-98页)和崔石岗的《鲁迅与<四库全书>》(《图书馆建设》,1997年第6期,第69-70页)等文章。提出的“鲁迅对《四库全书》基本上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1]“有理有据地对四库馆臣根据清朝统治的需要抽毁删改古籍文献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2]等论断已为大家接受的一般认识。实际上,仔细研读鲁迅著作,他对《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态度,自1934年民国政府成立图书杂志检查处后*民国政府此时期的图书杂志禁毁史料可以参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对于鲁迅创作的“钻网”策略,包子衍《文化“围剿”的阶段性与鲁迅反“围剿”战术的演变》(《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第31-39页)、杨华丽《国民党治下的文网与鲁迅的钻网术——以1933-1935年为核心》(《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2期,第44-57页)等文章有严谨扎实的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鲁迅受时局风气的影响,使得其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从最初的古籍善本上的学理探讨转向寓“古”讽“今”的批评,造成此番差异的缘由,值得细细深究。就笔记目力所及,现今未见到结合鲁迅撰写的古籍序跋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之关系来专文讨论其对两书情感评判的分野问题,本文拟做一尝试,以方便后来研究。
一、由注意其是“钦定”的到“暗杀中国著作”
鲁迅1913年3月撰写的《谢承<后汉书>序》、《谢承<后汉书>考》等序跋、提要未能看出是否查阅《四库全书》或《四库提要》,较明显可以看出抄校古籍时翻检过《四库全书》的记载,是其从《说郛》中辑出《云谷杂记》时。1913年6月1日《日记》:“昨今两夜从《说郛》写出《云谷杂记》一卷,多为聚珍版本所无,惜颇有讹夺耳”,[3](P129)《<云谷杂记>跋》也说:“证以《大典》本,重见者廿五条,然小有殊异,余皆《大典》本所无。”[3](P129)到1914年3月11日《<云谷杂记>序》里,则说的更为明白:“《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皆不载。明《文渊阁书目》有之,云一册,然亦不传。清乾隆中,从《永乐大典》辑成四卷,见行于世。……《大典》本百二十余条,此卷重出大半,详略亦颇不同,各有意谊,殊不类转写讹异。”[3](P231)翻检《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四卷本《云谷杂记》,即为永乐大典本,且说:“此书《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不载,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册。其本久佚,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得一百十条”,[4](P1580)二者的文字叙述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字直接提及了乾隆时期辑出的四卷本,且说到相互对照了两版本之不同,可以说这是鲁迅利用《四库全书》进行辑佚、研究记录下的较早线索。当然,鲁迅文章直接评价《四库全书》,则要到1925年写《这个与那个·读经与读史》一文: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个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重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而猜闷壶卢。[5](P523-524)
从两种《茅亭客话》的不同发现《四库全书》的删改,鲁迅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书信中常提及:“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6](P277-278)还有一例就是,1927年9月的《谈“激烈”》一文,鲁迅直接抄引不同版本的《鸡肋编》的两条文献,以对比文澜阁本与元钞本的不同,“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7](P433)很明显地看出,鲁迅批评《四库全书》的着眼点,最初只是在于它是“钦定”的。对于“华夷”等字眼的删削、表达意见的含蓄委婉,鲁迅从学术研究出发,追求古籍善本,重在学术批评的立场上来观照《四库全书》。这在1933年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以库本还是旧刻本、钞本为底本的争论时,《四库全书珍本》一文表达得更彻底:
况且“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淹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8](P321-322)
鲁迅更强调的是不让“善本淹没下去”,认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对于影印的“珍本”,也认为有“无意的错字”和“故意的删改”,鲁迅是从学术研究中应该重视古籍善本的立场来看待库本的删改、讹误的,“‘善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8](P321)也就是直到此年,鲁迅都还没有把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寓禁于征”中的删禁效用进行发挥、放大论述。而且由这些文章里反复拈出的“钦定”二字,自然就联系上1930年《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十二种书中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简介了,“其实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需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9](P195)强调要注意批评是“钦定”的,这与鲁迅对《四库全书》的认知是一贯的,而且与民国学者在当时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也是一致的。当时开列的各种国学必读书目,只要胪列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都流露出推崇之意。梁启超的《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开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时说:“清乾隆间四裤馆,董其事者皆一时大学者,故所作提要,最称精审,读之可略见各书内容(中多偏至语自亦不能免)。”[10](P66)胡适出具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发端“工具之部”第二本书即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10](P73)汪辟疆在《读书举要》“纲领之部”也举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录》,并说:“所录各书,皆有极详细之提要。今先去其总序、小序读之,学术纲要,已略备具。再能进而阅提要全书,终身受益不浅矣。”[10](P130)此外,王云五“国学基本要籍书目”、陈锺凡“治国学书目”、邵祖平“国学应读各书要目”等皆列有《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书。诸多大师的选入缘由,或“使人一览了然”,[10](P151)或“可备求书之用”。[10](P44)鲁迅虽以“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5](P52)给《京报副刊》的推荐“青年必读书”交卷,1927年7月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谈》时更指出:“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看的书目”。[7](P375)实际上,鲁迅自己编纂的《采录小说史材料书目》就特别著录了“《四库全书总目》两百卷”,[11](P395)而且与其他55本书详细著录作者、成书年代不同,是书只标题名,独具一格,顾农认为:“估计是草拟、修订《中国小说史略》时编制的”。[12]也就是说,鲁迅对《四库全书总目》是十分熟稔的,自己用之为翻检工具书,并且也向许世瑛进行了推荐,这时候的出发点,大体仍是善本、学术的角度。
但是到了1934年上半年,民国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后,鲁迅发表的文字常常需经审查并被恣意删改,《鲁迅全集》里论述到《四库全书》时,批评的重点开始有意识地发生了转向,把乾隆时期的禁毁政策与民国政府的文网联系了起来,开始有意识地寓“古”讽“今”。
1934年12月31日夜,鲁迅在给刘炜明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言语:
今年设立的书报检查处,很有些“文学家”在那里面做官,他们虽然不会做文章,却会禁文章,真禁得什么话也不能说。现在如果我用真名,那是不要紧的,他们只将文章大删一通,删得连骨子也没有;新近给明年的《文学》写了一篇随笔,约七八千字,但给他们只删剩了一千余字,不能用了。……他们的理由是:这里特别禁止。[6](P317-318)
这里提到的《文学》杂志删稿的事情,即指《病后杂谈》一文。1935年1月8日鲁迅写信给郑振铎时也提及此事:“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年底做了一篇关于明末的随笔,去登《文学》(第一期),并无放肆之处,然而竟被删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了一个头,我要求将这头在第二期登出,聊以示众而已。”[13](P317-318)4月9日给日本的增田涉写信,仍不忘此次删稿之事,同时又谈到三月号刊稿被删之事:
中国日本之外,还有洋学者对《四库全书》如此关怀,实为不解。这次记述,只是一鳞半爪,如再详细研究,还可以发现很多不妥之处。并且还有取舍的不公,清初反满派的文集被舍弃,尚可以说是由于清朝之故,但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品也被排斥,这就说不过去。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甚大。
《文学》三月号刊出的拙作,也大被删削。现在国民党的做法,实在与满清时大致相同,也许当时的汉人就以这种做法告诉满人……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倘对此种情形没有仔细了解,就不免很隔膜了。[14](P497-498)
鲁迅这封信是为回复增田涉3月30日来信而作的,对于增田涉信中提及洋学者关注《四库全书》所指为何,今不得而知了。3月1日刊出的《文学》三月号文章,是指写于1934年12月17日写的《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6](P277-279)
根据写作时间可以发现,鲁迅把《四库全书》禁毁图书与时局删改书籍联系起来,大多是1934年书报检查处设立之后的事情。文章对《四库全书》的批评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苛。从一开始的只是从善本书的角度要注意是“钦定”的,这时候称其为“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之一,甚至是“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以及“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15](P266-267)单单谈到鲁迅著作被删禁之事,1934年开始的文章、书信和日记可以找到很多线索,如10月13日《致合众书店》说:“要将删余之《二心集》改名出版,以售去版权之作者,自无异议。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6](P87)、《致杨霁云》云:“近来有了检查会,好的作品,除自印之外,是不能出版的,如果要书店印,就得先送审查,删改一通,弄得不成样子,像一个人被拆去了骨头一样”,[6](P88)不胜枚举。如果沿着1930年书单里只拈出“钦定”二字的批评,可以发现,随着图书杂志检查及书籍删改政策的严密化,鲁迅不满《四库全书》的出发点,更多地转移到书籍禁毁之害上来。
二、小说研究、古籍序跋的“提要风格”
非常有趣的是,如上节所言,鲁迅最初是站在学术探讨的立场对待《四库全书》的“钦定”,后来受时局禁令的影响转向完全批评乾隆编撰《四库全书》的删改、禁毁行为,可是对《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却一直停留在“钦定”的态度,甚至还进行一定的辩解。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是:“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15](P265)对纪昀的评价,也是宽容居多,“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7](P458)个中缘由,大约是鲁迅内心里是接受和学习《四库全书总目》的,这方面除了前文提及的古籍序跋中明显利用《四库全书》比照、校刊的例证外,鲁迅的小说研究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来的更为深远。
1935年5月的《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开篇就说:“因为唐代传奇,是至今还有标本可见的,但现在之所谓六朝小说,我们所依据的只是从《新唐书·艺文志》以至清《四库书目》的判定,有许多种,在六朝当时,却并不视为小说。”[13](P312)而《中国小说史略》开篇讨论历来小说著录及论述时,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叙言,并认为“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16](P10)具体到小说文本的论述,受到《四库总目提要》论述影响的文字亦为不少,试以馆臣“小说类”首录的两部书《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为例:
今检书后有洪跋,称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有小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补《汉书》之阙”云云。伯思所说,盖据其文。案《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亦引为葛洪《西京杂记》,则指为葛洪者,实起于唐。故《旧唐书·经籍志》载此书,遂注曰:“晋葛洪撰。”然《酉阳杂俎·语资篇》别载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晁公武《读书志》亦称:“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盖即据段成式所载庾信语也。……然庾信指为吴均,别无他证。段成式所述信语,亦未见于他书,流传既久,未可遽更。今姑从原跋,兼题刘歆、葛洪姓名,以存其旧。其书诸志皆作二卷,今作六卷。据《书录解题》,盖宋人所分,今亦仍之。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17](P1835)
至于杂载人间琐事者,有《西京杂记》,本二卷,今六卷者宋人所分也。末有葛洪跋,言“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小有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以补《汉书》之阙。”然《隋志》不著撰人,《唐志》则云葛洪撰,可知当时皆不信为真出于歆。段成式(《西杂俎》《语资篇》)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后人因以为均作。然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然此乃判以史裁,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16](P39-40)
对于《西京杂记》,鲁迅言说次序所引证《汉书》《隋志》《唐志》《酉阳杂俎·语资篇》等皆与《四库总目提要》同,而馆臣提及的《酉阳杂俎·广动植篇》《历代名画记》及《直接书录解题》等书,《中国小说史略》进行了删节。最后对小说本身的评价,鲁迅着重提出文学欣赏的价值,而馆臣强调的史料性质,与黄省曾在《西京杂记序》中重史实仍是一贯的。
黄伯思《东观馀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今其本皆不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合。……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亟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17](P1836)
今存者三卷曰《世说新语》,……然不知何人又加新语二字,唐时则曰新书,殆以《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谬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郑重之。[16](P63)
两书论述《世说新语》的文字相似性已一目了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对鬼神志怪之说,往往黜落不录,但提要中流露出的评价,往往显示四库馆臣对此类杂史、小说之说十分熟悉,如“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4](P923)“非《山海经》、《神异经》等纯构虚词、诞幻不经者比”,[4](P978)即便著录存目之书如《幽怪录》,亦说:“然志怪之书,无关风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17](P1906)鲁迅对此类现象,并未提出批评,反而以此为线索,辑录古小说,以《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来看,《四库全书总目》应该是提供了很大的找寻指引的。这也许也是鲁迅内心对《四库全书总目》颇有好感的缘由之一。同时,对照鲁迅撰写的古籍序跋来看,其论述的语句及风格,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也不小,以《嵇康集》来比较: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宋以来,乃仅存十卷。郑樵《通志》所载卷数,与唐不异者,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王楙已尝辨之矣。至于椠刻,宋元者未尝闻,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18](P63)
《隋书·经籍志》载康文集十五卷,新、旧《唐书》并同,郑樵《通志略》所载卷数尚合。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则已作十卷,且称“康所作《文论》六七万言,其存于世者仅如此”,则宋时已无全本矣。疑郑樵所载,亦因仍旧史之文,未必真见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丛书》云:“……《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尔。《唐·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观楙所言,则樵之妄载确矣。”……实共诗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旧。盖明嘉靖乙酉吴县黄省曾所重辑也。[17](P1984)
很显然,鲁迅在序文中直接认同了四库馆臣“宋时已无全本”的考述,对王楙的辨正不再征引而直录郑樵“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的结论。另外,如鲁迅在《<云谷杂记>序》提到《会稽续志》八卷:“越中故实,往往赖以考见。”[18](P23)《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宋代张淏《续志》于《会稽志》条目下:“作为续编,复于前志内补其遗逸,广其疏略,正其讹误,釐为八卷。……淏所续亦简核不苟,皆地志中之有体要者。”[4](P930)馆臣对《云谷杂记》也撰有提要,与鲁迅之序文字上十分相像,前文已有论及。对于该书的价值,一说:“今此卷虽残阙,而厓略故在,传之世间,当亦越人之责耶!”[18](P23)一说:“其厘正是非,确有依据,颇足为稽古之资,宜当时极重其书也。”[4](P931)可见都极其推崇。而且鲁迅在序文末尾也论及其所校对本与四库本的差异,“间有异同,辄疏其要于末。其与《大典》本重出者,亦不删汰,以略见原书次第云”。[18](P23)
当然,如果只考虑用语相同或论述逻辑相似的话,鲁迅在小说史略、古文序跋等文字中呈现的提要性叙述风格,则遍地皆可寻觅。如《<唐宋传奇集>序例》说:“而后贤秉正,视同土沙,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18](P87)而《四库全书总目》常有:“残编断简,收拾于缺佚之余者,尚得以考见其什一。是亦可为宝贵也”[4](P1201)“其书采摭繁富,汉以来佚文绪论,多赖以存”[4](P1482)“至于前贤法帖,释者聚讼,珂所载亦间有异同,其已经《钦定重刻阁帖》厘定者,并敬遵驳正。间有参差岐出,数说皆通者,亦并用参存,不没其实焉”[4](P1492)等论调;鲁迅序跋末尾往往言及:“或疑本在《后汉书》百二十卷中,《唐志》乃复析出之,然据本传当为别书,今无遗文,不复可考。惟《后汉书》尚存十余条,辄缀辑为一卷”[18](P15),而《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常见这样的论述:“惟《永乐大典》所载尚为全书,而已经合并连书,二十卷之界限,不复可考。谨详加校订,析为八卷。卷数虽减于旧,其文则无所缺失也。”[4](P1317)
三、对清人评价的转向
鲁迅生活的年代离《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年代还不远,其对于清代书籍、清代士人的评价,甚至可以说是当朝人论当朝事。也就短短的一百来年时间,鲁迅所处之时回首审视纪昀等四库馆臣的评价、认同,就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比如在文学流派的评判上,四库馆臣对于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评价都不太高,鲁迅就已提出反对意见,“清初反满派的文集被舍弃,尚可以说是由于清朝之故,但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品也被排斥,这就说不过去。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甚大。”[14](P497-498)《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认为:“三袁者,一庶子宗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即宏道也。其诗文变板重为清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是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17](P2493)而民国时期的鲁迅等人,却是大力提倡晚明性灵文学的健将,晚明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复兴也由此生发。这基本奠定了之后中国文学史书写时对公安派、竟陵派的评价基础,1915年曾毅的《中国文学》、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等等,都对此两大流派用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学性灵之思潮风靡民国初年的诸多论述之中,陈子展在当时所言的:“书架上不摆部把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无法吐属风流”,[19](P21)确为当时文坛上“时髦的风气”,也足见此番批评转向带来的巨大影响。
再进一步具体到评价有清一代士人上来看,如上提及的袁宏道,鲁迅不仅从文学上赞扬公安派的影响,并且从“关心世道”的高度提升袁宏道,“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13](P51)这里的“吴中大贤”指的是辞官的顾宪成,鲁迅在文章里引用顾宪成的话语:“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大体。……”认为“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嫉恶如仇,对小人绝不假借。”[13](P51-52)这样的评价与《四库全书总目》完全相反,四库馆臣责难顾宪成,“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4](P1264)实际上,民国以来对顾宪成评价的提高、文学史对东林党气节的称誉,自鲁迅时态度的转变即已发其端。
下及清代,鲁迅对当时的士大夫及对应书籍的批评,如金圣叹、尹嘉铨、钱谦益、纪昀等等,其态度与四库馆臣们比起来,早已发生了许多转变。相对来看,鲁迅等民国学者提出的一些观念、认知,与如今中国文学史接受或所持的观点是有非常大的一致性的。因此,如果站在现在的角度来反思,对于距离《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完成后仅仅只有百余年的时间,鲁迅等一代学人就开始生发出批评、认同的变化,作为文学接受、发展的一环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民国时的这种变化呢?与之对应的是,现今的文学史、学术史及历史学史等等,无论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的叙写,对明清、民国的人、事和书都有了新的观感和态度,这种学术批评或认同演化的背后,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怎样的关联,在思想史、文化史的发展中是否有着一般的轨迹、脉络,以及将呈现出如何的趋向、态势,这些都是值得将来的研究继续关注和深挖的。
[1] 崔石岗.鲁迅与《四库全书》[J].图书馆建设,1997,(6):69.
[2] 陈得媛.鲁迅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保护和认识[J].教育教学论坛,2010,(35):235.
[3]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黄章明,王志成编著.国学方法论丛(书目篇)[M].台北:学人文教出版社,1979.
[11] 刘运锋编.鲁迅全集补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2] 顾农.鲁迅与书目[J].上海鲁迅研究,2004,(02):256.
[13]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8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解放军报社编.鲁迅佚文辑[M].北京:解放军报社,1976.
[15]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8]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 孙郁,黄乔生.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高 雪
The Transition of Luxun's Evaluation ofSiKu:Focusing onSiKuQuanShuandSiKuQuanShuZongMu
Luo Yaoj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H3A3R1, Canada)
After a thorough study of Lu Xun's works and letter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since the year 1934, his perspective on the great booksSiKuQuanShuandSiKuQuanShuZongMushowed a clear transition, from taking academic research to use the models of the past to criticize the present. Previous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research, Lu Xun commented thatSiKuQuanShuwas compiled under the order of the emperor; later 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forbidding and damaging, Lu Xun recommended that it did great harm to Chinese great works. However, the style ofSiKuQuanShuwas reflected in Lu Xun's novel studies, writing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nd other texts.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opening of Si Ku, scholars such as Lu Xun changed their attitude of the evaluation of Si Ku made by Gu Xiancheng and Yuan Hongdao living in Qing Dynasty.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modern scholars to reflect on the criticism, agreements or changes in attitude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both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 the future.
Lu Xun;SiKuQuanShu;SiKuQuanShuZongMu; transition
2016-09-06
教育部重点项目“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11JZD011);江苏省2015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省立省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报刊对中国小说的译介与评论”(KYZZ15-0012);南京大学2015年度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跨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民国档案文献中的环中国南海文化电函与报道研究”(2015CW04)阶段性成果
骆耀军(1989- ),男,江西赣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明清文学及晚清民国报纸小说与档案。
I210.97
A
1672-335X(2017)03-01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