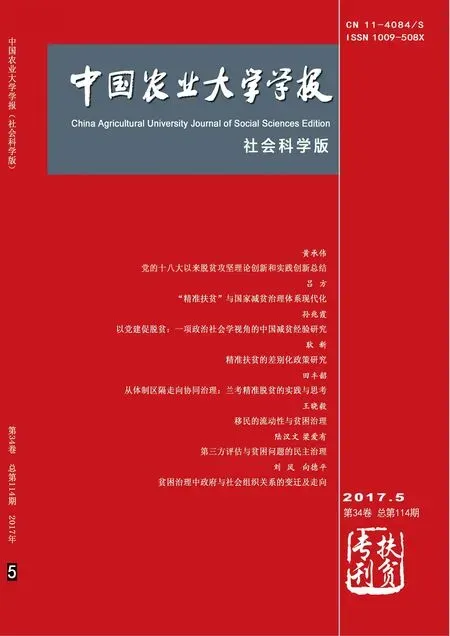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万 君 张 琦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万 君 张 琦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可以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考察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本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精准扶贫; 绿色减贫; 产业扶贫; 利益联结机制
绿色减贫,即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减贫手段[1]。我国贫困发生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耦合,环保部《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指出,我国592个贫困县中80%以上地处生态脆弱区,这些县的土地面积、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分别占到生态脆弱地区土地面积的43%、耕地面积的68%、人口数量的76%;绝对贫困人口中,95%以上分布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贫困与生态的交织作用,如何实现绿色减贫一直是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指南与根本遵循。2013年,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标志着“两山”理论成为当前我国治国理政的主要思想之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两山理论”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注重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的关系以及绿色减贫的路径,指出“脱贫攻坚要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绿色资源的减贫机理:“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化为护林员等生态管护员”。
近几年,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各地围绕绿色减贫的模式开展了实践探索。绿色减贫的理念已经初步形成,理论界也较为广泛开始就绿色减贫的机理、机制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张琦教授团队围绕绿色减贫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就我国绿色减贫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测度[1-3]。雷明较早就“两山理论”与绿色减贫的结合点进行了论述[4]。莫光辉也发表系列论文就绿色减贫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5-7]。王晓毅探讨了绿色发展下的精准扶贫[8]。此外,也有学者也总结出一些绿色减贫的成功模式,例如黄承伟认为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是兼顾减贫与生态双重目标下的创新模式,这种绿色减贫发展模式破解了石漠化地区的“贫困陷阱”,实现了贫困地区减贫目标和生态文明的双赢目标[9]。
总的来看,绿色减贫理论与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就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实际来看,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的目标毫无疑问可以如期完成。当下扶贫的重点除了确保深度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之外,也应该考虑如何优化扶贫效率、创新扶贫思路、改革工作机制。因此,我们组织了此项研究,对近几年绿色减贫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与梳理,以提升减贫质量为目的,把绿色减贫的理论与实践放在贫困治理的视角下去审视,阐释其减贫的路径与机理,并就近两年绿色减贫主要模式在不同层面进行总结,最后展望绿色减贫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贫困治理与绿色减贫
贫困问题也是治理问题,贫困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贫困治理水平和贫困地区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理论上和实践上已有初步共识:农村贫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减贫的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囿于中国实际,1949年至今,我国的反贫困战略重点一直在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计问题,尽管在理论上早就提出系统的解决贫困问题,但在具体的减贫策略上,仍然是以经济为导向,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的收入问题,没有重视有关贫困治理的问题。
1986年,中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其重点是解决“三不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的“吃、穿、住”问题;1994年,《国家八七攻坚扶贫计划》重点解决“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解决的是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近40年的减贫政策,对于贫困人口的保障内容不断扩展、保障水平也不断提升,但基本局限于生存方面的内容,对于内生发展、治理能力等贫困治理问题关注较少,可以说,我国的反贫困政策对于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贫困治理问题的关注,在扶贫的具体方法策略上,也是长期依赖于送项目、送资金,外援推动的色彩较为浓厚。
精准扶贫以来,在“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压力下,扶贫手段中对于外源性、输血式扶贫的路径依赖愈发突出,从我们参与的几次第三方评估以及贫困监测的研究来看,部分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有超过40%收入的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养懒汉的现象也较为突出,极个别地方精准扶贫已经有“精准送吃、送喝、送穿、送钱”的趋势。也恰因这种“路径依赖”,导致长久以来倡导的“提升内生动力”一直以来难以实现。可以说,目前的扶贫工作已经出现了“内卷化”的趋势[10]。更重要的是,贫困治理水平、贫困地区的治理能力也有下降的趋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2017年各地广泛开展的“贫困村提升工程”。但贫困村提升工程有走传统扶贫开发老路的趋势,各地的工作重点仍然集中在解决贫困人口收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没有把贫困村的治理问题通盘考虑。
因此,亟需从贫困治理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系统的解决贫困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除了前述现实问题之外,可以预见的是,2020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我国的反贫困战略也有转型的需求,需要提升减贫的质量,从单纯的解决贫困人口的收入、生计问题,转变到综合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注重贫困人口能力的培育、贫困地区治理水平的提升。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绿色减贫至少是将来贫困治理可行的路径之一。绿色减贫不仅能够解决收入、生计等传统问题,还能够综合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贫困地区目前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诸如经济发展的“非绿色化”面临瓶颈,经济与生态矛盾日益凸显;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面临的两大短板等,都可以通过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的方式去解决。同时,近几年的绿色减贫实践表明,由于大多数绿色减贫的项目都是依托于本地的绿色资源,参与门槛较低,贫困人口通过参与绿色产业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发展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绿色减贫的相关产业项目在实践中创新利益联结机制,贫困地区内部不同的个体、群体、组织之间的互动也大幅增加,也促进了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
二、绿色减贫产业的实践模式
近几年,各地围绕绿色减贫的探索主要在绿色产业扶贫方面,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在传统的以绿色资源为核心的扶贫产业基础上,由于技术推动、消费需求升级、三产融合等因素,促进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业态,绿色减贫的各项产业已经没有了明确的产业界限,贫困人口已经初步能够享受到农业经营的多重价值和产业链的延伸价值。第二,利益联结机制推陈出新,贫困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同利益主体带动贫困人口增收的能力越发增强。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绿色减贫大概有以下几类实践模式。
(一)经济业态视角下的绿色减贫模式
精准扶贫以来,中央支持和地方实践二者合力,通过产业融合,探索了一些新型的绿色减贫模式。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也已经将产业融合上升为宏观战略,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下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特别指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贫困户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实际上,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有关“发展特色产业脱贫”一节中,提出的措施基本是围绕产业融合发展展开。
总体来看,产业融合推动下的绿色减贫模式,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传统“帮扶导向”扶贫的路径依赖,有较为明显的“改革导向”。就各地的实践来看,一般是通过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了一些成效较为突出的绿色减贫模式。有以下几种较为典型的路径:第一,通过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的改革,促进农业产业内部各子产业的融合,形成了循环农业、庭院经济等新型经济业态;第二,通过供需匹配,基于消费升级的客观规律,推动了诸如旅游产业扶贫、观光农业、电商扶贫等业态的绿色减贫模式;第三,基于提升农业产业的竞争力、提升农村地区的竞争力,探索了一些基于贫困地区绿色资源和比较优势的新型产业业态,此类绿色减贫模式大多数是二三产业,较为典型的有光伏扶贫、大数据产业等。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类典型模式。
1.农业内部产业融合形成的绿色减贫模式
此类绿色减贫产业主要是基于农业产业内部的产业融合,通过整合农业产业内部上下游之间的资源,特别是打通农业内部各子产业之间的联系,形成新型种养殖业,达到贫困人口增收的目的。其适用性也较广,工商业资本、合作社、农户均能比较广泛的参与,部分产业的技术门槛也比较低,带动贫困人口增收的效果比较直接。
除了传统的种养殖业之外,较为典型的还有以下几种:第一,循环农业模式。以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为手段,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产出率,实现绿色发展的生产方式。循环农业在贫困地区发展的历史比较长,也曾经形成一些典型案例,安徽省阜南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07年被批准为全国唯一的“农业(林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县”。精准扶贫以来,阜南县在脱贫攻坚中引入循环经济理念、模式和技术,通过利用废弃物为原料进行柳编加工,累计解决26万人就业,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3%,其中属于贫困人口20万人以上。
第二,林下经济模式。林地确权以后,一些贫困人口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发展了林下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和森林旅游业。林下经济门槛低、投入少、见效快,无论是林禽模式、林畜模式、林菜模式、林草模式、林菌模式、林药模式,都是贫困人口比较熟悉的,操作起来非常容易。国家林业局对于林业扶贫的推动力度也很大,2016年5月,国家林业局出台的《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通知》对林下经济着墨颇多,此后又发文《关于在贫困地区开展国家林下经济及绿色特色产业示范基地推荐认定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示范活动。
第三,庭院经济模式。庭院经济(courtyard economy)顾名思义是在贫困地区房前院后展开的各类产业,其形式多样、技术要求低,也能够直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农村重要的生活方式。近几年,随着脱贫攻坚的进行,各地对于庭院经济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也催生了不同的庭院经济业态,更加注重庭院经济的生产功能,形成了庭院养殖、庭院生态循环、庭院园艺、庭院手工加工业、庭院休闲产业等等。
2.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绿色减贫模式
此类绿色产业减贫模式是基于农业产业链延伸的产业融合方式,主要是通过农业由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而实现的,也就是“接二连三”,通过农业产加销一条龙最大限度获取生产利润,最大程度让贫困人口分享产业链延伸各个环节的价值。较为典型的是电商扶贫模式。
电商扶贫模式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一大创举之一,是以电子商务为手段,拉动网络创业和网络消费,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品销售的一种信息化扶贫模式,电商扶贫将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深度融合,并且与“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即让贫困人口分享了产业延伸的价值,也促进了贫困人口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参与市场竞争,提升了人力资本和内生动力,深刻的改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效。2012年以后,随着农产品电商的爆发,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开始根据本地实际探索电商脱贫的路径,涌现出了甘肃成县、吉林通榆、黑龙江明水、甘肃陇南等一批电商扶贫的县域先行者,为县域电商扶贫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典范。目前已有山东、甘肃、河北等多地印发电商扶贫文件,将通过“平台+园区+培训”等方式,整合贫困地区优势产品对接市场。此外,各大电商平台的电商下乡战略为县域扶贫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精准扶贫以来,国家对此也是非常重视,2015年11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在顶层设计上为电商扶贫发展明确了思路。2015年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把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以建档立卡贫困村为工作重点,提升贫困户运用电子商务创业增收的能力,鼓励引导电商企业开辟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网上销售平台,与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建立直采直供关系,增加就业和增收渠道。《“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指出要培育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给予电商扶贫的技术支持和政策扶持也比较多。总体来看,电商扶贫模式是绿色减贫实践模式中较为成功的一类。
3.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形成的绿色减贫模式
此类绿色减贫产业基于贫困地区优势资源,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也是三产融合比较彻底的方式,,完全打通了产业的界限,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连接和延伸”向“一二三产业的交叉和渗透”转型,利用贫困地区绿色资源实现全产业链条促进要素融合的一种模式。
总的来看,各地较为成功的有旅游扶贫模式、观光农业模式:第一,旅游扶贫模式。旅游扶贫是各地基于自己的区位情况和旅游资源情况,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的扶贫开发方式,有的依托旅游扶贫也发展了休闲农业。我国政府曾将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总结为我国绿色减贫的三大模式。精准扶贫以来,对于旅游扶贫的支持力度也很大,中央不断发文支持旅游扶贫,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旅游扶贫确实也是三产融合紧密、脱贫效果突出的扶贫开发方式,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旅游经营、参与接待服务、出售农副产品、流转土地、甚至量化折股参与合作社和旅游公司经营,可以直接、大幅的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并且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很快,集体经济壮大也很快。较为典型的是陕西的梁家河村,2015年5月,梁家河村成立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仅仅一年就带动164人脱贫致富,整个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达到1.5万元。
第二,观光农业模式。观光农业是依托城市,在城市近郊形成的以旅游业和农业交叉融合的绿色减贫模式,通过吸引城市人口感受农业生产,增加贫困人口收入。观光农业的模式较多,但目前较为成功的是观光农园和民俗观光村,观光农园即在城市近郊开辟各类果园、菜园,游客通过采摘感受农业生产。民俗观光村即通过重新发现、打造贫困村落的传统文化价值,吸引游客观光的扶贫模式,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具有很好的扶贫效果。例如,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切洼乡嘎布久嘎村,是一个拥有1 300多年历史的自然村落,全村有64户384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户135人,该村历来以“四古”著称,分别是1 300多年的古村;1 100多年的古树;500多年历史的古寺,还有曾作为班禅大师贡品远近闻名的古糌粑。嘎布久嘎村围绕“四古”找题目、做文章,投资了400万元,建设完成了游客服务中心和旅步道等景点建设,每年稳定脱贫50多人。
4.新技术推动形成的绿色减贫模式
新技术的诞生重新发现了贫困地区绿色资源的价值,贫困地区富集但曾经未能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资源逐步显现,形成了贫困地区特有的资源。此类产业融合主要是先进技术在农业、农村的体现,目前来看,较为典型的是光伏扶贫、大数据产业扶贫:
第一,光伏扶贫。即利用光伏发电技术开展的各类扶贫。光伏扶贫始于2013年后的技术革命,太阳能光伏产业逐步成为新兴产业,而贫困地区丰富的日照成了资源优势。也逐渐成立了各地较为青睐的绿色减贫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明确表示在2020年前,要以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16个省471个县约3.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200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包括残疾人),每年每户增收3 000元以上。目前光伏扶贫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户用光伏发电扶贫,利用贫困户屋顶或院落空地建设发电系统,产权和收益均归贫困户所有;二是村级光伏电站扶贫,以村集体为建设主体,利用村集体的土地建设小型电站,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收益由村集体、贫困户按比例分配;三是光伏大棚扶贫,利用农业大棚等现代农业设施现有支架建设的光伏电站,产权归投资企业和贫困户共有;四是光伏地面电站扶贫,利用荒山荒坡建设大型地面光伏电站,产权归投资企业所有,部分收益由当地政府将这部分收益分配给贫困户。
第二,大数据产业扶贫。大数据产业是围绕大数据的搜集、整理、储存、分析的产业集群。大数据产业数据储存和分析对于自然环境要求比较严苛,贵州天气凉爽、地质条件稳定、空气洁净、电量充足,因此,中国目前大数据产业的中心在贫困省份贵州。大数据产业极大的推动了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也创造了很多机会。虽然其在贵州的发展极为成功,但其在其他贫困地区推广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利益联结机制视角下的绿色减贫模式
利益联结视角下的绿色减贫模式,核心在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联系机制、组合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绿色减贫诸多模式里,核心在于实现了绿色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核心内容,即“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过程。在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里,绿色资源通过“折股量化”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向资本和资产的转移。其较为典型的模式是肇始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三变改革盘活了沉淀的绿色资源。
可以看出,这个转化过程的基石在于近些年中央推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长久以来由于农村集体产权的归属不清,导致很多在市场机制中具有巨大价值的绿色资源长期沉淀在农村,对这些资源的权责划分不明、保护乏力、开发流转不畅,各类市场主体在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很难顺畅挖掘绿色资源的原有价值。从实践来看,各地基本是基于中央近几年有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精神,对集体经济组织掌握的各类绿色资源,通过折股量化等手段明确到个人,同时按照一定的比例留存或提取集体经济部分,再按照市场化运作,参与各种绿色减贫的模式。通过明晰产权、理顺各类市场主体关系的基础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集体经济的议价能力逐步提升,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也有了可能。从利益联结机制视角来看,绿色减贫模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企业主导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组织或其他组织的参与,带动贫困人口增收,公司+农户、“订单农业”是基本形式,此外,还形成了诸多的派生形式,比如公司+农户+基地+市场、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党支部等。在此模式下,目前已经形成了“入股返利”(农户入社,合作社入股企业,企业保证收益率)、“订单合作”(企业带动,合作社标准化定单生产)、“托管保底”(企业、合作社、农户相互委托种养殖)及“合资兜底”(财政补助,企业、合作社、农户共同出资建设,企业保底收购)等形式的利益联结模式。
第二,大户主导模式。即通过一些在生产、销售有特长的农户带动,贫困人口以土地、劳动力等形式参与,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包括所谓“能人带动”、“抱团经营”等形式,大户主导实际上也是企业主导模式的派生形式。
第三,集体经济主导模式。即通过集体经济的壮大,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此模式主要是一批依托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明星村,各村将村集体经济收入重点支持贫困户,精准扶贫以来,除了传统的明星村之外,依靠扶贫政策,也诞生了一批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
第四,政策主导模式。此模式主要是依靠精准扶贫以来中央扶贫的各类奖补政策支持,通过奖补扶持政策与资源开发对接,贫困户的各类奖补政策通过折股量化形式入股,使得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受益,较为典型的是光伏扶贫。还有各地较为通行的小额信贷扶贫,大部分地区将小额信贷资金通过挂靠经营和保底分红的形式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第五,资产收益模式。该模式将绿色资源、公共资产(资金)或农户权益资本化或股权化,相关经营主体利用这类资产产生经济收益后,贫困农户按照股份或特定比例获得合理的收益。这种模式对失能和弱能贫困人口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因为它不依赖农户的独立经营能力,重点放在扶贫效率到户,不强调资金到户。通过赋予贫困户产权或股权,有利于贫困农户积累资产并利用这些资产持续受益,从而持久脱贫。
三、绿色减贫的经验
第一,绿色减贫能够盘活了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些贫困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绿色资源,有的是自然资源即所谓“绿水青山”,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贫困地区富集但未曾利用过的资源价值不断凸显,贫困地区已经有利用丰富的绿色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旅游扶贫、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的出现,盘活了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提升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几年兴起的大数据技术,很多企业将数据中心建立在贫困省份贵州,其依托的不是诸如低廉的劳动力、财税优惠、土地优惠等以往贫困地区吸引投资的传统因素,而是因为贵州的地质结构稳定、森林覆盖率高、气候凉爽、电力充沛等绿色资源。又如,光伏发电技术也使大量的贫困地区由于空气洁净度高、日照时间长等优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产业。此外,由于传统工业地区环境的恶化,贫困地区形成了环境资源意义上的“洼地”,就有相当的优势。这些绿色资源,通过产业化逐渐积淀、形成了大量的绿色资本,对贫困地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持久的推动作用。
第二,绿色减贫的实践表明,绿色产业化推动的三产融合能够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质量。过去,贫困地区的规模产业,要么是资源型产业要么是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很多产业对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不友好,贫困地区的规模产业往往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恶性循环,三产的融合程度比较低、产业结构不甚合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比较低。就绿色减贫目前的实践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来看,绿色减贫能够较大的促进的三产融合,能一定程度上提升贫困地区的发展质量。如前所述,目前贫困地区已经探索了一些可行的的产业融合方式,绿色减贫与传统扶贫方式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能够促进三产融合,在注重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质量,并且能够吸引部分劳动力回流,解决村庄衰败等问题。
第三,通过参与绿色减贫过程,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提升。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在贫困地区广泛存在,除了少部分是受益于“制度养懒汉”而主观上缺乏脱贫意愿之外,大部分是受制于条件所限,或者缺乏生产要素或者缺乏生产手段和经营手段,不能通过参与脱贫攻坚进程而实现内生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只能被动接受帮扶。绿色减贫核心在于立足贫困地区绿色资源,培植和扶持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绿色减贫产业相对门槛较低,以基于种养殖业的农业融合产业、资产收益等模式为主,贫困人口能够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的过程,有的贫困人口直接负责经营具体的产业项目,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得到提升,也能通过扩大参与、典型示范等手段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近几年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旅游扶贫、农家乐、电商扶贫等绿色减贫手段,都有此方面的特征,贫困人口参与程度深,与市场、外界的接触和交流比较密切,对新的经济业态、新的生产和经营技术了解和掌握也非常深入,不仅收入提升较快,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也较高。
第四,利益联结机制创新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治理结构,提升贫困治理水平。绿色减贫机制与传统扶贫产业区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绿色减贫产业下的贫困人口有了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议价能力。绿色减贫的基础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绿色资源,近些年,随着国家在农村推动诸如土地确权、林地确权等各项产权制度改革,绿色资源的产权归属愈发清晰,贫困人口与工商业资本的议价能力逐步增强,因此也出现了集体资源、农户资源多种多样的折股量化方式。在此基础上,绿色减贫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也很多,直接对贫困地区的治理结构转型有了很大的推动。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工商业资本之间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治理结构,各类主体的社会责任也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凸显,贫困地区的治理水平和贫困治理能力也能够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
四、绿色减贫的提升路径
第一,国家的绿色减贫策略应实现转型,减贫技术应从“帮扶导向”到“改革导向”,通过深化农村、农业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贫困地区发展。自1986年扶贫开发以来,我国对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一直是帮扶优先,通过送资金送项目以期推动贫困地区发展。这种“帮扶导向”的扶贫技术,其效率一直遭人诟病。事实上,通过对绿色减贫产业业态和联结机制的考察,我们发现,绿色减贫技术上的基石恰恰在于近几年土地、林地的所有权制度改革,让一些新兴的绿色减贫产业才有了发展的可能,贫困人口也才有了议价权力和分享收益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到1986年,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并未有特殊的项目、资金投入,但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5年时间减贫2亿人口,贫困人口年均下降4000万。二者的历史时代条件和历史背景确有差异,但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路径应该正确无误。因此,如果国家在未来注重减贫质量,注重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应该将减贫的策略从“帮扶导向”转变至“改革导向”,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沉淀在农村的各类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第二,绿色减贫产业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选择新的经济业态,提升产业融合水平。可以看到,绿色减贫的基础是农业产业融合,产业融合的驱动多来自于社会发展变化的驱动。新的产业业态、更深入的产业融合水平,才有可能让贫困人口在二、三产业中获得相应的利润,工商业资本、企业、大户等多元主体才有可能和贫困人口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因此,绿色减贫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升产业融合产业水平,立足农村与农业,但不局限于农村与农业,既是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融合、也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各类生产要素的融合。这也是绿色扶贫产业与其他扶贫模式、传统乡镇企业的不同之处。
第三,部分绿色减贫产业的益贫性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绿色资源的收益率需要进一步放大。绿色资源资本化和资产化的过程在技术上是通过“折股量化”的形式来解决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绿色资源的股份来分享各类收益。但在实践中,“量化入股”的形式有异化的趋势,部分绿色资源实现“量化”后,名义上是入股,实际上是“放贷”,只能享受到微薄的“利息”或者“股息”,而这部分甚至低于国家在相关优惠政策上的转移支付。国家对于某些产业的支持和帮扶,并未全部到贫困人口,而被相关企业截留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部分产业的益贫性是比较低的,绿色资源的收益也是比较低的。
第四,绿色减贫相关产业的选择需要智力支持。绿色减贫是通过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来实现的,产业选择是绿色减贫实施推进中的重点环节。从我国扶贫开发的实际来看,产业选择一直是我国扶贫治理技术的短板之一,“粮丰价跌,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高新技术和新兴业态的出现,因地制宜、统筹考虑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社会状况、经济环境、思想观念、比较优势,选择适合当地的产业愈发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各类产业生产与销售更需要精细化的核算,这需要一定的科学决策水平。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应该立足目前产业转型和产业融合的实际,建立绿色减贫产业科学决策的相关机制。
[1] 张琦.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报告2014.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
[2] 张琦.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报告2016,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
[3] 冯丹萌.中国绿色减贫机制及综合效应评价分析.北京师范大学,2017
[4] 雷明.两山理论与绿色减贫.经济研究参考,2015(64):21-22
[5] 莫光辉,张菁.绿色减贫:脱贫攻坚战的生态精准扶贫策略.广西社会科学,2017(1):144-147
[6] 莫光辉.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02-112
[7] 莫光辉.绿色减贫:脱贫攻坚战的生态扶贫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现代经济探讨,2016(11):10-14
[8] 王晓毅.绿色发展模式下的精准扶贫.中国财政,2016(11):29-31
[9] 黄承伟,周晶.减贫与生态耦合目标下的产业扶贫模式探索——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案例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6(2):21-25
[10] 方劲.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内卷化”困境及其治理. 社会建设,2014(2):84-94
GreenPovertyReduction:thePathandModelofPovertyGovernance
Wan Jun Zhang Qi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overty governance, and its mechanism lies in green industry and green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the model of green industry is investigat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industry convergence and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 From the angle of industry convergence, the model of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includes circular agriculture, forest economy, courtyard economy, electricity supplier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photovoltaic poverty alleviation, big data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linkage, the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model mainly includes five models: enterprise leading, big family leading, collective economy leading, policy leading and asset income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is bas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
2017-08-0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贫困治理视角下精准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7CSH013)的阶段性成果。
万 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讲师;张 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邮编: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