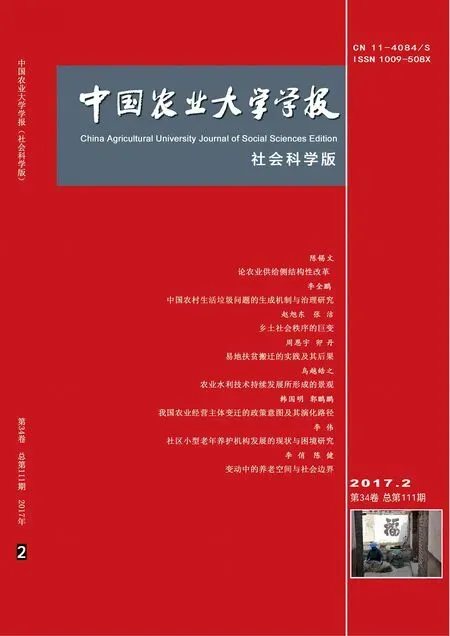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与多元主体参与:一个文献综述
杨 嬛 王习孟
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与多元主体参与:一个文献综述
杨 嬛 王习孟
文章旨在全面回顾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相关研究,总结主要研究成果,并为进一步探讨寻找方向。文章首先梳理了研究的不同理论视角,包括社区支持农业、巢状市场、食品短链和农消对接。综合不同视角的研究,文章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食品体系主体力量不均衡、中等收入群体兴起是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替代性食品体系的发展与全球食品体系变化紧密相连,但政府主导了认证体系建立,对新兴体系发展支持不够。消费者与大部分生产者都是社会精英群体,小农户在中介机构的支持下参与到新体系之中。现有研究在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总体情况调查分析、行动主体价值观念构建、企业与替代性食品体系构建、与生态农业技术研究互动等方面有待加强。
替代性食物体系; 社区支持农业; 巢状市场; 食品短链; 农消对接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的食物体系(agro-food system)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带来了一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退化、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小规模农业生产者被边缘化,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过度加工食品造成普遍健康等[1]。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社会运动,替代性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应运而生,意在建立新的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结构,重新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一条替代性道路[2-3]。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实践丰富多样,呈现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消费者购买团体(buying clubs)等多种形式[4]。
替代性食物体系最早产生于日本、瑞士和德国,后来在欧洲、美国迅速扩展开来,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当前这一理念和实践也成为中国三农领域的关注热点。相比发达国家,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压力,人均资源占有量小、环境急剧退化严重阻碍到了农业和食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农业生产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食品加工中大量使用添加剂和非自然成分也为食品安全带来了严重问题,产生了社会、经济多重层面的负作用[2]。面对这一困境,一方面社会自发产生了以消费者、生产者主导的生态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模式,如广西爱农会发起的“土生良品”餐厅和农圩;另一方面,学者、NGO等外部主体也在替代性食物体系理念指导下倡导和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包括香港NGO组织“社区伙伴”在西南地区推动的“生态农耕”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倡导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华北农村推动的“巢状市场”实践。这些实践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推动了替代性食物体系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替代性食物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涉及了替代性食物体系的理念、产生背景、实践过程及成效等多个方面[5-6]。由于替代性食物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相关研究也刚刚起步,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学术概念探讨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功能、实践与发展,丰富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点、建立了一个议题广泛的讨论平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本文将系统梳理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相关概念,理清替代性食物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综合分析不同主体在替代性食物体系中的参与及相互关系,让读者对我国当前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研究寻找突破点和方向。
一、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大量国内外学者对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学术界并没有为替代性食物体系给出明确定义,而是从内涵上探讨其特点。Feenstra认为替代性食物体系“根植于特定的地点,目标是经济上有利于农民和消费者,生产和流通中采用生态友好的方式,在社区成员间增强社会公平和民主”[7]29。其替代性体现为空间上缩短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社会上促进产消双方的信息交流、增强相互信任,经济上强调公平交易和社区发展[8-9]。因此这一理论概念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涵盖了与这类新兴市场相关的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现有研究中,多个与其相关和类似的概念,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理解同类社会想象,比如短链农业(short food supply chain)[10]、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11]、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12]。国内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既有学者采用了这些概念,也有学者从中国的实践和理论体系出发提出了本土化概念,比如农消对接[13]。以上概念与“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只是从某一方面突出了这一体系的特点,以及分析和实践的重点。
(一)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是替代性食物体系重要实践形式,也是在国内影响最为广泛、研究讨论最多的一种模式[9]。在现有文献中,沈旭较早将“社区支持农业”概念引入国内,主要介绍了国外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历程、主要操作方法和特点,认为这一模式能够支持和保障地方的农业发展和食品供应,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农产品,为小型农场提供发展机会,减少农业对环境的影响,从而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食品安全无保障、农业生产不可持续等问题[14]。
在国内,公认的最早以社区支持农业理念指导的实践为2009年开始运行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基地。从2010年1月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小毛驴市民农园等团体的推动下,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开始举办,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七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实践领域、研究领域、政府领域的参与人员。人大农发院的一系列项目和活动不仅推动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推广,“小毛驴”也为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15-18]。
近年来,社区支持农业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在知网期刊数据库内搜索,标题中含有“社区支持农业”的文章有150多篇。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社区是指生活在一定的共同区域范围内,在共同纽带中形成了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19]。潘家恩和杜洁认为社区支持农业研究视角之所以强调“社区”,是重视替代性食物体系构建中微观社会单位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是实体性的具有实际运作功能的消费者购买群体、生产者联合群体,另一方面也是价值上的象征性群体,让人合理想象可以通过共同行动寻找到一种可能形式,缩短过度耗能和污染的食品产业经济链条[20]。因此在人大农发院的实践和研究中,社区支持农业是乡村建设和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主流的以现代化和工业化农业生产为目标的发展路径,通过生态农业和城乡公平交易促进社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1],其他研究者也十分重视消费者社区的形成和功能实现[22]。
(二)巢状市场
巢状市场概念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提出,开始于2010年启动的“巢状市场减贫项目”。这一项目与河北省易县、北京市延庆县的4个村庄建立合作,通过项目运作推动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进行农产品交易、建立信任,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对乡村环境和耕作传统的修复。巢状市场既指实体性的交易场所,也强调制度化的市场关系,是指通过特定的运载系统,在特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发生的特殊产品的交易。特殊产品主要包括高质量产品、地方特色产品,有机粮食产品,乡村旅游等;特定的消费者是指能够区分出这些产品和服务特殊品种的消费者;特定的运载系统包括农夫市场、农场商店、定期配送计划等实现形式[23]。
范德普勒格指出采用 “巢状”这一定语是为了突出这种新兴市场与其嵌入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特殊关系。与主流的食品体系试图重构其所嵌入的结构有所不同,巢状市场是明确地认可这种嵌入关系[11]。首先,目标上巢状市场嵌入当前的社会结构之中,力图解决主流食品体系的问题和危机,社会关系上它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任和互动为基础;其次巢状市场根植于地方的资源结构,尊重和认可产品产地的气候、种植结构、劳动力投入等资源基础;再次巢状市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不仅有提高生产者收入、改善消费者消费的经济功能,还有促进消费者和生产者信任和信任的社会功能,维护农村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生态功能[24]。
巢状市场视角还强调这类新兴市场的运作机制——公共池塘资源。公共池塘资源概念借用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但又超出了对概念所指对象的实体性理解。在巢状市场概念下,公共池塘资源不仅指用于交易的特定资源和特定产品,也包括围绕产品的“特殊性”而产生出的一系列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共享的规范和对产品的期望,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特定生产者和消费相互联系[24]。这一概念显示出新兴市场的建构过程为所有参与主体提供了发挥自身能动性的空间,消费者、生产者、中介组织(科研机构、NGO、社会企业等)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观念来参与产品质量标准的界定;共同认可的价值规范是在互动中形成,而不是某一个主体单独决定;最终产品是共同认可规范的物质载体。
(三)食品短链
食品短链也称为食品供应短链(short food supply chain),是国外研究替代食品体系常用概念,产生于食品供应链视角下的食品体系研究[10]。杜志雄和檀学文是较早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的学者,他们认为食品短链中的“短”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地域范围的短,指食品消费的本地化和地方性,减少食品运输带来的成本和环境污染;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三是信息的透明和可见,消费者尽可能了解食品生产和流动过程的全部信息[25-26]。殷戈和朱战国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减少中间商数量、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确实能够提高农民参与食品短链的积极性[27]。
杜志雄和檀学文将中国与西方进行对比,认为中国食品供应链条发展还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食品加工程度,即食品链长度远低于西方,但是由于食品工业发展缺乏有效监督,产生了负面效应[28]。中国生态农业生产实践的主流方向还是对早期现代农业的改进和发展,并没有走到替代现代农业的后现代农业阶段,作者将其称为“建设性”现代农业,虽然重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食品安全等问题,但是对节能减排、本地化消费等非经济价值层面的实现关注不多,在生产规模上仍追求规模化经营[25]。不过随着相关实践的增多,作者也认识到采用短链农业模式的农场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利益公平分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其经济可持续性目前还不明朗,并认为短链农业实践的借鉴意义在于具有生态农业观念和技术能力的农业经营者的培养和发掘[29]。
(四)农消对接
“农消对接”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团队,针对新兴的替代性农业模式提出的一个本土化概念,并提出农消对接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人情关系的建立和人际信任的巩固”[13]62。作者认为随着土地、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资本的逐利倾向助长了企业的投机行为,造成了食品市场的安全问题恶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基于个体理性会采取“个体自保行为”,具体表现为生产者针对自我消费和市场销售产品采取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保证自己家庭食品消费安全,又不损失农产销售利润;消费者压缩主流食品消费支出和成本,同时寻找替代性的食品消费渠道[30]。同时作者也认识到,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体自保行为的规模扩大,“个体自保”就具有转为“社会共保”的可能性,其前提是促进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的联合,增进了解和互信[31]。
在“农消对接”概念下,周立教授团队分析了中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内在特点和对发展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挑战。在生产者方面,分散的小农户没有独立开发市场的能力,产品数量、质量和价格标准都难以直接对接市场,因此类似农户市集、都市农场、NGO等食品中介的协助作用十分重要[13]。在消费者方面,消费责任意识的缺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主要体现为以“物美价廉”为消费标准、缺乏合作消费组织[30]。因此建立“社会共保”的食品安全体系需要食品体系所有主体的共同参与,实现断裂的社会联系的重建。
二、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
(一)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的社会背景
替代性食物体系之所以在国内落地生根,并迅速发展开来,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食品安全问题是社区支持农业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从追求数量转为追求质量。但是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比如三鹿三聚氰胺事件、鸡蛋苏丹红事件、高明毒菜心、沈阳韭菜中毒事件,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甚至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利益,一些消费者通过自我联合发起了社区支持农业,建立与生态生产农户的长期联系,比如北京绿之盟妈妈生活馆[32];对于加入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获得高品质的安全食品是他们的首要动机[33]。
食品体系内不同主体力量不平衡是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的内在动因。在现代食品体系中,大型中间商、农资供应商掌握了生产资料和食品的定价权,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成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32]。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食品安全成为低价格的牺牲品。在生产环节,农民为了适应市场对生产环节利润不断压缩的现实,通过使用大量化肥、农药、添加剂来提高产品产量、美化产品外观。在加工环节,加工商使用劣质原材料、大量食品添加剂,同样力图达到“物廉价美”的效果[2]。消费者无法直观判断食品质量,只能逆向选择“物廉价美”的产品。因此看似“物美价廉”是多个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却带来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积极寻找替代性的食品体系组织方式。其次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岌岌可危。一方面农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对生态可持续造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利润低下导致了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社会可持续前景堪忧[34]。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替代性食物体系建设更是被视为摆脱市场力量控制,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社会信任与合作,实现城乡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20]。
中等收入群体兴起是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在收入水平上在群体居民中处于中等水平,而且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里特征上相近[35]。在相当经济实力和反思现有食品体系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他们对食品消费提出更高的利益诉求,比如食品安全、公平贸易、环境保护[6]。因此,这一群体成为新兴的替代性食物体系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16, 22]。
(二)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历程
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起步较晚,大多出现在2005年以后,但是中国替代食品体系实践却远远早于对它的研究,而且与全球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全球范围内,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最早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于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消费者发起的社会运动反思了资本导向的食品体系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从而推动了关注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的食品认证体系的建立,例如有机认证、公平交易认证,这些认证以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产者基本权益为价值出发点,是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实践形式之一。主流食品体系的企业也抓住了这一机会,掌握了食品认证体系的主导权,导致了这一替代性实践的传统化(conventionalization),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高品质食品供应链[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早期的有机农产品以出口为主,参与运作主体不乏跨国食品公司的身影,生产者取得的主要是国外机构认证。最早出口的有机农产品为1990年从浙江南部出口到荷兰的有机茶叶。作为国内最大的有机产品认证机构,1999年有机食品发展中心认证的有机产品生产面积为2 495.27公顷,有105种产品,共有20 540千克产品[36]。
与西方国家社会运动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和认证体系建立不同,政府在中国生态农业认证体系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早在1992年,农业部就成立了绿色农产品发展中心,负责绿色农产品的认证和管理,绿色产品在生产中允许限量使用相对安全的化学合成剂。1994年环保部在南京成立了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对全国的有机农产品进行认证和管理。2001年,农业部实施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以提高对食品安全的管理[37]。但是由于认证体系设计及其运作存在的种种问题,政府主导的食品认证体系并没有增加食品生产过程信息透明度,反而让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可信度与高附加值产生了怀疑[38]。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产生了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对食品消费有了更高的价值需求。广西爱农会是现有研究中提到较早的这类消费者组织,由一群身居广西柳州热爱农村生活的年轻人发起,2004他们开始寻找本地生产农产品,2005年在柳州设立了“土生良品展室”,2007年在柳州开设了第一个“土生良品餐馆”,餐馆所有食材都来于爱农会的合作农户,餐馆食材还在社区农圩上销售。与此同时,生产者也看到了市场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河南南马庄农民合作社在2005年自发开始无公害大米的生产,并在温铁军和何慧丽教授的支持下发起来了“购米包地”活动,成为自发社区支持农业的经典案例[12]。在香港NGO组织“社区伙伴”的支持下,广西横县三叉和陈塘村在2005年开始了有机水稻种植,将有机大米以市场大米2倍以上价格销售给香港、广州、南宁等地消费者[39]。在这一阶段,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主要以零散的方式出现,他们跳出了主流的市场和政府主导模式,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影响力有一定的局限性。
2008年可以作为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三聚氰胺牛奶事件深刻撼动了主流食品体系的信任基础,让消费者进一步感受到寻找安全食品的迫切性,特别是有婴幼儿的家庭[33]。同年人大农发学院与北京海淀区政府合作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并在此基础上发起了全国社区支持农业大会,是社区支持农业这一新型食品体系实践形式在全国快速推广的重要推力。此后,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NGO组织参与到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和研究中,2010年中国农大人发学院发起了“巢状市场减贫项目”,2016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起成立了清华i侬生态农业消费合作网络。国内最早建立的农夫市集为2010年开始运作的有机农夫市集,由日本艺术家植村绘美联合当地有机小农场发起,已由开始的不定期志愿者活动发展为一个规范运作的社会企业,并联合上海农好农夫市集、广州沃土工坊、西安农夫市集开始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参与式有机认证体系。根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底在全国近20个省市出现了80家左右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北京、上海、南京、常州、广州、成都等城市都建立了常规性的农夫市集[12]。
除了直接与食品消费相关的活动,很多以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运作的都市农园还具有市民文化休闲的功能,通过劳动份额吸引消费者参与到农园的日常运作,并且举办各种农事活动,促进了消费者之间的交流,开展消费者教育,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城市日常的自然生态环境[40]。同时,巢状市场研究认为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农村旅游都具有替代主流市场模式的作用,拓展了农业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充分发掘农业的多功能性[23]。从这个角度看,国内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发展规模更大,且十分具有中国内在的特色。
三、替代食品体系中多元主体参与互动
基于替代性食物体系在中国发展历程,研究者们达成共识:替代性食物体系是对主流食品体系的解构与重建,其中以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为核心,并离不开政府和不同类型中介组织的参与和支持。
(一)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结
替代性食物体系新型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减少乃至去除中间商等中间环节,建立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如范德普勒格教授所说,新型结构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有特殊性[11]。
1.替代性食物体系中生产者特征
通过对全国13个省市不同替代性食物体系案例调查,司振中等发现“真正”的农民在替代性食物体系中参与较少,很多发起者和生产者是自称为“新农人”的城市精英[4]。檀学文和杜志雄对“新农人”的特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他们的研究对象为北京郊区及周边从事替代性食物体系生产的41家农场,他们发现这些农场的经营者70%在40岁以下,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63%,半数以上都不是农业户籍。也就是说主动从事替代性农业的生产者大多数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对主流食品体系运作有较为深刻认识和反思的青年城市精英。由于其自身特点,他们的经营也存在优势和不足,优势是他们具有相对丰厚的资金投入,根据调查投入在10万~500万元的农场占78%,而且都采用了生态型的农业技术,不足在于大多数生产者没有农业户籍,因此不拥有农场耕地承包经营权,50%的农场完全依靠租赁土地,26%的农场部分依靠租赁土地[29]。
不过并不能说“真正”的农民完全被排斥在新型结构之外,这也并不是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的本意,比如爱农会的合作农户都是传统农户,中国农大“巢状市场”项目中的生产者也都是合作村庄的村民。只是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由于其自身能力和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到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建设中。
2.替代性食物体系中消费者特征
参与替代性食物体系构建的消费者大多数都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陈卫平等对5个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会员进行了调查,65%的会员在31~40岁,19%的会员在41~50岁;86%的被调查者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50%左右的会员家庭月收入在15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上的占21%[33]。这与国外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消费者大多数由城市精英组成的情况是一致的。
不过中国的消费者又有其自身特点,他们参与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最为主要的动机是获得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保护、食品交易过程中的公平贸易的关注程度不高[4]。这与中国消费者总体上缺少消费者责任感,对自己消费行为的负外部性认识不足具有相关性[30]。
3.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
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是解决食品体系中信息不对称的核心路径,进而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形成食品生产和消费的良性互动[41]。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建立和加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一是采用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中可能出现的自然和市场风险,改变主流食品体系中生产者、消费者以个人理性为中心、相互割裂的结构,提高生产者参与健康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二是采用开放式的生产方式,消费者、媒体和其他第三方机构可以随时通过实地考察来了解生产过程,消费者不仅能够获得真实的信息,也自然形成对生产者的监督;三是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频率,比如四川安龙村高家农户要求消费者在定菜之前必须到安龙村进行实地考察,不同类型的生产者也会定期组织各种活动,邀请消费者参加,既了解生产过程,也体验乡村文化和生活,促进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流[18, 42];四是共享的第三方关系,陈卫平和帅满的研究都表明朋友、亲戚或是熟人推荐是消费者加入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最主要原因[42,22]。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提供了便利,成为加强他们联结的重要方式。一种模式是整个农庄生产和管理基于现代物联网技术,江苏常州的e农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消费者租赁农庄土地后,既可以自己亲自参与耕种,也可以通过网络向农庄管理人员发出种植指令,让管理人员代为种植,通过网络实时通信,消费者可以随时了解自己作物的生长状况[43]。另一种模式是将网络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交流的平台。很多生产者在QQ、微信、微博、豆瓣、淘宝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媒体上建立了自己的账号或是店铺,生产者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发布与生产者理念、产品、生产过程相关的各类信息,消费者也可以参与相关信息的讨论和评价,从而建立起有效互动。陈卫平的研究表明网络平台的互动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增强了消费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从而提高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信任度[17]。
不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连接并不能完全解决两者之间的互动和信任问题,双方自身特点对紧密联结的形成提出了挑战:首先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注点不一致造成了两者关系的内在张力。消费者主要关心食品安全,生产者除了保证安全生产外还重视本地化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因此农产品供应的种类有限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之间矛盾明显[33, 44]。其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缺乏有效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双方不能有效传达各自的价值观念和需求。笔者研究案例中农民给自己生产的生态猪肉定价为市场产品价格的两倍,但是并没有说明定价背后的原则和价值,由于当年猪肉价格高企,两倍市场价格引起了消费者的疑虑和不满,但是消费者出于对农民的尊重,没有提出质疑,而是选择不再继续购买,这对农民和消费者双方都是一种损失[45]。现在很多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定价方式都是农场单方面定价,缺乏与消费者的友好协商[33]。由此可见,在替代性食物体系中建立“公共池塘资源”——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以及对应的产品——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产消双方深度互动,形成高度共识。
(二)中介组织参与
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中介组织的进入有利于建立和稳定替代性食物体系结构,主要类型有生产者组织、消费者组织和第三方机构。
生产者组织具体形式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为小规模农户提供平台,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有机会参与到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决策过程中[46]。具体来讲,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了多种服务,帮助农民解决从生产到市场渠道建设的多重困难,技术服务帮助农户合理总结和应用传统的生态种养方式,或是引入新的有机种植技术;生产过程管理让合作社成员按照统一要求进行田间管理,从生产过程保证产品质量;市场销售服务建立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组织各种农事活动,管理销售过程等。但是,合作社作为小农户的联合体仍然是食品体系中的弱势一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小农户技术和沟通能力不足、资金资本匮乏等问题[45]。
消费者组织是社区支持农业中“社区”的实体性体现。帅满指出消费者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通过关系网动员具有相同生态环保理念的成员加入,成员间的互动增进了相互间的感情,从而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关系[22]。除了共同理念外,公共活动空间和物流等基础设施、已有社区组织的支持也是消费者社区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者以组织的形式与生产者建立联系能够减少单个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与生产者保持持续的、制度化的互动,从而建立起信任关系[22]。目前我国消费者组织发育还是相对薄弱的环节[30]。
第三方机构包括NGO、社会企业、科研机构等多种类型组织。NGO组织香港社区伙伴从2003年开始在国内开展“社区支持农业”培训,2004年开始在云贵川和两广开始社区生态农业项目活动,广西横县是其项目点之一。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是一个环保NGO,从2003年开始向消费者宣传化学农业的危害和生态农业优势,并组织有机农产品购买。相比NGO对替代性食物体系建设的支持作用,社会企业更加直接地参与到新结构的运作中,比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广州沃土工坊,他们成为交易活动的组织者和生态农产品的中间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产品和信息交流的平台,扩大了替代性食物体系的网络覆盖范围[40]。科研机构在替代性食物体系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包括前面提到的人大农发学院、中国农大人发学院,他们不仅仅是新理念的引入者,更是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通过组织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和活动,极大推动了替代性食物体系理念在公众中的广泛传播。
相比生产者和消费者组织,第三方机构在知识储备和社会网络上具有优势,他们往往是替代性食物体系相关价值和理念的引入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开展食品安全、公平交易等价值理念的教育工作,有助于克服国内产消双方在知识和价值认识上的不足。不过由于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社会影响认识不足,为了维持新型结构的运转,第三方机构会有一定的妥协,更多地从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者教育中的社会价值观念塑造[47]。随着实践发展,第三方机构在新结构中的协调和统筹功能愈发显著,比如由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发起的参与式保障体系建设是国内第一个非商业性的有机认证体系,旨在通过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参与对有机生产者进行认证,简化认证中的文本工作,降低认证成本,这一工作一方面借鉴了大量国外经验,另一方面还联合了国内多个从事相关工作的NGO和社会企业,是替代性食物体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新探索[48]。
(三)政府支持
农业生产和食品消费具有强外部效应,需要政府在制度建设和政策扶持上给予重视。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将食品安全管理和生态农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内容,国内与食品安全和生态农业发展相关的认证规则和认证机构都是由农业部和环保部制定和设立。同时,地方政府也鼓励生产者对农产品进行认证,比如山东寿光对获得食品认证的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给予补贴[45]。但是操作中这些认证体系在消费者中的认可程度不高,甚至有部分消费者表示他们对所在地区的认证食品极度不信任。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建立和运转认证体系中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和参与,整个体系运转的信息透明度不高[38]。
丁溴东莨菪碱为M胆碱受体阻滞药,对胃肠道、胆道和泌尿生殖道平滑肌有解痉作用。作为一种季铵衍生物,丁溴东莨菪碱不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因此,不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抗胆碱能副作用,但脏器壁层内的神经节阻滞作用和抗毒蕈碱活性会导致周围抗胆碱能副作用。丁溴东莨菪碱注射液可引起严重不良反应,包括心动过速、低血压和过敏反应,这些不良影响可能导致基础性心脏病患者(如心力衰竭、冠心病、心律失常)或高血压患者的致死性结局。心脏病患者应慎用丁溴东莨菪碱注射液,如必须使用,应对这些患者进行监测,并确保急救设备处于备用状态,且经过设备使用培训的人员可随时响应;心动过速患者仍禁用丁溴东莨菪碱注射液[1-2]。
檀学文和杜志雄指出政府虽然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但是更多采用是规模化经营、大市场流通路径,对农业生产和食品消费中的节能减排、公平交易、小农户发展等社会价值关注不多[25]。总体来看,政府对社会内生的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关注和支持不够,现有研究发现的案例只有两个: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对小毛驴市民农园提供的土地优惠和支持、贵阳市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中明确倡导“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因此,学者认为政府应在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建议包括:政府承担起化学农业对土壤侵害造成的生态欠账,对实施生态农业的生产者在生产转换期提供补贴;支持小农生态农业,对生产者提供扶持政策;鼓励和吸引人才进入替代性食物体系,促进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和新型市场渠道建设[18, 49]。
四、总结与评论
替代性食物体系是对主流食品体系的反思,诸多社会行动者通过实践来改善消费者食品安全、生产者生计持续、保护生态环境。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的不同理论视角,他们的关注对象都是以建立生产者消费者联结、促进健康食品生产和消费为目标的行动,他们认为替代性食物体系是以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建立了新的信任关系和社会结构。不同概念又有不同的关注点,社区支持农业强调微观层面的集体行动单位——“社区”——的重要性,并认为生态农业和城乡互助是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巢状市场关注不同主体间的多元互动,提出以共同规范和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产品是替代食品体系发展的核心;食品短链关注中国食品供应链发展实践;农消对接重点分析食品体系与社会结构的脱嵌和重新嵌入的过程。
文章接下来总结了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的社会背景,并综合相关文献分析了发展过程。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是与全球主流和替代食品体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且具有中国特点,包括政府在认证系统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消费者参与价值基础、农村旅游的大规模发展。第三部分论述了现有文献关于不同主体在替代性食物体系中的参与和互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主体都是社会精英群体,小农户在中介机构的支持下参与到替代性食物体系之中,中介组织在理念引入和网络协调中发挥了重要功能,现代信息技术也为不同主体的互动提供了便利。目前政府对基层内生性的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支持力度不够,有待加强。
我国现有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社会实践,这一领域还有大量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评价这一社会现象:(1)现有研究主要都是基于少数个案的分析,对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整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不够,目前仅有小毛驴农场提供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不完全统计名单。由于替代性食物体系实践具有多样性,加上中国地域广阔,进行全国性调查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全面了解不同实践模式发展数量、参与主体、对食品安全、农业和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是评估这一新兴市场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必要基础;(2)替代性食物体系在理论上强调价值观念在新的食物体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对不同行动者价值观念建立、转变和达成共识过程的调查和分析深度不够;(3)现有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参与的市场结构,没有对企业在生态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中的参与进行研究,但是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这一议题也是国外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的讨论热点,通常称为替代性食物体系的传统化(conventionalization);(4)目前替代性食品体系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内部,缺少与生态农业生产研究者的互动,因此不能有效回答生态农业的生产效率、可行性等技术问题。因此跨学科研究可以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多个维度充分理解和分析替代性食品体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1] Busch, L.and Bain, C. New! Improv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Agrifood System.RuralSociology, 2004(3): 321-346
[2] 叶敬忠.发展的故事:幻想的形成与破灭.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 Goodman D, DuPuis E M, Goodman M K.AlternativeFoodNetworks:Knowledge,Practicesand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2012
[4] Si Z, Schumilas T, Scott S. Characterizing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China.Agriculture&HumanValues, 2015(2): 299-313
[5] 屈学书,矫丽会.我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研究进展.广东农业科学,2013(9): 214-217
[7] Feenstra G W. Local food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AmericanJournalofAlternativeAgriculture, 1997(1): 28-36
[8] Watts D C H, Ilbery Maye D. Making reconnections in agro-food geography: alternative systems of food provision.ProgressinHumanGeography, 2005(1): 22-40
[9] 陆继霞.替代性食物体系的特征和发展困境——以社区支持农业和巢状市场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6(4): 158-162
[10] Marsden T, Banks J, Bristow G. Food supply chain approaches: Exploring their role in rural development.SociologiaRuralis, 2000(4): 424-438
[11] van der Ploeg, J.D., Ye, J., and Schneider, S.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nested, marke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Brazil and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ofPeasantStudies, 2012(1): 133-173
[12] 石嫣,世界范围内的社区支持农业∥第七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资料汇编.北京,2015
[13] 徐立成,周立. “农消对接”模式的兴起于食品安全信任共同体的重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59-70
[14] 沈旭. CSA:可持续农业的另一种市场体系.农业环境与发展2006(5): 22-24
[15] Chen, W. Perceived value of 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ae (CSA) working share. The construct and its dimensions.Appetite,2012(2): 37-49
[16] Shi, Y, et al. Safe food, green food, good food: Chines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d the rising middle class.InternationalJournalofAgriculturalSustainability,2011(4): 551-558
[17] 陈卫平.社区支持农业(CSA)消费者对生产者信任的建立:消费者社交媒体参与的作用. 中国农村经济,2015(6): 33-46
[18] 程存旺,周华东,石嫣,温铁军.多元主体参与、生态农产品与信任——“小毛驴市民农园”参与式实验研究分析报告.兰州学刊,2011(12):55-60
[19] 肖芬蓉.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探析.绿色科技,2011(9): 7-8
[20] 潘家恩,杜洁.社会经济作为视野——以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为例.开放时代,2012(6):55-68
[21] Si, Z.and Scott, S. The convergence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within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the case of the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China.LocalEnvironment: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JusticeandSustainability,2015: 1-18
[22] 帅满.安全食品的信任建构机制——以H市“菜团”为例.社会学研究,2013(3):183-206
[23] 叶敬忠,王雯.巢状市场的兴起:对无限市场和现代农业的抵抗.贵州社会科学,2011(2): 48-54
[24] 叶敬忠,丁宝寅,王雯.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 2012(10):4-12
[25] 檀学文,杜志雄.从可持续食品供应链分析视角看“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56-165
[26] 赵玻,葛海燕.食品供应短链:流通体系治理机制新视角.学习与实践,2014(8):35-43
[27] 殷戈,朱战国.农户参与食品短链模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江苏农业科学,2016(4):501-504
[28] 杜志雄,檀学文.食品短链的理念与实践.农村经济,2009(6):3-5
[29] 檀学文,杜志雄.食品短链、生态农场与农业永续“京郊例证.改革,2015(5):102-110
[30] 徐立成,周立.食品安全威胁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消费者行为分析与“一家两制”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24-135
[31] 徐立成,周立,潘素梅.“一家两制”:食品安全威胁下的社会自我保护.中国农村经济, 2013(5):32-44
[32] Yang, H., Vernooy, R., and Leeuwis, C. Farmer cooperatives and the changing agri-food system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AJournalonContemporaryChinaStudies, forthcoming
[33] 吴天龙,刘同山.“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商业研究,2014(8):90-94
[34] 陈卫平,黄娇,刘濛洋.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展望.农业展望,2011(1):54-58
[35] 冯彦敏,赵海波.社区支持农业(CSA)——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绿色之路.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8):67-72
[36] 石嫣,程存旺,等.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1(2):55-60
[37] Sanders, R. A Market Road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Green Food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Developmentandchange, 2006(1):201-226
[38] Scott, S., et al. Contradictions in state-and civil society-driven developments in China’s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ector.FoodPolicy, 2014(C):158-166
[39] Mol, A.P.J. Governing China’s food quality through transparency: A review.FoodControl, 2014(43): 49-56
[40] Vernooy, R. For Food Security, China Tries an Alternative to Industrial Agriculture.Solutions,2012(1): 62-69
[41] 绍隽,张玉钧,等.社区支持农业型市民农园休闲模式研究.旅游学刊,2012(12):74-79
[42] 李峻.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创新模式分析.世界农业,2012(9):130-132
[43] 陈卫平.社区支持农业情境下生产者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的策略——以四川安龙村高家农户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3(2):48-60
[44] 陈莉莉,胡以涛,等.基于社区支持农业的食品安全解决途径——以常州的都市e农庄为例. 安徽农业科学 2012(7):4376-4380
[45] 杨波.“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流通渠道分析:机遇和主流渠道对比的视角.消费经济,2012(5):21-25
[46] Chen, A. China’s Path in Developing Organic Agriculture: Opportun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Small-Scale Farmers and Rural Development//Department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al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Waterloo: Waterloo, Ontario, Canada,2014
[47] Klein, J.A. Creating ethical food consumers? Promoting organic foods in urban Southwest China.SocialAnthropology,2009(1): 74-89
[48] 陈宇辉,蒋亦凡,等. 专题:城乡信任与PGS∥比邻泥土香.社区伙伴: 香港,2016
[49] 何飞,李怀英. 我国社区支持农业(CSA)发展模式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农村经济, 2013(10): 51-54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Development and Multiple Actors’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 Review
Yang Hua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ies about the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 development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results and identifies the iss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It first introduces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 studies in China, including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nested market, short food supply chains and producer-consumer connection. The causes of rising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re the serious food safety problem, the un-balanced power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in the mainstream agro-food system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ddle income citizens. Its development close relates to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gro-food system. And the government domin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give limited support to the emerging food networks. The consumers and majorityof producers are social elites, and the small scale farmers participate in the networks under the support of intermediaries. Further studies c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llowing issues: the landscape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valu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the role of companies in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introducing technical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to research.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Nested market; Short food supply Chain; Producer-consumer connection
2016-07-26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产要素均衡视角下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项目编号14CJY044)资助。
杨 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讲师,邮编:430079; 王习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