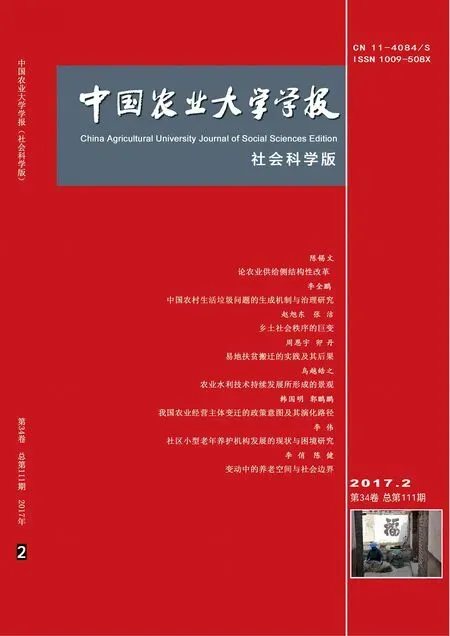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李全鹏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李全鹏
文明的高度如同木桶定律那样,取决于其短板而非长处。作为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垃圾问题虽然像梦魇一般纠缠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是那块不被关注的短板。伴随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路线,中国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已使这块短板凸显了出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作为现代文明之病已从城市快速渗透到广袤的,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地区。当农民完全被纳入大众消费社会之时,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就不可能逆转,也是现代文明崩溃的起点。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迄今大都集中在垃圾问题的分类、回收再利用等技术和经济层面的探索上,但散乱的垃圾处理和生活垃圾的日常性取决于农村空间的再造和村民主体意识的重建。因此,文章基于农村地区的调研,从被裹挟于现代化浪潮的村民和村落治理的角度来解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层面探讨一条综合治理的途径,即共助体系的形成。一是发展社会导向的政策与退耕还林模式的公助;二是基于公共性互助纽带的重建;三是通过乡土教育来推动村民的自助和对乡土价值的重新认识。
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困境; 退耕还林模式; 基于私情的公共性; 乡土价值
一、问题的提起
垃圾是现代化的产物,其问题的辐射面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发展或处理技术水平的范畴。当这样的产物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与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社会病理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的复杂问题。但对于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垃圾问题,迄今的研究焦点大都可归为对现状的概述与技术性研究,即垃圾处理与资源化管理等层面。如张英民、张立秋、李广贺主编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及资源化系列丛书》对农村生活垃圾的特征、处理、资源化管理进行了系统性概述,并对部分农村生活垃圾产业进行了调查,以及对不同类型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实例进行了分析[1-3]。由此指出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乡村规划编制和实施较为滞后,用地布局不尽合理,农村规划建设管理较为薄弱,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管理体制落后等。与此类似的研究论文,例如,王莎等、赵晶薇等、杨曙辉等、陈军等皆对农村垃圾的现状与处理模式进行了探讨,也都指出了村民环保意识欠缺,政府治理农村垃圾的缺位,缺乏垃圾治理制度体系的管理等问题[4-7]。章也微将环境问题当作一个经济问题,主张应该加强政府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中的主导作用[8]。此外,对现状的量化研究,岳波等共统计134个村庄生活垃圾情况,分析了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特性及其组分特点[9]。
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垃圾问题的政策导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缺乏解决垃圾问题的主体——村民的角色,以及主体间的互动。生活垃圾问题与每一个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垃圾的散乱看似村民的自我选择,并营造出的恶果,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浪潮,村民生活方式的结构性转变往往将村民置于无力选择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境下,如何促动村民的参与是垃圾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垃圾问题绝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其背后是整个村落的凋敝、人心涣散的社会病理。特别是针对一些村落,业已形成的延绵几公里的垃圾路带,该由谁、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理,需要探讨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因此,本文依据在H省(2014年8月)和J省(2015年8月)的农村地区展开的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首先对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困境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来探讨“公助·互助·自助”的综合治理模式。
二、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与治理困境
伴随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大众消费社会已逐渐形成。大众的特质,如同奧特嘉所指出的那样,是他律的,而非自律的,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物质恩惠,却对整体社会的未来欠缺责任感[10]。近年所谓“双十一”的消费狂欢恰恰印证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弊端。盲目的消费即使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对资源和能源的掠夺性开采,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及消费过后的大量废弃。在地球资源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现代文明之病,就是生活垃圾的无节制增多。2007年为止,农村地区的垃圾已致使1.3万公顷农田不能耕种,3亿农民的水源被污染*新华网:环保总局副局长:农村3亿多人面临饮水不安全.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70607/14147059.html,2007-6-7。,每年新增7 000万吨生活垃圾未做任何处理*人民网:农村垃圾数量猛增 住建部未来5年破解“垃圾围村”http:∥env.people.com.cn/n/2014/1119/c1010-26051391.html,2014-11-19。。至2016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垃圾总量已达到每年1.5亿吨,其中经过处理的垃圾只有50%*央视网:农村垃圾年产生量达1.5亿吨只有一半被处理.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6-19/7909149.shtml,2016-6-19。。垃圾的增多无疑是人类为追求更快捷、更富裕生活的结果,但文明的高度不是取决于其长处,如同木桶定律那样,是取决于其短板。在中国,这种无反思的现代消费生活模式已从城市快速渗透到广袤的、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地区。当农民完全被纳入大众消费社会之时,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就不可能逆转,也是现代文明崩溃的起点。
这是因为,垃圾的大量出现,所折射出的并不只是该如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处理技术上的课题,更是揭示了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的文明危机。比如日本,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国家,好似已经跨越了环境问题这一屏障,然而现实是,环境问题不仅没有消失,而是深刻地融入到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虽然日本社会拥有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但垃圾问题这个无法消解的难题,将会长时期地萦绕在这个列岛之上。日本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即便是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处理技术也无法对应这个难题,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时,除了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外,还应该思考如下所述的问题生成机制和所面临的治理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首先,垃圾是现代化的产物,在无机物产品的大量消费下,无法降解的垃圾才会应运而生。这一点在H省和J省的村落调研中也得到了印证。H省A村位于山区,村内有一条长达几公里沟堑,在沟下和斜坡的四周散落着大量的垃圾,有方便面的盒子、香肠包装皮、塑料制品、瓶子、罐子等,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垃圾路带。经观察,每日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村民会毫不犹豫地抛向沟内或沟堑的周边。对此,村民A(女,67岁)说,“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可扔的,有瓶瓶罐罐都要留着装东西,有塑料也会留着包个东西什么的,(当时)有不要的东西也会往沟里扔,但在沟外垃圾的增多,不过是这7~8年的事”*2014年8月16日,于H省A村。。另一位,在农闲期去城里打工的村民B(男,45岁)说,“垃圾多了,可能是生活好了,买的多了,但和城里(生活水平)还是有差距……我希望孩子高中毕业以后留在城里工作生活,虽然自己不太想去城里生活”*2014年8月16日,于H省A村。。
中国的农村,由于二元结构的影响,村民不只是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保障上,甚至在心理层面,相较于城市居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从上述两位村民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垃圾问题的凸显只是最近几年生活改善的结果,但往沟里的丢弃行为,却是作为一种“传统”的惯习沿袭了下来。因此,在无法降解的现代化产物和传统丢弃行为的冲突下,垃圾问题凸显了出来。传统的丢弃行为本身并没有多少负面的意义,因为,所丢之物皆为有机物品,终究会回归土地。但是,急速的商品消费大潮将每个人裹挟在内,村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长久积习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但在访谈中,几乎每个被访者都认为“往沟里扔垃圾是不好,但大家都这么做”的行为规范下,难以建立起自己既是环境问题制造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意识。当沟堑作为共有地被垃圾填满的时候,势必会反噬每一个垃圾丢弃者和他们的下一代。
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环境问题的相关性同样体现在J省D县的农村里。D县的J村不仅面临着生活垃圾增多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兴起,禽类和牛、猪等家畜的排泄物在当地引起了一系列的难题。村民的养殖场大多设置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招致大量的苍蝇,异味也不断引起邻里之间的纠纷。未经任何处理的排泄物被放置在道路和田端,成为寄生虫的温床,雨天过后,排泄物被冲进田里,引起农作物的枯死。现代科学诞生之前,世间没有无用、可丢弃之物。动物的排泄物本来作为肥料,化为土地的养分,滋养农作物,即人类·动物的排泄物→农作物·土地→食粮→人·动物,这一循环体系在农村社会里的劳作与生计发挥着功能。然而,传统的循环哲学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堪一击。
D县位于省会城市的2小时经济圈内,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外出务工的村民逐渐增多。在所调查的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或长或短的外出务工成员。当中,所访问的老年人都坚持认为,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但自己不想去城市生活,觉得不会适应那里。J村C村民夫妇(丈夫62岁,妻子59岁)都表示,“去城里生活过,但还是觉得这里(农村)好,城市什么都贵,不像这里还能种点菜和水果,冬天在窖子放些蔬菜,不用再买了”*2015年8月20日,于J省J村。。该夫妇的儿子、D村民(男,36岁)则表示,“家里除了苞米地以外,自己(没时间)已经不种菜了,苞米价格又低,自己和老婆都要出去打工,而且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还是想让他在城市工作、生活”*2015年8月20日,于J省J村。。两代村民相较而言,父母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种水果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而儿子除了苞米地的收入以外,要寻求打工才能拟补家用。这就意味着,原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村落共同体的自给自足或互帮互助的体系得以维持,当生计被纳入大城市经济圈后,加大了对货币经济的依赖。因此,进城打工并没有实现他们最初的预想——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比父辈更加宽裕一些,相反在城里的打工经历使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穷困感和焦虑。
然而,维持生计方式的转变,除了没有让他们更加宽裕之外,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加重了环境的恶化。C村民(妻子)说,“儿子只在农忙期回来帮助种地,其余时间都在外面打工挣钱……粪便我们都不用了,就用化肥,省事还干净”*2015年8月20日,于J省J村。。E村民(女,42岁)说,“家里也没几亩地,丈夫在外面打工,我也有时候去(打零工),家畜的粪便早就不用了”*2015年8月20日,于J省J村。。J村委会G干部说,“化肥的用量用法我们也都讲过,但是都图省事,本来化肥要分几次撒,但要去打工,没时间回来,所以干脆在种的时候,把(几次量的)化肥一起埋进去”*2015年8月21日,于J省J村。。为了弥补与城市生活上的差距,村民不得不做出了一些作为个人的合理化决定,然而这种个体合理化的行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社会整体陷入不合理的状态。J省所在地被称为肥沃的黑土地,但黑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每年流失的黑土层厚度为1厘米左右,同时有机质以平均每年0.1%的速度下降,导致土壤生物学特征退化,作物病虫害发生率提高,耕种全部依靠化肥来支撑*人民网:黑土地长期“超载”流失严重:种地靠化肥撑着.http:∥sc.people.com.cn/n/2015/0804/c345167-25832233.html,2015-08-04。。正如村干部E所说的那样,“土地本来是具有力量的,即‘地力’,可以自我消化、净化,但现在不行了,化肥已经让土地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村民觉得产量下降,于是就加大化肥的使用量”*2015年8月21日,于J省J村。。化肥是省事的、干净的,而动物的排泄物则是污秽的、麻烦的,以及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都可以看出,村民对现代化毫无防备的拥抱。在这当中,与生态系统融合为一体的传统生活体系,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抛弃掉,甚至形成了化肥→土地退化→低产→加大化肥使用量→土地更退化的恶性循环。
(二)人心的涣散与行政权威的弱化
垃圾的散乱是由于在共有地的丢弃和堆积,所调查的H省和J省的村和乡镇干部并没有强烈的紧迫感。对他们来说,垃圾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积累下来的,并且还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与经济发展相比,不会成为当前的主要课题。
对于H省A村大面积垃圾带的问题,乡干部说,“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我们也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但解决需要时间和资金……现阶段能做的,加强对村民的教育,比如垃圾站点写上一些环保的标语”*2014年8月18日,于H省A乡政府。。从中可以看出,垃圾治理依然有赖于上级(国家政策)的扶持,在没有具体对策之前,用口号进行弥补。然而A村垃圾站点的环保标语,反讽式地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村民并没有把垃圾倒进垃圾桶里。不仅如此,口号治理的弊端,即反功能的效果却异常地突出。首先,复杂问题的单纯化。垃圾作为将一个关乎当地所有人的问题,需要共同关注、商讨、应对,但这一系列的措施被简化为几句口号。其次,作为主管部门,口号治理成为工作任务终结的装饰,掩盖了工作的不到位。如,“村民看到了(不要随便倒垃圾)标语,但都不配合”*2014年8月18日,于H省A乡政府。。而现实是,村民B说,“(该村)哪没有垃圾,扔哪都一样”*2014年8月16日,于H省A村。,如实地反映出破窗理论[11]的效应。第三,在一些村落,甚至出现诅咒谩骂式的标语,不仅将责任简单地推卸掉,并且严重阻碍了理性思维的绽放。对垃圾治理口号的理解,管理部门和村民之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断裂。既然是一个复杂的、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反思、梳理问题的所在是问题解决的第一步,而情绪宣泄式的口号治理于事无补。
相较而言,J省J村的状况明显好于H省A村,并没有大规模的垃圾路带问题,上级镇政府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但村内外不难发现零零散散的未回收垃圾。即便像日本那样,将垃圾非可视化,但问题依然存在——在哪里烧,在哪里埋的纷争不断。从根本上来说,垃圾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每个村民的主体性意识,在生活中实践4R的理念,即REFUSE(拒绝过渡消费)、REDUCE(减少浪费)、REUSE(反复使用)、RECYCLE(循环再利用)。从J村和镇干部的角度来说,家畜排泄物的问题,由于直接引起了邻里之间的纠纷,更让他们感到棘手。对于随手扔垃圾和粪便所引起的纠纷,村镇干部皆认为,“一些村民不顾别人的感受,是由于个人主义的蔓延……比起以前,现在的村民都不太听话了……水利道路等公共设施的修缮,出钱出力的活儿,都不情愿了”*2015年8月21日,于J省J村。。他们认为,村民态度变化的契机就是农业税的取消,村干部丧失了根据国家政策可进行强制性征收的法宝,对村民的控制力大幅度降低。但如果农业税征收时期有集体主义的话,那么也只能称之为“强制性集体主义”,现阶段的所谓“个人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钟摆效应的体现?
对农业税和各种分担金的强制性征收,村民们记忆犹新,再加上近年来青壮年的流失、以及消费欲望和贫富差距的同时扩大,加重了对未来的焦虑感。在这些因素的重叠下,即使2007年国务院和农业部共同发布了“一事一议制度”,规定了农田水利和土地治理等公益事业所需资金,采取由村民参加的“一事一议”的筹集办法,但都没有改变行政权威的不断衰落。虽然,在中国一些富庶的村落中,其治理看似章法得当,但并非是在村民参与下的治理,而是依赖于将村落成功企业化的村干部的个人权威,反之,在没有经济活力的村落则成为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散漫的村落组织[12]。在所调查的村落中,并没有一个卡里斯玛型的企业家,因此,村落急需的公共事业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村民所渴求的卡里斯玛是一个能让村落快速发展,其中所谓的发展即是指经济条件的改善。在追求更富裕、更便利的现代化生活中,主体性地去解决垃圾问题的意识自然也就被稀释掉了。
三、综合治理模式的探析
(一)“退耕还林模式”的公助
公助是指行政体系在政策上的导向与资金上的扶持。如果以发展的语境来概括当今中国现状的话,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爆发式的经济发展,与严重滞后的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如同在双轨道上单轮运行的双轮车一样,无法保证可持续的运转。垃圾问题在消费社会下的凸显,即是其写照之一。那么,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较有何区别?
经济发展包括,为促进产业开发而建设的基础设施、工厂等实体上的开发,可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学习等途径,较容易达到。而社会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硬件设施,这是与经济发展相重合的部分,包括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教育设施等生活条件的改善。第二是软件方面,包括社会组织和以社区建设为主的发展。第三是人本主义,即促进居民潜在能力的发展[13]。其中第二点和第三点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区别。对于社会发展的概念,在所调查的村镇干部中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工作的重心和规划依然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处于等而次之的地位。即使是在日益凸显的垃圾问题上,也是期待着国家指令的下达和资金的到位,对组织的散漫和村民的不合作,也只是对过往可强制性动员时代的怀旧。其潜台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而现实的逻辑是,村民在未完全富裕起来的情况下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并且,日本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经济与技术的发展非但没能消解生活垃圾问题,相反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在战略层面上,基层村落组织有必要转变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重建基于与他人的纽带和共生的共同体,以提高村民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课题的参与程度。
对于垃圾处理体系的建立,即回收、运送、分类、再利用这一具体的问题上,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解决、由谁解决散乱在各处长期积累下来的垃圾问题。如H省A村长达十几公里的垃圾带,是在村内共有地上形成,并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垃圾堆放地。快速且彻底清除这个共有地的垃圾,是摧毁破窗效应持续发生的基础,如若不然,随意丢弃行为的再生产将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但即便设立了垃圾处理部门,也不可能应对如此庞大的回收工程,如前所述,只是2016年的农村垃圾就已达到1.5亿吨,其中50%未加任何处理,这需要村民的集体力量,而基层村落组织也不可能再回到强制性动员的时代。因此,在思考如何激励村民参与垃圾回收的政策,可以借鉴退耕还林模式的途径。
退耕还林工程在世界环境保护历史上,是一项投资最大、政策性最强、区域面积最大、民众参与程度最广泛的生态重建工程。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退耕还林条例》规定,其政策是指国家向森林和草地环境弱化地区的农民发放粮食、资金、种苗等补助,激励村民进行复原林地的一项政策[14]。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用生态补偿和经济上的激励方式带动了村民的广泛参与,并促进了村民的增收和森林覆盖率的上升。以此模式为基础,在对应大面积垃圾路带的时候,可以期待在短时期内将散乱的垃圾彻底清除掉。第一,行政体系和回收部门的单独行动不可能在短期内回收多年积累下来的垃圾,花费时间过长,破窗效应则无法消解。第二,需要多数村民的参与,国家按回收垃圾的重量和劳动时间支付给村民一定的经济补助,激励参与度的提高。第三,规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和时间内完成回收、分类及搬运。第四,此后产生的生活垃圾由重建的垃圾处理体系进行回收。
农村地区工业垃圾的倾倒和堆放,以及污染工厂的排污,其中的受益人与受损人利益界限分明,相较而言,在法律和政策的完善下易于产生问题意识和采取行动。而农村生活垃圾,比如随意丢弃垃圾行为,其中所产生的利益没有人可以进行独占,因为受益者和受损者是“大家”,由所有村民共同承担,利益界限不明确。这样一个隐蔽的、长期的、复杂的,是村民在并没有完全富裕起来而产生的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问题的社会化,而行政手段或公权力对个人生活介入的程度有限。因此,对于共有地的垃圾问题最初运用经济补助方式来促进村民的参与,在短期内是一个有效的权宜之计。村民在参与中,必然会理解到无法自然降解的垃圾对居住环境和农业耕种的危害。同时,焕然一新的自然空间和居住环境的诞生,是个人调整自己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契机——自己是破坏者还是保护者的角色定位,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终结随意丢弃行为的再生产链条。
(二)基于公共性的互助纽带
以经济方式激励村民的参与是为了保证能够集中地、快速地清除共有地的垃圾,杜绝随意丢弃行为再生产的举措。但既然是一个公共课题,那么长期内还是需要村民在互助的纽带下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现有的课题,而不是将问题甩给行政部门。对此,行政部门和NGO等团体可提供有关垃圾分类、有害物质的学习,以及对4R理念实践的支援。对于村民来说,互助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对乡村的爱护,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即公共性的建立。
对于公共性的解析,日本学者荒川康指出其具有三个层面,第一是“法律和制度的公共性”,第二是“国民共同财产(自然及文化遗产)的公共性”,这两种公共性可以从上述的公助当中去寻求。第三是与前两者所体现出的“公”不同,相较而言具有“私”的性质,即“基于私情的公共性”[15]。对于共有地的保护和再生,不能只以前两种公共性为基础进行论述,因为“基于私情的公共性”依托的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生活世界,是支撑个人行为的根源性要素,并且无论哪种公共性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活动而习得,即“可培育的公共性”[16]。对于村民来说,“基于私情的公共性”是对生我养我的村落、山川的爱护,是一种基于情感纽带,共同保护村落的公共性。与“基于私情的公共性”对照起来,垃圾的散乱所折射出的问题是,村民为何对自己不可替代的生活世界的恶化会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以及是什么阻碍了公共性的建立。
在前近代的历史长河中,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没有直接渗透到村落内部,村落自治在宗族的团结和族长的权威下得以维持。其内部建立起自卫、防火和互助的体系来巩固内部自治,这就是“基于私情的公共性”而形成的纽带和自治体系。但近代之后,在历经战争、饥馑所导致的人口流动中,自然村减少,行政村增多,自治体系逐渐弱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村民纷纷被编入生产队,再加上宗族权威的来源——祠堂和族训被作为迷信成为彻底批判的对象,进而村民不得不依附于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和村民的地位下降,以及村民对曾经的强制性集体主义的抵触,都反应在对村落公共事业建设的消极态度之上。被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的中国农民,村落整体的宗族观念稀薄化,依托于村落自治的“基于私情的公共性”消退。互为表里关系中的自治无法真正贯彻下去的时候,村民的公共性自然无法彰显出来。因此,在村民的精神结构中,村落作为一个公共圈已然缩小为家庭或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
至于“可培育的公共性”,在现时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土壤并不丰厚。近年来,随着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相较以前已有大幅度的改善。这些政策基本是为了纠正城乡差距所作出的补偿性措施,对于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即村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和能力的促进,却并没有太大的改观。相反,在所调查的村和乡镇干部皆怀念过去强制性集体主义的便利性,对所谓“个人主义的蔓延”和“农业税的取消”而导致的村民不合作深恶痛绝。究其原因,除了强制性集体主义已不再具有正当性以外,还有村落内部曾经均质化的结构也被打破。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浪潮的裹挟,职业和住所的分离增多,特别是城乡差距加速了分离的节奏。然而,除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村落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17]。在J省J村,田地拥有数量的多寡,以及养殖等副业的有无,决定了在村落这个场域中的经济资本占有量,收入差距可达10数倍以上。经济资本的基础是对子女教育进行投资的保障,进而又可转化为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曾经均质化的村落内部在出现阶层化现象后,如J村那样,养殖业者和田地大量拥有者与邻居之间,出现了雇佣关系。离农现象和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打击着曾经紧密的村民关系,有形的或无形的藩篱已然修葺在村民的内心深处。在这样的状况中,无法将一个长期的课题——公共性的培育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相较于村落整体的公共圈长期利益,充满焦虑的村民会转为向短期利益及家庭利己主义倾斜,正如所调查的农户中,其院子里都是规整的、干净的,而院子外则是垃圾散乱的世界。
传统的自治体系在今日已不可复制,但在今时与往日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与村民活动范围大幅增加相反,对公共课题的关心和行动的公共精神却大幅度缩小、稀薄化。无论是对权力体系的依附,还是对经济资本的追逐,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是一个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金钱与权力代替了语言沟通,对社会的整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已不再起到相应的功能[18-19]。因此,一个村落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大多数村民都能够参与协商、沟通的公共领域,那么共有地的垃圾只会成为大家的、他人的、政府的问题。因此,源于个人的,又成为公共课题的生活垃圾,势必要以主体间的对话,没有外在强制因素的对话中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需要时间一点一滴地达成新的行为规范。这种基于协商制度而形成的互助体系,是减少行政负担和促进村落治理的关键。对共有地垃圾问题的治理是村落空间的再造和自然环境的管理,同时也是“可培育的公共性”逐渐形成的契机。只有以村民为主体的沟通互动中,已然缩小为家庭和个人间网络的村民公共圈才有可能重新扩大,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能得以革新。
(三)乡土教育对村民自助的推动
成为公共课题的生活垃圾,其源头是在每个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积累出来的问题,无论是公助,还是互助,没有村民的日常实践不可能成功。因此,村民能否认识到自己既是问题的制造者,又是问题的受损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确立村民以自助的姿态,作为问题解决的主体,重新习得新的规范,如4R的理念和实践。对此,教育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教育行为往往存在于权力关系当中,带有象征暴力的色彩[20]。因此,促进村民的自助要竭力摒弃以上对下的指令式宣教,不仅是因为强制性的动员已不再具有正当性,也是将教育的实质回归于对学习者的支援。
推动教育不是期望学校回归乡村。因为,即便是回归,作为制度化的教育模式,其学习内容已然背离乡村的本位,甚至贬低乡村的生产和生活,已不再是能够给乡村人带来灵感、幸福与希望的教育了[21-22]。而且,学校的环境学习并没有对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发挥遏制的功能,恰恰相反,学校教育成为了既有生活生产路线的再生产装置[23-24]。现代社会中,对学校教育的偏重和对学历的偏执,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文明之病[25],因为其严重阻碍了作为人类本能的学习能力的发展。这个能力不是局限于青少年时期,也不是消极地等着被灌输的态度,而是贯穿人一生的自律知性[26]。但大多数关注中国农村教育的人士,往往将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将学习行为天然地限定为青少年时期,仿佛普通的成人村民不存在学习的需求一般,选择性地忘却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这一点恰恰印证了学历社会成为当今社会的文明之病。
因此,农村教育的重建,更应该思考如何促进自律知性的建立,面向终身教育的学习型社区的建立。在H省和J省的村落里,都已开设小型的村民学习室或图书室,但藏书大都为关于计生和农畜牧业生产类的书籍,并且利用者寥寥无几,所举办的学习活动屈指可数,其内容大多为农畜牧业的技术学习。终身教育的学习型社区需要将学习活动和村民的生活及现实课题结合起来,才能促发学习者的动力。这样的学习型社区,可以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与前述的互助是相呼应的关系。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参与人通过对话来形成公共意见[27]。这个源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原本是指与行政体系并行的,依据自由的、自发的语境而成立的体系,但在实践中其行使主体往往只限定于有学识的阶层,所以,该概念已逐渐转变为以民众文化活动为基础的公共领域[16]。因此,在思考如何形成新的公共意见和行为规范时,如果要通过乡村教育,那么与村民生活、与民众文化息息相关的乡土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首先,乡土教育是以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自然、地理为题材而进行的学习内容的收集、编纂、传承的参与式学习过程,是根植乡土,聚焦现实问题的学习活动。村民对乡土环境变化的了解,必然会折射出问题的所在。这是促动其能够自主地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即自助的实践,而这一点更加符合学习作为人类本能的特质。因为,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在近代社会才开始出现,是为了迎合工业社会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划一性教育体制不符合各具特色、问题不同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的传统生活中,人类在幼小时跟随长辈在实践中学习农作物的耕种,气候变化的掌握,家畜的管理、土地的利用。作为主体的个人,在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技术的活动中,积累经验,教育(=学习)与行为是一体的。其中并没有教与被教的概念,而是自己通过观察、试行、再修正这一过程来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也保证了当地生活体系和生态特色的融合,是当地作为一个可持续社会的根本。这一系列的实践恰好地体现出自助的重要性,乡土教育和垃圾问题的结合,是村落空间再造的契机,也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
其次,乡土教育是对当地固有价值的再确认,是培育对自己生活世界的“基于私情的公共性”的重建,同时需要纳入关于垃圾问题的学习和4R理念的实践。固有价值的重新确立,是以优势视角来重新审视乡土的途径,而一个垃圾遍地的乡村不可能让村民会感到有任何优势。在H省和J省所调查的村民中,即便是不愿意移居到城市的老人,也都无一例外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到城市里生活,认为城市是发展的前沿,至少看起来是干净的。一方面,说明村民对垃圾问题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但对应问题的知识和信息,无法从适当的渠道获得。另一方面说明这样的认知显示了在长期的二元结构下,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心理弱势和自我否定,加速了他们离开农村的步伐。这种对现状的妥协心理是建立自助精神和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对村民来说,经济落后尚在容忍范围之内,而一向优异于城市的田园风光已因为垃圾遍地而不复存在。一个凋敝的、环境恶劣的,村民以加速度脱离的村落,若要重新振兴,亟待乡土教育来促动村民重新认识当地的固有价值,而垃圾问题就是遮蔽其固有价值的一大障碍。这样的价值并非已完全消散,它就存活在村民的集体记忆当中,这是乡土重建的精神基础,也是村落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21]。此种情感力量同基于私情的公共性的意涵相契合,亟待学者等更多的人士去关注,去发掘。
五、结束语——共助体系的形成
垃圾问题,如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日本那样,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得以解决。但更让人忧虑的是对现代化毫无防备的、彻底的拥抱。当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病理,与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病理相结合的时候,垃圾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课题。可以说,农村生活垃圾是多重病理相叠加而凸显出来的问题,对其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思考一副综合性的处方。因此,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即行政体系的公助、村民主体间的互助和对村民自助的学习触发,探讨了根植于村落空间再造的治理模式。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那么,其顺序应该是,自助、互助、公助,也就是说在自助和互助不能完全应对的时候,才会有公助登台亮相的机会。但在中国农村地区,无论是快速清除共有地散乱的垃圾,还是公共领域成立和对乡土教育的推动,公助的力量不可或缺。但长期对公助的依赖,不啻于强化了村民生活世界的空洞化和殖民化,再加上无论是乡村干部或是普通村民对社会发展的概念和规划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其问题的所在也折射出当今社会整体对后者轻视的现状,因此本文特别强调了二者的区别,这是因为对于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质的生活垃圾问题,社会发展对互助和自助的促进更是长久的、根本性的机制。而在现阶段,对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的现实处方是,从这三个层面同时推进,以形成有机的共助体系,才能使4R的理念与实践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张英民,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管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2] 张立秋,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调查与实例分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3] 李广贺,编.村镇生活垃圾处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4] 王莎,马俊杰,赵丹,雷品婷.农村生活垃圾问题及其污染防治对策.山东农业科学,2014(1):148-151
[5] 赵晶薇,赵蕊,何艳芬,王森,安勤勤.基于“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探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S2):263-266
[6] 杨曙辉,宋天庆,陈怀军,欧阳作富.中国农村垃圾污染问题试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S1):405-408
[7] 陈军.农村垃圾处理模式探讨.江苏环境科技,2007(S2):96-100
[8] 章也微.从农村垃圾问题谈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事务中的职责.农村经济,2004(3):89-91
[9] 岳波,张志彬,孙英杰,李海玲.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特性研究.环境科学与技术,2014(6):129-134
[10] 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大众の反逆.神吉敬三,译.东京:筑摩学芸文庫出版,1995
[11] 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凯萨琳·柯尔(Catherine M. Coles).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陈智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12] 滝田豪.“村民自治”の衰退と“住民組織”のゆくえ∥黒田由彦,南裕子,編.中国における住民組織の再編と自治への模索:地域自治の存立基盤.日中社会学叢書No.6.东京:明石书店,2009
[13] 恩田守雄.開発社会学.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1
[14] 李国平,张文彬.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契约设计及效率问题研究.资源科学,2014(8):1670-1678
[15] 荒川康.墓地山開発と公共性.宮内泰介編.コモンズをささえるしくみ.东京:新曜社,2006
[16] 御代川贵久夫,关启子.環境教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2009.
[17] 李全鹏.中国農村部におけるゴミ問題の診断と治療∥林良嗣,黑田由彦,高野雅夫.中国都市化の診断と処方——開発·成長のパラダイム転換.东京:明石书店,2014
[1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9]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0] 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Pierre),让-克劳德·帕瑟仑(Passeron, Jean-Claude).再生産——教育·社会·文化.宫岛乔,译.东京:藤原书店,1991
[21] 孙庆忠.社会记忆与村落的价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32-35
[22] 孙庆忠.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人民政协报,2014-12-10
[23] 李全鹏.中国の初·中等教育における環境教育の制約要因について:その歴史と現状を通してー.日本一橋社会科学,2008(4):109-149
[24] 李全鹏.科学における環境教育の挑戦:環境知識から環境智慧へ∥教育実践検討会,編. 問い続けるわれら:生涯学習人として生きる.东京:教育実践検討会発行,2012
[25] Ronald P.Dore.TheDiplomaDisease:Education,QualificationandDevelopment. Great Britain: Inst of Education,1997[1976]
[26] Ivan Illich.DeschoolingSociety. Great Britain: Marion Boyars,1999
[27] 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4-121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of Rural Living Refuse in China
Li Quanpeng
The civilization degree is similar to Cannikin Law that relies completely on its shortest board. As a by-produc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household waste has affected the proceeding of modern civilization heavily, but it is ignored because of its role as the shortest board. In China, as the government is sparing no effort to promote the domestic-led economic strategy after year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shortest board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era of mass consumption. This means the mode of mass production, mass consumption, and mass abandonment has created a great deal of household waste. Furthermore, the waste as a diseas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rapidly penetrated from cities to vast and populous rural areas. When farmers a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mass consumer society, it is conceivable that the unsustainable social model will be irreversibl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will also begin to collapse. So far, the study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has mainly focused o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such as waste sorting and recycling techniques. But in fact, the treatment of scattered household waste in rural areas is linked closely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and villag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wing to the problem’s ordinarines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al dilemma of the waste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who are drawn into the wave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based on field work in China’s rural areas. Subsequently,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the formation of co-assisted system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was discuss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levels. The first is the making of social-oriented policy and public assistance similar to the model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The second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tual aid based on the affection publicity. The third is the promotion of villagers’ self-help and recognition of rural value through local education.
Rural Household Waste; Governmental Dilemma; Model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Publicity Based on Affection; Rural Value
2016-12-27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农村垃圾问题对村民生活结构的影响研究”(课题号为15BSH081)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李全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邮编: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