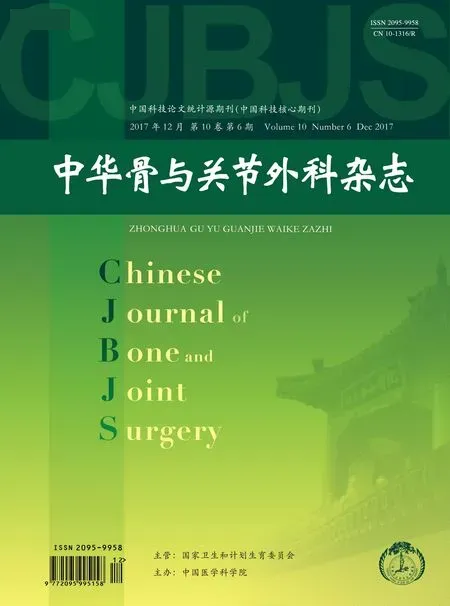叙事医学及其在临床医学的实践
郭莉萍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北京 100191
早在1979年,美国医学人文的先驱佩里格里诺(Edmund Pellegrino)就指出了当时美国生物医学模式之“罪”,今天看来,似乎也是我国医学教育和医学实践的写照:
“过度专业化;技术至上;过度职业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文化价值;医生角色职责过于狭窄;太多的治疗而非疗愈;预防、患者参与和患者教育不够;科学太多,人文太少;经济激励过多;忽视穷人和弱势群体;日常生活过度医学化;医学生受到非人道对待;住院医师劳累过度;语言和非语言沟通能力不足[1]。”
“叙事医学”这个概念近几年来被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医学教育者、临床医生、医学生所熟知,究其原因,大抵因为国内医学界普遍意识到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同时国内亟需改善的医患关系也敦促上述相关者找到破解困局的方式。被寄予厚望的医学人文如何在医学实践中落地?不少人意识到应该借助叙事医学的理论和方法。那么,叙事医学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它对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的作用究竟表现在何处?它是可以实践的吗?如何实践?叙事医学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本文将在以下探讨这几方面的内容。
1 临床工作为什么需要叙事医学?
“叙事医学”一词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丽塔·卡伦(国内有学者把Charon的姓翻译成“夏蓉”、“卡蓉”;但她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一书中指出,在希腊神话中Charon是把死者的灵魂从冥河摆渡到冥府的船夫,因此笔者认为将其译为“卡伦”这一男性化的名字更合适)于2000年正式提出,其定义为“由具有叙事能力的临床工作者所实践的医学”;而叙事能力又是“认识、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感动而采取行动的能力[2]”。叙事医学的来源包括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的“文学与医学”和“患者为中心的医疗”[3]。国内学者也对叙事医学的来源和工具性做了阐述,如凌峰教授认为:
“叙事医学(是)……跨越了文学、心理学、认识论、美学和各种后现代理论的交叉学科,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重新认识身体和心灵、痛苦和疾病,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潜力巨大的新工具。”[4]
除了上述来源,叙事医学也从晚近兴起的概念如“关系医学”(relational medicine)和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中吸取了养分。关系医学认为医学的本质是医患的互动。患者的疾病经历由其对意义、自我效能(agency)、自尊和对未来的感知所塑造,而疾病经历又是在与医生的互动当中产生的,如果医生可以了解患者的“心理-社会”方面的需求,他/她就可以为患者创造具有疗愈效果的治疗关系(therapeutic relationship)[5]。在医患共同决策的过程中,医生的专业能力、可信任程度、对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的了解、为患者提供信息的质量、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等方面决定了医疗决策的质量和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依从程度[6]。可以看出,关系医学和医患共同决策的核心思想都认为临床工作一方面是人与病的关系,但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代表着健康人的医生与脆弱和艰难处境中的患者的关系,因此关系医学和医患共同决策都要求临床工作者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看问题,即能够与他们共情。
共情的定义多种多样,至今尚未有被广泛接受的、唯一的定义[7]。简言之,共情就是能够把自己投射到他人的境遇中,想象处在他人的立场该如何看待问题。医学界和医学教育界普遍认为共情能力在医患关系中至关重要,因此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与共情相关的方方面面。很多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医生的共情可以增加患者满意度以及对治疗方案的依从性,甚至可以提高患者可测量的生理健康程度[8];医生的共情能力可以提高临床效果(clinical outcome),增进医生的职业满足感[9];医生的共情能力可使就医过程节省时间和费用[10]。相反,自感在就医过程中没有得到医生足够的关心和共情的患者更有可能进行医疗诉讼[11];当患者感到医生没有倾听他们的时候也更容易起诉医生[12]。共情能力高的医学生,其学业表现和临床胜任力也好[13];但遗憾的是,医学教育和医学实践会越来越钝化共情[14],导致共情意愿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职业倦怠(burnout)[15]。职业倦怠表现为情感枯竭、态度疏远、个人成就感降低[16];职业倦怠的增加和共情能力的降低对医疗质量有着消极影响,导致医疗错误增加[17,18]。
在医生的成长过程中,责任、利他、尊重、关心等正向价值观的教育比较普遍,但几乎没有关于情感(特别是负面情感)的教育和讨论,痛苦、愤怒、恐惧、困惑、沮丧、内疚、无助、不被认可等负面情感很少被谈及,也几乎没有途径宣泄。患者和医生都会经历这些负面情感,医生需要认识这些负面情感对治疗和医患关系的消极影响,也要认识它们对自己的有害影响,因为负面情感的累积会导致职业倦怠。叙事医学关注的焦点恰恰就是人,特别是人的情感,是在技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医学中关注人的情感的医学实践。叙事医学鼓励讲述和书写“疾病的故事”,因为“叙事”即为“故事”。一方面,医生通过倾听患者的疾病故事可以了解他们患病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全方位地了解患者,并能站在患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实现与患者共情。另一方面,医患双方都可以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为自己的负面情感找到出口——“在把经历建构成故事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意义”[19]。这个“意义”对深处其中的医患双方都是重要的,负面的情感得以被宣泄、认识之后,讲者或书写者就可以找到其中的意义,从而可以超越这些情感,开始新的一页。
2 如何实践叙事医学
叙事医学的实践与其特点是密不可分的。叙事医学包含着不可分割、层层递进的三要素:关注、再现、归属。任何医疗工作都始于对患者的关注,而倾听是关注的开始,但是很多生物医学模式训练出来的医生会认为患者的讲述“没用”,患者对各种感觉和感受的讲述通常不到一分钟就会被医生打断——国外一个经典研究的发现是从问诊开始到医生第一次打断患者的平均时间为18秒[20]。特别是在电子病历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如果不需要检查患者,医生可能从头到尾都在面对着屏幕书写病历而不看患者一眼。更多的时候医生是看各种检查结果而非患者进行诊断,患者感觉到自己在就医过程中是完全被忽略的,更不要奢望医生会与她/他建立“具有疗愈效果的治疗关系”。而叙事医学关注的重点恰恰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患者——是痛苦中的患者、具有过去和社会关系的患者、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患者。患者看待疾病的方式与医生是不一样的,社会语言学家米施勒(Elliott Mishler)区分了“医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思维习惯,前者关注时间顺序,以便理解疾病的生物学意义,后者关注事件顺序,以理解个人的生活意义[21]。因此,医生若要与患者共情,首先需要关注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对疾病的理解也许与自己是不一样的,他/她来到我这里,只是因为“这个人恰巧患了我这科能看的病”,我需要以看待“人”而非“病”的方式去面对他/她。叙事医学的第一要素就是关注,关注始于倾听,倾听患者、理解他/她的故事,需要共情能力。共情需要医生“暂时放弃自己对世界的经验,有勇气去采取患者的观点看问题,身临其境,从患者的角度去体验整个事件”;这样“冒险”的好处是“你不需要亲历患者的痛苦体验,甚至都不需要为他感到难过,就可以理解他”[2]。
叙事医学的第二要素是再现。医生在日常工作中,或多或少都会反思自己的实践,有时医生会一再回味让人痛苦和兴奋的临床工作经历,这其实就是一种自发性的“再现”。叙事医学要求医生自觉地反思自己的工作以及所见所闻,并以书写“平行病历”(parallel chart,下文将详述)的形式将其再现。书写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认知和发现意义的过程,神经生物学家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认为“意识通过意象的产生而产生”[22],只有再现才有感知,感知则赋予反思持久的形式,并可以深化反思。再现的过程是运用想象力对相关的记忆、经历、感觉和认知进行加工,“把有价值的东西挤出来[2]”。再现是叙事的主要方法,叙事书写揭示的不仅是客观事实,对医生来说,再现的过程是深化共情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理解患者的过程,也是自我反思的过程、是自己情感的宣泄过程、是为负面情绪找到出口、为自己的工作找到意义的过程,它具有独特的个人化特征,这一过程有助于降低职业倦怠感、提升职业满足感。
叙事医学的第三要素是归属,这是由关注和再现过程而螺旋上升得到的信任,是结果。通过倾听患者的讲述,医生得以关注作为独立个体的患者;通过“平行病历”的书写,医生会进一步关注患者的生物学维度和情感维度,并试着从他/她的角度看问题,实现与患者共情;同时再现的过程也会促使医生关注到自己的情感维度,对自我有更深入的了解。由于对全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医生会竭尽全力去做到最好:“关注和再现在行动中达到顶峰”[2],也就是与患者建立了归属关系,即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疗愈效果的治疗关系”。卡伦认为,归属关系不仅局限于医患之间,它还可以表现在带教老师和学生之间、同事之间、医生之间的伙伴关系,甚至是医生与自己的和解[2]。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叙事医学的三要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自然会达到的结果:关注学生、同事、社会的诉求,并以某种形式将其再现就一定会与之共情;审视自己的思想行为并换位思考带来的是理解,理解之后则会采取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而这种为他人所想的做法注定会带来信任。
3 叙事医学的工具及其发展
叙事医学运用的两个工具都来自于文学,分别是细读(close reading)和反思性写作(reflective writing),这两个工具被用来训练和提高“叙事能力”(narrative competence)。笔者认为叙事能力的基础就是共情能力,与患者共情后为之采取他们乐于接受的行动就是叙事能力,上述关注、再现、归属三要素就是共情能力和叙事能力向临床效果转变的过程。
“细读”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卡伦及其团队发展了一套叙事医学的细读法,即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关注文本的框架、形式、时间、情节和意愿。文本的框架就是文本的来源及去向,即文本的作者、读者和它的空间结构;文本的形式则包括了文本的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随笔等文类)可见结构(如章节或句子的长短、标点符号的运用)、叙述者、隐喻、典故和用词;文本的时间包括顺序、持续时间、故事时间、话语时间和速度;情节就是文本中发生的故事;意愿指作者创作的目的、文本中讲述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以及读者想要从文本中获得内容。卡伦认为,阅读行为和治疗行为是相似的,读者对话语的阅读发生在词语的表面,其意义则埋藏在词语之下;医生对疾病的“阅读”发生在身体的表层以及皮肤之下的病生理结构中。上述的细读训练可以培养医学生和医生在倾听患者的时候关注细节、容忍不确定性、理解多重视角、接受不同的观点、与患者共情[2]。因此,细读也是国外医疗团队和医学教育中运用很多的一种方法,细读选择的作品均为文学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疾病经验的作品,疾病只是阅读时关注的内容之一,更多关注的是文本的框架、形式、时间、情节和意愿,以及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叙事者和人物的关系、叙事者与读者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23],这种方法也凸显了“关系医学”的关切,是叙事写作的基础。但遗憾的是,我国医学界和医学教育界还没有意识到阅读对培养叙事能力的重要性[24],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医学院缺乏在教师指导下的文学阅读;可喜的是,一些医院已经开始了自发的文学阅读活动[25],但尚未把文学阅读与叙事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如果掌握叙事医学理论的文学教师能够参与到医院的文学阅读当中,指导临床工作者用细读法来进行阅读,将会极大地提升医生的共情能力和叙事能力,并会使其在临床工作中持续受益,这已经在叙事医学的起源地哥伦比亚大学得到了证实[26]。
与细读法在临床情境中几乎不被所知的情况不同,在我国反思性写作即“平行病历”拥有一定的知晓度,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其作用,“平行病历”又被称为“平行人文病历”、“叙事病历”或“影子病历”(为节约篇幅,以下统称“平行病历”)。平行病历指与医院标准病历不同的、以第一人称和非技术性语言书写的关于患者的记述和医生本人的反思,它可以使临床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成为一名医生”[2]。任何一位患者背后都有故事,如果医生愿意去关注地倾听他/她的故事,并以平行病历的方式书写出来,就会实现与患者的共情。由于平行病历的书写并不需要文学知识的支撑,因此能够得以普及,越来越多的医生发现了这个工具,开始书写平行病历,讲述患者的故事、反思自己的实践。在百度网上以“平行病历”和“叙事病历”进行搜索,分别得到了129万个和15.7万个结果;此外,《健康报》、《中国医学论坛报》等报纸也不定期刊登医生和医学生撰写的平行病历,一些出版社也将平行病历结集出版[27,28],这些故事成为医学生的“从业指南”,以及民众了解医生的窗口,是医院文化建设和人文科室建设的重要工具。
叙事医学的发展日臻成熟,不仅找到了现象学和叙事诠释学作为其哲学基础[29],也从文学批评、人类学、口述史和意识研究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作为其特色工具的细读法可以训练临床工作中的细听(close listening)[30];在再现工具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平行病历之外,更具创意特色的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音乐也成为再现的新方式;此外,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培养共情能力和叙事能力[31,32],这都为我们在国内开展叙事医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正如卡伦在2009年笔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谈她时说的那样:叙事医学是医生可以“做”的事情,其他的医学人文都是学者“说”的想法。因此,医学人文在现实中“落地”,需要借助叙事医学的工具,让医生能够认真地倾听患者,再现他们听到、看到和想到的,这种用心最终就会螺旋上升为医患之间的归属关系和伙伴关系。
[1]Pellegrino ED.Humanism and the Physician.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9:9.
[2]Charon R.Narrative Medicine: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郭莉萍等译.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5.
[3]郭莉萍.从“文学与医学”到“叙事医学”.科学文化评论,2013,10(3):5-22.
[4]凌峰.千风之歌的回想.死亡如此多情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6.
[5] Zukier H.Flipping patients and frames:the patient in relational medicine.Rambam Maimonides Medical Journal,2017, 8(3): e0034. Published online 2017 July 31.doi:10.5041/RMMJ.10310
[6]Dy SM,Purnell TS.Key concepts relevant to quality of complex and shared decision-making in health care:a literature review.Social Science&Medicine,2012,74:582-587.
[7]郭莉萍,魏继红,李晏锋,等.医学人文与共情.中国医学人文,2015,1(10):7-10.
[8]Garden R.The problem of empathy:medicine and the humanities.New Literary History,2007,38:552.
[9]Stepien KA,Baernstein A.Educating for empathy.Gen Intern Med,2006,21(5):524-530.
[10]Bellet PS,Maloney KJ.The importance of empathy as an interview skill in medicine.JAMA Dermatol,1991,266(13):1831-1832.
[11]Bylund CL,Makoul G.Empathic communication and gender in the physician patient encounter.Patient Educ Couns,2002,48(3):207-216.
[12]Levison W,Roter D,Mullooly JP,et al.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with malpractice claims among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and surgeons.JAMA,1997,227:553-559.
[13]Hojat M,Gonnella JS,Mangione S,et al.Empathy in medical students as related to academic performance,clinical competence,and gender.Med Edu,2002,36(6):522-527.
[14]Hojat M,Vergare MJ,Maxwell K,et al.The devil is in the third year:a longitudinal study of erosion of empathy in medical school.Academic Medicine,2009,84(9):1182-1191.
[15]Thomas MR,Dyrbye LN,Huntington JL,et al.How do distress and well-being relate to medical students'empathy:a multicenter study.J Gen Intern Med,2007,22(22):177-183.
[16]Prins JT,Gazendam-Donofrio SM,Tubben BJ,et al.Burnout in medical residents:a review.Med Educ,2007,41:788-800.
[17]Shanafelt TD,Bradley KA,Wipf JE,et al.Burnout and selfreported patient care in an internal medicine residency program.Ann Intern Med,2002,136(5):358-367.
[18]West CP,Huschka MM,Novotny PJ,et al.Association of perceived medical errors with resident distress and empathy: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JAMA,2006,296(9):1071-1078.
[19]White M,Epston D.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1990:27.
[20]Beckman H,Frankel R.The effect of physician behavior on the collection of data.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1984,101:692-696.
[21]Mishler EG.The discourse of medicine:Dialectics of medical interviews.Norwood,N.J.:Ablex Press,1984,as quoted in Charon R.Narrative medicine: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6.
[22]Damasio AR.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9,as quoted in Charon R.Narrative medicine: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 Press,2006,137.
[23]Spiegel M,Spencer D.Accounts of self:exploring relationality through literature.In Charon R,DasGupta S,Hermann N,et al.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16.
[24]杨晓霖.疾病叙事阅读:叙事医学能力培养.医学与哲学,2014,21:36-39.
[25]苏家春,陈勤奋.快乐工作,健康生活:华山医院开展员工帮助计划(EAP),为医务人员身心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学论坛报,2017年8月31日,A12版.
[26]Miller E,Balmer D,Hermann N,et al.Sounding narrative medicine:studying students'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Academic Medicine,2014,89:335-342.
[27]张抒扬主编.医之心:好医生执业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8]李飞.直面医事危机——住院医师的人生大考,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7.
[29]Irvine C,Spencer D.Du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medicine;Du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I:philosophical tinctures.In Charon R,DasGupta S,Hermann,N.et al.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63-105.
[30]Charon R.Close reading:the signature method of narrative medicine.In Charon R,DasGupta S,Hermann,N,et al.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157-179.
[31]McDonald P,Ashton K,Barratt R,et al.Clinical realism:a new literary genre and a potential tool for encouraging empathy in medical students.BMC Medical Education,2015,15(1):112
[32]Hermann N.Creativity:what,why and where?In Charon R,DasGupta S,Hermann,N,et al.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2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