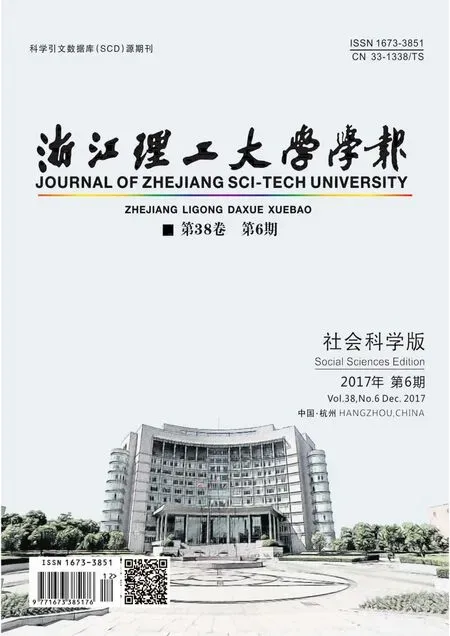小说的历史兴趣与诗性本质
——以《玫瑰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红》为例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小说的历史兴趣与诗性本质
——以《玫瑰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红》为例
肖泳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历史学研究陷入文学性阐释的危机。但诗从未与历史发生过冲突,畅销书《玫瑰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红》都显示了历史兴趣。《玫瑰的名字》通过迷宫这一象征带领读者一起思考历史迷局,随后将之解构;《我的名字叫红》则以小说作为文本织体,把业已消失的中古伊斯坦布尔从历史深处拉出来,尝试着复现历史经验的真实。
历史;小说;迷宫;细密画传统;话语;诗性
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有一段对诗与历史的经典阐述,“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海登·怀特对历史阐释的清理,更将历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置于前所未有的怀疑之下,他借用诺思罗普·弗莱文学史研究的批评模式,即悲剧、喜剧、传奇、讽刺剧四种类型,指出它们同样适用于某些历史学著作的阐释。他甚至不客气地说,历史学研究者对一个历史事件为何如此发生所作的阐释,难免在言辞上会增加一些“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2]这种质疑对历史研究的确是解构性的打击。文学性阐释不知不觉进入历史研究,引起了历史学的警觉,但对于文学而言,诗的记忆本质及作家与生俱来的对历史记录者身份的兴趣,则从未与历史发生过冲突。本文拟从翁贝托·艾柯《玫瑰的名字》[3]、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4]这两部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历史兴趣入手,探究纠缠着历史科学的历史阐释难题,如何在小说中被合法地诗性阐发,但同时也体现出小说作为表现历史兴趣的文本形式,在后现代语境中有着何种不同的延伸与利用。
一、《玫瑰的名字》:用小说话语完成的历史反思
《玫瑰的名字》是翁贝托·艾柯写于1980年的小说,至今在全球销售了一千五百万册,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不少评论都提到艾柯写这部小说与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之间的关系[5],以及它本身具有的“迷宫”性。如果说象征的积极运用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之一,那么另一个特征便是象征所寓含的自我的深度。卡夫卡的小说在体现现代主义小说这两大特征方面,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继承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某些形式,比如,同样自如地运用象征。但是不同于现代主义小说的是,不少后现代主义小说既建构象征,最后又解构苦心营造的象征,让那个象征及其蕴涵的寓意碎裂、消散于无。
“迷宫”在《玫瑰的名字》里是一个具有多重所指的象征。修道院里年老而昏聩的僧侣阿利纳多,这个说话颠三倒四的人用最简洁的话语道出了迷宫的象征性寓意:
“迷宫是这个世界的象征,”老人陶醉地吟诵着,“入口很宽敞,出口却十分狭小。藏书馆是一座大迷宫,象征着世界的迷宫。你进得去,然而不知是否出得来。”[3]178
迷宫,在小说中首先典型地显现为修道院里图书馆神秘的迷宫式的结构,最终,这座迷宫的结构规则在威廉与弟子阿德索执著的求索中解开了,图书馆也烧毁了。第二个迷宫的显性形式是谋杀案的发生及侦破案情的错综复杂过程,犹如行走迷宫。第三个迷宫性的显现是修道院众僧侣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与案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情节的迷宫性。如果说显性的迷宫作为小说能指被读者轻易领会,并在追索案情真相中品尝到类似于迷宫游戏般的快乐的话,那么就作者艾柯本人的意图来看,读者只解出了一重文本译码。迷宫能指之下,还有一个所指,是文本的第二重译码,这一重,是向所有读者开放的思想“迷宫”,正是在这里,关于此书的主题引起各路评论者的纷纷议论。有人认为《玫瑰的名字》是理解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的极好读本[6]。有人从精英/大众、差异等概念推敲其主题[6]133。本文则认为,艾柯写作这部小说很大的兴趣,是对于“历史”这一迷局的兴趣。这一兴趣也是身为学者的艾柯的学术和思想兴趣所在,它是思想史上关于“历史”的,关于“真相”的追问,即一个后现代的疑问: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它存在吗? 这样的问题,以艾柯的学者身份,他本可以用学术话语写成哲学或历史学论文、著作,不过,颇具后现代性的是,艾柯进行了一次跨文体的尝试,用小说话语来探讨一个历史科学的难题。迷宫,则作为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象征,从现代主义的深层寓意中脱离,飘浮为后现代的符号,为艾柯历史学、宗教学甚至语言学话语的混搭提供了某种形式功能。
那么,作为小说,历史的兴趣是如何布设为一个迷宫的?
(一)在迷宫式的图书馆里寻找真相
不少评论者发现长达五百多页的小说,模仿了《圣经·启示录》七天的框架,艾柯本人也承认这种模仿。一个修道院在七天里发生六起谋杀,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对谋杀进行调查,线索不约而同指向了修道院最宏伟的建筑——图书馆。书的前页特意附上了图书馆的建筑结构图,是一座迷宫式的神秘建筑。威廉以为,历史事件遗留的痕迹,就像事物的符号,符号与符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他可以像解开迷宫规则一样,根据普遍规律找到那些“痕迹(符号)”之间的联系,最终发现真相。图书馆藏书的规则正是像威廉所信奉的宇宙秩序一样,是按照某种符号规则编码了所有图书。然而,威廉虽然凭才智接近了真相,却发现六起谋杀案并非像他最初推断的那样是按照《启示录》七声号角的顺序、有计划的谋杀,它们之间的相互一致完全是巧合。小说最后,大火烧毁了图书馆和修道院,威廉倍受打击,他说:
“我通过《启示录》的模式,追寻到了豪尔赫,那模式仿佛主宰着所有的命案,然而那却是偶然的巧合。我在寻找所有凶杀案主犯的过程中追寻到豪尔赫,然而,我们发现每一起凶杀案实际上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或者根本没有人。我按一个心灵邪恶却具有推理能力的人所设计的方案追寻到豪尔赫,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方案,或者说豪尔赫是被自己当初的方案所击败,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相互矛盾和制约的因果效应,事情按照各自的规律进展,并不产生于任何方案。我的智慧又在哪里呢?我表现得很固执,追寻着表面的秩序,而其实我该明白,宇宙本无秩序。”[3]
对历史真相的推断,知识、想象只是接近真相的工具,而真相本身并无必然秩序,也许碰巧接近了真相,却是瞎猫碰上死老鼠,纯属偶然。
(二)历史阐释的迷宫
《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艾柯现代文学演讲集》收有《小说的表述和历史的表述》一文,关于小说文本与历史表述文本的本质区别,艾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小说文本中虚构一个事实,是不会遭到置疑的,比如“安娜卧轨自杀”,没有人会质疑安娜是不是真的卧轨自杀了。而在历史学文本中表述一个事实,却不会像小说一样不受质疑,因为文本的表述是一回事,经验的实在是另一回事。但历史表述往往表现的似乎事实真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它只是从言的。
这样的历史观在《玫瑰的名字》中得到了文学化阐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是否存在?怎样失传的?是至今无法证明的历史事实,艾柯则通过小说文本虚构了关于这本书失传的六起谋杀案的故事。身为历史学家的艾柯,显然无法通过史学的表述去探究《诗学》第二卷的去向以及存在与否,无论怎样阐释都必将遭到质疑。然而,文学的虚构却使他免于任何讼争。
威廉的弟子阿德索,即手稿叙述人,对修士多里奇诺案历史事实的发现则体现出从言的历史叙述与经验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巨大出入。尽管修道院里多数人避而不谈多里奇诺,即使谈起也称呼他为异教徒,然而阿德索在缮写室偶然读到的手抄本《异端首领多里奇诺修士的历史》,却把多里奇诺遭受酷刑,从容赴死的情形写成一个高贵的殉道者,让这个年轻的见习僧大受震动。而在多里奇诺的跟随者和亲睹其受刑过程的修士雷米乔的叙述中,呈现的则是另一个多里奇诺,其人的一生没有神圣性可言,只有残忍、痛苦、狂热和几分不可思议的荒谬。
怎样一清二楚地区分异教徒与殉道者、善与恶?要说有标准,大概就看谁握有划定标准的权力。“第二天·午后经”这一章,是博学的威廉与同样博学但观点不同的修道院院长阿博内之间的一番对话,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判断异教徒,其中涉及到多里奇诺修士的争议。威廉说:
“我亲眼见到,一些生活节俭,品德高尚的人,他们诚挚地信奉清贫和贞节,但他们是主教的敌人,那些主教逼着他们去受世俗的武力处置,不管是皇帝的武力还是自由城邦的武力。他们被指控乱伦、鸡奸、胡作非为。其实,犯有这些罪行的往往是别人,而不是他们。当贱民可以被利用致使敌对政权陷入危机时,往往是任人宰割的肥肉,而当他们失去被利用价值时,就成了牺牲品。”阿博内问:“真理究竟何在?”威廉忧伤地说“有时候,哪儿都没有真理。”[3]172
在《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艾柯现代文学演讲集》里,艾柯自述他的博士论文是写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观,答辩的时候被一位评委批评说他堕入了“叙事的误区”,把学术论文写成了侦探故事[7]10。海登·怀特认为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避免不了文学性的阐释,艾柯则反其道而行,《玫瑰的名字》仍然是用侦探小说探讨学术和思想问题,它用小说话语来呈现历史叙述的“迷局”,历史的阐释的确像个迷宫,走进去却不知道出口在哪儿。
(三)手稿的历史真实性存疑
有学者在2008年就发文指出《玫瑰的名字》第一个中文版存在巨大的遗漏,艾柯本人为此书洋洋得意的一句话“自然,这是一部手稿”,竟然被删掉,连同删掉的还有修道院的布局图、手稿发现者对手稿来历的叙述、按语等几个部分。这种遗漏严重影响了艾柯为此书精心布置的叙述结构[7]38。所幸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这本《玫瑰的名字》将遗漏的部分都补齐了。艾柯在演讲中颇为得意地把书的前页对手稿来历的叙述解释为一种互文性反讽,它使人们很容易想起哥特小说常见的套路,目的是制造故事似是而非的暧昧[7]12。
不过,中文研究(读)者对此则有不同理解。朱桃香在《书与书的游戏:<玫瑰的名字>叙事结构论》一文中把手稿几经人手的转译、流传的过程,与《红楼梦》卷一道士抄录、转手《石头记》,曹雪芹改名、编辑手稿的过程作比较,认为“《玫》内容是阿德索手稿,但是阿德索手稿并不是《玫》。那么,《玫》又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呢?”[8]也就是说,我们读到的手稿已经是几经转译、拼贴、互文交叉的手稿历史的集纂,那么,有多少手稿内容是真实保留下来的?有多少是后人添加、删改的呢?修道院里发生的,真有其事吗?这一疑问非常致命,实际上取消了这个故事的严肃意义,而仅可视为游戏之作。在这里,小说只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富于巧智性地阐述其学术见解的工具形式,它已从现代主义所信奉的作为表现的、审美的、哲理的人类表达沦为游戏性的话语工具形式,它昭示了一种后现代的小说文本意义:探察历史真相如何,不过是让小说话语得以游戏性地展示的由头,而探察过程则极为醒目地突出了小说是一种多么有趣的话语形式。
二、《我的名字叫红》:何为历史叙述之真?
与《玫瑰的名字》一样,《我的名字叫红》的故事也起因于几起谋杀案,但帕慕克的努力方向显然与艾柯不一样。首先是作为一位诗人,希望用诗人的笔法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学术执著,再现一个中古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一个下雪的早晨,孤独的游子隔着街道和树枝,遥遥望着旧情人模糊的面容,野狗和流浪汉游荡的黑夜,咖啡馆里一派欢声笑语,气派而富有的小楼房飘出杏仁肉饭的香气,年轻的母亲搂着孩子一起阅读有着美丽细密画插图的书本,还有红,这激情、鲜血与火的颜色……这是吊死鬼屋传说与月光下的席琳同时萦绕着童年的充满诗意想象的伊斯坦布尔。
其次,同样以连续发生的谋杀案作为故事情节主线,帕慕克探索真相的方式,以及对于真相的哲学质疑与艾柯截然不同。那个叫黑的男人受命来调查这起谋杀案,与威廉的任务很相似,但是,小说倾力呈现的并非是对历史真相的解构,勿庸说是对历史真相深深的迷恋。《玫瑰的名字》完全可以解读为对一系列煞有介事的关于历史真相的哲学思考的取笑,艾柯用小说跟读者开了个玩笑。帕慕克则正相反,他相信中古的土耳其土地上,就在伊斯坦布尔这个不断经历血与火的城市中,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细密画这一业已衰落的历史传统的继承者——细密画画师。他尝试实现的是,如何借助小说叙述而又超越小说叙述的传统局限,生动再现细密画的传统,以及那个历史时空中流淌着细密画血液的一群画师的灵魂。这是一种希望把历史意图与诗性意图完美结合的尝试。
帕慕克为他的人物投入了诗人的激情和好奇心,真相不仅仅是史书上、传说中记载的话语表层,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内心世界才是历史人物真实中更值得挖掘的幽深部分。帕慕克承认写作这部小说时,艾柯的《玫瑰的名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某些深刻见解曾给过他启发[9]。尤瑟纳尔的作品《哈德良回忆录》[10]非常大胆地以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形式自述一生中的重要时刻的所思所想,使这部历史小说成为哈德良内心的历史。《我的名字叫红》最引人瞩目的正是其叙述的独特性,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让小说中的每个存在物甚至包括画中的马、狗、色彩(红)都开口向读者讲述,杀人凶手也隐身于众讲述人之中。这种叙述类似于“口述历史”,只是带有小说独有的神话色彩,人物的内心由此向读者敞开。但这种貌似坦白并被认为能直接进入真相内部的口述形式,却造成叙述的困局。在这里,帕慕克探索着一个关于“叙述-真相”的问题。
如果某种经验的历史,比如与细密画相关的经验以各种符号形式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文本中——首先是细密画图册,其次是历史典籍文献,再次是坊间流传的传说——那么,小说如何能仅仅通过“叙述”,在叙述的空间里诗性地复现这些经验,使读者感同身受它那发自历史洞深之处的鲜活脉跳,并信以为真实存在?也即,真相是否仅仅通过“叙述”即可信其为真?信其为真的“叙述”有哪些可操作的“叙述”空间?通常,我们认为当事人直接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然而,《我的名字叫红》几起谋杀案的被害人与凶手都多次自述事件,却盘桓于自我的倾诉焦点中,始终没有说出谁是凶手。每种叙述在坦白的同时也必然存在遮蔽。凶手多次亲口说话,讲述了前后杀害高雅先生和姨父大人的详细经过,叙述的遮蔽性却不能使读者知道凶手的名字。
于是,关于案件真相的叙述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小说的元叙述,人物貌似很坦白直接面向读者,毫无隐瞒地讲述自己的犹豫、诡计、担忧、欲望和犯罪;另一方面,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叙述,往往神秘莫测、各怀目的、不可信任。美丽的谢库瑞在哈桑与黑之间摇摆不定,她传递给黑的信总是在拒绝黑,她知道她的传信人那个犹太女人艾斯特一直是个双面掮客,她的信同时也被犹太女人拿给哈桑看了。黑收到的散发着杏仁幽香的信,白纸黑字是谢库瑞漂亮的字体,一字一句是她得体的书写,却是无论黑、哈桑还是犹太女人都不会相信的美丽谎言。
但是,“何种叙述为真?”的命题,乍看之下似乎是作为诗人、小说家的帕慕克尝试解决的形式问题,它并不涉及对历史真相的怀疑与否。那么,《我的名字叫红》使人深切体会到的对历史深处某种坚实存在的信念,以及努力再现业已消逝的某种历史经验的热情,这种为其感动的阅读体验源自哪里?帕慕克像一位文本考古学家,借用历史文献、传说、寓言、图画等超小说的文本,每一种都从叙述上发挥作用,一层层地讲述覆盖于伊斯坦布尔土地上的历史的沉积。这些文本内在地构成小说特殊的叙述空间,讲述着某种穿行于历史时空中的细密画经验,因而使之具有了恒远的实在性。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2007年分别出版了《我的名字叫红》两种版本。2006年出版的是无插图和详细注释的版本,显然从帕慕克的创作意图上来说,这是不完整的版本。紧接着2007年出版了“插图注释本”,这个版本才是正确阅读该书的版本。这一版本中,图画的历史经验(由细密画图册提供,书中选用了部分作为插图)、官方文献典籍的历史记载(由每一章末的注释提供)、小说叙述的个人历史经验三者分别以文本的形式汇聚于近600页的书页中。分别来看,它们各有叙述指向。但当耐心的读者读小说同时也不忽略插图和注释,将阅读在三种文本混合的历史记忆中展开时,它们交映成辉。帕慕克试图让小说中的每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都成为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11],他们吐露自己的内心活动,也转述与其他人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常常穿插着传说或寓言,那些属于伊斯坦布尔和属于细密画历史的共同经验便在这口口相传的讲述中被心领神会了,也许帕慕克希望它们因此能代代相传。因此,小说中的每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都试图成为实在的历史叙述者,而不仅仅具有叙述策略层面上的形式意义。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经验的记忆,假如失去了这些记忆,个人、民族、文化的存在也随之变得可疑。小说主人公之一黑反复出现一个疑问:他离开家乡四处游历,始终坚信支持他忍受各种生活艰辛的是他对谢库瑞的爱,可是为什么他却忘了谢库瑞的面容?直到他受命调查高雅先生被杀案,再次沉浸于所热爱的细密画中时,才恍悟到:如果当年离开伊斯坦布尔时带着少女谢库瑞的画像,他不至于忘记她的面容。小说中还提到另一个发现,热爱细密画的苏丹和王妃,会命令画师把他们自己的面容作为画中的某个人物而绘入画中,这样他们就会随书本而永远地留在画中,他们以为细密画是不朽的。由此可见,对于中古时代的伊斯坦布尔而言,细密画就是它的历史记忆方式。
然而,遗憾的是,不留个人印记、永远追随前辈大师的传统、表现阿拉全知视角的细密画,毕竟是有缺陷的个人所作,不朽,看起来是亵渎神圣的渴望,实际上却涌动在每一代细密画大师的心中。橄榄对姨父大人的击杀,与其说是预谋已久的周密计划,不如说更是被姨父大人那一番对细密画必将消失前景的无情描述所激起的绝望而冲动地下了杀手。姨父大人这样对他说:
“对之不感兴趣、时间和灾难将渐渐摧毁我们的绘画。装订用的阿拉伯胶水含有鱼、蜂蜜和骨头,书页表面则是用蛋白和糨糊混成的涂料上胶打亮,因而贪婪无耻的老鼠会咬坏这些纸张,白蚁、蛀虫等千百种虫子将把我们的书本啃光……一位画家又如何能幻想他的经典之作流传超过百年,或者期望有一天他的图画能够得到认同,自己被人们像贝赫扎德般受尊崇?……成千上万个忧郁的王子,在开花的树下,在鲜艳的花海间,坐在一块漂亮的地毯上,聆听着美丽的女人与男孩们吹奏的音乐;图画中各种精美的瓷器与地毯,归功于过去一百五十年来从撒马尔罕到伊斯坦布尔,成千上万个插画学徒在鞭打责骂下的努力:如今你仍以同样的激情所画的美丽花园和游弋在其中的鸢,你笔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和死亡场景、机智地狩猎中的苏丹、同样机智地逃窜着的胆小羚羊、垂死的君王、被俘的敌人、异教徒的帆船舰队、敌人的城市以及你笔下流出的像黑屋脊一样的莹莹闪烁的黑夜、繁星,鬼魅般的柏树和你用殷红渲染出的爱与死亡的画面,这一切的一切,都终将灰飞烟灭……”[4]229
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刀光火影、几易其主、唯独不变的是君主们对细密画热爱的土地上,细密画的衰落和消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命运,到今天,它已破碎成零星的文化片断存在于历史档案馆里。当历史记忆交叠又散乱地出现在图画、卷轶浩繁的历史文献、民间传说与寓言等等多种形式的文本中,完整与真实性几近淹没的时候,就《我的名字叫红》来说,只有小说担当并完成了充当多种文本织体的工作,以一种整体的、想象的方式复现了真实的历史经验。
李欧梵曾盛赞《我的名字叫红》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把传统小说把握历史整体 “鸟瞰”所得的内容重新加以描绘,是二十世纪末最伟大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他认为帕慕克完成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即同样都希望超越时间限制而成为历史记忆的细密画与小说,如何做到突破各自的局限而叙述历史和自我?李欧梵认为,小说打破了线性叙述的框架,全书的结构体现出一种“织毡式”手法,类似于阿拉伯人织地毯,既有全景式鸟瞰的视角,这来自细密画的宗教传统,细密画表现的是阿拉的视角——从高处俯瞰众生,无所不知的全能视角;也有对局部的精工细描[12]。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三、小说的诗性
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中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他离开祖国曾流亡到法属马提尼克岛。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岛,居民是17世纪从非洲被贩卖到这里的黑奴,时至20世纪,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曾经的语言是什么?怎么来到岛上……没有口头传说、没有历史记载,都被遗忘了。直到埃梅·塞泽尔于1939年发表了诗《回祖国手记》,诗中是一个回到黑奴岛上的黑奴质问自己:我是谁?从哪里来?我有怎样的过去?诗歌引起了全岛的震动,人们像爱戴英雄一样爱戴塞泽尔,因为他用诗歌提醒人们存在着遗忘的历史,也用诗歌激励人们可以创造历史。在缺少历史书写的地方,诗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来抵抗遗忘[13]。
然而,诗,首先是诗,即使它保有历史记忆,也是以诗性的方式。《玫瑰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叫红》,都显示了作者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艾柯是一位博学而睿智的学者,他身兼符号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多职,熟知小说传统,自从他开始写小说,他就成为一位畅销小说作家。《玫瑰的名字》刚问世就引起各方争议,其中一个焦点就在小说的生成方法上。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成书过程是依靠电脑程序完成,即先把一百来种书的内容输入电脑,有科学、宗教、历史等等书籍,甚至包括电话号码簿,然后用一个特殊的电脑程序对这些内容进行随机编排,那么所有书的内容都混杂在了一起。在此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加工,如此等等。艾柯虽然认为这种写法并非不可能,他后来写的小说《傅科摆》中,有意让书中主人公之一贝尔勃尝试了这种写法。但他强调《玫瑰的名字》不是这样写出来的,理由是他写作的两年里,计算机技术还没有达到能处理和完成那种混杂之书的水平。还有读者指出书中阿德索在厨房里经历性狂喜那一幕,来自《圣经·旧约·雅歌》。不少索隐癖的读者,都在书中追索它与其他书之间的关联。出现这样的争议,说明艾柯小说的特点:一是太博学,以至于读者不相信有人能博学到把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书都写进一本小说,不得不怀疑是机器合成之作;二是语体、文体不统一,拼贴混杂明显。书与书之间“进行着人们觉察不到的对话”[3]324,在小说中呈现书与书之间的联系,这是艾柯所欣赏的互文性表现,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实现双重文本译码,即表层能指满足一部分读者之外,深层的所指能为另一些有经验的读者译解,小说应该一读再读,而不是只读一遍。笔者可以理解他为此在心智上的付出超于常人。但是,如果要问《玫瑰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叫红》,哪一部你愿意一读再读,本文的回答将是后者。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富于巧智的小说,从能指到所指都是一场迷宫游戏,沉浸其中感受到的是作家与读者共谋的智力的快乐。笔者却更愿把《我的名字叫红》一读再读。原因无他,《我的名字叫红》有诗性,是艺术的审美创造结晶,《玫瑰的名字》则更像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纯粹智力活动的科研产品。《我的名字叫红》更能证明别林斯基所说的诗本身是目的,形象“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失明,是细密画大师的最高荣誉,假如年老还未失明,他们就刺瞎双眼走上这个荣誉的领奖台。为调查裂鼻马的师承,黑与奥斯曼大师一起进入皇家内库,从最丰富的细密画收藏中寻找线索。一个据传是贝赫扎德大师刺瞎双眼的帽针,悄悄被奥斯曼大师拿走,并悄无声息用它刺向自己的眼睛。帽针又被黑冒着生命危险带出皇宫。这个帽针的细节,在情节上微不足道,却悲剧性地赋予细密画传统以崇高美。这样的细节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常常出现,它不具有情节功能,却令读者心灵为之震颤。帕慕克遵循诗的逻辑,审美而非智性目的才是他的追求。这里所说的智性目的,指认知性突出的求真动机,就像《玫瑰的名字》,思想和学术探讨的智力兴趣、对小说写作的巧智性追求高于审美。诗、形象、美本身作为创作目的时,才会有黑衣的谢库瑞美丽忧伤,如同永留画中的席琳一样,成为神秘的召唤,令读者一读再读。
四、结 语
《玫瑰的名字》与《我的名字叫红》 两部小说不约而同通过谋杀案的侦破这一貌似通俗文学的情节,来展现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画面,显示了作者各自的历史兴趣。小说,无疑成为两位作者借以探察某些历史真相、以极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历史哲思的路径选择,我们因此得以管窥两位同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家的作品中,小说在他们笔下体现出怎样的特征。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关于图书馆的书,图书馆在小说中则既有着“迷宫”般的结构,又作为历史“迷宫”的象征出现。全书颇可作为中世纪文化史、宗教史的参考书来读,同时也是一部欧洲读者所熟知的各种经典书籍、典故的互文交汇的场所。这部小说更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的科研课题,小说只是混杂着学术质疑、思想探险,然而全然是游戏的话语工具,所有通过情节构织起来的关于历史真相的 思考及对知识探索的怀疑,最终都归于零。这一过程将现代以来小说赢得的深刻性与生动性都解构为纯粹的游戏手段。
就《我的名字叫红》与《玫瑰的名字》来说,帕慕克与艾柯最明显的不同是,他遵循诗的逻辑,仍然发挥小说具有的诗性功能,他进行审美的艺术创造。这种审美追求同时也是诗性追求,使《我的名字叫红》表现出对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活的人物灵魂的尊重。全书处处是富有魅力的细节,它们振荡人心,让人愿意一读再读。显然,小说具有历史性,但毕竟不同于历史,更不等同于历史思想或历史研究。后现代小说在话语形式上的跨界综合,也许可以理解为小说话语边界的移动拓展,但也可以反向理解为小说话语变得更加工具化进而存在其内质空洞化的可能。
[1]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9.
[2] 海登·怀特.元史学[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4.
[3] 翁贝托·艾柯.玫瑰的名字[M].沈萼梅,刘锡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M].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傅铿.迷宫中的玫瑰[J].书屋,2013(10):44-47.
[6] 张琦.“笑”与“贫穷”:论埃柯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主题[J].当代外国文学,2006(2):133.
[7] 艾柯.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艾柯现代文学演讲集[M].李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 朱桃香.书与书的游戏:《玫瑰的名字》叙事结构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1):110.
[9] 杨振同.奥尔罕·帕慕克访谈录:我的名字叫红[J].世界文化,2007(5):29-30.
[10]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M].陈筱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1] 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李茂增,苏仲乐,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79.
[12] 李欧梵.解画的艺术:关于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M].上海:书城,上海三联书店,2007(6):70.
[13] 米兰·昆德拉.帷幕[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3.
TheInterestofHistoryandtheNatureofPoetryaboutNovels—CaseStudyofⅡNomeDellaRosaandMyNameisRed
XIAOYong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The poem is richer in philosophical meaning than the history.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is caught in the crisis of literary explanation. But the poem has never conflicted with the history. The bestsellers ⅡNomeDellaRosaandMyNameisRedshow the interest in history. In ⅡNomeDellaRosa, the labyrinth as a symbol leads readers to pass through the puzzle of history, but it is then deconstructed. InMyNameisRed, the novel as the text texture, and mediaeval Istanbul which has disappeared is drawn out from the history to try to make the truth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appear.
history; novel; labyrinth; tradition of miniature; discourse; the nature of poetry
任中峰)
I106.4
A
1673- 3851 (2017) 06- 0511- 07
10.3969/j.issn.1673-3851.2017.12.005
2017-09-01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2-01
肖 泳(1971-),湖南宁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小说美学、艺术批评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