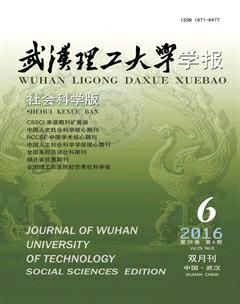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学术分野与人学整合
摘要:学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存在着重大的学术分野,主要体现为“二形态说”、“三形态说”、“五形态说”,并各执一词。由于人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本质,这就使得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人学整合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站在马克思人学的高度来看社会形态理论就会发现,原本看似分散、甚至矛盾的社会形态学论说实则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其统一性展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差异性既从不同的维度标示了人类生命特性的发展进程,又从不同的层面诠释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学术分野;人学整合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0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在批判性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产阶级人类学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横向结构与纵向演进所作出的历史性阐释。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全面客观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生活状态进而为提出人的解放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理论界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却存在着明显的学术分野。这种学术分野在理论上不利于人们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实践中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那么究竟能不能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整合?如果可能的话,那应该从什么维度对其进行整合?又应该如何阐释整合过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本文即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学术分野
在1852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首次在表述人类社会更替的意义上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术语。他指出:“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1]随后马克思曾“多次提出过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论说,每次论说的时代背景、语境、历史指向和列举的社会形态名目和更迭顺序都不相同”[2]。这些不同的论说给人们准确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人们往往片面地抓住马克思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下对社会形态的论述,并把它普世化、绝对化以此来否定、排斥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的其他论说。在这种思维范式的指引下,国内外学者形成了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不同版本,其中“二形态说”、“三形态说”、“五形态说”是较具代表性且争议最多的三种说法。从文献上看马克思确实提出过“二形态理论”、“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下面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用何种标准来划分社会形态的。
“二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以人类社会是否具有强制性的物质生产为标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做出的总体性勾勒。在“二形态理论”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前后相继的两个历史阶段。其主要文献依据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有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 其中,必然王国是指人受盲目必然性支配,特别是受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关系的奴役和支配的社会状态,马克思用必然王国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时期;自由王国是指人们认识和掌握了社会历史和大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使自己成了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盲目力量的支配和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而能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这样一种状态,马克思用自由王国来指称共产主义社会。
“三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以人类的生产能力为标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作出的客观判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一章中,马克思正式提出了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他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由此可见,从人的能力发展的维度看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自由个性”三大历史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主要包括“家长式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此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内在地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依赖关系,人的个性发展处于尚未真正经历社会化的“自然人”阶段。
“物的依赖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此时期人的个性发展已经由“自然人”阶段演变为“经济人”阶段。
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随着资本的解体人类在现实和观念双重层面彻底摆脱了物的奴役;物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对人的威慑和驾驭将不复存在。此时的人已经完全成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主人,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人。
“五形态理论”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运动和客观规律出发,以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性质)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考察重点,从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样态所作的一种划分[5]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较为完整地阐明了他的“五形态理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的几个时代。”[6] 五种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准对社会形态作出的阶段划分。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具有科学性。生产关系不仅是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活跃、易变的生产力相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稳定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形态的显性特征。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形态的整个横向剖面。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7]724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突破某种质的规定性时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较为直观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来追踪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同样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社会形态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高阶段的根本动力。“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8]142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不能容纳其所创造的强大生产力,到了那时资本主义社会也会无可避免地被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
虽然“二形态说”、“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各具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无论上述哪一种论说都只是抓住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部分真理,都不能单独呈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全貌,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认知应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应注重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从实质出发来把握各种形态论说的差异与联系。
二、人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本质
在各种哲学教科书和文献中,社会形态被普遍定义为“由社会经济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与社会活动这二者同时构成的社会模式。社会形态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如此定义社会形态,人们往往会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二者的互动上而忽视了进行这些活动的主体——人的存在。“实质上,社会形态就是人本身,社会形态就是人的形态的扩大,而人则是社会形态的缩影。”[9]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人是社会形态的创造者,是社会形态的当事人,还是社会形态的变革者。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史就是人类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史。任何社会形态的变迁都可以在人类自身的演化发展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人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联性意味着社会形态学就是一门关于人类发展阶段的学说,仅从此种意义而言,社会形态学就是人学的一个分支。这就使得以马克思人学为视角审视、整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
首先,人是社会形态的创造者,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人根据自己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而创造出来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8]1。“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8]71-72这就意味着人类所进行自主活动、自主创造是社会形态的来源,社会形态只不过是表征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存在物而已。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阶段性特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搭建起了不同层次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离开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形态就会失去骨骼和血肉,整个社会形态的存在就无从谈起。
其次,人是社会形态的当事人,处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在社会形态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构建者,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社会关系就是由各种独具特色的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在诸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性质。比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处于奴隶社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处于封建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曾就资本主义社会作了特别的分析:“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0]生产关系如此,其他关系亦是如此。社会形态中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有自己的当事人,人们总是处于自己编织的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中,受着各种关系的制约。
再次,人是社会形态的变革者,社会形态的变革实质上是处于特定社会形态中人的变革。社会形态的变革从本质上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还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改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处于其中的人的改变。生产力的改变体现了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改变体现了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所形成的关系的变化;上层建筑的改变体现了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因此,社会形态的变革说到底是人的变革,是人的发展变化推动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人的生成性本质决定了人将处于永不停顿地变化发展当中。这就意味着社会形态将不断地由低级形式发展为高级形式,任何企图阻止社会形态变迁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对于那些历史终结论者,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道:“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11]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将逐步摆脱异化劳动和资本的束缚,将逐步地由片面发展转为全面发展。到了那时资产者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会被人类发展的更高形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第四,人的能力的发展状态是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社会形态的成熟程度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而社会形态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其创造者——人的能力的大小。也就是说,人的能力越强大,其所创造的社会形态就越完善;人的能力越弱小,其所创造的社会形态就越具缺陷性。总体来看,人的能力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程度、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己身心的协调程度”三个方面。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引导、规范、制约着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使得各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呈现出特有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进而与其他种类的社会形态区分开来。
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人学整合
既然社会形态就是人本身,就是人的形态的扩大,那么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史就是一部扩大了的人类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史。社会形态理论从根本上说要遵循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体现人类生命特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遵从马克思人学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较之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人学理论是更高一层的理论形态,它对社会形态理论具有统摄作用。倘若站在马克思人学的高度来看社会形态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原本看似分散、甚至矛盾的形态划分实则有着共同的价值主题、共同的价值目标,它们都是为这一共同的价值目标服务的。多种社会划分标准所体现的分歧与矛盾只是表明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因素的缺场都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
马克思依据不同的标准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了多样性的界定。这些界定虽有不同甚至有莫大的时空差异但均服务于人类解放这一价值主题,均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换言之,马克思的各种社会形态理论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规律而去揭示规律的,马克思是为了实现人类解放、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去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为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更加关注人类的现实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起点,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内在地决定了人类解放的条件和路径。也正是出于此种原因,马克思诸种社会形态界定的重点均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在“二种社会形态理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与理想社会相对立的现实社会的最高阶段”的身份出场的;在“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中,马克思更是以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通向理想社会的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所带给人类的物质前提和物的奴役。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12]由此可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逻辑主线就极为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马克思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种形式是为了全面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为了实现人类解放、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终极目标,与其相比,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还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诸种形式的比较、研究都只是手段而已。
在马克思人学的视域中“二种社会形态理论”、“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以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三者的统一性表现为它们都是人类生命特性发展的产物,都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共同展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的差异性表现为它们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人类生命特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只是从不同的维度揭示了人类生命特性发展的进程。
具体而言,“二种社会形态理论”对接的是人的生命自由。生命自由源自人的类特性——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人类独有的生命特质使人不甘于像动物那样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在与自然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然、不断地突破自然对人的束缚与限制,不断地把自然变成人化的自然。从生产力的维度看,生命自由具有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的自由为必然王国领域内的自由——人类“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13]——生存自由;高层次的自由为自由王国领域的自由——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发展自由。生存自由是发展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生存自由才会转化为发展自由。发展自由是生存自由的目的和归宿,发展自由使生存自由具有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14]。因此,生命自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是人在依赖自然前提下对自然的统治与征服,人类只有彻底摆脱外在目的规定的束缚才能实现生存自由,也才有可能实现发展自由。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对接的是人的个体自由。个体自由源自于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统一。一方面,由于个人的有限性,使其必须和他人进行交往、联合,必须借助他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合作性、联合性使个人与社会的利益趋于一致。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7]161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发展。自人类从社会利益中分化出自我利益以来,先后受到了血缘关系、土地关系、资本关系的束缚。这些束缚使人类生活在虚幻的集体当中。个体与社会产生的激烈对抗使得个人无法充分地借助社会平台得以自由地发展。马克思认为,个人若想获得个体自由就必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119。就此意义而言,个体自由是个人与社会对抗性的消解,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个人只有在生产关系中消除人与人的对立,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才有可能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个体自由。
“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对接的是人的个性自由。个性自由是人的自由的一种特定形式,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主地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设计,或者说是指社会生活允许人们自主地追求自身区别于他人的特异性[15]。个性自由就是个人通过自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生存条件的一种自觉控制。个人在这种自觉控制自身生存条件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个性,从而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自我。首先,个性自由是人的自我实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主地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设计就意味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对象世界;就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得以运用;就意味着人实现了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实践中确证了人自身的存在。其次,个性自由是人的自我超越。人能动地实现了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就表征着人已经告别了原来的自我,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新我。个人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6]人的自我生成的本质使人不是止步于刚刚形成的新我,而是进行新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如此一来,人就不断地自我选择、自我设计,不断地超越自我、形成新我。
综上所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生命自由、个体自由、个性自由的三位一体。离开了任何一种自由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难以实现。与之相对应,在马克思人学视阈中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划分非但不相矛盾而且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它们既从不同的维度标示了人类生命特性的发展进程,又从不同的层面诠释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三者的差异恰恰反映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1-472.
[2]庞卓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8-2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5]孙来斌.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内在统一[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5-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9]孙显元.“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J].学术界,2006(6):21-3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4-48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
[14]周鹏.马克思人学思想层次论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月刊,2014(5):28-34.
[15]汪信砚.论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概念[J].学习与探索,2004(5):11-1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The academic has a significant academic difference about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form in Marxist theory. It mainly embodies on “two kinds of theory form”, “three kinds of theory form” and “five kinds of theory form”, and each expert sticks to his argument. It is possible and inevitable to start integration of human study to the social formation in Marxist theory because the pers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in Marxist theory. From the height of Marxist humanism to research the social formation theory, we will find that a scattered and even contradictory social formation theory actually is a unity of opposites. The unity shows that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is an outcome function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 diversity sho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man lif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om different aspects.
Key words:the social formation theory of Marx; academic division; integration of human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