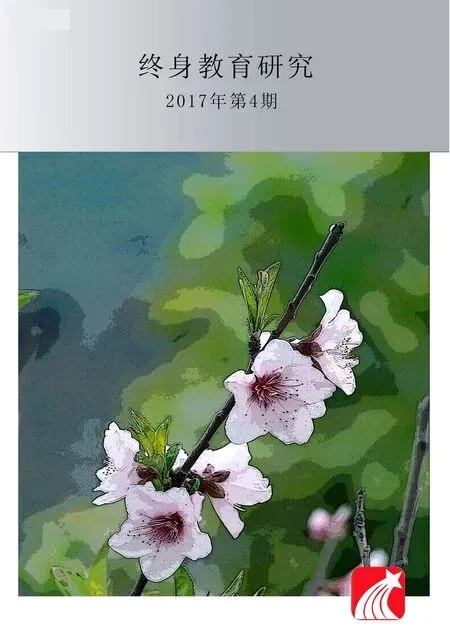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马洪正
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马洪正
社会教育在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民国社会教育开始被纳入研究范围,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研究热潮。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思想研究和实践研究;研究范式可概括为整体研究和分类研究;研究特点表现为重实践、轻理论,重史料、轻关照。学术史研究、理论史研究应该成为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重要任务。
近代;社会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教育”一词于20世纪初期引入我国,由于切合了我国当时的教育实践,所以很快被赋予了中国本土元素。民国初期社会教育制度化以后,社会教育“本土化”进程加速。于述胜教授认为:“社会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的制度设计中,是一个处在流变过程中的历史概念,其历史功能包括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两个方面,其具体职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1]诸如“通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成人教育”“补习教育”“扩充教育”“识字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等教育形态都具有近代社会教育的内涵和功能,在我国近代的一定时段都曾承担过重要的社会教育职能。从当时的制度设计、职能表现以及当今学者的研究来看,上述各类教育形态都可纳入近代社会教育的研究范畴。因此,我们将本文中的社会教育概念界定为: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学制系统之外,利用社会设施(包括中小学及大学)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活动的统称。鉴于近代社会教育具体形态纷繁复杂,本文仅对通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等几种主要的社会教育形态和“社会教育”这一整体概念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将这些研究的内容进行纵向梳理,对研究方法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思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0年代:社会教育概念的偏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学界鲜有近代社会教育的专门研究成果,仅有的几部人物类专著,也主要涉及人物的社会教育思想介绍及其对社会教育运动的影响,如《梁漱溟思想批判第1辑》(1955)、《梁漱溟教育文集》(1987)、《陶行知研究》(1987)、《陶行知教育思想讲话》(1988)、《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1988),等等。工农教育、职工教育、业余教育、成人教育等成了“社会教育”的代名词,譬如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编写的《中国成人教育词汇》对“社会教育”词条的解释是:“在中国,习惯把教育分为三大类,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主要用于幼儿、少年;学校教育受益于少年和青年;社会教育主要面向成年人。社会教育的形式、内容更为广泛多样无限,它在中国除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以学校和班级形式进行系统文化技术知识教学外,迅速发展着的图书馆、博物馆、报纸杂志、文学艺术、电影戏剧、音乐美术,以及机关、团体、部队经常性的会议报告、知识讲座等,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一生中知识的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这一表述中的社会教育概念即是在近代社会教育实践基础上进行概括的。王文林认为:“在旧中国,……曾经把成人教育称为平民教育、社会教育、补习教育、民众教育”[3]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称成人教育为社会教育,后又改称工农教育、业余教育,从1982年开始,才正式称为成人教育”[3]22。可以看出,王文林将社会教育概念与成人教育概念画了等号。王茂荣在《成人教育学基础(上册)》(1988)也将我国近代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干部教育、职工教育等悉数纳入成人教育的研究范畴。
即使学者以“成人教育”概念来考察近代社会教育,但是研究内容已经不再涵盖当时社会教育的全貌,而主要以当时共产党主导的社会教育为主线。譬如,1984年5月时任中国成人教育学会秘书长姚仲达认为:“将成人教育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使其成为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发展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4]。文章仅探讨了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成人教育的政策主张。秦向阳在《成人教育学》(1989)中也将我国成人教育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概括: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补习教育、通俗教育;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平民教育;三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包括自修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红军大学、劳动学院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干部学校;四是解放战争时期,包括职工教育以及逐步实施系统的政治、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等。[5]这些成果回避了我国近代产生的“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乡村教育”等概念。但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华东师范学院教育系曾编著《儿童社会教育》一书,试图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的儿童社会教育实施,可惜的是“社会教育”的提法在当时并未引起共鸣。我们认为,大陆学者对历史的不同回应,正是思想转折时期的一种自然反映。
二、1990年代以来:两种基本研究范式的形成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到了1990年代,“通史”类型的教育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这些著作中多对民国社会教育有所涉及,譬如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1994—1996年)就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生产教育、国民基础教育、科学教育、民众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潮进行研究,并指出“对此,我们曾一度采取否定态度,显然是不公平的”[6]。评价上的解禁,为此后的近代社会教育研究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禁区”被打开之后,立即在大陆形成了一股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热潮,并逐步形成了两种基本研究范式,即整体研究和分类研究。
1.整体研究
整体研究就是将“社会教育”作为一个核心词汇,将其视为一个统合性的概念进行研究,在论述的过程中往往将诸如通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成人教育、民众教育等具体教育形态纳入社会教育研究范畴。
首先,对社会教育概念的历史溯源及再定义。台湾学者詹栋梁曾对西方社会教育概念的产生进行过考察,他认为:“1835年,德国教育学者狄斯特威格(Diesterweg)在其《德国教师陶冶的引路者》(Wegweiserzur Bildung duestcher Lehrer)中首先使用社会教育(Sozialp dagogik)这个名词,并建立了社会教育理论。”[7]这种说法也被众多研究者引用。王雷教授较早对我国近代“社会教育”概念传入进行过考察,他认为:“我国近代‘社会教育’名词,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最初是由日文翻译而来。”[8]虽不是由德国直接传入我国,但“近代社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受日本和德国社会教育双重影响的结果。”[8]杨才林、孙伟等绝大多数学者都支持王雷的观点。当然,学者们并没有仅仅满足于社会教育概念传入的考略,在研究中,他们也给出自己的概念界定。譬如,庄志龄认为,“广义上讲,凡教育事业皆可称为社会教育。狭义的社会教育,是指普通教育以外的所有教育形式,即以不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人为对象的教育,它包括职业教育、补习教育、扫盲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科学教育等。[9]王雷给出的定义是:“近代社会教育主要指学制系统以外、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私人和民间团体推动为辅,为了提高失学民众以及全体国民的素质,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10]8杨才林教授认为:“从理论上看,通俗教育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平民教育亦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民众教育名理混乱,与社会教育名异实同。从史实上看,通俗教育强调了这类教育的‘浅显易懂’,平民教育、民众教育强调了这类教育的受教对象,而社会教育则强调的是施教场所。所以,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指家庭教育、普通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11]31很显然,在杨才林看来,社会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于述胜教授通过对民国时期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职掌范围变动的分析认为:民国初年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专门教育相对应,是指通过建立和完善面向社会民众的现代文化设施、组织,以充分发挥其教育效能;大学区制期间,社会教育是在与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对应中,并在与一般文化事业相分化的基础上,获得其具体内涵;1936年对社会教育实施范围又作调整,这时社会教育概念,实指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外、面向普通民众的一切教育设施和活动;1947年教育部调整官制,成立国民教育司,过去社会教育中的扫除文盲、办理成年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等,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故而,于述胜归纳指出:“社会教育是一个流变的概念,它随着当时教育实践形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即便如此,由于建设现代文化事业为其重要内容之一,故当时社会教育概念的外延是异常宽泛的。”[1]
其次,对社会教育目的、功能和意义的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近代社会教育的功能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国家统治(政权巩固)的需要、社会改造的需要、教育改造的需要以及人的社会化需要等几个方面。譬如,杨才林、周慧梅《论清末和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一文认为:从严复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再到陈独秀的“新青年”主张,进而到晏阳初“作新民”的教育、南京政府“唤起民众”的教育和毛泽东的“人民教育”,经过各种概念的语义变迁及其教育实践,可以将社会教育宗旨总结为“民众”在中国近代被“重新发现”的历程。“作新民”的宗旨更多彰显了社会教育的价值理性,而“唤起民众”的口号则更多体现了社会教育的工具理性,但两者都可以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其同一性则是变革教育、培养新国民,担负起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12]黄正林认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13]张孝芳从社会教育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农民生活的中心从此由自家的场院转移到党所期望的集体活动框架中,为党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4]扶小兰从宏观层面分析了社会教育的功能,表现在:推动了近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近代政治的变革;促进了近代文化的转型和变迁。[15]仪淑丽认为,无论是乡村建设派还是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均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是在通盘考虑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前提下,将社会教育与改造农村、拯救中国结合起来,都将“改造社会”作为社会教育的终极目的。[16]于述胜将社会教育的功能定位于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两大方面。李中亮认为社会教育的本旨是在“道德、学术、艺术、政治、实业和体育等方面,启发一般社会民众的智识。”[17]另外,庄志龄、扶小兰等还论述了社会教育在促进传统城市人向现代城市人转变的重要意义。
第三,划分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阶段。对历史实践进行分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近代社会教育纷繁复杂,一些学者依据不同时期社会教育主要实践形态的差异对社会教育发展进行了分期。王雷的分期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中将我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分为萌芽期、确立期、发展期和分化期。几年后,他在《我国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一文中对这四个发展阶段的社会教育作了进一步概括[18]:第一阶段:社会教育的萌芽——以识字教育为起点(1895—1912年),这个时期的社会教育是在晚清政府推动下进行的;第二阶段:社会教育的确立——以通俗教育为中心(1912—1919年),受欧美及日本通俗教育的影响以及国内失学民众教育的现实需要,随着社会教育司的建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通俗教育运动开始形成;第三阶段:社会教育的发展——以平民教育为中心(1919—1927年),这个时期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总的特点是以平民教育的实践与实验为中心来开展的。第四个阶段:社会教育的分化——工农教育与民众教育并起(1927—1949年),这个时期国内两个政府对立并存,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社会教育在发展和选择中开始分化,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社会教育格局。杨才林将民国社会教育发展也分为四个时期[11]59-83,即通俗教育运动时期(1912—1918年)、平民教育运动时期(1919—1926年)、民众教育时期(1927—1936年)、战时社会教育时期(1937—1949年)。其他研究者的同类研究基本没有突破王雷和杨才林的分期方式。侯怀银、张宏波等将我国社会教育在整个20世纪的研究历程分为两段[19]:即起步阶段(1906—1911年)和高潮阶段(1912—1948年)。另外,有学者还将近代社会教育发展史纳入学科史进行考察。譬如,侯怀银、吕慧等将1904—1948年的社会教育视为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初建阶段;吕春枝将我国近代社会教育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社会教育学”的萌芽、“社会教育学”的探索、“社会教育学”的发展(1927—1949年)。
鉴于民众教育在民国社会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学者从民众教育视角来考察民国社会教育发展分期,他们将“民众教育”视为社会教育的主体形态,其他形态的社会教育都是民众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譬如,张蓉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将民众教育思潮的演进分为三个时期:酝酿萌芽期(1912—1925年),期间社会教育制度确立,通俗教育推行,平民教育思想兴起;形成发展期(1926—1937年),政府提出了民众教育概念并出台大量法规,大力推进民众教育运动;转型衰落期(1938—1949年),抗战时期,包括民众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民众教育思潮最终退出了时代舞台。[20]周慧梅的博士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认为,南京政府成立后,民众教育成为近代社会教育的一个特定阶段和典型形态,此前存在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等可视为“泛指的民众教育”。她将民众教育发展在广义上分为通俗教育、平民教育和民众教育三个阶段。[21]
2.分类研究
整个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定义和范畴,议论纷纷,并没有弄得很清楚。以至一般人对于社会教育还没有明确的认识。”[22]事实也是如此,各种社会教育形态之间的概念和内涵纷争一直伴随着整个民国时期。这使得当今学者常常以近代社会教育的不同具体形态为研究对象,笔者将此概括为分类研究范式。这些社会教育形态分别出现于近代不同具体时段,主要包括通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等,它们各自发挥着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等重要功能。
(1)通俗教育。一般认为,通俗教育的形成、发展与当时日本同一形态的社会教育是紧密相关的,实施方法也经常采用当时日本的一些做法。贾蕊华等曾有表述:“据 1904年12月3日《大公报》记载河北保定的官绅谷钟秀等人援引日本通俗演说之例,设立茶话所,以推广通俗教育,并主张从戏剧开始。”[23]作者有意追溯通俗教育概念的起源,但是显得信心不够;王雷将中华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起人伍达翻译日本的《通俗教育事业实施法》(1912)作为研究我国近代通俗教育的起点。截至2016年底,中国知网以近代“通俗教育”为篇名收录的期刊论文17篇,博士论文1篇。从成果来看,较多地集中在通俗教育的功能、重要人物与通俗教育事业发展,以及区域通俗教育设施(如通俗教育馆)等方面。
(2)平民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及民众教育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教育形态。由于它们与教育公平、教育民主等教育理念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在教育理论上与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公民教育同构,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平民教育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其较早受到学者关注,1960年代便有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杨东平教授认为:“最早提出平民教育理念的,可能是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提出的‘提倡平民普及教育’的办刊宗旨。1915年,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以人民为主人’的‘民主国家’的‘唯民主义’教育方针。”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轫的平民教育,则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一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由邓中夏等共产党人提倡和举办的平民的教育活动;二是由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24]截至2016年底,中国知网以近代“平民教育”为篇名收录的期刊论文309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18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人物平民教育思想、理论与方法,平民教育事业(如平民学校等)、区域平民教育或者整个平民教育运动等。大多研究成果注重历史呈现,也有的研究成果关照现实,譬如杨东平的《平民教育的流变和当代发展》(2008)沟通了历史与现实,在对平民教育理论层面分析基础上,认为当代平民教育、“穷人教育学”的实践,重新强调了面向大多数人的价值,重视面向农村、农民工及其子女等弱势群体的教育,倡导“平民化的教育”,坚持教育平等、教育民主的价值。[24]潘家恩的《“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历史及当代平民教育实践为例》(2011)以实践者的独特视角,通过历史与当代结合的平民教育的具体脉络分析,“跳出平民教育看平民教育”。[25]
(3)乡村教育。一定意义上讲,平民教育对象是“市民”,而乡村教育对象是“乡民”,我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延伸。就概念源头而言,顾明远教授认为:“1920年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发表的《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首倡‘乡村教育’一语。”[26]但是,在众多的社会教育著述中,将乡村教育纳入社会教育研究范围的并不多见,往往将乡村教育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客观而言,在实践层面上,我国近代乡村教育可以分为乡村学校教育和乡村社会教育两大部分,张菊霞等就曾对梁漱溟乡村社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进而联系当今培养新型农民的现实,提出了它对培养新型农民的启示。[27]王雷也认为:“从社会教育的意义上来看乡村教育运动,它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下,由教育家和教育家团体所开展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10]72截至2016年底,中国知网以“近代乡村教育”“民国乡村教育”“近代乡村教育思想”为篇名收录的期刊论文112篇,以“近代乡村教育”为主题的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45篇。其中人物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占绝大多数,其他还涉及乡村教育实施方法、区域乡村教育或整个乡村教育运动。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视角对近代乡村教育的特殊功能进行深度挖掘,研究视角焕然一新。
(4)民众教育。民众教育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社会参与最为广泛、国家资源投入最多的一种社会教育形态。民众教育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和语义,似乎与现实距离遥远,从研究成果来看,也更多地侧重于民众教育的历史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众教育思想研究,范围基本涵盖了当时主要的民众教育家;二是民众教育事业研究,主要包括民众教育制度、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民众学校以及电化教育、娱乐教育、体育教育实施等;三是民众教育概念内涵及其功能研究。截至2016年底,中国知网以“民众教育”为篇名收录的期刊论文136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22篇。譬如,周慧梅对民众教育概念、民众教育制度等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毛文君、周慧梅对民众教育馆进行过深入的历史研究,张蓉曾对民众教育思潮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并将民众教育置于终身教育思想中进行研究,等等。
(5)成人教育。作为一个专有概念,成人教育在我国近代出现要稍早于民众教育,但是却没有获得民众教育那样的历史地位与评价。总体看来,将成人教育视为近代社会教育一种具体形态进行研究还没有走出1990年代以前思维模式,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共产党当时主导区域的社会教育实施,成人教育思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者”。
综上,将近代社会教育研究概括为整体研究和分类研究两大范式,主要是基于社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形态之间的实践关系(而不是逻辑关系)考量的。首先在制度设计上,社会教育统一了其他几类教育形态;在学理层面上,其他几类社会教育形态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均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教育思想与理论的传播密切相关;在实践层面上,正是由于不同时段面临不同问题,也出于强烈的教育实践愿望,才会在不同时段产生不同的社会教育实践形态。
三、我国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经世致用”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功能,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以传承经验和汲取智慧,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进而获得教训和启示,是谓“彰往而知来”,通过社会教育史料的呈现和解释同样有着获得经验、以古喻今的重大现实意义。回顾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历史,不仅是因为社会教育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术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因为近代社会教育研究与当下社会教育研究有着天然而直接的关联性和一致性。通过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回顾和反思,可以进一步提高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效度,最终更有效地指向现实。
1.对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反思
不可否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社会教育研究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除了长期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之外,一大批年轻研究者也纷纷加入到研究行列,较大程度地丰富了近代社会教育的研究成果。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重于近代社会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由于当时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问题导向,重于解决当时社会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史料也呈现出强烈的实践性特征,这种研究旨趣充分体现了民国学者“务实”的学术品质和风格。限于史料,当今学者更多集中于社会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
其次,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受到重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早在1990年代,上海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就汇编出版了近代(民国)教育史料,社会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国第一批较为完整的近代社会教育史料。近年来,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越发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社会教育的专门史料开始出现,《近代北京社会教育史料汇编》(刘晓云主编,2011)《民国教育史料丛刊》(李景文、马小泉主编,2015)中的社会教育单行本都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支撑。另外,史料电子资源越发丰富,一些高校电子文献开始广泛收录近代社会教育史料。
再次,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宽。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视角不断拓宽,如有学者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近代社会教育进行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教育学视角,这些不同的学科视角为人们呈现了多元研究旨趣。随着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研究者在历史回溯中,也开始关注现实,增强了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现实意义。
最后,理论研究受到重视。有学者认为,近代社会教育的理论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理论性”史料的不足确实给近代社会教育理论史研究带来了困难。尽管如此,近代社会教育的理论史研究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史料的真实呈现,当前我国近代社会教育研究主要还处于这一阶段,即事业发展的研究。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至今已经有了近30年的研究历史,但是事业发展的研究依然还有很大的空间,譬如从横向上看,区域性研究覆盖面不够,由于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制度复杂,社会教育事业呈现出区域性特点,不同区域的社会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纵向上看,时段性研究较为集中于民国时期产生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等,对这一时期的其他形态的社会教育关注不够。从内容上看,历史叙述痕迹较重,社会教育学理层面的挖掘不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另外偏重“自上而下”的研究,缺乏社会教育实施对象的体验性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尽管已经有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但是重视程度不够,成果不多;另外鉴于近代特别是民国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缺乏与普通学校教育的比较研究(包括普通学校承担社会教育义务)。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上,偏重于社会教育现象和活动本身的研究,缺乏研究的现实指向。
2.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综合上述对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特点和不足的分析,本文认为,未来对于近代社会教育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加强。
一是将社会教育置于社会近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要从多学科视角挖掘近代社会教育的历史存在价值。因为近代社会教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的本身,更重要的目的是从教育的视角关注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
二是从学术史的视角,深度挖掘近代社会教育的学术人物、学术活动、学术事件、学术规律等。社会教育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与当今社区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概念存在着内涵和理念上的高度关联,学术史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这些教育形态的内涵,对学科史的贡献也有着重大意义。
三是不局限于思想研究,加强近代社会教育的理论研究,增强理论关怀,注重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和逻辑性,“合零为整”,努力挖掘社会教育事业背后的理论支撑。如果说学术史研究更多地关注历史的真实存在,那么理论史研究则可以有效沟通历史与现实,凸显历史研究的“以古喻今”功能。
四是破除历史“不是一般人民的历史”的“魔咒”,努力避免历史研究的单向性,转变自上而下的史观。历史研究就是要努力还原历史真实,不能只看到制度下的“社会教育”,也要顾及老百姓心中的“社会教育”,研究中要阐释上下互动的过程,不能只做一半的研究。
五是通过历史发现来认识社会教育的本质,丰富社会教育的内涵;通过不同学科视角(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研究,更大领域、更大程度地关照现实,努力增强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六是研究者要有一定的学术担当,立足于学术发现,加强史料的解释力,善于或勇于提出学术见解;将近代社会教育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客观、理性评价近代社会教育的历史贡献,以“科学”的态度,努力追求真善美,崇尚学术自由,注重学术创新。
总而言之,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问题,社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不仅因为社会教育是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社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来讲,与学校教育研究、家庭教育研究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对近代社会教育的研究工作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是我们深信,随着现代教育日益向着整个社会和个人终身方向延伸,以及“全民学习终身化”理念的提出,我国传统学校教育必将向社会教育拓展,社会教育的研究将越发受到更高的重视。我们也将从社会教育的历史研究中发现更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人们对近代社会教育研究的深度、广度、视角和方法等也将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 于述胜.民国时期社会教育问题论纲——以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多维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3):18.
[2] 《中国成人教育词汇》编写组.中国成人教育词汇[M].北京: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1984:2.
[3] 王文林,余博,宋文举.成人教育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 姚中达.生产力发展推动成人教育前进[C]∥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上海国际成人教育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5.
[5] 秦向阳.成人教育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1-2.
[6] 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七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451.
[7] 詹栋梁.现代社会教育思潮[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3.
[8] 王雷.“社会教育”传入中国考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4):40.
[9] 庄志龄.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社会教育[J].史林,1998(4):75.
[10] 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1] 杨才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2] 杨才林,周慧梅.论清末和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5):167.
[13] 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50.
[14] 张孝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J].山东社会科学,2008(8):137.
[15] 扶小兰.论社会教育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J].中国成人教育,2010(10):5-7.
[16] 仪淑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教育——乡村建设派的社会教育与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之比较[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4):143.
[17] 李中亮.中国成人教育学发展史纲要(上) [J].成人教育,2007(11):17.
[18] 王雷.我国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82-84.
[19] 侯怀银,张宏波.中国社会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3):119.
[20] 张蓉.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
[21] 周慧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6.
[22] 陈大白.展开社会教育之复兴运动[J].中华教育界(复刊),1948,2(11):8.
[23] 贾蕊华,贾俊兰.昙花一现的民初通俗教育研究会初探[J].沧桑,2006(6):120.
[24] 杨东平.平民教育的流变和当代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29(3):8-9.
[25] 潘家恩,温铁军.“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历史及当代平民教育实践为例[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3):67.
[26]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554.
[27] 张菊霞,夏金星.梁漱溟乡村社会教育思想与新型农民培养[J].职教论坛,2007(1):62.
责任编辑 虞晓骏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MAHong-zheng/
NanjingNormalUniversity
Social education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1980s, with the lifting of ideology, the social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gan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search area, beginning to form a research craz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90s.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thought and practice. The research paradigm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overall research and the classified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presen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actice, underestimating theor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underestimating care. The research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history should be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education research in modern society.
modern China;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
2017-05-30
10.13425/j.cnki.jjou.2017.04.006
马洪正,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教育史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基本理论研究(50005@nj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