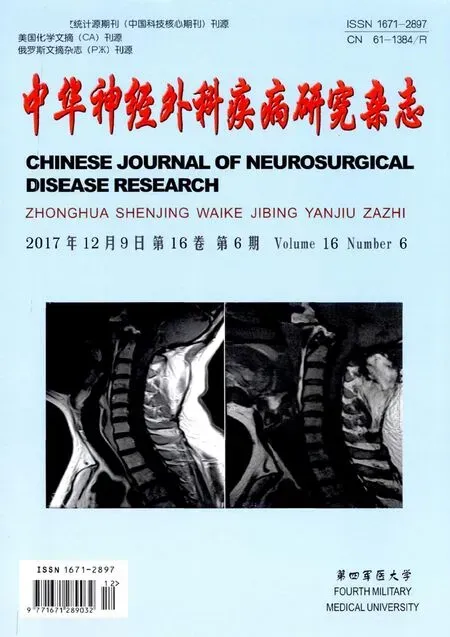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机制研究进展
李智敏 王任直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北京 100730)
脑深部电刺激是近30年飞速发展的一种治疗运动障碍性疾病和神经精神疾病的外科治疗手段,对于帕金森病及其他神经精神疾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然而,尽管脑深部电刺激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我们对于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作用机制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因此,针对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机制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可以更好地理解脑深部电刺激对人脑和疾病产生的影响,并对更深入的科学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一、概述
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是通过立体定向方法进行精确定位,在脑内特定的靶点植入刺激电极进行高频电刺激,从而改变相应核团兴奋性,以达到改善帕金森病症状、控制癫痫发作、缓解疼痛等的一种神经外科新疗法,现已成为治疗神经外科功能性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可以用于治疗如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特发性震颤(essential tremor, ET)、肌张力障碍、癫痫、妥瑞氏综合症(Tourette's syndrome, TS)、重度抑郁、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等疾病。2014年,因为在高频电刺激丘脑底核治疗晚期帕金森病患者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Alim Louis Benabid和Mahlon DeLong被授予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Lasker-DeBakey Award)[1],这也意味着DBS在21世纪的神经科学领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又称震颤麻痹,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该病起病缓慢,呈慢性进行性发展,主要临床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强直、运动徐缓和姿势步态异常,该疾病的临床表现最早由James Parkinson在1817年描述。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然而对于中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常不可避免地出现药物疗效减退和一些严重并发症,通过系统的药物调整也无法解决,这时就可以考虑脑深部电刺激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最早的将电刺激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记录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人们利用电鳐放电刺激人体来治疗疼痛,这也是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的雏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脑深部电刺激的应用越来越广泛。DBS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用于治疗顽固性疼痛,后又用于治疗癫痫。1987年,Benabid等[2]采用DBS刺激丘脑腹外侧核(ventral intermediate nucleus, VIM)治疗PD性震颤和特发性震颤获得成功,并且通过研究表明DBS可以获得与丘脑毁损术相似的治疗效果,且前者比后者并发症更少、死亡率更低。自此,DBS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93年,Benabid等[3]首次应用高频电刺激丘脑底核(subthalamic nucleus, STN)治疗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对运动障碍和运动波动症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1997年,脑深部电刺激系统(activa system, Medtronic Inc.)用于治疗特发性震颤(ET)获得美国FDA批准,随后该项手术技术分别于2002年、2003年和2009年获FDA批准治疗帕金森病(PD)、肌张力障碍(dystonia)和强迫症(OCD)[4]。1998年,我国实施了首例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手术。
DBS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逐渐发展成为治疗晚期帕金森病的一种有效治疗方式,尤其对于缓解晚期帕金森病的运动功能障碍有很好的效果。DBS治疗PD的靶点包括丘脑底核(STN)、苍白球内侧核(internal part of the globus pallidum, GPi)以及脚桥核(pedunculopontine nucleus, PPN),其中最常用的靶点是STN和GPi。研究发现STN或GPi脑深部电刺激可以显著减少患者的左旋多巴药物用量,李维新等[5]对进行双侧DBS治疗的32例帕金森病患者进行3年的随访评估,使用帕金森病统一评分量表(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 UPDRS)进行评分,发现未同时使用左旋多巴组改善率为48.7%,使用左旋多巴组改善率为50.6%,同时左旋多巴用药量减少了46%。然而也有研究报道长期STN-DBS可能会造成患者的认知障碍[6]。因此,普遍认为STN-DBS更适合于用药剂量较大且没有明显认知功能减退的PD患者;GPi-DBS更适合于运动障碍或已经存在认知功能减退的患者。有研究证实,针对于STN-DBS或GPi-DBS治疗的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其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且其效果优于最佳药物用量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
二、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机制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现在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分别在细胞、组织和系统水平研究DBS的起效机制,例如电生理学、影像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法。电生理学技术有很好的时间分辨率,而功能成像技术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通过电生理学方法可以直接测量神经元活动,而通过影像学技术如PET、fMRI,不仅可以测量局部信号的变化,还可以研究整体水平的改变。因此,这些技术手段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下面将根据研究技术方法的不同,分别探讨DBS治疗PD机制的研究进展。
1.电生理学方面的研究:早期的电生理学研究发现在STN-DBS和GPi-DBS中,靶点区域的神经元放电减少,因此提出了高频脑深部电刺激抑制了神经元活动的假说。针对高频电刺激使神经元活动被抑制的现象,人们假设出三种可能的机制:①去极化阻滞(depolarization blockade),即刺激改变了电压门控钠通道的活性或引起细胞外钾离子的聚集[7]而阻滞了刺激电极周围的神经信号输出。②突触抑制(synaptic inhibition),刺激通过抑制与刺激电极周围神经元有突触联系的轴突终末,间接调节神经信号的输出[8]。③突触耗竭(synaptic depletion),高频刺激使得神经递质耗竭,阻碍突触信息传递,从而抑制了电极周围的神经元活动[9]。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上述假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假说并没有将传出神经纤维的独立电活动考虑在内。McIntyre等[10]认为神经元胞体在高频电刺激下的反应并不能完全代表传出神经纤维轴突的反应。Hashimoto等[11]发现对MPTP猴行STN-DBS导致了GPi的神经元放电频率增加。因此人们推测DBS在刺激神经元胞体与刺激轴突时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电刺激作用于神经元胞体会抑制传入通路,而作用于神经纤维轴突会激活神经传出通路。
然而,虽然上述研究中观察到STN-DBS导致了向GPi的传出信号增加,但是GPi的神经元活动仍表现为被抑制,这是因为神经轴突的电活动还能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或改变细胞膜或突触的电生理属性来激动或抑制下位神经元。Hashimoto等[11]发现STN神经纤维轴突输出信号的增加同时还伴有基底节区其它部位的多突触激活,单脉冲刺激STN后可以监测到GPi神经元的短暂兴奋继而出现强烈的抑制。这些现象也说明在DBS治疗帕金森病的过程中,复杂的多突触反应比单突触反应起到更主要的调控作用。
脑深部电刺激神经纤维轴突,其产生的电位可以在神经纤维上双向传导。顺行传导峰电位可以将病理性的神经元活动调整至刺激频率,McConnell等[12]在对6-羟基多巴胺(6-hydroxydopamine, 6-OHDA)大鼠PD模型行STN-DBS后发现,在苍白球外侧部(external part of the Globus Pallidum, GPe)和黑质网状区(substantia nigra reticular part, SNr)记录到的病理性低频电生理震荡被调整至与刺激频率相同的模式。而逆行传导峰电位可能与神经元胞体发出的冲动相冲突或激活神经元胞体并使其处于不应期,从而抑制了病理性神经网络中信号的继续传导。
因此,DBS治疗PD在电生理学方面有多种机制假说,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假说可以很好的解释所有的治疗后改变,并且神经网络的精密性和复杂性也使得电生理机制互相影响和干扰。在多种机制对基底节环路的影响下,DBS对神经元胞体的抑制作用和对神经纤维轴突的兴奋作用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来恢复正常的基底节功能。
2.影像学方面的研究:由于影像学检查拥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因此,多种影像学技术常被用来从整体角度研究DBS后PD患者或模型的脑内变化情况。如应用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blood-oxygen level dependent fMRI, BOLD-fMRI)、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SPE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PET)等可以估计局部脑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应用18-FDG PET检查可以测量脑代谢率,基于特异性配体的PET可以用来测量特定神经递质及神经递质受体的含量。然而,fMRI在研究DBS作用机制方面的应用还不是很广泛,因为刺激电极对成像的影响、金属电极的电磁效应以及设备功能易受干扰等因素均使MRI的应用受限,因此,指南规定关闭刺激器并应用不超过1.5 T的低场强MRI可以进行MRI检查。201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脑起搏器在给帕金森病患者植入后进行了全球首例3.0 T MRI检查,此项技术可能使MRI在DBS机制方面的研究应用更加广泛。
有研究者通过影像学研究了不同的皮层环路,发现纹状体-中脑-额叶运动环路,包括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等与自发运动相关的结构在PD患者中减少。且STN-DBS可以减少初级运动皮层(primary motor cortex, M1)、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前运动皮层(premotor cortex, PMC)在静息状态时的脑血流量,同时也可以减少SMA、ACC、DLPFC在静息状态的局部脑血流量。Yu等[13]发现STN-DBS可以降低安静时皮层的过度兴奋,而这也可能是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僵硬症状的基础。而Karimi等[14]通过监测丘脑局部脑血流发现,DBS改善帕金森病运动徐缓症状的作用与运动丘脑区域的活性改变是相关的。
在正常人自主活动时可以通过影像学的方法观察到SMA、ACC、DLPFC、同侧小脑、壳核以及岛叶皮层的兴奋性增加,而同侧M1以及对侧小脑的兴奋性减退。Eckert等[15]通过PET扫描PD患者后发现,苍白球、丘脑以及运动皮层的代谢活性增加,同时还有PMC及顶枕叶的代谢活性降低。而这一PD患者脑内病理性的代谢模式经STN-DBS后可有好转。
FDG-PET扫描PD患者后发现感觉运动皮层、小脑、脑桥和壳核等代谢增高,Mure等[16]称之为帕金森病震颤相关代谢模式(PD tremor-related metabolic pattern, PDTP),这一代谢模式在行Vim-DBS后缓解。与此不同,另一种代谢模式称为帕金森病相关代谢模式(PD-related metabolic pattern, PDRP),表现为苍白球、壳核、丘脑、脑桥、小脑和感觉运动皮层代谢增高以及侧前运动皮层代谢减低。这提示PD中震颤症状和肌强直-运动障碍症状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是不同的。Vim-DBS可以显著减少PDTP的兴奋性,这与Vim-DBS可以明显改善PD的震颤症状是一致的。而STN-DBS可以显著减少PDRP的兴奋性,这提示STN-DBS可以更好的控制肌强直-运动障碍症状。
3.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锥体外系中主要起信息传导作用的神经递质包括多巴胺(dopamine, DA)、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谷氨酸(glutamate acid)。神经系统中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神经递质的作用,因此,神经递质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神经网络的信息传递随之改变。DBS治疗帕金森病,也会通过改变递质水平来改善疾病症状。
多巴胺(DA)是调节运动功能的关键神经递质,黑质纹状体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是PD的主要特点。STN-DBS可能通过直接刺激存活的黑质-纹状体神经元来促进多巴胺的释放。有研究者应用微量透析法和伏安法等分析技术,发现STN-DBS可以明显提升细胞外多巴胺水平,同时引起6-OHDA大鼠PD模型的纹状体多巴胺释放[17]。曹依群等[18]对偏侧帕金森病模型猴进行STN-DBS,并分别在术前、刺激后1个月、刺激后3个月行SPECT检查,发现纹状体区多巴胺转运体特异性摄取率增高,多巴胺D2受体特异性摄取率下降,表明DBS提高了纹状体区多巴胺的代谢活性。虽然在许多动物模型中观察到了多巴胺释放增加,但是在人体中的研究并不支持STN-DBS导致多巴胺释放的假说。Abosch等[19]应用11C-Raclopride-PET来评估多巴胺受体水平,并没有发现在STN-DBS后多巴胺受体水平有变化。因此,对于DBS是否引起了多巴胺释放增加就,目前仍存有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
γ-氨基丁酸(GABA)是脑中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在PD患者中,GPi的GABA抑制性传出信号增加,导致了丘脑、大脑皮层的兴奋性降低,这是PD的运动相关临床表现的生化基础之一。Dostrovsky等[20]研究发现GPi-DBS可以兴奋发自纹状体和GPe神经元的轴突终末,导致GABA释放增加并抑制GPi神经元。Filali等[21]发现STN-DBS可以使GPe传至STN的GABA增加,从而抑制STN神经元兴奋性并进而导致GPi的神经元兴奋性降低。
谷氨酸是基底节区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且STN神经元也是谷氨酸能细胞。Yoon等[22]认为STN-DBS可能通过抑制STN来减少向GPi的谷氨酸释放,从而减少对丘脑皮层环路的抑制并改善PD的运动症状。然而,Windels等[23]发现STN-DBS刺激麻醉状态的正常大鼠,用微量透析方法发现在SNr和GPe中的谷氨酸水平升高,且STN释放谷氨酸增加。因此,DBS调节谷氨酸释放的机制比较复杂,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4.分子生物学及神经保护、再生与重塑方面的研究:给予PD患者或动物模型脑深部电刺激后,根据治疗效果出现的先后时间,可以分为在数小时内出现的快速效应和在刺激数月或数年后出现的长期效应。前面所述电生理改变、影像学改变以及神经递质水平改变可以解释快速效应,但是不能很好的解释长期效应。
Wallace等[24]对猴MPTP模型行长期(<7个月)单侧STN-DBS,发现在刺激侧SNc的多巴胺能细胞比对侧多20%~24%,这提示了长期DBS可能具有潜在的神经保护作用。Vedam-Mai等[25]通过尸检发现长期DBS治疗的PD患者的室管膜下区(subventricular zone, SVZ)有神经元再生的现象。但是尸检的研究结果无法与临床症状的变化关联起来,因此无法判断神经元再生与症状改善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长期DBS后神经再生的相关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Van Hartevelt等[26]通过比较双侧STN-DBS的PD患者术前术后的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结果,发现在长期DBS后,这些患者在感觉运动皮层、前额叶皮层和嗅觉脑区有结构联系上的变化。这提示长期DBS可能影响人脑整体的结构和功能联系,并且可导致神经重塑。目前我们对于神经保护、再生和重塑等方面的探索还远远不够,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正在逐渐深入。
三、总结与展望
脑深部电刺激自开始应用于治疗帕金森病至今已有30年时间,随着临床和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DBS治疗的疾病谱范围愈来愈广,治疗效果愈来愈好。虽然与之相关的DBS治疗机制的研究也在不断开展和深入,但是目前已知的DBS治疗机制尚不能很好的解释DBS的临床治疗效果。因此,需要更多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来探索DBS的治疗机制,这将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改善DBS临床治疗效果、探寻新的DBS靶点、扩大DBS适用范围。
未来DBS治疗机制的进一步探索仍然离不开技术和设备水平的支持。更加精密的仪器将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定位与分析脑内电生理学方面的改变,从而对电生理机制有更加整体的理解。对人脑解剖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究以及影像学技术对于脑功能区和纤维束的精准定位,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DBS对脑功能和结构的影响。关于神经保护、再生和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新兴的研究领域,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组学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等多种技术的联合应用,将有利于我们探究神经保护、再生和重塑的机制,并且有可能成为未来DBS应用领域的新的转折点。
1DELONG M R, BENABID A L. Discovery of high-frequency deep brain stimulation for treatment of Parkinson disease: 2014 Lasker Award [J]. JAMA, 2014, 312(11): 1093-1094.
2BENABID A L, POLLAK P, LOUVEAU A, et al. Combined (thalamotomy and stimulation) stereotactic surgery of the VIM thalamic nucleus for bilateral Parkinson disease [J]. Appl Neurophysiol, 1987, 50(1-6): 344-346.
3BENABID A L, POLLAK P, GROSS C, et al. Acute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subthalamic nucleus stimula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J]. Stereotact Funct Neurosurg, 1994, 62(1-4): 76-84.
4SCHWALB J M, HAMANI C.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 [J]. Neurotherapeutics, 2008, 5(1): 3-13.
5李维新, 王举磊, 梁秦川, 等. 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3年随访 [J].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 2007, 6(6): 506-508.
6WEAVER F M, FOLLETT K A, STERN M,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 for Parkinson disease: thirty-six-month outcomes [J]. Neurology, 2012, 79(1): 55-65.
7SHIN D S, SAMOILOVA M, COTIC M, et al. High frequency stimulation or elevated K+depresses neuronal activity in the rat entopeduncular nucleus [J]. Neuroscience, 2007, 149(1): 68-86.
8ANDERSON T R, HU B, IREMONGER K, et al. Selective attenuation of afferent synaptic transmission as a mechanism of thalamic deep brain stimulation-induced tremor arrest [J]. J Neurosci, 2006, 26(3): 841-850.
9LOZANO A M, DOSTROVSKY J, CHEN R, et al. Deep brain stimulation for Parkinson's disease: disrupting the disruption [J]. Lancet Neurol, 2002, 1(4): 225-231.
10MCINTYRE C C, GRILL W M, SHERMAN D L, et al. Cellular effects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 model-based analysis of activation and inhibition [J]. J Neurophysiol, 2004, 91(4): 1457-1469.
11HASHIMOTO T, ELDER C M, OKUN M S, et al. Stimulation of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changes the firing pattern of pallidal neurons [J]. J Neurosci, 2003, 23(5): 1916-1923.
12MCCONNELL G C, SO R Q, HILLIARD J D, et al. Effective deep brain stimulation suppresses low-frequency network oscillations in the basal ganglia by regularizing neural firing patterns [J]. J Neurosci, 2012, 32(45): 15657-15668.
13YU H, STERNAD D, CORCOS D M, et al. Role of hyperactive cerebellum and motor cortex in Parkinson's disease [J]. Neuroimage, 2007, 35(1): 222-233.
14KARIMI M, GOLCHIN N, TABBAL S D, et al. Subthalamic nucleus stimulation-induced regional blood flow responses correlate with improvement of motor signs in Parkinson disease [J]. Brain, 2008, 131(Pt 10): 2710-2719.
15ECKERT T, TANG C, EIDELBERG D. Assessment of the progression of Parkinson's disease: a metabolic network approach [J]. Lancet Neurol, 2007, 6(10): 926-932.
16MURE H, HIRANO S, TANG C C, et al. Parkinson's disease tremor-related metabolic network: characterization, progression, and treatment effects [J]. Neuroimage, 2011, 54(2): 1244-1253.
17HE Z, JIANG Y, XU H, et al. High frequency stimulation of subthalamic nucleus results in behavioral recovery by increasing striatal dopamine release in 6-hydroxydopamine lesioned rat [J]. Behav Brain Res, 2014, 263: 108-114.
18曹依群, 周晓平, 胡小吾, 等. 偏侧猴帕金森病模型的脑深部电刺激研究 [J].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 2005, 4(3): 262-264.
19ABOSCH A, KAPUR S, LANG A E, et al. Stimulation of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in Parkinson's disease does not produce striatal dopamine release [J]. Neurosurgery, 2003, 53(5): 1095-1105.
20DOSTROVSKY J O, LEVY R, WU J P, et al. Microstimulation-induced inhibition of neuronal firing in human globus pallidus [J]. J Neurophysiol, 2000, 84(1): 570-574.
21FILALI M, HUTCHISON W D, PALTER V N, et al. Stimulation-induced inhibition of neuronal firing in human subthalamic nucleus [J]. Exp Brain Res, 2004, 156(3): 274-281.
22YOON H H, PARK J H, KIM Y H, et al. Optogenetic inactivation of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improves forelimb akinesia in a rat model of Parkinson disease [J]. Neurosurgery, 2014, 74(5): 533-541.
23WINDELS F, BRUET N, POUPARD A, et al. Influence of the frequency parameter on extracellular glutamate and gamma-aminobutyric acid in substantia nigra and globus pallidus during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subthalamic nucleus in rats [J]. J Neurosci Res, 2003, 72(2): 259-267.
24WALLACE B A, ASHKAN K, HEISE C E, et al. Survival of midbrain dopaminergic cells after lesion or deep brain stimulation of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in MPTP-treated monkeys [J]. Brain, 2007, 130(Pt 8): 2129-2145.
25VEDAM-MAI V, GARDNER B, OKUN M S, et al. Increased precursor cell proliferation after deep brain stimulation for Parkinson's disease: a human study [J]. PLoS One, 2014, 9(3): e88770.
26VAN HARTEVELT T J, CABRAL J, DECO G, et al. Neural plasticity in human brain connectivity: the effects of long term deep brain stimulation of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in Parkinson's disease [J]. PLoS One, 2014, 9(1): e86496.
-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的其它文章
- 广泛开展脊柱-脊髓神经外科诊疗技术
- 反思性教学在培养病理学青年教师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