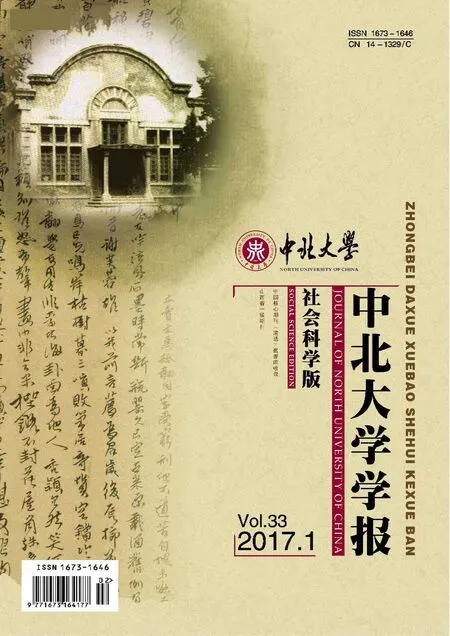论改编与视听翻译
刘大燕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74)
论改编与视听翻译
刘大燕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74)
改编是最自由的翻译形式, 处于翻译的边缘。 本文探讨改编与翻译研究新领域的视听翻译之间的关联, 以及改编在视听翻译中的应用。 首先分析了改编与翻译概念的关系, 然后剖析视听翻译的特色和本质, 指出视听翻译跨越了书面文本和语言符号的界限, 同时由于有符号和媒介等方面的要求, 受到技术的限制, 因此, 视听翻译的本质是改编,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在视听翻译中, 改编主要表现在视听翻译的步骤和技巧中, 并在一些主要的视听翻译模式, 如配音、 字幕翻译、 歌剧的唱词字幕翻译中得到应用。
改编; 视听翻译; 视听文本; 配音; 字幕翻译
0 引 言
改编活动“一直存在”, 是“任何智力活动的‘常见’部分”[1]3。 作为一种极为自由的翻译, 改编也涵盖了其他一些模糊的概念, 如挪用(Appropriation)、 归化(Domestication)、 拟作(Imitation)和改写(Rewriting)等。 许多翻译学者一直排斥改编, 把这种形式看作是一种“扭曲” “篡改”或者“审查”。[1]3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把翻译仅仅视作“直译”, 在他看来, 译者的任务只有一个, 即“把整个文本, 仅仅是文本, 绝对精确地再现”, 由此否定了包括改编在内的其他翻译形式, 认为“任何不是真正译本的东西就是拟作、 改编或者拙劣的模仿作品”[2]77。 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曾提出包括拟作在内的翻译三分法, 但他本人却建议避免采用拟作, 认为拟作把源文本当作“写作的模版, 假设原作者生活在译者自己的时代和国度”, 虽凸显了译者自己, 却“万分愧对已故作者的印象和声誉”。[3]25
毕竟传统翻译基于书面文本, 严格限制了改编的用途, 使之仅用于诗歌、 戏剧和部分文学作品。 随后, 翻译跨越了语言的界限, 扩展到视听和多媒体领域, 对改编的理解和应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译界越来越接受改编译法。 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重新审视改编译法, 探讨在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 简称AVT)这一新兴领域, 改编与视听翻译的关系, 以及视听翻译的一些常见模式中改编的具体表现和应用。
1 改编与翻译
改编虽为译界常用概念, 却很少有清楚明了的定义, 原因之一, “改编”与“翻译”概念共生, 而“翻译”概念本身的定义就五花八门; 再者, 二者之间的界限为译界长期争论的焦点。 对于改编否属于翻译这个问题, 译界学者各持己见。 笔者认为, 改编是属于翻译的一种类型, 即使从传统的翻译概念角度看, 这点也能得到印证。
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较早把改编归入翻译的学者。 他曾指出, 翻译的中心问题是:翻得直白些, 还是自由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宽泛的翻译概念, 不仅包含这两个极端, 还涵盖了二者之间的各种书面翻译类型, 采用了一个V形平面图来说明侧重点和自由度不同的各种翻译形式[4]45, 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种翻译形式
纽马克认为, 改编(黑体标出)是侧重目标语的“最自由”的翻译形式, 主要用于戏剧和诗歌, 尤其是喜剧, 通常保留主题、 角色和情节, 但将源语文化转换为译入语文化, 同时改写文本。[4]46西班牙维克大学教授玛丽亚·戴维斯(Maria González Davies)也曾给改编下定义, 认为改编是“一种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具有松散对等的面向用户的翻译, 包含了源文本文化和目标文本文化间的转变(常出现在戏剧和诗歌的翻译中)”[5]227。 二人对改编的理解有共识, 从中可以归纳出改编的特征, 如表 1 所示。

表 1 改编的特征
在此框架下, 改编与翻译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McGuire)就反对区分戏剧翻译是“翻译版”, 还是“改编版”, 或是“大杂烩”, 认为这样的讨论毫无成效, 是“误区”。 她指出:“源语文本的‘翻译版’和‘改编版’之间的区别, 在我看来完全是误区。 应该抛开这些误导人的词汇了。”[6]93
另一些学者从功能角度出发, 也把改编纳入翻译的范畴。 德国翻译家诺德(Christiane Nord)甚至主张弃用“改编”这个词, 认为“翻译”概念可以包容所有转换或者干预的类型, 甚至预期的目标文本功能与源文本功能是否相同并不重要, 只要“目标文本效果与预期的目标文本功能一致”[7]93。 改编代表了某种转换和干预, 只要满足这一条件, 就属于翻译的范畴。
图里(Gideon Toury)曾给出最广泛的翻译定义: “译本即被接受为译本之物。”[8]156此定义包罗万象, 容纳了改编和其他传统上排除在翻译之外的现象。 为显示翻译与改编密不可分, 来自魁北克的诗人兼译者米歇尔·加诺(Michel Garneau)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tradaptation”(译编)。[1]5
2 改编与视听翻译
2.1 视听翻译的范畴
视听翻译是翻译研究的新类别, 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把翻译的疆界扩展到视听范畴, 为翻译研究揭开了新篇章。 视听翻译本身也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 从最初的影视翻译(Film and TV Translation)到屏幕翻译(Screen Translation), 随后到视听翻译, 再发展到多媒体翻译(Multimedia Translation)。[9]
早期的影视翻译涉及电影和电视, 之后屏幕翻译还包括录像、 光盘、 DVD这些可以在屏幕上放映的产品。 视听翻译则超出了屏幕媒介的限制, 采用视听元素相结合的二维传播模式, 包括了芬兰学者甘比尔(Yves Gambier)所归纳的媒体中多语种转换类型:电影字幕、 同声字幕、 多语种字幕、 配音、 口译、 话语覆盖、 同声传译以及歌剧的唱词字幕等。[10]162视听翻译把戏剧和歌剧的字幕翻译纳入其中, 而屏幕翻译通常把二者排除在外。[11]124到目前为止, 视听翻译仍是这个新兴领域最通用的称呼, 最广义的定义为:
对用任一媒体(或格式)来制作的节目(或后期制作)进行的所有翻译形式(或多符号转换), 还包括媒体普及这个新研究领域, 即为耳聋和有听觉障碍的人提供的字幕翻译, 以及为盲人和有视觉障碍的人进行的有声描述。[12]ⅷ
除此之外, 多媒体翻译源自传递信息所通过的众多媒介和渠道, 主要涉及信息与交际技术产品(ICT)的本土化、 互联网产品的翻译, 如软件和游戏的本土化、 业余爱好者组织的字幕组(Fansub)和配音组(Fandub)、 网络动画(Webtoons)等。
2.2 视听翻译的本质
无论从翻译的对象和内容, 还是技术上, 视听翻译都到达了翻译的边界, 是最自由的翻译形式, 其本质是改编。
2.2.1 视听翻译的新文本类型
传统翻译概念指出, “翻译是将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13]23。 视听翻译从对象和内容方面拓展了“文本”的概念, 超越了语言符号的范畴。
首先, 视听翻译的文本(Audiovisual Text)融合了视听元素, 是一种新文本类型。 早期翻译研究均针对书面文本, 视听翻译则扩大了“文本”的疆界, 将其从文字元素扩展到非文字元素, 涉及不同的符号系统, 结合了视觉和听觉两个渠道。 视听文本有四大构成元素:
1) 听觉-非文字元素:如乐曲、 音效、 音类;
2) 听觉-文字元素:如对白、 独白、 歌词;
3) 视觉-非文字元素:如图像、 照片、 身势;
4) 视觉-文字元素:如插页、 标语、 信件、 电脑屏幕上的信息、 报纸的标题。[14]2-3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也提出了类似的依赖非文字元素的四种文本:多媒介文本(Multimedial Text)、 多模式文本(Multimodal Text)、 多符号文本(Multisemiotic Text)和听觉媒介文本(Audiomedial Text), 包括了影视、 戏剧、 连环漫画、 政治演说等的翻译。[8]85在多媒体翻译中, 文本中还添加了三维的超文本构架和交互性特征。
其次, 视听翻译超越了语言符号的范畴, 包含了文字和非文字元素、 不同的图示符号系统和代码, 这意味着不仅要翻译文字, 也要“翻译”图像等, 语言的作用取决于文本的用途。 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翻译三分法来看, 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是“用另一种语言来解释某种语言符号”, 而视听翻译讨论的现象超越了语际翻译范畴, 属于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变形(Transmutation), 即“用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15]114。 如斯内尔·霍恩比所说, 符际翻译是多媒介和多模式转换中的构成元素, 包括了电脑软件的本土化、 戏剧和影视翻译。[8]20-21
综上所述, 视听翻译拓展了书面文本, 融合了视听元素, 包含语言符号、 图示符号系统、 代码、 图像、 音效等等, 形成了自成一派的视听文本。 这些使视听翻译超越了严格意义上“将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概念。 如果以广义的翻译概念而论, 无论是文本还是语言, 视听翻译皆处于翻译概念最边缘最自由的位置, 一般归入改编的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视听翻译的本质是改编,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因此, 视听翻译有时也被称为“视听改编”(Audiovisual Versioning)。
2.2.2 技术的限制
比利时学者拉米尔(Aline Remael)曾指出, 某个文本中, 哪种模式支配其他模式, 或者要达到何种平衡, 取决于符号编写者的目的和背景, 也取决于该文本如何使用, 在何处用, 通过何种媒介方式来用。[16]15由于有符号和媒介等方面的要求, 视听翻译受到技术的限制,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视听翻译的改编性质。 以视听翻译的模式之一——歌剧字幕翻译(Surtitling)为例, 音乐对文本有限制作用, 音乐不能变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用的语言, 所以歌剧字幕翻译必须改编歌剧剧本, 以满足现场表演的需要。
在视听翻译模式中, 配音(Dubbing)是采用改编最多的模式。 技术方面, 配音主要受“同步”(Synchrony)所限,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口型”(Lip-sync)。[17]3“同步”要求完成翻译的连续镜头必须与原话序列的时长相等, 而且在显示演员脸部时, 对白要与任何可见的嘴唇动作一致。 如果声画不同步, 观众必然难以适应。 所以, 为了让对白能对上口型, 改编的幅度很大, 配音团队对语言、 文化、 技术的细枝末节都要力求完美。
再者, 由于配音的性质和观众的局限性, 也允许配音具有较高的改编程度。 从本质上说, 配音是一种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 隐性翻译指在译文中再现源文本的文本目的, 通过生成与源文本功能对等的文本, 来隐藏其翻译文本的本质。[18]188配音版的声音替代了原版影片中演员的声音, 配音版的对白口型与原版的也一致, 这样一来, 目标观众误以为屏幕上的演员和自己说同种语言, 以为译文就是原文。 由于观众听不到原声, 无法判断配音版与原版在语义内容上是否一致, 即使二者差别很大, 只要口型一致, 观众也很难觉察, 所以配音一般不会因改编幅度大而遭受非议。 如上所述, 视听翻译受到技术的限制,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改编为视听翻译之必然, 而非单纯将一种语言直接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3 改编在视听翻译中的表现
视听翻译在本质上属于改编, 这种改编译法具体表现在作为视听翻译的步骤和技巧这两个方面。
3.1 改编作为视听翻译的步骤
鉴于视听翻译的特殊性, 以及受到的语言和技术限制, 改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步骤, 应用于诸多视听翻译模式中, 如电影字幕、 配音、 话语覆盖以及歌剧的唱词字幕等。 以歌剧为例, 为了现场表演, 歌剧字幕翻译必须先改编歌剧剧本。 与之类似, 考虑到字幕在屏幕上的显示时长要与镜头的转换一致, 字幕翻译也时常进行改编。 其中, 配音是采用改编步骤最为显著的模式。 比起其他模式, 配音更加耗时, 主要原因是语言改编过程费时。 例如, 与配音相比, 话语覆盖(Voice-over)相当迅速, 不需要演员来扮演各个受访者的角色; 字幕翻译也比较迅速, 若是新闻报道, 字幕翻译可以在新闻开始前几分钟进行, 若是影视剧, 如一部美国连续剧发往欧洲, 完成字幕翻译到播出仅需几个小时。 反观配音, 仅语言改编就要花上几周时间, 还牵涉大量人员, 既要改编对白, 还要为配音演员预留时间, 演练角色, 录音也需要时间。[19]95
相比其他视听翻译模式, 配音的改编程度最高, 改编过程最复杂, 是“一个根据文化、 语言和技术的限制对本土化的剧本进行改编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20]53。 此处以配音为例, 说明其改编的步骤。 法国雷恩大学教授葛岱克(Daniel Gouadec)列出配音的二十八个详细步骤, 从发行商购买外语版的制作版权、 招聘配音主管或配音导演开始, 一直到制作最终拷贝为止, 纵观整个过程, 改编如影随形, 出现在多个步骤中。[20]50-53
首先, 配音导演组建团队, 要求在文本检查、 改编、 转写、 演员日程安排、 录音、 混音等阶段, 各配备一名专家。 整个配音团队包括:配音经理、 译者、 改编者、 录音师、 演员和其他人员。 这说明早在组建团队时, 就考虑到改编和所需要的专业人士。
改编阶段的具体步骤如下: ① 接收材料。 配音导演收到剧本, 但这个剧本是由“普通”译者翻译, 没有考虑同步, 只忠实地翻译原作, 是个粗略的直译版本, 并非配音版, 只负责为后者提供原材料。 ② 改编译本。 配音团队对该译本进行改编, 以满足电影情景和同步的要求, 再转换成口型一致的对白。 对口型时, 口音和讲话节奏、 目标语言和语言行为的特色, 都要与原版中肢体语言和表述一致。 改编者与译者时常碰面, 审阅译文和改编文本, 大声朗读译文和对白, 还要反复检查、 修改, 直到对白自然, 与动作和角色完美契合。
即使到录音阶段, 也在进行改编。 一部影片角色众多, 对白更是数量庞大, 因此录音部分工作复杂。 配音演员边观看原版, 边录制对白, 效果满意就切换到下一个镜头, 如果不满意, 录音经理就要指导配音演员, 甚至修改对白, 重新录制, 直至效果满意。 这个改编过程一直持续到完成最终拷贝。 改编这个步骤也出现在其他视听翻译模式中, 只不过程度各有不同, 而配音不仅程度最高, 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视听翻译模式。
3.2 改编作为视听翻译的技巧
3.2.1 改编的技巧
改编可以作为一种局部翻译技巧, 主要针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在语言或文化方面的差异, 尤其是情景或文化方面的不恰当之处。 维奈(Jean-Paul Vinay)和达贝尔内(Jean Darbelnet)曾对这种改编技巧有过论述, 列举了七种翻译方法, 其中改编译法“达到了翻译的极限”。
源语中提到某些情景类型, 而在目标语文化中比较陌生, 改编便用在这种情况。 译者必须创造出对等的新情景。 因此改编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对等, 一种情景对等。[15]90
如果原文提到的背景或者源语文化的某种情景在目标文化中不存在或不合适, 改编要求根据目标文化习俗调整内容, 进行某种形式的再创造, 变更文化参照物, 毕竟源语观众熟悉的东西, 对于目标观众可能不知所云。 有一个经典的同声传译例子:某个情景提到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运动, 口译员把英文的“板球运动”译成法语的“环法自行车比赛”, 二者的文化内涵相同, 皆为各自国家的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运动, 只是文化参照物不同。[15]90维奈和达贝尔内所列的七种译法在视听翻译中也适用, 只是改编译法的重要性更突出, 尤其在配音中。
与此类似, 波兰翻译学教授汤玛斯格威奇(T. Tomaszkiewicz)特别针对电影字幕翻译提出了包括改编在内的八种翻译策略, 即省略、 直译、 借译、 对等、 改编、 用指示词替代文化词汇、 概括、 明晰化。[21]45这些翻译策略可以用于视听翻译的不同模式, 但不同模式对各策略的偏重不同, 可能好几种策略同时起作用。 改编策略要求调整译文, 使之符合目标语言文化, 产生与原作相似的内涵意义和功能, 也可看作是某种形式的对等。
仅就改编策略而言, 巴斯丁(Georges Bastin)归纳出七个改编步骤:
1) 转写原文:用原文的语言重新改写部分原文, 通常附带一个直译本。
2) 省略:删掉部分文本或使之含糊些。
3) 扩展:无论正文或前言、 脚注或术语表中, 添加原信息或使其更清楚明了。
对两组患者关节病变数、超声表现行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25.0,关节病变数、超声表现为计数资料,用%表示,行χ2检验,以P<0.05为统计检验标准。
4) 替代异国情调:用目标语的大致对等物来替代原文中的俚语、 方言、 无意义的词等(有时以斜体或下划线标注)。
5) 更新:用现代的对等物来替代过时或者含糊的信息。
6) 使情景或文化恰当:放弃原作的背景, 重新创造目标读者更熟悉或在文化上更合适的背景。
7) 创新:用新文本全面替代原文本, 只保留原作必要信息、 观点或者功能。[1]4-5
以上步骤根据具体的视听模式、 翻译目的和会话场景各有取舍, 其中替代异国情调、 更新、 使情景或文化恰当这几个步骤与文化息息相关, 经常使用, 例如汤玛斯格威奇讨论的就是特有的文化词汇的翻译。
3.2.2 改编技巧的应用
视听翻译的两种主要模式为字幕翻译和配音, 二者各有特征, 所受限制不同, 如翻译时限、 媒介的制约、 两种语言同时出现与否、 翻译目的等。[23]81因此, 二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 但同样面临文化因素问题, 与每种语言文化特有的符号代码相关, 所以皆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改编技巧, 对这些特有符号代码的指示意义和内涵意义进行适当改编, 以满足各自目标观众的需要。 现以配音与字幕翻译为例, 说明改编技巧的应用。
例 1

英语原版法语字幕版法语配音版Theslumberpartyisover.(留宿晚会已经结束。)Lapartiederonfletteestfinie.(打瞌睡时间已经结束。)Lapartiederonfletteestterminée.(打瞌睡时间已经到头了。)
影片故事围绕几个人物的生活展开, 他们因纽约布鲁克林街头的一家小烟店而结缘, 探讨了复杂的人生故事和人伦亲情的可贵。 影片中, 失意作家保罗对朋友拉希德说了以上这句话。 原版中, “slumber party”是英语的文化符号, 原指“留宿晚会”, 即专为十几岁女孩举行、 在主人家过夜的晚会。 法语文化中并没有这种活动, 因此, 配字幕和配音的法语版都采用了改编法, 出现了“la partie de ronflette”这个法语词, 意即“打鼾的时候”或者“打瞌睡时间”。 保罗借此唤醒拉希德, 同时也表达了微妙的打趣之意。 此处用目标语中的大致对等物来替代原文, 在文化上更加恰当。
例 2 选自1994年的美国影片《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在西班牙语配音版中也采用了改编法来处理一些文化参照物[22]79-80:
例 2

英语原版西班牙语配音版FamousereventhanCaptainKangaroo.(甚至比袋鼠船长还出名)MásfamosoinclusoquePino⁃cho.(甚至比匹诺曹还出名)
影片描述了有些智障却极赋奔跑天分的主人公阿甘一生中的几段时期, 他见证甚至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的重大事件。 影片中, 阿甘谈到自己的时候, 说自己甚至比袋鼠船长(Captain Kangaroo)还出名。CaptainKangaroo(《袋鼠船长》)是美国放映时间最长(约30年)、 全国联播的儿童电视节目, 主人公被称为“袋鼠”, 得名于外衣上有个大口袋。 如果在西班牙语中保留这个形象, 观众会迷惑不解, 毕竟此社会文化典故仅限于美国文化, 而西班牙观众看不到背后的文化符号, 也体会不到其中蕴含的幽默。 因此, 西班牙语配音版采用了改编法, 用《木偶奇遇记》的“匹诺曹”(Pinocho)来替代, 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观众理解毫不费劲, 同时也保留了阿甘将自身名望与一个儿童角色相提并论所带来的幽默。 这种译法改变了原版的文化参照物, 而新的文化参照物更为观众所熟悉。
再以2012年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3》(Madagascar 3: Europe’s Most Wanted)为例, 说明字幕翻译中的改编, 该片由长影译制中文字幕:
例 3

英语原版中文字幕版Isayweletitride.Thenwe’llpickupthehippiesAndflybacktoNewYorkinstyle.继续下注没商量去接动物团的星哥星姐回纽约
故事讲述四个动物伙伴逃出非洲后, 历经艰险回到纽约的故事。 剧中, 打算施以援手的企鹅如此说道。 英文“hippies”指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 一群年轻人过着公社式的流浪生活, 穿着前卫, 反抗习俗、 传统价值观和当时的政治(民族主义和越南战争)。 这个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出现的人群, 是个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 即使在字幕中大费周章地解释其时代背景和符号意义, 国内观众也未必能理解。 考虑到该词仅仅指那四个想回纽约的动物伙伴, 同时也透露出企鹅的不屑和嘲讽之意, 中文字幕采用了改编, 用“动物团的星哥星姐”来替代“嬉皮士”这个概念, 同时也传达了“时髦、 成功”(in style)的意思, 由此联想到明星出场, 大摇大摆, 风光无限。
视听翻译中, 改编技巧的使用主要涉及文化参照物。 民族间的习俗传统各不相同, 某些文化符号为一种文化特有, 并不存在于另一种文化, 或者同一词在两种文化中意思截然不同, 也有可能同一习语在说同种语言的不同国家内涵意义不同, 诸如此类的情况都适合采用改编译法, 在视听翻译中频频使用。
4 结 语
相较其他翻译领域, 改编在视听翻译中应用甚广。 近年来, 国内的视听翻译领域, 尤其是电影的字幕翻译和配音, 改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频频出现改编过度的情形, 饱受争议。 改编并非可以随心所欲, 也受到某些限制, 如目标读者的知识和预期; 目标语的限制, 即必须在目标语范围内寻找能匹配源文本的语篇类型, 探索改编模式的连贯性; 源文本的限制, 即为潜在的观众着想, 考虑源文本应该包含多少新信息和共享信息, 必须评估这个度; 最后还要受到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意义和目的的限制。[1]5
国内电影市场繁荣, 视听翻译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十年前, 我国著名影视翻译家钱绍昌教授就预见, 影视翻译将在国内蓬勃发展, 指出“如今译制片受众(观众)的数量远远超过翻译文学作品受众(读者)的数量, 影视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也决不在文学翻译之下”[22]。 如今预言已然成真, 2012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再创新高, 达到170.73亿元, 同年中美电影新政实施, 美国进口大片增加14部。[23]此新形势下, 视听翻译面临更大的压力, 必须应对一系列问题, 如电影的字幕翻译和配音应该采用什么标准、 改编到什么程度合适等, 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也迫切需要解决。
[1]Baker M, Saldanha G.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4]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5]González Davies M. Multiple Voices in the Translation Classroom: Activities, Tasks and Project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6]Hermans T.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 Croom Helm, 1985.
[7]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8]Snell-Hornby M.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9]刘大燕. 析AVT名称演变:从电影翻译到多媒体翻译[J].上海翻译, 2010(4): 61-65.
[10]Duarte J F, Rosa A A.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6.
[11]Karamitroglou F.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 Choice between Subtitling and Revoicing in Greece[M]. Amsterdam: Rodopi B.V., 2000.
[12]Orero P. Topic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13]Kuhiwczak P, Littau K.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14]Chiaro D, Heiss C. Between Text and Image: Updating research in screen transla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15]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6]Remael A. (Multi) Media Translation: Concepts, Practices, and Research[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17]Whitman-Linsen C. Through the Dubbing Glass: The Synchronization of American Motion Pictures into German, French and Spanish[M].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2.
[18]House J, Blum-Kulka 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6.
[19]Díaz-Cintas J, Anderman G.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Language Transfer on Screen[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0]Gouadec D.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21]Díaz-Cintas J. New Trend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9.
[22]钱绍昌.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中国翻译, 2000 (1): 61-65.
[23]中国电影票房2012年收获170亿 十年增长18.5倍领跑世界[EB/OL]. 2013-01-09[2016-04-18]. http: ∥finance.cnr.cn/gundong/201301/t20130109_511746139.shtml. Retrieved January 29, 2013.
On Adaptation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LIU Da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daptation is the freest form of translation, on the border of which adaptation resid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aptation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VT), and the use of adaptation in AVT. It firs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aptation and translation. It then ident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VT and pinpoints its nature as adaptation rather than translation proper, with its crossing over the boundaries of verbal texts and verbal languages, and the restriction of technology and media. In AVT, adaptation is exhibited both as a translation procedure and a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applied in some major AVT modes, such as dubbing, subtitling, surtitling, etc.
adaptatio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udiovisual text; dubbing; subtitling
1673-1646(2017)01-0069-07
2016-09-23
刘大燕(1974-), 女, 副教授, 硕士, 从事专业: 英语教学。
H059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