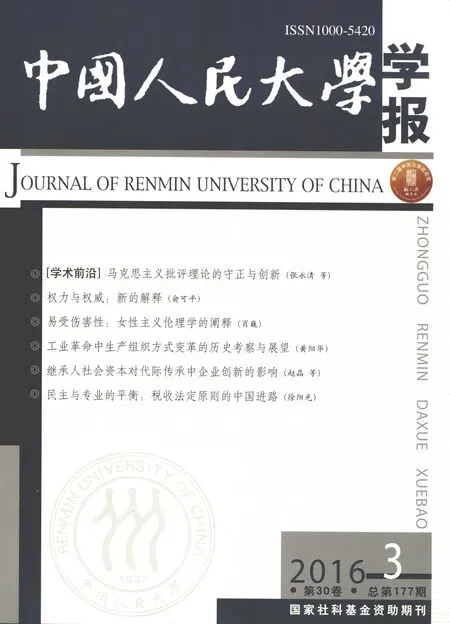工业革命中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历史考察与展望
——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分析
黄阳华
工业革命中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历史考察与展望
——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分析
黄阳华
对当前新一轮产业变革可以按照技术经济范式核心组件协同演化的框架加以剖析。新一轮产业变革可能是第六次技术经济范式(也即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导入期,将在如下方面发生“革命”:数据要素将成为新型核心投入,以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超过交通基础设施,以数据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驱动的制造业智能化将引领国民体系的智能化;最终,大规模生产也将受到严峻挑战,大规模定制化和社会化制造等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将兴起。为此,我们必须从技术经济范式的视角认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进程。在此背景下,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不仅要如《中国制造2025》那样重视装备工业的高端化,更需要重视制造业各环节数据要素的利用和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配套升级,增强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
工业革命;技术经济范式;长波;生产组织方式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使得经济首次实现了持续增长,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也得以改弦易辙。机器、能源和材料的推陈出新及广泛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史无前例的增长,与人均收入、人口总量、知识、投资及技术创新形成了正反馈机制,助力人类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1](P259-260)。诚然,一系列重大发明的产业化是促成这一切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技术进步就只能是一种“潜力”,伴随技术创新扩散过程而渐次出现的经济社会巨变也仅是一种可能性。本文试图在微观层面上从工业发展史中归纳出历次重大技术变革中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规律,并以这种“理性化的历史”为启发式,展望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特点与趋势。
本文将在演化经济学经典的技术经济范式分析框架下,剖析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初现端倪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核心构件的演进,力图在如下三个方面拓展既有研究:一是在演化经济学家已有工业革命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当代现实变化,并根据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最新进展对他们过去做出的预测加以必要的校正。二是推动现有关于新一轮产业变革的研究从现象描述向结构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转变,以更好地把握这场变革的核心节点,为制定和优化产业政策提供扎实的理论指导。三是重视微观层面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推动当前以宏观战略和产业分析为主的新工业革命研究深入至微观层面,为更好地认识和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本文的分析结构如下:第一节对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浪潮进行历史考察,重申演化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技术浪潮”、“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和“技术经济范式”等概念的界定,并主张以创新及其扩散作为工业革命分析框架的核心,指导后文对技术经济范式演进的研究。第二节对历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进行细致梳理,说明历史上典型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形态所构成的特定情境相匹配,其基本功能是有效提升生产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组织的制度成本。基于上述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第三节展望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技术经济范式各核心构件的演进,特别关注演进过程更漫长、更复杂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增进我们对新一轮产业变革的理解。第四部分以一些政策性评论对全文进行总结。
一、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浪潮的历史考察
相比于历史学家常用“工业革命”概念,深受熊彼特创新理论影响的演化经济学家更青睐“技术浪潮”这一概念。在传统工业革命史研究中,技术虽然居于重要地位,但是技术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却常被视为是外生的和线性的。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工业革命史更为复杂。
第一,重大技术演进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如果仅仅将技术作为外生冲击,那么对工业革命的解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这也是以新政治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在解释工业革命时面对的主要批评。例如,图洛克(G. Tullock)认为,英国大刀阔斧地削减特许专营数量、废除限制性制度,从而提高了寻租成本,引导人们从寻租活动转向生产活动,这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主要原因。[2]阿西莫格鲁(D. Acem ̄oglu)等指出,1500—1850年大西洋贸易孕育了对私有产权保护怀有强烈诉求的新兴商业阶层,它们以多种方式限制了王室权力侵犯私有财产,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制度基础。[3]我们认为,这些研究过于强调制度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以至于忽视了技术创新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故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其他私有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时代(或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第二,技术创新对产业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如果机械地认为技术突破将自发地导致工业革命,那就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演化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发明必须经成功的商业化才能成为创新,才能引发产业、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变化。这个过程极为漫长、复杂且不确定,应成为工业革命史研究的重点。创新可分为非连续的激进创新和既定技术路线上的渐进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引爆“工业革命”的是激进创新还是渐进式改进呢?对此,弗里曼(C.Freeman)和卢桑(S.Louçã)认为,激进创新带来了通用技术的更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跨越式增长。[4](P140)因此,在工业化历史长河中发现里程碑式的激进创新,成为研究工业革命的切入点。
第三,研究创新及其扩散的历史甚至比技术史更为重要。激进创新通常是在某些先导产业率先出现后向其他产业扩散,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效应是多种形式的,如提供关键原材料和通用装备,或者改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因此,聚焦先导产业的成长有助于深入揭示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在给定技术机会的前提下,先导产业的发展受制于三个因素,即核心要素的可得、基础设施的支撑和经济组织的支撑。先导产业与这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技术经济范式的核心构件。可见,管理与组织变革贯穿于历次长波当中[5],以至于钱德勒(A. Chandler)以“组织能力”所处的制度环境、组织能力的构建和扩散分析历次工业革命中典型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提出“组织能力即为核心能力”这一著名命题[6](P594)。
综上,在注重过程分析的演化经济学家看来,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可用图1表示。首先,从技术突破到非均衡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漫长、复杂但层次清晰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创新的发生及其扩散居于核心地位,先导产业是激进创新的载体。其次,激进创新的扩散需要与核心投入、基础设施和生产组织协同演化,促进先导产业部门的成长。再次,先导产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产业关联和示范效应,带动产业体系发生显著变化。整个过程也被称为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

图1 以创新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家借助该分析框架,运用翔实的史料,不仅全景式地分析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演化史,而且还精巧地将历次激进创新浪潮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相匹配(见表1),赋予创新浪潮更丰富的经济学意义。[7]在技术层面看似跳跃的工业革命在经济层面却是连续展开的,“革命”一词虽然突显了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但模糊了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过程的连续性。因此,弗里曼和卢桑主张使用“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来反映波澜壮阔的产业演进过程。相应地,他们提出18世纪中期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的工业机械化,实质是第一、第二次创新浪潮的演进过程,19世纪第三、第四次创新浪潮则实现了以工业自动化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依照上述理论分析框架和历史过程研究,有学者推断,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是第五、第六次创新浪潮的涌现与拓展过程。[8]当前被热切关注的新一轮产业变革极可能是第六次创新浪潮,应该按照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加以系统化的深入研究。

表1 技术创新浪潮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
二、前五次长波中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生产组织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为“制造业的机械化革命”,由第一次和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组成。在这两次长波中形成的典型生产组织方式是工厂制和技工承包制。
1.第一次长波与工厂制度的形成
棉纺织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在工业革命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纺织机械的技术进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棉花加工效率从1780年的1磅/小时提高至1830年的14.3磅/小时,单个工人在一个童工的配合下可同时操作4台动力织布机,生产效率相当于20名手织工。[9]铁是轧棉机的主要原料,铁的成本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轧棉机的成本。所以,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铁成为制约先进生产工艺大规模推广的瓶颈。18世纪焦炭炼铁法和科特搅炼法两项关键炼铁技术的突破,使得铁能够廉价供给,促进了以蒸汽机和轧棉机为代表的机械装备的广泛采用,工业革命步入快车道。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引致了煤炭需求,采煤业引入蒸汽机后生产效率得以提升,煤炭价格下降又降低了蒸汽机的使用成本。因此,受棉纺织业刺激而发展起来的铁和煤成为工业革命的核心投入要素,不仅极大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机械化,而且还推动运输力从水力转变为蒸汽动力。
1890年前后,纺纱业经历了从分包制到工厂制的转变。一方面,传统生产工艺下纺纱业劳动密集程度高,早期企业不具备雇佣、培训和监督工人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不适应工厂的工作制度,不愿意进入工厂工作。按照经典的企业理论[10],企业主倾向于采用市场交易的方式,将纺纱外包给纺纱工(即“外包制”),降低企业招聘、培训和监督工人的成本。随着企业增加专用性固定资产投资,外包会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发展规模经济。18世纪90年代,工厂制凭借资本集中、企业内部分工、再生产和分销网络的优势及严格的劳动纪律,成为纺纱业的主流生产组织方式。诸多行业纷纷效仿。蒸汽动力代替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为工厂的选址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也促进了工厂制的流行。早期工厂内部管理分工尚不发达,限制了工厂规模的扩张,随后出现的合伙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限制。
2.第二次长波与技工承包制
瓦特改良的双动式蒸汽机虽然大幅度提升了功率,但由于成本高昂,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取得商业成功。直到以下两个条件具备后,瓦特蒸汽机才被广泛采用:一是机器、铁、煤被广泛应用,特别是机床的出现降低了蒸汽机的成本;二是铁路网的扩张拉动了蒸汽机车制造、铁路车辆和铁路装备产业的成长。机床作为通用装备可被广泛应用至其他产业,形成了“铁—煤—蒸汽机—铁路装备—精密机床”之间的协同效应,既提高了工业生产率,也促进了工业革命向更广阔地区(特别是欧洲大陆)传播。首先,工厂增加机器和专用设备种类后,专用性投资随之提高,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工厂组织的制度成本也不断上涨。为此,工厂内部兴起了技术工人承包制(即“内包制”),即将生产责任发包下放至技术工人或领班,由他们组织工人生产和管理机器。[11]这一时期的分包制是在工厂内部分包(“内包制”),而18世纪90年代以前则是“外包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包制与工厂制的结合。相比于工厂制,技术工人承包制增加了生产的科层,形成了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降低了监管成本。相比于外包制,工厂可以实行指令管理,节约了交易成本。技术工人承包制持续了约1个世纪,促进了英国产业工人积累专业技能,提升了行业合作精神和技术工人的责任感,塑造了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其次,铁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产生了示范效应。[12](P79)今天高效企业所具备的属性很多源于铁路运营和扩张(特别是长距离运输)的实践,例如守时、前向服务规划、惯例化检修、控制关键供应商、及时配送、总部管控、分段运营形成的科层制、层次分明的职责体系,乃至围绕铁路建设运行创新投融资体系(如股份制)等。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生产组织变革
第二次工业革命被称之为“制造业的电气化革命”,由第三次和第四次长波组成,依次形成了泰勒制和福特制两种典型的生产组织方式。
1.第三次长波与泰勒制的诞生
电力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意义堪比铁和煤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电枢、交流发电机、转子等发电设备的核心部件得以突破后,一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大规模发电和输变电。电力作为一种新兴工业品,初始市场是有轨电车和城市电气轨道交通,在推广过程中涉及昂贵的设备、先进的技术、复杂的保养、繁琐的会计核算及各类协调工作。过去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分的马车市政管理机构难以胜任电气化交通的管理任务,受薪职业经理人阶层应运而生[13](P226),对工厂制形成了较大冲击。电力通过改善工作环境和优化工业流程重塑了工业生产组织方式。[14](P187)在使用电力之前,生产线依靠多台蒸汽机协作提供动力,任一蒸汽机故障都会影响整条生产线的运转。经电气化改造后,生产流程变得简洁、稳定、灵活,电网扩张也提高了工厂选址的灵活度。电力还改变了机械装备的设计、制造和操作,优化了生产流程。在这些创新的驱动下,不仅工业生产效率快速增长,而且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5](P185)
在制造业电气化浪潮的推动下,一批新兴产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快速发展,并且产生了极强的溢出效应。钢材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且可被有效压缩,价格下降空间大,以钢为原材料的中间产品创新提升了下游产业的效率,形成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相互促进的“内生增长模式”。[16]在交通运输方面,工程性能更优的钢轨替代了铁轨。铜是理想的导电材料,电解铜技术降低了铜价,廉价铜线压低了输电成本和电价,又反过来降低了铜的成本,形成“铜材—输变电—电价”的正反馈效应。这个时期,蒸汽船、铁路得到长足发展,电话电报和打字机促进了生产和分销的快速扩张,全球市场一体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早期的国际产业分工网络,工业领域内出现了最早的跨国公司,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了新的形式。一是小工厂演变成对产业和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企业[17],对传统的企业治理结构提出新挑战。二是产品复杂度不断提高,生产流程的持续延长和技术知识的快速增长提高了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急剧上升。三是技术工人难以掌握全部生产知识,职业经理人管控模式逐渐形成。四是企业主和管理者不分的私人企业演变为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被后世称为“管理革命”。[18]企业管理的职业化、专业化促进了成本会计、生产流程控制、营销等发展成为专业技能,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人力资源、公共关系、信息、市场研究等管理活动也逐渐专业化。以专业管理团队为基础的“泰勒制”发展起来,企业管理逐渐从车间上移至管理团队。[19]专业管理团队的分工协作也增强了企业的动态能力,多元化战略逐渐流行。
2.第四次长波与福特制的形成
福特制的建立标志着制造业进入了自动化阶段,被视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制造业自动化可上溯至19世纪末的“美国制造体系”。[20]“美国制造体系”脱胎于美国军工产业,基本特征是产品(武器)标准化,可互换零部件和采用大功率生产设备。这种基于标准化制造的理念不仅提高了军工产业的生产效率,而且衍生了庞大的制造体系,成为美国工业化重要的推进器。这一时期,以新型机床为代表的装备工业大发展强化了以高效率、标准化、可互换性为特征的“美国制造体系”,为推广流水线奠定了产业基础,并最终使其成为第四次长波的典型组织方式,推动了国民经济从电气化向自动化跃升。在本次长波中,产业结构的突出特征是耐用消费品制造业成为先导部门,需求因素超过供给因素成为拉动产业成长的首要驱动力。首先,1929年“大萧条”抑制了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激化,全球笼罩着战争阴霾。铁路投送军队不再适应机动化作战的需要,军事列强纷纷加快了摩托化和机械化的进程。巨大的军事需求刺激了汽车、卡车、坦克和航空器的增长。其次,汽车、卡车和拖拉机等耐用消费品虽颇受民用市场青睐,但居高不下的生产和使用成本抑制了需求。在福特“T型车”之前,主流的生产方式是用户直接向汽车制造商“定制”汽车,虽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缺乏规模经济,汽车价格昂贵,交付周期较长,汽车是富人标榜社会地位的炫耀性商品。福特“T型车”实现了从定制生产到标准化生产的转变,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生产成本。以伯顿裂化炼油工艺和胡德利催化裂化工艺为代表的炼化技术进步降低了汽油的价格,加油站和公路网的拓展降低了汽车使用成本。
福特制利用标准化生产打破了工人技能对产量的限制,上下游工序流程再造形成了流水线,专业化分工提高了各工序的生产效率,标准化零部件生产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提高了工资水平与消费能力,金钱外部性又刺激了对其他产品的市场需求。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后,企业的主要竞争策略有二:一是产品多样化策略。设立不同的产品线,开拓细分市场并差异化定价。采取这种策略的企业规模也会随之扩大,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二是成本控制策略。实施福特制的必要条件是零部件的标准化和及时供应,供应链和车间管理效率对福特制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该策略的成功案例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采取的精益生产方式(即“丰田制”)。[21]
总之,在第三次和第四次长波构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不仅涌现了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新兴产业,产生了复杂耐用消费品和高效率的长流程生产工艺,新材料、新能源被广泛应用,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具有更强的网络效应,而且为了提高对复杂度日益增加的生产的管理效率,企业管理现代化也快速推进,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制)等代表性生产组织方式相继建立起来,主宰工业生产组织方式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三)第五次长波与生产组织变革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信息化时代可以被视作第五次长波。在这次长波中,电子芯片扮演了核心投入的角色。自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块集成电路板诞生后,电子产品日趋小型化、高精度、高稳定、高能效和智能化。与前四次长波类似,核心投入产品的供给速度决定了先导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水平。“摩尔定律”很好地归纳了电子芯片技术的演变特征,即每隔1~2年芯片容量就会翻倍,电子芯片的性价比不断提高,加快了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速度。
计算机的出现对工业的影响极为深刻。20世纪中期,机床植入了计算机系统后形成了数控机床的雏形,逐渐发展出工业控制系统,促进了工业设计、控制和编程的持续改进。1972年英特尔处理器大幅降低了计算机的成本,计算机同时在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制造业信息化促进了自动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出现了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的“柔性制造系统”(FMS)。建立在标准化之上的大规模生产减少了产品种类以追求规模经济,但是数控机床出现后,厂商可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分门别类,减少生产设备的调整,缩短生产延时,生产出不同批次的差异化产品。柔性生产方式对企业竞争策略具有显著的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纷纷着手构建FMS。得益于计算机芯片、传感数控机床、软件工程、目标导向数据库、可视化工具和数控检测设备的改进,FMS不断更新换代,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灵活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风行一时,不仅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自动化,而且制造柔性更高,适应小批量生产之需。
生产工艺的巨变使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如下变化:一是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下,企业为了实现产品差异化,通常会在内部设立不同事业部负责不同的生产线,科层组织可以更有效地协调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一些企业横向一体化发展速度加快后,部门间信息传递效率低下的“大企业病”日益严重。但是到了信息化时代,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分析的成本明显降低,企业管理对科层结构的依赖程度也相应下降,企业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二是企业网络这一新型产业组织兴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生产高度一体化要求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要求企业掌握技术、职能和管理三类知识。[22]通常而言,一体化大企业能够利用相对稳定的盈利支撑这三类知识的获取,因而更具优势。但是到了信息化时代,生产一体化转向碎片化,原先在企业内部完成的业务流程越来越多地由企业间协作完成。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大爆炸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知识学习成本,另一方面,企业间信息传递效率的提高也更方便利用知识的互补性。因此,企业网络这种新型产业组织方式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三、第六次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转变
目前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最常见的表述有:一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二是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又称“工业4.0”)。[23]无论采用哪种表述方法,均认为呼之欲出的“工业革命”将助推工业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跃升。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新一轮工业革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200多年“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的拓展与升华。因此,笔者吸纳贾根良的观点[24],将新一轮工业革命称之为第六次技术浪潮。我们将严格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分析框架,结合当前主要工业化国家及我国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探索实践和政策调整,研判第六次长波发生与拓展过程,展望生产组织方式可能的变革及相应的理论含义。*根据前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周期(特别是第五次长波拓展期)可以判断,第六次长波的导入期可能发生在2020年前后,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都将是长周期的上升期,之后进入拓展期,延续到本世纪中期结束。这与德国“工业4.0”计划规划的愿景将于本世纪30年代实现相吻合。受传统工业革命史研究思路的影响,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新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是什么,是3D打印、工业机器人,抑或是人工智能?按照演化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新型制造技术更准确的表述是先导产业,它们虽然对产业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发展并不是自我实现的,而是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核心要素变得物美价廉,二是基础设施及时升级以满足先导产业发展所需。因此,虽然各界普遍关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标志性技术或者先导产业,但是忽略了两个本质性问题:一是什么要素是这些先导产业部门扩张所必需的核心投入?二是这些先导产业扩张需要什么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
(一)数据将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投入
种种迹象表明,不同于以往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高度依赖于物理装备的升级,驱动第六次长波的核心要素将是数据。换言之,数据要素将成为决定未来工业化水平的最稀缺的要素。[25]因此,相比于先导产业的更替,核心要素的更替更具革命性意义。虽然工业机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型制造装备提升了生产的自动化和柔性水平,但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不足以引发“革命性”的变化。按照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计划和我国“互联网+”战略的设计和部署,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将加速向制造业领域渗透,与新型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后推动既有制造系统发生重大转变[26],这就促使数据成为驱动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关键要素。
虽然20世纪70年代工厂引入“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可编程控制器即工业控制计算机,其基本架构与个人计算机类似,即通过可编程存储器执行顺序控制、定时和计算等操作指令,通过输入和输出接口控制各类制造设备,达到干预生产过程的目的。后逐渐完成了初等信息化,但是与智能制造仍然有显著区别。PLC仅实现虚拟信息世界向现实物理世界的单向输出,物理世界并不能向信息世界作出反馈,数据的产生、采集、分析和利用也都是单向的,数据要素对企业边际利润的贡献附着于物质资本之上,缺乏显著性和独立性。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向生产的全面渗透将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大幅提升数据对企业边际利润的贡献。当前,代表全球制造业最高水平的国际知名企业的探索实践征兆着数据的获取和配置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正在挑战流水线生产方式。博世集团和西门子集团等德国工业巨头是德国“工业4.0”计划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它们围绕数据构建智能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智能工厂”,即在制造装备、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施及产品上广泛植入智能传感器,借助物联网和服务网实现终端之间的实时数据交换,达到实时行动触发和智能控制,对生产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化管理。智能工厂为智能产品的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智能产品记录了消费者的需求特征以及从生产、配送到使用的全过程数据,在生产过程中可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以数据交换的形式与生产设备“对话”,选择最优的配料和生产方案,极大地提高了制造系统的柔性。曾被福特制替代的“大规模定制”生产组织方式重新具有了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数据要素对于生产系统重构的意义还在于形成智能工厂和智能产品的闭环。依托物理—信息系统,生产数据和消费数据形成大数据系统,经实时分析和数据归并后形成“智能数据”,再经可视化和交互式处理后,实时向智能工厂反馈产品和工艺的优化方案,从而形成“智能工厂—智能产品—智能数据”的闭环,驱动生产系统智能化。这一切的实现既依赖于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生成和利用,也依赖于“云设施”的升级与完善。如同资本要素的供给来自于资本积累,劳动要素的供给来自于人口增长和教育,数据要素的供给则依赖于传感器和高速通讯设施的广泛应用。因此,在数据要素成为核心投入的过程中,可以廉价获得的传感器便是新一轮长波中派生出的核心要素。按照德国“工业4.0”计划的部署,新型传感器单价将降至1欧元以下,即便广泛植入也不会造成使用成本的显著增加,这可以有效提高数据要素的积累效率。
(二)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将超过交通基础设施
核心投入与基础设施的动态匹配是促进先导产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表明,核心投入可以廉价获得是基础设施快速完善的产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为核心投入产业的发展提供初始市场,从而形成正反馈效应。例如,与铁、煤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是运河和铁路,与钢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是钢轨和钢船,与石油、天然气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是高速公路、机场等,与集成电路相匹配的是互联网。随着数据要素(及其相派生的传感器)成为新一轮长波的核心投入,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第五次长波中形成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是否与新兴的数据要素相适应?
互联网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互联网(1969—1989),即军事和科研阿帕网,主要用于公共部门的内网使用。第二代互联网(1990—2005),即基于个人计算机的万维网,刺激了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互联网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架构灵活性不高,难以适应不断涌现的新业态的需求;二是难以满足未来海量数据增长的需求;三是实时性、安全性和灵活性尚不能满足产业融合发展所需,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互联网金融、车联网等对互联网的升级提出了强烈且迫切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互联网技术正在通过多条技术路线向第三个阶段演进。其中,传统IP网络向软件定义网络(SDN)转变便是一大趋势。SDN可实现数据层和控制层的分离,定义和编程网络设备资源,实时反馈网络及网络设施的运行状态,提高网络部署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当前,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对核心要素和先导产业的支撑还远远不够,但已经在加速集聚爆炸式发展所需的资源。首先,在政府层面,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的公共研究机构立项研究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路线,讨论和制定新一代互联网的协议。例如,2011年美国通过了《联邦政府云战略》,将联邦政府1/4(约200亿美元)IT支出转为采购第三方公共云服务;2012年欧盟发布“发挥欧洲云计算潜力”战略,在各领域推广云计算的应用。其次,在产业层面,2012年,13家全球主要电信运营商共同发起了网络功能虚拟化组织,截至2014年10月,已有250家网络运营商、电信设备供应商、IT设备供应商以及技术供应商参与。另外,2013年全球主要电信设备和软件公司联合开发SDN控制器和操作系统。再次,在技术层面,新一代光网络、新一代无线网络(5G、Wi-Fi)、物联网、云计算(云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在硬件设备开发、网络协议和标准制定、网络传输速度和频谱利用率提升、功耗和延时降低,以及兼容性、灵活性和安全性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最后,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应用层面的潜力逐步显现。在产业应用层面,2012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约为1 700亿美元,预计2015年将接近3 500亿美元,年增长率约25%。2012年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1 072亿美元,预计2017年将达到2 442亿美元。在企业应用层面,除了德国企业正在利用物联网和服务网构建智能工厂之外,谷歌公司数据中心也通过SDN将链路平均使用率从30%提升至95%,并于2014年第1季度投入23亿美元,采用最新网络技术构建骨干网,以满足公司快速增长的需要。在政府应用层面,2014年6月,新加坡推出建设世界首个“智慧国家2025计划”,为大多数家庭提供超快的1Gbps网速,在线提供98%的政府公共服务。我国政府也提出“互联网+”,促进互联网技术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各行各业。[27]
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将为数据要素的积累和配置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数据的利用能够提升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率,从而形成第六次长波的两大核心构件。
(三)制造业智能化将发挥先导产业的作用
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后,将为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带来新的机遇。第一,引领产品的智能化和网络化。“硬件+软件+网络互联”正逐渐成为产品的基本构成,并呈现出个性化和差异化趋势。智能产品可通过网络,实时和厂商、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或上层智能控制平台通信,拓展产品功能和延伸服务需求。第二,推动生产和管理流程智能化。企业内部制造流程将整合至一个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平台,各种机器设备和数据信息互联互通,为优化决策提供支持。制造业的柔性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能得到充分满足。第三,推动研发设计的网络化协同发展。研发设计部门和生产制造部门的界面信息进一步整合,“虚拟制造”提高研发效率,客户可通过网络参与在线设计,融入个性化需求,缩短研发设计周期。第四,推动企业组织变革。不同层面的数据和信息可通过高速网络便捷传递,企业组织进一步扁平化。企业间组织趋于模块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成本,重塑产业价值链。第五,推动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制造过程高度数字化,产品数据全生命周期集成,企业通过互联网及时获取消费者需求,从而实现服务型制造,“私人定制”、“按需定制”和“网络定制”等服务模式将更加普遍。
制造业智能化将为其他领域提供通用技术。第一,在生产端,智能工厂生产的智能化装备和中间产品是其他产业的投入物。无论是新一代互联网设施的建设,传感器价廉量大的供给,还是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智能家居等智能系统的建设,都依赖于智能中间品的供给。第二,在消费端,满足消费者对智能化、个性化产品需求的前提是生产系统的智能化,没有制造业智能化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将是空中楼阁。第三,智能制造将对其他产业产生较好的示范效应。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业互联网为例,该公司的新一代GEnx飞机发动机上装有26个传感器,以16次/秒的频率监测300个参数,仅一次长途飞行就可以存储1.5亿份数据,翔实地记录航班的运行状态、发动机性能与效率。这些数据被传送至驾驶室和地面数据中心,经分析后用于监测、预测和改进发动机性能,有效缓解飞机的维修压力,从而降低航班延误的损失。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约20亿美元的成本。
(四)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兴起
虽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和企业间网络不断增强,但并不表示生产组织方式不会出现“革命性变化”。以数据为核心投入、智能制造为先导部门、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正在蚕食福特制(及其改进版)的经济合理性。
零部件的标准化是流水线生产的前提,这就限制了产品的多样化,导致产品多样化大幅度减少。之所以出现产品多样化(个性化)和产量(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制造业的生产流程投资具有专用性,调整产品种类需要转换生产线;二是产品零部件标准化程度高,零部件的调整成本高。过高的生产线和零部件转换成本使得产品调整不经济。因此,以标准化为核心的福特制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必须支付制造系统柔性低下的机会成本。
以数据为核心投入的新型制造系统具有更高的柔性。
第一,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生产系统,客户需求管理能力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可重构生产系统以重排、重复利用和更新系统组态或子系统的方式,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实现快速调试及制造,具有很强的兼容性、灵活性及出色的生产能力,实现生产制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动态匹配。例如,德国大众汽车开发的“模块化横向矩阵”实现了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所有车型的底盘,可及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车型和产能。这一过程表明制造业从产品模块化演化为生产线模块化。
第二,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范围经济可能超过规模经济成为企业的优先竞争策略。[28](P14)可重构生产系统使得大规模定制具备经济可行性,企业依靠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竞争策略的重要性也将有所下降。未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将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企业的主流竞争策略。为此,未来的企业组织将开放更多的接口直接面对消费者。例如,海尔集团进行企业组织的“倒三角”变革和组建以订单为中心的“自主经营体”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企业组织正演变为连接用户和员工的平台型企业。
第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需要调整,以提高数据要素的附加值。制造业智能化显著增加了生产的复杂度,对企业管理复杂度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从产品设计、原型开发、企业资源、订单、生产计划获取和执行、物流、能源到营销、售后服务,都需要按照新的产品价值链加以整合。包括:顺应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提升企业内部支撑制造的服务部门的重要性;顺应从提供单一产品到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趋势,增强与消费者的互动能力;利用新型基础设施进行投融资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大对员工(特别是技术工人)终身学习计划的投入。
第四,工厂制造转向社会化制造,产能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企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降低生产的信息成本,随着大量物质流被数字化为信息流,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碎片化,企业的信息成本大幅度增加,生产出现了“去企业化”,从而呈现出社会化制造的势头。目前一些地区出现了专门为网络设计者、用户提供制造和产销服务的在线社区工厂,有效地降低了产业的进入门槛;社交网络上出现了由个体组成的“虚拟工厂”,个人能够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筛选和完善,社会制造这一新型产业组织逐渐形成。[29]这将有利于向全社会疏散产能,有效防范产能的集中和过剩风险,这对深受产能过剩问题困扰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本文运用正统的技术经济范式分析框架梳理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核心投入、先导产业、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规律,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技术经济范式可能的演进形态与特征做出展望。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涌现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核心构件具有如下特征:数据要素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投入,数据的分析与利用能力将成为国家之间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新型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或将超过交通基础设施,信息标准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调整的基础;智能制造仍然是国民经济体系进步的先导部门,范围经济的重要性可与规模经济比肩,智能制造的发展还将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层次,重塑产业价值链;大规模定制将与当前主流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分庭抗礼,企业内部结构也必须按照新的价值链加以重新整合,企业组织的变革将使生产呈现出平台化和社会化的趋势。
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以智能制造为方向、以建设制造强国为战略目标的《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制造业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对我国制造业的提质升级产生深远影响。今后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宜按照技术经济范式核心组件的变化规律进行系统性调整,增强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性。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要增强我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的能力,《中国制造2025》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首先,要从重视“硬”装备转向重视“软”系统。《中国制造2025》提出国家将引导社会各类资源集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航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十大重点领域突破发展。虽然这些复杂装备是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重点,也是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整体升级的重要支撑,但相对而言,低估了数据要素在制造业智能化中的核心地位。实际上,长期对数据要素的重视不够,不仅是我国高端装备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也是影响我国高端装备产品品质(如产品稳定性)提升的制约因素。更重要的是,对数据要素的轻视不符合制造业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相比于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计划以数据要素重新定义制造业,发展以“智能装备+智能软件+网络互联”三位一体的智能制造架构,我国“重装备、轻软件”的局限性必将显现出来,可能在未来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需要培育出能提供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集成企业,加强数据要素的积累和开发利用,促进制造装备、工艺、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
其次,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需要加速升级。我国虽然已经在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社会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渗透率等指标都上升较快,但是距离满足“互联网+”向各领域融合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要在网络传输速度、降低网络能耗和降低数据服务资费方面继续加强。目前,我国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局限于信息通信技术本身,发展重点着眼于消费领域,对制造业智能化的支撑作用直到最近才开始被关注。通信基础设施升级是数据要素能廉价且大量供给的必要条件,是制造业智能化的基础。今后在通信基础设施升级中应加强信息通信服务商与工业企业的对接,使信息通信服务与企业智能化改造的需求相匹配。同时,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标准制定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以信息通信技术标准的国际合作推动智能制造的国际化发展。
再次,数据要素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向制造业领域的渗透亟须加速。制造业智能化是驱动国民经济体系智能化的主要驱动力,脱离制造业升级的商业模式创新难以为继。我国互联网服务最广、数据要素积累最多、利用水平较高的是商业服务领域,如百度积累的用户需求数据、阿里巴巴积累的消费数据和腾讯积累的社交数据。但是,这些在我国互联网高速发展中涌现出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尚未将资本、数据、品牌、人才和技术优势导入制造业领域。应鼓励这些企业集合各方面的资源,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之路。
最后,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相比于核心要素、基础设施、主导产业的演变,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过程中新旧利益集团的斗争更为激烈。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过程顺利与否,直接影响到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效率。目前的产业规制和政策形成于上一轮技术经济范式,过去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可能会成为新型产业组织成长的障碍,如产业边界划定、行业准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政策等都可能难以与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给予新型生产组织试错机会,及时调整不合时宜的管制和政策。
[1] 哈巴库克、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 G. Tullock. “Why di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ccur in England”. In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and Gordon Tullock(eds.).ThePoliticalEconomyofRentSeeking. Boston / Dordrecht / Lancast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3] Acemoglu, D., Johnson, S.,and J.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 2005, 95(3).
[4][13] Freeman, C., and F.Louçã.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Freeman, C., and F.Louçã.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 Lazonick.CompetitiveAdvantageontheShop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 Chander.TheVisibleHand:TheManagerialRevolutioninAmerican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6][18] A. Chander.TheVisibleHand:TheManagerialRevolutioninAmerican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Freeman, C., and F.Louçã.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 Perez.TechnologicalRevolutionsandFinancialCapital:TheDynamicsofBubblesandGoldenAg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2.
[8][24] 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
[9] 兰德斯:《1750—1914年间西欧的技术变迁与工业发展》,载哈巴库克、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0] R. Coase. “The Nature of Firms”.Economica, 1937,4 (16).
[11] Freeman, C., and F.Louçã.AsTimeGoesby:TheInformation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 Lazonick.CompetitiveAdvantageontheShop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Chandler,A.,and T. Hikino.BigBusinessandtheWealthofN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4][15] D. Nye.ElectrifyingAmerica:SocialMeaningsofaNewTechn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1992.
[16][25][29] Agion, P.,and P. Howitt.EndogenousGrowth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17] A. Chandler.TheVisibleHand:TheManagerialRevolutioninAmerican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ndler, A., and T. Hikino.BigBusinessandtheWealthofN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W. Lazonick.CompetitiveAdvantageontheShop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 Pisano, G., and W. Shih.ProducingProsperity:WhyAmericaNeedsaManufacturingRenaissan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 罗森伯格:《探索黑箱:技术、经济学和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1] T. Ohno.ToyotaProductionSystem:BeyondLarge-ScaleProduction. New York: CRC Press, 1988; T. Fujimoto.TheEvolutionofaManufacturingSystematToyot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A. Chandler.ShapingtheIndustrialCentury:TheRemarkableStoryoftheEvolutionoftheModernChemicalandPharmaceuticalIndus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 黄阳华:《德国“工业4.0”计划及其对我国产业创新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2)。
[26] 黄阳华、吕铁:《市场需求与新兴产业演进——用户创新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展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3)。
[27] 黄阳华、林智、李萌:《“互联网+”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7)。
[28] A. Chandler.ScaleandScope:theDynamicsofIndustrial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责任编辑 武京闽)
A Retrospect of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in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Beyond——An Analysis Based on Kondratiev Long Wave
HUANG Yang-hu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
This paper employs the orthodoxy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and brings the currently emerging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back into a two centuries’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uld be grounded on established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co-evolution of core components of in the shift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likely to be an extension period of the 6thtechno-economic paradigm(or the 6thKondratiev long wave)and introduces revolutional changes as follows:data would be a new core input;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new internet technology would exceed traffic infrastructure,and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based on data and new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is going to build a smart national system.As a consequence,the dominating mass production model is challenged by emerging mass customization and social production.China should move its policy from emphasizing the high-end equipment industries to the utilization of data and upgrading new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and 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olicies.
industrial revolution;Techno-economic paradigm;long wage;production organiza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技术创新发展对通货紧缩预期的影响研究”(7154100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路径、产业选择与战略规划研究”(15ZDB149)
黄阳华: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