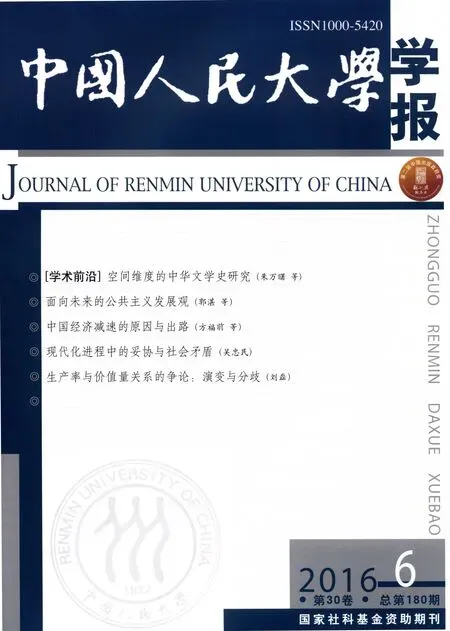湖畔水滨: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
罗时进
湖畔水滨: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
罗时进
江南遍布的山庄园林、无数的居宅堂室,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文事活动中 “活的元素”(文人)、“静止的元素”(文本)都被注意或重视,而介于“文人”与“文本”之间的“物质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考察清代江南地区的“水环境”,探讨与“水”相关的“场景”与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江南文人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了以水为环境特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长期被感知又反过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共存的耦合关系。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大量写于湖畔水滨的作品及其背后群体活动的故事,成为一种特有的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的认知地图,是我们回忆清代江南文人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参照,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清代;江南;文学社团;湖畔水滨;自然书写;创作现场
江南有得天独厚的山水之胜,有遍布城内或郊野的山庄园林,以及无数平凡或不平凡的居宅堂室,这些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通常我们对文事活动都注意“活的元素”,其核心是文人;抑或重视“静止的元素”,主要是文本;但介于“文人”与“文本”之间的“物质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了。而地点场景恰恰构成了当时作家创作的条件和感知对象,也成为特殊的空间记忆进入作家创作之中。因此,所谓“场景”应该作为文学创作的“先期文本”来看待,“后期文本”与“先期文本”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联系。本文着重对清代江南地区“水环境”进行考察,由此探讨与“水”相关的“场景”同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
一、水环境与江南文人的耦合关系
江南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水是构成江南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水环境对文明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水的历史文化意义,俄国著名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在《文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中认为:“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界的领域中,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发展,刺激文化从河流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海过渡的力量。”[1](P237)把水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极富见识的,我们在研究江南文学的发展与贡献、讨论江南文学社团的形成与特点时,如果要选取和切入那些与本质相通的因素,自然应关注水环境。
江南具有江、河、湖、海一切水环境的优势,而其中太湖之“水”具有核心的地位。“太湖,巨浸也。东西洞庭,奥区也。山在水中,目景斯聚,心景斯别。从旷处望,三吴数百里不能遁形。”[2](P482)浩瀚广袤的太湖是江南之母,她决定了江南的性格,也维系着江南的存在。“惟吴泽国,民以田为命,田以水为命,水不利则为害。”[3]《宋史·食货志》也说:“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4](P4182)。明人吕光洵《修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亦云:“今天下大计,在西北莫重于军旅,在东南莫重于财赋。而苏、松等府,地方不过数百里,岁计其财赋所入,乃略当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业故也。”[5]除“耕稼之业”外,栉比鳞次的市镇也蕴藏着极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在江南,“四周皆大泽,环之如带,其中林木掩映,港汊蟠曲”[6]的市镇不可胜数,其得“擅水之利”也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水为江南的交通带来了便利,开阔的水面境域,四通八达的水上路线,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形成了门户开放的态势。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这样描述松江:“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之关键。盖风帆出入,瞬息千里,而钱塘灌输于南,长淮、扬子灌输于北,与松江之口皆辐列海滨,互为形援。津途不越数百里间,而利害所关且半天下。”[7](P270—271)而清代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8](P331)。江南向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文化观念上得风气之先,本土传统观念与新观念、新思潮在这里交汇激荡,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态势,江南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中得以发展的。
这里让我们看一看英承科《湖光山色记》所云:“宋圣简为余两弟设皋比于挺秀堂,时为余谈包山胜概,属寰中第一。余时神往,谓他日一了经生债,便当买扁舟,浮沉七十二峰间。”[9](P165—166)陈去病《松陵诗派行》站在文化高度总结道:
端委化俗文明开,延陵观乐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学,宗风肇起孳胚胎。加以太湖三万六,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钟夕毓孕灵秀,天然降兹攀奇才……笠泽丛书才告成,松陵唱和多新制。因斯篇帙盛流传,踵事增华发凡例。三高祠宇乍经营,亭子鲈乡斗清丽。滩名钓雪桥垂虹,风景吴江绝尘世。[10](P12)

江南的范围应该怎样界定是需要讨论的。理论上,今天以长江下游“江之南”地区皆称江南,但这是较为宽泛的,如论其核心地区仍然应该是明清时代苏、松、常、镇、太、杭、嘉、湖七府一州所涵盖的地方。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曾指出:
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之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然其学风所衍,又自有分野:大抵自江以南之苏、常、松、太,自浙以西之杭、嘉、湖,合为一区域;江宁、淮扬为一区域;皖南徽、宁、广、池为一区域;皖北安、庐为一区域;浙东宁、绍、温、台为一区域。此数域者,东南精华所攸聚也。[15](P60—61)
将“江以南之苏、常、松、太,自浙以西之杭、嘉、湖,合为一区域”,不仅符合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也符合文学的地理分布。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地域范围对水环境与文化、文学的关系的考察,除了应关注密集的太湖水网外,杭州西湖无疑也应作为一个重点。
西湖在江南文化、江南文学发展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西湖之地域范围与太湖无法比拟,且西湖由泻湖到筑塘与海隔绝,从而使湖水逐渐淡化成为城郊优胜水境,其间历代开浚之力甚着,这与太湖完全由自然造化而成亦非同等意义,但西湖特殊的美学构造形成的集约性优美山水意境恰恰与开放性的太湖相对照。吴庆洲先生分析道:“西湖除去邻接市街的一面,三面环山,这样,山遮挡了视野,限定了视界,而这一闭锁性反而令湖水成为前景,使一个独立的山水构图浮现出来。而且因为西湖也正好是视界能容纳的大小,对游览者来说,作为没有显著差别的映射,盘结在各自的心里。山水的配置,防止了游客对于景观注意力的扩散,起到了向某一种意象集约的效果。”[16](P66)
苏轼曾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17](P864)如果说浩瀚的太湖造就了江南的美学身段的话,那么西湖之于江南,亦似眉目之传神,而宋代以来形成的西湖十景,连同唐代李泌、白居易,宋代林逋、苏轼,元代赵孟頫、黄公望、杨维桢等一大批著名文人留下的人文遗迹,更为西湖增加了美学空间,使之成为文士向往的绝胜佳境。至明清两代杭州的城市影响有扩大的趋势,西湖文学亦蔚为大观。《西湖志》卷十九曰:“西湖名流辈出,或选胜而来,或抱奇而处,山高水长,有令人流连向往而不能置者。”[18]江南文人是如何心仪西湖的,从王应奎《海虞诗苑》中关于清代海虞诗人王维宁的记载可窥一斑:
维宁,字古臣,隐居邑东之韩庄,自号寒溪子。好游山水,而又善画,所至辄图其胜以归。尝与友人结西湖看花社,岁必一往,计一生湖上游迹,凡二十七度云。人有延之为师者,君必访其居,有园亭、竹树可供赏览者,然后就之。得束修钱,辄出片楮裹置漉囊,曰:此吾快游具也,其负胜情如此。嘉定黄陶庵尝序其诗,拟诸方玄英、陆鲁望,庶几得其伦矣。[19](P54)
王维宁“岁必一往”西湖,平生凡二十七次,且专门组织文学社团“西湖看花社”作群体性的“快游”,可谓对西湖情结的极致化,很有代表意义。其中反映的文人与水的亲和感情,文人对水的依赖关系,是颇能说明文人和文学社团在江南水环境中发展的“心理——审美”因素的。“名区胜境必待人而后显,果其人功业文章足为湖山增重,则不必尽属浙人自当与西湖并垂不朽,至迁客骚人、缁流羽士亦例得并载。”[20]天下文人墨客都是西湖的欣赏者和文学创作者,而江南文人有地利之便,更能满足对西湖的审美愿望,以之为题材的作品极多。
太湖与西湖胚育了苏州和杭州两个中心城市,也滋润繁茂了由这两个城市连接的江南沃土上的文学。江南文人散布在广袤的江南地域中,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着文本上的以水为环境特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在江南文人的生命过程中长期被知觉渐而类化为特定情感,又反过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生成了某种文学观念。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相须、共存、并演的耦合关系。这在清代文学社团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特定文化空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乐群”是文人的普遍心理倾向,并深化为一种“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惯习[21](P170)。这种群体心理往往通过“聚”来表达,“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士,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尊之乐,爰寓诸篇章,而诗作焉”[22](P597)。可见文学社团是文人“乐群”精神的产物,而当庙堂朝殿、莲府官署这样的空间被一些文人否定或放弃了之后,山水空间便成为“聚”的重要选项了。
山与水本相互依傍,文人往往并置而言,文学作品中“山水”往往连绵孪生。但就现地、场景而论,在“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23](P8)的江南,文学社团最常见的是以水环境为首选文化空间。清代江南士族吟咏酬酢的群体性文学活动往往即在湖畔水滨进行,甚至可以说凡水边湖岸无不有文学社团活动,许多文学社团便直接以水名作为社团之称,这里略举数例:西湖诗社、平泉诗社、西溪吟社、花川诗社、南湖瑶纶阁社、南湖吟社、秀水诗课、绿溪诗社、莺脰湖诗社、柳洲八子、鹦湖花社、清溪社、溇上诗社、苕溪诗社、双溪诗社、语溪澄社、鸳湖吟社、竹溪诗社、春湖吟社、泖东诗课、泖东文社、棠溪诗社、莺湖九老会、金溪五老社、蓉湖吟社、梁溪社、槐江社、苕溪社。*以上所列社团均见笔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环太湖地区文学社团与文化生态研究”(10BZW056)结项报告书。
其实仅凭社名来判断文社或诗社是否与湖畔水滨有联系还是比较机械的,即使以江干社、汐社、水村诗课、湖舫吟社、五湖诗社之类有“水”为符号的名称来认定社团与湖畔水滨的关系也会陷入教条。以道光十年(1830年)春陈希恕等在吴江盛泽创立的红梨社*该社成立时推举周梦台为社长,其社员主要有周梦台、唐寿萼、冯泰、陈希恕、张宝璇、张沅、仲湘、沈烿、贾敦临、张宝钟、史致充、金钟秀、沈汉金、沈曰寿、沈曰富、沈曰康、陈应元、杨秉桂、翁雒、金作霖、沈焕、杨澥、张开福、赵懿、张衔、张钧、吴山嘉、叶树枚、蒋宝龄、吴鸣锵等。来说,社名似乎与水无涉,其实不然。周梦台《红梨社诗钞跋》言:“吾乡有水名红梨渡。”[24]据《盛湖志》载:“红梨荡在盛泽荡北,邑沈志名白马寺后荡,昔人种红梨于湖滨,故名。国朝康熙间里人俞南万开设渡舟,建凉亭,以通谢天港来往之路,因名俞家渡。”[25]由此可见,“红梨社”其实亦因水而名。只要认真考察,这类情况会发现很多。
为什么江南文学社团往往选择以水滨湖畔为文学社团活动的现场?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起主要作用。
一是水路通达,舟楫甚便。江南多水,而当时水路交通也优于陆路交通,舟楫往来较为方便,与山区道路崎岖阻隔颇为不同。中唐时期李肇撰写《唐国史补》,在论及江南的区域优势时,就着重强调“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26](P448)。正是处处“无不通水”而“舟楫居多”的便利,使整个环太湖地区文人的联系相当密切,文学社团网络由水湾港汊、湖滨汀州层层组合连接起来,呼远唤近,脉息相通,社团的组织状态于焉形成。
明末清初社集活动伴随着政治潮流风卷云涌,复社作为文学色彩涂抹下的一个具有极强政治诉求的民间社团,声势浩大。张溥登高一呼之下,应者云起雷动。复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分别为吴江的尹山大会、南京的金陵大会和苏州的虎丘大会。这三次大会都极富江南水国特色,即舟上往还大张旗鼓、水滨浪漫竭尽风流。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记录了复社集会舳舻绵延的盛况:
松陵水乡,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嘉会,辄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风波为苦也。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之拏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栏骋望,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飞琼王乔,吹瑶笙,击云璈,凭虚凌云以下集也。[27](P353)
复社旗下诸多社团关系复杂,张溥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逝世,同声、慎交二社生出种种嫌隙。身为一时文坛巨魁的吴伟业出面调和,折冲樽俎,顺治十四年再次将各社揉拢起来,倡导成立十郡大社,决定续崇祯年间盛事,仍然在虎丘举行集会。*王应奎在《柳南续笔》中对这次集会的情况也有所记载:“顺治癸巳重三日,吴门宋既庭、章素文。复举社事,飞笺订客,大会虎丘,而延太仓吴祭酒莅盟焉。时远近赴者,几至二千人。舳舻相接,飞觞赋诗,歌舞达旦。翌日,各挟一小册,汇书籍贯、姓名、年庚而散。”参见王应奎:《柳南续笔》卷3《虎丘社稷》,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据记载:
癸巳春,同声、慎交两社各治具虎丘申订,九郡同人至者五百人。先一日慎交为主,次日同声为主……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28](P1463)
江南四处通水而舟楫居多,不但为男性开展文学群体活动带来了拏舟而行的方便,而且清代女性文学社团活动亦往往在水上、舟中。在这方面,蕉园诗社是一个典型。吴颢曾这样记载蕉园诗社才性文气极盛的女诗人在西湖出游授管分笺的情景:
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霄蝉縠,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29]
显然“舟楫”与“水滨”构成了清代江南文学社团一个特具情韵的文化空间和创作现场。地之便、水之利,都成为江南文人乐群雅集的天然条件。
二是湖畔忘机,栖水高逸。清代江南文学社团每每以湖畔水滨为自我文化空间,还在于水环境提供了隐逸氛围。明清时代文人结社,除复社、三千剑气社、南社等政治色彩明显的社团外,绝大多数都与隐逸具有通约性,很多文人结社的事迹往往见于地志的《隐逸传》,如《常熟县志》载:“钱润,字惟霖,布政使昕族弟。性高旷,席有丰业,不以家萦怀,独喜近林薮词墨士,与邑善诗者为吟社,每月集于其家,遇风雨必遣舟舆迎之。客至,出所业评窜,夕而后散。时以醪米馈遗,口不及俗事,人或犯之,茹而弗校,以是岁租常不入。诗温丽可诵,书仿宋仲温。”[30]《苏州府志》载:“陆志熙,字予敬,长洲人。吏部郞中康稷子,明末由诸生选贡。尚气节,工诗文,承先志,不谒选人。康熙初,迁昆山南星渎,与归庄、王晨、吴殳辈结社赋诗。”[31]
隐逸,是文人结社的基本出场状态,也是选择水滨湖畔的心理意向。即如上述的南社,我们虽然能够读到诗人们在社团成立时乘船至虎丘雅集的诗句“画船箫鼓山塘路,容与中流放棹来。衣带临风池水绉,长眉如画远山开”[32](P114),能够感受到时代的鼓声中“容与中流放棹来”的侠义剑气;在后来的鸥社*鸥社是南社的一个分社,据鸥社发起者之一胡朴安的介绍:“民国九年,我们几个在上海南社的朋友,由子实与我发起,组织了一个鸥社。”“诗中所言之人,只孙小舫一人,非南社社员,是子实同事也。我们这个鸥社,每月雅集两次,继续有一年半之久。当日各人每次雅集诗之手迹,我处尚存一册。”“鸥社虽非南社,而除孙小舫一人外,皆是南社社员,故其诗亦可编入《南社诗话》中,为南社增一故实。”参见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152-1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阶段,也仍然可以在“碧浪粼粼软,轻舟荡漾来。荒村围古树,斜塔倚颜台。云影孤帆静,歌声几处哀。浊酒如可买,遣兴且衔杯”[33]的诗行中听到云影孤帆歌声沉哀,可知轻舟荡漾也有与时代相通的脉息。但总的来看,隐逸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诗遇知音堪结社,瓶储余粟可致仕”[34](P506)是清代文人结成文学社团的一般动因,而“独坐看梅倚钓矶,与梅相对澹忘机”[35](P542),则是湖畔水滨社中人普遍心态。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江南文人湖畔忘机、水滨高逸心态。清末民初柳亚子请擅长丹青的南社成员陆子美绘《分湖旧隐图》,并于次年广征众社友题咏。陆子美水墨《分湖旧隐图》浩渺澄静、荒寒凄清,表现出浓厚的向隐之意,“分湖便是子陵滩”的隐逸流脉构成了一片水国气象。该图题咏前后长达七年,其作品数量近三百篇,诗人们都洞透并呼应其中的隐逸内涵。王德钟诗云:“鱼庄蟹舍两模糊,渺渺山连淡淡湖。绝妙分湖好点缀,一丛密树一丛芦。”余十眉云:“烟波十里荻花秋,张翰莼鲈渺渺愁。输与当年杨铁笛,画船犹得载花游。”徐大纯云:“葭苍露白吟无已,知是诗人忆故乡。”朱剑芒云:“文章憎命隐樵渔,露白葭苍忆故居。”[36](P25-141)袁圻云:“我是风尘倦游客,买田也要傍分湖。”[37](P366)戴德章云: “如此风光如此宅,何妨归隐做神仙。”[38](P4383)水环境与世俗之间形成了一道隐然的隔离带,当诗人们占得一片水滨湖岸幽胜佳地时,自然生出渔樵之思,抒发出离开现实世界是非后心与物冥合,尘俗烦恼澹然俱忘的情怀,其心境清净愉悦,姿态潇洒澹荡。
三是接踵前贤,追步风雅。清人选择水滨、湖畔、舟上作为社团活动的现场,也是对前人结社文化记忆的再次展开。前贤曾经将那些地方作为文学现场置酒高会联袂唱和,湖山啸咏极尽风雅,特定的空间留下了文学映射,成为江南士族阶层的集体记忆。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对空间的选择及其行为模式,都带着对过去的风雅识记、保持和再现的意义。西湖是一个典范性文学地景,这是历代文人会聚酬唱的胜地,嘉靖年间以“西湖八社”著名,明末又现“西湖八社”,而清代杭州的不少诗社都追步风流。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杭州诸诗社》云:
吾杭自明季张右民与龙门诸子创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则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也;北门四子,则陆荩思、王仲昭、陆升黉、王丹麓也;鹫山盟十六子,则徐元文、毛驰黄诸人也;南屏吟社,则杭、厉诸人也;湖南诗社,会者凡二十人,兹为最盛。嘉道间,屠琴坞、应叔雅、马秋药、陈树堂、张仲雅诸人有潜园吟社,而汪氏东轩吟社创于海宁吴子律,小米舍人继之,前后百集。舍人刊社诗为《清尊集》。戴简恪寓杭州天后宫,有秋鸿馆诗社,亦骖靳焉。潜园、东轩皆有图。《东轩吟社图》,费晓楼画,今尚存;汪氏《潜园图》,则不可得见。咸同以后,雅集无闻。光绪戊寅,族伯父筠轩先生创铁华吟社,首尾九年。先生殁,而湖山啸咏风流阒寂矣。[39](P96)

另一个突出的文学地景是嘉兴之鸳鸯湖。鸳鸯湖虽仅一隅,却因自然风光绝胜而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唱和之地。其赓和之什、联唱之章,自唐宋以来蔚为大观。刘长卿《南湖送徐二十七西上》为较早歌咏鸳鸯湖风光的作品:“家在横塘曲,那能万里违。门临秋水掩,帆带夕阳飞。傲俗宜纱帽,干时倚布衣。独将湖上月,相逐去还归。”[43](P249)苏轼亦有“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之句[44](P410)。宋朱敦儒晚年隐居嘉禾,卜居鸳鸯湖畔之放鹤洲,与文人雅士悠游其间,作《樵歌》多咏鸳鸯湖。前人虽未见结社之举,但其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如朱敦儒,既解组南归,筑室鸳鸯湖畔为读书堂,道光年间的鸳水联吟社曾以之为题作社诗,以表达对前贤的追慕。清初朱彝尊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以诗歌的形式对鸳鸯湖及嘉禾一带的风土民情及地方掌故进行描写,影响巨大,《鸳水联吟集》卷二十所载《题小长芦钓鱼师图》,即是以禹之鼎为朱彝尊绘写的《小长芦钓鱼师图》为目进行专题性集体唱和。沈筠《鸳水联吟·草堂雅集》有风流五百年、鸳社继今日之说。显然,道光年间的鸳水联吟社正是继美前贤,是对历史的贯通衔接。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累积进步的过程;文学家从来不是孤光自照者,都是在对先贤的记忆中成长的。优胜的水环境是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天然受容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而他们是湖畔水上文学史最有力的续书者,他们行为上仿效前人风范,写作上参照原生文本,在自己的时空中开掘新的文学话语。
三、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自然书写
“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45](P22)清代江南文学社团二百多年间在湖山秀水的物质空间中活跃着、显示着自我存在的意义。这种存在感是在“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46](P115)的自然书写中产生的,而意义的彰显,则来自于江南文人的生命体验与环境所累积的互动。
清代文人以社团的名义群体性地走向了山水,在天赐的诗境中表现以山水为乐趣,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志。这种境界颇似寒山所说的“野情便山水”[47](P582)。山水中天然具有的野逸的生态因素能够与主体精神交会契合,满足人身体安逸的生理需要和心理自由的审美需求。江南既然给予了他们天造地设的自然环境,取境适性便是文人的权利,社团共趋于此,依存于此,则显示出文人群体的意向。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清代江南文学社团那样热衷于集体性地潜于文、游于艺,是不能不考虑“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的环境因素的。
欲说明清代江南文学社团与湖畔水滨之依存关系,不妨稍稍检视一下不少社团留下的“雅集图”。自兰亭修禊以降,文学社团活动每有雅集图录。此类图画,地域特征相当明显,而江南之雅集之绘,往往以水环境为背景,或一定程度纳入湖光山色。试看清嘉庆年间的《泖东莲社图》:
其一人负手蕉阴者,青浦何其伟书田。自蕉阴卷幄界石阑中,背幄设树根床坐而拈髭者,山人也。绿衣撰杖者,山人之少子嘉禄……迥溪枉渚,沄沄荡空,双鹤翔其上,一人行而至举手,若有所指者,夏璇秋圆也。临流涤砚者,高崇瑚鞠裳。两人乘野航,泛泛出芦荻间,欹坐船首者,姜皋小枚,弄篷船尾者,改琦七芗。披袈裟度桥者,西林退院僧寄公觉圆也。当投壶处,隔水露一屋,启其牖,一人执笔对镜,自写其面,面出于镜中者,南汇王埙和中。倚几观之者,恕子六郎也。[48](P59)

正因为如此,我们分析清代江南的文学社团何以以湖畔水滨为文化空间,是不能缺少环境美学视角的。如果说是湖山秀水吸引了远近文人当符合事实。且看鸳鸯湖:“淑景布丽,微风扇和,青莎绿堤,虹梁跨波,都人仕女,往来婆娑。列绮席,间清歌,扬桂楫,浮彩舸,以乐时雍,既丽且都。又若潦水尽,寒潭澄,天翳绝,湖镜平,望颓阳之西下,见明月之东生。渔歌互答,水调凄清,轻艖短棹,比渚连汀;实豫且之攸乐,匪伊人之所恒。”[52](P40-41)陶元镛曰:“鸳鸯湖,久著名胜。广袤不过百余顷,而来有源、去有委,水利之潴泄系焉。楼台烟雨,杨柳湖塘,风景之清茜属焉。自宋以降,骚人羁士,流连歌咏,篇什綦繁,近虽风雅道微,而远客戾止,无不汲汲以游鸳鸯湖、登烟雨楼为预定之游程。”[53](P2)鸳水联吟社今存社集《鸳水联吟集》中所列社友173人,以嘉兴、苏州两府最多,亦有来自杭州府、湖州府、松江府、温州府、宁波府者,每次文会都有三十多人前来参与,不能亲与者则邮筒寄诗,共襄联吟雅举,这关乎社友间之人情,亦关乎内在审美之需求。
湖山秀水凝聚了江南文学社团,也锻铸了他们的文学品位。吴江的荇藻湖,是太湖支流的一汪碧波,云烟水竹,湖光秀丽,是道光间红梨社雅集的向往之处。红梨社集第六会“七子荇藻湖观荷,以白石词‘水佩风裳无数句’分韵”,此次雅集社长周梦台因病未能参加,事后所作《荇藻湖观荷诗序》颇可一读:
夫人端居一室,心常湛然其中。及有所托,则虽在微物,皆得造端兴起,以自写其用情之所致。况地有烟波之胜,人多著作之才,具一时之选也。今年余假榻沈氏,以主人雅故,得与里近同志诸君子昕夕相见为乐,且时时以诗作会,会无杂宾,诗各言志……诸君子有荇藻湖观荷之举,余以不得与为恨,诸君子亦未尝不以余之不与为恨也。诸君子分韵赋诗,汇而录之,余疾未尽愈,读之若身入其中,而不知疾之失也。荇藻湖在雁湖东,是水耶?是花耶?洋洋焉,并效于心目之间,意得而神动,更若有不能不形之于言者。余本无所托,因诸君子之所托而托之,亦乐也。[54]
读“是水耶?是花耶?洋洋焉,并效于心目之间,意得而神动,更若有不能不形之于言者”数语,知湖水之美如何感动诗人,如何胚育出江南文会的美学灵气。前文论述到文人结社几可与隐逸通约,事实上这种隐逸是很难归到传统的“小隐”概念中去的,其所呈现的雅趣显示出的是一种化入身心的赏心自得,一种近乎奢华的美感。试看:
春光妍媚,柳暗花明,兰亭流修禊之觞,华林驰校射之马。湔裙人远,胜纪长安;袚宴汀回,诗题曲水。上巳之辰,古称佳日,时维甲寅,南社开第十次雅集于歇浦,裙屐咸集,车马载途。既茗话于名园,复飞觞于酒阵。赏心乐事,把酒论文,泚笔记之,留为佳话。[55](P1745)
在湖畔水滨举行文会,自然环境是主要歌咏对象。罗星洲为吴江同里湖口的一个小岛,是同里胜景之一,顾我钧尝作《募修罗星洲并建阁筑塘公启》云:“我同里之有罗星洲也,宛在中央。藉为内蔽,临波涛于无地,远拟方壶,撑突兀于中流,近同浮玉”[56]。可见其风景颇佳。竹溪诗社诸子倾慕罗星洲的美景,月夜游此限韵赋诗,顾汝敬有诗《月夜偕袁朴村景辂陈芝房家东岩弟我鲁同游罗星洲即限罗星洲三字为韵》云:
尚余秋暑酷,不奈此宵何。携客远同载,披荆一放歌。满篷风色好,映水月明多。望里瀛洲近,天疑是大罗。(其一)
行行殊未远,水寺旧曾经。十里湖光白,三更佛火青。临流疑捉月。倚阁欲扪星,乘兴吹长笛,声声入杳冥。(其二)
凭高望不极,天外俨沧州。一笑鱼龙静,高歌天地秋。霜钟清客耳,银汉澹归舟,回首烟波渺,苍茫动远愁。(其三)[57]
其一概写诸子泛舟湖上,在明月照耀下远看罗星洲的美不胜收之感。后两首侧重具象描写罗星洲的美景。诗人们登洲,回首是“十里湖光”,向前是“三更佛火”,天上秋月皎洁,映在水中,银汉无声,舟影澹澹漾漾,与歌声、笛声、霜钟构成岑寂渺远的秋夜意境。三首小诗,将罗星洲夜景写得清高淡远,极富神韵。袁景辂此会亦有《秋夕同诸社友罗星洲玩月以洲名为韵》[58]之作,诗中“水石惊涛浪,云霞灿绮罗”、“空明涵万象,皎洁失繁星”、“水共遥村白,天连远岫青”的描绘,在清代江南山水诗中皆为值得玩味的秀句。
在水滨的社团文会活动中,他们也常以水上风物为对象,笔下多见江南浪漫情调。鸳水联吟社的诗人尝有对当地四种船——太平船、总宜船、赤马船、乌篷船的联吟,这里试读其中两首:
九姓渔家旧,生涯倚一篷。惯随潮上下,只在浙西东。花月春江好,吹弹小妹工。廿年鸥梦醒,谁复认衰翁。[60]
细雨疏烟的湖山风景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柔美的风情,诗中几乎没有对作为“物”的船进行描写,只有渔人和吹弹的妙龄女船工,更多的是作为“景”的花月春江、花港酒家、潮水荡漾的迭现,而“鸥梦醒”和“认衰翁”的淡淡的伤感其实只是“泛仙槎”的一种衬托,映现的是高隐的闲逸,世外的清幽和湖畔社集者的高雅。当我们阅读更多的水滨社集诗时,可以发现他们最常见的是描写如此情境的作品:“双髻潜修处,清流水一湾。林高秋色敞,花老鸟声闲。诗客能携屐,幽人定启关。为言同社客,有酒胜庐山。”[61]诗人在静观天地万物中,品味着自然造化的生气流动,欣赏着流水带来的生机,用晚明小品的清言方式与雅集者晤谈,互相激发性灵,创造出自然与人文美感的欣遇辉映。
江南水国呈现出多种美学风貌,有杏花春雨的闲逸潇洒,也有耕织渔桑的散淡宁静;有林泉山石野放逍遥,也有引水莳竹的清远适性;有河港汊湾的曲折逶迤,也有浩渺波浪的含宏万汇。不管何种风貌,对于清代江南文人,都乐于联袂吟诵,写到水便臻雅萃,道艺双美,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固然是由于向往自然、唯美尚文的诗意追求更贴近江南文人性情,同时也因山水清嘉的自然生态足以承载江南文人心灵的栖宿。
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自然书写是心灵与环境共感、文学想象与地缘情结融聚的知性书写,他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也造就或放大了许多文学地景。大量的作品连同其背后文学社团群体活动的故事,都累积为某种地方性知识,成为一种特有的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的认知地图,是我们回忆清代江南文人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参照,其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都值得充分重视。
[1]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2] 怀应聘:《登洞庭两山记》,载杨循吉等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
[3]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序》,载《张忠敏公遗集》,卷5,清咸丰刻本。
[4] 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吕光洵:《修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载陈子龙等选编:《明经世文编》,卷211,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6] 朱春生:《袁景辂墓志铭》,载《铁箫庵文集》,卷4,清道光五年观复斋刻本。
[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4《南直六·松江府》,载《续修四库全书》,第6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史茂:《陕西会馆碑记》(乾隆二十七年),载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9] 英承科:《湖光山色记》,载朱剑心编:《晚明小品选注》,卷5,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
[10] 殷安如、刘颍白编:《陈去病诗文集》,上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1] 汪珂玉:《石田自题画卷》,载张修龄等点校:《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2] 归有光:《吴山图记》,载《震川先生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 皇甫汸:《春日游西山作》,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 文征明:《记震泽钟灵寿崦西徐公》,载周道振辑校:《文征明集·补辑》,卷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41。
[16] 吴庆洲:《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兴废及其启示》,载《南方建筑》,2013(5)。
[17] 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20] 李卫修、傅王露等纂:《[雍正]西湖志》,卷19《名贤》,卷首《凡例》,清雍正九年刻本。
[19] 王应奎编:《海虞诗苑》卷3,载罗时进、王文荣点校:《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1]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2] 方九叙:《西湖八社诗帖序》,载祝时泰等撰:《西湖八社诗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3] 袁宏道:《西洞庭》,载《袁中郎随笔》,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24] 周梦台:《红梨社诗钞跋》,载陈希恕辑:《红梨社诗钞》,卷首,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25] 仲廷机纂修,仲虎腾续纂修:《[民国]盛湖志》卷2《水》,民国十四年刻本。
[26]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7] 陈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8]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4,载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9] 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卷32,清同治十三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
[30] 杨振藻纂修:《[康熙]常熟县志》卷21《隐逸》,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31] 宋如林等修,石韫玉纂:《苏州府志》,卷104《隐逸》,清道光四年刻本。
[32] 柳亚子:《十月朔日泛舟山塘即事八用韵》,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3] 胡朴安:《和傅尃〈兰皋朴安约游槜李,余以后期往登烟雨楼,泛杉青闸,归过于车中次来台韵〉》,载汪兰皋辑:《来台集》,民国九年铅印本。
[34] 陆义宾:《次和周仔玉四首》其四,载陈瑚:《顽潭诗话》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6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5] 陆世仪:《过鸿逸道兄斋看梅七绝句效子美漫兴体呈政》其四,载陈瑚:《顽潭诗话》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6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6] 张明观、倪明、吴根荣编:《分湖诗钞续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7] 柳亚子:《南社诗集》,第3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6。
[38] 柳亚子:《南社丛刻》,第18集,扬州,广陵书社,1996。
[39][42] 吴庆坻:《杭州诸诗社》《铁华吟社》,载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0。
[40] 金埴著,王湜华点校:《巾箱说》,北京,中华书局,1982。
[41] 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3] 刘长卿:《南湖送徐二十七西上》,载储仲君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
[44] 苏轼:《至秀州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载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2。
[45] Henri 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 Cambridge, Mass: Wiley-Blackwall,1991.
[46] 董其昌:《评诗》,载《画禅室随笔》,卷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7] 寒山:《自见天台顶》,载项楚:《寒山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48] 王芑孙:《泖东莲社图记》,载《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4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9] 黄士珣:《东轩吟社画像记》,载汪曾唯:《东轩吟社画像》卷首,清光绪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
[50] 陈毓升:《竹溪雅集图歌并赠芥舟》,载《砚陶小屋诗钞》,卷2,吴江图书馆藏抄本。
[51] 王育:《娄东十老歌》,载汪学金:《娄东诗派》,卷9,清嘉庆九年诗志斋刻本。
[52] 陈世昌:《南湖赋》,载朱彝尊:《鸳鸯湖棹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53] 陶元镛:《鸳鸯湖小志》卷首《自序》,载朱彝尊:《鸳鸯湖棹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54] 陈希恕辑:《红梨社诗钞》,第6会,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55] 柳亚子:《南社丛刻》,第9集,扬州,广陵书社,1996。
[56] 阎登云修,周之祯纂:《[嘉庆]同里志》卷23《集文》,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57] 顾汝敬:《研渔庄诗稿》,卷上,清道光七年刻本。
[58] 袁景辂:《小桐庐诗草》,卷8,清乾隆三十二年爱吟斋刻本。
[59][60] 黄安涛:《总宜船》《乌篷船》,载于源、岳鸿庆等辑:《鸳水联吟集》,卷8,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责任编辑 张 静)
Waterside: A Field for Literary Societies inJiangnanin the Qing Dynasty
LUO Shi-jin
(Institute for Classics, School of Humanities,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Jiangsu 215006)
Unique landscapes, numerous gardens and resorts, and mansions and residences inJiangnan, or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a, are the common fields for the creative engagements of literary socie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Regarding literary activities, due emphasis is usually put on “dynamic elements”, whose core is literati, or on “static elements” such as texts, but not on what is in between literati and texts, that is, the physical scenario.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related field” inJiangnan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ocie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argues that men of letters then and there constructed in their literary writings nature featuring water, and that their perception of nature as such helped construct their literary experience. Such mutual construction generated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Jiangnanliterati and the water-related environ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numerous “waterside” works by theJiangnanliterary societies and their stories accumulatively turned local knowledge, and, a step further, memories of the times containing literary and social, cognitive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thus becoming significant clues to the lif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Jiangnanliterati of the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literary groups; lakeside; nature writing; creation site
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江苏 苏州 21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