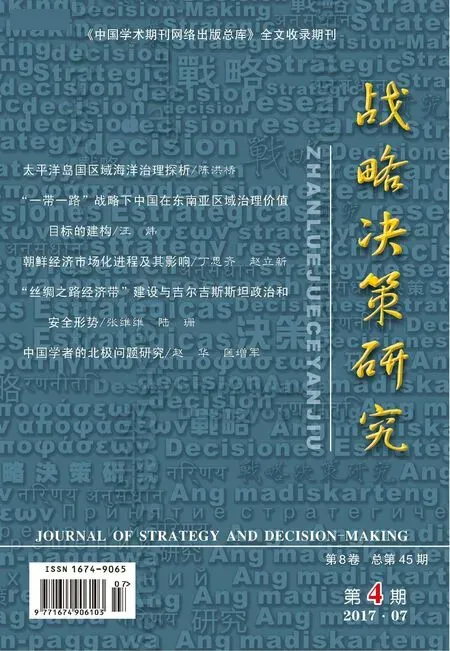“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价值目标的建构
汪炜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价值目标的建构
汪炜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两个历史阶段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上均发生过价值目标发生偏差的现象,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产生过消极影响。2015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规划蓝图到全面落地,年底,东盟共同体建成。鉴于此,中国在东南亚区域治理的价值目标应有新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现实情况的新发展。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结合现实环境,一个融合了底线性质、责任伦理和共同命运的“最大公约数”的价值目标将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及东南亚区域利益的维护及延展,并将规范着中国在该区的区域治理行为。
区域治理;价值目标;东南亚
一、引言
“一带一路”规划的推行使得周边外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周边外交的传统涵义上,①有研究者将中国周边板块分为“大周边”与“小周边”或内环核心圈、基本圈和重要利益圈等概念,相关讨论可参见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6-45页;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26页;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24-41页。中国在东南亚这一区域的治理问题成为中国周边国家外交议程中的显要性问题。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涉及区域治理的决策越来越被置于集体协商的程序中。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处于共同利益不断升级的进程当中,那么中国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上就应该回答要确立怎样的价值目标以及如何建构这些目标等问题。
学界对中国的地区主义、东南亚外交、东南亚区域治理等议题研究颇多,有的从历史维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政策,基本厘清了政策脉络,具有较珍贵的史学价值。②可参见唐希中等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Elleman,Vruce A.,Stephen Kotkin and Clive Schofield,eds.,Beijing′s Power and China′s Borders:Twenty Neighbors in Asia,(Armonk,N.Y.:M.E.Sharpe,2013).Kang,David C.,China Rising:Peas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有的从周边国家的视角来研究它们的对华政策,以期分析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和基本框架。③可参见陈乔之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许利平:《当代周边国家的中国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Mahbubani,Kishore,The New Asian Hemisphere:The Irresista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Public Affairs,2008。还有的对21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区域治理模式提出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构想。④See Acharya Am itav,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1).Calder,Kent E.and Francis Fukuyama,eds.,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Prospects for Regional Stabilit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8).Ba,A lice D.,“China and ASEAN: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t Century Asia,”Asian Survey,Vol.43,No.4(July/August,2003)。祁怀高:《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55-59页。这些研究给本课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与历史基础,但他们对东南亚区域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目标缺乏必要的探讨,更鲜有关于当代区域治理价值取向的基本共识。
所谓“价值目标”,是围绕特定对象的价值取向和标的,是人们对某种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获得性或者实用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人的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围绕功能性展开的矛盾运动过程。⑤高小平:《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载《行政管理改革》2014第12期,第71页。区域治理的价值目标就是一定时期内某一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在区域范围内就实现善治而与其他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评价与看法的总和,其容易随着时间的流变性、行为主体的差异性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并指导着该行为主体的具体区域政策,其目的在于对区域公共利益予以保护并促进其增加。
本文将首先梳理建国60多年来东南亚区域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偏离现象并分析其原因,进而分析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下区域治理价值目标如何建构。
二、历史叙事:偏离的价值目标
国际社会中两类最基本的价值倾向就是秩序与正义。在如何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生存及推进其发展的问题上,对秩序与正义的不同偏好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⑥秩序至少意味着维护规则与现状、变化的可预测性和一定程度的稳定;正义则包括国际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等,在本文中主要指国际正义。可参见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透视》,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52页。新中国成立后,以1979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线,⑦王逸舟等人在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时也采用了以1979年为分界线的分法。参见: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9年9月版,第198-223页。在东南亚区域治理的价值倾向上采取了不同的偏好,并且均出现过程度不同的价值失衡现象,从而导致了在区域治理上出现了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家间关系交易成本的上升等非良性结果。
(一)1949~1979年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冷战模式”。⑧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67页。这时的中国“不是从地区(Region)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⑨Rosemary Foot.Pacific Asia: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alogue.in Lou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39.中共领导人将安南(越南)、马来亚、缅甸、泰国、印尼、菲律宾和印度等当作“亚洲尚未解放的、被压迫的国家”,并将在这些国家推进民族革命运动视为自己的责任,⑩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0-53页。区域治理价值目标糅合了“革命”色彩,并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⑪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乃至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可参见,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5-46页。
尽管中国于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外交政策上进入自主的探索时期,甚至中共八大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介入东南亚地区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如1959年推动越南劳动党和老挝爱国阵线重新开展武装斗争;1960年至1961年与越南秘密出兵老挝,帮助老挝人民革命党一举夺取了与中国云南接壤的数省;1966年“文革”的开展更使得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外交政策偏离了理性方向,区域政策的特征由“守成”和“适度”转变为“过于积极”。此时的中国“在一个想象中的以‘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梦”。⑬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页。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采取应对措施,于1967年8月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防止东南亚共产主义化、遏制社会主义力量向本地区扩张。⑭中国的革命输出使东南亚国家感到威胁,以致于当时的马来西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加扎利·莎菲(Ghazali Shafie)说“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别无选择,以应对中国对我们东南亚人的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我们可能还将继续面对几十年”。参见:D.Rajendran,ASEAN′s Foreign Relations:A Shift to Collective Action,(Kuala Lumpur:arenabukul sdn.bhd.),p.17.由此中国的东南亚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历史上最恶劣的境地。
这一阶段以“世界革命”为特征的价值目标与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以及中共领导集体关于整体世界形势及东南亚地区形势的阶段性和局部性误判,加之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共同促成。⑮可参见: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Kuo-kang Shao,Zhou Enlai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New York:St.Martin′s,1996).对应于国内政治,这一时期大致确立了一种东南亚区域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情所淹没。⑯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6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出来的中共领导人,是充满激情和使命感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⑰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在一段时间内把国际社会(首先是亚非拉地区)建设成一个道德统一体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泰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各弱小国家的关系上喜欢讲‘义气’。不论是毛泽东或者邓小平当领导的年代都有这种作风……中国不能眼看着其近邻‘弟子’被西方列强霸占;中国亦不能容忍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欺凌其友邦(或许是‘弟子’)柬埔寨……中国把这种政策称之为反对霸权主义。问题在于中国在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时候过了火,那么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自己也难免其嫌了。”⑱强·提拉逸著,刘源泓译:《中国外交政策》,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2001年版,第20页。引自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7页。这种诉诸于国际正义的意识形态冲动使得客观上中国在区域体系内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成为所谓的国际社会边界之外“修正主义国家”。
革命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存在一种有形或无形、政治或经济上的等级结构,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结构中处于一种不公正的弱势地位。这种理论假设折射出革命主义者对正义(主要是国际正义)的强烈关注。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或无产阶级则付出太多而获得太少,他们对这种情况深感痛心并力主改变。⑲李开盛:前引文,第54页。因此革命主义者希望看到的是权利义务能够在发达国家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之间重新分配。于是,中国的东南亚区域治理及其价值目标逐渐偏向政治光谱中的左端。
(二)1979~2009年
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上反帝反殖运动的退潮,“在国际政治中思考正义是一件特别令人感到挫败的事情”,“很少有证据显示,正义在政治家和政治领导人的考虑中发挥了实际作用。”⑳Moorhead Wright.“Thinking About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illiam Clinton Olson ed.,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ight Edition),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91。转引自李开盛:前引文,第56页。在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重要调整,如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实行对外开放;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革命输出;实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等。㉑此类研究可参见张明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71-76页;任晓:《经验与理念——中国对外政策思想三十年的发展及其意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36-45页。这些改变带来了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行为的重大转向,从1979年开始,中国逐步建立健全与东盟开展经贸关系的合作机制;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2003年中国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与此同时一些隐忧同样浮现出来。
冷战后期,中国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在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一起反对越南,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越南问题所掩盖。而在1991年柬埔寨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与中国直接的矛盾冲突成为双方关系的焦点之一,㉒王子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时事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76页。如南海岛礁问题;同时,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在东南亚撤军的可能性加大,突出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力量等,这一切加重了中国未来行为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时间不久,对多边国际制度的运用尚欠圆熟,中国一般奉行工具性多边主义战略(instrumental multilateralism strategy),将多边国际制度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体现出选择性或工具性的特征。㉓门洪华:《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223页。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是消极而游离的。中国官方在1999年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发表过对亚洲经济和安全的系统看法。㉔庞中英:《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30-35页。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地区战略走向高度关注,普遍担心中国主导地区合作事务。
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主要就该地区的“秩序”问题展开互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对周边地区和平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大,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和主导的区域治理模式,即在政策行为上突出以经济换稳定,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基本表现为逆差,这一特征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后变得更为明显,据测算,从2001-2009年中国对东盟国家逆差总额约为1727亿美元。对于东盟部分国家来说,巨大的贸易顺差极大的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逆差情况直到2012年才开始好转。可参见:刘一姣:《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中的竞合》,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65-67页。以战略保证缓解争端纠纷,以增信释疑稀释不安猜忌,支持东盟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保证东南亚地区的大致秩序。然而,中国在这一时期对“秩序”内涵中“稳定”的过分关注导致目标结构一定的不平衡。在政治军事诸传统安全领域以及部分非传统安全领域缺乏信任的情形下,中国的这种过分关注以及试图减少紧张性的自我否认姿态很容易被东南亚国家误读或曲解。中国近年来对东南亚国家一再的“战略保证”和增信释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论”,解决现有的安全争端就部分说明了这一点。如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就公开说“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新加坡、泰国则对东南亚地区安全表示忧虑。㉖罗杰:《东南亚国家如何看“中国威胁论”》,载《亚太参考》1997年第5期。总之,中国为确保南部边疆的稳定以及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有影响力大国的存在地位,以经济反哺安全、以贸易支持稳定,在国内外都留下了一个“示弱”的形象。
中国在建国以后的两段历史时期中,在东南亚区域治理的价值目标没有脱离对“正义”和“秩序”的基本叙述,但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建构起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国情及人类基本道德的东南亚区域治理价值目标。
三、底线特质、责任伦理、共同命运:建构新型的区域治理价值目标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阶段,中国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的价值目标包含着不同的成分,进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治理失序。就新时期中国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而言,其价值目标不仅仅要追求安全和经济合作,同时还应对文化和价值联通提出需求。
(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在国际上,一方面,东盟对其在东南亚区域治理的角色认知愈发清晰。2015年12月31日,以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东南亚形成一个人口超6亿、经济总量超2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并且预计到2020年,内部贸易占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将从目前的25%提升至30%。㉗“东盟共同体成立意味什么”,ht t p://news.xinhuanet.com/wor l d/2015-12/31/c_1117640667. htm。(上网时间:2016年10月10日)东盟采取照顾各方舒适度、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并坚持其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大国角逐东南亚的竞争愈发激烈。美国2010年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订单外交”有声有色,《2005~2015年推进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行动计划》进入收官阶段;日本以ODA为先行军,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取得提升政治大国地位和拉近民心之效,并在重要议题上与美国保持大致一致;印度将“东向”战略推向纵深,与东南亚国家在各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大国的因素使得东南亚各国和东盟大体上发挥“大国平衡手”和“政治上的调解人”(Political Middlement)㉘Evelyn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13-157。的作用,但不可预测的事件仍有可能促使其在某一阶段采取“选边站”策略。
在国内,2009年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的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㉙这可表现在中国手握相当于印度、韩国和泰国三国名义G D P总和以及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当量的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巨额经济体量已经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砝码。可参见:Evan A.Feigenbaum,The New Asian Order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Fits In,Foreign Affairs,2015.05,p.6。党中央加强外交顶层设计,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展开新的周边外交布局。同时在东南亚区域治理问题上面临新的挑战:经济上,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增长点不断涌现,但围绕贸易差额、产业结构等矛盾点同时增加;政治上,双边与多边往来更加频繁,但中国的“安全困境症”和“大国焦虑症”并存并发。中国的东南亚区域治理战略逐渐由过去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为主,改变为政治、经贸、安全、文化和生态多元合作并举。
内外情势的变化要求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的价值目标明晰化,并带有递进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特征,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度来擘画区域治理格局。
(二)区域治理价值目标的选择及其建构路径
区域治理从本源上讲是一种危机管理策略,从解决本国经济困难、对外贸易赤字和避免与邻国战争开始,久而久之上升为一种发展与合作的策略,当进入发展与合作的深度之后,文化整合的要求就时隐时现。㉚郭树勇:《区域治理理论与中国外交定位》,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2期,第48页。据此,区域治理分为“共创经济利益——共担发展责任——共享文化价值”三个层次。对应于区域治理的价值目标,即构成了以共创经济利益为标志的底线特质、以共担发展责任为标志的责任伦理和以共享文化价值为标志的共同命运,三个层次层层递进,彼此关联。
1.以底线特质为内核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底线价值具有最为广泛的认同空间。从价值结构特质上讲,底线价值既可以是各种价值体系、价值观念、价值主张、价值传统都可能认可的价值,也可以是理想价值、制度价值和生活价值共同实践的价值规范。这就注定了底线价值是一种人类之构成人类活动的不可突破的底线原则,它源自于人类活动的共同结构、相似经历和应付环境的共同处境。㉛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0页。这一价值目标就是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及多边关系的多年经营上打造利益共同体。国家与国家/地区交往的最直接动力来自于利益,共同的利益最易成为价值体系大厦中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中国外交话语中的“不”字句式体现了维护利益的底线思维与底线价值。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们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㉜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于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而言,就是在保持这些底线的前提下开展双边及多边外交,共谋发展。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内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中国倡导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各国建立互信机制,通过战略合作机制争取共同安全,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求同存异,通过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解决事关世界与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即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㉝黄仁伟:《新安全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增刊,第24-29页。当前,能够体现共同利益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一般认为CAFTA开启并加速了中国区域战略的实施。随着2010年1月1日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仅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9.3%,自东盟进口增长5.3%。中国与东盟进出口额达到3466亿美元,占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比重总额的11%,接近美国的13%和欧盟的15%。㉞“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4年秋季)”,http://zhs.mo f com.gov.cn/article/cbw/201411/ 20141100787624.shtm l。(上网时间:2016年10月10日)2015年一季度,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20.6%,㉟“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5年春季)”,h t t p://zhs.m of com.gov.cn/article/Nocat ego r y/ 201505/20150500961512.shtml。(上网时间:2016年10月10日)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保证了双边治理单位之间的平等关系,并体现协同合作的“治理精神”。这种经济层面的互利共赢体现了共创经济利益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最基础的特征。
就今后一段时期底线价值的实现路径来说,应以构建“中国-东南亚共通体”为主要方式,“共通体”㊱关于共通体的阐释,更多可参见[法]让吕克南希著,夏可君等译:《解构的共通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的建立会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上拥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现在各种类型的“共同体”更多展示的是一致性,或者说是差异性的消除,其资源分配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而“共通体”更多展示的是协调性,或是在协调与沟通的基础上逐步克服差异性的消极影响并力图寻求一致性,其特征是差异性团结,㊲高奇琦:《民族区域与共通体:欧洲转型的两个阶段》,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第40-41页。这种不涉及主权让渡、集体安全的“共通体”具备了中国在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底线价值特质,可以成为促进中国深度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基本前提。
2.以责任伦理为内核的中坚价值目标
所谓“责任伦理”就是“以信念为前提,但现实地寻求相关政策的可预期的后果,以及特别是那些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并对它们负责”。㊳汉斯·昆著,张庆熊等:《世界伦理新探—为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世界伦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年。它的本质是将现代现实政治的政治计算与理想政治的伦理判断结合起来,而又志于超越两者的局限性。㊴孙章季、崔杰通:《国际关系伦理分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7页。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于东南亚就是中国如何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承担起促进东南亚区域繁荣、维护东南亚区域安全稳定责任的战略,构建责任共同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责任仍应主要是区域治理责任。中国努力成为该区域的“负责任大国”,是顺应潮流、主动承担责任的国家诉求与建构,这既是中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切入点,还是中国国家利益走向全球化的重要路径。㊵门洪华:《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198页。同时也是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决不允许在我们自己家门口生乱生事,绝不接受中国的发展进程再度受到干扰和打断…”㊶中共中央宣传部:前引书,第153页。的重要举措。
因此,制度建设对于成为“负责任大国”显得至关重要。中国积极参与了与东南亚国家的一系列基于合作原则和共识的多边制度建设,“这些制度…为中国及其邻国提供了和平共处并缓解潜在冲突的机制,从而大大改变了此前中国相对孤立的处境,为中国提供了进行制度化合作的经验。”㊷Michael Yahuda,“The Evolving Asian Order,”in David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347.责任伦理要求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多边关系中,责任需要认真厘清、共同划定、共同承担。中国向来注重“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构,在多次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中努力塑造“更负责任”的形象,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宣布人民币不贬值,2004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外援参与印尼海啸的救灾等,在该地区塑造自己负责任大国形象,但一定时期内在诸如湄公河水资源问题、SARS疫情防治问题上出现的形象受损问题则又影响了责任伦理的铺开。今后,中国可以主持多方面治理议题的进程,突出解决东南亚国家关心的贫困、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跨国犯罪等问题,使国家信任度更高。因此,将“责任伦理”作为价值目标的中坚力量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3.以共同命运为内核的远景价值目标
温特将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个人)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个人身份是对自我的根本认知,是其他身份的基础,类属身份对应着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角色身份生成于与他者的关系中,比如无政府文化中的“朋友”、“敌人”关系,而集体身份则将国家归于某一认同。㊸[美]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8页。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而言,其各自的角色身份是在区域治理过程中通过控制争端、增进对话、改善相互关系来确认的,而集体身份则是在治理过程中建立认同,赋予各国共同体感和归属感,而这种共同体感和归属感的最大集合就是所谓的“共同命运”。
“共同命运”借助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而在区域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上都有体现。从《论语·卫灵公》中体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黄金律”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到《孟子·尽心上》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再到《古今贤文》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㊹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表达均被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于外交事务的一系列论述当中,体现了关于“共同命运”的东方智慧。可参见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第182页、第201页、第187页。是中国人对于多元化的世界和文明的一种理想表达,亦是对天下共同命运的追求。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于此种价值目标的阐述有一个不断递进和抵达的过程。
2005年4 月在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的亚非峰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问题,进而提出其系统理念。温家宝总理随后进一步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谐世界”理念以安全、发展、和谐三个概念为核心,将中国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和新秩序观等战略思维有机结合起来。
2013年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到,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要在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和开放包容这五个方面做出努力,以“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心态打造共同命运。㊺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2-295页。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表示各国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㊻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423/c70731-26889779.html。(上网时间:2016年10月10日)。
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的这一“共同命运”的价值远景表达,体现了中国主动根据自身实力、国际环境来更为积极地参与区域规范和世界伦理的创建、维护以及提升,并且契合了东盟内部建设共同体的愿景。㊼当前东盟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来规划和引导三种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制和命令式的管治模式逐渐向多中心的、自主的和协作的治理模式过渡。在“共同命运”价值体系建设上,一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地区合作与制度建设上应该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双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同等的重视,共同的规范能够同等的体现各方的政治意愿、民族文化并得到共同的遵守,“命运相系”的价值理念能够在各方中生长。另一方面,中国-东南亚区域的“共同命运”应立基于该区域的实际情况,要防止出现“共同命运”价值体系的习得性依赖,将一些已经成型的共同体诸如美欧联盟或欧盟的成长过程当作本地区产生共同体的唯一道路,甚至是简单膜拜。㊽美欧联盟是一种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法制等价值理念的文明共同体。具体可参见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Summer,2002),pp.575-607。
综上所述,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价值目标基于实力、制度和文化因素,形成了以底线特质为内核的基础性价值目标、以责任伦理为内核的中坚价值目标以及以共同命运为内核的远景价值目标,能够并行不悖,各有侧重,指导着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开展。
四、结语:价值目标的“最大公约数”
在新中国建国60多年来与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互动行为中,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存在着较强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价值目标,对中国的国家建设、国家形象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需要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上建构自己的价值目标。
本文认为,一种以底线特质为内核的基础性价值目标、以责任伦理为内核的中坚价值目标以及以共同命运为内核的远景价值目标可以构成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价值目标的“最大公约数”并呈现出三个层次,这三类价值目标在时空象限上具有同时性,在逻辑理路上具有递进性,是中国东南亚区域治理价值目的现实性和理想化相糅合的表达方式,将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及东南亚区域利益的维护及延展,从而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区域中真正的做到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保障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和平与稳定,促成“两个百年”目标的顺利实现。
汪炜,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