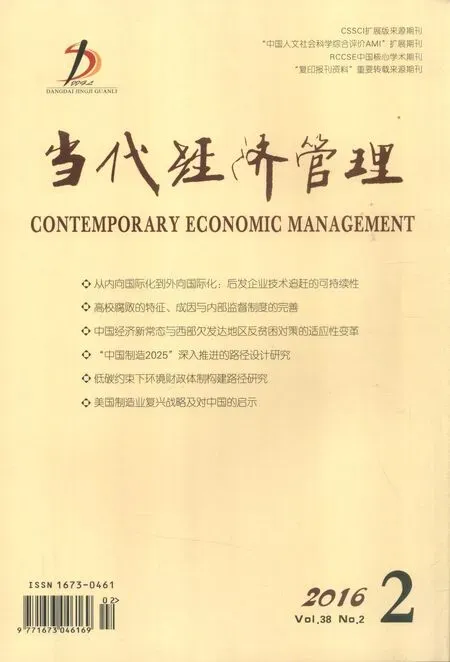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对策的适应性变革
■姜英华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对策的适应性变革
■姜英华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贫困是关乎民族国家发展前途的世界性难题,贫困的消除和反贫困对策的制定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步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新任务,适时调整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策略,提高反贫困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意义。
[关键词]新常态;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策略
网络出版网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201.1137.009.html网络出版时间:2016-2-1 11:37:33
“两个一百年”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西部①欠发达地区贫困的消除和反贫困对策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途径。目前,我国步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处于新阶段和新形态,伴随宏观经济条件的变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对于反贫困对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制定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的因应之策,提高反贫困政策的针对性、时效性和绩效,对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意义。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于2002年前后屡屡见诸国际媒体,作为经济术语,“新常态”最早用以描述经济反常现象的常态化。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总裁埃里安最早用“新常态”概念阐述经历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新特征和新走势,即肇始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由于超高消费、随意冒险、过度负债和信贷扩张导致经济系统内部严重破损,一反V字形快速复苏的常态,陷入长期低迷疲软、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负担加重、不平等加剧的困境无法自拔。2013年美国劳动统计局(BLS)正式发布题为《2022年的美国经济:通向新常态》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出现新的转机,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也将从1.6%恢复到2.6%。在中国,“新常态”(New Normal)成为描述经济发展形势的高频词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发展特征做出的科学论断。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用“新常态”来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总格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上,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目标和方向。
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丰富、维度广泛、意义深远,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质量、经济调控方式、经济转型升级、经济改革活力等6个方面,具体而言:
(一)经济增长速度中高换挡
“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从已有的经济成绩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8%的高速水平,超出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2.8%)3倍多。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高出日本4 044亿美元的实力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以人均国民总收入5 680美元的世界银行标准跻身于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和提高,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阶段。从现有的经济状况来看,中国经济进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阶段,从偏重高速低质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向追求中速优质内涵式增长模式过渡,要求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增效益、固基础、利长远的节奏和步伐,将经济增长保持在防止通货膨胀的“上限”和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之间。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维持在7%~9%的弹性区间内,为经济发展的转型留下充足的空间。从未来的经济目标来看,维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说不能,主要是因为以耗费和牺牲资源能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说不为,主要是因为根据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充分测算,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年均增速维持在7%就足够了。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7.4%的经济增长率仍在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内,因而无需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超高速,而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质量升级。
(二)经济结构调整提质增效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低质的速度型向提质增效的优质型迈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发展情况的倒逼机制更加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刻不容缓和势在必行。从产业内部结构来说,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新变化,2013年以服务业为表征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占比达到46.1%,第三产业的增速和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为三大产业的结构优化和新兴产业的战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服务业新兴业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中国正在从制造业主导的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转型。同时,部分行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制约瓶颈正在得到有效缓解,2014年上半年,钢铁、电解铝等行业投资同比下降8.4%和31%,遏制了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过度发展,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异质性和互益性的产业结构升级。从消费需求结构来说,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强化居民需求导向,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建立刺激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取得初步成效。我国国民经济需求结构正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消费需求拉动方向转变。从区域经济结构来说,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创新发展效果显著,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制度创新优势持续增强,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接续跟进,以及其他城市群的建设和崛起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崭新的条件。
(三)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
我国经济已经从单纯追求线性增长向注重科学发展的方面过渡。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时强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经济发展是规律性与合意性统一的结果,首先要以尊重规律为前提。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起点较低,依靠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资本投资政策倾斜的软预算约束以及土地与资源能源的低成本制约,形成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劳动力红利的消减、资本预算的硬性约束以及其他要素供给的趋紧,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致使一定时期内经济潜在增长率出现趋缓或回落的趋势。这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主动适应性减速,符合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要以尊重价值为旨归。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标准除了客观规律之外,还要考虑发展的价值导向。不能把增加生产总值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不能一味迷信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排名,不能扭曲发展人本性价值而低估发展的成本和代价,给长远发展留下隐患和后遗症。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趋向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形态。
(四)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
我国经济已经由主要依靠要素供给驱动升级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从国际情况来看,伴随经济的全球化,以科技为核心的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成为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要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获得致胜的比较优势,中国就必须从数量大国转变为科技强国。从国内情况来看,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一般性改革效益的递减,潜藏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原有的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等传统的要素组合无法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根本的出路只能在于科技力量的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通过“破坏性的创造”能力能够牵动创新的制度和管理要素与创新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重新组合,协同合作,催生经济发展新的孵化细胞。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发展将以自主创新为抓手,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形成协同创新的机制体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完善技术集成体系和商业创新模式,冲破要素禀赋的先天束缚和区域地理位置的后天桎梏,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升级。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创新驱动将整合和衔接所有要素,构筑经济质量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持久联动机制,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永续和谐地发展。
(五)经济改革活力深度释放
我国经济已经由全面改革进入到深度改革的重要时期。经济改革是激发经济活力和促进经济进步的关键,是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由增量阶段步入到存量阶段,根本性的变革代替细枝末节的改革已经成为新的发展主题和旋律。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既有的和固化的利益阻滞了改革的步伐,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症结消解着改革的成绩,打破利益集团的掣肘和冲破深度矛盾的阻碍,需要全面深化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进法治化进程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助力。另一方面,经济开放已经由局部区域型提升到全面深化型。区域合作特区、区域连片责任和区域延伸帮扶等区域经济整合措施渐次展开,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对于培育新的经济发展契机提供了保障。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对外“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也是全面贯彻开放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步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补益、延伸扩展的发展阶段。
二、经济新常态条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现状和致贫原因
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和价值偏好的差异,对于贫困内涵的揭示和贫困标准的划定也不尽相同。从贫困理论的发展来看,关于贫困的内涵大致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就业、健康、教育、卫生等关乎社会整体发展的方方面面。随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政治权力、政治参与、普遍人权等新的元素也不断纳入进来。将这些多元的因素整合起来,贫困主要涉及物质匮乏(硬件)和精神贫瘠(软件)两方面,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发展程度,对于我国而言,贫困主要是指“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1]而就全国各大区域发展水平而言,西部欠发达地区又是贫困的多发区和重灾区,这些地区贫困治理的绩效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乎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新时期经济新常态为西部欠发达地区脱离贫困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把握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现状,剖析新条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致贫原因,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打胜反贫困的攻坚战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
就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状况而言,改革开放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各区域的经济获得了飞跃式的提升和发展,西部欠发达地区也已经相继完成由初期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有些地区通过赶超发展也脱掉了特困的帽子,向温饱型和初步小康逼近。根据人的发展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于全国性经济水平和发展程度的提升,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因而向社会提出了富裕、发展等更高层次的要求,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的任务也显得越发困难和紧迫。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对比2014年第一、第二季度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生产总值,东部地区的总值分别达到75 152.75亿元和173 216.64亿元,中部地区的总值也各自达到32 138.12亿元和72 542.91亿元,西部地区第一、第二季度区域总值仅为25 616.46亿元和56 924.1亿元,与东、中部同期相比具有相当的距离。就2014年前三季度三大地区农林牧渔发展的比较情况而言,东、中、西农林牧渔的总产值分别为47 786.5亿元、37 001.3亿元和28 176.5亿元,西部与另两个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加之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偏远落后的农村,很少有额外收入,农林牧渔构成他们全部收入的主要部分,这一现实又扩大了东中西经济发展的实际差距。而对比以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居民消费全年支出、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人均住房及居住条件、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为主要内容的人民生活,西部欠发达地区总体福利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近些年来,西部欠发达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的实践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下一阶段,要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和展开进一步的工作,需要明确自身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提高反贫困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的成效。
造成西部欠发达地区现有发展瓶颈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先天的自然禀赋差异也有后天的循环累积效应,其中“资源环境的决定性制约、经济现状的基础性制约、产业递进的规律性制约、发展环境的体制性制约、社会选择的人本性制约、路径依赖的观念性制约、发展差距的跟从性制约”[2]等全面地厘清了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致贫原因。具体而言,脆弱的生态环境、稀缺的资源能源、深居内陆的地理区位是西部经济起步的前在劣势,耗竭资源的低度开发、破坏生态的粗放循环以及污染环境的偏畸增长加剧了要素环境的恶化,使区域经济在低水平条件下陷入“无未来”恶性循环的困境。生产力落后和经济总量不足造成科学技术投入有限和教育管理的重视不够,进一步割裂了经济发展的连接链条。分散的生产要素相互消解,滚动累积产生负面效应,以倍加的消极作用反馈给自然,增加了经济发展成本,延缓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很长时期以来,西部地区用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制式的人口增长速度弥补了效率低下对经济整体的影响,然而,过度的人口销蚀了新创造的经济成果,形成了经济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的怪圈,即使发达地区转移落后淘汰产业,碍于规避风险的路径依赖观念,西部欠发达地区也无法承接高技术含量的企业,进而迟滞了赶超战略的贯彻落实。
三、经济新常态条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对策的适应性变革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势,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形态,是一切政策措施取得成功的关键。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现状既是经济新形态的表现,也是适应经济新形态从而实现赶超战略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关节。厘清新形态下的致贫原因,变革和创新反贫困对策和机制,是化解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的一种尝试性试验,对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反贫困的对策机制
有效的预防和治理对策,对于减少贫困的发生几率和有效治理贫困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经济新常态的常态化为生态反贫困、教育反贫困、发展反贫困等反贫困对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新的场域和机会。对于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和利益诉求来讲,贫困的未然防范不啻于贫困的已然治理。随着和谐理念由宏观化到具象化到细量化的发展,防范型反贫困对策替代补救型反贫困对策有针对性地减少了西部欠发达地区原有贫困的基数,遏制了贫困的范围扩散和强度加深。在防范贫困的同时,培育发展型反贫困对策,用动态发展的办法解决在发展中可能导致的贫困问题。同时,反贫困政策的动态—针对性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要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期,经过60年的反贫困努力,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8%,人口规模也从2000年的9 423万减少到3 597万,经济增长对反贫困的正面效应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成果。为了强化反贫困链条的完整性,防止贫困的复发,针对贫困—脱贫—返贫—持续贫困—代际遗传的现象,要强化彻底脱贫的成果,杜绝返贫的可能,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使反贫困政策能够发挥持久的效力,比如,对于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和非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要区别对待,对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分散贫困区域要分块解决,对于由于致贫原因不同而产生的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脆弱性贫困,要制定不同的针对性措施进行救治。由于贫困的惯性和顽固性,单一的扶助政策效用有限,要制定功能互补的多重复合政策,将政策的持久性与阶段性、常规性与专项性、暂时遏止和长期根除相结合,从发生源上减少和杜绝贫困,在经济发展的动态中发掘治理贫困的有效对策。
(二)激活反贫困的合作机制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贫困的产生既有资源、能源、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原因,也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贫困的情况关乎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命运和福祉,因此需要构建多元参与的活动机制和综合治理的合作机制。新时期,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民主政治的法治化进程要求政府、市场、企业、个人之间边界清晰,体现在贫困治理过程之中,就是遵循和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和规律,政府发挥国家财政和宏观调控的作用,财政支出科学调度,定向调控精准发力,为贫困治理提供坚强保障。但是政府单一治理模式会加重政府负担,也不符合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因此要加强各种力量之间的横向分工协作,综合利用经济、法律、管理、文化等各种政策工具和治理工具,化解贫困产生的风险。聚集社会力量,建立扶贫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协调反贫困的力量;强化企业责任,扩大企业的正外部性,融合反贫困的能力;发挥个体智慧,培育反贫困的内在动力,激活合作机制的活力,形成多元参与的大扶贫格局。除此之外,还可以借鉴对口援建,加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海外地区与贫困地区的联系、交流与学习,通过引智、引技、引资助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反贫困,缩短落后地区发展建设的周期,减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也为先进地区的组织、企业推广成功经验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在合作中相互传递和补益,共同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形成反贫困的合作联盟。
(三)培育反贫困的内生机制
培育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的内生机制是完善反贫困政策机制和激活反贫困合作机制的重要目标。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向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表现之一,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最大的潜在消费族群,日益生长的消费预期与落后贫穷的发展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凸显了将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如此,就必须培育反贫困主体的自主能力。以往去贫困化政策多是人道主义的救济,作为嵌入式的“输血”方式无法彻底根除贫困的病兆,往往形成“二次处境变差”的遗憾结局。为了巩固反贫困的治理效果,就要培育西部欠发达地区内植式的“造血”功能,提升自身对贫困的免疫力,抓住反贫困的内在机理,从内部蕴生出反贫困的主体功能,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改变,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的发生。随着粗放外延型经济增长红利的消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要素的分化组合带来了集中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时期,适应这一模式的变迁,传统以集中化为条件的开发式扶贫方式不适应贫困的分散化和选择性现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修复周期长、见效慢,而社会资本快速的增殖能力和人力资本倍增的增长效益不仅能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扩大经济发展的容量,提升经济发展的人本性,而且能够为自然恢复争取更充裕的时间,增强各生产要素的平滑粘连和整体效益。因此,反贫困内生机制需要向以培育积累和储蓄为主的内生资本及提升教育和管理为主的人力资本方向转化,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反哺自然环境,实现反贫困效果的帕累托改进。
(四)创新反贫困的制度机制
贫困的产生和演变基于一定的制度框架,贫困的消减和去除也需要良好的制度依托,尤其是好的制度能够保证完善的对策、紧密的组织以及坚强的内生机制相互衔接与契合,从而形成治理贫困的最大合力。
制度是制约贫困产生和扩展的内生因素,过去贫困治理由政策性过渡到制度创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国家主导型的贫困治理路径在前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加之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经济发展主题的变化,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迎合了新时期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民主自治制度的确立、社会资本建设制度的形成以及个人资本账户制度和反贫困法的呼吁构成了益贫式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贫困治理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展开。具体而言,建立纠正制度,纠正以GDP论英雄的短期行为,树立重大扶贫决策和项目的终身追责和倒查制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及区际恶性竞争,加强反贫困的地方合作与联合。实行保底制度,“构建囊括普遍性保障、普惠型福利、选择性救助在内的层次化的社保体系”[3],统筹兼顾各个范围和层次的贫困问题。构建发展制度,建设社会资本制度和个人资产账户制度,维护和赋予人的发展权利和能力,更加公平地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巩固民主制度,畅通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拓宽贫困地区人民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渠道,通过调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壮大自助的能力,满足他们过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出台《反贫困法》,将贫困治理纳入到法治化和规范化轨道,确保法律的公正和程序的公开,巩固去贫困化的效果。
(五)构建反贫困的监测机制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反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个环节的实施都会影响到反贫困的整体效果,为了防范期间的不可控因素和防止偏离目标的行为举措,就需要建立严格的约束监控机制,包括事前的追踪调查约束、事后的成果评估约束以及贯穿整个脱贫过程的调控纠偏约束,约束要兼顾现实要求和环境因素的变化,明确实施规则和细则,保持指标体系与环境实况之间的弹性。
构建反贫困的监测机制,首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现实进行监测。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集团在制定反贫困方案之前,要借助一定的技术和量度工具,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规范的组织系统对于贫困主体的状况进行动态的追踪调查和分析评价,为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的依据。其次,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过程进行监督调控。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包括价值目标、过程指标和成果鉴定,为了确保反贫困目标的实现,对过程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贫困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反贫困政策也要根据贫困的动态发展做出变化,同时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偏离价值目标的举措进行调整,使其满足价值目标的追求顺利展开,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反贫困结果进行评估巩固。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为了防止脱贫地区和人口再度陷入贫困,形成长期贫困或恶性贫困,必须对反贫困的阶段性成果进行评价和巩固,评价标准和巩固方案应该是多重的,既包括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也包括教育、培训、劳动工作等生存能力的培育、还包括分权、民主、参与等发展权利的提升。
[注释]
①文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区、市)。
[参考文献]
[1]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1994(3):87.
[2]姜英华,王维平.破解西部欠发达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制约因素的现实路径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4(8):75-77.
[3]郭佩霞,邓晓丽.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4(3):112.
(责任编辑:李萌)
The "New Normal"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Anti-poverty Strategies of the Wester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Jiang Yinghua
(School of the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Poverty is a worldwide problem concerning about the futur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ties. Poverty eliminating and themaking of the anti -poverty strategies are historically and realistically significan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urrently,our countr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s at a critical phase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well -off society. It is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realizing of the "two a -hundred-year" goal,that we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and the new task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imely adjust the anti-poverty strategies of the wester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nti-poverty policies.
Key words:new normal;western underdeveloped regions;anti -poverty strategies
作者简介:姜英华(1985-),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本论>的批判视界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15LZUJBWYJ020)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7-13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2.009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2-004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