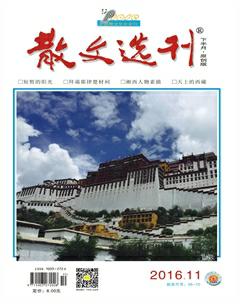姨父的爱情
褚福海
晨曦微露,睡意蒙眬的我隐约听见姨父粗犷的大嗓门,便一个激灵从躺椅上坐起,抬腕看了下表,时针指在6点8分。
“姨父早!”我似醒非醒,说话嗡嗡的。
“唉,女婿啊,我急得夜里哪能也困不着觉。好不容易熬到四点钟,要紧爬起身,烧了个丝瓜蛋汤,拿来给你姨妈吃。”
汤,虽不是给我吃的,可我心里倏地暖暖的。
姨妈时年八十五岁。
今年的中秋或算是个多事之秋。那一日,姨妈午休起来,试图去开电视机,顺带拿盒牛奶喝,谁知坐在床边刚站到地上,头一晕眩,一个踉跄,“啪”地摔倒了。在隔壁房间的姨父听见动静,赶忙蹒跚着过来察看情况,但见老太太侧卧在地上,嘴里直哼哼……120救护车一路呼啸着疾驰向市第二人民医院而去。尽管只是在自己房内摔了一跤,可还是把姨妈疏松脆弱的髋关节给摔断裂了。经与医生沟通探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决定施行复位固定手术。
然,姨妈的生理指标暂不适宜手术,需调养一些时日好转后才可动刀。于是,每天不停地输血,挂盐水。姨妈被伤筋动骨后,疼痛得无法动弹,只能躺在病榻上痛苦地呻吟。当然,小辈们陪夜的陪夜,值守的值守,按摩的按摩,拳拳孝心让姨妈甚感欣慰,冲淡了疼痛的程度。姨妈入院后,姨父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恨不能为姨妈消除病痛。心挂老伴的姨父,远离市区,年岁又大,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每日清早,手拎马甲袋,带上姨妈喜欢吃的食物,颤颤巍巍地坐公交来病房看望陪伴老伴。
十三个朝夕一晃而过,姨父依然如故,每日按时出现,始终未曾中断。隔壁的病友或家属看到姨父去,有时带些调侃地戏谑道:“今天又烧什么好东西给你老娘子吃的呀?”每逢那时,憨厚的姨父便坦言:“我呐实在烧不像,就学着老太太,依样画葫芦,炖了个草鸡蛋。”一边说着,一边轻缓地坐到姨妈旁边,端起餐盒,手执调羹,舀起一勺蛋羹,轻轻吹了吹,动作有些僵硬地送至姨妈嘴里。喂完鸡蛋,老实巴交的姨父开始略显不安,而后淡定地伸出右手,佝偻着背,隔着被单,在姨妈的那条坏腿上轻抚慢掳,我扫视了一眼姨妈,分明瞥见姨妈那沟壑纵深的脸上绽满了笑意……
相濡以沫了一个甲子的姨父姨妈,从未有过甜蜜浪漫的举动,可他们却能从对方的一个眼神,甚至是一缕表情里读懂对方,彼此契合得严丝合缝。
姨妈手术那日,姨父天没亮就赶到病房,紧握着姨妈枯槁的手,低声细语地宽慰着姨妈。推车进来的瞬间,姨父骤然局促了起来,不过,旋即就镇定了下来,几乎是一路小跑,抚着推车追到手术室,傻傻地守在门外,等候他老伴出来……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