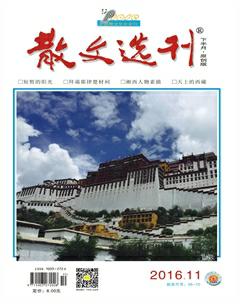父亲的呢裤
江雪
那一年,父亲24岁,年轻、英俊。
5月,父亲结婚了,娶了母亲。10月,父亲由驻东北的某部队调到成都某部队,成为了成都飞机场的一名飞行员。
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在北京转车。北京是大都市,是皇帝曾经坐天下的地方。等车的间隙,父亲与战友们一起在北京城转。我不知道是西单还是王府井,反正,那天,他的战友们在商城里看上了一条呢裤——深蓝色,厚重、展括,当时最流行的样式。父亲的战友们一个个试穿了起来,穿惯了宽大的军装,呢裤上身,果然一个个越发英姿飒爽。
“40元一条!”售货员说。
“40元就40元吧,只要穿了好看。”“这是咱山西肯定没有的稀罕货,成都也未必有。”“这是皇城根,不能错过了;再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留些纪念也是好的。”父亲的战友一个个开始掏腰包。
父亲很帅,是标准的中国美男子,那时候父亲当兵的津贴是每月6块钱;调到成都后,津贴调高了,是每月37块钱。父亲当兵走的第二年,奶奶去世,埋葬奶奶,父亲已经背上了债。之后,父亲娶母亲,又花了100多块钱彩礼,彩礼的来源仍旧是父亲攒的津贴和借来的钱。
面对那条呢裤,父亲一定犹豫了好久,父亲口袋里没有钱,还背着累累债务。父亲的战友,后来与父亲一起转业回到山西的刘土城叔叔,看父亲犹豫,便用手捅捅愣着的父亲,说:“老李,你也买一条吧!”
父亲闷闷地说:“算了,我不买了,你们买吧。”
刘叔叔说:“瞧你,咱到了成都也不能总穿军装啊!这么熨帖的裤子,不买会后悔的。是不是带的钱不够?钱不够我先给你出!来来来,再拿一条……”
1959年春节前夕,母亲从山西辗转到成都与父亲相聚,父亲就是穿着这条呢裤迎接的母亲。回到部队,父亲赶紧把裤子脱下来,小心翼翼地叠整齐了,放进了衣箱。
那年的春节,呢裤还算是崭新的,是一件真正的春节的新装。
在老家,父亲是继子。爷爷虽健在,但父亲深刻记得,他是长兄。
二叔要娶媳妇了,爷爷捎信来,要钱。母亲不止一次回忆说,你二爸娶你二娘时,花的钱全部是你爸寄来的。你二娘里外三新,皮鞋、大衣,什么时兴买什么,你爸生怕委屈了你二娘,不满意,不嫁他弟弟。你们知道我那件绒大衣吧,就是你爸给你二娘买了,他那些战友看不过眼了,说这要是捎回家,让嫂子看见,心里不难受?你好歹给嫂子也买一件,你爸才给我买的……
1968年,为照顾家里,父亲听从爷爷建议,转业到山西的一家兵工企业。
那年腊月,三叔要结婚了。一个寒冷的飘雪的黄昏,祖父、二叔、三叔将父亲母亲在老院住的“北一间”里的铺盖卷抱出来,狠狠扔到了院子里,爷爷放出话来——不给仁顺(三叔的名字)筹好娶媳妇的钱,就别想进这个家!村里干部调解不下,父亲不得已,只好带着刚刚出生怀抱着二姐的母亲、7岁的哥哥和3岁的大姐到他工作的淮海厂附近,赁了一间民房。
家总得回。筹够了三叔娶妻的钱,父亲母亲总算有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北一间”的家。
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哥哥因为小小的痢疾夭折了。
母亲疯了,满天满地疯跑,呼唤着哥哥的名字,寻找哥哥,见人就问:“见到我家鹏慧了吗?”
哥哥的夭折,坚定了父亲再生一个男孩的决心。我是哥哥死后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但我是个女孩儿,接着是大妹、小妹。儿多母受苦,父亲瘦弱的脊背上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穷”字,一直没有翻过身来。
1974年,父亲在外祖父的资助下,千难万难,东挪西借,终于“独立”了出来,在村里批下的新址上盖起了4间半“砖挂脸”土坯房,父亲也背了900多块钱的债务。
“光屁股孩儿,盼年年儿,盼到年年儿穿花鞋儿……不论怎么难,孩子们过年的衣服,必须准备好!”父亲对母亲说。
每年春节,母亲都会将父亲的工资打点又打点,精打细算出为我们添置新衣服的钱来,不论是扯了布料让裁缝做,还是买现成的新衣服,母亲都会早早将五套新衣服准备好,锁好扣眼,钉好扣子,让我们试穿一下后,锁在那口巨大的黑色的木箱里。那时的春节是掐着手指一天一天盼来的。到了除夕夜,母亲打开那口黑色木箱的锁,将五套衣服取出来,分发给我们。我们欣喜如狂,再一次试穿、照镜子、扭来扭去、互相欣赏、评价,直到嬉闹累了,才会枕着新衣服甜美入睡!
那时的春节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终于,除夕夜那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鞭炮声,还是会给这一天带来很多快乐。我们在一声声划破天际的鞭炮声中醒来,母亲不用担心我们会赖床,我们嘻嘻哈哈抓起枕边的新衣服开始往身上套。父亲也起来了,点燃了年火,燃放了鞭炮,回到屋子里,打开了他那口边沿磨得毛乎乎的黑色皮箱。我从来没关心过春节那天父亲、母亲穿什么。从我记事起,一年一年,春节那天清晨,父亲都会打开他那口磨花了边的黑色皮箱,拿出那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深蓝色呢裤来,穿在身上。拜年、挣压岁钱,拣未炸响的小炮,吃煮了饺子和肉丸的川汤,然后,跟村里一大群孩子一起,跟在锣鼓队后面,给一家家军属去拜年,送年画。
父亲在部队上学会了吹笛子,父亲也是拜年队伍中的一员。父亲一辈子没吃胖过,任何时候穿了那条呢裤,都显得那么得体、合适、精神、好看。
夜晚来临的时候,父亲从棉裤上褪下呢裤,照着裤缝,叠整齐了,用手将每一个小褶皱细心地摩挲平,然后,小心翼翼放入皮箱。再穿上它,就是一年后的春节了。
1993年夏天,大妹结婚,妹夫入赘我家。1995年正月初九,为我们遮风避雨的四间半房被拆倒,父亲想给大妹建五间崭新的二层瓦房。就在这时,妹妹因为与妹夫吵架引发了一场灾难,妹夫动用他本村三个舅舅的四辆拖拉机,一直开到了我家老屋前,宣称,不把新房产权写到妹夫名下,就把堆放在路边的建筑材料全部拉走!
工程不得不停下。一眼明了的官司,因为妹夫的舅舅是村长,千辛万苦地打了半年。旧房拆了,新房未盖,所有的建筑材料堆在路边,父亲不放心哪。父亲就睡在四面透风、春寒料峭的门洞里,入夏后,官司终于打赢,工程重新开始。房子一盖好,没等干一干,父亲、母亲便住了进去。
那年秋天,父亲的脚开始红肿。经过很多乡医、医院医生的诊治,父亲患的是脉管炎。父亲苦汤苦水吃了大量药物,还是没能挽救了他的腿。烂骨的疼痛让要强的父亲不得不下了截肢的决心。2002年6月19日,父亲失去右腿;2006年正月十一,父亲失去了最后一条腿!
父亲最后的生命几乎全部用来与疾病抗争了。他什么也舍不得买,退休金几乎全部用来吃药了。一件普通的白衬衣,父亲能穿10年,直到衣服薄如蝉翼,一触即破;1985年,大姐大学毕业时,给父亲买来一件丝质半袖,父亲一直舍不得穿,叠整齐收在那个黑色的皮箱里,有事时才肯拿出来穿一下;2000年春节,我在集贸市场花了60元钱给父亲买了一条裤子,父亲看看,慢慢说,以后,不要瞎花钱,你正困难哩,然后,叠好,也收在了他的皮箱里。
最后的日子里,失去的了双腿的父亲更加不在意穿什么过年了。他再不需要在除夕夜打开皮箱,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条呢裤,将呢裤展展挂挂地穿在腿上了——父亲已经没有了腿!
2006年5月,父亲出院刚刚3个多月,母亲遭遇了一场意外的车祸。少不更事的我们在父亲生病的几年里已经麻木,依旧忙于上班、生计、照顾母亲,而将刚刚失去最后一条腿的父亲一个人扔在了家里……
父亲大大小小住了七八次医院,失去了两条曾经走南闯北的腿,父亲的两个弟弟没有一个来看望过他。
2006年农历六月二十九,父亲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深深遗憾和绝望去世了。
为父亲装殓时,我把后来为父亲买的衬衣、那条新裤子放在了父亲身边。母亲嘱咐我,带毛的东西不要放进去——于是,那条呢裤留了下来。
2016年清明节,我们为父亲烧10周年纸,母亲找出那条呢裤,连同父亲的假肢、毛衣之类,让我拿到村外,烧掉。
我摩挲着呢裤,呢裤屁股处已经磨薄,里面衬了一层布,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一点不知道。在我心里,父亲的呢裤始终是崭新的、展刮的,是父亲的新年装。我嗫嚅说:“能不能留下,留个念想。”母亲说:“烧了吧,你爸钟爱了一辈子的东西。”
那一天,天气很冷,枯瘦的草木在早春的风里凄凄摇动。我拔了几把荒草,用打火机点燃,再把那些东西引燃。最后,我拿出呢裤,放在燃烧的火焰上,火焰立即熄灭了,一股黑烟蛇一般袅娜着升起来……呢裤慢慢引燃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煳的味道。我按照母亲的嘱咐,对着苍黄的天空,对着父亲长眠的坟茔,含着泪,颤抖着轻轻喊:“爸,来收您的呢子裤了……”
父亲,您还会打开皮箱,穿上这条呢裤吗?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