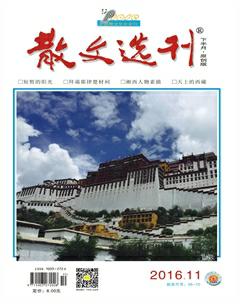陈忠实:大山倒地亦巍然
我知道,忠实先生一辈子没啥业余爱好,就是好抽卷烟,好听几句秦腔,尤其以华阴老腔为甚。先生不会唱,就是喜欢听。每每听到忘情,就会哈哈大笑或是咬牙切齿、捶胸弹脚。那我就以老腔贯穿这篇悼文的始终,以求得先生共鸣,唱曰:
中国文坛一硬汉,来去堂堂七尺男。
秦岭八水情未了,万众注目白鹿原。
一
2016年4月29日一大早,收到陈忠实先生凌晨逝世的讣告,身心为之震悸,随后渐渐平静下来。一个人独立书房,临窗西望,潸然无语。几十年同先生交往相知的情形,一幕幕清晰浮现。我同先生的交往,完全是仰慕与尊重,是思想和精神的相通,是文学创作之缘。所谓一杯清茶,两颗文心是也。我想象着,先生那布满岁月沧桑的木刻般面容……医院心电图监护仪上象征生命的那一根细线……眼下,那原本跃动的绿色线条苍白僵硬地静止着。
陈忠实走了!
4月最后的这天黎明,西安气温骤降,先生没来得及看到又一个风和日丽的白昼……活力无限的顽强生命就此悄然消逝,却并不像某人所言,是带着“病毒、疼痛与恐惧”离去,而是堂堂正正,轰然倒地。习近平、胡锦涛前后两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几乎所有新老常委都送了花圈,更有他生前并不认识的来自全国各地、遥远农村的男女老少,从没见过面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也都络绎不绝地赶来吊唁。一个作家去世,在一个国家上下引起如此大的震动,缘由何在?这绝不是仅仅因为《白鹿原》代表着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也不是因为陈先生生前人缘特好,而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与精神风范代表着社会正义和人们的期望。
先生并非倒下,而是更高地崛起。终于回到他历来敬仰的文学前辈中间,回到杜鹏程、柳青、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中间,定格成其中一座永恒雕像。想到此,我不由得要吼老腔:
独坐故原常放眼,华岳渭水襟怀间。
兴来挥洒激情真,开腔一吼正乱谈。
曾经知遇古长安,虚怀若谷非等闲。
嘱余笔耕不得辍,语重心长铭心田。
二
“两三年不见,陈忠实明显瘦了。如同一匹长途奔腾后刚刚收蹄的老马安卧下来,颧骨高隆,脸颊松弛,一双老眼更显深邃,头顶的苍发有些零乱,额头上的抬头纹像几道深深的犁沟,把睿智、宽厚、正直与苦乐播进眉宇之间……这位作家,平时就是一个普通的秦川汉子:喜好看足球喝啤酒,喜欢吃羊肉泡馍啃乾县锅盔,不过偶尔也会吟诗书联,听说他每天的案头工作还排得很满。为了潜心投入工作,原本需要人照顾的他却离开家人,独住一处,埋头写作。”这是4年前,陈忠实给我的印象。
那是在夏季,一天下午我和文友艾庆伟相约先生到东大街老孙家吃泡馍。每次到了西安,先生再忙,都要抽空一聚。先生喜欢吃家乡的牛羊肉泡馍,可是他性子急,饼总是掐得大,吃得也生快。饭来了,他先不吃,只是坐着抽烟,看着你吃。目光慈祥而随和,俨然宽厚长兄。别人吃饭,他就这么一根接一根抽烟,把饭凉在那里。指尖夹着的还是那种黑棒棒廉价工字牌卷烟。烟雾缭绕中目光越显慈祥,人也越发显得苍老,更像是一尊古铜色雕像。抽黑棒棒卷烟,对于作家陈忠实,那就像画家刘文西永远不变的一身灰色中山装。这是属于他们标志性的个性化道具。陈先生抽着烟眼看大家吃,估摸饭也凉了,这才掐了烟端起饭碗,呼哧呼哧大口地开喋。大约十分钟功夫,碗就空了。陈先生放下碗,心满意足把嘴一抹,就算完事。现在回头看,其实那时他已经病了,只不过自己一无所知,还一如既往拼命工作。
作家陈忠实,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关中农民,或是一头农民看重的犍牛,天生就是劳作的命。我当时很担心先生的身体,建议他少抽烟,多吃滋补品。先生嘿嘿一笑,没有回答。那次见他消瘦衰老的样子,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担忧。事后好几天,他那苍老疲惫的容颜总是挥之不去。想着先生为人的真诚与宽厚,想着我们几十年的友谊,我突然觉得应当为他做点什么,又不知该做什么。回京以后便写了特写《老柿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还配了素描肖像。令人欣慰的是,陈先生比我还早看到报纸。他显然是高兴,主动打来电话说,培元呀,咳,你……文章我看了,嗨呀,你呀……叫你费心了。我说,稿子事先没请你审,是不是有些冒昧?先生哈哈一笑说,你写我还审啥,我啥啥你不知道?我故意说总有不知道的,电话那边又是哈哈一笑。陈先生就是这样,在朋友面前,总是真诚宽厚,没有一点名人架子,言语坦诚真挚得叫你感动。他的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透在话里,融化在那些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句子中间。
那次相聚,记得还有省委原副书记牟玲生老和几位文学青年,年龄从二十来岁,到八十多岁,是真正的忘年之交。大家因文学而结缘,又因文学的话题而充实愉快。这样的“饭局”实质是雅集,陈先生乐于参加。他显然不是为的吃饭,而是为了见人,了解人的心境与生活。席间常常会有粉丝不请自到,要他签书、照相,他都尽量满足。有人也许认为这是浪费时间、耗费生命,陈先生当然不这么认为。那种不事张扬的慷慨大度,教你想到白鹿原上果实累累的老柿树品格。丰年锦上添花,荒年雪中送炭。大作家也是普通人,参加自己愿意参加的社交活动,怎么能说是“绑架”呢?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更不希望看到那些自以为功成名就的人,整天神神秘秘把自己圈在书房或闺房中自我陶醉、闭门造车,写那些阴阳怪气、不疼不痒、于世无益的狗屁文章。
那天,陈先生放下老碗,轻松愉快地说,培元,看到你这些年一直坚持写作,我很高兴也很羡慕。说真的,年龄不饶人,我现在想写大东西都感觉体力不支。我仰头看着先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心想,这也多亏先生你的鞭策。1998年在榆林你叮嘱的话我还记着。《群山》研讨会上,陈先生紧挨我坐着,另一边的何西来先生正在发言。陈先生小声对我说,培元你记着,工作再忙也不要丢了写作。近二十年过去了,我自感欣慰的是,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陈先生见我沉默才说,不少人当了官就撂了笔,你还真是一个例外。不久前,何西来先生到西安,我问到你的情况,何先生说,培元是红色歌者,《群山》之后,说你一路走来,干啥吆喝啥,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可我想知道的还是《群山》续集写得怎样了?我说,续集《长河》,原计划写到“文革”结束为止,后来发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有不少重要内容,因此就又写了第三部《浩海》,总名称《苍生三部曲》。陈先生听得目光一亮说,你这又是叫我惊喜呀,我很想先睹为快。我说已经完稿,准备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回到北京我立即把《长河》、《浩海》各打印一份托人转送陈先生阅正。过了不久,陈先生来电话说稿子大致看了,两大摞子,令人敬畏。说里面有好多他不知道的人和事,可惜太长,没能细读。先生说话总是这样的真诚,令人感觉踏实,心悦诚服。见我无话,先生又说,你文笔好,《群山》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细看后也许会写一篇心得。我只有感动,无话可说,丝毫不敢再烦劳先生。不料又过些日子,陈先生竟然写了一篇不短的书评,先生诚心所致,古道热肠,令我没齿难忘。忍不住再为先生吼几句老腔,感恩高风亮节:
日辉晚霞灿如血,点点源自心头滴。
多少思虑多少难,总是利人忧民艰。
硬汉倒地魂如山,何必凄凉挥泪衫。
天下多少苟且者,不过行尸走肉团。
三
我常想,陈先生何以最爱听秦腔,何以对华阴民间老腔那么着迷?秦腔吼起来字正腔圆、音乐形象顶天立地,是豁达豪放、爱憎分明、撼天动地的艺术,而华阴老腔更甚。这正同陈先生堂堂正正的品格一样。他的作品中,多见金石有声、慷慨悲歌之士,关键时候,常能克己为人,甚至舍身成仁。那是他的理想化身与精神寄托。同时,他作品里面也不乏苟且淫乱、成天日鬼捣棒槌的小人混混。那是他视为仇敌,甚至不屑一顾的一堆人渣。他的文字里,似乎并没有多少正面描写秦腔的,而秦腔慷慨激昂的旋律,吃钢咬铁的气势,仿佛永远都是他作品的背景音乐。我的印象中,陈先生迟早说起话来,总是是非分明、斩钉截铁,绝不含糊其辞,阳奉阴违。
记不清头一回同先生见面是在何时何地。也许是先生来延安为文学青年作过报告?也可能是陕西文学界的某次活动吧。用先生的话说,我们“结识多年”。其实,应当说我认识先生更早。开始读他作品,是四十年前上高中时。他的《高家兄弟》和《忠诚》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延河》和《陕西日报》副刊。文字质朴简练,就像农民说话,实话实说,铁骨铮铮,令人读着比吃羊肉泡馍还囊口。先生是运用关中方言的高手,那种经过提炼的口语化原汁原味,比起柳青《创业史》的语言似乎还要地道。柳青先生陕北人学说关中话,略微有点隔生也是难免。然而柳青毕竟是文学大家,在创作上一直被陈忠实视为第一导师。一次陈先生对我说,《创业史》是我的守护神,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年轻时总是压在枕头下面才睡得踏实。柳青一生践行深入生活,心系百姓,陈忠实是忠实的效仿躬行者。《创业史》写蛤蟆滩稻地沿一村的故事,反映中国农村变迁和农民精神的嬗变。相比之下,新时期《白鹿原》视野的宽度、思想的厚度与历史的跨度都有了新的追求和突破。两部不朽之作,都是中国农村的村史、中华民族的秘史。长途接力的两棒,两代作家的领跑者,堪称双子星座。一次,我谈了这个观点,先生立即“纠正”说,这话不对,应当说我们当代陕西作家都是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辈作家的学生,我充其量也就是个“入室弟子”,因为我进了作协的院子,勉强算是入了“室”。他的品格中,总令你感受到有一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比如谦虚谨慎与与人为善,言谈话语中时常体现出常人容易忽略,更难以做到的清醒与自律。这使我常常想到,颗粒越饱满的谷子,腰总是弯得更低。
很长一个时期,陈忠实都是陕西文坛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他不是一举成名,而是属于那种一步一个脚印艰难步入文坛又攀上高峰的实力派作家。此前可以说他一直“无权无势”。路遥开玩笑说他时常扛一袋子面粉上作协院子逢人便问“谁要白面?”回头看,他也的确是白手起家。没有当过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编辑。有这个经历,这在一个作家起步阶段无疑是最大的优势和捷径。他也没有当过什么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授,甚至开始好长时间都不在文学圈子里面。陈忠实开始是真正的农村业余作者,属于那种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而不得不回乡劳动,连一张稿纸都要自己掏钱去买的地道的农民作者。他就像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土地上劳作首先是为了生计和争一口气,更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生存理由。这或许也是天意,使得他同柳青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成长轨迹。把根脉深深地扎进了农村和农民中间,一生不离不弃。
《白鹿原》的出版、引起轰动与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给陈先生带来了荣誉与各种实际的好处,也使他经受了某种压力与困惑。他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我还在延安市委工作。一天陈先生来电话说,培元,我现在给呐作协管事,不管事不知道难。作协这些人,只有一辆破桑塔纳,都快开不动了。我一上任,大家对我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想办法换一辆新车。你说我到哪里给呐弄新车呀?唉,想来想去,我只有给你打电话。我理解先生的意思,当即表态说,车我给你想办法协调。放下电话,我就分别同书记、市长商量,决定在炼油厂平调一辆新奥迪给省作协用。我当即告诉陈先生,不料他却说,奥迪我不敢要,你还是给我弄个桑塔纳。我问为啥,他说车太好,费钱不说,还怕有人说闲话。我说那就桑塔纳吧。过了几个月,我陪一批客人去炼油厂参观。厂长问我,怎么省作协要的车还没人来提。我事后问陈先生,他说,唉,这事别提了,车还没回来,就有人告状,我就莫敢要。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为人处世上处处谨慎小心,也俨然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其实,就他当时的影响力,直接找省长、书记批一辆新车也是很容易的。先生品格的另一方面由此可见。如今回忆起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真想再为先生吼几声老腔,听他喝彩大笑:
不苟言笑冷幽默,开言铿锵乃随和。
炯然如炬穿浮泛,时有箴金似鸣铎。
文章千古不朽事,陈公呕心铸奇书。
白鹿未老青春在,浐灞长流追三苏。
四
陈先生为人重情重义,但是原则性却很强。见不得蝇营狗苟,更不喜欢拍马逢迎的官场习气。但是,作家中,包括文学新人谁出了一本好书,他总是热情鼓励,大力推介。记得拙作《耕耘者:修军评传》出版前,先生看了稿子,认为不错,还欣然应邀题写了书名。后设计者没有采用,先生也不计较。书出版时我已经离开陕西,但是先生看到书,就提议在西安举办一次研讨会。由省作协、省美协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美术出版社联合开。那次会议,由于陈先生的积极张罗推动,开得十分成功。陕西主要作家、评论家和美协大画家几乎都来了。研讨很深入,为以后作品获全国大奖起到了重要评定和宣传作用。
如今,先生的灵魂,正同那令人静穆的高山古原化为了一体……也终于解脱了文学劳作与纠结的痛苦,可以安静地长眠休息了。作家这碗饭,本来就不好吃,更何况先生对自己的严格与苛求都是远超常人。他时常谦虚地说,咱这行当本来就劳人,再加上咱人笨,就更得笨鸟勤飞。他的每一个字,都是全身心投入所为,那其中的每一句,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句子”。从一开始创作,他就不会取巧偷懒。他没有像不少作家那样,在起步阶段或多或少都依赖过“模仿”这根拐杖。从作品看得出,先生从一开始写作,就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先生不愧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鲁迅先生享年56岁,先生73岁还多,也算是功成名就,善始善终了。先生真正是一生没有停笔,这在中国作家中,也许是空前的。据说即将倒下的那一刻,即所谓弥留之际,他的手中还紧紧握着笔在写,他的视力已经模糊,字已经分不出行了,重重叠叠地书写,最后留下可以辨认的文字竟然是:生命活力!这真是一个奇迹,就像是太阳落山时努力留给大地的一道绚丽晚霞。生命活力!多么精准的一个呼唤,这说明直到最后一刻,陈先生头脑还是清醒的。“生命活力”,这是先生留给这个世界和亲人、文友的最后遗言!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在最后一瞬间的灵光爆破!这样也好,一条硬汉倒下了,我们面前又耸立起一座大山。他生于秦岭脚下,如今又化作了秦岭一部分。
同陈先生最后一次通话,大约是去年年初,先生在电话里,声音低沉而沙哑,吐字已经有些含糊不清,这令我十分担忧。我说,陈老师,你关心的《苍生三部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先生说,好呀,向你祝贺……我泪水盈盈,无话可说。
人世间有许多名不副实的事物,但陈忠实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作家。作家这个行当,没有才情智慧不行,但作家最难能可贵的,倒还不仅仅是才智,而更要看德行。陈忠实,他笔下的白嘉轩、朱先生和蓝袍先生们同作者本人一样,都是植根于同一片土壤的佳木奇树。我因此为先生再吼老腔:
风雨骤来胸有壑,满目烟霞多困惑。
生前常忧身后事,最盼生民久康乐。
桑沧雕就中华范,除尽粉装余贞坚。
洞天深邃不见底,丘壑川原貌森然。
一世勤奋当代稀,劳模却未过五一。
大家忍痛撒手去,恩公含笑在梦里。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绘画:忽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