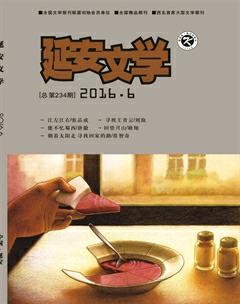汹涌诗潮中的瑰丽风景
王可田
陕西是小说大省,也是诗歌大省。陕西诗人孜孜以求的经典性、原创性和现代性的写作范式,以及倾向于神性,对历史、文化的诗性观照和深刻洞察,是能够为这个时代留下具有恒久价值的诗歌文本的。陕西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省份,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反映,已成为众多诗人对社会良知和责任心的自觉承担。同时,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实践,也能在这里找到生发的土壤。可以说,陕西诗歌的庞杂和多元,相互之间的共生共荣是罕见的,也是珍贵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汉家雄风、大唐气度在这块土地上的延续、彰显,以及时代精神辉映下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
作为陕西诗歌的“半边天”,陕西女诗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并不亚于男性诗人。她们有自己的独特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或者说,并不适宜将她们和男性诗人进行比较,他们之间重要的不是可比性,而是各有优长、不可替代的差异性。甚至差异性也不必过于强调,互补性才是根本。正是她们瑰丽多姿的诗歌风景,才与男性诗人的创作共同构成丰富、多元的陕西诗歌的完整面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就活跃着一大批陕西女诗人的身影。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梅绍静,以饱含黄土情味的吟唱加入波澜壮阔的新诗潮运动,诗集《她就是那个梅》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集奖,为陕西女诗人作了表率。紧接着,陕西本土的刘亚丽、胡香、南嫫、小宛、刘晓桦等,以各具特色的诗歌实践和艺术审美为陕西诗歌写下浓重的一笔,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珍贵样本。但随着时代变迁和诗人的分化、流失,在陕西本土只有少数女诗人留了下来,坚持下来,卓然独立,显现不凡的气度,她们是刘亚丽和胡香。刘亚丽是获得过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诗人。她的诗平易舒展,光润细腻,意蕴弘深。她善于用日常生活物象传达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体验,宗教情怀已内化为生命本身,诗歌发现充满新意,跃动着无限的喜乐和生机。胡香近些年很少发表作品,也很少参加诗歌活动,但她的诗愈加开阔和精深,或许在这种状态下,她更能全身心地进入幽暗莫测的诗歌本体,窥见那道引领人类精神的光芒。胡香的诗在悲剧性基调上,传达出对命运的接纳、对生命的感恩,令人喟然动容。她并没有过多地表现诗歌的社会性主题,而是倾向于生命和灵魂热切的吁求,诗歌的精神性表达,指向存在的终极。
在六十年代这批诗人中,杨莹也专注于其它文体的写作,但毫无疑问,诗歌仍是最贴近她心灵的体裁。她的诗短小、清丽,散发着浓郁的女性气息。三色堇成名较晚,给人的错觉是和70后一起成长起来的。这或许可以说她是一个晚成的诗人,孜孜不倦地勤奋创作令人钦佩。她的诗节制、明净,在含与露、隐与显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这得益于她对诗歌意象及隐喻的娴熟运用。神木的闫秀娟虽处边地,诗风也较为传统,但扎实的功底和充满地域风情的独特书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像定边的张晓润、铜川的刘爱玲、西安的白芳芳、渭南的赵红娟等,多年的坚持让她们在诗歌上有了不俗的表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千年,陕西70后诗人纷纷登场,在诗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独特的艺术个性。女诗人无论是在影响还是创作实绩上,似乎都走在了男性诗人的前面。眼下,她们已经成为陕西女诗人群落最具活力和可能性的群体,写作上渐趋成熟,进一步走向深入和开阔的境地。安康的李小洛,率先为陕西70后赢得全国性的影响和声誉,她的《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省下我》组诗《孤独书》等一经发表,就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在诗歌和生活之间,李小洛执迷于营造栖居的诗意,小城安康便成为这样一个代称。她的诗歌明澈透亮,语感极好,意象在清晰和模糊之间游移,如真似幻,耐人寻味。临潼的横行胭脂,其诗歌作品的发表也如她的网名一样席卷国内各大刊物。她执拗而绵长的诉说,带来出其不意的感染力,她对诗歌语言的不断刷新,频频点亮人们的眼睛。
在陕西70后女诗人中,郦楹和宁颖芳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她们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急不躁,安静从容。诗歌对于她们已是生活方式乃至休闲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诗歌艺术上的精进。相反,正是这种良好的心态,让她们更深地潜入生活和诗歌内部,发现种种神奇。郦楹诗歌有一种难得的知性美,广泛的涉猎和汲取赋予她开阔的视野,沉潜和智慧带来抵达事物本质的发现与领悟。宁颖芳早期诗歌的女性化特征很明显,轻柔唯美,近年来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进一步加强,诗歌的厚度和内部空间在进一步扩增。杨芳侠近些年才走入人们的视野,但她的诗歌实践已相当漫长。诗歌对于杨芳侠来说,几乎就是生命的全部。饱满而炽热的情感,悲怆情怀,以及对于美和崇高的精神诉求,让她的诗有了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诗歌的面貌,印证着写作者的理念;诗与写作者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诗歌的状态、面貌、格调乃至格局。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诗与名利的逐渐绝缘,在很多诗人那里,诗歌不再是事业,而退居为一种精神自足的方式。在陕西70后中,就有很多不大抛头露面的女诗人,但她们的实力却不容小觑。阿眉就职于新闻媒体,但纷纭的社会事件和娱乐快餐并没有冲淡她内心丰沛的诗意,时而舒缓时而跳荡的节奏传递出现代语境下的古典审美。作为医务工作者的闻风,其诗简隽明晰,语言富有暗示性,短小的篇幅中呈现的是自我世界的广博和隐秘。初梅的知识女性气质在诗歌中体现为一种优雅,一种反观自身的从容不迫,一种情调和意蕴的渲染。还有在绘画和诗歌之间自由穿梭的沈向阳和高小雅,一个沉雄有力,一个散淡徐舒,以不同的方式叩击阅读者的心扉。名字像穆蕾蕾、烟雨、蒋书蓱、苦李子、传凌云、南南千雪、陌上寒烟、屈丽娜、琴音、诩真、崔彦等。就目前来看,这一批诗人的名声和写作实力并不一定是最大、最好的,但经过充分的沉淀和打磨,艺术上的突飞猛进或一鸣惊人,完全是有可能的。正是她们以各自的文本实践构成陕西女性诗歌的有机整体,营造了浓厚的诗歌氛围。
就在70后诗人不断超越自我,在诗歌的道路上稳步推进,并逐渐成为诗坛中坚力量的时候,80后不知不觉已成长起来,以饱满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显现强劲的活力。商洛的吕布布这些年在南方发展,良好的诗歌素养和悟性以及广泛的诗歌交流让她从同龄诗人中脱颖而出。她的诗对日常生活的表述打着鲜明的个人化烙印,主体的私密和幽暗给了她更大的探索空间。西安的木小叶较少发表作品,但她的诗技艺娴熟,语言流利雅致,表达上倾向于幻念和冥想的再现。在八十年代末出生的女诗人中,榆林的惠诗钦很突出,作品在各地刊物频频发表。她的诗带着这个年龄段特有的清浅和灵性,散发清澈莹润的光泽。陕西80后女诗人还有很多,像延安的李亮、汉中的杨菁、咸阳的郝娟子、长安的刘欢、商洛的牛磊等。她们目前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正寻找自我的独特发声,但广泛的学习和借鉴,广泛的汲取,已让她们锋芒初露。
最后说一下90后诗人。她们大都活跃在大学校园,是陕西女诗人群体中最年轻的一代,是诗歌的未来。诗意的种子在心田萌发,抽枝展叶,摇曳一片新绿。年龄没有成为艺术探索的障碍,诗歌才华早早地显露出来。像出名较早的“少年诗人”高璨,宝鸡的张筠涵,在校园诗歌奖评选中脱颖而出的唐棠、马映、郭林等。
对陕西女诗人的写作进行简单地梳理和概括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在诗歌主张、艺术理想和文本呈现方面的巨大差异,也清晰感受到女性本身所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她们有着普遍的对自身和情感体验的执迷,也放眼身外世界,表达人类的共同命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她们之间的差异性或许并不亚于性别差異,她们的诗歌多向度展开,异彩纷呈,成为这个时代汹涌诗潮中的瑰丽风景。当然,诗歌不是才华禀赋的逞能,不是一蹴而就所能到达的巅峰。一种在时光的沉淀下愈见精纯的手艺,只有经过深入透彻的思考和艰苦锤炼,方显足够的成色和艺术品位。
作为女性,自然有着区别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结构,思维及意识,在写作上则表现为独有的视角和表现方式,这也是女性写作的底色和独特性所在。过分强调性别身份,忽视人性的共通,人类所要共同面对的生活、遭遇的命运,以及生命和世界的根本性问题,也必然走向自我迷恋的浅薄和诗学上的狭隘。如果抛开“女性意识”和“女性诗歌”的理论纠葛,以及所谓“新红颜写作”的诸多争议,我们不妨回归最简单最朴素的立场:女诗人就是写诗的女性,她们有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也有社会家庭角色的负累、现实处境的艰辛,她们的写作在彰显独特性的同时,也无法割舍与男性共同面对和分担的整体性问题。选择诗歌,让她们面临更大的压力,也预示着无限的可能,为此,我们向她们的辛勤付出和丰硕成果表示由衷的赞美和敬意。
责任编辑:薛宪 高权
——喜迎十九大 追赶超越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