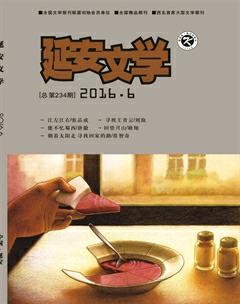朝着太阳走 寻找回家的路
常智奇
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新诗走过的道路,我们在欣赏胡适、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徐志摩、贺敬之、艾青、海子、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人的作品时,在欣慰之余,独坐静思,还有期待:中国新诗整体建设的步子还显慢了一些,在汇通一种时代诗体的历史美学形态的规范上,还显孱弱。有识之士隐痛“新诗体弱形枯缺钙少质”。其实,歌谣之质一直贯穿在中国诗学体势之中。从《诗经·生民》到汉乐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到魏晋时代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到南朝的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到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宋代范成大的《催租行》,到元代杨维桢的《五湖游》,到明代李梦阳的《长歌行》,到清代郑燮的《姑恶》,到柯仲平、田间、余光中等,许多有理想、有才华、有抱负的诗人都在这条路上延续民族诗性的烟火“味道”。霍竹山是紧随其后,用“信天游”的形式加入到中国新诗大合唱的行列。我认为:开掘、继承、发扬光大歌谣之质,是健全完善新诗体性,歌咏中国经验,体现中国气魄和中国诗风的唯一通途。也正是出于此,我评霍竹山用“信天游”形式创作的叙事诗。
霍竹山出生在陕北靖边县的一个农家(李季早先创作《王贵与李香香》的地方),他的父辈曾在“走西口”的途中唱着“信天游”走南闯北。他是在“信天游”的歌窝窝里长大的。“信天游”的旋律、节奏、音韵渗透在他的血液中,他身上的每一个诗性的细胞都扎根在“信天游”的歌声里。加之他慧敏的诗感,善良仁爱的天性,几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整理、研究“信天游”,创作出了长篇叙事诗《金鸡沙》《广羊湾情事》《走西口》《赶牲灵》《陕北恋歌》《红头巾飘过沙梁梁》等诗集。其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新诗赏析》《中国年度最佳诗歌》《陕西诗歌选集》《中国西部诗歌选集》等多种选本。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诗选刊》《星星》《绿风》《人民日报》等,曾获多类奖项。在“信天游”这种诗歌形式的创作中,他是目前中国文坛站在前沿的诗人。
一
人类诗歌起源于劳动,生于民间,长于神话,臻精于文人。来自民间的诗情永远是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民间诗情来自生命、生存、生活的“质”底;文人诗境来自语言、修辞、意义的“文”采。重“质”的诗流露出醇厚、朴茂、率性、自然、通俗、畅达、清新、刚健;重“文”的诗表现出典雅、风流、绚丽、华贵、隽永、工巧、炼字、考典。文人的诗多是汉语在长期的词语规范中形成的书面语,不太直接再现口语。民间的诗大多倾向于直接再现口语。霍竹山走的是一条尚“土”崇“质”的道路,在歌谣之质的泥土中培育“信天游”的诗性之花。他在近乎于素体诗的创作道路上,控制自己敏感而又浪漫的激情,写下了近乎于和土地一样朴素而又耐人寻味的诗篇。
“信天游”是陕北、山西一带流传的民歌,它是社会底层劳苦大众在长期的生活苦难中,用生命本能酿造的一种艺术形式。人的生命本能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阿波罗本能,一种是狄奥尼索斯本能。阿波罗本能面向远方的地平线,依靠太阳判断,创造梦境,虚构假象,在理想中超越生命感受生活经验;狄奥尼索斯本能匍匐于大地,沉醉于生命情感体验,肯定生活鲜活的流变,在现实中感受生命真实的存在。前者要将生命之流定形于某种瞬间而获得可能把握的形式(梦境、假象),后者则要摧毁任何固定生命之流的举动,将生命还原为奔腾不止的滔滔激流;前者静息于澄澈的形式,后者激动于动荡的混沌;前者将无形的混沌形式化,以此方式来支配、征服、控制、转移、升华流变不已的生命(信仰、理想);后者则拒绝任何形式化,摧毁任何形式,以此方式来彰显生命之流并反抗对生命的控制(上帝死了)。“信天游”诞生于人的生命本能形式化和反形式化的冲突。在那个无起源、无终点、无意图的莽苍的黄土高原,在那个无目的、无意义、无价值,万里黄沙扑面来的路上,在那个无秩序、无规律,惟有孤独的人的生命存在的环境,人必须对“存在的环境”表态、发话,必须创造和虚构自己“生存的环境”,必须在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有规律”的世界中生存。“信天游”这种艺术就是人的生命在极其孤独、疲劳、饥渴的情况下,为发泄胸中的郁闷,排遣寂寞,自己创作的歌。它积淀着生存论、人本主义的思想感情。“信天游”是苦难者的歌,它充满着英雄主义悲剧的情感和旋律。它激越悲壮,悲而不伤;它悲怆哀婉,哀而不怨;它哀怜忧凄,凄而不惨。这种诗性品质是人类诗学创建自己“诗意地栖居”精神家园的通途。
在这条路上,李季、贺敬之、阮章竞、公木们的“信天游”,更多的偏向于用这种形式进行革命、鼓动和教育。他们在诗与社会功能的“他律”寻找民族“诗意栖居”的芳草地。霍竹山更多的强调诗的本源开掘、精神传承、生命记录、时代创新。他在诗的审美功能“自律”中开疆拓土,求索进取。李季他们被时代、历史、政治所召唤,在生存、反抗、战争的硝烟中,为挽救民族的存亡而歌。霍竹山被寻根、清源、正本、创建艺术生存论的诗美所召唤,在求真、向善、爱美的创作中,为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而唱。前者,在民族面临灭种的危险的情况下,救亡求生。后者,在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坚守民族复兴。这是两代人面对诗的不同态度和做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不存在孰高孰低,谁上谁下的问题。
中国的新诗走过了近一个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叙事诗面临全面萎缩。这是人类在现代化的建设中,理性遮蔽诗性的一个“诡谲”现象。诗性源于人类生命在创造生存环境、生存必需中的“叙事”体验。叙事诗带有人类“创世说”的生命“胎记”,它积淀着人类诗性陈陈相因的“精血”,它承传着人类创建“诗意栖居”美好家园的“薪火”。人类感发诗性的“慧能”、“才情”、“别趣”沉潜在叙事的情感意緒之中。离开叙事的时空认知和经验记忆,离开叙事语言的能指、意指、声韵的历史积淀,抒情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赋新词强说愁”。诗情永远离不开叙事基因的滋养,离不开叙事思维的烘托,离不开言不尽意的叙事剪裁,离不开别趣对常规叙事的重铸与再造。中国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个文明薪火传承未断的国家和民族。中国是一个诗国,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传》、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打歌《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拉祜族的《牡帕蜜帕》、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苗族的《苗族古歌》、壮族的《布伯》,以及布依族和侗族古歌等长篇和短篇创世叙事诗的这种“英雄创世说”的精神血脉、阳光慧能、认知基因遗传和继承下来,这是中国新诗健全自己体格的一笔不可或缺的重要财富。
中国的新诗创作,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创建”人的生存环境而来的。从本土的大众生活语言中寻找新诗的出路,这是时代对新诗的呼唤,也是新诗历史之必然,不存在对与不对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在新诗的培土、施肥和浇灌中,是否科学?优秀园丁的用土、用水是很有讲究的,其中的成分,用的时空等等,都是不能错乱的。回顾近百年中国新诗的成长过程,我们觉得对诗体之“文”,诗语之“言”偏于西语译诗的借鉴和模仿。这样就形成了“道”迷惘而“味”不足。这里的“道”是用哲理冲击形象,用平面化的照搬生活用语代替用诗性对生活用语的锤炼和加工,不自觉地冲淡了千百年中国诗学中那种白话中蕴诗意,土话中含诗情,民歌中有诗魂的血脉之源。又舍弃了经历史反复淘洗的一些纯洁、自然、精美的语言。诗在通俗的名义下走向直白,在易懂的名义下走向无味。诗是用语言创建真的艺术。在自然、优美、准确、清新的词语命名中敞亮真的存在,是诗的天职。而这种用语言创建真的诗语,要在“创世说”的原初语言的历史中去寻找。海德格尔是通过回到古希腊的词语中去而建立起自己诗学大厦的。霍竹山的“信天游”创作,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民歌的叙事形式上继承、开掘和提炼的,这是令人欣慰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命器官移植、克隆人,物化、异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真正贴近诗歌生长“大地”的好诗不多。一些青年诗人沉醉在物质主义的自满自足之中,满足于喧哗浮躁的虚荣享受之中,迷恋于想当大师的“运动情结”之中;有的从个人狭窄的情感之窗看世界,用个性化的精神叙事对大众语言进行无情的拆解,对历史叙事进行深度消解;还有人认为“现代抒情诗要剔除叙事元素”。在这样的背景下,霍竹山“信天游”的低姿态、大众化、民族性的创作更显得有意义。
二
霍竹山的“信天游”是生在大地上的诗,长在生命里的歌。它表现的内容是乡土情怀、家国忧思、人生况味,主体是土地、阳光、劳苦一族,表现的形式是传统民歌体,表现的角度从爱入手。霍竹山的“信天游”是焰焰烈日下,赶着牲灵走西口的人唱的歌。它表现生命在追求生存的苦难与焦灼中的深切体验,社会变更中的人生选择,诗人对土地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深度思考。他的作品充盈着一股热恋土地,同情和关心耕作在这片土地上的劳苦大众的命运的赤子情怀。诗人用朴素、自然、优美的语言表现了人性在追求爱与善中的笃实和纯朴,表现了崇高的太阳对原野的绿叶的深情呼唤,表现了土地、太阳、生命、创造、再生中的蓬勃与平静。信天游是华夏民族诗歌武库中的瑰宝,霍竹山用这种瑰美的形式表现大野蕴瑰宝,深山有俊鸟,人民是创造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他用普通人在苍莽的大地上朝着太阳走的歌声,表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灵波澜,一个时代前进的律动。他用濒临灭绝的这块“石头”点燃人类诗性承传的火种。他的“信天游”在天地人太阳的整体合一中呈现出一种“望乡”与“现代”的二重唱。
《金鸡沙》是作者以自己居住的村名取名的诗集。作者站在农民面对土地耕作形式发生变化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的基点上,写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写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状态。诗中随处可以看到陕北高原乡村生活意象:红柳、小河、土地、村庄、桃花、沙枣、艾草、豌豆、荞麦、沙滩、阳光、月亮、骡子、山羊……几乎聚拢了乡村生活所有的美学元素。他写的焦土萧索,旷野平阔,鸡鸣狗吠,男欢女笑,平实而跌宕,朴素又真切。《金鸡沙》凝结了他对生活太多的体验、感受、欢愉、痛苦和诗情。读他的诗,我们能感到他身上带来的那股散发着大漠沙土味的风,我们能嗅到他字里行间潜伏着的田禾的芬芳。泥土的朴实与博大,太阳的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执着坚守、简约、朴素、流畅、铿锵的诗语。但,他不是一个传统的乡土诗人,不是一个田园牧歌者。他笔下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非常宁静、恬淡、舒适、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场景。他笔下的土地和乡村、土地和人、人们的爱情和土地的变迁是处于某种激烈的冲突之中的。他写辛勤耕耘在这块大地上的父老乡亲们包产到户,联帮结对,治沙植树,办厂养殖,出外打工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写这群太阳的子孙在乡村秩序和权力重组中的火中栽莲,凤凰涅槃,去腐生肌,除陋从新的现代性蝉蜕。写通过土地确认两代人的身份、地位、生存方式和人生追求:华成娃与屈彩英在分产到户的矛盾冲突中“和”了,屈保顺、彩英妈在黄土变成金的改革中理顺了爱意,赵大炮在“共同体”的创业路上背着钱袋拿着手机喊话,治沙总统张改玲成为“劳模”,李有才让位华成娃……霍竹山笔下的乡村题材,是一种精神家园的隐喻,而非对农耕时代的依恋。金鸡在万顷黄沙上,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引颈长鸣。屈彩英、华成娃、张改玲他们这群火凤凰驾着朝霞,带领村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狭隘走向开阔,从自然走向社会,从欲望走向理智,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卑怯走向健康,從卑贱走向高贵。“信天游”的歌声回荡在金鸡沙村的天地之间,灿烂的阳光照耀在静穆、朴素的村舍、农家、田园,歌声召唤着人性在历史的前进中植根于生命的大地,沐浴于崇高的阳光,在“太阳神”和“酒神”相对和谐平衡中,育植一片抵御来自西伯利亚风沙的绿色林障,创造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
《金鸡沙》也冷静也呈现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无情地批判了农民身上的狭隘、自私、保守、落后,显示了诗人的独立精神。
广羊湾是“信天游”的故乡,也是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取材的地方。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思想,农民普遍过上了好日子,当年的王贵与李香香的后人们生活得怎么样呢?霍竹山以一个现代诗人应有的目光,真诚而善良地叙说了他们的生存状况,重复了毛泽东的一个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广羊湾情事》深刻地揭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严峻性。作品取材于广羊湾这个当年李季创作《王贵与李香香》人物原型生活的地方,写王贵与李香香原型人物后代的生存状态。作品中的“二秃子”王二强是“王贵”的孙子,作品中的李丕是“李香香”的侄子,而李丕女儿李秀英爱的是“崔二爷”的孙子崔换平。这是历史发展中的规律,还是文明前进中的“曲折”?是生活的照搬,还是艺术典型化的加工?无论怎么讲,诗人关注现实,关注农村的改革,关注农民命运的诗心是显而易见的。《广羊湾情事》用生活情态的叙事涵盖革命的宏大叙事,用浓郁的生活气息稀释政治说教,在传统的题材、主题、形式中开掘时代精神、现代意识,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诗人站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看到了昔日反封建,闹革命,争自由的人们的后代,重复陷入封建残余的旧思想的束缚之中:王二强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从土地中掘取文物;李丕不种不耕,摒弃人间父女情感,演出一场卖女求富的人生悲剧;刘二嫂靠说媒卖肉,寻欢作乐;牛村长是见钱眼开……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令他心焦、心急、心痛,也令人深省。在作品中,诗人也透过这些历史大潮前进中的漩涡,塑造了李秀英、崔换平一对新时代的新人,他们在新时代的阳光雨露哺育下,甩掉了先辈们的仇怨,在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地上爱恋,带领村民们致富。《广羊湾情事》主题厚重、严峻,但诗人表现得轻松、诙谐、幽默、自然,与当年李季他们创作的紧张、严肃拉开了距离。霍竹山在历史与现实、生命与爱情、乡村与都市的交叉处,在表现广羊湾人在社会革命中自身人性中的自私、卑怯、懦弱也得到改造。作品被誉为《王贵与李香香》的续篇,可见读者对诗人真诚、勇气、担当的认可。
经过现实的体察,历史的思考,《走西口》回到“信天游”这种民歌形式产生的本源上来了。诗人在艺术和艺术形式产生的生存土壤上展开自己诗意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走西口人们生存的艰难、困苦、无奈,餐风宿野,披星戴月,走南闯北的凄惨和悲怆。诗人在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基础上,融进社会革命的思想,提炼、加工,塑造了一个个青年革命者的新人形象。杨五娃是放羊五哥的演化和发展,石榴花是大地任何一种草木名称的撷取,五娃当学徒,当二掌柜,被迫割爱无奈与巧巧结婚……在个人命运与历史的选择中,最后他们一个个自觉地参加了革命。诗人去污采莲,拂尘见珠,把民间流传已久的古老题材、主题、形式,时代化、革命化,点石成金,谱写出时代的新诗章。《走西口》,人生被迫走,走到黄河口,唱到黄河头,一路风霜,一路苦,想妹妹想得泪往肚里流。绿林山匪来打劫,红军救了咱的命。诗作人少事单,但情节曲折,对话入诗,笔触自由,作品的文本诗性大于它的思想意义。具有现代革命色彩的《东方红》来自于陕北民歌,其中的奥妙不仅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反映了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的愿望和要求,政党、领袖与人民的鱼水关系,还包含着人民的语言在时代的上空响彻,是因为这种语言的生命活力深根于丰腴的生活大地,神圣的太阳与野性的欲望是人走向纯洁与高贵的通途,远古的叙事因血泪的记忆使人的诗性永驻。
《赶牲灵》是2015年5月出版发行的,这是距离我们评论最近的一本诗集。在这里,诗人完全走向赶牲灵的主体。在骡子自生走,“信天游”飞出口的沙圪梁梁上,捕捉古老的“信天游”民歌中的诗语、诗韵、诗律、诗魂。《赶牲灵》依然沿用了“合理的爱情被无情的不合理所阻,爱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获得新生”的模式。可贵的是诗人极尽描写刘双成与张彩彩天各一方的思念,在炽烈焚烧的思念中表现人性在理性熔炉中的炼狱、自省、自新、自立。
霍竹山的“信天游”,是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农民思想变化、情感律动的“信天游”;是古调重弹,老曲新唱,具有故事性、传奇性、革命性的“信天游”。它真实地记录了属于诗人脚下的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生动地表现了耕耘在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英烈前辈、兄弟姐妹们在社会发生剧变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表现了他们追求真、善、美,鞭笞假、丑、恶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样态。他的作品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自然的困境和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把生命的欲望与时代的文明联系在一起。他在继承中迎着太阳,在创新中寻找家园。
三
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用语言创建真的存在。霍竹山的“信天游”在用生活化的口语,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形而“下”的创作观念,比兴陈述的手法,表现一个民族艰苦跋涉,艰难生存的繁衍史。
一条弯弯曲曲,通往天边的羊肠小路。
一队驮着沉重货物的骡子。
一轮喷火吐焰的炎炎烈日。
一个饥渴难耐的人赶着牲灵前行。
这是霍竹山《信天游》给我们描绘的一幅“苦行僧式的行旅图”。路,是道,道,是所有存在的原初,是永恒,是存在的分享,是光照,是超然。骡子,是通过大自然向人说话的牲灵,是实现人道和谐的“天使”,是“载道”的行者。太阳,是宇宙之“丹”,生命之源,光明之根,崇高与神圣的指南,是照亮人行走在道上的光。人,是万物之灵长,天地之精华,是驾驭牲灵之主,又是养护牲灵之仆,是走在道上的行者,又是荆棘丛生的莽野开辟新道的拓荒者。这四者构成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诗人在这“共同体”中真实表现人的一种艰苦卓绝的创建:生命在天地之间肆意疯长又被太阳所照耀、提升,开出芬香美丽之花。可贵的是,诗人自觉地表现人性中的本欲、“自我”在现实原则的压抑和束缚下走向自醒自觉的“规范”过程,表现“五月里天上刮旱风/越是跌年成税越重”的天灾人祸,表现人的根性——饮食男女,生存真情在人类理性中的历练,表现这种带着鲜活的生命“血丝”,带着生活泥土的粘粒的情感在“神与物游”中的文明升华:“瞅彩彩瞅得瓷瞪瞪/一脚踏熄两盏灯”。“耳朵侧转跟风跑/一把逮住个黄羊羔”。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充盈诗的字里行间。他的诗里回荡着孤雁在天际无边的凄鸣,渗透着霜打茅棚的唦唦声,浸渍着负重者的血汗。这里有“肩膀磨烂没觉见疼/想妹妹想成了羊羔风”的苦恋绝唱,也有好汉劈天飞,十里听鼓声的求生、求爱、求善的激情奔涌。求生的主人公匍匐于大地,在泥土草木中求活,在极其贫瘠土壤中求存,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求得自己的一线生机。这样,他的诗中就有一股“真筋”、“真力”、“元气”蕴涵其中,这股“真气”来自生命的“根性”,生活的“地气”。
这种蓬勃的生命激情和意兴表现的方式往往是控制浪漫,压抑夸张,把浪漫和夸张融汇在民间比喻和生活经验之中:“人要是不怕苦和累/天塌下来敢捆起来背。”“恨不得房子顶种上一分豆/恨不得井台撒上白萝卜/恨不得锅项种上两畦韭菜/恨不得水缸沿沿上栽海带/要是有个梯子能上天/一犁犍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要是能借来牛郎的牛/月亮上面也种它几亩地”。
霍竹山的“信天游”往往是通过写爱情而反映社会生活的。爱情在这里是诗人自己“关怀存在”的一种方式,是诗人自我心灵诗化生活的路径,是“终极关怀”的“返璞归真”。优秀的诗是从爱出发,超越自我、超越日常的“终极关怀”。灿烂之极归于平淡,本真的诗学意念必然是朴素的。霍竹山所表现的爱情是真挚、圣洁、纯净的,是灿烂、炽热、与阳光同在的。爱因真的质朴而光华四射。他笔下的爱情是植根于柴米油盐中的草根族的真爱。爱因耕耘而博大。他诗中的爱者是大地的耕耘者,爱的奉献者。他们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享受生命在创造中的欢乐、愉悦和自豪,同时也正视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提升生命。他们在播撒爱情的沃土上,沐浴着太阳的甘霖,用自然之风梳拢着爱情的长发,也用太阳的光芒照亮爱情的暗地。他诗中表现的爱情,有草根之土,但无卑污之气,有朴茂之情,但无粗野之意,有欲望之火,但无肆虐之端。他诗中的爱情是“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人圪崂崂里走”的羞涩和拘谨;是“门闩闩抹点老麻子油/轻轻开来慢慢走/绣花红鞋提手中/就像狸猫溜墙根”的私密、收敛、庄严与神圣。这是他的诗接地气的一个方面。他的诗还有赶着牲灵,迎着太阳走,表现人的生命在“光合作用”下求愛、求善、求美、求真、求圣的另一面:“缝新补烂多少年/我怎么能做负心汉”“人活眉脸树活皮/我甚时能主自己的事”,“刘双成当了运输队长/想看彩灵忙得顾不上”,“马儿马儿你飞呀飞/为抗战你就受点儿累”,“过去赶牲灵为几个线/来回贩卖一些土特产/现在驮队像一条河/赶牲灵为了反封锁”,“叫一声妹妹听我话/共产党才是咱活菩萨”。这是人往高处走的道德约束,这是生命在天地人神关系中的命运召唤。霍竹山因为心中有爱,才写出了华成娃与屈彩英爱得那么深;因为心中有情,才写出了李秀英和崔换平、彩彩与双成爱得那么真,因为心中有理,才写出了杨五娃和石榴花爱得那么纯。霍竹山“信天游”中的生命意识侧重于写人在生存苦难中的不屈追求,人在绝望境遇中的意志坚守,人在苦恋中的情志不移;侧重于写人的情欲在现实矛盾中的伦理约束,自然野性在道德自审中的理性收敛。他在人的本我中彰显他在,在屋有中张扬家存,在家欢中诠释国有。他诗中的生命一定是在生活的贫穷、困苦、挤压、无奈、熬煎、撕扯中,为生而艰苦卓立,为存而矢志不移,为在而忍辱负重,为爱而吃糠咽菜。爱情在这个层次已经升华。她是社会历史发展前进的力量和个人为爱而坚守的机遇的结果,是人性中的爱与善在生活的艰难之途相互认领。他诗中的爱情更富生命性、生活性、情感性、精神性、人类性。与那些养在咖啡和牛奶中的金字塔的爱情相比,她有土地的质朴,没有穿金戴银的华贵;有锅碗瓢盆、相濡以沫的白头偕老,没有霓虹灯下轻歌曼舞的朝三暮四;她有太阳光照下的明媚、澄亮、清纯、坦诚、无私,沒有金屋藏娇下的阴暗、潮湿、冰冷、狭窄、压抑、沉重、自私。诗人写她们的爱情,往往借用“王母娘娘天河阻爱”的模式,揭示生活的真,人性的爱。他常常用比兴、铺排、特写、叠加、复唱、递进等形式,把爱情的叙事推到一个缘情叙事,叙事抒情,情事交融,情真意切,缠绵悱恻,余韵绕梁的境界。例如“对对蝴蝶对对飞/对对花儿亲亲嘴/对对柜子对对箱/两个凳子成一双/对对枕头花顶顶/两条棉毡对棱棱/对对穿衣镜柜上摆/天天等不见妹妹来/对对唢呐对对号/只哥哥一个单爪爪”。“三姓庄外沤麻坑/沤烂生铁沤不烂妹妹心”,“只要哥哥你情意长/讨吃要饭咱也相跟上”……。这种爱情的绝唱是单纯的,也是炙热的;是草根的,也是地久天长的;是泥土的,也是自然质朴的;是穿衣吃饭的,也是相濡以沫的;是拦羊放牛的,也是天高地厚的;是难离难弃的,也是守爱如玉的;是隔山隔水的,也是望穿秋水的;是生命张扬的,也是舍生取义的……。作品中的杨五娃、石榴花、张巧巧(《走西口》)、刘双成(《赶牲灵》)、秀英(《广羊湾情事》)、华成娃(《金鸡沙》)等,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憎有爱,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侠肝义胆,铁骨柔肠的真人形象。他们的爱情不仅仅生长在柴米油盐的窘困之中,他们的爱情也生长在肝胆相照,生死相依,同甘共苦的坚守之中;他们的爱情不仅仅生长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家族血缘的观念中,也生长在为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流血流汗,出生入死的奋战之中:“要找榴花你背上枪/咱们一搭里打东洋”。“你赶牲灵我纺线/咱二人比赛作贡献”。“我赶牲灵你纺线/为咱边区多生产”。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忧国”的爱情价值观,是霍竹山的“信天游”的“太阳”所在。
他写爱情,写人的常情、常爱、常理中的出众超群;人的常存、常在、常态中的仁爱纯真;人在生命、生活的艰难困苦中的意志坚守、精神追求、社会责任、历史担当。他写时代风雨对爱的心灵的浸润,历史烟云对爱的心灵的重建,社会的进步对爱的心灵的呼唤。爱情,是他切入生活的“切口”,是他叙事抒情的“载体”,也是他展示人类进步的“途径”。
四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诗人可以称得起是土地和太阳的歌者,至少有三位:郭沫若、艾青和海子。霍竹山是远步后尘的一位当代诗人。郭沫若、艾青和海子他们三人在承袭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基础上,接受外来的东西多了一些。霍竹山更多地承接了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东西。他在语言本体中开掘诗性,他在民歌常用修辞比兴的手法中寻找诗意:“天上的大雁排成行/刘双成赶牲灵坡坡里上。”“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交口难开”。这种“大雁好比是刘双成”、“樱桃是朋友”型的恒等陈述,把人与自然中的物体化为一体,主客一体,景随情移,移情化物,神与物游,人物互融。这种陈述就出现了两个层面的状况:一方面是不管诗歌中的人物由我们一般想象中的神思变成什么模样,诗歌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具有多种神思性质的。这个“好像是”的陈述中,把人引向植根于现实经验的生存大地。另一方面,这个陈述始终确认人类意识与其自身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事实上是粗暴违反——基于主体与客体永远分离的那种合乎常情的想法的。这个层面在“不应该是”的陈述中,把人引向心灵飞升的澄澈明净的天空。通常以“A是B”形式出现的比兴(无论明喻或隐喻)仅是多种修辞格中的一种。在霍竹山的“信天游”创作中举隅、换喻、拟人等等手法都有。“A是B”型的恒等陈述是基于“是”字的明确陈述。“你若是我的妹妹哟,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妹妹哟,走你的那个路”。“是”字型的明确陈述热衷于神与物游,主客一体,万物有灵。霍竹山是在运用这种“A是B”型的恒等陈述中装进自己的“新酒”,使枯木抽新枝,老树开新花。他在比喻中言此及彼,在象征中推己及人,在隐喻中移花接木,在暗示中叙事抒情,在相似中寻神通,在相向中找抒情叙事的旋律和节奏。例如:“你妈妈生你花眼眼”是古老的“信天游”的一句,为了主题的需要,他在此句的基础上提炼、推敲、创建了一句“山桃儿花开九卷卷”,这就使原来的这句老枝开出了新花。再例如:他在传统的古老的“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的比兴中,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一眼能化开黄河的冰/两眼看不透妹妹的心”的诗句。他在“老牛眼太阳当天上挂/吃一口干粮半口沙”,“羊羔羔落地四蹄蹄刨/起鸡叫睡半夜不说熬”的创建中,再创建“贼来了不怕客来了怕/家里头穷得光蹋蹋”的诗意、诗境。霍竹山在黄土沟峁、柴米油盐、田间地头的场景物象中捕捉比喻、比拟的灵感,在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穿衣吃饭中提炼复调重唱的诗情、诗意:“几回回梦见荞麦花开/笑得把一炕人都吵醒来”。“燕娃娃垒窝几嘴嘴泥/我尔个就去当这个媒”……。他的“比兴”追求杏熟麦黄,茅屋土墙,缝补浆洗,巷短家長,乡土情结,语言平实,生活味道浓,富有诗意:“满天星星眨眼眼/梦见了妹妹的白脸脸”。“清早喜鹊树梢上喳/你给妹妹捎上句话”。“想起妹妹咽不下饭/心火上来把嘴燎烂。”其价值之处便是对《诗经》中“赋”的手法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霍竹山在他的诗集《赶牲灵》后记所写:在信天游里,我努力找寻生活的细节——这才是诗歌的黄金,当然也是一切艺术生命力的黄金。我更注重“赋”的铺陈手法。我以为在信天游的创作中,“赋”是“比”和“兴”的延伸,只有在“赋”的作用下,“比”和“兴”才具有无限的张力。如:
稠的拨拉稀的喝,
饭菜不知冷热哩。
反盖被子错枕袄,
睡觉不知颠倒哩。
月落西山三星升,
耳朵贴着窗棱棱。
以上所列,便是细节描写,用铺陈的手法表现了出来,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的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好像写的就是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真好!
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如下诗:
沟里一条河水等你哩,
哥哥不来嘴撅的老高哩。
硷畔一棵杨树等你哩,
哥哥不来脖伸的老长哩。
山坡一阵风儿等你哩,
哥哥不来耳朵地上听着哩。
山顶一朵儿云彩等你哩,
哥哥不来眼睛望的淌泪哩。
窑里的妹妹等着哥哥哩,
花轿梦里几回回抬来哩。
从河水、到云彩、再到窑洞里的妹妹,可以说,很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妙处。在诗里不仅是妹妹一个人思念哥哥,还有一切物体,都陪她不停地思念。一个场地有一个神情,嘴撅的老高,脖伸的老长,眼睛望的淌泪。此时,我想起了家乡的一个场景:一个问:“你哪搭想我了?”另一个把手放在心口,说:“这哒哒。”而在这首诗里,妹妹是浑身上下都想哥哥。实在太令人心疼了!
他追求丰富多彩,五味杂陈的诗味:“一口黄连一口糖/死去活来无良方。”
他追求生活的形象生动,叙事抒情的自然流畅:“划一根火柴照一照亮/好像看见妹妹的人模样。”他的“比兴”,是生活感受的诗化提升,是叙事抒情的艺术妙用。
他在民间鼓点的重复、累加、叠合的节奏、韵律中寻找生动形象地表现诗情的节奏和旋律:“一格嘟嘟葱一格嘟嘟蒜/一格嘟嘟婆姨一格嘟嘟汉/一格嘟嘟秧歌满沟转/一格嘟嘟娃娃撵上看”。
他在“接龙”的手法中寻找复调叠唱的诗格:“半前晌照到半后晌/半后晌照到灯点亮”,“大路小路十八道弯/弯弯都转在我心庵庵”。“笑的人哭哭的人笑/情事一下子乱了套”。“像是做梦像是醒/醒来又像跌进了梦/说是梦还听见吵闹声/不是梦怎没了人影影/是梦是醒还眯瞪/醒时有梦梦难醒”。
他在特定生活情景的环境下,用复调、递进、重唱的形式,通过具体、形象、生动、真实、准确的细节描写,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样态:“双手手我端起三盅盅酒,叫一声哥哥你不要羞回我的手”,“细擀杂面油调汤,第一碗我双手手给你端上”,“墙头上栽葱浇不上水,玻璃上吊线线亲不上嘴”,“前山上听见串铃响/脖子伸了丈二长/坡底下听见串铃响/扫炕铺毡换衣裳/硷畔上听见串铃响//一舌头舔烂三层窗”——这种富有表现形式的复调叠唱,把“信天游”原本的特征推向了更典型、更缠绵、更回环萦绕、更富有诗性、诗味、诗意的境地。
他在语言本身纯净的声响中寻找叙事的诗意表达:“洗一回脸呀搽一回粉/照一回镜子丢一回魂”。
他在拟声词(模仿的和谐)音响与含义的回声中拓展新意:“雁咕噜雁咕噜你不要叫/你给我的妹妹把话捎”。“哨子吹的吱哇哇响/游击队赤卫军上战场”。“拔起萝卜带起泥/什么人留下个活分离?”
他在同音异字的差别中寻找龙尾凤头的接点:“黄龙核桃神木枣/早生贵子挖四角”。“丝溜溜东南风满天云/你道是有晴还是无情”。
他在语言辞藻的韵脚中寻情感递进中的节拍:“锅焦沤得黑豆烂/迟早要跟你把账算”。“荞麦皮皮打糨糨/年年就那个穷样样”。“耍家家,耍家家/柳条轿轿抬娃娃”。
他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成语的拆解与重组中寻找妙对:“哥哥好比百灵鸟/天天在妹的心里叫”。“黑老鸦报喜名在外/几年跌下一屁股债”。“土圪垯林里一起耍大/也算是青梅配了竹马。”
他在民间的生活俗语、方言中提炼诗意的创新:“水米没打牙放大站/日谋夜算把妹妹看”。“说不定哪天就过门/做上些花针扎打散人”。“馍馍白糖就苦菜,口甜心苦你把良心坏;有朝一日天睁眼,小刀子戳你没深浅”。“炕头上狸猫耍瓜瓜/你把谁当成了憨娃娃”。“你妈命薄走得早/就怕没娘的女子疯马野道”。“把那‘烧火棍都放下/老子飞马揭过一房的瓦”。
他在形象、生动的生活场景的形容中营造诗意盎然的境界:“面汤锅里煮红薯/大大呀你怎老糊涂”。
他在农谚、警句、格言的积淀中开掘:“人有钱话大马有膘艳乍/就好像旧社会的黑老大”。“宽天展地说路不平/一定是腿上有毛病”。“狼戒腥荤没人信/盘盘算算有原因”。“长舌婆姨说是非/人没主意受一辈子罪。”“信天游就是没梁的斗/甚会儿想唱甚会儿有”。
他在象声词里寻找诗的节奏:“一串串鞭炮扑啦啦响/欢天喜地进洞房”。“旱苗子逢雨咯嘣嘣长/穷苦人都跟了共产党”。
他在名词动用、动词名用的互换互置中,提炼直率中的含蓄,自然中的意蕴:“大白天走路还梦梦”,“冒铰牡丹胡画画”,“又是哭来又是闹/才把张掌柜说听了”。
他在“我把你当成穿衣镜/你把我当作了一阵风”的形象对比中寻找,他在“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长流”的老调重弹的蝉蜕中寻找,他在“叫一声‘干大你喝醉了?/婆姨还不知在哪个炕圪崂”的特定场景下寻找——俗里是雅的具有无限张力的诗句。
他在努力地寻找、开掘、提炼、创新。他在精心地筛选、推敲、打磨、整理。正由于他长期扎根于“信天游”这片广袤的沃土,加之他聪慧的天赋和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耕耘,才浇灌出属于他的这片“信天游”的园地。
霍竹山“信天游”的叙事,是用诗性表达方式裁剪叙事情节,用比兴手法切割叙事时空,用语言声响、韵味重铸叙事情感的节奏和律动,用榫接套铆的技巧再造詩性叙事的内在层次。他的叙事有时在“蒙太奇”和“拉洋片”式的款式里;有时在把叙述融化、消解、埋藏、包裹于抒情的节奏、声响、音韵、旋律中;有时在一个行为方式引发的多种结果的反复咏叹中;有时在对象、事物、场景的渲染、烘托、夸张的叙说中。他的叙事往往与抒情只连那么“一口气”。看“老郝双手拉定杨五娃/快跟我上你丈人家”,完全是一种生活情景的白描;再看“老侄儿踏一脚喊一声/整个河套会刮一阵风”,贴近生活,夸张得当。还有“啧啧啧,再说人家张巧巧/打上灯笼你哪里找!”绘声给色,携情带韵。这些形成了他在神与物游,移情叙事,时空交融,叙唱结合,情理并行,递进叠合,比兴对应,逐类旁通,象征隐喻,携情带韵的审美效果。
五
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的诗时,提出:“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诗意地栖居是“天地人神”和谐相处在整体存在之中。海德格尔的“神”在这里应理解为“神圣”、“崇高”、“圣洁”、“超越”。她连接着人的“神情”、“神思”、“神态”、“神气”、“神志”、“神心”、“神往”、“神通”、“神经”。在这关联“中间”,她们共居一体,相依相在,相克相生,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转位、各成其是。这种关联是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的。这种“天地人神”和谐相处的诗意地栖居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道家认为天体宇宙之“丹”是太阳,它无私、公平、崇高、纯洁、神圣、博大,光照千秋,哺育万物。如果海德格尔的“神”在中国的诗学中可以重新命名的话,我以为是“太阳”。霍竹山在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和谐相处的经营中,用太阳置换神位。“骡子马儿一色色红/太阳照亮延安城。”他在陕北信天游的民歌形式中,用赶牲灵人的心灵、人言点燃诗化的情感,敞亮被“遮蔽”已久的“原本性关联”的语言,营造诗境豁然,诗情沛然,诗意盎然的叙事抒情诗。
赶牲灵的人的生存是艰辛的、劳累的、饥寒的、严峻的、现实的、残酷的,而诗是浪漫的、理想的、奢华的、超越的。苦难的生存者如何以诗,排遣胸中之悲怆呢?痛极而歌,长歌当哭,悲歌动地。苦者以悲唱的形式排遣心中的苦闷,化孤寂于长天,融孤苦于大地,在凄婉苍凉、苦笑放达中,听从命运之音的召唤,朝着太阳走,追寻自已理想的精神家园。
人类真正理想的栖居家园是天地人神和谐共处的生存状况。这里的“神”就是高居于人头顶之上的太阳神——阿波罗。当《东方红》的歌声回荡在宝塔山上、黄河两岸、紫禁城头、宇宙太空时,诗神就把“太阳崇拜”镶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陕北信天游民歌的形式中。这里的“太阳崇拜”是领袖崇拜、青天崇拜、平等向往、自由企盼、幸福渴望。霍竹山的信天游中弥漫着“日神崇拜”的耀眼光芒。他的这种“日神崇拜”的思想是本能的从民间文学固有的品格中继承过来的:“红格彤彤太阳蓝格英英天/跟着党走路路越宽……”,“眼瞅着宝塔山暖洋洋/延安升起了红太阳”,不就是续唱着李有源《东方红》的主题吗!太阳在他的诗中是崇高、伟大、光荣的:“太阳上来满山红/为边区赶牲灵真光荣”。太阳在他的诗中是前行者的“报时表”、“领路人”:“太阳冒花花天放明/李丕把牛村长拧起身”,“六月的日头当天烤/运输队爬上了红崖窑”,“七月的日头热难挡/运输队路过阳平庄”。太阳在他的诗中是守望爱情的象征:“太阳从西边出来东边掉/哥哥也忘不了妹妹的好”,“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什么人留下个人爱人”。太阳在他的诗中是苦难者向崇高、伟大、神圣、高天倾诉生活之苦的对象:“风吹日晒脱了一层皮/朝思夜梦头也抬不起”,“月亮底下晒阳哩/不知白天黑夜哩”,“太阳出来好像浇了水/晴死的天气也有几分霉”。
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中的人是天地中的人,是自然中的人。人的诗性、诗能、诗慧、诗才、诗智、诗思、诗品就是人能以自然的天籁之声,风雨之音,山水之韵与太阳之上崇高、神圣、伟大、仁慈的精神对话。巴赫金指出:“自然元素是深刻的积极因素,这种自然元素在这里完全不是以个人利己主义的形式展现出来,也完全没有脱离其他生活领域。在这里,物质——肉体的因素被看作包罗万象的和全民性的,并且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而同一切脱离世界物质——肉体本源的东西相对立,同一切自我隔离和自我封闭相对立,同一切抽象的理想相对立,同一切与世隔绝和无视大地和身体的重要性的自命不凡相对立。……因此,一切肉体的东西在这里都这样硕大无朋、夸张过甚和不可估量。这种夸张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性质。在所有这些物质——肉体生活的形象中,主导因素都是丰腴、生长和情感洋溢。”霍竹山“信天游”中是肯定自然因素的,牲灵是自然的符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诗人赞美张彩彩的女性人体美:“端格溜溜的好身材/长辫子一甩惹人爱/水灵灵脸蛋妙条条手/扑闪闪的眼睛露水珠”。诗人承认人的性爱存在的合理性。他在人的自然性在苦难的炼狱过程中,与崇高、神圣、伟大、博爱的太阳精神对话中,表现其迎着太阳走,靠近神圣、崇高的进步性和文明性。彩彩和石榴花一样从狭隘自私的爱情中走向革命,都是走向太阳的行动。太阳是自然的灵魂,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太阳给予的。人的生命中的自然属性是带有原始野性的,但人的生命大脑中毕竟含着太阳给予的思维,向太阳靠拢是人思维——慧性的本能(向善、求真、爱美)。人靠着这种天赋的慧性本能,与“天地神”平等和谐相处。天,在霍竹山的诗中不仅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生活化、情感化、精神化、人格化、心灵化的对象:“老天爷高兴了看人面”、“咱金鸡沙就好比两重天”、“富贵由天不由命”、“一人头上顶一方天”、“我把你当头顶一方天”、“过去哥哥就是我的天”、“就盼着天上把票子下”、“天上牛郎会织女”。地,在他的诗中不仅是万物生长、五谷飘香、藏宝聚才、百兽生息的土壤,也是通天通人通神的有灵之地,是人把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圣地:“天灵灵,地灵灵”、“黄土地好比刮金板”、“土地好比咱命根根”、“抓一把黄土当药贴”。
天地人太阳是一个整体和谐的关联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天地人太阳各有其性,各赋其职,各负其责,各行其道,他们非你不可的关联着。他们互相依存,彼此借道,任何一方不可能独立存在;他们又彼此自由,相对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成为主宰与中心;这种关联是隐匿的、本原的、不会消失的;这种关联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也是无法逃避的。人与自然、人与天地太阳、人与存在、人与语言的关联是本原性关联,这种关联决定了人的本质,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家园。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历史悠久的古老大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培育了散发着东方审美意趣的审美之花。天人合一,以自然写人生,恬逸乐感,一片自然风光就是一个心灵世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诗心、诗魂、诗胆、诗质、诗核。“古风”、“乐府”、“敦煌曲子”、“竹枝词”、“民谣”、“山歌”、“农谚”、“说唱”、“川江号子”、“爬山调”、“花儿”、“信天游”等形式的民间诗歌,构成了中国诗歌这只大鹏的一翼。中国新诗这只大鹏要“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不能没有这一翼。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公木的《十里盐湾》,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阮章竞的《漳河水》等人及其他们的作品。直到今天的霍竹山的系列信天游叙事诗创作,都是这一羽翼上的羽毛。
严格地说,霍竹山是一个在民间文学的原野上采集“信天游”的新古典主义的诗人。人类生命“母题”的原始叙事是人类生命“子题”的现代抒情的源泉。不管“母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发生怎样的形式和特征的变化,其“子题”的生发、成长和变化都潜在深植于“母題”原初赋予它生命形式的“血脉”之中的。“英雄创世说”的叙事诗是“母题”,“现代言志说”的抒情诗是“子题”。现代抒情诗只有连着叙事诗的“母题”呼吸,才能永葆生命的活力。
我们这个民族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太看重外国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发展到有一些文化精英对我们民族文化缺乏基本的、应有的、起码的自信心,他们骂梅兰芳,贬低中国戏曲,蔑视中医是巫术……。
霍竹山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者。他在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的创作立场上,为新诗的民族化、生活化、现代化、诗性化建设而努力,这正是我所肯定的。
责任编辑:张天煜 贺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