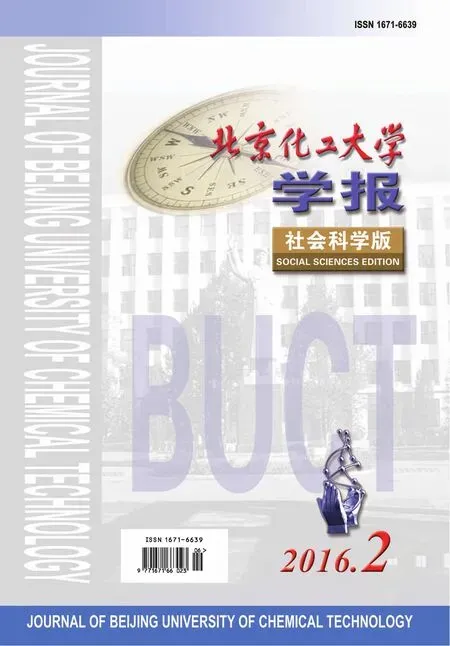关于《破产法》中重整计划规定的再思考
——以破产重整第一案为视角
楼秋然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关于《破产法》中重整计划规定的再思考
——以破产重整第一案为视角
楼秋然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作为我国法院适用《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的第一案,不仅体现了我国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方面的能动性,也折射出《破产法》相关法律规定仍存诸多有待完善之处。为实现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法院一方面应当利用其所拥有的批准权对未出席债权人会议或者投反对票的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应当借鉴美国破产法中的“净收益资本化法”确定重整计划草案是否满足“不低于”的法定标准。另外,《破产法》也应当通过另设投票分组或者例外允许其作为普通债权人表决的方式对未能全部受偿的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护。
重整程序;重整计划;利益平衡
一、案情概要[1]
北京市仙琚生殖健康专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仙琚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26日,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仙琚公司于2006年10月因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破产偿债申请,随后在同年12月向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停业 (申请停业的期限为1年)。根据中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仙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992.68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151余万元人民币,净资产额为负1159余万元”。海淀区法院于2006年12月22日裁定仙琚公司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并进行了公告。经过法定的债权申报程序后,共有45名债权人进行了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2200余万元 (假设全部债权均为无担保债权,则债权人的可受偿率为45.12%)。
在仙琚公司申请破产后,一直有意运作一家医院的维多丽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多丽亚公司”)迅速与仙琚公司取得了联系,表示有意获得仙琚公司的全部股权。在双方已经就收购的方式和价格谈妥后,维多丽亚公司又和仙琚公司的部分债权人进行了协商并且了解了这些债权人对于债权清偿比例的期望值。在此基础上,一份对仙琚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方案逐步形成。2007年4月10日,在法院组织下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该重整协议进行了讨论。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仙琚公司的39名债权人与维多丽亚公司达成了关于债务清偿的和解协议。在2007年5月25日举行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中,该重整协议以88%(赞成重整协议的债权人人数比例)和97%(赞成重整协议的债权比例)的双重多数予以通过。
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是第一例适用新《破产法》中规定的“重整程序”的案件,在此案中,海淀法院的处理方式获得了来自学界的好评,例如王卫国教授认为:“此案是企业重整的典型案例,海淀法院的创造性处理方式符合《破产法》规定破产重整的立法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拯救破产企业,尊重商事主体的团体性,维护商事主体的稳定,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同时,此案的处理过程表明法院尊重市场对资源的调配机制,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法院公开、谨慎、适当地适用了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保证重整程序不因个别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导致破产重整程序的失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2]尽管如此,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仍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之处。本文试图从维多丽亚公司分别与债权人订立让步协议的方式是否妥当、对于未参与债权人会议表决或者投票反对重整方案的债权人的利益如何进行保护、法院如何判断重整方案之可行性尤其是仙琚公司获得的行政许可权能否被认定为资产等角度进行论述。
二、对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中问题的反思
虽然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在海淀区法院的积极推动下顺利结案且参与重整各方均未提出异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该案就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反思和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本文将从已经通过的重整方案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假设债权人会议并未通过该重整方案时法院应当如何行使其“强制批准权”这两个角度进行论述。
(一)已经通过的重整方案是否仍然存在瑕疵?
1.维多利亚公司分别与债权人订立让步协议是否妥当。维多丽亚公司在与仙琚公司谈妥收购的方式和价格后,通过与债权人进行个别协商的方式共与39名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了协议。事实上,在2007年5月25日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中通过的“重整计划”不过是这39份协议的内容附加“根据已达成和解协议的债权清偿比例的平均值41%的比例”对于其他债权人进行清偿。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维多丽亚公司的行为是否妥当?本文认为,维多丽亚公司的上述行为并不存在问题。虽然,《破产法》第82条明确规定“重整计划”应当在“债权人会议”上进行表决,但却并没有规定重整计划的内容也必须在“债权人会议”上形成。相反地,《破产法》第80条规定,“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债务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应当包括一些必备的内容如债权的受偿方案等(第81条)。因此,维多丽亚公司通过个别协商形成重整计划草案的方式至少从《破产法》的表面规定来看并不存在不妥之处。更进一步,虽然维多丽亚公司与债权人进行的是个别协商并且债权人之间彼此全无沟通,很可能产生“厚此薄彼”的情况,但是,由于最终的重整计划草案的内容需要在债权人会议上进行公开并征得双重2/3的债权及债权人的同意,而这也就在另一层面上保障了各债权人的知情权和真实意思之保护。但此时还存在另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未参加债权人会议或者投出反对票的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护?
2.未参加债权人会议或者投出反对票的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在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中便存在这种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在通过草案的债权人会议上有5名债权人没有参加、4名债权人投出了反对票[3]。对于少数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在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大多数债权人已经通过私下协商获得自己满意的结果从而使得“债权人会议”更像是在“走过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破产法》除双重多数表决以外并没有在“债权人会议”的表决问题上进行更多的限制,但是,我国《破产法》也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不批准已经被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而法院的这一权力完全可以被用来保护少数债权人利益。在美国破产法上,法院强制通过的重整计划必须满足第1129条(b)(1)的规定,即该计划没有不公平的歧视对待并且是公正、衡平的[4]。虽然该项条款仅仅是用来限制“强制批准权”的,但其法理内涵和精神完全可以用来保护债权人会议中的少数债权人。因此,虽然我国《破产法》并没有对于法院如何行使“不批准”的权力进行规定,但在重整计划草案的内容对于少数债权人构成不合理的歧视对待或者明显的不公平时,不予批准是符合法律实现正义的基本精神的。在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中,由于对未参加会议及投反对票的债权人按照所有债权人的平均清偿率41%进行了清偿,加之没有其他不公平的情况,少数债权人保护的问题便不能成为法院动用不批准的权力的理由。
(二)假设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法院如何行使其强制批准的自由裁量权?
在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中,由于重整计划草案获得了债权人会议的通过,便不存在法院行使其强制批准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该项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通过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在破产法上非常重要而我国《破产法》却付之阙如的问题。我国《破产法》第87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必须使得 “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并且“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但是,“不低于”的判断标准即判定重整计划执行后债权人能否获得更多清偿的方法是什么?“具有可行性”又是依据什么进行衡量?结合仙琚公司案的特殊情况,即“卫生经营许可权”这样的行政许可权的存在是否可以作为法院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判断的考量因素等等,无论是《破产法》还是理论界都似乎准备不足。因此,本文将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简短的分析和回答。
1.依据何种标准判断“不低于”要求的满足与否。王卫国教授认为:“法院强制批准的具体条件界定主要采用清算检验标准,所谓清算检验标准,是指债权人依照重整计划可获得的清偿,以不低于他们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清偿分配额为已足。”[5]这种清算检验标准对于计算债权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的受偿数额固然十分妥当,但是,《破产法》第87条对此没有规定,而且在学理上也不适合将它作为计算重整计划执行后债权人可以获得的清偿比例的标准。因为,破产重整程序的法理基础在于,特定企业的资产只有在整合使用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因为只有如此企业作为一个持续经营主体的价值才能得以保存。而“清算检验标准”则是要将企业这一整体进行分拆,即使存在某些财产整体出售价格超越单价的情况,各财产也只能按照自己的单独价值进行变现,而且企业原本拥有的商誉、市场份额、交易关系、各项可以产生大量实质性利益的行政许可权等都将随着企业的终结而消灭。正是这种显著的差别,使得清算检验标准不适合在重整程序中计算企业的价值。因此,在美国破产法中,在判断重整计划执行后的债权人可受清偿比例时,采用的是一种被称为“净收益资本化”(The Net Capitalized Earnings)的方法,这种计算方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过符合条件的专家证言确定该公司未来可能的收益额度再除以合理的资本化率从而得出公司的价值[6]。这种企业价值的衡量方法能够从企业整体出发,将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资产纳入企业价值的衡量范围内,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企业的真实价值。
2.“行政特许权”的存在是否可以作为计算方法的考量因素。由于行政许可权尤其是仙琚公司案中的“卫生特许经营许可权”不具有可转让性,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其不可以作为财产计入企业的价值。对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高富平教授即认为,虽然行政许可本质上属于一种资格,权利人不能进行出租、出借、转让等处分行为,但是由于在商业领域中商号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在商号下所有能够带来利益或影响营业能力的东西均可以成为企业财产,并且在重整中与企业一并转让[7]。
(2)一项权利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并不是判断其是否具有“财产属性”的决定性标准。从民法理论上说,财产权只要具有直接财产利益即可[8],并不必须具有可转让性,例如宅基地使用权不具有可转让性但仍然属于“财产权”。
(3)行政许可权的内容具有“双重”性质,其中的许多内容具有财产权的属性。按照霍菲尔德教授的“权利分析”理论,我们可以将任何权利(无论公权或者私权)分解为“权利、特权、权力、豁免”四项内容[9]。仅以其中的“特权”为例,拥有行政许可权的主体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获取经济利益,便可见其具有的私权性质和财产权性质。值得注意的是,王涌教授早就指出:“将财产权仅限于私法上的权利是财产权观念的最隐蔽的误区。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由于国家公法对经济领域的规制与调控,私法所赋予人们的经济自由又被公法收回,然后赋予特定的少数主体,使经济自由成为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许多重要的财产权实质上已经表现为公法上的权利。”[10]
(4)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判决的一个案件中,该法院对于已经取得行政部门同意而进行行政许可权转让的合同的效力进行了肯定①参见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3)怀民初字第01341号民事判决书。。
(5)《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规定,任何“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都可以认定为属于“无形资产”从而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公司价值。如此进行会计上的无形资产确认的目的和宗旨在于“尽量保证商誉的最小损失”。由此可见,在会计上是完全可以将“行政许可权”纳入企业价值的计算的。
(6)如果采用和美国破产法相同的“净收益资本化”方法计算公司作为持续经营实体的价值的话,行政许可权包括仙琚公司案中牵涉到的 “卫生特许经营许可权”由于能够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未来收益的有无和多寡,因此也就应该被允许作为法院考量的标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即使行政许可权不被认为是一种“私权”或者“财产权”,只要它能够确实地对于企业的未来收益或者价值产生影响,就应该被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内。
(7)不将类似于“行政许可权”这样的能够产生公司未来收益的“资产”纳入企业价值的衡量将有悖于商业实践。例如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在电子产品市场上占据巨大的利润份额,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它迷人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在破产清算中是不可能体现为金钱利益进行变现的,但是在企业重整的过程中就将大大地影响未来收益的可能性和公司收购者对于公司价值的衡量。
(8)本节对于“行政许可权”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应当纳入企业价值计算的论述还可以延伸到其他不可转让但对于企业未来收益产生影响的各种公司组成部分之中,例如公司对于一位非常具有才干的管理者拥有的劳动合同等。
3.“可行性”的判断标准。我国《破产法》第87条明确规定,法院只有在重整计划具有“可行性”时方可行使其强制批准权,但是其并没有对如何判断可行性作出更多规定,破产法教科书也并没有对该法条进行更多的解释[11],但不少学者借鉴美国破产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论述[12]。美国法院在处理重整计划的可行性或者企业作为持续经营实体的价值的可信性的问题上,除了依赖专家证人的意见之外也会作出许多实质性的判断。比如,在“In Re Ascher”案中[13],法院在听取专家证人的意见之后,还对专家预测的合理性、申请重整的洗衣公司在营运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及可能的损失 (尤其是考虑了个案中该公司所在地区的水质对于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的特殊情况)等问题作出了实质性的判断。美国法院的这种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司价值衡量的态度与我国法院恰恰形成了对照。邓峰教授便曾经指出,对公司价值的衡量虽然主要是会计、审计等职业的长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就应当袖手旁观[14]。结合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的个案情况来看,法院不仅应该关注会计、审计报告中对于企业价值的衡量,还应当充分考虑行政许可权可能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增值、仙琚公司所处市场的竞争状况、其他供货商和债权人等交易对象对其所保持的信心、新投资方的能力等问题进行综合考量得出独立的判断。
三、对《破产法》关于重整计划的其余规定的思考
(一)强制批准权行使条件对于债权人保护仍存缺漏
我国《破产法》第87条既规定了法院的强制批准权,也规定了行使该权力的条件。从条文的内容来看,因为其要求所有债权人均获得不低于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所能受偿的比例,从而给予了债权人充分的保障。然而,第87条对于少数债权人的保护却存在缺漏。以普通债权人为例,第87条规定了“不低于”这一要件但忽视了在“不低于”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少数债权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可能性。因而,本文主张参考上文提及的美国破产法方案,要求法院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确保该计划没有对于债权人进行不公平的歧视对待且内容公正、衡平。这不仅符合法的正义要求也符合《破产法》第87条的内在精神,因为87条第4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由此可见公平、公正同样是强制批准权的一大内涵。
(二)对于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存在不足
我国《破产法》第75条规定:“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这意味着在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担保债权人的担保物权将被限制行使,对于担保债权人的保护问题便比和解、清算程序中的担保债权人的保护更加突出。当然,担保债权人可以通过拒绝重整计划草案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即便如此,法院仍然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批准权推进重整程序。当然,这一权力也会受到第87条第1款的限制,即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就用作担保的特定财产获得全额清偿。该款的规定与美国破产法第1129条(b)(2)的内容具有实质上的相似性[15]。第87条第1款的含义是,只要重整计划执行后给予担保债权人的清偿超过了重整计划通过时的担保物价值,就可以由法院行使强制批准权,但是,这种看似对于担保债权人提供了充分保护的规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在许多情况下,用作债权担保的特定财产从设定担保权时其价值便低于债权额,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其他原因发生了贬值,那么担保债权人便会有一部分权利处于无担保的状态。而根据《破产法》第59条第3款的规定,除非其放弃优先受偿的权利,否则便不对债权人会议的许多事项享有投票权。另外《破产法》第87条又将担保债权人与普通债权人分为两组不同类别的债权人,却并没有明确规定担保债权人是否可以参加普通债权组的投票。如果在此情况下,部分债权已经不受担保的担保债权人(不放弃优先受偿权)不能参与普通债权组的投票,那么这部分债权是否受 “重整计划执行后受偿比例不低于清算程序中的受偿比例”这一要求的保护?
本文认为,针对此种情形下的担保债权人保护可以采用以下方案:1.允许担保债权人就不受担保部分的债权参加普通债权组的投票;2.在《破产法》的重整程序中增加一个投票分组即 “不受担保部分的担保债权人组”;3.要求在决定是否强制批准时将这部分不受担保的债权纳入“普通债权”的“不低于”要求进行衡量。
(三)是否需要引入美国破产法上的“绝对优先权”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权力行使问题上,美国破产法第1129条(b)(2)(B)要求只有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时,法院才可以强制批准重整计划:(1)或者确保无担保债权人能够获得计划通过当时所有债权的价值;(2)或者在无担保债权获得充分补偿后才能对其他劣后权利人进行利益分配[16]。以上内容被学界称为“绝对优先权”规则。由于在债务人破产的情况下,(1)中的情况大多数意味着全部清偿,如果(1)可以被满足,那么许多债务人就根本不会申请破产。而(2)要求劣后于普通债权者在普通债权获得充分补偿前不能获取任何利益,从而很可能大大挫伤了以收购者身份参与破产重整程序的外部投资者。由此可见,“绝对优先权”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有力地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却很有可能挫伤外部投资者参与破产重整的热情。在讨论是否应当引入该规则之前,我们必须注意,美国破产法上存在一项被称为 “新价值”的例外(New Value Exception),该项例外的含义是,如果劣后于普通债权人的其他利益持有者能够为公司输入一种“新的价值”,就可以获取其自身能够获得的部分或者全部利益。不过,目前美国破产法的发展趋势是只有在这种向公司输入新价值的机会是同时可以在劣后利益持有人和其他更高顺位的利益持有人之间进行竞争时,方能适用此项“新价值”例外[17]。
我国《破产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所谓的“绝对优先权”规则,但是该法第77条明确规定:“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出资人不得请求投资收益分配。”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建立了保护债权人的“绝对优先权”规则。但是由于《破产法》第77条使用的是“不得”这种“强制性”的术语,如果就此将其认定为“强制性规则”很可能与“绝对优先权”规则一样挫伤外部投资者参与破产重整程序的积极性。因此,本文认为,为了充分发挥“绝对优先权”规则保护债权人的功能,并且避免其僵化适用的弊端,有必要引入“新价值”例外,或者在法解释学上将第77条解释为“任意性条款”,允许各债权组进行表决并接受法院关于“公正和衡平”的检验。
四、结语
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是我国法院适用《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的第一案。该案体现了我国法院在适用《破产法》方面的积极态度和能动性,同时也因其特殊的案情反映出我国《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尤其是“重整计划”的内容有诸多待完善之处。破产重整程序是在破产法中与破产清算、破产和解并驾齐驱的一项内容,也是使企业重获新生的重要途径。因此,完善破产重整程序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关于重整计划的内容更是具有平衡不同类别债权人以及破产重整程序参与各方利益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从仙琚公司破产重整案出发,认为维多丽亚公司分别与债权人进行联系确定让步协议后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方式并不违背《破产法》规定的程序,但认为应当要求法院在行使“批准权”时考虑公正和衡平,保护未参加会议或者投票反对的债权人的利益。在假设该重整协议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时,法院应当采用“净收益资本化”方法确认“不低于”标准的满足,应将行政许可权等可以为公司提供未来收益的无形资产纳入企业价值的判断之中,除会计、审计报告之外,还必须结合个案特殊情况综合判断可行性。法院在行使强制批准权时也必须考量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公平原则。本文还建议允许担保债权人在特定情况下参与普通债权人的投票,或者法院在普通债权组中也考虑不受担保部分债权的保护问题。对《破产法》第77条的适当突破也是提升重整程序成功率的重要内容。
[1][3]吴晓锋.适用新破产法审理全国首例破产重整案之台前幕后[N].法制日报,2007-08-12(10).
[2]北京商报.北京首次依新破产法使企业重生[EB/OL]. [2007-10-18].[2015-09-15].http://money.163.com/07/1018/02 /3R290OK1002524SJ.html.
[4][15][16][17]Holleran,Holleran,McMickle,Corr. Bankruptcy Code Manual[M].Thomson West,2003.p1129, p1143~1144,p1145.
[5]王卫国.破产法精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p260.
[6][13]Margaret Howard.Bankruptcy:Cases and Materials [M].Thomson West,2001.p791,p891~892,p890~895.
[7]高富平.浅析行政许可的财产属性[J].法学,2000(8):p24.
[8]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p36.
[9]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J].Yale Law Journal,1913(26):p26.
[10]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1999.p110.
[11]范健,王建文.破产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p220~221.
[12]赵泓任.企业破产重整计划可行性的法律分析[J].法学杂志,2010(6):p37~39.
[14]邓峰.普通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p320.
On the Reorganization Plan in Chinese Bankruptcy Law
Lou Qiuran
(College of Civil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 CUPL,Beijing 100088,China)
As the first case applied pertinent provisions governing the reorganization plan in Chinese Bankruptcy Law,the case Xianju reflects some flaws of those provisions in the Bankruptcy Law.In order to achieve both the goals of justice and efficiency,court should not only use its approval authority to protect the creditors who’s absent in the creditors’meeting or against the plan,but also take the relevant articles on capitalization of net earnings in American Bankruptcy Law as reference to determine whether reorganization plan draft meet the mandatory standard of“no-lower-than”.In addition,the law should take some measures to protect secured creditors whose claim cannot be covered by guaranties.
recombination procedure;reorganization plan;interests balance
D922.291.92
A
1671-6639(2016)02-0040-05
2016-03-02
楼秋然(1990-),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商法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
——以《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五条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