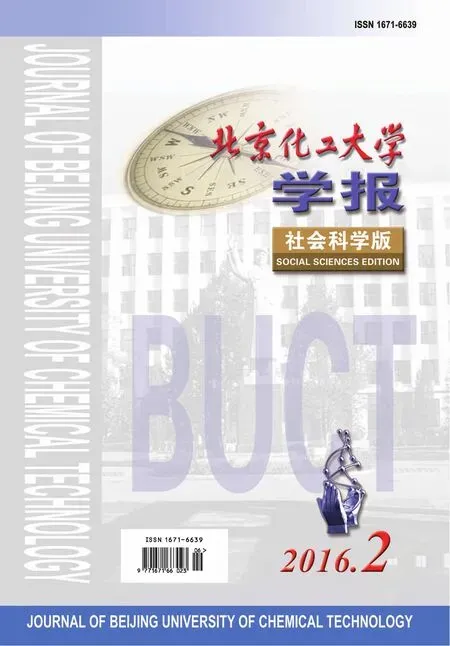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宿命意识
——以《聊斋志异》中的果报不爽模式为例
包树望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29)
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宿命意识
——以《聊斋志异》中的果报不爽模式为例
包树望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29)
果报不爽思想是人们对坚守、践履善德予以鼓励和奖赏的空幻的宿命性许诺,其本质是道德宿命意识,具体表现在古典小说果报不爽模式的德行之因、福祸之果、果报相继不爽及其主宰力量上,因为展现德福相配、人际和谐、世俗幸福等,道德宿命意识也具有审美特质,《聊斋志异》中的果报不爽相关篇章对这些的表现较为集中细致。此外,《聊斋志异》部分篇章、情节以心理情感为依据,突破了道德宿命意识,有的还达到了理想的自由境界。
果报不爽;道德宿命意识;聊斋志异
佛教果报观念主要包含因果缘起、业报报应、六道轮回等,认为世间万物必有原因、缘起和结果,即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相继,进而将人内心活动及其外在表现的言语行动称为业,根据其是否感召有益或有害于众生身心的结果,将其划分为善、恶、无记,世间众生因造业的不同而有不同业报,业报分别为天道、人道、畜生道、阿修罗道、饿鬼道、地狱道,是为六道,世间众生如不寻得解脱,则永远在此六道中生死流转。道教的承负观载于 《太平经》:“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滴,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畜大功,来流及此人也”[1]。个人的福祸受到祖先善恶的影响,同样自己的善恶也对后代的福祸发生影响,祖先的积蓄大功或大过是“力行善反得恶”、“行恶反得善”的原因。
传统文化中的果报不爽思想是底层民众结合传统道德观念,吸收了上述佛教果报、道教承负观有关个人福祸受先人善恶影响、佛教果报观中因果业报和六道轮回的宿命性观念与形式,分别予以扩展化,将所有道德范畴和整个物质人生纳入进来,将儒家道德对个人精神人格的建构作用转换为对个人物质生存的决定性影响,形成的个人道德与现实物质人生具有绝对因果律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简言之,果报不爽以主体的道德意识与行动为判断依据,或对其行德积德、失德败德分别施以奖惩,或以主体的道德之善恶解释其所受之福祸,强调善恶福祸丝毫不爽,力图劝人向善。
文学孕育于文化并表现、塑造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研究需要将古代文学纳入探讨视野。中国古典小说的劝惩创作理念、作品的印售与说演等形式使民众事实上参与创作,其思想情感、理想观念等对小说题材的选取、人物的设计、情节的发展等有着极大的影响。古典小说及其情节模式、思想意涵是蕴涵于、也蕴含着古代社会底层
民众的思想观念世界,并不是儒释道思想学说、宗教教义简单直接地敷衍,而是俗文化层面的底层民众对儒释道等思想观念进行吸收、改造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学化表现。与其他小说相比,《聊斋志异》中涉及到果报不爽的篇目更多,通过神仙狐鬼精魅等超现实的形象,“用传奇法,而以志怪”[2],全面细致地展现了此模式的诸方面特质。因此,关于《聊斋志异》果报不爽故事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对果报不爽模式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道德宿命意识的探讨尚有不足。所以,以《聊斋志异》为例,结合其中果报不爽的相关章节,有助于我们具体而微、深入细致地探讨道德宿命意识这一文化心理结构,也有助于我们对《聊斋志异》这一经典文本的理解。
一、果报不爽的具体表现
果报不爽具体可分为德行之因、福祸之果、因果前后相继不爽及其实现力量等要素,其在 《聊斋志异》中表现如下:
(一)德行之因与福祸之果在性质上正相关,具有一致性,即善有善报(福)、恶有恶报(祸)。如“异史氏曰:‘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3]“福善祸淫,天之常道”[4]。“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5]。《聊斋志异》中作为果报之因的善德主要有恭敬孝顺、坚贞慧勇、情深义重、友恭和睦等等,其果报之福果则主要关注个体自身生命以及作为自身生命延伸的虚幻魂灵和现世子孙的现实物质性人生幸福,如娇妻美妾、子孙众多、科举及第、富足显贵、长寿成仙等;恶德有淫荡负心、悍妒悖逆、贪财忘恩、悭吝贪墨等,其果报之祸果则有恶疾短命、家破人亡、堕入地狱、托生畜生等。果报不爽在德之善恶、报之福祸上几乎涵盖了传统道德与生活的所有方面,其具有对世事人生普遍绝对的影响和对个人心理与行为的善恶的精微明辨,善福恶祸之相继纤毫不爽,具有普遍必然性。这样上节引述的儒家对道德的强调被推到极端,道德对个人精神人格的建构作用也被转换为对个人物质生存的决定性影响。
(二)德行之因与福祸之果在数量规模上并不正相关,不具有一致性,即作为因由的德行的善恶并不因为其单一、微小而决定作为果报的福祸的单一和纤微。首先,善恶的心理、行为有一,则会有福祸果报相随,有的时候甚至能够达到“一善拯万恶”、“一恶毁百善”的程度。如“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某耶?罪恶贯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为己有。此等横暴,合置铛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阅簿,其色稍霁,便云:‘暂送他去。’……上记:崇祯十三年,用钱三百,救一人夫妇完聚。吏曰:‘非此,则今日命当绝,宜堕畜生道。’”[6]“冥王曰:‘是宜作羊。’……吏白:‘是曾拯一人死。’王检籍覆视,示曰:‘免之。恶虽多,此善可赎。’”[7]“主人曰:‘秀才以阴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8]邑中刘姓和陕右某公恶行累累,因果早定,本来“合置铛鼎”、“是宜作羊”,但分别因曾救一人夫妇完聚、曾拯一死而免除恶报,即“此人有一善合不死”、“恶虽多,此善可赎”;而毛纪多次被以他人之梦的形式预示其富贵之命运,“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旦夕当有毛解元来,后且脱汝于厄”[9]。但在考前却起了富贵易妻的念头,于是名落孙山,先定的富贵命运未能实现。其次,福祸之果报并不唯一有限,往往是福有多至、祸不单行,福祸遍及个人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善报的福有多至。如《陈云栖》中真毓生得双美为妻,生二女四男,长子中乡选,“母八十余岁而终”[10];《某甲》中某甲私其仆妇而杀仆,十九年后,其仆转世为盗贼,杀尽其家七十二口而去。
传统道德观念一方面强调德行的纯粹,极力避免德行的亏损,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11]。另一方面鼓励迁善改过,重视善心善念的萌生、保有等,如“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12]。“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13]。“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14]。所以果报不爽模式在重视善恶的区分之后,对善无比珍视、对恶深恶痛绝,对善的奖励、对恶的惩罚都是不遗余力,强调福祸的叠加性、丰富性,这是传统文化中道德纯粹、道德至上观念和奖善惩恶、劝善去恶目的的双重作用。
(三)实现善恶福祸的前后相继并纤毫不爽的主宰力量主要有:政府官员或游侠刺客,如《胡四娘》中擢第后“十余年历秩清显,凡遇乡党厄急,罔不极力”[15]的程孝思、《红玉》中倏忽而来、不留姓名、“越重垣入,杀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16]的无名侠客;魂鬼,如《霍生》中被无端污蔑、不堪凌虐、自经而死的严妻的鬼魂、《聂政》中从墓中突出“抱义愤而惩荒淫”的聂政魂灵;宗教偶像、花精狐魅等,如《公孙夏》中的关帝、《香玉》中耐冬精和牡丹精、《小翠》中的狐狸精;冥间地狱,如《僧孽》、《邵九娘》;无具体形象的天帝、造物等,如《王六郎》、《青梅》。个人或亲朋及第为官、官员的清廉崇德、侠客的出现等都不是普遍必然的,所以在本质上与后四类相同,都是超现实的想象,是虚幻的。
此外,果报不爽模式还一方面体现在小说人物心态上,即其“自怜、自大、自安的心态”[17],顾影自怜、妄自尊大、苟且偷安,内心虚弱而寄希望于道德宿命改变一切、获得一切;另一方面体现在情节发展、人物性格等方面,即根据果报不爽模式、为了实现果报不爽而对人物情节等或借助巧合、奇遇、神迹与神力,或直接进行僵硬地安排,如《锦瑟》中,王生家清贫,妻兄弟鄙之,妇尤骄倨,自享馐馔,与生脱粟,王悉隐忍之。一日,王应试归,“妇适不在室,釜中烹羊臛熟,就啖之。妇入,不语,移釜去。生大惭,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妇恚,问死期,即授索为自经之具。生忿投羹碗,败妇颡。……妻召两兄至,将箠楚报之……”[18]。妻之骄倨无忌跃然纸上,且“于沟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余无耗”,方招赘贾某,似有充足的理由和方式应对王生归来后可能的责难,且其骄倨无德很可能置责难于不顾,所以其自杀不符合其人物性格,可能只是果报不爽模式的僵硬作用。为了实现善恶有报、果报不爽,作者脱离甚至违背人物性格强硬安排人物行动和故事情节。
二、果报不爽的道德宿命本质
果报不爽思想对传统传统道德观念、佛教果报、道教承负观等都有继承和改造,将传统道德观念对道德的强调推到极端,并建构起德福之间的绝对因果关系,其实质是道德宿命意识。
果报不爽对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曲解也能说明其道德宿命本质。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9],“天道无亲,常与善人”[20]。将善恶同天道的肯定与辅助、个人与家族的福祸联系起来。但这些与佛教果报、道教承负思想只是表面形式的相似,其实质并不相同。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例,其本意并不是个人的宿命,而是人类总体存在必然规律的揭示,是人类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着人类社会政治和个体心理行为的逻辑规律。《左传·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可谓明证:“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若是则必广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21]刘康公认为“宽肃宣惠”、“敬恪恭俭”是君主和臣下必备的品质和行事原则,并详细论证节俭、奢侈与个人、家族存亡的关系。节俭与奢侈涉及对个人内在方面的动物性欲望的态度,涉及对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源、物质财富的态度,涉对人类存在发展、国家政治事务、底层百姓的态度。类似的说法很多,比如:“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韩非子·十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 《咏史》),“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五代十伶官传序》)。这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践履与个人、家族乃至国家福祸之间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思考的对象范围是个人的整个人生、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长久历史,并没有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在一时一事上将个人道德善恶与福祸建立起普遍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果报不爽则将人类总体的必然转化为个人一时一事的必然,并幻想出种种外在主宰力量来实现这种必然,人类总体意义上的“天”也就转变为人格神意义上的“天”,其实质是将道德予以宿命化,将人类总体的必然宿命化为个人的必然。
“‘命’具有个体意义上的无定的偶然性,但因‘自天降’,必然具有超越偶然的品格。因此,人类总体的必然谓之‘天命’,了解并奉行这种必然叫做‘知命’;如果将人类总体的必然机械地照搬到个人命运上,则谓之 ‘宿命’(如就总体或长远来讲是善有善报,但对具体的个体来讲未必如此)。君子知命是对人类总体的光明前途与个人为实现这种光明前途而必然遭遇的命运坎坷有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孔子的‘天命’与‘知命’的意义”[22]。原始儒家道德观念在道德纯粹、道德至上之外,还蕴含着对人的道德追求的主体性的强调,并没有以个人现世物质幸福作为修养道德、迁善改过的目的或劝导手段,而且强调道德高于物质乃至生死。“君子去仁,恶乎成名?”[23]“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4]“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矣”[25]。而上述《聊斋志异》的果报不爽情节一方面将现实物质幸福突出出来,并与个人德行建立绝对的关系,分别赋予目的与手段的意义;另一方面主体选择只是守德或失德,是笼罩在果报不爽模式的外在主宰力量之下的,也就失去了主体性。因为在上述虚幻力量的保障下,果报不爽广布宇内、贯穿古今,不但无所遗漏,亦无可逃避,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服从其安排,所以守德失德的主体选择意味,实质是将个体德行作为致福祸之果报的起因与手段,只是对善赏恶罚的果报规律的把握和利用,是对虚幻主宰力量的崇信。一般而言,底层民众面对德福不相配的不合理现实,既不愿、也无力援引此道德主体意识和理想人格,以悲剧精神加以审视观照而奋然前行,故转而结合果报轮回、灵魂不灭、传统的“报”等思想,选取道德宿命的、虚幻精神上的扭转与解脱的思维方式。这其中,传统道德观念、佛教果报、道教承负观是是此宿命幻想的思想基础和资源,作者、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对真善美、现世幸福、德福相配的心理期望是此道德宿命虚幻想象的内在动力,对人类总体存在的向善的必然要求及具体情境下具体正义人格的体认是其想象的内在依据,对德福相配的应然祈望转变为必然宿命是其内在流程。这既是道德的绝对化,又是现实功利的道德化,道德与现实物质功利幸福从而建立起普遍必然的因果联系,德福之相配、善福恶祸之相继从而纤毫不爽。
于是,个人命运早已被决定,现世之苦乐皆因自己或自己之前世或自己之祖先的作恶失德或行善积德所致。所谓“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26]。“茫茫大劫中,惟孝嗣无恙,谁谓天公无皂白耶?”[27]果报不爽成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成为人们应对、追求福祸苦乐的解释方法、思维方式和可靠途径,即“数”、“定数”、“天数”[28],将宿命道德化,同时也将道德宿命化。“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9]“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0]“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1]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道德要求,而道德宿命意识则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主体性、自足性性彻底消弭。“道德宿命意识,其本质是一种道德上的虚幻的承诺,在设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本体乃至宿命的前提下,告诉人们只要恪守正统的道德观念就会获得应有的一切”[32]。
所以,果报不爽思想的实质是对道德宿命意识文化心理结构的具体展开和形式固化。
三、道德宿命意识的审美特质
道德宿命意识 “因其根深蒂固而不需询问和不准询问,并与迷信心理相融合,故而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宗教的某种功能。它已经积淀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和人们的审美心理之中,因此具有了真正的审美品格”[33]。上面提到德行之因、福祸之果、果报相继不爽和实现此相继不爽的主宰力量等是构成道德宿命意识的主要元素和环节,对这些元素和环节的审美体认,也即对道德本身、现实人生、宿命本身的审美体认,形成了道德宿命三个方面的审美特质。
首先,道德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必须,代表着人类理性,是人类历史实践形成的,并积淀入人的感性心理,从而具有审美品格。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道德本身、德行、有德者都是美的。“妇由此不茹荤酒,闭户诵佛而已。……更衣入棺而卒。颜色如生,异香满室;既殓,香始灭。”[34]死亡本意味着生命力的枯竭消逝、生命的结束,但“颜色如生,异香满室”却使这一过程审美化,其实是对悍妇王氏的迁善改过的道德行为、道德人格的审美。
其次,经过西周初年的理性化、春秋战国的轴心突破,殷商时期的宗教巫舞传统被理性化,中国人从虚幻神灵转向现实人生,并不执著于宗教的彼岸世界,而是珍重于现世生活、此际人生。特别是宋代以后,世俗生活、感性生命在哲学、文学等领域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民间宗教也多落实到现实世俗幸福,人们普遍对现世人生的世俗生活予以审美化的审视。前面提到道德宿命意识的赏善罚恶都是落实于个体自身生命及其延伸的虚幻魂灵和现世子孙、亲属友朋等的寿夭、贫富、贵贱等,这些恰恰是现实世俗人生、人际、生活的幸福、和谐、自由,这就使道德宿命意识具有了第二层的审美品格,即对现实人生、人际乃至物质生活的审美。如,曾经争斗不止的家族,最后“一门事皆决于友于。因而门庭雍穆,称孝友焉”[35]。王成“性最懒。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数间,与妻卧牛衣中,交谪不堪”,但在祖先之狐妻帮助、督促下,终于“治良田三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36]。“后数年,宁果登进士。女举一男。纳妾后,又各生一男,皆仕进,有声”[37]。丰富的现实物质财物、和谐的家族家庭关系、娇妻美妾、儿孙满堂、进士及第、富贵悠游等等,世俗的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其中,对此的种种描写既是人们对现实人生的执著,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审美。
再次,果报不爽的善恶福祸必然相继、纤毫不爽,在形式上成为一种宿命性的必然,由此构成宇宙自然和世事人生的根本规律。它无所不包,不可逃避,即使现世现实肉体生命不受赏罚,死后的灵魂、转世的肉体、繁衍的子孙等也必承受赏之福、罚之祸,对其只能服膺和期盼,每次由福祸溯源此前的善恶都是对果报不爽及其中道德宿命意识的必然性的体认。另一方面,对道德宿命在服膺、期盼之外,亦可加以把握、利用,或积善以求福,或迁善改过以避祸、以求否极泰来,人们对其既深信不疑,又期待得到现实验证,对其现实实现有着强烈心理期待。当此必然规律得到现实经验或主观神秘验证、把握时,便会有较大的心理满足感和对宿命性的果报不爽的体认感。人们因体认、把握此“必然”的形式规律,从而体认由它构成和主宰的世界——宇宙自然的循环反馈、往复回环,以及个体的存在、自由、个体与外界(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等,审美感由此而生。
最后,善恶福祸之必然相继、纤毫不爽的形式蕴含着德福必然相配的内容,而在中国伦理本体型文化中德福相配本身就具有审美品格。在现实中德福难相配,但果报不爽世界中的外在道德正义主宰力量却冥冥中安排此德福相配不爽,惩善扬恶,善恶福祸相继不爽,这是善的,也是美的。实现此相继不爽的道德宿命主宰力量也是美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力量的崇高与巧妙。“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气象威猛,厉声日:‘我聂政也!良家子岂可强占!念汝辈不能自由,姑且宥恕。寄语无道王:若不改行,不日将抉其首!’众大骇,弃车而走。丈夫亦人墓中而没。夫妻叩墓归,犹惧王命复临。过十余日,竟无消息,心始安。王自是淫威亦少杀云。”[38]“颠倒众生,不可思议。此造物之巧也!”[39]“一人不杀,而诸恨并雪,可不谓神乎!”[40]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和人自身力量、人类理性和道德的审美,但其实质上是对想象的外在宿命性力量的审美。这和前一种共同构成对宿命本身的审美。
因为道德宿命意识使道德与物质幸福普遍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前者成为后者的充要条件,使其对道德、世俗生活、宿命的审美相互交融。《考城隍》中,将“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的诗句放入“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和“九年而母果卒”、宋公入室而没、“镂膺朱幩、舆马甚重”[41]赴任城隍的情节之间,更能理解其意蕴。首句是对日常世俗生活的执著,末句是自身凭借道德修养而贯穿阴阳两界,是对自身道德的自足感和审美感,所以“春常在”、“夜自明”。一方面是对儒家道德意识的强调、自足的吟咏,另一方面也有宿命的色彩,是对因九年之赏、九年母卒、赴任城隍等而得到验证的道德宿命、果报不爽中的“必然”的审美体认。由此,诗句既是对道德的自足完满和孝养母亲的世俗生活的审美,更是对道德宿命意识和果报不爽模式所代表的宿命性的 “客观规律”的承认、体认、利用而产生的存在感、自由感、审美感[42]。
当然,道德宿命意识是委个人命运于人类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将人类历史总体的必然幻化为具体个人一时一事的必然,并信仰、期待外在主宰力量保证善恶福祸因果的前后相继与纤毫不爽。正义主宰力量的巧妙、阳刚之美的虚幻自不待言,其所保证的德福相配、人际和睦等和谐之美实际是主体服从、屈服于外在虚幻力量的结果,是自我的麻醉和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主体自身力量的缺失,是主体和谐于外在的、宿命性的道德的果报不爽,是宿命性的和谐之美,有着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内在孱弱性和本质上的虚幻特征。由此,其对现世幸福、善之道德的审美也是虚幻的。
在道德宿命意识中,一切皆是果报,不是反抗,而是接受、等待,寄希望于外界力量审判、奖惩、安排、主宰一切,在自我解脱麻醉的同时,也便安于既定的命运和无奈的现实,并加以虚幻性的审美,其最终结果是封闭僵化、消极退缩的幻想意淫。如蒲松龄对悍妒之妻予以宿命果报的解释,《江城》中江城原为长生鼠,为公子前生误毙,故今作恶报,“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 。将悍妒之妻视为果报,并由贤妇少、悍妇多的现实推断出“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因而只能抒发面对现实的无奈,寄希望于虚幻的主宰力量:“观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43]“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44]人最终苟安在宿命道德的虚幻想象中。
四、对道德宿命意识的突破
《聊斋志异》中大量的果报不爽故事突出地表现了其道德宿命特质,表现了道德宿命意识的方方面面。但蒲松龄并不是一味地对传统果报不爽加以演绎,他在一些篇章中突破了果报不爽模式,也就突破了道德宿命意识,有的还达到了理想的自由境界。
首先,果报不爽模式从情节结构模式转化为一种叙事策略、情节模块。即不是以全部或主要情节单一地演绎果报不爽,而是以果报不爽作为故事叙述的一种技法、策略,或作为情节的某一环节,在开头或中间部分,作为故事的开端或情节的转折。如《王六郎》中,王六郎不忍以母子二命相代,放弃投生的机会,“许感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前一念恻隐,果达帝天。今授为招远县邬镇土地,来朝赴任。’”[45]这一果报不爽的情节更多的只是作为王六郎与许氏二人朋友知己交往的一个突转,服务于之后许氏不惮修阻前往探望的情节和朋友之情不因外在因素改变(“置身青云,无忘贫贱”)的主旨。爱情故事中也多以恩报情节作为故事的开始、爱情萌生的因由等,如《聂小倩》、《小翠》等。
其次,超越现实生活细节以及对果报的心理期待与现实验证,而是诉诸本真的心灵情感。《石清虚》中邢云飞甘愿为石减损寿命,甚至以身殉石,石亦与之相终始。“卒之石与人相终始,谁谓石无情哉?”[46]《橘树》中,刘氏幼女得盆橘,爱护异常,随父离去后,“橘甚茂而不实”;随夫再临,“橘已十围,实累累以千计”,三年间,“繁实不懈”;第四年,“憔悴无少华”,夫亦解任。蒲松龄感叹“其实也似感恩,其不华也似伤离”[47]。在这些故事中,一般没有外在主宰力量或退居次要,而是以人与人、人与物的纯粹的情感往来为主,由外在力量回归内在心理,以内在的心理情感突破外在的束缚、反抗不合理的现实。这些最典型地表现在《聊斋志异》的《香玉》等爱情篇章中,这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是对本真情感的描绘,表现了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达到了亦幻亦真的艺术境界,对心灵成长、人性积淀、价值建构等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蒲松龄还突破了一些传统观念,尽管这种突破仍是在道德宿命、果报不爽的背景中。比如,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一般对商人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对商人阶层及其商贸行为的社会功能虽有所认知,但一般未从道德上予以肯定,而是对许多商人的奸诈谋利予以道德批判。《聊斋志异》中《金永年》视商贸公平为商人之善德,并因之施以果报:金永年夫妇皆八十岁上下,无子嗣,忽梦神告曰:“本应绝嗣,念汝贸贩平准,予一子。”[48]此外,以宿命性的姻缘前定说和果报不爽模式反抗和惩罚父母“弃德行而求膏粱”[49]、强迫子女婚嫁,也是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突破,蕴含着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自由的婚恋观。
五、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体型文化,其核心是儒家学说,认为道德是评价个体、评判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标准,是个体人格建构和社会政治改善的关键。汉代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观念将先秦原始儒家哲学改造为“天人同构”、“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哲学,使之谶纬化,内化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心理,其中“不可避免地同迷信思想、果报轮回意识、消极退隐意识乃至‘精神胜利法’等俗文化意识相互融合,整合成道德宿命意识”[50]。因为是伦理本体型文化的必然产物,建立了道德与个人现实物质幸福的绝对因果关系,契合人们对德福相配的期盼,道德宿命意识成为我们民族重要的文化心理结构。从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的角度讲,道德宿命意识与果报不爽具有劝善去恶等积极作用,但对个体而言,则会导向宿命、消极、退缩等。《聊斋志异》中果报不爽模式相关故事情节深入细致地展现了道德宿命意识这一文化心理的具体内涵、审美呈现、宿命与内弱等特征。时至今日,道德宿命意识仍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存在于文艺作品、社会观念中,这是我们思考现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与心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等问题时不能忽视的。
[1]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p22.
[2]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p216.
[3][4][5][6][7][8][9][10][15][16][18][26][27][28][34][35] [36][37][38][39][40][41][43][44][45][46][47][48][49][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p272,p532,p441,p877~878,p208,p524,p523~524,p1481,p961, p270,p1640~1643,p441,p169,p506,p1115~1116,p1552, p111~114,p164,p842,p1538,p696,p1,p855~856,p1178,p506, p1319~1323,p921,p635,p461.
[11][12][14][23][24][25][29][30][3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p234,p100,p331,p70,p61,p71,p131, p167,p100.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p657.
[17][32][33][50]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p410~411,p410,p410,p410.
[19]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p16.
[2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p2124~2125.
[21]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p69~71.
[22]冷成金.“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证——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p70.
[42]包树望.雅俗文化在“道德宿命意识”上的冲突与整合——以《考城隍》为例[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 (2):p39~40.
On the Moral Sense of Fatality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aking the Mode Guobao in Liao Zhai Zhi Yi as an Example
Bao Shuw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BUCT,Beijing 100029,China)
Guobao is the fictional promise on fate,based on reward for such virtues as fulfilling perseverance, practicing good deeds.Its essence is the moral sense of fatality.The specific performances embodies in the mode “unhappiness of retribution”in ancient classical novels,such as the cause in moral,results of fortune and misfortune,unhappy mood because of retribution,dominant power,etc.In fact,revealing the match of morals and happiness,interpersonal harmony,worldly happiness,the moral sense of fatality has aesthetic qualities.Relevant chapters of Liao Zhai Zhi Yi just provide more focused and detailed performance on these.Some chapters of Liao Zhai Zhi Yi,based on emotions,break the moral sense of fatality,and realize the ideal of freedom.
Guobao(unhappiness of retribution);moral sense of fatality;Liao Zhai Zhi Yi(a collection of bizarre stories by Pu Songling of the Qing Dynasty)
I207.41
A
1671-6639(2016)02-0063-06
2016-03-08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从义观念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蕴”(项目编号ZY1423)的部分成果。
包树望(1983-),男,文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