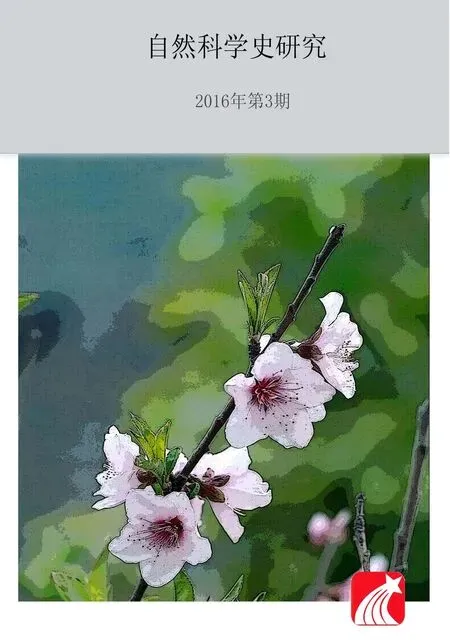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以桑志华、巴尔博对泥河湾研究的优先权为中心
陈 蜜 韩 琦
(1.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
——以桑志华、巴尔博对泥河湾研究的优先权为中心
陈 蜜1,2,3韩 琦3
(1.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泥河湾盆地是国际地质界公认的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对泥河湾进行地质古生物学考察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有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三位外国科学家。本文依据新发现的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并结合考察记和出版物,通过回顾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过程以及早期研究情况,梳理了泥河湾研究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考证了泥河湾地点线索提供人樊尚神父的重要作用,首次深入探讨了巴尔博与桑志华围绕泥河湾地点发现展开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了两人在泥河湾早期研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和做出的贡献。
泥河湾 巴尔博 桑志华 优先权 第四纪地质
0 导 言

图1 桑志华护照照片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
泥河湾盆地,早先称作桑干河河谷,①20世纪初的地质学家多使用“桑干河河谷”,现在统一称作“泥河湾盆地”。本文中对这两个称法不作区别,均指同一地区。位于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桑干河流域。盆地东北端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村附近,地表被桑干河流水切割得沟壑纵横,第四纪地层露头显目,埋藏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泥河湾遗址由此得名。“泥河湾层”指三趾马红土之上、黄土之下的湖相沉积,在第四纪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国际地质界公认的华北早更新世标准地层。[1]对泥河湾早期的科学发现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三位外国科学家:巴尔博(George Brown Barbour,1890~1977)、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图1)*桑志华,耶稣会神父,1876年出生于法国北方省(Nord)的容比村(Rombies),1913年6月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1914年来到中国,1938年返回法国,天津北疆博物院(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创建人。在华期间,他考察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所著《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1914—1923)》和《黄河流域十一年实地调查记(1923—1933)》详细记录了历次考察经过,1952年在巴黎去世。和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
此前,学者们在回顾泥河湾盆地研究史的时候,主要参考《中国地质学会志》上提及相关研究背景的几篇英文报告[2- 6]。此外,德日进与皮孚托(Jean Piveteau,1899~1991)合著的《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Les Mammifères Fossiles de Nihowan (Chine))[7]、桑志华撰写的《桑干河阶地调查记》(VoyageauxTerrassesdeSangkanho,l′entréedelaplainedeSininghien)[8]和《黄河流域十一年实地调查记》(Onzeannées(1923-1933)deséjouretd′explorationdanslebassinduFleuveJaune,duPaihoetdesautrestributairesduGolfeduPeiTcheuLy)[9]等法文发表物也或多或少谈及研究经过。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物提供的信息不仅模糊零散,而且不乏互相矛盾之处,加之时隔久远、史料不足或原本稀见等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常常在基本史实上出现错误,例如误认为桑志华曾在泥河湾村传教[10],或混淆了桑志华最早获知泥河湾出土哺乳动物化石的时间与其来华时间[11],更为普遍的误解是认为巴尔博与桑志华曾两次共同考察泥河湾村*抱有此误解的包括整理过德日进、桑志华信件的贝拉尔(Hugues Beylard)神父以及德日进、桑志华的传记作者居艾诺(Claude Cuénot)。。关于巴尔博第一次到达泥河湾村的年份,也就是泥河湾遗址被发现的时间,以往的普遍看法是1924年,近年也出现了1923年的不同观点[12]。
近年来,笔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包括巴尔博的日记(1919~1928)和信件、桑志华与德日进的通信(1921~1936),以及桑志华的考察日记。*巴尔博的日记和信件收藏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本文关于巴尔博行程的记述主要参考其日记,下文不再重复说明;巴尔博部分信件已发表,参见文献[15]。桑志华与德日进的往来书信以及桑志华的考察日记现存于巴黎耶稣会档案馆。通过对这些一手文献的细致解读,并结合当时的报刊报道及出版物,本文将力图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还原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过程,首次深入分析巴尔博与桑志华之间的优先权之争*居艾诺在为桑志华所写的传记文章中,简略提及了二人的优先权之争,主要侧重分析桑志华的性格,并未从科学史角度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该优先权之争背后反映出的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充满激烈国际竞争的场面。
1 樊尚①之前的论文中提及该神父时,一般按照英文发音将其姓氏Vincent译作“文森”或“文森特”。鉴于神父是法国人,本文按照法语发音,采用商务印书馆《法语姓名译名手册》中“樊尚”的译法。:泥河湾化石的最初发现者
1924年是泥河湾作为地质古生物遗址进入科学界视野的开端之年,但在泥河湾发现古生物化石却并不是新鲜事,当地老百姓根据泥河湾地层盛产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浅水水生动物化石,很早就认识到这里曾经是大片水域。该地点之所以能吸引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这些在华外国科学家的注意,泥河湾教区第一位本堂神父樊尚(Ernest Vincent)作为泥河湾动物化石的最初发现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泥河湾村是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大部分村民都是天主教徒,村里最大也是最早开始信教的赵氏家族,其信教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末嘉庆年间[13]。1901年,泥河湾村与周边其他几个信教的村庄从南屯教区被归入新成立的东城镇教区。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和传教范围的扩大,1911年,东城教区神父决定把教区一分为二,东城镇以东除了小庄子之外的25个村庄归入新成立的泥河湾教区。以泥河湾村为传教中心点,当时教区共有1284位教徒,樊尚神父被任命为该新教区的第一位本堂神父。在他的努力下,泥河湾的传教事业发展迅速,教区成立的第二年(1912),新教堂落成,到1917年教徒人数已经达到4600人。[14]
樊尚同时也是一位博物学爱好者,在传教之外进行一些博物学研究。他注意到了桑干河谷表现出经河水切割过的湖底地貌。这个观点不仅与当地普遍流行的看法一致,而且也反映了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关于中国北部古代水系历史的部分结论[2]。1921年,樊尚在其住宅附近发现了一批古生物化石,包括一颗猛犸象齿、一大块鹿角、半块犀牛长骨、一个带前额的水牛角以及一些蚌科化石。([9],192页)他积极响应桑志华同年3月发出的让各地传教士提供化石线索的号召*“Appel aux Missionnaires et renseignements pour la récolte et l’envoi d’objets d’histoire naturelle”(《召告传教士以及有关采集与寄送自然史物件之说明》)。桑志华来华之前就曾读过谭卫道(Armand David,1826~1900)神父于188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远东传教士为博物学研究提供帮助的文章,见文献[16],445页。此外,1916年,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曾为搜集古生物化石消息向在华传教士、外国人发放英文小册子,并委托专门的代理人发放了上千份中文小册子。桑志华发放这份说明,有可能是受谭卫道、安特生的启发。关于桑志华这份说明的具体介绍,见文献[17]。,于6月来到天津北疆博物院拜访桑志华,告知发现化石的消息,表示愿意将这批化石赠与北疆博物院,并邀请桑志华一同前往化石发现地点做进一步考察。([8],1页)之后他还向北疆博物院寄去了一些蚌科化石。([9],214页)
如果没有樊尚神父提供线索,泥河湾作为地质古生物遗址被世人所了解的时间很可能会推迟许多年。然而对泥河湾科学价值的首次发掘还要等到三年之后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的到来。
2 巴尔博:“泥河湾层”的首创者
巴尔博1890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911年获爱丁堡大学古典学文学硕士学位,1918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地质学博士。1911年,巴尔博在毕业环球旅行期间曾来过中国,见证了辛亥革命,萌发了到中国工作的愿望。1920年3月,他写信给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正式提出希望前往中国任教,并完成基于中国地质情况的博士论文。其时,巴尔博的未婚妻多罗茜(Dorothy D. Barbour)已经接到去燕京大学任教的邀请。([15],13~14页)巴尔博的申请得到了伦敦会的支持。同年5月,他与多罗茜结婚,并着手为前往燕京大学任教做准备[18]。12月,他们从爱丁堡乘船前往中国,次年1月16日到达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们。1922年1月25日,巴尔博到天津担任北洋大学地质系代课教授。9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第三次中亚考察团从蒙古返回,在张家口暂留,在考察团首席地质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勃吉(Charles Peter Berkey,1867~1955)*勃吉是巴尔博的博士论文导师。的建议下,考察团组织了由北洋大学地质系教授毛里士(Frederick Kuhn Morris,1885~1962)*毛里士来华前是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的青年讲师,通过葛利普的介绍来到中国,成为北洋大学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地质学教授。巴尔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二人相识并成为好友,巴尔博到达北京当晚,毛里士即与巴尔博通电话,两人长谈半个小时。1922年毛里士应勃吉的邀请加入安得思带队的第三次美国中亚考察团。由于考察时间长达半年(4~10月),毛里士便邀请巴尔博到北洋大学代课。得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同意后,巴尔博便来到天津,代课时间从1922年1月持续到 1923年上半年学期结束,1923年6月返回北京。带队的小分队,重点考察从万全关进入蒙古高原交界地带的红土层,以验证考察团地质学家们提出的白垩纪地层可能继续往长城以内地区延伸的观点。应考察团团长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之邀,巴尔博也加入了该小分队,同行的还有北京大学地质系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和孙云铸(1895~1979)。[2]正是在这次考察中,受毛里士的启发和鼓励,巴尔博选定张家口地质作为其博士论文题目*巴尔博1928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第二年该博士论文部分章节由中国地质学家侯德封译成中文发表在《地质专报》上,并由翁文灏作序。见文献[19]。。从这一年起至1925年,巴尔博连续四年利用夏季暑期时间多次到张家口进行地质考察。对泥河湾村的实地考察是他与德日进、达伟德(Walter Wiley Davis, 1882~1947)*达伟德,美国来华传教士后代,生于北京,回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于1907年返回中国,隶美以美会,1924年时在燕京大学任教,曾担任地质地理系主任。浙江大学沈弘教授提供了相关信息,特此致谢。共同考察张家口南天门阶地之后进行的。([2],168页)他们三人考察张家口的时间是1924年8月,巴尔博到达泥河湾村的时间是9月。这是第一位来到泥河湾进行实地考察的地质学家(详细过程见下文3.2部分)。
1924年,巴尔博发表了《张家口地区地质初步观察》(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Kalgan area)一文,在和该文一并发表的《关于桑干河晚新生代地层的注记》(Note on the Late Cenozoic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下文简称《注记》)中,*巴尔博的这篇报告在1924年1月5日年会期间宣读,见文献[20],但正式发表时间在9月份完成泥河湾考察并写完《注记》之后。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创办初期,延期出版的情况时有发生。他首次将泥河湾典型的灰绿色河湖相沉积命名为“泥河湾层”(Nihowan Beds),泥河湾这个地点从此正式进入了科学界的视野。随后,根据在泥河湾的此次考察,他于年底又完成了题为《桑干河谷的堆积》(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Valley)的报告,并在1925年1月3日地质学会年会上宣读[21]。这是第一篇正式以桑干河河谷为题的地质学学术论文,该文不仅继续沿用“泥河湾层”的概念,并在最后提到了“组”(formation)这一更高级别的岩层单位。1927年,巴尔博又发表了两篇以桑干河地质为主题的论文。*这一期的《中国地质学会志》虽然被收入1926年第5卷,但实际发表时间是1927年12月。一篇由其单独署名,题为《桑干河盆地地形时期之比较》(Note on Correlation of Physiographic Stages),他在文中将桑干河盆地放到整个华北地区范围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指出泥河湾层与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和安特生发现的汾河地层有直接关联。[6]另一篇《桑干河盆地沉积之地质研究》(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Basin)与德日进、桑志华共同署名。[5]该文对桑干河盆地的地质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篇幅较之前的文章更长,影响也更大。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巴尔博不仅最早到达泥河湾,而且在随后几年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其作为泥河湾地质地貌第一研究者的地位毋庸置疑。
然而,同时期关注泥河湾遗址的并不止巴尔博一人,从现有史料来看,桑志华不仅比巴尔博更早获得泥河湾出土化石的消息(1921年6月樊尚神父即向其提供),而且几乎与巴尔博同步进行着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两人之间围绕泥河湾盆地的发现和研究展开了复杂的优先权之争。
3 巴尔博与桑志华的优先权之争
巴尔博与桑志华的优先权之争表现在化石来源地消息、实地考察和发表文章等多个方面。
3.1 化石消息的优先权之争
在1925年春桑干河考察的记述中,桑志华特意插入了一大段关于巴尔博的内容,明确提出对泥河湾化石地点的消息拥有优先权:
紧张忙碌了一上午,我回到泥河湾,在那儿与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巴尔博先生会合。这位地质学家目前正在对张家口地区进行研究(泥河湾在张家口以北约65公里),*原文如此。泥河湾在张家口南,此处应为桑志华的笔误。他对泥河湾周边的地质情况很感兴趣,希望能在这里为一些地文学难题找到答案。他在张家口看到了樊尚神父早在1921年6月就指定提供给北疆博物院的化石材料,以及我当时记下的一些信息;樊尚神父还向我提议找时间一同前往该地区考察。然而,正如我在《桑干河阶地调查记》的引言中所提到的,山西的考察(1921)、萨拉乌苏化石考察(1922)、以及桑志华-德日进古生物考察(1923)这些接连的旅行,让我无法回应樊尚神父的邀请。直到1924年9月我才得以来到泥河湾。
当时巴尔博先生早了我几天到达。这位地质学家知道樊尚先生找到的化石是要提供给本博物院的。这些化石中就包含蚌科化石,樊尚先生还给我寄过其中的几个样品。巴尔博先生采集到若干蚌科化石,便获得该属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回报。
此外,他还在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的一篇报告中写道“希望邀请我与他合作”,共同考察桑干河的湖相沉积。
对我而言,既然相关消息的优先权是属于北疆博物院及其院长的,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我完全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前往以及何时前往;如有必要,按理说,桑干河考察本应跟随我去做,而且应当是在去泥河湾村之前。
巴尔博先生对泥河湾的这第二次考察持续了三天半,从古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在泥河湾的地层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是我于这一年挖掘出的动物群化石使得三门系的新年代得以牢固建立起来。我在该地区绘制的剖面图,确证了在下沙沟村和泥河湾村,存在着介于红土层和大黄土底层之间的砂土沉积层,从而正式确定了这些地层属于第四纪早期,此前,该地区的年代一直未能确定。
必要的细节已经交代完了,考察记录继续。([9],214页)
桑志华的调查记一贯是按时间顺序详细记述,像这样较大篇幅的插入性叙述非常少见(图2、图3)*巴黎耶稣会档案馆保存有桑志华当年考察日记的原件(图2、图3),并没有这段描述,此段文字显然是桑志华出版时添加的。,而且该书出版时距离泥河湾考察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由此可见他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对巴尔博抢占优先权的深深不满,他提到的那段巴尔博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的话正是《注记》的最后一段,内容如下:
我计划晚些时候与樊尚神父一同参观该地区,并希望邀请桑志华神父进行合作,他在中国其他地区以及蒙古更新世地层的丰富考察经验,对于值得在该地点展开的细致研究而言,将提供不可估量的有利条件。[2]
桑志华比巴尔博更早获得泥河湾化石的消息,这一点上文已提及。接下来的问题是巴尔博获得这个消息是否与桑志华有关?为何桑志华对巴尔博的这段话感到如此不满?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回顾两人的往来情况,尤其是德日进来华后在其间起到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既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起步阶段,也是多国科学家来华实地考察和研究、充满国际交流与竞争的活跃时期。1922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作为国际性学术组织,学会的发展很快,到1923年1月召开第一次年会的时候,学会规模已经从创会时的26人增加到77人(68位正式会员和9名准会员),其中外籍科学家人数达到29人。[22]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和若干次常会,学者们在会上宣读最新研究成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成为中国地质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巴尔博和桑志华都是在1922年学会成立当年就加入学会的第一批正式会员[23],学会秘书谢家荣在年会报告中提到外籍会员中的一位英国人和一位法国人分别指的就是他们二人。可见,在德日进来华前,巴尔博与桑志华已经通过地质学会彼此认识。

图3 桑志华泥河湾考察日记(1925年4月24日,手绘地形图)
除了共同出席地质学会的活动,两人在天津很可能也有往来。巴尔博1922年初到天津,同年10月,北疆博物院北楼即主楼完工([24],1554页)。博物院于1928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9],431页),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第一座也是唯一的自然史博物馆,加之桑志华在华多年从事地质考察已获得一定声誉*《工商大学季刊》(天津)1927年5月第一期附有“最近参观北疆博物院之来宾姓名表”,其中就有巴尔博。,在北洋大学地质学系任教的巴尔博成为北疆博物院最早的参观者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1923年5月23日,德日进到达天津,6月5日即与桑志华一起到北京,参加地质学会的第六次常会,德日进应邀做了报告*见文献[25],此次会议记录的时间有误,比对德日进的信件和桑志华调查记上的时间,可以确定实际开会时间是6月5日而不是6月15日。,并加入学会成为会员[26]。巴尔博并未参加此次常会*根据日记记载,巴尔博当天从天津到北京拜访友人。。11月,德日进结束鄂尔多斯考察后再次来到北京与地质学界同仁交流,期间与巴尔博相识。两位地质学家互相赏识,结下深厚友谊,彼此往来密切。11月22日,两人共进午餐,并一起到地质调查所参观巴尔博采集的地质样本。12月2日,巴尔博到天津参加伦敦会会议,还专程前往拜访德日进。([15],72~73页)
1924年1月,巴尔博、德日进和桑志华均出席了中国地质学会当年的年会。1月5日会议第一天,巴尔博宣读了 《张家口地区地质初步观察》,由葛利普、丁文江、翁文灏讨论。[20]这篇论文是巴尔博在1922、1923年两次张家口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也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泥河湾的消息。
7月6日,桑志华与德日进从蒙古东部考察返回途中经过张家口,已把泥河湾定为下一个考察目的地的桑志华原计划顺道拜访已调任张家口的樊尚神父,带回后者之前承诺赠与北疆博物院的化石,并咨询泥河湾化石出土地点的详细信息、周边情况以及前往该地的路线。鉴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交通状况,事先了解考察地点的情况对于确保考察的顺利进行是十分必要的。桑志华能够以一己之力在中国北方进行数万公里的考察,正是充分利用了在华传教士提供的信息网络。由于当时樊尚神父有事外出,不在张家口,桑志华的计划一时未能实现([8],1页)。7月8日,两人便乘火车返回天津,幸运地躲过了几天之后的大洪水*德日进与桑志华离开后第5天,即7月13日,张家口因连降暴雨发生五十年一遇的洪灾,他们住过的旅馆完全被冲毁。见文献[9],184~185,188页。。而当时在张家口周边地区考察的巴尔博,恰好于7月12日下午回到张家口市,赶上了这场洪水,亲眼目睹了水情之猛烈,他于15日离开张家口。期间,德日进曾给巴尔博写信,提到希望尽快见面交流一些关于张家口地质的重要看法(important ideas about your area)。([15],81~82页)7月20日,巴尔博在前往北戴河与家人会合途中取道天津,拜访德日进。巴尔博很可能就是在这次会面中邀请德日进返回法国前与之共同考察张家口,并首次了解到泥河湾的情况。泥河湾盆地毗邻张家口,以巴尔博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的观察力,这条线索势必会引起他的兴趣。7月25、26日,地质学会第八次常会在北京召开, 德日进和桑志华均参会并做了报告[27]。巴尔博也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出席会议。7月26日上午,德日进和桑志华还一同拜访了巴尔博。在如此频繁的接触中,桑志华不会不了解巴尔博对泥河湾的兴趣,势必感到一定的潜在竞争压力。
按照商定的计划,巴尔博与德日进、达伟德8月19日到达张家口南天门,这是巴尔博连续第三年考察张家口地区。他们的考察路线包括张家口周边的永丰堡、万川等地。德日进此行还受桑志华的委托,从樊尚神父那里将原计划7月份拿到的那批泥河湾动物化石带回北疆博物院。25日,三位地质学家拜访樊尚神父,巴尔博看到了泥河湾的哺乳动物化石。26日,德日进和达伟德离开张家口。考虑到当时直奉军阀对峙的紧张局势,德日进离开前催促巴尔博尽快前往泥河湾村进行实地考察([28],30页)。回到天津后,德日进在给其导师、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古生物实验室主任步勒(Marcelin Boule,1861~1942)的信中写道:“这些化石似乎出自与萨拉乌苏相似的地层,对该地层的研究应该能够大大促进关于中国第四纪地质的了解。”([29],134页)可见他也立刻充分认识到了这些化石及其发现地点的研究价值。
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巴尔博获得的泥河湾化石消息确实来自桑志华,而不是直接来自樊尚神父。德日进在其中扮演了消息传递者的角色。他不仅催促巴尔博前往实地考察,也希望桑志华尽快成行,并且为自己因为归期在即无法亲自去泥河湾颇感遗憾。([29],134页)可见,德日进对优先权并不在意,他迫切想要了解的是泥河湾地点是否有助于解决相关地质年代问题。
3.2 实地考察优先权之争
德日进与达伟德离开后,巴尔博并未立刻赶往泥河湾,而是继续在张家口周边地区考察并绘制地图,为博士论文积累材料。既定工作完成之后,他于9月8日经十八盘前往泥河湾村,9日到达,10日即离开,也就是说巴尔博的泥河湾之行头尾两天在路上,真正在泥河湾村实地考察只有9月9日一天时间。行程如此匆忙也和当时可能爆发战事的传言有关。另一方面,从张家口返回天津的德日进带回的不仅有化石,很可能还有巴尔博继续在张家口考察并将前往泥河湾的消息,这无疑让桑志华更加感到时间紧迫,决定尽快出发。此外,樊尚神父也给桑志华来信,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详细行程信息。9月10日,桑志华从天津出发,13日到达泥河湾村,15日到达东水地,16日即返程,18日回到天津。([8],1~14页)此次调查时间不长,也没有组织挖掘,桑志华在化石方面收获寥寥,仅发现了几处含有蚌科(Quadrula)、椎实螺(Limnée)和扁卷螺(Planorbe)的地层,收到村民送来的几件在泥河湾村东北挖出的动物骨化石,并在沿途零星发现了少量骨化石。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熟悉周边地形民情,初步了解地质情况,与当地传教士建立联系,为后期的考察探好路。
从时间上看,桑志华仅比巴尔博晚了4天到达泥河湾村。如果樊尚神父7月份在张家口没有外出,桑志华按原计划获得行程信息,很可能会更早动身,赶在巴尔博之前到达泥河湾。
3.3 发表文章的优先权之争
在发表文章方面,仍然是巴尔博领先,这也是二人矛盾最突出的阶段。
作为出色的地质学家,巴尔博在仅仅一天的匆忙考察中观察并捕捉到泥河湾地质的主要特点,将观察结果写成《注记》,赶在当年第二期《中国地质学会志》印刷之前交稿,得以和年初宣读的《张家口地区地质初步观察》同时刊登出来,共同构成其研究张家口地质的第一阶段研究成果。在这篇拉开泥河湾研究序幕、篇幅并不长的《注记》中,巴尔博按照地质学论文的惯例先介绍考察背景,包括如何获取地点线索。在提到向其提供东城镇化石的农民时,他明确交代了1923年这一时间点,但接下来谈到樊尚神父的时候他却没有指出拜访的确切时间(1924年8月),而是含糊地写道“during the year”,这可能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巴尔博1923年到达泥河湾村的主要原因。根据上文的考证,桑志华虽然没有直接告知巴尔博泥河湾的消息,但如果没有通过他和德日进,巴尔博无从获知泥河湾这个地点,更不可能拜访樊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巴尔博在获得关键信息时间点上的模糊措辞来看,不排除刻意避免提及桑志华的意图。不仅如此,他还在文章末尾以第一发现人的语气,表示希望“邀请桑志华加入合作”,共同考察泥河湾。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他的傲慢态度是很明显的,这无疑惹怒了桑志华。向来注重优先权的桑志华读到这段文字后满腔愤懑、耿耿于怀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结合中国地质学界发展初期的国际竞争环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巴尔博的抢先意图和桑志华的不平之意。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多样,矿物化石丰富,有大片未被开发考察过的地区,为地质学家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20世纪初,西方地质学家纷纷来到中国进行考察。民国政府也出于勘探开发矿产资源的需要,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然而广泛深入的地质调查研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深厚的学科知识积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地质学界来说,仅凭本国科学家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丁文江(1887~1936)等地质调查所早期领导人不仅积极邀请安特生、葛利普等西方知名学者直接参与调查所的工作,也对来华的各国学者在中国开展科学考察持欢迎态度。与此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地质调查所作为政府机构需要把握住在华地质考察的主导权。于是他们一方面积极拓展考察范围,不断发现有价值的新地点,另一方面为避免重复竞争,主动与各国学者协商,争取合作*1921年2月,安特生和丁文江曾先后到天津拜访桑志华,希望通过桑志华与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步勒教授建立起合作关系,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国的学术期刊如《中国古生物志》上。见文献[24], 1373页。,或者划清考察范围,达成互不越界的默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1年,安得思在与丁文江会面时提出美国打算考察蒙古地质的计划,丁文江告知其地质调查所近年来所从事的地质考察计划,同时也提出希望他们避免考察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的夔州和万县以及热河附近的部分地区。1921年,该考察团先期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谷兰阶(Walter W. Granger,1872~1941)一行,也是在得到丁文江、安特生的许可后,才得以前往由地质调查所发现但暂时无暇顾及的四川万县盐井沟进行化石挖掘。
巴尔博以教员身份来华,不依托于任何研究机构,更多是以个人身份进行地质考察。他通过参加美国中亚考察团“获得”了张家口地区这个研究“地盘”,在其日记以及与妻子多罗茜的通信中经常能读到“my area”“your area”这样的表述。然而,对于张家口如此重要的地区,安特生更早就注意到了这里的地质研究价值,并于 1919、1920年两次前往张家口进行过初步考察。大概是由于地质调查所人手有限,暂时没有展开正式考察。192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地质调查所也开始派人前往张家口,巴尔博“发现地质调查所在压制他的发现,并派了一个人去实地进行考察,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拥有优先权”。([15],73页)竞争压力之下,泥河湾这个此前从未有地质学家踏足过的新地点对巴尔博自然格外有吸引力。*巴尔博本人的竞争意识也很强。1925年8月,张家口考察接近尾声,巴尔博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我的地层年代晚于髫髻山的褶皱。如果在西山我能够找到比安特生更好的材料,就像我在张家口做到的这样,就可以证明这是上侏罗纪,也就相应地可以把一些新的地层归入白垩纪——这正是我想做的。”见文献[15], 115页。然而,位于张家口以南近百公里的泥河湾显然已经超出他的地盘,即从张家口向蒙古高原逐级过渡的阶地。([15],80页)对此,他在《注记》中从地质关联性的学术角度解释了前往泥河湾的必要性,“张家口地区的一些问题必须到这个地区本身之外寻找答案”[2]。只要他不提桑志华先于他获知泥河湾的消息,就不会让人觉得他破坏了互不越界的默契。而对桑志华而言,泥河湾本来已经被他视作自己的考察范围,并制定好了考察计划,突然被巴尔博抢了先,恼火在所难免。
《注记》发表后不久,二人矛盾继续升级。巴尔博在前期考察基础上很快又完成了一篇正式报告《桑干河谷的堆积》,并于1925年宣读及发表。这篇报告篇幅较短*报告共3页,其中还有近一半篇幅介绍相关背景,三段涉及泥河湾地层,一段谈到化石,并提出了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对“泥河湾层”的地质描写较为概略,可以看出抓紧发表的意图。而就在巴尔博写这篇报告的同时,桑志华也在争分夺秒写他的《桑干河阶地调查记》,并准备在年底前付梓,计划带到1925年初的地质年会上宣读。不料由于印刷过程中意外频出,桑志华最终未能在原定日期拿到这本小册子。1925年1月2日(地质学年会召开的前一天),他在写给德日进(当时在法国)的信中表达了预见到优先权被抢占的强烈不满和沮丧之情:
(印刷厂的)神父承诺最晚于1月1日交给我的关于樊尚先生那批化石的实地调查记,最终没有送来,我担心一直在搅局的巴尔博明天会在地质学会的年会上发言,从而获得了优先权。我对这种让人气馁的含混不清的局面深感愤怒。(桑志华致德日进信,1925- 1- 2)
他在信中解释说,他第二天不去北京参加年会是因为交通不安全,但显然这不是取消行程的主要原因。倘若小册子能按时交到桑志华手中,他一定会到北京出席年会,并很可能与巴尔博就发现泥河湾遗址的优先权归属问题当面发生争论。
几天之后,桑志华终于拿到了印刷好的《桑干河阶地调查记》。当时已经是1925年初,但值得注意的是出版时间却写的是1924年9月,也就是桑志华到桑干河考察的时间,他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强调自己的优先权[30]。在这本14页的小册子中,桑志华以他一贯事无巨细的叙事风格详细记述了9月10~18日的首次桑干河之行。小册子印刷完成的同时,桑志华也得到了巴尔博宣读报告并将发表的消息。虽然此前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甘心将优先权拱手相让,而是在拿到小册子后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反击”,广为寄送,希望自己发现泥河湾地层的贡献能够得到科学界的认可。他在给德日进的信中写道:
他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地质学会发表了关于桑干河阶地的文章。我得到消息后,通知了他,同时我也抓紧赶在他的前面。我自己出版了《桑干河阶地调查记》,就是近期寄给您的那本,我也寄给了翁先生、欧洲和美洲的博物馆以及巴尔博本人。我在书里没有提到他,因为如果说到他,我就不得不提到他没有按照公平游戏的规则行事。事实上(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和。为了修补关系,我等着巴尔博收到我的《阶地调查记》后做出答复。如果他不回应,我就回到阶地去,一开春那里就已经有人为我工作了。我不需要别人来帮我指出一个地质事实,即含结核的红土层与含蚌科化石地层之间的连续性,而巴尔博,从您寄给我的剖面图来看,仍将这个事实视作一个假设。(桑志华致德日进信,1925- 1- 10)
虽然桑志华在《桑干河阶地调查记》中刻意避免提到巴尔博的名字,但紧随在巴尔博宣读桑干河报告之后广为寄送这本小册子的举动本身,足以表明他对巴尔博获得优先权的不认可态度。对此,巴尔博在正式发表的 《桑干河谷的堆积》文章中写道:“我对这些阶地的重要性及其与周围湖相沉积之间关联性的最初印象,在北疆博物院院长桑志华神父随后的考察中得到了印证”。[3]这句话脚注中的文献正是《桑干河阶地调查记》。作为对桑志华的回复,巴尔博在这里明显暗示“泥河湾层”的优先权属于他,桑志华无论从到达考察地点的时间还是从地质观察层面做出第一判断都在其之后。至此,二人的优先权之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正面交锋、互不相让。
桑志华在写给德日进的信中不仅对巴尔博抢占其优先权表示不满,而且对其研究结论也提出了质疑,他对于自己独立进行泥河湾地质研究充满信心,对巴尔博的参与则持排斥态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中心封闭性格和高估自身学术能力的倾向。居艾诺在桑志华传记中对其过于坚持以北疆博物院为中心、不善与他人合作、易怒又固执的性格特点做了非常充分的描述[30]。巴尔博对桑志华也有类似评价,认为他“本质上是个采集者,比起将所采集化石和石器作为了解史前史的关键线索去发掘它们更广阔的意义,他更感兴趣的是给它们命名和贴标签,他更愿意寻找的是‘什么’(what),而不是化石中包含的关于远古生命的新线索,即‘为什么’(why)、‘何时’(when)以及‘如何’(how)。”([28],31页)可见,在巴尔博眼中,桑志华并不具备专业学者应有的素质。
从学术背景来看,桑志华的博士论文是昆虫学研究,缺乏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学术训练,不具备独立撰写相关学术论文的能力,他参与学术研究的方式就是通过组织实地考察,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提供材料,以合作者身份共同发表文章,这一点在他与德日进共同署名的多篇萨拉乌苏研究报告中体现得很充分。桑志华原本希望沿用萨拉乌苏的研究模式继续与德日进合作,却没有料到出现了巴尔博这位竞争者,打乱了既定计划。桑志华来华的目标是将北疆博物院建设成为一所具备“资料与信息流通中心”功能的科研机构[31],泥河湾是其为实现该目标所制定的全盘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桑志华而言,所有他争取到署名的发表物都是为北疆博物院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的特点就是高度依赖材料,古生物化石在20世纪初仍然是确定地层年代的最主要手段,桑志华在发掘化石和石器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在当时动荡的中国尤为不易。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桑志华过度在乎优先权的表现。巴尔博在对桑志华的评价中只提其缺点,而不言其贡献,是看似客观的偏颇,透露出几分傲慢。这份偏见在时隔30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从他写给居艾诺的信中读出来*见文献[32],Bibliographie VIII. 1958年5月4日,即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共同署名的文章发表32年之后,巴尔博在写给居艾诺的信中特别指出:“据我所知,桑志华(对这篇文章)一个字贡献也没有!”(Licent did not contribute a word,as far as I know !! )。巴尔博似乎在暗示桑志华没有署名资格,这多少有失偏颇,毕竟桑志华确实在化石材料的挖掘上贡献不小。另外,就文章的学术价值来看,德日进无疑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却愿意最后署名,他的胸怀由此可见。。可以说,科学史上大大小小优先权之争中普遍存在的偏见、固执、傲慢同样出现在了巴尔博与桑志华的矛盾中。
3.4 短暂的共同考察
德日进与巴尔博是终生互相信任的好友,桑志华则是德日进来华初期最重要的合作者。对于二人围绕泥河湾产生的优先权之争,他一贯主张进行合作,认为科学发现本身比优先权重要。虽然德日进1924年9月即返回法国,桑志华与巴尔博矛盾最突出的时候并不在中国,无法通过当面沟通来调解二人的不和,但他一直通过信件往来努力缓和二人的矛盾,充当“和事佬”的角色,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人的紧张关系。
回法国后不久,德日进获知两人间的不愉快,他在给桑志华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收到了巴尔博的一封长信,谈到了他在桑干河的调查结果。这让我非常希望能读到您的调查结果。……我将(以我们三人共同的名义)在地质学会做一场临时性的初步报告。巴尔博对其在桑干河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方式深感为难和不安:一方面,他无法停止和舍弃与张家口的工作密切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无论如何无意冒犯您。我建议他与您保持密切联系,如果找到化石的话和您一起研究,总之就是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你们两人共同来解决并不显得太多。(德日进致桑志华信,1924- 11- 26)
从这封信中可以读出,巴尔博意识到自己单独前往泥河湾引起了桑志华的不快,并向德日进解释了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其博士研究课题的需要。德日进本意是向桑志华说明巴尔博希望避免矛盾,且对合作抱开放态度,但桑志华对这个解释并不接受,他的理解是“巴尔博在他的信里与其说向您寻求和解,不如说是请求宽恕。”(桑志华致德日进信,1925- 1- 10)
针对桑志华最在意的优先权归属,德日进的看法是:
关于优先权问题,我认为您为此过于忧虑是不明智的。就优先权本身来说,它在我眼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真正有价值的是关于某一点或某一领域的严肃的工作,无论这项工作涉及相关问题的首次发现,还是仅仅确认或扩展了已经指出的结果。关于樊尚的地层,我觉得您本可以在北京与巴尔博共同发表一篇报告,因为你们的观察结果涉及不同的方面,并且或多或少互相补充。我肯定巴尔博很乐意这么做。我一贯认为(在其他各种令人愉快的好处之外)一定程度的合作是避免被剽窃的最可靠的办法。(德日进致桑志华信,1925- 1- 23)
德日进对优先权的超然态度反映出他对科学研究本质和价值的深刻认识。1924年8月,在张家口见到泥河湾化石的时候,德日进已充分意识到泥河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他看来,尽快确定泥河湾地层的年代比起谁最先到达泥河湾,显然要重要得多。
经过德日进的协调,加上当时各国科学家团体在中国的激烈竞争环境,巴尔博和桑志华都意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最终接受了合作考察,德日进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在给桑志华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巴尔博的事情已经平静下来了。从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希望看到我认为会对北疆博物院有利的一次合作。”(德日进致桑志华信,1925- 2- 18)或许是出于对二人性格的了解,担心合作可能出现不愉快,德日进还暗示桑志华考虑到比巴尔博年长,不妨更包容一些:“我收到巴尔博的来信,告诉我他和您进行了一次和平的会面。我对此感到很高兴。不过这是位相当敏感的男孩。到了考察地点,您可以让他感受到您是真心和他一起(合作)的”。(德日进致桑志华信,1925- 3- 6)
不过,桑志华并不愿轻易信任巴尔博,他在共同考察前不久写给德日进的信充分体现了他的保留心态:
现在既然事情都已经说清楚了,我只求‘诚心诚意’地进行合作。在正当权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我既不是难以相处的人,也不算糟糕的同伴。(桑志华致德日进信,1925- 4- 2)
和他算是和好了。但我三天后会去桑干河阶地,而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告知巴尔博我将在那里等他。我将从容不迫地进行自己的考察研究。巴尔博似乎但心美国人抢了我们的先,而我也同样担心;并且我还没算上另外的担心,那就是一个人可能倒戈相向,与原本害怕之人打成一片。只有在掌控中,我才有信任感。(桑志华致德日进信,1925- 4- 6)
桑志华于4月19日到达泥河湾村。巴尔博比桑志华晚两天,即4月21日到达,25日上午离开,实际考察时间仅三天半。除了泥河湾村,他们还去了附近的海螺沟、沙沟、下沙沟、柳沟、白井子等多个村庄,既有地质考察,也进行了古生物挖掘,挖出了包括蚌科、剑齿虎、反刍亚目动物等多个种类的化石。([9],214~216)4月23日,在沙沟右岸进行地质考察的时候,巴尔博绘制了地质剖面图,桑志华在调查记中特意提及自己已经在19日来泥河湾途中经过沙沟时绘制过同样的剖面图,处处不忘强调自己的优先权。
关于这次共同考察,桑志华认为自己在泥河湾年代确定方面的贡献是最重要的([9],214)。1926年,他甚至在信里抱怨德日进在一篇综述性报告[4]中写错了他与巴尔博共同考察的时间,担心会让人们误以为是巴尔博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德日进1926年12月15日写信回应了桑志华的不满。,可见其对泥河湾的优先权问题始终无法释怀。其实,巴尔博的研究侧重地貌地文,泥河湾地层的年代在他看来仍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需要古生物学研究的支持:“将来发现的哺乳动物类型肯定能建立这个组的确切年代,将其置于三趾马红土和黄土之间的准确位置,并同时确定出不同的地文阶段”。[3]正如德日进所指出的,巴尔博和桑志华二人本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但各自的性格与竞争意识让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合作难以实现。
巴尔博4月25日从泥河湾离开,5月9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刊登了一篇报道泥河湾考察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史前时期骨化石:科学家在张家口附近河谷发现奇异怪兽遗迹》(Prehistoric Bones of China: Remnants of Strange Monsters Found by Scientists in Valley Near Kalgan)。该报道不仅介绍了桑志华和巴尔博的情况、此次考察的经过及找到的化石种类,而且将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更早些时候安特生在河南、丁文江在三门峡以及葛利普正在研究的发现于天津的不同化石进行比较,还交代了这批化石将被送往巴黎由德日进进行研究。文章最后指出,这些新发现的化石表明泥河湾盆地的地质年代可能处于上新世或早更新世,可能与欧洲和美洲大冰期的早期阶段处于同一时代。[33]该报道写作完成的时间是4月30日,其时桑志华还在泥河湾继续考察,从行文的语气和内容看,作者很可能就是巴尔博本人。
按照德日进此前在信中提过的计划,1927年,三人共同署名发表了《桑干河盆地沉积之地质研究》这篇重要报告*该论文先是在1927年2月份的年会上宣读,见文献[34],报告题目是《桑干河沿岸泥河湾层之地质研究》(Geological Study of the Nihowan Beds, along the Sangkanho),最终发表时题目改为《桑干河盆地沉积之地质研究》(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Basin)。。巴尔博在引言中介绍前期考察背景时写道:“初期的调查由巴尔博和桑志华于1924年秋季进行……,1925年初有了第二次共同考察。”[5]不同于他在之前的文章中对优先权或多或少的暗示,巴尔博在这里措辞含糊,不仅避免谈及优先权,而且刻意营造出与桑志华合作良好的印象。至此,巴尔博和桑志华的优先权之争以友好(合作)和共赢(共同署名)方式划上了句号。如果没有德日进的努力协调,这样的结果恐怕很难实现。鉴于这篇报告对泥河湾遗址的分析无论从篇幅还是深度都远超此前发表的《注记》和《桑干河谷的堆积》,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在缺少相关史料作为参照的情况下,关注泥河湾考古史的研究者大多误以为桑志华与巴尔博共同进行过两次考察。
4 桑志华的泥河湾之行
巴尔博到泥河湾进行了两次短促的实地考察,德日进只去过一次,而桑志华前后共到泥河湾盆地考察了6次,除了上述与巴尔博的短暂合作(1925年)以及与德日进的共同考察(1926年),其余四次皆独立完成,发掘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细致的地质观察,绘制了许多地图和剖面图。上文已经概述了1924年的第一次考察,与德日进的第五次考察笔者将在另一篇关于德日进对泥河湾化石研究的专文中展开详述。在这部分我们通过回顾桑志华1925年的三次连续考察和1929年的最后一次考察,更充分地了解和评价其在泥河湾遗址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1925年春夏之际,桑志华以一己之力在泥河湾村和下沙沟村一带发现并组织村民挖掘了23处化石地点,出土了大量的化石,为后期德日进进行泥河湾古生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1925年4月,在快到泥河湾村、经过沙沟的时候,惯于沿途观察地质情况的桑志华已经发现了1号化石地点;进入下沙沟村,村民主动带来“龙骨”向其售卖,其中就有后来为桑志华在当地挖掘化石提供了很大帮助的喇有计。第二天,即4月20日,在泥河湾村一带的化石挖掘正式开始。桑志华在调查记中写道:“在樊尚先生提供信息(1921)、去年秋天(1924)第一次调查、昨晚的发现以及下沙沟村民提供信息之后,我现在能够预见到这些地层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寻找和挖掘化石的方法。”([9],212页)巴尔博离开后,桑志华又继续在泥河湾村待了9天(4月25日~5月3日),发现了多处化石地点,大部分位于下沙沟村,共出土了15箱化石。同期还到泥河湾村周边不同方向的石匣里村、岑家湾村、和尚坪、油房村等多个村庄调查,深入考察了桑干河峡谷及其支流壶流河的地质地貌。([9],216~230页)
回到天津不久,桑志华便于5月25日第三次出发到泥河湾盆地,继续挖掘化石和进行地质调查。由于化石地点集中在下沙沟村附近,为了方便指导挖掘,桑志华这次住在了下沙沟村民喇有计家中。调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月28日~6月14日),桑志华在指导化石挖掘的同时继续到周边多处村庄进行地质考察。出土的化石种类包括马、羚羊、披毛犀、大象、鹿、羊、椎实螺等,共计19箱。第二阶段(6月14~27日),桑志华前往壶流河一带进行更深入的地质调查,但几乎没有发现化石,他判断“这一带由于离古湖的岸边太远,不存在可以与下沙沟及周边地区类似的埋藏有大量化石的地点。”([9],253页)第三阶段(6月27~28日),桑志华返回下沙沟村,又发现两处化石地点,新添7箱化石,包括当地人在修建河堤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件长达3.5米的象牙化石。到28日准备返程的时候,桑志华共挖掘出28大箱、总重达1280千克的化石,还有一些易碎的化石被单独打包,装入随身旅行箱中,满载而归。([9],258~259页)
仍然是在1925年夏天,桑志华于8月10~27日第四次考察了泥河湾盆地,但此行目的地不再是前三次的泥河湾村、下沙沟村一带,而是桑干河上游、大同府以南的山西北部地区。桑志华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泥河湾地层相关问题的有价值的信息,并在山西北部发现新的古生物、旧石器或新石器遗址。这次旅途以地质、地貌考察为主,桑志华调查记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对沿途各地地质情况的记录,仅发现少量的新石器和动物化石。([9],265~286页)
随着化石发现量的增加,泥河湾遗址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桑志华希望能持续到泥河湾进行考察,并且需要古生物学家与其合作研究采集到的大量化石。然而从1927年开始,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停止了对德日进的资助,周口店遗址也开始了大规模发掘,德日进受地质调查所之邀加入发掘工作,其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北京,与桑志华的合作减少*1927年夏天的围场之行和1929年5~6月的满洲行是二人最后两次共同考察。。在德日进的建议下(德日进致桑志华信,1929- 4- 1),桑志华曾经考虑过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便通过德日进与翁文灏商量合作的可能,但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翁文灏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必须坚持调查所的绝对优先权,外国专家只能作为受邀请方加入联合考察,这在桑志华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作为折中方案,翁文灏表示地质调查所1929年不对桑干河盆地进行考察,但如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介入,他无法为桑志华提供任何官方的保障和便利(德日进致桑志华信,1929- 4- 11)。
对于坚韧的桑志华来说,缺少合作者虽然一直是他的苦恼,却从未阻止过他考察的步伐。1929年6月18日,桑志华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泥河湾盆地考察。受周口店新发现人牙化石的启发和激励,他对在泥河湾盆地找到新的三门系古生物动物群抱有很大期望。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年代位于三门系的最顶端,他希望通过坚持不懈寻找新的化石地点最终也能找到古人类化石([9],620页)。这次行程持续了2个半月(6月18日~8月31日),大致也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在泥河湾村、下沙沟村及大田洼村附近共出土了30箱、重2820斤(livre,法国重量单位,相当于489.5克)的化石;第二阶段在榆林关村附近发现一处三门系化石地点,也有不少收获;第三阶段侧重地质观察和动植物标本采集,采集到少量化石。在结束榆林关村化石地点挖掘的时候,桑志华写道:“如果接下来几年我能够再回来,到时候安全形式和工作条件有所好转,我将更深入地挖掘泥河湾的新地点和榆林关的丘陵。”([9],643页)可见,桑志华非常清楚泥河湾盆地的科学价值,对于这一带的古生物地质调查抱有长远的考察计划,但他当时不可能预料到,接下来种种世事变化使得这次考察成为他本人、也是泥河湾盆地早期研究的最后一次实地科学调查。卫奇对于当年桑志华没有继续坚持调查,从而错过让泥河湾崭露头角的黄金时机深感遗憾[12],殊不知非其不愿为之,奈何不能为之。
相比于资金充足、设备先进、集体行动的美国、瑞典科考团,桑志华一直是孤军奋战,即使1923~1924年间他带队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也不过他和德日进两人加上助手和车夫。在内战频仍的民国初期,他在华北漫漫数万里的行程中遇到的艰辛与困难是今人难以想象的。除了异常艰苦的旅行条件,桑志华调查过程中还要处理各种不利情况:村民对化石地点的蓄意破坏、以风水为由拒绝其挖掘化石实则为获得更高赔偿金、盗匪(兵匪)出没、车夫出高价敲诈、村民开出过高的化石售价等等,桑志华既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又能把握原则性和主导权,并且根据形势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挖掘化石,在条件不允许或代价过高的时候果断放弃。限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桑志华很难单独在泥河湾遗址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他对泥河湾研究尤其是古生物学方面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其实,不仅在泥河湾,桑志华对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古生物学研究都做出了贡献,德日进对其作出的高度评价是很恰当的:
我们在此描述的绝大部分材料是由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桑志华神父在1924至1925年间,以及之后在1926年,桑志华神父与代表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古生物研究室的德日进神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集而来的。没有桑志华神父持续不懈的努力,(我们)可能仍然对桑干河动物群一无所知。对该地点的发现及地层的挖掘,连同对鄂尔多斯旧石器遗址和甘肃蓬第期红土遗址的发现与挖掘,构成了天津北疆博物院的创建者十五年来在中国进行的科考活动中最重要的古生物学成果。[7]
5 结 论
从1924年9月巴尔博到达泥河湾村到1929年8月桑志华结束最后一次泥河湾考察,对泥河湾遗址的早期实地考察持续进行了5年。相关研究结果除了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的若干篇文章,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德日进和皮孚托合著、1930年发表的《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该书记述了42种哺乳动物,其中鉴定到种的18个,包括10个新种,首次将泥河湾动物群的整体面貌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填补了我国新第三纪和第四纪过渡阶段的关键空白。[35]在整个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承担了不同的学术角色,桑志华和巴尔博的优先权之争似乎对泥河湾早期研究没有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巴尔博的傲慢还是桑志华的愤懑,都表现得比较克制,加上德日进的积极调解,二人的矛盾没有真正公开激化,三人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章更进一步给人们留下了他们积极合作的印象。
然而,实际上巴尔博与桑志华之间并未展开真正有效的合作。一方面,巴尔博始终没能找到期待中的化石,1925年8月结束张家口考察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在地层年代这一主要问题上,我的运气不够好——没有发现任何能够用来鉴定年代的骨化石。如果我有设备、随从和牲畜,或者敢于利用铁路,我本可以继续往西走得更远一些。所以我只能遗憾地承认我还没有此前期待找到的确切证据。([15],115页)
本来巴尔博对此行抱有很大期望,“找到一个真正的好化石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15],114页),但最终失望而归。另一方面,这一年德日进远在法国,桑志华虽然挖掘出了大量化石,却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化石进行研究。倘若巴尔博与桑志华能够抛开彼此的成见,发挥各自优势展开切实的合作,泥河湾盆地早期研究很可能取得更为丰富和深入的成果。可见这场鲜为人知的优先权之争多少留下了一些遗憾。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还得以更清晰地界定出巴尔博和桑志华在泥河湾早期研究过程中做出的不同贡献。巴尔博作为第一位对泥河湾盆地地层与地貌进行研究的地质学家,最早连续发表了一批与泥河湾相关的学术论文,最早提出“泥河湾层”,使得泥河湾首次成为科学界关注的地质遗址。1929年其博士论文部分章节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对后来学者研究包括泥河湾在内的张家口地区地质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黄土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人们对于桑志华在泥河湾早期考察研究中具体的参与情况了解却十分有限。这一方面是由于桑志华仅在1926年发表了一篇与泥河湾相关的学术文章,且是与巴尔博、德日进共同署名,影响力远不能与巴尔博的一系列文章、博士论文以及德日进、皮孚托合著的《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此前,桑志华与步勒在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领导权和化石归属权问题上产生矛盾以致关系破裂。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出版印刷过程中,由于步勒的反对,桑志华的名字没能以作者身份出现在这本他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专著中。相比;另一方面桑志华多次考察泥河湾的详细记录只出现在他本人所著的《黄河流域十一年实地调查记》中,然而该书印数有限,用法语写成,且内容的叙述性大于学术性,真正关注的人并不多。如今,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在生物地层学中的独立地位已被国内外的地质学工作者所普遍认可,德日进与皮孚托的开拓性工作虽然对桑志华发现的大部分化石进行了系统研究,但他们对化石的产出地点和记述过于笼统,而且研究范围不包括桑志华1929年最后一次去泥河湾挖掘出的、现存于天津博物馆的两千多件化石,如能结合桑志华留下的原始考察日记继续对1929年的这批化石展开分析鉴定工作,无疑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泥河湾哺乳动物群的认识。[36]
20世纪初期,西方多国科学家竞相来到广袤的中国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察,其中包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团、桑志华和德日进组成的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以及瑞典人斯文赫定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的西北考察团。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1929年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这些本土的科研机构也在积极地组织和推进全国范围的实地考察。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俨然成为一个各国科学家围绕人类起源以及黄土研究问题展开竞争的国际化竞技场。泥河湾地质遗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发现的,其中不乏矛盾纷争。由于几位当事人的刻意低调处理,一直以来,人们对该地点的发现经过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在一些重要信息上产生误解。如今,通过对大量原始书信、档案的细致爬梳,我们终于得以更为完整清晰地认识并还原这段面貌模糊的历史。从牛顿和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发明权之争,到华莱士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论学说的优先权事件,科学史上不乏优先权之争的例子,桑志华与巴尔博对泥河湾研究的优先权之争为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中国地质学发展初期充满活力和竞争的国际化面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致 谢 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承蒙法国巴黎耶稣会档案馆Robert Bonfils神父、Barbara Baudry女士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Kevin Grace先生提供帮助,杜鼎克(Ad Dudink)博士提供了樊尚神父的相关信息,谨致谢忱。
附录1

泥河湾地质遗址早期考察研究大事系年(1921~1930)

续表
1 袁宝印,夏正楷,牛平山. 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2.
2 Barbour G B.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in the Kalgan Area[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4,3(2):153~168.
3 Barbour G B.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valley[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5,4(1):53~55.
4 Teilhard de Chardin P.Palaeontological Notes[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6,5(1):57~59.
5 Barbour G B,Teilhard de Chardin P,Licent E.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Basin[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6,5(3~4):263~278.
6 Barbour G B.Note on Correlation of Physiographic Stages[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6,5(3~4):279~280.
7 Teilhard de Chardin P, Piveteau J.Les Mammifères Fossiles de Nihowan(Chine)[J].AnnalesdePaléontologie,1930,19:1~132.
8 Licent E.VoyageauxTerrassesdeSangkanho,l′entréedelaplainedeSininghien[M].Sienhien: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Tcheu Ly S.E., 1924.
9 Licent E.Onzeannées(1923-1933)deséjouretd′explorationdanslebassinduFleuveJaune,duPaihoetdesautrestri-butairesduGolfeduPeiTcheuLy[M].Tientsin: Mission de Sienhien, 1935.
10 松藤和人. 探访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J]. 胡金华,译.文物春秋,2001,61(5):62~74.
11 夏正楷. 泥河湾层的研究现状和展望[J]. 第四纪研究,2001,21(3):262~269.
12 卫奇,黄卫龙. 泥河湾盆地的科学开拓者[J]. 化石,2009,(4):28~33.
13 Vincent E. Une paroisse chinoise Ni-ho-ouan[J].LeBulletinCatholiquedePékin, 1914, 1(3): 69~ 72.
14 Vincent E. La paroisse de Ni-ho-ouan[J].LeBulletinCatholiquedePékin, 1917, 4(48): 297~303.
15 Barbour G B.InChinaWhen...[M].Cincinnati:University of Cincinnati,1975.
16 Bernard H.Une méthode d’exploration scientifique:Le P.Licent dans la Chine du Nord et la collaboration des missionnaires[J].LeBulletinCatholiquedePékin,1925, 12(145):443~454,1926,13(146):17~23.
17 戴丽娟.在“边缘”建立“中心”——法国耶稣会士桑志华与天津北疆博物院[J].辅仁历史学报,2009,(24):231~256.
18 燕京研究院. 燕京大学人物志[M].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2~145.
19 巴尔博. 张家口附近地质志[J].侯德封,译. 地质专报,1929,甲种(6):1~25.
20 Sun Y C.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held in Peking,January 5,6 and 7,1924[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4,3(1):1~19.
21 Sun Y C.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held in Peking,January 3,4 and 5,1925[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5,4(1):1~14.
22 Hsieh C Y.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held in Peking,January 6,7 and 8, 1923[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3,2(1~2): 1~16.
23 Membership,1922[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2,1(1~4):97~99.
24 Licent E.Dixannées(1914-1923)danslebassinduFleuveJauneetautrestributairesduGolfeduPeiTcheuLy[M].Tientsin:La Librairie Française,1924.
25 Wong W H.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General Meeting, June 15th 1923[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3,2(3~4):1~4.
26 List of New Members[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4,3(1): 89.
27 Wong W H.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general meeting held in Peking, July 25th and 26th,1924[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1924,3(3~4): 193~194.
28 Barbour G B.IntheFieldwithTeilharddeChardin[M].Cincinnati:University Publications,University of Cincinnati,1975.
29 Teilhard de Chardin P.TeilharddeChardinenChine,correspondanceinédite[1923~1940][M]. Aix-en-Provence:Edisud,2004.
30 Cuénot C.Le Révérend Père Emile Licent S.J.[J].BulletindelaSociétédesétudesindochinoises,1966,41(1):9~83.
31 Licent E.Douzeannéesd′explorationdanslenorddelaChine,enMongolieetauTibet(1914-1925) [M]. Publications du Musée Hoangho Paiho No C.Tientsin: Musée Hoangho Paiho, 1926. 4.
32 Cuénot C.PierreTeilharddeChardin,lesgrandesétapesdesonévolution[M]. 2eédition. Monarco:Le Rocher,1986.
33 Correspondent.Prehistoric Bones of China: Remnants of Strange Monsters Found by Scientists in Valley Near Kalgan[N].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1925- 05- 09: 226.
34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nual Meeting held at Peking, February 12~14, 1927[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27, 6 (1): 1~7.
35 邱占祥. 桑志华和他的哺乳动物化石藏品——试谈桑志华藏品中哺乳动物化石的历史及现实意义[C]//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90(1914-2004)周年文集.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6~10.
36 邱占祥. 桑志华与中国的古哺乳动物学[C]//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44~46.
The Discovery of the Nihewan Geological Site: A Case Study of the Priority Conflict in Nihewan Research between E. Licent and G. B. Barbour
CHEN Mi1,2,3, HAN Qi3
(1.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Beijing100091,China; 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3.InstitutefortheHistoryofNaturalSciences,CAS,Beijing100190,China)
Nihewan Formation,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as the standard sequence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in north China, occupies a major place in Quaternary science and paleolithic research in China. E. Licent (1876-1952), G.B.Barbour (1890-1977) and P.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were the three pioneer geologists who carried out the earliest reconnaissances and investigations at the Nihewan geological site.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newly found letters, diaries and some publications, this essay reviews some ke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Nihewan research, such as the process of the discovery of this important site, and analys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iority conflict between Licent and Barbour. It examines also the role played by Father E. Vincent, who provided the first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laeontological site in Nihewan village.
Nihewan, E. Licent, G. B. Barbour, Priority, Quaternary geology
陈蜜,女,1982年生,福建福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国地质学史;韩琦,1963年生,浙江嵊州人,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科学史,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和清末民初地质学史。
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项目编号:KZZD-EW-TZ- 01)
N092∶P5- 092
A
1000- 0224(2016)03- 0320- 21
2016- 06- 20;
2016- 08-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