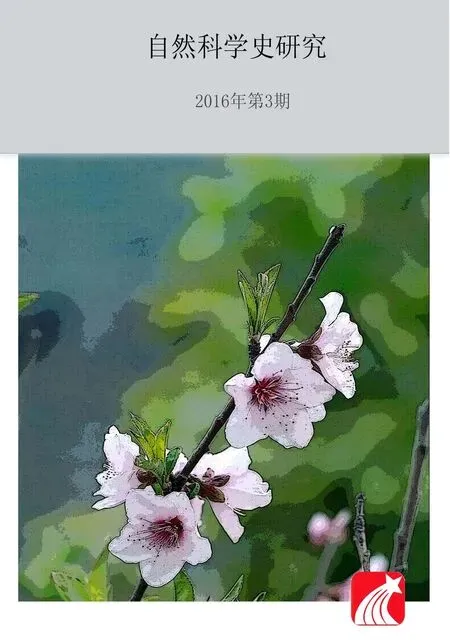“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
吴 燕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呼和浩特 010022)
“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
吴 燕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呼和浩特 010022)
以西历取代中国原有的阴阳合历,此举发生在近代化背景之下,是民国时期政府参照或依据西方科学在中国社会完成的一次对时间秩序的重构。西历相比于旧历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社会建构。在废除旧历运动中,西历被定为“国历”,而旧历则被称为“废历”;同时,在当时以“革命”与“进步”为线索的社会情境之下,“废历”还被附载了不属于它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与“废历”成为一体,从而实现对旧历的污名化。
废除旧历运动 国历 废历 社会建构
民国时期改用阳历一事,已有左玉河[1- 4]、湛晓白[5- 7]、许冠亭[8]、刘力[9]、吕文浩[10]、方潇[11]等多位学者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首先,尽管研究者大多注意或提到“废历”一词,但有关这一概念的形成与传播尚未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其次,在此前的研究中,有观点认为,“民国初年改用阳历,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识,也是革故鼎新、万象更新之明举”([1],66~67页;[2],222页),并有研究注意到“所谓阳历的科学性及旧历的封建迷信色彩,仅仅是一种铺垫和充分理由,‘改正朔’的政治寓意及取得政府的合法性,是国民政府发起废除旧历运动的根本所在”[5],但“改用阳历”的“社会进步”性并不可一概而论,同时“阳历的科学性及旧历的封建迷信色彩”是如何建构的,此中也仍有较多细节值得深入讨论。再次,此前的研究对官方推行西历①即格里高利历,下同。本文引文中提到的“阳历”也指格里高利历。与社会各界的反应都已做出详尽研究,但在官方与社会民众之间尚有一个“中间地带”,即报刊杂志,尽管在此前的研究中也有提及,但并未做出专门研究。民国时期是近代报刊在中国发展的成熟时期,一方面报刊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方式与程度在推行阳历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它们构成了当时社会的舆论环境。因此,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着眼于民国时期的报刊,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舆论空间中“废历”一词从提出到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意味演变,以此探究西历相比于中国原有的阴阳合历*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采用的是阴阳合历,即在编历时同时考虑回归年和朔望月的运动周期,而非通常被认为的“阴历”。民国时期,中国原有历法一度被称为“阴历”、“旧历”、“废历”等。几种称法中,“阴历”的称法并不符合实际;“废历”的称法则带有较为明显的褒贬意味,而本文所要分析讨论的恰恰是这个称法以及其所包含的意义,因此如果在分析时也使用这个词也是不合适的。有鉴于此,本文姑且借用“旧历”一词来指代中国原有的阴阳合历。更“进步”、更“科学”的形象是如何在当时的氛围下建构出来的。
1 背 景
前人的研究已对中国推行西历的过程做出了非常细致的梳理,这里首先根据已有研究对这一线索稍做概括以做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尽管中国正式推行西历开始于民国时期,但这种呼声早已有之。例如在1909年,《申报》即曾发表文章谈及“西历”时称“现在地球各国多用之,即我国将来恐亦不免改用阳历。盖大势所趋,而非人力所能强制者也”。[12]1910年即有资政院议员易宗夔、姚大荣提出改用阳历议案;1911年,新成立的军咨府有意推动改用阳历,资政院更于这一年3月再次向清廷提出改历。([5],39~40页)但官方正式推行西历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完成的。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宣誓就职当日同时颁布“改用阳历令”,宣布中华民国采用世界通行的西历,即格里高利历。此后,除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期间曾一度短暂地恢复旧历外,官方都一直致力于推行西历。([5],42页)正如左玉河的研究注意到的,在此过程中,旧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民众除民国纪年外,对西历并未完全接受,从而形成了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上层社会——政府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报馆等,基本上采用西历;而下层民众——广大的农民、城市商民等,则仍沿用旧历。[2]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即行“废除旧历、推行国历”运动,此时,正如国民政府所观察到的,在改用阳历17年后,“对于国历,除官厅照例表示遵行外,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13]。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8年5月7日提交给国民政府的提案中拟定了“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八条办法,“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13],425~426页)。废除旧历运动自此拉开帷幕,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西历则被官方正式确立为“国历”。
历法是判别节气、记载时日、确定时间计算标准等的方法。它的普遍内容是说明每月的日数怎样分配,一年中月的安排和闰月、闰日等的安插规则,节气的安排,等等。[14]西历是一种太阳历,一年12个月的“月”与朔望月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人为创造的计时单位。而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使用阴阳历,它兼顾回归年和朔望月两个周期,使每个月符合月亮盈亏的变化,每年符合春夏秋冬的变化,而由于地球绕日公转的运动(年)、地球自转(日)以及月球绕地球公转(月)这三种运动是互相独立的,并不存在简单的倍数关系,因此,编制阴阳历事实上比编制阳历和阴历都更为复杂。[15]中国传统历法中尤其重视日月五星运行的推算,而它们也是验证历法准确性的一个重要手段。[14]由此可见,一方面历法作为一种推算历的方法,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并与之相适,是一种具有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因此并不适宜以一种相同标准评判高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历法的上述特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传统历法的编算工作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而西历则是一种历谱,以月份安排为主。如果一定要加以比较,即使就科学性来说,中国传统历法也并不弱于西历。
从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当时的知识界人士对两种历法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在三个层面:
(1)两种历法各有优劣。在论及西历优于旧历的观点中,较少涉及历法本身编订的精确性问题,即使在行文中会出现诸如“科学”、“精确”这样的描述和评价,但它与判断历法本身是否“科学”、“精确”其实非指同一个意思,后者主要指一部历法是否较好地反映了日月五星的运行,而前者更多地是指一种社会时间管理是否高效。
以竺可桢的文章为例,其对西历的优势概括为四点:一是月份“无论平年闰年平均为十二月,且所差不过一日”,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便于进行历年财政、进出口等的比较,从民间来说,工资、房租等都可以按12个月收付;二是阳历二十四节气均有定时,即使逢闰年稍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三是阳历计年较为精确;四是“世界各国均用阳历,我国若用阴历,则独持异议,在今日铁道轮舶交通时代,必致诸多不便”,即与世界各国沟通之必要。[16,17]在当时支持推行西历的人士中,竺氏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18,19]*其他持相似观点的文章还有蔡元培、朱炳海等人的文章。在1930年推行国历演讲大会上的演讲中,蔡元培认为,孙中山之所以采用阳历,一是“为了适合经济制度,如预算等项,他的目的,完全为了民众的利益起见,并不是包含着皇历的意思在内”;二是因为“阳历完全是根据天文学,加以理性方面之研究而产生的,是最合理的办法,并非盲目的学外人”;三是“在全世界各种历法中,择一最合理最科学的历法,以为应用上之便利与准确”。[18]这里也可看到,蔡氏所谓之“科学”也并非指历算上的“科学”,而是社会时间管理意义上的评价。朱炳海则在题为“究竟为什么要改用阳历”的文章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了阳历的好处:(1)计时精密程度;(2)使用的便利性。[19]。
在竺氏所总结的西历的四个优势中,一和四是科学之外的因素,其中一是人为月份划分给社会时间管理带来的便利,四是国际交往的需要;二和三是太阳历本身的特点,也就是说西历本来就是按照太阳周年运动周期来制订的,相比于阴阳合历,不必兼顾月球运动周期,因此比阴阳合历能更好地符合太阳运动周期。
西历作为太阳历的特点也决定了其与中国原有阴阳合历相比所具有的明显劣势,即“阳历之朔望与月之盈亏全无关系”,而潮汐涨落与月之盈亏大有关联,从事船业者可凭阴历月日而预知潮汐,改用阳历后会带来不便。[16,17]
因此,由于西历与中国原有阴阳合历各自的特点而使得二者各有其优势与更为适用的范围,这一点是得到当时学者认同的。尤其是,西历相比于旧历最明显的优势其实在于,它更适合于近代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这并不是一个天文学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这在当时的学者中是有觉察的。
(2)尽管西历相对于旧历更适合近代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但在当时的学者看来,西历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使是像竺可桢这样支持采用西历的知识界人士也认为,“虽阳历较优于阴历,而阳历自身亦不无可訾议之处”[16]。西历虽较之旧历稍有优势,但其本身也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在有关西历的缺点问题上,天文学家高均(平子)的分析是具有代表性的。高均在追溯了西历的历史基础上,认为这部改定于1582年的历法“可谓世界上甚旧之历”,“其法于岁实之长,在四千年中不差一日,此点可称美备”。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是“苟合当时政教流传习惯,并无改革之彻底精神”,二是“年月日周之支配,支离疏漏,既乖论理,又不合用。如年之所始,既过冬至,更非春分,不值月朔,无关日度。月之长短,大者三十一,小者二十八,相□至于三日。”这些缺点还包括置闰法、七日礼拜每年无定期等“彼土所认为于民生日用大不便者”,但“特以西人对于法制,守旧者多,惮于改作,以致千余年来,因循沿用,未之或改”。[20]
这一点在当时的历法编订者中也有相同的认识。《中华民国元年历书》中附有“介绍普天万国始终不变之通历”一文,其中写道:“废旧历易正朔,本世界大同便民利用之意,采用阳历,全国耳目为之一新。而孰知吾国所视为最新者,彼西人已习而为旧矣。法有星学名家佛那马海员先生者,高揭改良阳历之旗已不下三十载,而巴黎博士会之采用通历也亦已二十有余年。由此观之,西人之不满足于阳历久矣。”[21]
基于对已有历法缺陷的认识,民间改历运动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有关民国改历运动的研究,可见文献[7]。。竺可桢、刘永贞、高梦旦、钱理、王亢元、虞和寅、王兆埙、赖信、高均、钱宝琮等人均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改历思路,而中国天文学会在当时也曾多次开会对这些方案进行讨论。陈遵妫则对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改历案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分析,在共计38个改历案中,置闰法改良案9个,年始变更案3个,配日法改良案3个,闰周案5个,除日案14个,废周案4个。[22]
由此可见,天文学界对于西历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着明确的认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存在于西历中的问题大多涉及天文历算本身。
(3)当时的科学界,尤其是天文学界已经意识到,改历并不只是历算问题,而一种历法之被采纳,其原因与影响也远在科学之外。例如在1929年3月22日举行的关于钱宝琮的沈括历法讨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天文学家高均就曾提出“将来扩大的历法讨论委员会……不但不由天文学会,且并不由天文研究所召集,索性由中央研究院召集。因今后之改历,与以前之改历情形不同;以前所改者仅为用数及算法之属。今后所改者,为年月日纪法上之定义,故所召集之人应不限于天文学家历学家,并须兼有研究社会暨民俗等学者”。高均的意见得到了当时与会的高鲁的认同。对于各种改历方案,尽管当时的中国天文学会多经讨论而未达成共识,但“惟有一点为同人一致赞同者,即改历事关政教习惯,须由国家召集全国热心研究历法之学者,组织大规模之委员会,详加讨论后,再行决定采用何种”。[23]
综上所述,如果从天文历算的角度来说,西历相比于旧历的“科学性”与“进步性”是值得推敲的;二者相比,西历的优势更多地是体现在它更适合近代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生活及国际交往,因为当时处于强势文化的西方大多采用了西历计日。
民国改历并非独立事件。在当时的亚洲,日本、朝鲜先于中国于1873年和1895年相继宣布改用西历。作为亚洲最早近代化的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于1873年1月1日(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正式以西历计历,并将这一天改称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即著名的明治改历。此次改历被认为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标志之一,也是日本“时间”近代化的开端。[24]
因此,民国改历其实是在近代化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时间秩序的重构,是近代西方时间秩序及其所体现的西方时间意识在地域上的扩张的组成部分。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一时间秩序的重构意味是双重的。首先,民国南北诸府建政之初,亟待重建一种新的时间秩序——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正朔观是相通的,藉以与旧时代进行切割。其次是接受一种世界通行的时间秩序,将中国的时间“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3];同时也以此行为表明“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全面开启中国社会近代化之意愿。
因此,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组成部分,以西历取代旧历这一行为本身也成为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西历相比于旧历的“科学性”与“进步性”的形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社会建构,“废历”*在当时的出版物中,“废历”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废除旧历”之简称;二是“废弃不用的阴阳合历”。本文所研究之“废历”系指第二种用法,即名词性的“废历”。一词从形成到在社会生活中大范围使用,再到这一概念的演变,为考察这种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样本。
2 “废历”一词的提出及官方认可
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可以看到,西历与旧历的称谓分别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前者一度被称为“阳历”、“新历”、“国历”,后者则相继被称为“阴历”、“旧历”、“废历”。其中,“阳历”与“阴历”*如前所述,中国的历法一直是阴阳历,即同时考虑回归年和朔望月进行编算,并不是纯粹的“阴历”,因此这一称谓其实是有问题的。是根据历法推算方法所做的分类,“新历”和“旧历”可以理解为对于采用时间先后的描述,与此相比,“国历”与“废历”的说法则带有较为明显的褒贬意味,这在“废历”之说法甫一出现即已显现出来,并在后来逐渐得到了强化。
此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阳历定为‘国历’,将阴历(旧历)视为‘废历’,并‘特制国民历颁行各省,凡属国民,均应遵守’”([4],1170~1171页)。不过,“废历”之说法并非始于南京国民政府,而是首先由知识界人士提出并使用,后得到官方确认。
1923年,《责任》杂志发表署名“大白”的文章《实行国历问题》。该文以“废历”指称“已废的阴阳合历”[25],从而在“废历”与旧历之间划上了等号。同年,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署名“仲雍”(即顾仲雍)的文章《学校放寒假的我见》中,作者也使用了“废历”一词。该文的立场更为激进,其中陈述的两个首要观点,一是社会沿用废历,实是中华民国的叛贼;二是学校放寒假,实有沿用废历的嫌疑[26]。
1928年,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在呈送中华民国大学院的一份报告中草拟了“实行国历禁止沿用废历办法草案”。蒋梦麟呈文到院后,大学院批交中研院天文所核议。当时的天文所主任高鲁签注之审查意见第一条即对“国历”一词提出异议云:“国历之名称,不甚恰当。国历似系本国独有之历法。不如用国民历,则可以国民政府所采用之历解释之。”([23],22~24页)不过从“国历”与“废历”在后来的使用来看,高鲁的理解显得有些书生气了。
在官方层面,“废历”一词的使用则要稍迟一些,甚至在废除旧历运动之初也还尚未被官方正式采用,一直到1929年才开始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先是在少数通令中零星使用,例如1929年7月20日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的“内政部训令:令首都公安局、各省民政厅:关于各书局附印废历于国历一事仰即转饬所属于十九年起不得再为附印务须遵照由(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在这份内政部训令的正文中可以看到,中国原有的阴阳合历仍被称作“旧历”,而“废历”一词是出现在“目录”中的。[27]另一例是《行政院公报》第102期中发布的“训令第四零七七号(1929年11月18日)”,关于查处一起“将废历揭载于国历之下”,“公然将废历与国历并列”事件的通报。[28]
1930年7月18日,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行政院函件中抄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推行国历办法”*该件于1930年6月26日经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8次常务会议通过([29],435页)。中将原有的阴阳历称为“废历”[29]。此后,“废历”一词不仅在官方文件中,也在公共空间中全面推开,尽管此间“旧历”一词也仍有沿用,但两相比较已呈明显弱势。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废历”一词自被提出起就已经包含有两重意味:一是字面本身的意思,即“废弃不用的阴阳合历”的简称;另一重意味则来自它与“国历”的二元对峙。尽管在当时的报刊上,有关两种历法的称谓经常混用,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废历”一词自被文化界、知识界提出之时,便是与“国历”放在一起使用,即与“国历”处于二元对峙状态;而且这种用法此后一直延续,从而使得这种二元对峙状态也因此得以延续。
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其宣传策略中也尽力突显这种二元对峙。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实行国历宣传大纲》,对实行“国历”的原因及意义做出解说。这份“宣传大纲”最后附有15条“实行国历的宣传标语”,其中之一便是“沿用旧历,就是奉行满清的正朔,也就是民国的叛徒”[30]。尽管在此时,国民政府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尚未采用“废历”一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说法其实可以看作上述顾仲雍“社会沿用废历,实是中华民国的叛贼”之说法的延续,或者说是对这种已经在舆论空间形成的观念的官方认可与强化。而到几年后“废历”一词正式进入官方文件之时,这种体现在历法中的国家意志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废历”与“国历”二元对峙的一个旁证是历书中对旧历的处理方式。
自民国元年[31]*编制历书应提前开始进行推算,但中央观象台接到任务时已是民国元年5月。因此中央观象台最早以格里高利历推算的历书为《中华民国二年历书》,在《二年历书》付印后才开始补编《元年历书》([31],84页)。开始,历书开始采用西历推算,但印制时也仍保留了旧历,原因是“民国采用阳历,则旧历自在应删之列,惟习俗相沿未可以朝夕废,故旧历月日仍附注于阳历月日之下,以从民便”[32]。但到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8年5月7日提交给国民政府的提案中拟定了“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八条办法中明确要求,“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月份牌及附印旧历之皂神画片等”([13],425页)。1929年,行政院公布对两起私自印售附载有旧历的历书事件的处理时这样写道:
乃查上海国粹一局,竟印售二百年阴阳历对照全书,藉资牟利,又有未标明发行书局之“民众日用百年国历便览”一书,内容系将废历揭载于国历之下,而诡称为便利国民检查以前之废历,希图避免查禁,用心狡猾,殊为可恶。此两种历书,一则公然将废历与国历并列,一则暗示人以阴历之可查,均系为废历作留传之资料,实属有碍国历之推行,亟应严行查禁,以重国历。[28]
从官授历书附注旧历“以从民便”,到以“公然将废历与国历并列”为由对书商做出处罚,无论是查禁废历的行为本身,还是行政院所发布的训令,都是具有规训意味的,而在“国历”作为唯一合法的时间制度的地位得到强化的同时,处于对峙另一方的“废历”也从“废弃不用的”逐渐演变成为“不被官方承认的”、“被查禁的”形象。
3 社会情境中的“废历”形象分析
1931年的《时事月报》曾刊出一张漫画,题为“废历的前途”(图1)。画面中,一名肢体残缺的残疾者正拄着双拐走向一间“残废收容所”,人物背后写着两个大字:废历。[33]按照国民政府内政部1928年制定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当时,“残废所”的救济条件是“凡残废人无人抚养者不问男女老幼均得收养于本所”[34],即应具备“残废”且“无人抚养”两个条件方可进入“残废所”。因此,漫画之构思很可能意喻了“废历”遭人摒弃、无人问津的处境,而形单影只的人物、残缺不全的身体与破败的收容所景象无一不在暗示废历黯淡的前景。该漫画为转载之作(但该刊并未注明转自何处),而转载该作的《时事月报》,当时的社长为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因此具有官方媒体性质。由此也可以判断,这一转载行为本身也意味着对该作品意味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者说官方也乐于通过此种形式来营造一种氛围。

图1 漫画《废历的前途》(引自《时事月报》,第4卷第1期,1931年)
自20世纪30年代起,“废历”一词越来越广泛地在报刊文章中被使用,这些文章包括政论、科普、随笔乃至文艺作品。“废历”形象的进一步演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的。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为这一建构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社会情境。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随着过去数十年西方科学与文化陆续进入中国,对近代化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思想线索之一。自20世纪初年帝制的倾覆,到20世纪20年代北伐成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革命”与“进步”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叙事线索。在这一背景下,处于“革命”与“进步”对立面的“守旧”观念与行为以及亟待革除的社会陋习因此成为这一叙事线索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但无论是“守旧”观念与行为还是社会陋习,都有必要附载于某些具体的事物之上,才能使得表达言之有物。
至此,“废历”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政府希图对民众进行的教化与民众对政府的作为以及社会问题的不满都可以藉由对“废历”的批判而得以表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废历”也就被赋予了原本并不属于它的文化象征意味。
3.1 作为“革命不彻底”的一种表现
作为对民众习惯的妥协之策,1930年6月26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八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推行国历办法》第一条即规定“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29],435页)。时评《废历不废》正以此展开讨论,作者对移置新年的做法并不认同,认为:
既要废除,就应该废除个彻底。譬如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目的在推倒清廷,但是打倒了宣统并不能就说是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进一步,必须把清政府的一切政制及其他含有封建意味的附属品都全盘推翻才行,不如此便不得谓之革命。当局要废止阴历,自然是件值得称赞的事,然而要废止,就得从根本做起,阴历固然从此不得再用,关于阴历过年时的许多无意识的举动,也应该连带地一扫而光。但是,事实竟不然。当局的目的只要从阴历搬到国历便为满足,好像宣统虽然跑了,后来的大总统们的民主政府仍不妨袭用宣统的老套。[35]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反复使用譬喻的手法,首先将称旧历为“废历”的做法比做在1911年革命之后“称宣统曰‘废帝’”,而“如果我们现在称宣统曰‘废帝’当局一定要说我们太不革命了”,从而对政府仅仅给旧历一个“废历”的称呼但将废历新年移置国历新年的做法提出质疑,即认为“废历”只不过“名义上是废止了,实际上却还是存在着”;随后,作者进一步将“废历”视为“清政府的含有封建意味的附属品”,如同被推翻的宣统的道统,因此,政府提出将废历新年移置国历新年的做法,不过是将这一前朝的含有封建意味的附属品改头换面继续沿用,如同继续袭用宣统的道统。由此可见,尽管作者通篇都是在评论“废历不废”,但它在这里更多是作为“革命不彻底”的其中一种表现,而“革命不彻底”才是文章批评的最终指向。
《废历新年在上海》一文描述了作为大城市的上海春节时的热闹景象,进而评论道:“废历新年,照理讲,上海应比其他各地冷淡些才对,上海到底比中国其他各地要近代化些,对于废历新年旧习惯的保守性,应该是很稀薄才说得过去。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上海就是在保守方面也做了全国的领袖了”。在这里,“上海”是作为“现代大都市”的形象出现的,在作者寄望中,这个“现代大都市”本应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比中国其他地方走得更远,但现实却是在除夕夜“一夜被鞭爆锣鼓之声弄得不能安眠”,而影院也制作了相当于今天的贺岁片的电影。面对这种现代的形象与沿用旧俗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作者批评道:“‘摩登’,在今日中国的解释并不是纯粹的现代化,只是皮毛的所谓‘时髦’”。[36]由此,作者在这里所批判的仍然是革命及近代化的流于表面,上海照过“废历”新年则是其中一个表现。
3.2 作为社会陋习的一种载体
与“革命”主题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部分,对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与对社会陋习的批判在民国时期的大众传媒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当论及这一主题时,“废历”往往是作为社会陋习的载体而被提到的。
在《从废历新年赌的狂热想到禁赌运动》一文中,作者评论说:“在废历新年中,赌风之盛,已成普遍的现象……在现在训政开始,建设方殷,这种障碍社会进化的赌风,若不及时取缔,的确是革命社会的污点,人类生活上的危险品”[37]。而在《废历春节的罪恶》中,在历数赌博、嫖娼等恶习之后,作者将原因归结到“废历”春节,认为“只因春节太闲在,就闹得无法无天。好人参在歹人堆里。变坏再快没有,一滑脚就堕落了。社会上无形中增加许多犯人。这不都是废历春节所赐么。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罪恶假汝以行。我则套着她的口吻说,春节春节,罪恶假汝以行”[38]。
在《废历新年志俗》一文中,身为一个小职员的作者抱怨“废历”新年不得不送礼应酬,徒增开销,“在低薪阶级的人,要抽出生活费为人凑热闹,以取得别人欢心!像这种恶习,太普遍了,实在要废除才好”。同时,作者更看到这种陋习背后的驱动力是商业利益,即“商人们为着生意兴隆,做了不少的年货,引起太太为废历而奋斗,所以在旧历年送礼,请客之酒特别盛行”[39]。刊载该文的《新运导报》系由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办,1937年正值“新生活运动”三周年之际。这篇文章所在的1937年第3期系“各地三周年纪念特辑”,主要内容包括:《蒋会长三周年纪念训词》、《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感想》(钱大钧)、《我们对新运应有的认识和实践》(陈仪)等专论文章以及“三周年纪念讲演录”、“新运消息”等专题。而上文引述的《废历新年志俗》与另一篇《废年谈旧录》系这一期刊物中“文艺”栏目下的两篇文章。尽管两篇文章并未放入专门的新运专题,但从全刊布局可见,这种编辑思路其实是将对“废历”以及附载于“废历”新年之上的陋习的批判置于整个新生活运动“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40]的氛围之中。
与这些媒体文章相呼应的是,民国时期各地民众教育活动也往往会利用“废历”新年举行讲演或其他礼俗改良活动。例如当时某些学校在春节期间举行的面向民众的通俗讲演活动,讲演内容大同小异。以福建连城第一民校为例,1936年的通俗讲演内容依次为:(1)为什么要废除阴历;(2)实行国历的好处;(3)不应该吃鸦片和赌博;(4)为什么要破除迷信;(5)怎样才是良好的娱乐;(6)怎样做个好人。[41]
此类活动的意味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加以解读:一是讲演内容设置上所具有的暗示意味,即坚持使用“废历”是与鸦片、赌博、迷信等并列的,是与当局所倡导的“良好的娱乐”以及“做个好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二是选择在“废历”新年举行此类活动则表明了活动组织者是希望以此种“良好的娱乐”方式,启发民智,并取代在“废历”新年的种种陋习。当时一份有关此类活动的报告正好为上述二重意味的解读提供了佐证,该报告称“民众在废历新年中的一举一动,没有一件不充满了迷信与附会,浪费金钱,数固可观,而对于民众迷信依赖心理的养成,有害更大,所以这种阳奉阴违的情形,在抗战已到第五个年头的今天,我们认为是非予切实改正不可”。因此,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这家民众教育馆在是年“废历的年首年尾……特地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礼俗改良运动,想以宣传娱乐等方式,以达到改革民众不良习俗与不良消遣,以及推行合理风尚等目的”。[42]
3.3 作为一种有必要被摒弃的生活方式
在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中,新式家庭与新女性被赋予的其中一种角色就是这一生活方式的载体与体现者。因此,在有关新式家庭与新女性的文章中,“废历”有时也会被借用来指代一种有必要被摒弃的生活方式。
《去吧,跟着废历》一文发表于1931年。文章中,作者首先叙述了自己在某银行取款时受到一名女性柜员态度恶劣的对待,而在对职员道德以及“作为国际贸易场的上海”仿效国外而雇用女性职员事做出评论后,作者写道:“对于这样的宝贝,我们可以说:‘去吧!跟着废历!’”[43]在这里,作者借用“废历”一词中所包含的“被废弃的”之意,暗讽这名获得了职业机会却不肯恪守员工本分的女柜员也应当被淘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虽未进一步展开但已隐含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现代文明生活中职业女性的教养问题。
在《女学生模范日记》里的一段“日记”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性教养问题得到了呈现。在这篇“日记”中,作者记述了自己在废历新年外出时的所见所闻,“我家是个新式家庭,所以对废历新年并不举行庆贺”,而在结束了这一天的游玩之后,作者想到:
阳历比阴历进步得多,世界各文明国家莫不采用,我国也早已明令采用。我们以后应该积极推行阳历。不过废历新年里有些风俗,像祭祖等,是未可厚非的,理应加以提倡。依我的意见,大可把这种好风俗,移用到阳历新年。至于一切迷信的以及耗费金钱的无聊举动,准可以一并革除![44]
“学生模范日记”是当时为学生所编的一种作文范本,除了给学生示范日记的写作之外,具体文本也尤其注重对学生日常行为的养成。这册《女学生模范日记》尤其针对女学生所编,它与普通学生模范日记不同之处在于,“女学生需要的日记范本,所取的资料,必须着重于治理家政的诀巧;虽然我们并不要在这新时代里把活泼的女学生们造成贤母良妻的典型,但每一个女子,应该懂得一些治理家政的常识,实在是必要的”。至于鲍维湘所编的这部《女学生模范日记》,则被认为“运用清新流利的笔法,在日记里随时灌输女子应具的知识……意识正确,而且富有兴味”。[45]由是观之,此书的主要意图是对女学生进行女性社会角色的教化,而写入“日记”的内容则是作者认为一名受过教育的女性所应具备的教养。
在这种意义上再来看上面引述的这一段“日记”,其意味是层层递进的:首先,新式家庭不过“废历”新年,相应地,新式家庭也同样拒绝“废历”;其次,被“世界各文明国家”所采用的西历比“废历”“进步”,因此,使用西历也体现了一种“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再次,原来依附于“废历”新年的某些风俗(比如祭祖)仍是值得提倡的,因此在摒弃“废历”的同时,保留这些好的风俗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其移至西历新年来进行。由此可以看到,作者所提倡的现代女性教养可以归结为既保留某些传统风俗,同时又对这些传统风俗所依附的“废历”加以摒弃,而采用更为“进步”的西历。相比于前面视“废历”为一种社会陋习的载体的看法而言,这里对待“废历”的态度也更进了一步,即把“废历”本身视作一种应当摒弃的生活方式。
4 结 论
民国时期对西历的推行是政府在近代化背景下以西方时间秩序在中国进行的一次时间秩序重构,这是当时重建国内秩序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加入国际秩序与对话的需要。西历相比于旧历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社会建构,“废历”一词从提出到被官方认可再到后来的意味演变就是一个考察样本*由于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诸如“国历”、“废历”等话题也出现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这些文艺作品以戏谑的方式消解了推行西历一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种对权威性与严肃性的消解在推行西历之初即已开始出现,这也成为为旧历所做的间接辩护。对于这些反对以及辩护的声音,笔者将以专文做出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建构在两条线索上几乎同时展开:一方面,“废历”一词在由当时激进知识分子提出之后数年即得到官方认可而被写入正式文件,通过给某一事物加上一个不好的标签,从而使人们不检查证据就拒绝和谴责之,这一做法在传播学上被称为“辱骂法”(name calling)[46],是一种最为直接的宣传技巧。同时,在使用“废历”一词时,使用者更有意识地始终使其与“国历”处于二元对峙状态,从而也加深了这一宣传效果。另一方面则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为“废历”附载某些不属于它的内容,从而实现对“废历”所指称的旧历的污名化。在第一条线索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在第二条线索中,官方的角色主要是通过组织一些公众宣传活动来得到体现的,而一些非官方力量,例如激进人士、主张社会改良人士等参与了这种社会建构,并成为主要力量,但这一行为并不总是有意为之。
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构成了“废历”形象建构所需要的文化氛围与资源。西历,作为被世界大多数“文明国家”普遍采用的历法顺理成章地成为文明生活方式的体现,是“革命”与“进步”的。在这种社会情境下,“废历”的角色其实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解读:一是“废历”的象征意味——“革命不彻底”的一种表现方式;二是将“废历”视作守旧观念、社会陋习等的载体;三是直接将“废历”本身视为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生活方式。此三重意味之间存在一种递进的关系,后一重意味均可视为是对前一重意味的延伸。
无论是作为“革命不彻底”的一种表现方式,还是作为“守旧”与社会陋习的载体,抑或是作为文明生活方式对立面的体现,“废历”之被选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它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在面向民众的传播中也更容易理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被取代了的“正朔”,它代表了有必要革除的旧秩序。
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陈年陋习其实并非“废历”新年所独有;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废历”以及“废历”新年,这些陋习也仍然可能延续。因此,将“废历”视为这些陋习的载体之做法本身是有必要商榷的。至于将“废历”本身即视为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生活方式,这一做法其实是受到当时社会情境的影响,而非理性的判断。吕文浩曾对俞平伯、邹韬奋等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废除旧历有关的文章做出分析,并注意到“他们的旧历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痛恨依附在旧历书上的迷信,将旧历法和依附其间的迷信内容看做一体以后,自然对废除旧历大唱赞歌,而对采用阳历加以竭诚拥护了”([10],487页)。由“痛恨依附在旧历书上的迷信”到“将旧历法和依附其间的迷信内容看做一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尤其在当时“革命”与“进步”成为主要叙事线索并反思进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氛围之下,要将此二者截然分开并不容易。
“废历”形象建构看来产生了某些效果。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从当时出版的一些校刊可以看到,对“废历”的这种认识也出现在中小学生的作文中。比如一个小学生因为家中佣人不肯扫掉大年初一的垃圾而认为“这都是贪懒人想出来的办法,以为新年是休息的时间”,因此“废历新年,只是贪懒和迷信的表现”[47]。在另一名小学生的笔下,“如果要提倡新生活运动来救国,那么先要从信用阳历做起!”[48]而在一名中学生的作文里,国家与革命的叙事更是藉由对“废历”的讨论而进入到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国家既然废除废历,提倡新历,为什么大家都不实行新历,反盛行废历呢?这可想而知,中国人是无药可救的,这样小的事,都不能实行,何况大的呢?不能说国家的不是,国家提倡的事,要大家实行,人民非但不听,仍照旧例。照这样看来,中国是不会强盛的,国家的基本,是人民,人民既不服从国家的主张,还能成国家吗?还能富强吗?虽然也有人,实行新历,不过是极少数。我们是受到中等教育的人,我们宣传给无知的人,使他们照国家提倡的,而实行才好”[49]。
一般而言,学生作文未必真是心中所想,而更有可能是对现实世界中的舆论的模仿与借用。将沿用旧历者视为迷信、无知,同时将使用西历视作文明的新式生活,甚至救国之道,这些学生作文中陈述的观点,既是当时意见气候的反映,也参与了“废历”形象的建构。
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语言对事实的建构功能,认为“语言(包括图像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物,而且参与建构事实”[50]。尤其在处理历史文本时,如果不做辨别即加以使用,则可能导致误读。语言对事实的建构功能在“废历”形象建构中也得到体现,本文就是基于这一分析角度而做出的一种尝试。
致 谢 本文曾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2015年夏至论坛与首届科学史大衍论坛(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主办,2015)上报告,得到与会专家的点评与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1 左玉河. 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J]. 民间文化论坛, 2005, (2): 62~68.
2 左玉河. 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J]. 近代史研究, 2002, (3): 222~247.
3 左玉河. 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论南京国民废除旧历运动[C]//刘东. 中国学术. 第21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9~192.
4 左玉河.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C]//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 下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167~1219.
5 湛晓白.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 湛晓白. 民国岁时节令中的政治与民俗——以陈果夫所著《中华民国生活历》为中心[J]. 民俗研究, 2012, (3): 80~86.
7 湛晓白. 科学史和文化史双重检视下的民国改历思潮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3, 32(4): 456~479.
8 许冠亭. 上海市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国历运动[J]. 史学月刊, 2010, (7): 46~50.
9 刘力. 政令与民俗——以民国年间废除阴历为中心的考察[J].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6): 120~125.
10 吕文浩. 知识分子与民国废历运动三题[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9年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81~502.
11 方潇. 革命与承袭:中国传统历法的近代转型[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 (3): 76~87.
12 说日月与地球[N]. 申报,1909- 12- 03: 4.
13 内政部致国民政府呈(1928年5月7日)[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1编文化一.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424.
14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 中国天文学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71.
15 陈久金,杨怡.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93.
16 竺可桢. 改良阳历之商榷[J]. 史地学报, 1922,1(4): 7.
17 竺可桢. 改良阳历之商榷[J]. 科学, 1922,7(6): 525.
18 推行国历演讲大会昨日开始讲演,昨请蔡元培先生演讲[N]. 申报,1930- 12- 29: 3.
19 朱炳海. 究竟为什么要改用阳历[J]. 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1(1~3): 209~216.
20 高均. 改历平议[J]. 中国天文学会会报, 1928, 5(历法专刊): 29~43.
21 介绍普天万国始终不变之通历[M]//教育部观象台. 中华民国元年历书. 1912年石印本.
22 陈遵妫. 改历案之分类及其比较[J]. 中国天文学会会刊, 1928, 5(历法专刊): 44~59.
23 陈展云. 最近一年中国内之改历运动及普及国历运动[J]. 中国天文学会会报, 1928, 5(历法专刊): 1~28.
24 李卓. 日本历法的“脱亚入欧”与“时间”的近代化[C]//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第八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81.
25 大白. 实行国历问题[J]. 责任, 1923, (8): 1.
26 仲雍. 推行国历[N]. 民国日报·觉悟, 1924- 01- 20.
27 赵戴文. 内政部训令:令各省民政厅、首都公安局:关于各书局附印废历于国厅一事仰即转饬所属于十九年起不得再为附印务须遵照由(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日)[J]. 内政部内政公报, 1929, 2(7): 2(目录), 19.
28 行政院训令第四零七七号(1929年11月18日)[J]. 行政院公报,1929, (102): 55~56.
29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行政院函(7月18日)所附“推行国历办法”[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1编文化一.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435~436.
30 实行国历宣传大纲[J]. 中央周报. 1928, (30): 42.
31 陈展云. 中国近代天文事迹[M]. 昆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 84.
32 教育部观象台. 中华民国元年历书·凡例[M]. 1912年石印本.
33 爱魂辑. 一月来之时事社会漫画(三):废历的前途[J]. 时事月报, 1931,4(1).
34 各地方救济院规则(部令第二四二号公布)[J]. 内政公报, 1928,1(2): 26.
35 尼一. 废历不废[J]. 现代社会, 1930, 1(8): 114.
36 允一. 废历新年在上海[J]. 生活学校, 1937, 1(1): 1.
37 王逸清. 从废历新年赌的狂热想到禁赌运动[J]. 节制月刊, 1929,8(2~3): 6~7.
38 呆呆. 废历春节的罪恶[J]. 大亚画报, 1930,(206): 2.
39 王荫槐. 废历新年志俗[J]. 新运导报,1937,(3): 106~108.
40 新生活运动纲要[J].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 1934,1: 12.
41 李正畴. 废历岁首实施社会工作报告[J]. 福建特教通讯, 1936,2(7): 11~13.
42 朱仰曾. 利用废历新年推行礼俗改良运动:浙江省立处州民众教育馆中心活动报告之一[J]. 进修, 1942,4(4): 99~100.
43 白晖. 去吧,跟着废历[J]. 红叶周刊, 1931, (35): 5.
44 鲍维湘. 女学生模范日记[M]. 上海: 上海春明书店, 1941. 77.
45 姚乃麟. 序[M]//鲍维湘. 女学生模范日记. 上海: 上海春明书店, 1941. 2.
46 沃纳·赛佛林, 小詹姆士·坦卡德.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主译, 北京:中国传播大学出版社, 2006. 97~100.
47 刘明德(润文),乐嘉裕(作). 贪懒的废历新年[J]. 民智, 1937, (26): 161.
48 严根良. 废历新年的感想[J]. 敬业附小周刊, 1935, (44~45): 25.
49 范迪锦. 废历新年与国历新年[J]. 英华校刊, 1936, (6): 53.
50 张世明. 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M]//杨念群. 新史学. 第5卷.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101.
“Abolished Calendar” (feili):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in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 and Progress
WU Yan
(Institutefor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ohhot010022,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to replac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can be regarded as a restructuring of time-ordering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xpressions that the Gregorian calendar was more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w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Abolishing the Old Calendar Movement, the Western calendar was called the “National Calendar”,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was called the “Abolished Calendar”, an appellation first proposed by radical intellectuals. At the same time, in certain social discourses oriented around “revolution” and “advancement”, the “Abolished Calendar” was laden with some interpretations which didn’t belong to it, and was integrated with those “bad” images that were used to disparag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Abolishing the Old Calendar Movement, National Calendar, Abolished Calendar, Social Construction
2015- 12- 23;
2016- 05- 02
吴燕,1973年生,北京市人,理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天文学史、科学传播。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计量史”(项目编号:15ZDB030)
N092∶P1- 092
A
1000- 0224(2016)03- 0297- 14